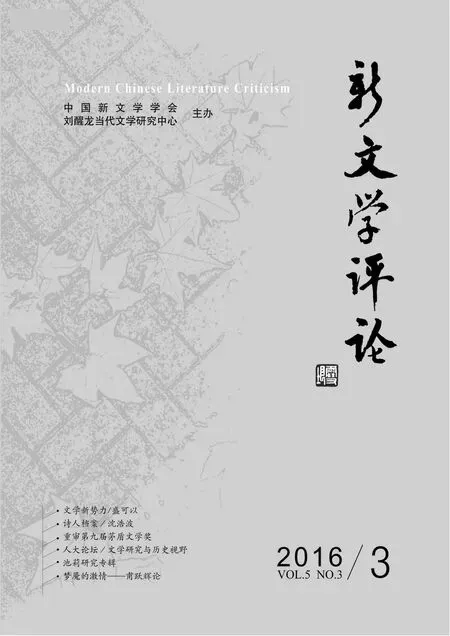飄蕩在“失去”的路上
——盛可以小說論
◆ 佘愛春 朱曉晴
?
飄蕩在“失去”的路上
——盛可以小說論
◆ 佘愛春 朱曉晴
盛可以,上世紀70年代生于湖南益陽,高中還未畢業的她南下打工,輾轉多地,從事過街道宣傳員、證券交易員等多種職業,豐富的底層生活形成她猛烈冷酷的文風和野蠻潑辣的敘事姿態。李敬澤曾評價道:“盛可以的小說有一種粗暴的力量。她幾乎是兇猛地撲向事物的本質,在這個動作中,她省略了一切華麗的細致的表現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變得柔軟的因素,她由此與同時代的寫作劃清了界限,但她也在界限之外獲得了新的力量,那就是,她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現了我們混亂的經驗和黑暗的靈魂。”①這種以潑辣暴烈的文風對“混亂的經驗和黑暗的靈魂”的執著表達,以“銳利如刀的語言”對情感之虛、人性之丑、道德之偽和靈魂之萎的痛切批判,使得盛可以在“70后”作家中顯得與眾不同,成為當下文壇的一個獨特存在。在盛可以筆下,人物常處在“在路上”的無根游離的飄蕩狀態;他們一直是“在路上”,一直在追尋,一直在抗爭,又一直在失去。
一、 失落的鄉土文明
鄉土,曾是陶淵明筆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般的世外桃源;是沈從文《邊城》里雖然閉塞,但是美麗、恬靜、民風淳樸的湘西小鎮;也是莫言《紅高粱》中充滿野性的生命力和淳樸自然的“高密東北鄉”。中國是一個以鄉村(鄉土)社會為主體的國家,鄉土性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就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②可以說,鄉土是扎在我們心田的根,鄉土文明也以其特有的自然生態的和諧美、淳樸溫厚的人性美被很多鄉土小說所盛贊,被視為對現代物質文明物欲泛濫的有力批判。
然而,在當今現代文明侵蝕下的鄉土文明,還能如處子般純凈樸質嗎?或許在盛可以的小說里,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異象。不同于以往鄉土小說中田園牧歌般的鄉村描寫,盛可以筆下的鄉村故事沒有一絲粉飾太平的意思,大部分從開頭就能感受到一股肅殺感,有的甚至帶著濃濃的殺氣。似乎鄉土的溫情和諧、人性人情在她的小說里都是浮于表面,輕輕一揭就能看見表層下暗涌的黑流。正如盛可以在訪談中所說:“殘缺、悲觀、幽暗、稍縱即逝的歡樂,痛苦中隱約的溫情,這些是我表達的,童話般的美好,大團圓,對生活虛偽的贊歌,不是我的習慣。”③因而,在盛可以筆下,鄉村處處隱現的是殘缺與幽暗,麻木與苦痛;“鄉村里的人們只關心兩件事,生存和亂搞,這兩者都是生活的本質,他們只是為這樣的本質而活著”④。
著名宗教理論家保羅·蒂里希指出:“惡魔性是連上帝也可能具有的一種因素。”⑤盛可以對鄉村惡瘤和幽暗的揭露主要通過描寫鄉村兒女們的生活情狀來表現。女性,尤其是鄉村女性,由于物質的貧乏和受教育程度低下,往往不能在物質和精神上實現獨立,在鄉村社會的社會分工中也往往是男人的依附。所以這些女性往往是處在底層的受壓迫者和悲劇的承擔者,而女性的悲劇卻往往是那些男人造成的,像《致命隱情》中魚場廠長劉文化的妻子桂貞。劉文化一直以文化人、夾公文包的體面人自居,卻與前廠長兒子二桿子的老婆胡麗偷情,結果被二桿子發現。倉皇逃跑的他再也顧不上文化人的體面,藏在豬糞池里,結果染上了一身紅斑。染病的他還是礙于面子,沒有積極治療,不久便暴斃身亡。故事表面上看是一場偷情引發的命案,劉文化也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這場悲劇的承擔者難道只是劉文化嗎?他死后,桂貞瘦小的身軀跟在擔架后面,她也只能邊哭喪邊在心里罵道:“豬日的騷堂客,發情的母狗,你害死我的男人,你這一世又何得安樂啊!我高處有老的,腳下有小的,帶噠四個崽何得清白何解活哦!”⑥因為劉文化的自負和淫欲,桂貞守寡,還要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窘境。即使這個男人把自己弄到這般田地,桂貞最終詛咒的還是勾引他男人的“騷堂客”,并埋怨自己沒有照顧好劉文化。由此可見,鄉村婦女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她們的婚姻被包辦,婚后也沒有得到丈夫應有的尊重,像劉文化抱怨桂貞多管閑事,對她吼道:“你栽你的菜喂你的豬煮你的飯!”⑦似乎在他心中,妻子只是這些勞作的代言人,不具備其他的屬性。所以桂貞只能通過努力耕種勞作、與“土地相親”來得到心理的慰藉。在這種不對等的婚姻關系中,女性被無形地奪去話語權,成了無聲的勞作機器,默默承受著生活的苦難。
村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不僅在精神上,更表現在對女性肉體的蹂躪上。在男權盛行的鄉村社會里,女性的身體在男權的重壓和性的雙重打擊下極易被侵占和淪陷。而被侵占的肉體帶給女性的是進一步的精神禁錮,造成鄉村女性的又一生活悲劇。《淡黃柳》中的桑桑和《歸妹卦》中的采西就是其中的代表。桑桑本是一個美麗活潑的女孩,卻因為青春的懵懂被新婚不久的魯一同騙去了貞操。她一直喜歡同村高大帥氣的烏獲君,卻因為烏獲君高考落榜,無緣軍校遭到了母親嚴厲的反對。母親也幫桑桑張羅了一個小法官李闊朗,心系烏獲君的桑桑自然看不上矮小的李闊朗。但在母親的提醒下,她明白了自己是個“不完整”的女人,她只是母親“以一個成年人的智慧,制造的一個生活贗品”⑧,而母親又以成年人的智慧一語將這個贗品擊碎。桑桑自覺已配不上烏獲君,心灰意冷地嫁給了李闊朗,然后桑桑“關閉了對烏獲君的熱情,也熄滅了對生活的幻想,她想生活大概就是如此日復一日”⑨。直到多年以后,桑桑終于與烏獲君重逢,才知道愛情的味道、男人的味道。毀滅桑桑愛情的不僅是被侵占的身子,更是女性被腐化的貞操觀。傳統含蓄的貞操觀在男權社會和現代商品經濟的沖擊下,似乎已經變成了女性婚姻中等價交換的籌碼。一旦女性的貞潔受到懷疑,她就會被自動歸為“差貨”,《青桔子》中的桔子因為被懷疑婚前不潔,備受婆婆的唾棄,連回娘家時也被父親訓為“差貨”,最后她自己也深陷“差貨”的詛咒中,用身體實行了對全家人的報復。《歸妹卦》中的采西被倒插門的姐夫阿良強奸,而后被姐夫處理給又窮又有蘿卜花眼的張角,張角知道采西之前有過男人以后“感覺自己被坑了,耿耿于懷”⑩,之后還把妓女帶回家。一場水災過后,采西一無所有地回娘家,不僅沒有得到一絲溫情,還被姐夫當作潑出去的臟水極力排斥,最后姐妹倆一起動手殺了這個禍害了她們一輩子的男人。這么多女性的悲劇赤裸裸地展現出鄉村殘忍的面影:女性被物品化,身體淪陷,物質匱乏,精神虛無,生活陷入惡性循環。
故鄉,已然退化成另一個異鄉。盛可以作品中的許多進城返鄉人員,在故鄉中感受到的只是不適和疏離。記憶里鳥語花香的小鎮已然消失,就像《道德頌》里描述的那樣:“經濟似乎好起來,部分舊木樓消失了,代之以洋樓小景。河里的水污染太重,不能飲用,游泳也不行了,政府把它包給個體戶養魚(一年到頭往里撒肥料),改變了全鎮人的生活趣味。年輕人都在吸毒,和抽煙一樣普遍,毒癮上來,趁黑到鄉下偷雞摸狗,打家劫舍,弄得村民們天黑閉戶,每家養好幾條狗。派出所的伙計們是認錢不認人的,行賄者能拿出上百萬的人民幣上下疏通。一個純樸的小鎮都變成了這樣,其他自不待說。”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帶來的卻是民風的凋敝和生態環境的破壞。鄉村拋棄了它最珍貴的特質,已然異化成城市糟粕的腹地和游子們的噩夢;淳樸的鄉里情也沾滿了世俗的功利和勢利。在盛可以的小說里,有很多刻薄潑辣、愛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亂的鄉村婦女。她們一般生活不幸,更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一旦別人不能達成自己的目的,便會惡言相向。像《北妹》里的春樹嫂子一邊想讓錢小紅幫她女兒在深圳找工作,一邊宣傳錢小紅在深圳賣淫。當錢小紅沒能幫上忙,“她說錢小紅尾巴翅得像猴子,撅起紅屁股挺起奶子到處發情,哪有閑心幫她二妮子找工作”。鄉土女性的淪陷,民風的凋敝以及生態環境的破壞代表的是鄉土社會文明的整體失落。在城市里身心疲憊的游子回歸故里,不僅得不到絲毫慰藉,還被傷得體無完膚。哪個人不會心灰意冷?只能在城鄉之間漫無目的地游走,尋找那遺失的美好,尋找那失落的鄉土文明。
二、 失衡的兩性關系
腐朽的鄉村制度剝奪了許多鄉村女性自由婚戀的權利,造成了不少婚戀悲劇。然而在繁華的都市里,兩性關系失衡導致的婚戀悲劇更是屢見不鮮。盛可以在她的多部都市婚戀題材小說中對兩性關系失衡及其原因進行了有力的揭示和深入的思考。
正如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存在陰陽兩面,人也一樣存在男女兩性。兩性關系正如這陰陽兩極,互相平衡,陰陽調和。理想的兩性關系應是愛情關系、婚姻關系、性關系三者的和諧統一。然而,在盛可以的小說里,我們看到了很多有性無愛、有婚姻無愛情、靈與肉分離的兩性悲劇。似乎在物質化和消費主義的荼毒下,人們已經進入了“炮禮時代”,沉迷于享樂主義,愛情無處依附,婚姻茍延殘喘,兩性關系已經嚴重失衡。
愛情本是美好、甜蜜、依戀的化身,是人類歌頌的最純粹最神圣的情感。無論是寶黛的純真之愛還是柏拉圖的精神之愛,愛情的產生不僅僅是剎那的悸動,更是精神上的契合。愛情也是情感和情欲的結合,是靈與肉的統一。然而,在盛可以的小說里,愛與性被狠狠地撕裂開來,似乎要讓我們看清愛情血淋淋的真相。《取暖運動》中巫小倩一人在北方的寒冬里備受煎熬,產生了找人肉體取暖的沖動。“愛情不是東西,可是沒有愛情,人活著就不是個東西。”巫小倩肉體的饑渴把原本屬于精神范疇的愛情轉移到了肉體領域,她認識了還未工作的劉夜并與他迅速建立了“肉體取暖關系”,但這種關系建立的根基原本就是無愛的、畸形的。處于甜蜜期的小倩曾幻想過與劉夜的未來,但她后來發現劉夜除了帥氣和青春的外表,幾乎沒有她欣賞的東西。身體的取暖終抵不過靈魂的燥熱,當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就像兩只機械取暖的動物,為了欲望而抱團,因為厭倦而離散。因性而起的所謂愛情終究是抵不過現實的生活,欲望越是強烈,消逝得就越快。取暖運動最后帶來的心靈虛妄反映出人性的自私和冷漠,以及現代社會人人都難以逃避的深層焦慮與慌亂。
在“炮禮時代”的影響下,人們肆意地生活,獲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但是,重便真的殘酷,而輕便真的美麗嗎?”正如米蘭·昆德拉筆下的托馬斯醫生在離婚以后與眾多女性保持所謂的純潔“性友誼”一樣,女性似乎獲得了身體的解放和自由,其實卻陷入了更深的情感危機。在與男性的速食愛情游戲里,女性的身體被消費,感情被欺騙。而男人的審美似乎總是在水性楊花與賢妻良母之間搖擺。在男性的眼里,女性的性自由無疑增添了不少無負擔的魅力。但當要論及歸宿和婚嫁時,女性的自由反而成為她們致命的枷鎖,是她們浪蕩不忠的印記,成為她們不可擺脫的精神之重。《無愛一身輕》中30歲的朱妙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建筑設計師和小說家,雖然在經濟上可以獨立,但是依然不能擺脫對男人精神上的依靠。但是對婚姻的不信任使她在國土局局長方東樹、海歸男程小奇、攝影師許知元之間周旋,自以為掌控全局,卻不知早已跌入男權的性游戲之中。當肉體的新鮮被消耗殆盡時,女人尋愛的歸屬感開始作祟。此時,三個號稱唯她馬首是瞻的男人也開始顯現出他們的別有居心,方東樹為了擺脫她不惜欺騙她;自詡純情的程小奇也僅是為了得到她的身體;說要娶她的許知遠也在知道她復雜的情感關系以后離他而去。因為她肆意的“自由”,她成了理所應當被愛情拋棄的人,掩不住內心空虛恐慌的她只能匆忙嫁給閨蜜的前夫。“無愛一身輕”,這種浮于生命表象的輕和自由,不過是一場空虛。完全失去責任和精神之愛的愛情就像披著狼皮的羊,只有欲望褪去的澀,沒有真情滋養的甜。缺乏精神寄托的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
在商品經濟的社會里,愛情似乎也少不了被物質化。盛可以的很多作品都讓人不禁懷疑,愛情是否已經成為一種赤裸裸的物質交易?《惜紅衣》里的外來務工少女董葡萄,為了幫父親落實工作的問題,把自己的愛情和身體當作了交易籌碼。《水乳》中的左依娜因為對原本沒有尊嚴的婚姻生活不滿,邂逅了律師莊嚴,即使后來兩人的關系陷入僵局,左伊娜還因為“莊嚴在市政府大院和機關單位進進出出,辦起來事來,順溜得很,左依娜的工作問題,還得指望莊嚴。嫁不嫁莊嚴,左依娜自己做不了主”,以至于后來二人的關系像是“騎驢看唱本——邊走邊瞧”。也許遇到更得力的人,這種表面和諧的關系就會土崩瓦解。
盛可以對兩性關系失衡原因的探索并沒有被傳統的道德框架所局限。她不僅書寫了圍城外女性的婚姻恐慌,更是深入窺探了圍城內男女貌合神離的兩性關系。婚姻本該是愛情的延續和升華,但在盛可以這里,婚姻不僅成了愛情的墳墓,更成了禁錮人性的壁壘。《無愛一身輕》里的方東樹和林芳菲的婚姻,兩者的結合本就不是因為愛,而是男方為了獲得更好的社會地位的一種利益聯姻。所以婚后兩者的關系自然寡淡如水,直接導致了兩人的婚內出軌。但妻子的出軌成了方東樹“摘不掉的綠帽”,他借此由頭對妻子展開婚內冷暴力,自己卻心安理得在外尋花問柳。當身心俱疲的妻子想要解脫要求離婚時,一直對妻子心有芥蒂的他卻突然想通了,因為“外面再怎么亂,家中的紅旗不能倒”。這樣的婚姻不僅是無愛的,更是自私、虛偽、勢力的結合。也許愛情和婚姻在精神內核的本質區別才是兩者失衡的原因所在。就像盛可以在《道德頌》中想要表達的一樣,一場婚外戀牽出的道德混戰,我們很難在既定婚姻道德的框架下用道德去評價他們。就像我們可以說愛上“偽君子”的“小三”旨邑是不符合婚姻道德的,但我們很難說殘忍拋棄她去維持與原配名存實亡婚姻的水荊秋就是道德的。盛可以并沒有站在普世婚戀價值觀的立場上對“小三”旨邑進行道德批判,反而諷刺了丈夫水荊秋的自私和虛假,以及他和妻子梅卡瑪那看似被倫理道德贊頌其實充滿人性污點的“模范婚姻”。從她對“小三”旨邑所受痛苦的同情以及對她真實愛情的贊美,我們可以看出盛可以隱沒的“道德觀”:道德不應該是維護世俗倫理的衛道士,而是基于人性的弱點和優點,對生命價值和真實情感的禮贊。正如寫在《道德頌》扉頁上尼采的那句話:“沒有道德現象這個東西,只有對現象的道德解釋。”而尼采所推崇的道德,其實就是一種“以肯定生命價值為基礎內容的道德的自然主義”,是“力圖祛除靈魂對肉體的桎梏,釋放人的本能欲望,放棄彼岸的虛假幸福,立足此案,立足現實生活”的新道德。
在對兩性關系的探索中,盛可以塑造了一個個分崩離析的愛情婚姻悲劇。她曾說過:“我對人世間各種情感都持懷疑和悲觀態度。”也因為這份懷疑和悲觀,她不懼去冒犯固有的道德體系、社會觀念和制度,肆無忌憚地揭露人性的丑惡面。她看見了愛情的脆弱、婚姻的虛偽,以及婚戀道德體系的腐朽。通過解剖對抗的兩性關系讓人們反思其中暴露出的社會、文化、制度問題,究竟是無愛時代造成了婚戀的虛妄,還是我們應該學會控制無限膨脹的欲望,還責任于愛情,還愛情于愛情,還愛情于婚姻。但這一切都沒有既定的答案,失衡的兩性關系還在尋覓和諧的路上。
三、 失守的精神家園
盛可以通過對故鄉溫情的失落和城市婚戀的失衡的描寫,展現出“在路上”人們的焦慮和虛妄,此岸彼岸皆不是家,這種無家的漂浮感在游子之間蔓延開來,帶來的是進一步精神家園的失守。
為了進一步表現失去精神寄托的人的生存狀態,盛可以不禁將人物打出常規,進入第二環境,以此暴露出他們的“第二心態”。其中以《中間手》的李大柱和《白草地》里的武仲永最具代表性。《中間手》里的李大柱是一名下崗工人,失業后的他在巨大的經濟和精神壓力下突然長出了一只中間手,這只手影響了他正常的生活,他只能穿雨衣上街,會忍不住在大街上調戲女性,與女朋友的關系也日漸緊張。終于在中間手獸性般的催化下,李大柱退化成了為了肉可以撕人的野獸,也為了滿足肉欲,他變成了關在動物園里供人觀賞的異物。《白草地》中的武仲永是一個看似衣冠楚楚的外企銷售員,結婚多年的他卻買不起房、給不了妻子鉆戒,甚至連拍婚紗照的時間都沒有。每天只有打不完的電話,陪不完的應酬,為了一張訂單磨破嘴皮,像一只哈巴狗一樣左右逢迎。工作無比辛苦,月底的業績卻如被打暈的水蛇一般,毫無起色。為了獲得可憐的一點業績,不被公司裁員,他諂媚地勾引年逾四十的大公司采購多麗,在情人瑪雅那獲得唯一一點男人的心理慰藉。自以為在三個女人之間自由游走的他其實已自身難保,在情人和妻子的苦心設計下,每天被灌以雌激素的他已經被異化成了一只活生生的“狗”了。細細思考,這看似夸張的異化其實隨處可見,紛繁的社會里人的靈魂不斷被物質化、異化甚至虛無化。生存的壓力、婚戀的困擾、都會導致精神的焦慮和荒蕪。像《中間手》的李大柱因為下崗,經濟上不得不依靠女友,傳統男權觀念的失落帶來的精神的變異和身體的萎縮,連避孕套的碼數都從大號縮到小號。他變得憤世嫉俗,連在路邊上看到的風干的狗屎都要發出“狗吃的比我好,再看路邊狗屎的多少,我明白這個城市有許多狗過著上等人的生活”之類人不如狗的感慨。所以,他懼怕與女友的婚姻,也是在這種精神無依的狀態下他變成了為一塊肉而放棄自由和尊嚴的異物。《白草地》中的武仲永從踏入工作之后就拋棄了這個土氣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所謂洋氣的Jason。這樣拋棄類的接軌似乎使他從開始就偏離了幸福的軌道。為了金錢利益,即使多麗是條“殘缺的肥魚”,他也要囫圇吞下。當得知多麗離職以后他兩眼昏黑——“假如你留在福斯公司,哪怕你是條卑鄙淫賤的母狗,我也能和你保持融洽的友誼”。他冷漠虛偽的同時,也是那么的膽小懦弱,他艱難維持著與妻子藍圖表面平靜卻無愛的婚姻,不敢正視自己的感情。在忙著經營欺騙和被欺騙的虛假圓滿里迷失了自己的靈魂,異化成了在黑白世界里虛無的存在。
盛可以筆下這類真實的荒誕作品,還有《快感》中瘋狂熱愛刀具的過氣歌手,《魚刺》中可有可無卻又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魚刺,《惟愿中年喪妻》中迷戀蛙神卻有著“喪妻情節”的中年男人等。就像卡夫卡的《變形記》一樣,人在現代節奏中已漸漸蛻化為“非人”。盛可以用這種悲哀的審視,奏出了精神荒原中一首首奇異的哀歌。
鄉村在鄉土文明的失落和現代文明的沖擊下已淪為精神的失樂園,無家的狀態從城市擴展到了鄉村。《蘭溪河橋的一次事件》中守寡又無子女的老太太,對身邊的一切活物都有喂養的沖動,精神的空虛使她把素未謀面的年輕人迅速當成了親人,當最后被其所騙時,她無處寄托的母性成了她最悔恨的錯誤。《苦棗樹上的巢》描繪了進城務工的“打工潮”給鄉村帶來的“空巢感”。老實巴交的村里男人麥根和刁鉆潑辣的三表嬸都是被留下的人,他們在進城和返鄉、留守和婚姻之間來回游蕩。面臨婚姻的破裂,親人的離散,只能守著這空巢咀嚼“無家”的苦味。
結語
盛可以曾說:“我作品的每一個人物,不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是我,或者是我的一部分,或者是我化身為人物,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她用分裂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來剖析人生,直面“人性中的原欲、瘋狂和變態,折射的就是種種社會性問題”。對惡的探究,“不討好、冒犯性的文學創作”也使盛可以成為獨特的上帝與藝術的“不孝子”。或許是作家本人的精神也無處安放,她作品中的人物總是呈現出一種“在路上”的游離狀態,越是奮力向前,就越是在失去。她通過對失落的鄉土文明、失衡的兩性關系以及失守的精神家園的剖析,書寫了這個時代人們的愛與痛,追求與失落,生存與流亡。既然失去如此慘痛,我們為何還要一直向前?也許正如沈浩波等人評論盛可以“已經變得太像一個職業化的很會寫小說的小說家了”,雖然盛可以的文風逐漸失去冷酷和疼痛感,但我們看到了像《墻》這樣用溫情理性化解矛盾的作品。“其實,我內心這一片柔軟,遠遠比我的尖酸刻薄、冷硬凌厲更豐盛,更強大。”就像她自己說的“就像揭露丑惡,是為了贊頌心中的美好”。盛可以通過這種撕裂心靈的疼痛來喚醒人們日益麻木的心靈,并試圖告訴人們只有懂得失去的痛,才能真正學會珍惜美好。然而這一切的答案還是“在路上”,人們只能揣著回家的念想,繼續飄蕩,繼續找尋,繼續失去……
注釋:
①洪治綱:《主持人語》,《當代文壇》2007年第2期。
②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③曹淑賢:《盛可以訪談錄》,《時代文學》2013年第11期。
④沈浩波:《像北妹一樣奔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1-19/41369.html。
⑤盛可以:《缺乏經驗的世界》,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頁。
⑥盛可以:《缺乏經驗的世界》,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頁。
⑦盛可以:《缺乏經驗的世界》,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頁。
⑧盛可以:《可以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第76頁。
⑨盛可以:《可以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第85頁。
⑩盛可以:《可以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第192頁。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