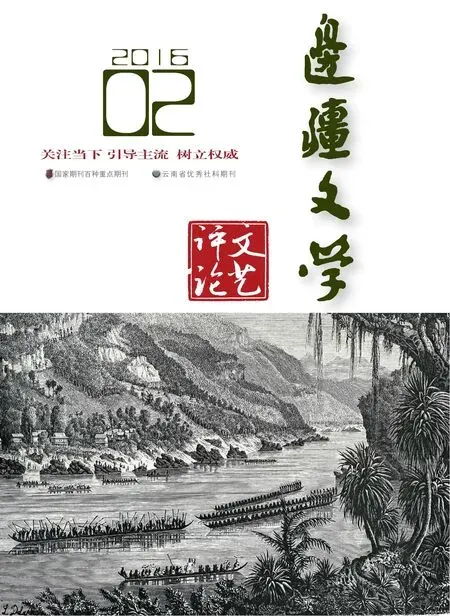狂歡的詩意
——論夏天敏小說中的傳奇敘事與詩性張力
◎張 偉
狂歡的詩意
——論夏天敏小說中的傳奇敘事與詩性張力
◎張 偉
昭通作家群中,夏天敏無疑是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如果要問夏天敏小說最大的特點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好看。閱讀夏天敏的小說,猶如參加了一場“底層農民弱勢群體”的聚會,其特殊性就在于,在塵世的熱鬧中,撲面而來的是沉重和壓抑,而感動讀者的則是一份對生命的悲憫以及對苦難超越的情懷。但這份悲憫如果離開了昭通底層農民的人生景觀便無從著落。所以對夏天敏作品的品評還應回到傳奇這類游戲文本的文化功能的理解上來。從對文本的闡釋中,梳理出那份充滿傳奇色彩的“狂歡精神”。我們不能因“狂歡”這個概念的西化背景,以及中國民族心理長期以來形成的不茍言笑的特點,便輕易否定“狂歡精神”的文化意義,無視夏天敏小說與“狂歡詩學”的內在關聯。
一、傳奇敘事與游戲筆墨
走進夏天敏的小說世界,雅俗共賞的“熱鬧”無疑是存在的,而這份熱鬧又顯然得益于小說所依仗的昭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離不開各式各樣的傳奇故事。這就意味著要真正深入夏天敏藝術創造的“門道”,不能遺忘這些作品的“傳奇”敘事。這也恰是評價夏天敏小說的一個難點所在。在他的《好大一對羊》《四爺收徒》《皇木滑竿》《土里的魚》《鄉場上的皮匠》等小說中,的確包含著現實和傳奇之間一種貌似相悖的沖動:既以一種清醒的姿態面對世界又以“游戲筆墨”超越日常生活。小說的獨特性就來自于這兩種沖動所構成的一種張力,處于這個“張力場”的中心的既是對現實世界苦難的仿造又是對昭通地方民風民俗“可能生活”的書寫,使得夏天敏的所有小說都有一方面看上去像傳奇。這類傳奇故事既能讓讀者獲得一種消遣性的滿足又始終如一的堅守著民間文化之根,總是顯現出超越日常事態人生的虛幻,同時又具有一種內在的游戲品格。如在他榮獲魯迅文學獎的作品《好大一對羊》中,德山老漢越來越貧窮,因為他養了一對“外國羊”,當羊的身價高貴于人的時候,人成為了奴役的工具;再加上鄉長們的層層施壓,使得這一對羊的生命價值、種的繁衍遠遠高于德山一家的生命價值,“羊”在此象征著難以抗拒的無形束縛的力量,不僅是權力的傳遞,更是德山老漢那愚鈍麻木的靈魂深處的痛。看似荒誕的情節卻隱透出一種殘忍,“黑色幽默”的筆法成功的構建了現實世界的荒誕,匠心獨具的構思創造了一個亦真亦幻的羊的世界,人被置于無望的怪圈而無力自救,虛構與真實的巧妙的結合,使傳奇書寫在 “游戲語境”中大顯身手。
在《接吻長安街》中農民工“我”最大的愿望不是改善自己的工作環境或者工資待遇,而是要和女友在長安街上當眾接一次吻,所有的一切都圍繞“主體愿望的滿足”這一主旨而存在,這也正是這篇小說的傳奇性所在,既揭露了喧囂世界背后小人物的種種夢幻,又使我們從中發現游戲的內在意義——生命為其無任何的自然束縛也無社會負擔的單純的存在感而感到由衷喜悅。這篇小說應當是對昭通人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大膽探索,具有深切的人文關懷,它的不同凡響之處在于,小說中的主角以生命盡興的方式來實現自我解放;而那種對日常生活模式和僵化文明儀式的解構為內涵的怪誕形象和粗鄙化行為,構成了狂歡文化的核心意識;體現了平等自在的生命樂趣和詼諧,彰顯的是作家和讀者的良知和道義,具有一種雅俗共享、藝術與生活相融的既奇異又現實的特點,令人解頤之余,又充滿了對人生的感悟。
其實,文學創作的出發點一般有兩種:一種為俗世而寫作,它追求的是“利”,即追求寫作者物質利益的最大化;一種是為精神而寫作,它追求的是“義”,即追求對人生的本質的探索和對人類精神的撫慰。毫無疑問這部作品是為“義”而作。小說通過想象力的空前活躍使底層人民的自由意志得以盡情釋放,使得藝術活動的終極目標得以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創造出一個既來自于現實,又高于現實的歷史風景。
又如在他寫的為數不多的長篇小說《極地邊城》中,夏天敏成功地塑造了云霓小姐這樣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女性形象,雖是大家閨秀卻使得一身好拳腳;雖出生在偏僻落后的滇東北,卻從小養尊處優沒有經歷過生活的磨難;更為傳奇的是,她并沒有身在政壇,卻為了百姓的利益鋌而走險。但這樣一位集百寵于一身的云霓小姐,卻未能逃脫自己的宿命,在出嫁當晚就淪為了寡婦;就在她守寡多年并最終決定追求自己幸福的時候,她的兒子卻成為她的俄狄浦斯。這篇小說成功的奧秘就在于她比別的同行具有更到位、更自覺的“游戲意識”、更善于舉重若輕,更徹底的解構了負載于生命之上一本正經,讓具有傳奇敘事的文本回歸其民間文化之根。語言繼承和發展了地道的民間話語的特色,既有高原人的“口氣”特色,又有潑辣的鄉村口語,既有詩化的情趣描寫,又有對飽蘸人生世態的嘲諷,形象與心靈、結構與節奏融合無間,營造出了一個強大的藝術磁場。正如小說所描寫的那樣:“她哀嘆自己顯赫的身世、哀嘆自己身上的光環,這些光懷實際是一條條鎖鏈,別人走不進來,她也走不出去。”曼杰利塔姆說“一想到我們的生活不是一個有情節,有英雄的故事,而是一個由憂傷、由玻璃紙品,由不停息的到處蔓延的狂熱的嘈雜聲、以及由彼得堡流感引發的譫妄囈語所構成的傳說,就讓人毛骨悚然。”曼杰利塔姆描繪的其實就是人性的荒誕,因無力而生發的恐懼和惱怒。這種“真實”嘲笑了虛幻的美,消解了優雅與空靈,裹挾著生活中的苦悶氣息,抗拒著智慧與玄思的過分炫耀。但歸根到底,這既是狂歡區別于一般游戲的根本品質,也是它能夠貫通傳奇與小說的最寶貴的詩性內涵。
在本土化的文學創作過程中,夏天敏小說的故事類型有著較一般生活化小說更多的限定,更像是一種“帶著鐐銬的舞者”,但顯然,只有不會跳舞的人才會怪腳鐐礙事。他的小說,并未因這種本土化的先天限定而影響其藝術的表現力,反而在作品中,以有限的人物性格演繹出了讓人別開生面、無與倫比的傳奇故事。這類傳奇敘事通過生動的情節大大強化了文字游戲的樂趣,使得小說文本擁有了一種本土韻味的狂歡精神,在倫理上具有雙重指向的叛逆性,即不僅挑戰現有的道德禮儀規范,而且還對最高的人道法則生命解放、追求幸福做出了一種肯定。
狂歡,雖然是西方詩學的概念,卻可以用來說明夏天敏小說敘事的藝術奧妙,所有的傳奇都具有游戲性,盡管并非所有的游戲都具有狂歡節的特征,但如果我們把游戲認可為生命的一種自律的自我確證,因而承認“游戲的基調是狂喜與熱情”,那么狂歡便是真正的游戲活動的最后歸宿和最高境界,也是游戲精神的本質的一種體現。夏天敏的作品并非完全體現在對貌似威嚴,不可侵犯的權威與規范的反叛和褻瀆,更多的是體現在對平等自在生命樂趣的詼諧,體現在貫穿整個文本的傳奇化的敘事氛圍;由于這一切都是在一種詼諧的氛圍下進行的,所以屬于真正的狂歡形態,具有了一種形而上的意義,小說也因此化玩笑為創造,使得那一個個貌似荒誕不經的粗俗故事,擁有了一種不可多得的詩性內涵。
二、詼諧中的詩性張力
讓我們再來談談《兩個女人的古鎮》,這也是一部充滿諧趣的小說,以鹽津豆沙鎮為人文背景,以日本的長驅直入為歷史背景,以歷史文物為底色,以自然風景為襯托,以古鎮上玉碗、蔣嫂兩個傳奇女人的愛恨情仇為線索,真實的展現了豆沙古鎮的繁華熱鬧和淳樸民風,再現了五尺道上的俗世奇人,把千年古鎮演繹得淋漓盡致,對人性的把握準確到位、對人生的體悟含蓄深刻,最后所有的愛恨情仇在“至善”中呈現“大美”。這樣的結局固然匪夷所思,卻滲透出了一種真情與和諧。這無疑是一個敘述圈套,因而讀罷小說你會有一種中了作者的“埋伏”的感覺。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在狂歡節的自由自在、不拘形跡的氣氛中,甚至連放蕩的舉止也獲得一席之地”。而讀者之所以不以為怪,是由于小說飽含真誠的鄉土書寫,節制而富文采的語言風格,對人性與社會的復雜性讓人產生一種忍俊不禁的詼諧。又如《鄉場上的皮匠》一文,講述了一位世世代代居住在滇東某鄉鎮并世世代代以修鞋為生的皮匠牛順德與一位外來皮匠之間的故事。牛順德的手藝是祖上傳下來的,早已得到鄉親們的認可。但由于沒有競爭,所以他嗜酒成性,常常忘記了干活。可是,一位外地皮匠打破了鄉場上秩序。外地皮匠手藝好、設備先進,還十分講信用。這就不可避免地奪去了牛順德的生意。最終,牛順德經過一番痛苦掙扎后,毅然決然地放棄了自己的祖傳手藝,改行當搟氈匠了。在這部小說中作者用詼諧的本土語言為我們描寫出了一個善良、和諧的小社會。毫無疑問,在夏天敏的文學世界里這兩部小說的藝術分量并不算重,但它特殊的價值在于以“反苦難”的方式來建構新的藝術天地,使“狂歡精神”成為小說中的一種主旋律,再經過詼諧化的處理,不僅使作為“苦難”主干的人性失去了沉重性和嗜血性,也使得小說充滿了人間的溫情,對最高的人道法則做出了一種肯定,使小說擁有了一種不可多得的詩性品質。
其實,在夏天敏的小說中,詼諧的場面描寫比比皆是,如《土里的魚》中狗剩老漢臨死前的遺言不是入土為安,也不是如何將遺產分給兒子們,而是要將自己“厝”起來,并相信這樣能給子孫后代帶來幸福;《皇木滑竿》講述的是陳滑竿和謝長腳這兩位靠抬滑竿為生的底層民眾對陳滑竿家那副祖傳的皇木滑竿的深情。他們對皇木滑竿有著如此深情——即使在不許抬滑竿的特殊時期,他們也要在院子里“過回干癮”;《四爺收徒》一開篇就撲面而來地呈現出了一種“異域文化”“評豬”,這對于非滇東烏蒙山區的讀者來說,想必是陌生的,而四爺就是這個行業德高望重的高手。這一系列奇人奇事的故事,道出了一種生命的大境界,一種建立于生命之間的互相溝通的人類之愛,使得這類小說較一般的苦難主題更多了一份美感。曹雪芹在《紅樓夢》里說得好:“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確,我們之所以將“狂歡”視作夏天敏小說的藝術審美的一個核心,并不是說夏天敏先生在創作時接受了巴赫金的指令,使其小說自覺地運用了狂歡詩學的理論。我的意思是指,借鑒這個“狂歡詩學”的思想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夏天敏小說的藝術奧秘。
夏天敏的小說沉重而又不乏幽默,作為狂歡文化風格所體現出來的詼諧,包含著一種嚴肅性,即對苦難生命的解放與再生,在笑聲中恢復人的尊嚴,讓精神高揚,所以這種狂歡的詼諧同一般狂歡搞笑之間,存在著一種深刻與膚淺的區別、文雅與粗俗的差異,也就是在那些看似隨心所欲、無遮無攔的敘述中,蘊含著對許多世態人生的深刻洞悉。
(作者系昭通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