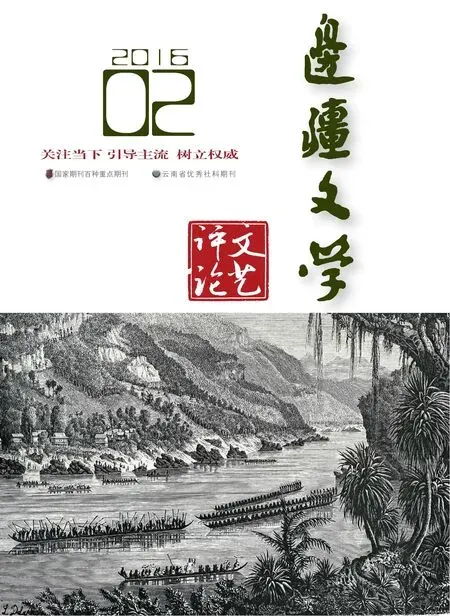審美情懷的堅守與超越
——秦錦屏小說論
◎楊榮昌
作家與作品
審美情懷的堅守與超越
——秦錦屏小說論
◎楊榮昌
主持人語:本期推出的兩篇作品,一研究荒誕性,一研究作家創作過程中審美情懷的堅守與超越。探究《生死疲勞》的中國式荒誕性敘事突圍,是個有趣的題目。文章認為:莫言的《生死疲勞》具有荒誕性敘事的典型性。它表現出來的荒誕性不僅透過其紙背,指向對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對文革的批判,更緣由其文革獨特的記憶和感受。文章分析莫言在書中吸納了更多的荒誕性元素,采用了更多的荒誕性手法,描寫了更多的荒誕性場景,采用了更多的荒誕邏輯。從其線索到整體故事,都滲透著荒誕的因子,認為莫言及其作品已經成為中國文學文化輸出的一張名片。最后提出:中國式荒誕,是對荒誕本身的描寫,從荒誕現實到荒誕文學的移植,用荒誕來反抗荒誕的反撥與批判!中國文學作品的荒誕性終帶著中國特色走向世界,成為世界荒誕性文學中的一面獨特旗幟。這些觀點未必準確恰當,但有個人思考與見解,可以一讀。(蔡毅)
一個有故鄉的寫作者,心靈深處始終存在一塊精神的“血地”,那里埋藏著人生全部的秘密,無論置身何方,只要是觸及靈魂的書寫,故鄉的影像會在不經意間浮現,召喚著他的文學表達。在此意義上,寫作注定是一場充滿陣痛的返鄉之旅,作家終其一生都將在故鄉的巨大精神容器中舒展騰挪。關中女子秦錦屏,當年與無數懷揣夢想的年輕人一樣,來到深圳這座由青春和激情造就的城市,開始她的尋夢歷程。十余年過去,她創造的文學世界已蔚為大觀,綜合審視之,會發現其作品始終有一個堅挺的支點,那就是生于斯長于斯的三秦大地。蒼涼厚重的黃土高原,累積起對生命不息的渴望,也孕育了這片土地的堅韌品質,從這里走出的寫作者,普遍承繼了對社會現實短兵相接、毫不妥協的人文傳統,無論書寫歷史,還是凝視過往,抑或觸摸時代體溫,都在執著勘探社會與人性深井的維度上努力,體現出可貴的藝術自覺。
在打工者匯集的南方大省,秦錦屏與之聯系的,多是各行各業的打工者,作為他們中的一員,她對同行所經歷的辛酸、屈辱,以及人生的愿景感同身受,打工者背后的那片故鄉,也曾佇立了作者的影子。小說《冬天里的一把火》,表現的是農村留守兒童的主題。主人公黑黑的父母與村里其他成年人一道,為了家庭生計遠走南方,留下孤單的他寄養在親戚家。通過他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軌跡,勾連起這座典型的空殼村的現實情狀。小說中的幾個重要場景,如豆豆爸媽再次外出打工,兒子的拉扯不舍,村里老人去世找不到精壯勞力抬棺的悲傷,“993861”這個黑色幽默般的村莊“番號”,等等,將中國農村的“空心”現狀表現到了極致。黑黑所在的那個村莊,也許是作者的出生地,同時也是當下中國農村的縮影。小說顯露出反思的力量,指出了在城市的極度擴張背后,是無數普通的外來務工者付出的巨大犧牲,他們拋下的老人尚須贍養,兒童更要接受愛和教育,但這些都缺失了。更可悲的是,到了光怪陸離的城市,原本質樸的心性丟失了,人成了欲望的俘虜,情篤意濃的夫妻從此分道揚鑣,社會的巨大轉型往往帶來人性的裂變,造成無數家庭的分崩離析。而留在家鄉的孩子,他們的成長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小說中的黑黑,無意識中一把火燒了所寄居的房屋,這個舉動,居然是為了渴望在火光中迎接爸爸的歸來,因為姑姑告訴他爸爸是救火英雄——這讓人欲哭無淚。
一名優秀的寫作者,注定不會漠視這個世界存在的傷痛,為卑微者代言,給弱者以心靈之光的燭照,是作家最為可貴的人格品質,它源于深沉的社會責任和充滿溫情的人文關懷。在與冰冷的現實對抗時,秦錦屏以筆為劍,以鋒銳的文字直刺這個時代的心臟,觸及了社會生活中被光鮮亮麗的外表所遮蔽的領域,小說有著讓人傷懷的人文之美。但她對社會的痛下針砭,又取決于對世界的深度愛戀,愛與恨常表現為二律背反的高度統一,殊途而同歸。心中潛藏著對善良人性的渴望,于是用點滴筆墨來匯聚這份明亮與溫馨,抵制近乎絕望的世界。所以,小說塑造了“明月姑姑”這個善良的女性青年形象,她堅執地信守諾言,留在家鄉撫養母親,照顧黑黑,包括未婚夫數次催促她前往南方發展也不為所動。然而,隨著母親的去世,明月究竟是該繼續留守,還是與心上人奔赴一個讓人向往的新世界,若是選擇后者,黑黑又該何去何從?對此,作者顯然無解,我們也無解。這就是文學的混沌與模糊性,它意義豐富,呈示問題卻不解決問題,為的是給讀者敞開一片無限可能的世界。
長年的戲劇創作經歷,秦錦屏接觸到了很多一線的文藝人才,他們或許并未聲名鵲起,大紅大紫,但把對藝術的追求與改變人生命運的期盼緊緊相連,自身便蘊藏著諸多的戲劇性。表現這類人群的生存狀態和心理掙扎,作者似乎顯得得心應手。如《朝天吼》,寫出了一位秦腔愛好者對本土藝術的摯愛,他為此得罪了地方權貴,也不受家人待見,從此命途多舛,顛沛流離,大半輩子的人生過去了,依然不改初衷。那些從生命中吼出來的秦腔,悲壯,激越,響徹在黃土地的上空,也寄予著那塊土地上的人民對命運的獨特理解和表達。作者的深層意圖,似乎是想借此為故鄉遠逝的藝術精魂做一次無言的祭奠。《女主角》從表面上看,是想揭露權力、欲望對人性與藝術的戕害,表達人生的“主角”其實掩藏在面具的背后。但小說真正動人心魄的,卻是“丁香雨”的為戲成癡,這位貌美如花的年輕女子,癡迷戲劇,為了能當上“主角”,甚至患上了間歇性精神分裂癥,青春和身體被無情的專制力量吞噬。小說顯示出作者對藝術的熟稔,那些或俚語方言,或文雅古奧的唱詞經人物之口唱出,為小說增添了豐富的審美元素。
從地域文化深厚的故鄉關中啟程,到現代性高度發達的南方城市寫作,立體多元的審美視域,給秦錦屏提供了豐富的觀察視角,過往的人生經歷經由她的凝聚、提煉,逐漸升華為一系列特色鮮明的人物形象,成為表達生命體驗的有效載體。作為一名積極追求人生,熱心擁抱生活的青年作家,繁華的南方都市生活,也為她的寫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火苗》可視為她之前創作風格的一次自我提升。小說講述了一個留守妻子到特區尋找丈夫,通過她的親眼所見,親身感受了丈夫及其他建設者為這座充滿新生力量的城市所付出的努力,洋溢著青春的激情。這篇小說可預示著作者正逐漸走出對鄉土中國的懷舊抒情,奮力開掘新的表達場域,顯示出感知時代脈搏、揭示社會面相的能力。《奇葩》也是她在創作題材上的新嘗試,以民國女子張竹君的傳奇經歷為主線,串聯起一段感慨悲歌的歷史,從書寫當下中國轉向回眸歷史,充滿著對人性的審視與拷問,表達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有著讓人驚異的表現。就藝術風格而言,小說似乎不會玩弄技巧,甚至文本的表達形式也還保留著出生地的樸拙。惟其拙,才能在與現實撞擊時發出沉穩有力的鈍響。
秦地沉郁包容的文化特質,南方激越奔放的生命活力,故鄉與異鄉在審美維度上的沖撞與互融,構成文學創作巨大的情感張力,表現在秦錦屏的小說中,形成了堅守傳統、穩固根基又求新求變、力主超越的美學追求。面對這樣一位正走向成熟與厚重的優秀作家,我們的任何期待都不為過。
(作者系楚雄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教師、楚雄州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責任編輯:徐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