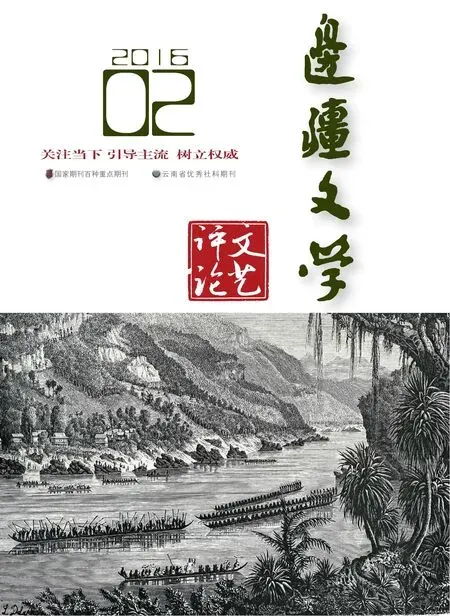對少數民族文學不能因“無知”而去“無視”
◎劉大先 周明全
對少數民族文學不能因“無知”而去“無視”
◎劉大先 周明全
“在暗夜里慢慢趟出自己的道路”
周明全:大先兄現在在批評界大名鼎鼎,但對你的求學經歷,似乎還有很多人不知,兄能否簡單介紹一下?
劉大先:明全兄過獎,我也才算起步,還沒有寫出讓自己真正滿意的著作。我是1996年考入安徽師范大學,高考志愿填的其實是英語系,服從調配到了文學院,可能因為我當時語文還不錯吧,單科成績是當年市的第一名,當然更多可能是我的分不夠上英語系,哈哈。那時對文學并無特別愛好,倒是喜歡健身,做了四年體育委員和業余長跑運動員。本科畢業那會兒原準備報考復旦新聞系黃旦教授的傳播學研究生,但是本校給我免試保研了,我也就懶得考了,上的是文藝學。因為本校的朱良志教授做中國古典美學還是很厲害的,我那時候讀了些孔孟與王陽明,想著跟他做古代文論也不錯,結果他那年調到北大美學系了,我就跟陳文忠先生讀西方文論了。2003年碩士畢業本來考到安徽省財政廳做公務員,正好那年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的關紀新主編到安師大開會,提到要招個編輯,學院原先推薦的那位同學要到人民大學讀博士,我那時從來沒有去過北京,就“替補”進了社科院的民族文學研究所,從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工作兩年后,單位允許在職讀博,我當時考了社科院文學所的美學專業和北京師范大學的現代文學專業,兩個都錄取了,但是后來想想可能在現在的單位無法純粹做西方美學研究,就上了北師大。2008年畢業后有個出國的機會,我申請到了當時由斯皮瓦克主持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比較文學與社會學研究中心,2009年去,2011年回國。
這個求學經歷中間充滿了各種陰差陽錯、隨波逐流,是個缺乏規劃的過程,就像是在暗夜里摸黑走路,磕磕絆絆地行走,慢慢趟出自己的道路。這樣當然會走許多彎路,白費了許多精力和工夫。但好處是轉益多師,文學的各個學科都接觸到了,不至于陷在某個偏狹的學科門徑中固步自封。我覺得一個人文學科的從業者,可能還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比較好,一開始就目標明確地步步為營、精心算計,就帶有了商人和謀士的刻意了。
周明全:之前和徐剛、李德南兩位“80后”批評家談過,他們當初走上文學批評這條路也和大先兄一樣充滿了偶然,從你們三位身上可看出,也許不刻意為之,反而能做好一件事。現如今不少年輕批評家見人介紹,總不免說:“我是某某人的學生”之類,感覺很滑稽,難道自己的導師有大名自己就有大名了?和大先兄相識這么久,從來沒聽說你這么自炫過,所以,今天想請你談談你碩士、博士時的導師對你的影響?另外,從事文學研究,還受到了哪些師友的影響?
劉大先:你說的對,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尤其對于學術研究來說,老師只是指路之人,更多還要靠個體的自我砥礪。我的老師們都比較低調,不是什么名人大腕,我自己也不愿意扯大旗拉虎皮的攀鴻附驥。碩導陳文忠先生對學生的基本功要求很嚴格,他一開始給我開的書目就是按照朱光潛《西方美學史》最后提到的四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和康德,我最早寫的論文就是關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這些閱讀讓我受益終身,因為他們構成了一條經典的線索,此后返本開新,無論是繼承發展還是對話批評,都離不開初始的影響。鄒紅老師是我的博導,她是專門做現代戲劇的,尤其是焦菊隱和“人藝”,我的同門幾乎全部是做戲劇相關研究的,不過我因為已經工作了,也逐漸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選的題目是“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博士論文就是后來出版了的同名著作。我很感激鄒老師和在清華大學任職的師公張海明教授給予我的支持和鼓勵,沒有他們的包容,我這個題目肯定無法畢業的。別的給我影響最大的學者就是關紀新、劉禾與李陀了。關老師是滿學大家,早年致力于老舍研究,后來擴展到滿族史,我受他啟發也做了一些關于滿族與清史方面的研究,不過成果還沒有出版。劉禾是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時候的導師,她的《跨語際實踐》《語際書寫》《帝國的話語政治》還有那本The Freudian Robot在國際上享譽甚廣,就不用我多介紹了。她的課常常會有阿君·阿帕杜萊、阿里夫·德里克、朱迪絲·巴特勒這樣各種學科的名家來做客和交流,跨學科的方法與思想沖擊非常巨大。最后一學期,我給她一門“魯迅與現代中國”的課做助教,由魯迅為基點關聯起政治、歷史、宗教、民俗、民族、性別諸多議題,是個系統而完整的學術訓練。李陀則改變了我的思想取向,有一年多時間,幾乎每個周日下午我都會去哈德遜河邊他家聊天。他屬于述而少作那種批評家,思路敏銳、視野開闊,邏輯嚴謹明晰,跟他對談往往讓人忘記時間,有時候甚至到深夜。他們家中有時沙龍會來馮象、商偉、卡爾·瑞貝卡、高彥頤、于曉丹、林鶴等學者作家,吉光片羽的言詞之中,也受益匪淺。這二位等于讓我重新讀了個博士。
周明全:你身邊大師云集,這和你文章視野開闊是有關聯的。那么,當初你是受誰的影響或者說受哪些書的影響走上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之路的?
劉大先:如同前面所說,我走上文學研究的道路充滿了偶然性,但是有一些啟示般的瞬間確實是某些人與書籍所帶來的。比如我研一的時候在圖書館亂翻書,偶然讀到薩義德的《東方學》,就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由薩義德回溯到福柯,再到法農和尼采,讓我對知識與權力、認知范式與現代學科都有了反省式的認識。到北京后也是機緣巧合,去清華聽過葛兆光和汪暉的課,他們都是偏向思想史的,這些可能當初并非有心的吸納,在后來無意中都會成為批評的滋養。我現在讀的最多的還是關于批判思想和歷史學方面的著作,像詹姆遜、安德森、伊格爾頓、齊澤克、阿蘭·巴迪歐、孔飛力、溝口雄三、柄谷行人這一類的,他們的著作也是國內文學批評學者的案頭書。我在2013年之前雖然已經寫了很多電影方面的評論,但那些都是本能式的寫作,真正開始當代文學批評,其實還是要得益于中國作協和現代文學館提供的客座研究員的機會,讓我進入到一個堪稱全新的領域,結識了一批前輩與同仁,否則可能就會完全是所謂“學院派”的道路了。
應給少數民族文學一席之地
周明全:相對于主流的文學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很滯后,你開始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是和你到民族研究所的工作有關,還是自己的興趣所在?
劉大先:這個確實是因為到民族文學研究所工作才開始的。你們云南還是多民族文化繁榮地區,而我之前的生活環境和教育背景中沒有這一維度,簡直稱得上全然無知。不過隨著接觸的時日愈久,倒是發現少數民族文學確實是個有著廣闊學術生長點的領域。2006年中國作協的《民族文學》改版,葉梅主編敦促我每年做一個創作綜述,這才開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閱讀和評論,此前我都是在做文學理論。
周明全:面對當下大力提倡的政治文化多元一體化與主流文學之間相互影響,我們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姿態和方式去面對少數民族文學?
劉大先:我覺得最根本的是要葆有一顆同情與理解的心靈,而不是因為對它們的“無知”就去“無視”,這種傲慢與偏見由來已久,也是許多現實的文化沖突與民族問題的根源。我們需要正視本土文化內部的多樣性,在“大傳統”之外的各種“小傳統”,它們也許在現代發展路途中是弱勢,但卻不能因此同質化了,這也正是“多元一體”的本義所在。
周明全:不能因“無知”就去“無視”,這個觀點極好,我們現在大多數情況就是對少數民族文學缺乏必要的了解,而導致了對其呈現出的多樣性的忽視。在你看來,少數民族作家應該如何在當下的漢文化語境中,保持自己獨特的民族性呢?
劉大先:我一直以來的觀點就是沒有什么靜止不變的“民族性”,它總是如同奔涌不息的流水一樣,不斷革故鼎新。因為歷史不會終結,少數民族作家同時也是中國作家,也是世界上的某個作家,在目前所面臨的并不是某種片面的“漢文化語境”,而是現代性、消費主義、階層固化、信息與科技爆炸等一系列與漢族和其他國外族群共同的語境。如果我們承認大家都是同時代的人,那么族別的區分就沒有那么重要,盡管少數民族作家可能有其獨特的關注,比如母語的衰落、傳統的式微、認同的轉變等,但這一切都應該超越于某種懷舊主義的感傷與族裔民族主義的憤怒,而進入到更為廣闊的議程之中。作為歷史中人,少數民族作家在哪里,他的“民族性”就在哪里,這個民族性顯然不是某種符號化的印象,而是內化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之中,如果改變必然來臨,那也是歷史理性自然的選擇。
周明全:現在的文學教育,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關注依然不夠,你認為,有必要在現當代文學上加重少數民族文學的比重嗎?
劉大先:很有必要。明全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就是我們的文學教育太多是主流文學史敘述的那種一以貫之的民族-國家范式倒溯式的知識,它們由少數文人化的精英人物與作品組成,平民大眾的內容尤其是邊緣、邊地、邊遠地區的族群文學幾乎是空洞的,如果有也只是插花式的點綴。在這種文學教育里,中國文學的整體傳統其實是被中原、漢文字書寫、精英文士所主導的。在現當代文學中,這種情形尤為明顯,由于殖民文化的附加值,我們的作家、批評家特別熱衷于外國文學尤其是西歐與北美的文學的傳播與頌揚,對于弱小民族國家比如非洲就所知甚少,他們難道是一片空白?本土的少數民族文學處境也是如此,很少出現在文學教育議程之中,而歷史與考古都一再證明,中華文化是“滿天星斗”遍地開花,而不是由某個中心輻射出去全面影響了周邊地區,那些處于無聲狀態的文學也應該有其一席之地。當然,這種文學態勢的形成有著現代文學發生時候的歷史根源,但時移世易,在我們宣傳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當下,是時候反思與清理這套既定的文學觀念與生態構成了。
周明全:我極為贊同你的觀點,我們有必要反思和清理目前的文學觀念,甚至文學史的建構,文學是多樣性、多元化的,不能按照一個單一的標準去評定和建構,人為地抹殺。你覺得當代的少數民族創作整體情況如何?少數民族作家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大先:整體創作情況是作品多、精品少,作家多、大家少,批評乏力,理論陳舊。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要全盤否定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實績,而是希望能夠涌現出類似納博科夫、布羅茨基、勒克萊齊奧、奈保爾那樣出身少數族裔卻改變了英語或法語文學整體格局那樣的能重新構建中文文學生態的少數民族作家。
少數民族作家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三點:一是母語與翻譯文學,中國55個少數民族,共使用100多種語言,許多民族也有著悠久的文字書寫傳統,即便現代漢語規范化以后,蒙、藏、維、哈、朝、彝等民族還有大量母語寫作。民漢文學的相互翻譯顯然不僅包括文本字面的迻譯,同時也是文化與美學的跨文化傳播。翻譯中常常會有對于源語言的歸化,但文學的特異之處恰在于它在核心處的不可譯性,這會將源語言中的差異性文化要素帶入到譯語中,這就帶來了語言的陌生化,無目的而合目的地產生了特有的美學效果。二是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書寫提供了有別于工具理性或市場功利的認知范式,比如伊斯蘭教、藏傳佛教之于穆斯林作家、藏族作家的寫作,更多以彌散性宗教形式存在于各地的各類薩滿教、道教分支、原始信仰(像云南就有白族的本主信仰、納西族的東巴信仰等),在擺脫了“迷信”的污名化后,顯示了在生態、人際關系和環境污染等全球性議題中獨特的參考與借鑒價值。三是少數民族文學攜帶的地域差別,不僅是邊緣目光的轉換,同時也重新繪制了文學地圖。我有專門論述過,就不展開了。
周明全: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作家都使用漢語進行創作,這在作品流通、傳播上肯定是有益的,但你覺得這是否也會導致少數民族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被逐漸抹殺掉?
劉大先:就像巴厘島旅游觀光業的發展反倒帶來了當地族群傳統文化的復興一樣,我覺得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作與自己文化特性的保持并不沖突。人類學上常講“邊界流動,核心穩定”,那些內含于精神與心靈深處的集體記憶、心理積淀、文化內核并沒有那么容易動搖,而能夠被改變的更多是外在的所謂“邊界”部分。假使某一天族別僅僅成為無意義的名詞,那也是民眾自己的選擇,我們也應該尊重歷史。
周明全:你在《文學的共和》的后記里說,“文學的共和”意指通過敞亮“不同”的文學,而最終達到“和”的風貌,是對“和而不同”傳統理念的再詮釋,所謂千燈互照、美美與共;同時也是對“人民共和”到“文學共和”的一個擴展到推演。我不明白的是,文學“共和”了,差異性減少或消失了,文學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劉大先:“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我說的“共和”所要強調的正是差異性的共生,而不是抹殺它們。即我們在保持各種“不同”之間的對話,才能對抗同質化、一體化帶來的活力喪失。“文學共和”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要表達對于不同美學理念、寫作風格、文學觀念差異性的尊重。
周明全:常年在少數民族地區做調查,給你的研究最大的啟示是什么?有什么特別的感受嗎?
劉大先:我抒個情吧,那就是天高地迥、江山無限。薩義德說文學研究要走出“室內游戲”,確實如此。在各種不同族群地方做調查,能夠獲得僅停留在書齋生活所沒有的鮮活體驗,以及對于自身局限性的認知。那種甚至帶有“文化震驚”效應的感受,能夠讓人更加謙卑,也更能激發求知的欲望。
“在時間的審判中,靠的是作品說話”
周明全:總有人說“70后”是被遮蔽的一個群體,其實以我最近的觀察,“70后”批評家的實力是很強的,并非是被遮蔽的一個群體,作為“70后”批評家中最優秀的批評家,你是如何看待所謂的“70后”批評家被遮蔽這一說法?
劉大先:你的觀察沒錯,“70后”確實有一大批實力型批評家,所謂“被遮蔽”可能只是在媒體上沒有那么熱鬧。當他青春,他的嚴肅被上一撥人遮蔽,他的張揚則被下一撥人所淹沒,這可能就是“70后”在大眾媒體時代的尷尬。他們出場的時候,文學從公共文化中退場了,折返到日常、個人、情感、欲望等私領域,而他們還沒有學會迅速適應洶涌而至的市場社會和文學產業化的消費浪潮。在“被遮蔽”的不滿背后是“成名的焦慮”。其實,文學批評本身就是個冷門的行業,再出名也不過是文學圈寥寥數人知道,這個我覺得倒無需介懷,因為最后在時間的審判中,靠的是作品說話,而不是喧囂的口水。
周明全:作為“70后”批評家中的一員,你覺得“70后”批評家這個群體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么?應該如何克服劣勢?
劉大先:“70后”本身是個復雜的星云式存在,他們共有的可能僅僅是出生的物理時間的相似性。當然,這樣說又有些極端,但我實在無法給這群人進行總體性的概括與歸納。從直觀上來說,“70后”成長期正是后文革時代而網絡媒體還沒有大行其道,這至少在兩方面構成了他們的學養積累環境:一方面是崇高意識形態的解體所帶來的對于個人、肉體、欲望、歷史、資本、市場的再認識,但理想主義的殘余依然煥發著微弱的光芒;另一方面是書面閱讀還沒有被碎片式閱讀沖擊得那么厲害,因而體系性的知識和細繹的方法還未被全然侵蝕,這反映在文本層面則是對于宏大命題的關懷,而不是“破碎思想的殘編”。但這樣的直觀感受不具有普遍意義,文學批評終究是個人事業,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每個批評家都有他的個性,優劣得失也是因人而異。
周明全:記得2015年4月,上海作協、北岳文藝出版社等為上海四位年輕批評家召開研討會后的某天,我們在一起喝酒,你說,真羨慕上海的批評家,有組織為他們的出道出力。但據我所知,業內不少人對“80后”批評家的“抱團取暖”式的出場是持批評立場的,你認為,年輕一代的批評家在成長中,外力的作用是否必不可少?年輕一代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出場?
劉大先:上海那次我不在,咱們應該是在呈貢聊到這個的吧。“80后”團體出場的機會,有前輩提攜、有同道切磋,實在是人生幸事:一方面薪火相傳,確實能夠很快進入到話語場域;另一方面“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這也是很好的琢磨互進的機會。不過,有外力助推當然事半功倍,平臺擴大,聲音自然也會放大;但這種機緣并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如果沒有也無需抱怨。說到底,文學研究終究是個體性很強的寂寞事業,而畢竟出場的華麗并不一定代表謝幕的輝煌,就像《紅旗譜》里面朱老忠說的“出水才看兩腿泥”嘛。
周明全:最近不少前輩批評家撰寫文章批評代際問題,你如何看待代際批評的劃分?
劉大先:我覺得代際劃分有利有弊,群體性形象出現容易形成規模和影響,同時也可能會在某種框架中埋沒彼此之間的差別,能夠從中打破山門出來的才是真正強者,畢竟每代人中間總會有鶴立雞群的人物。另外,代際劃分不應該是硬性的時間切割,比如“文革”結束到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無論從生長、教育和傳播環境都更像是一代人。當然,“70后”、“80后”這樣的提法本身有著易于操作的策略性因素在里面,這個無可厚非,就是一種方便的說法,并不構成學理上的意義。
批評家應該具有“匠人精神”
周明全: 當下批評失語、批評失效一直是媒體的熱門話題,你認為這個批評失語、失效了嗎?
劉大先:籠統地談“失語”、“失效”其實沒有意義,是對大的政治變革無效了,還是無法影響到讀者了,還是作家根本不理睬了呢?我覺得很大程度上,這種提法就是一種撒嬌。現象意義上的觀察,可能是批評再也無法像五六十年代批評《武訓傳》、《紅樓夢》那樣能夠引發巨大的政治效應,或者也不可能如同八十年代那樣對于“異化”、“人道主義”、“朦朧詩”、“先鋒小說”那樣能產生大范圍的爭議乃至文化理念和結構上的轉型了。因為許多原本需要通過文學曲折表達的思想與觀念,現在已經在更為寬松的環境中直接言說了。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吊詭的局面,依然掌握著話語通道的批評者失去了話語的權力:如果不掌握話語通道我們甚至連這種關于“失語”的抱怨都聽不到,但是話語權力顯然旁落了,因為絕大部分文學批評無人再當回事了。
這涉及到中國社會近三十年來整體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的變遷,文學在這種大轉型中被“邊緣化”了,但是這種邊緣化其實是文學不再是一種包打天下的普泛性話語,而是分化為社會與學術分科中的一種。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文學本體的“回歸”,向著精細化、技術化、專業化方向發展。與之并行的是,文學批評的同構,出于對庸俗社會學批評和泛政治化的反撥,興起的是“純文學”式的個人主義、犬儒主義、消費主義的“向內轉”式批評,主動放棄了言說重大問題的可能性。雖然它對狹義上的“文學”依然是有效的,但對更廣闊意義上的社會文化的“失語”則是必然的。如果我們要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建立批評的有效性,就要實現它與政治和歷史的對接,這并不是要重蹈某種“工具論”,而是要發明文學的潛力,重新界定批評的邊界和空間,從而有效地介入到當代文化與思想生產的實踐中去。
周明全:你認為文藝和政治應該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劉大先:這個問題關涉重大,真是很難一言以蔽之。不久前,在“中國文學博鰲論壇”上,我曾經對《人民日報》的記者談過這個話題,可以簡單概括一下。文學與政治一直都無法割裂開來,現代以來的文學尤其如此,它本身就是政治的產物。現代中國的主體是個中西融合的主體,文學在民族國家這樣的“想象的共同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與主權國家的規劃與建立密不可分。從19世紀中葉以來,從今文經學到洋務運動、從維新改良到國民革命,中國文學經歷了逐步確定其現代內涵與外延的“政治化”過程。盡管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文學政治化運動過于激進而陷入困境,但是隨后因為新一輪的向歐美學習而導致忽略了更廣闊的全球不平衡問題,導致文學的“去政治化”,后果是個人、肉身與欲望至上彌漫在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話語之中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在全球權重中的上升,文化軟實力的問題擺在議事日程之上,需要我們重提“政治化”,這個政治化不是簡單的、機械的、圖解式的政治化,而是指包含整體性視野、歷史性關懷、現實感的萃取和未來性想象的“新主體性”。如果沒有政治這一維度,那么文學就會淪為一種無足輕重的玩意兒。中國的“傳統”有著自我更新、融合新知、應對時勢嬗變的內在功能,我相信未來的中國文學一定會發生這樣的變局。
周明全:我看你現在經常到外參加各類會議,這樣會否走向你所批判的“表揚家”行列?在人情、作品的價值判斷上,你是否能真正堅持以作品說話?
劉大先:哈哈,你太犀利了。我參加會議算是少的,更多是做田野調查,即便是參加某個作家作品研討會,我也會從學理性的角度找到某個切入點來“六經注我”,而不是被它帶著跑。人情關系與作家價值之間可能產生的落差,是當代文學批評欲說還休的常見問題。我想一個真正嚴肅的作家都不會拒絕善意哪怕是犀利的批評。當然現在有很多作家自我膨脹的厲害,對他們也不必客氣。另外一個方面,我覺得一個研究者不應該懶惰到只讀符合自己審美品位的作品,而應該觀照哪怕從個人情感上來說根本就不喜歡的作品,這樣才能觀察到文學生態現場的全局。我的做法是對那些已經成名的作家本著“春秋責賢者”的態度要求高一些,對那些籍籍無名的作家則盡量發掘他獨特的閃光點予以鼓勵和期待。身在歷史之中,一個當代批評家不可避免要面對的悲劇就是他所解讀與評論的絕大多數作品終究會被歷史淘洗得灰飛煙滅,而他就像那個披沙揀金的工匠,在無數臟雜凌亂的塵屑中,鍛造屬于自己也屬于時間的薔薇。
周明全:我看你在《我們現在需要什么樣的批評》中說,當下的批評家在敗壞這些前輩苦心經營留下的遺產。那在你看來,我們應該如何承襲前輩批評家的遺產,又該如何重建批評的地位呢?
劉大先:凡是在文學史上留下聲名的批評家,都具備廣博的知識、漂亮的文本、與歷史和現實的對話、以及啟發性的一家之言。我們當然要讀他們的著作,但借鑒不等于規行矩步、照貓畫虎,囿于某種批評理念當中無力自拔,而更多的是要繼承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有揚有棄,推陳出新。事實上,任何一個時代的批評者都有自己的對話對象,將他們的文本從其語境中抽離出來作為普世原理來傳承就南轅北轍了。重建當代批評關鍵的問題是找到屬于自己的對話對象,無論這個對象是美學、社會還是政治,都要以自己獨特而不是前人的既有方式去回應對象所提出來的問題。
周明全:你認為好的文學批評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品質?
劉大先:首先它應該是明晰的,有自己的立場與觀點并且能夠將它們清通流暢地傳遞出來,能夠形成讓人愉悅的審美感受。其次,它應該富于真理性的啟發意義,不僅僅是附著于作品或者現象的文本,而是個獨立思想的成果,即便脫離開它的論述對象也具備足夠的參考價值。第三,它還應該具有倫理上的誠實,以其自身的誠懇給人以道德上的教益,是善的流布,而不是惡劣趣味和品德敗壞者的辯護人。
周明全:最后,想請教一下,你覺得一個好的批評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
劉大先:我覺得他應該具有“專業性”,換句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就是所謂“匠人精神”,他要把這個活兒做好,而不是流于普通讀者的感受。這包含的素質是多方面的,諸如敏感的觀察力,不屈不撓的博學,理性清明的洞察,平等公正的善良,同情弱者與抗爭不義的勇氣,將自己的美學目的與判斷付諸于實踐的能力。要有一顆感恩的心,感謝那些曾經默默支持與幫助過自己的人,感謝那些曾經否定與指責過自己的人,因為他們提供了溫情與改進的動力。最重要的是,還要有內在的激情,這種激情使得他不再停留于技術活的層面,而是把批評作為一種體驗生命的方式。
周明全:謝謝大先兄。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