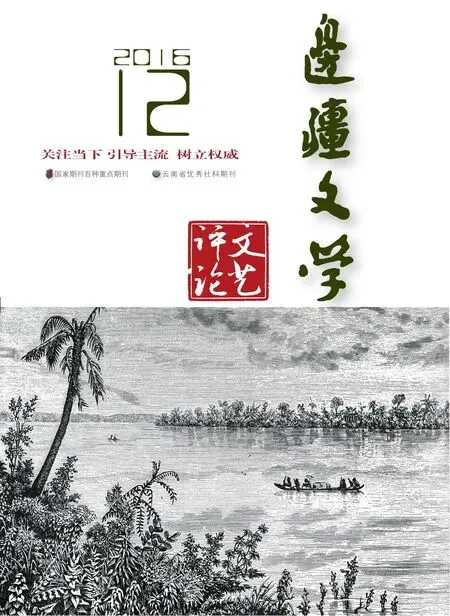紅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觀察(2012—2014)
◎南 馬
紅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觀察(2012—2014)
◎南 馬
紅河少數(shù)民族作家文學(xué)的繁榮發(fā)展已走過(guò)了60多年的歷史。這歷史潮流與全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一樣,有高峰,有低谷;有急流,有險(xiǎn)灘。新世紀(jì)以來(lái),尤其是進(jìn)入第二個(gè)十年,紅河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走出了低谷。
為了敘述的方便,筆者截取了2012—2014三個(gè)創(chuàng)作年度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發(fā)表情況,來(lái)觀察紅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繁榮發(fā)展的態(tài)勢(shì)。
在2012年至2014年三個(gè)創(chuàng)作年度中,紅河州作家有82人次在國(guó)家級(jí)、省級(jí)等二類以上報(bào)刊雜志上發(fā)表了詩(shī)歌、散文、小說(shuō)、報(bào)告文學(xué)(紀(jì)實(shí)文學(xué))、文藝評(píng)論等各類文學(xué)作品227件。這其中,少數(shù)民族作家有42人次,發(fā)表作品116件,分別占總?cè)藬?shù)的51.36%,發(fā)表總量的51.6%。紅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三個(gè)創(chuàng)作年度,成上升走高的態(tài)勢(shì)。在詩(shī)歌、散文、小說(shuō)三大版塊中,形成了三道靚麗的風(fēng)景。
詩(shī)歌高地金聲玉振
詩(shī)歌創(chuàng)作是新時(shí)期以來(lái)紅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強(qiáng)項(xiàng)之一。老一代詩(shī)人從“十年浩劫”的陰霾中掙脫出來(lái),心靈和身體重獲自由后,產(chǎn)生了一大批優(yōu)秀詩(shī)歌作品。上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少數(shù)民族詩(shī)人陳強(qiáng)、哥布、艾吉、莫獨(dú),黃光平、邵春生、普紅茹、朱客伊、蕭崇斌等加盟詩(shī)歌創(chuàng)作隊(duì)伍;90年代以后,又有李軍、李小麥、師立新、李松梅、馬冷莎、陳美仙、冉紅梅、李居斗、陸建輝、春愁、李勇、李紹蕓、藍(lán)狐、李志剛、王橋銀、葉凝、劉清華、釉綿高理等一批新人介入。詩(shī)人們用真摯的情感,執(zhí)著的追求,把詩(shī)人的主體性融于民族的精神時(shí)空,自覺(jué)地匯入時(shí)代大潮,在詩(shī)歌的高地上引吭高歌,金聲玉振,成為紅河州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中流砥柱。
哥布的詩(shī)歌:眾山小處是絕頂。哥布是紅河詩(shī)壇的“先行者”,2013年,其創(chuàng)作業(yè)績(jī)已被收入江蘇文藝社的《中國(guó)文學(xué)通史》。哥布的長(zhǎng)詩(shī)最為出彩。他發(fā)表于《民族文學(xué)》《邊疆文學(xué)》的詩(shī)歌,是長(zhǎng)詩(shī)《神圣的村莊》的一部分,是其代表作之一。該詩(shī)的“絕頂”之一是,既傳承了哈尼族民間“敘事詩(shī)”的藝術(shù)精髓,同時(shí)對(duì)當(dāng)下漢語(yǔ)詩(shī)歌(尤其是敘事長(zhǎng)詩(shī))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一次裂變,一次質(zhì)量的重大提升。在藝術(shù)實(shí)踐上,大膽引入了原生態(tài)審美的現(xiàn)代性審美意識(shí),在傳承民族民間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基礎(chǔ)上,大膽革新,勇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了當(dāng)下敘事長(zhǎng)詩(shī)的人物群形象,張揚(yáng)了敘事長(zhǎng)詩(shī)結(jié)構(gòu)的凹凸美,語(yǔ)言的樸拙美,將敘事長(zhǎng)詩(shī)創(chuàng)作推向了一個(gè)新的高度。
艾吉的詩(shī):山上的石頭也會(huì)唱歌。哈尼族詩(shī)人艾吉這個(gè)“文學(xué)黃埔”出來(lái)的哈尼漢子,用心把故鄉(xiāng)的石頭捂熱了。他的詩(shī)歌《山上》,泉水、石頭、寨子與父老鄉(xiāng)親都自然入詩(shī),榮獲了省政府文學(xué)獎(jiǎng)。《故鄉(xiāng)和家》《老去的母親》《寨神樹(shù)的兒女》《想起我
的故鄉(xiāng)》等,用獨(dú)特的詩(shī)歌意象,把故鄉(xiāng)、家、母親歌唱得如癡如醉,其情之真,意之濃,非“高地”者不可以有此景觀。
莫獨(dú)的散文詩(shī):把故鄉(xiāng)紅河打開(kāi)歌唱。哈尼族詩(shī)人莫獨(dú)自上世紀(jì)九十年代以散文詩(shī)的方式擂扣繆斯的門(mén)扉,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他從《守望村莊》開(kāi)始,通過(guò)《寨門(mén)》《在春天里出門(mén)》,回望《祖?zhèn)鞯拇迩f》,在跨世紀(jì)的20多年的堅(jiān)守與前行中,高舉著散文詩(shī)的大旗,為我們奉獻(xiàn)出了12部散文詩(shī)集。散文詩(shī)集《守望村莊》“清水芙蓉般”(哥布語(yǔ))斬獲了第六屆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駿馬獎(jiǎng)”。從深入稻香之路走來(lái)的莫獨(dú),在藝術(shù)追求上,是一個(gè)變與不變相統(tǒng)一的詩(shī)人。他的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以神性的衣胞故鄉(xiāng)為審美視角,其藝術(shù)風(fēng)格如哈尼梯田的田埂一般,“沒(méi)有一段是平鋪直敘”的。以《祖?zhèn)鞯拇迩f》為總篇名,發(fā)表于《詩(shī)刊》《散文詩(shī)》《山東文學(xué)》的散文詩(shī),凸現(xiàn)了民族文化與民族振興不可割離的普世性價(jià)值。莫獨(dú)的散文詩(shī),意象豐沛,情感篤誠(chéng),影響廣泛,是紅河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散文詩(shī)高地”的占領(lǐng)者和守衛(wèi)者。
黃光平的詩(shī):情迷鄉(xiāng)土。在紅河文學(xué)的詩(shī)歌高地上,黃光平的詩(shī)歌來(lái)源于鄉(xiāng)土,沉迷于鄉(xiāng)土。他自己宣稱:他“寫(xiě)詩(shī)只會(huì)散發(fā)泥土的味道/和汗水落地的聲音,甚至/把心掏出來(lái)掛成草尖上的露珠。”他的詩(shī)歌是真正的鄉(xiāng)土敘事,每首“詩(shī)眼”全扣在與鄉(xiāng)土有關(guān)的意象上——《這片田野盛大如天》《一群白鷺從田野上飛過(guò)》《垂向泥土的鞠躬》《大哥一樣的村莊》等,詩(shī)人從取象、立意到情感的宣泄,審美認(rèn)知的確立,都是建立在大地和泥土之上的。面對(duì)鄉(xiāng)土,情迷得難以自拔,只能把心都掏出來(lái)了!這是其一。 其二,詩(shī)人情迷于鄉(xiāng)土的另類抒情表達(dá),就是對(duì)“母親”的疼。其三,詩(shī)人情迷鄉(xiāng)土的第三視角是對(duì)當(dāng)下鄉(xiāng)村社會(huì)以及城市擴(kuò)張后“準(zhǔn)鄉(xiāng)土”的準(zhǔn)確把握與呈現(xiàn)。
女詩(shī)人李小麥的詩(shī):從網(wǎng)上下來(lái)的淳樸“麥子”。
“70后”末班車出生的彝族女子李小麥,崇尚詩(shī)歌、音樂(lè)和自由。創(chuàng)作詩(shī)歌、散文、小說(shuō)若干,作品見(jiàn)《詩(shī)刊》《邊疆文學(xué)》《云南日?qǐng)?bào)》等刊。她最近的詩(shī)歌先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中飄紅,后來(lái)進(jìn)入報(bào)刊編輯的視野,再到讀者的心中。其詩(shī)醇,醇到“喊我小麥吧”。張紹碧先生曾著文介紹說(shuō):“小麥的一聲呼喊,呼出了滿腔激情,喊開(kāi)了詩(shī)歌的大門(mén)。”于是,小麥以《喊我小麥吧》涌入《云南日?qǐng)?bào)》的“花潮”、健步在《北方》詩(shī)陣、步入詩(shī)歌的殿堂《詩(shī)刊》,在《人民文學(xué)》里徜徉。小麥的詩(shī)被選入《云南詩(shī)選1980-2012》,而且一選就選了10首。其中《種菊花》,入圍“昊龍·第五屆高黎貢文學(xué)節(jié)”詩(shī)歌評(píng)選,一連用了行囊、山巔、山嘴、溪谷、河埂、屋頂?shù)?5個(gè)意象,以排比式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充滿意象力的節(jié)奏,把詩(shī)人追求人間“清清白白”的精神向度推向了“絕頂”。《喊我小麥吧》,是一首轉(zhuǎn)喻與象征二合一的佳構(gòu)。詩(shī)人將“人性”與“詩(shī)性”的回歸疊映在平凡的“小麥”上,簡(jiǎn)單、樸素并溫暖著。其取象之妙,建構(gòu)之巧,露出了“新銳詩(shī)人”的端倪,實(shí)在是云南詩(shī)壇、紅河詩(shī)壇的幸事。
警察出身的彝族詩(shī)人李軍,不斷在滇南的大地上行走。進(jìn)入高鐵和挖掘機(jī)時(shí)代的當(dāng)下中國(guó)城鄉(xiāng),正在上演顛覆與反顛覆的鬧劇。城市化城鎮(zhèn)化的強(qiáng)烈推進(jìn),就是要最終殲滅割據(jù)在城市城鎮(zhèn)周邊那些耿耿于懷而又無(wú)能為力的鄉(xiāng)土。李軍的詩(shī)歌善于捕捉城市化進(jìn)程中人們的深層次感受。作品意象豐潤(rùn),情感豐沛,在紅河州公安文學(xué)中獨(dú)樹(shù)一幟。
新登文壇不久的彝族女詩(shī)人藍(lán)狐,僅在2014年里就先后在二類報(bào)刊中發(fā)表了詩(shī)、散文詩(shī)。其散文詩(shī)中凸顯了一個(gè)有抗?fàn)帲邢<接衷诂F(xiàn)實(shí)中遁入“花事闌珊”的紅粉佳人形象。回族女詩(shī)人春愁把詩(shī)歌的觸須深入到滾滾紅塵里,蕓蕓眾生中,力圖凸現(xiàn)“孤獨(dú)”、“憂愁”的情感態(tài)勢(shì)。布依族女詩(shī)人葉凝的詩(shī)歌向度,是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詩(shī)人看到的是“自不量力”,具有濃烈生態(tài)審美意識(shí),寫(xiě)得生態(tài)、坦蕩,詩(shī)美的空間明麗。
此外,哈尼族詩(shī)人陸建輝,女詩(shī)人李松梅、李紹蕓,傣族詩(shī)人劉清華等人的作品,在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面對(duì)鄉(xiāng)土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現(xiàn)。限于篇幅,此不一一而足。
散文園地群芳爭(zhēng)艷
紅河的散文園地像紅河大地的景色一樣,多姿多彩。作品發(fā)表數(shù)量之多,題材內(nèi)容之廣,作者創(chuàng)作人數(shù)之眾,都是令人喜不自禁的。從50后的哈尼族老
作家諾晗到90后彝族新人陳高位等,老中青都有,創(chuàng)作審美多樣。較有影響力的散文作品,大多出自詩(shī)人、小說(shuō)家之手。黃光平的《布衣聯(lián)圣》,艾吉的《祝福,世界遺產(chǎn)紅河哈尼梯田》,莫獨(dú)的《給母親搬家》榮獲2014年云南省“滇東文學(xué)獎(jiǎng)”。從總體看,紅河少數(shù)民族的散文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群芳爭(zhēng)艷的局面。艾吉、莫獨(dú)、師立新、趙鈺、冷莎、王橋銀、虹玲、黃永臻等作家貢獻(xiàn)較大。
艾吉發(fā)表在《民族文學(xué)》2013年第12期上的《祝福,世界遺產(chǎn)紅河哈尼梯田》,斬獲了由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作家學(xué)會(huì)和該刊聯(lián)合舉辦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作家‘我的中國(guó)夢(mèng)’征文二等獎(jiǎng)”。該文以“散點(diǎn)鋪排式”的藝術(shù)表達(dá)手段,把步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的故鄉(xiāng)哈尼梯田形象聳立在讀者的面前。散文作者的散文創(chuàng)作,必然要涉及到作者的視點(diǎn),站在一定的角度觀察社會(huì)、人生。作者站在不同的視點(diǎn),就會(huì)得出不同的思想感悟,把這些不同的感悟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就能夠形成一個(gè)整體的觀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藝術(shù)地穿插了詩(shī)歌的意象,從而構(gòu)建了散文的意境,這種雜糅的文體,又為“散點(diǎn)鋪排式”散文藝術(shù)思維提供了豐沛的情感空間。文中作者的“散點(diǎn)”,是非邏輯的,各節(jié)內(nèi)容的組合構(gòu)成了立體場(chǎng)域。
同樣是哈尼族的兩棲作家,莫獨(dú)發(fā)表在《散文百家》第9期的《給母親搬家》,算得上是作者的又一散文力作。該文在參加河北省“古貝春杯”第二屆散文大賽中,把一等獎(jiǎng)收入囊中。與艾吉的《祝福,世界遺產(chǎn)紅河哈尼梯田》所不同的是,《給母親搬家》是采用“縱貫”的方式,以為母親“遷墳”這一純民間事件為思維中心物象線索,用“搬家”過(guò)程的一系列的動(dòng)作為珠,串起了“為母親搬家”的整個(gè)行為方式。在具體的行為過(guò)程中,作者把民族文化的精髓熔融其中,形成了新的張力,內(nèi)斂,凝重。
彝族女作家?guī)熈⑿略谌齻€(gè)年度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作品豐收,用散文、詩(shī)歌和評(píng)論的把式反映生活。她的散文力作《彩云之下的神秘王城》發(fā)表于《旅游視野》2013年第10期,以此文榮獲第二屆“散文世界杯”全國(guó)散文獎(jiǎng)。她在彩云之下的孟連,用視覺(jué)、觸覺(jué)、嗅覺(jué)、味覺(jué),甚至“第六感官”,裊娜地為我們獻(xiàn)出神秘王城的韻味。同樣是游記,發(fā)表于《文藝報(bào)》的《飄入大圍山》,把自然景象與人生境界融合在一起,步轉(zhuǎn)景移,文由景生,景因文遠(yuǎn),在視覺(jué)的轉(zhuǎn)換,語(yǔ)言的洗煉上獨(dú)有“立新”的感覺(jué)。
哈尼族作家王橋銀的《作夫村:美在深山待人識(shí)》發(fā)表于《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詩(shī)意龍甲》發(fā)表于《今日民族》。這種以民族文化為底蘊(yùn),以“導(dǎo)游式”為審美節(jié)點(diǎn)的散文,在這幾年的紅河散文創(chuàng)作中不多見(jiàn),該文的成功登上國(guó)家一類報(bào)刊,實(shí)在難能可貴。
生活于邊陲金平的苗族青年女作家虹玲在創(chuàng)作網(wǎng)絡(luò)長(zhǎng)篇小說(shuō)和影視短劇的同時(shí),也涉足短篇小說(shuō)和散文。她的散文《火塘記憶》闖入了《文藝報(bào)》,另一篇散文《公鴨來(lái)來(lái)》在《邊疆文學(xué)》發(fā)表后,2014年被收入《新時(shí)期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作品選集·苗族卷》。
小說(shuō)之舟逆流奮進(jìn)
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豐歉與否,是衡量一個(gè)地區(qū)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標(biāo)尺之一。
新時(shí)期以來(lái),紅河的少數(shù)民族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曾有過(guò)輝煌時(shí)期。回族作家馬明康、王正恩,哈尼族作家艾扎、史軍超、白茫茫,彝族作家戈隆阿弘、蘇世勇等都有長(zhǎng)、中、短篇問(wèn)世。馬明康、艾扎等還獲得過(guò)國(guó)家級(jí)的大獎(jiǎng)。
在2012-2014三個(gè)創(chuàng)作年度中,紅河的少數(shù)民族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沒(méi)有出版過(guò)長(zhǎng)中篇。2012年和2013創(chuàng)作年度在二類以上報(bào)刊發(fā)表的作品為零。2014年度彝族女詩(shī)人李小麥和80后哈尼族新人批娘先后在《滇池》發(fā)表了5個(gè)短篇小說(shuō)。小說(shuō)之舟終于在創(chuàng)作的大潮中逆流奮進(jìn),實(shí)現(xiàn)了零的突破。
李小麥發(fā)表在《滇池》的小說(shuō)《車禍》具有直面現(xiàn)實(shí),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表達(dá)自己對(duì)現(xiàn)實(shí)獨(dú)有的深沉的文化關(guān)懷和生命關(guān)懷的特點(diǎn)。從中,我看到了作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洞察的廣度和深度,開(kāi)掘生活的寬度和生命的深度,進(jìn)而對(duì)人的前途、命運(yùn)本質(zhì)的思考,這就為書(shū)寫(xiě)心曲,思考人生提供了寬廣的空間。故事一波三折,情節(jié)緊湊流暢,細(xì)節(jié)豐沛精準(zhǔn),人物形象鮮明,語(yǔ)言凝練。
批娘,哈尼族,1988年生于綠春縣大山里一個(gè)傳統(tǒng)的哈尼村寨。高二時(shí)發(fā)表作品,高中畢業(yè)進(jìn)入社會(huì)。2014年批娘先后在《滇池》發(fā)表了《普杰和他的母親》《獵人》《生孩子》和《超瑪阿波》4篇小說(shuō)。《滇池》在第9期封面刊出頭像,在頭條集中推出了其小說(shuō)作品。第十一屆“滇池文學(xué)獎(jiǎng)”,《批娘作品》(短篇二篇)獲“提名獎(jiǎng)”。四篇小說(shuō)的敘事,都是建立在民族性、地方性的民族文化之上的。民族的固有文化傳統(tǒng)是民族的血脈,人們不可須臾離之。由于長(zhǎng)時(shí)期的運(yùn)行,文化血脈中浸入了不少的病毒,嚴(yán)重污染了血液,損傷了血管,造成了深刻威脅生命的“血栓”、“腦梗”。如何剔除“血栓”、“腦梗”,化解威脅,還民族一個(gè)健壯的體魄,是許多有良知敢擔(dān)當(dāng)?shù)淖骷覀兊淖非蟆E锏乃钠≌f(shuō)切入的都是這方面的主題。《滇池》在發(fā)表小說(shuō)時(shí)以《哈尼族生活的神奇敘事》為題進(jìn)行了扼要評(píng)論。
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小說(shuō)以少數(shù)民族生活的所謂“神奇”展開(kāi)敘事,需要把握好節(jié)點(diǎn)。從時(shí)代發(fā)展的角度看,當(dāng)今的中國(guó)社會(huì)已經(jīng)進(jìn)入了“高鐵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城鎮(zhèn)化、城市化、網(wǎng)絡(luò)化、信息化早已浸入了人們的機(jī)體,席卷并俘虜了大面積的鄉(xiāng)村,人們的日常生活幾無(wú)秘密可言,更遑論“神奇”了。其實(shí),這種所謂的“神奇敘事”,早在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哈尼族作家艾扎在其長(zhǎng)篇小說(shuō)《閹谷》,中短篇小說(shuō)集《紅河水從這里流過(guò)》等篇什中就有過(guò)較為精彩的書(shū)寫(xiě)了。批娘的這四篇小說(shuō)在時(shí)代背景上顯然不是哈尼族過(guò)往的歷史書(shū)寫(xiě),而是當(dāng)下社會(huì)生活的某個(gè)側(cè)面進(jìn)入。但挖掘的還不夠深,文而不夠“化”,甚而有展示題材之嫌。小說(shuō)不僅僅是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文化呈現(xiàn),更重要的是要讓讀者看到、感受到“神奇”生活背后人的美好追求。
(作者系云南省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
責(zé)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