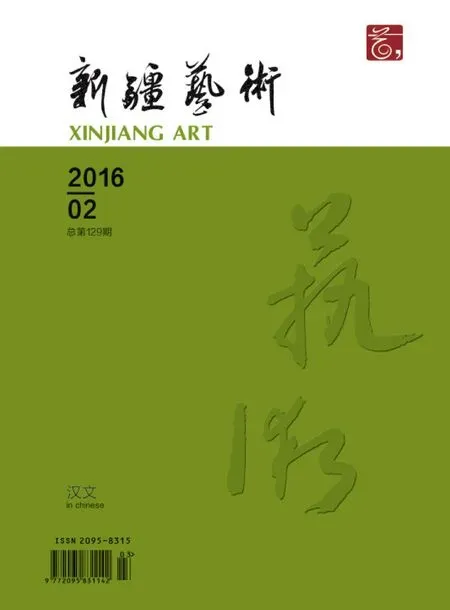關于斯布孜額的一次重要爭辯
——摩登楚吾爾與斯布孜額研究之二
□ 祁大慧
2012年我的《此曲只應天上有——喬龍巴特的摩登楚吾爾音樂藝術》一文,先后在《中國竹笛》《西部》《西域文化》等刊物上刊出,引起關注。我于2014年又幾次赴阿勒泰地區,進行了進一步實地考察,并多方查閱資料,撰寫了《草原喉簫——摩登楚吾爾與斯布孜額研究》(見《中國竹笛》2015年第 2期、《新疆藝術》2015年第1期),明確提出了我的觀點:

新疆圖瓦老人額爾德什演奏“摩登楚吾爾”(孫偉 攝)
一、摩登楚吾爾和斯布孜額是同一種樂器,它廣泛流傳于北方各游牧民族中。蒙古族稱其為摩登楚吾爾(筆者注:不能簡化為楚吾爾等),哈薩克族稱其為斯布孜額,柯爾克孜族稱其為卻奧爾,在蒙古國和都瓦共和國等都有流傳,名稱不同而已。
二、至少在學術界,應該將這一樂器統一定名為“草原喉簫”,以便于書記和研究。
三、摩登楚吾爾和斯布孜額等名稱仍可沿用,它體現了這種樂器在不同民族間形成的不同風格流派。
但是,很多問題仍難以釋懷。尤其被廣泛用來作證的說《突厥語大辭典》中有對斯布孜額的記載這一史料,原文到底怎么寫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那個精美的與古琴有相同音律的樂器(“綠琴翻出音律同”),真的就是摩登楚吾爾或者斯布孜額嗎?查遍了互聯網和紙質資料,皆找不到解答。倒是在本人還未調入前的《新疆藝術》雜志上,意外看到了周菁葆先生透露的一個消息,說有位專家告訴他,《突厥語大辭典》上根本就沒提過斯布孜額!周菁葆先生是著名的西域音樂藝術研究學者,著有《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等重要著作,他這篇文章是反駁王曾婉的。王曾婉是中國音樂家協會西域音樂研究專家。這兩個重量級的人物爭論的又恰好就是斯布孜額!
登載這兩篇文章時,雙月刊《新疆藝術》還處于草創期,留世刊物很少,那時還沒有電子版,所以這次爭辯幾乎無人知曉。因此,很有必要把這次爭辯的內容重新公布于世。況且,即便今天看來,這仍然是關于斯布孜額的一次重要爭辯。
一、王曾婉的《漢代胡笳與斯布孜額》
王曾婉的《漢代胡笳與斯布孜額》一文(以下簡稱王文)約6000字,刊載于《新疆藝術》1983年第6期。王文由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化藝術“曾給中原漢民族的文化以深遠的影響”出發,“聯想到我國漢代女詩人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從而提出論題:蔡文姬的胡笳“究竟是哪一種笳?它至今存在于我國那一個民族之中?”
王文的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根據《唐宋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史料分析,笳是多種吹管樂器的統稱,并歸納出五種類型:“第一種為卷蘆葉而吹之的;第二種是狀似篳篥而無孔的;第三種是管身長用以泛吹的;第四種則是用于鼓吹樂隊中的笳。”
(二)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胡笳屬第三種,即“管身長以泛吹的”笳,可吹五音,與古琴同音律,“具有完備的樂器形式與性能,并善奏哀音的優美的胡笳。”
(三)通過《說文》《辭源》《辭海》《風俗通》等典籍,考證了笳的制作材料“葮”與“箛”:“葮,通笳。”“葮,葦之未秀者。從草,段聲。”而古“箛”音姑,多年生草本。菰與箛混用,“箛者,吹鞭也,從竹,孤聲”說明笳的制作材料即蘆葦和竹子。并推斷“笳字大約在唐以后才普遍使用”。
(四)根據《與太子書》中對一位十四歲少年吹奏胡笳的描繪(注意!王文認定是吹胡笳而不是唱歌——筆者注),認為其演奏法的主要特征是:“喉囀引聲,與笳同音”,“喉所發音無不響應”。“笳在吹奏時是有兩個聲音,即喉音和笳音同時發音。”最后作者下結論說:“根據以上這些記載,今哈薩克族吹管樂器——斯布孜額,在原料、形制、音階、音律、音量、音色、演奏法以及相似的樂曲等方面,與胡笳幾乎完全相同。”作者還提供了烏魯木齊縣板房溝公社社員代依力汗·塔依阿合帕木演奏的三首斯布孜額樂曲《綁著的棗騮馬》《額爾齊斯河的波浪》《思念》的五線譜例,還提到現存于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布爾津縣牧民依曼拜克的演奏錄音,還提到《突厥語大詞典》關于斯布孜額的記載。最后,王文還順便對日本學者林謙三關于漢代胡笳早已失傳這一斷言進行了反駁與否定。
二、周菁葆《斯布孜額是漢代胡笳嗎?——與王曾婉同志商榷》
周菁葆《斯布孜額是漢代胡笳嗎?——與王曾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簡稱周文),發表于《新疆藝術》1984年第3期,約5500字。
周文開宗明義宣稱王文“立論不能成立”,說王文“一是對引用文獻缺乏研究;二是筆錄有誤;三是對史料的理解不確切”。并從以下三方面對王文進行反駁。

年輕的“摩登楚吾爾”演奏藝人
(一)王文“之所以認為斯布孜額是漢代胡笳,是因為胡笳‘喉囀引聲’、‘喉所發音無不響應’的演奏法類似斯布孜額。”實則魏繁《與文帝箋》(筆者注:即王文所說魏繁欽《與太子書》?)中明明還有一個唱歌的人——溫胡,明明“是指孩童的歌聲與溫胡(可能是一個胡人)所唱相互呼應。哪里是指什么胡笳的演奏法?王文得出‘喉音和笳音同時發音’的結論從何而來?難道‘與笳同音’可以理解成為同時發音?這里應該特別指出,古代文獻中根本沒有‘喉音和笳音同時發音’的記載。”
(二)漢代胡笳早已失傳。“《北堂書鈔》是我國現有最早的漢族類書,但其中對漢代胡笳的形制毫無敘述。宋代《樂書》中雖有圖示,但說的是唐宋胡笳的形制,并非漢代胡笳。”“因此我們說,漢代匈奴人使用的胡笳是長型還是短形,是有孔還是無孔,目前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說明。”“從形制上看,唐宋胡笳均是一種雙簧吹奏的無孔樂器,但現今斯布孜額是長管、有孔,與古代胡笳根本不一致。”“胡笳制作的原料中有蘆葉、羊角、羊骨、竹管。然現今斯布孜額用木制,葦管,與古代胡笳并不一樣。”
三、相關史料對斯布孜額的解釋
(一)“關于胡笳,日本學者林謙三先生早有考證,他認為漢代胡笳早已失傳。對此筆者完全贊同,斯布孜額與漢代胡笳無從聯系。”
(二)“根據新疆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校仲彝先生告知,1959年出版的土耳其文和1960年出版的烏茲別克文的《突厥語大辭典》中,根本沒有斯布孜額的名稱。新近出版的維吾爾文版中也沒有斯布孜額的稱謂。至于‘胡笳’則更不見記載。”“王文中說斯布孜額在《突厥語大辭典》中‘解釋為一種笛子’,實際情況是辭典中只有關于笛子的記載,根本沒有什么斯布孜額的解釋。”
(三)“翻檢古代文獻,只有清《皇朝禮器圖式》中的胡笳與斯布孜額有某些相同之處。這說明,斯布孜額的歷史不可能上溯到漢代。直到宋代尚未出現。《樂書》和成書于十一世紀的《突厥語大辭典》中沒有斯布孜額的記載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四、爭辯的意義
(一)一切正規的書寫,尤其是學術著述,都應充分重視以往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尊重定論。對尚無定論的問題,要尊重不同學術觀點的存在,不能以偏概全和恣意取舍。如摩登楚吾爾不能等同于楚吾爾,就是一例。又如,對《突厥語大辭典》有關于斯布孜額的記載這一史料,人云亦云,廣泛引用,卻鮮見對其認真考證者,更是突出一例。
(二)不言而喻,斯布孜額不是漢胡笳,二者不能等同。林謙三說漢胡笳已經失傳,周菁葆“完全贊同”;王曾婉說漢胡笳就是斯布孜額,它“千百年來仍保持著原始的風貌”,三人兩種觀點,也許都過于絕對了,而且,都忽略了自己熟知的一個常識——所謂胡笳,是一類吹管樂器的總稱,不可能都失傳。像對待其它事物一樣,我們對這一民間樂器應當持一種發展的、演變的眼光,說得相對寬泛一點,說斯布孜額有漢胡笳的遺傳基因,是由漢胡笳演變而來的一種屬于胡笳類的民間樂器,就可能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即是漢胡笳類的那件與斯布孜額最相似的樂器真的失傳了,類似的樂器肯定會誕生。猶如說尺八在中國失傳了,只有日本才有,筆者未探究也不相信。在民間肯定有與尺八相近的、各種形態樂器的存在。我們的所謂的短簫,難道和尺八沒有關系嗎?在我國西南一些少數民族中,也可見到它的蹤影。此不贅述。
(三)周菁葆對兩條重要史料的解讀,對胡笳和斯布孜額研究來說,無疑具有根本性、顛覆性的意義。首先就是《與文帝箋》中的那段話。

胡笳——蒙古族樂器
為使讀者掌握原文,現抄錄如下:
“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至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
繁欽(?—218),與建安七子齊名的鄴下文士之一,曾為曹操主簿。繁欽《與魏文帝牋》最早見于《文選》卷四十。此后唐代的《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和宋代的《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三也有收錄。《藝文類聚》題作《繁欽與魏太子箋》,(箋同牋。筆者注)《太平御覽》則作《繁欽箋魏文帝》,與《文選》的篇題相似。至清代嚴可均輯《全后漢文》,亦輯入此篇于該書九十三卷,改稱為《與魏太子箋》,同于《藝文類聚》而異于《太平御覽》。
如此鄭重介紹,蓋因此文此段話在研究胡笳和斯布孜額中至關重要。王曾婉和周菁葆的爭辯就由它而起。
王曾婉認為,這段話是專寫胡笳演奏法的。“喉囀引聲,與笳同音”,“喉所發音,無不響應”,“這說明胡笳在吹奏時是有兩個聲音,即喉音和笳音同時發音。”并進而推斷,今斯布孜額“與胡笳幾乎完全相同”。
而周菁葆卻認為,這段話根本不是寫吹奏樂器而是寫歌唱的。“古文獻中分明是說,一位十四歲的兒童善歌……‘喉囀引聲’是指孩童的歌唱,哪有王文中所說的‘善吹胡笳’?文獻中云‘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是指孩童的歌聲與溫胡(可能是一個胡人)所唱相互呼應。哪里是指什么胡笳的演奏法?王文得出‘喉音與笳音同時發音’的結論從何而來?難道‘與笳同音’可以理解為同時發音?這里應該特別指出,古代文獻中根本沒有‘喉音和笳音同時發音’的記載。”
王文說這是在寫吹笳,周文說這是在寫歌唱,而且是二人合唱!
中國古文本來就難弄,繁欽這位大文豪可能又賣了些關子,搞得后來人打文字官司。如果那位十四歲少年是呼麥歌唱家,那‘與笳同音’和‘聲悲舊笳’就只能這樣解釋了:少年的歌唱深沉渾厚得如同胡笳吹奏出的聲音一樣。或者是:少年的歌唱與伴奏的胡笳十分和諧。總之,除了要搞清楚那位少年到底是在唱歌呢還是在吹樂器,還要搞清楚胡笳在這段文字中的角色:主角?配角?或只是個比喻?
第二條史料即《突厥語大辭典》。
“十一世紀成書的《突厥語大辭典》將斯布孜額解釋為‘一種笛子’。由此可見,在此之前斯布孜額就已經出現并流傳民間了。”
這與其說是一條史料,不如說就是一種說法。《突厥語大辭典》中有關原文到底什么樣?到底有沒有斯布孜額這個詞?筆者至今沒有查到。但大家都在引用,而且基本就都這一句話,真真是人云亦云!
周菁葆說:“據新疆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校仲彜先生告知,1959年出版的烏茲別克文的《突厥語大辭典》中根本沒有斯布孜額的名稱。新近出版的維吾爾語版中也沒有斯布孜額的稱謂。至于‘胡笳’則更不見記載。”“王文說斯布孜額在《突厥語大辭典》中‘解釋為一種笛子’,實際情況是辭典中只有關于笛子的記載,根本沒有什么斯布孜額的解釋。”
校仲彝先生的話應該是可信的。但畢竟是周箐葆聽說的。并且,也并沒有說到《突厥語大詞典》的維吾爾文版、中文版等相關情況。“百度”《突厥語大詞典》中文版“斯布孜額”,出現的唯一一段相關文字,還是有關布爾津縣哈德勒別克·好安制作和吹奏斯布孜額的情況簡介。這位好安我曾重點采訪過,他是自治區級斯布孜額傳承人,退休教師,在斯布孜額名藝人中,算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好安也并沒有親自查閱過《突厥語大詞典》中關于斯布孜額的文字。那么,“百度”斯布孜額為什么又回到這里了呢?就是因為阿勒泰新聞網作者哈那提在這段三五百字的簡介中,也沒有忘記重點引用這句話:“十一世紀成書的《突厥語大詞典》將斯布孜額解釋為‘一種笛子’”。看!又是這句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話在糊弄人。這就如同貓兒咬著自己的尾巴轉圈子,一個怪圈,轉多少圈都沒結果。
周菁葆對這條史料的否定是令人信服的。對類似這樣一些重要史料的仔細甄別,不僅對相關課題的研究至關重要,也有利于匡正學風!
(本文圖片由孫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