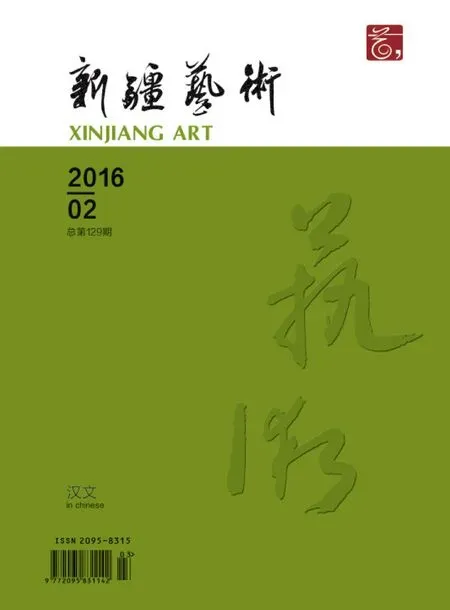淺論新疆少數民族戲劇表演
□ 周建國

哈薩克族的阿尤畢(熊舞)
戲劇的本質特征是演員的當眾表演。演員是戲劇的心臟和靈魂。演員以現場表演的方式,直接把戲劇活動和觀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使之與電影、電視等其他影像藝術相區別。只有當男女演員登臺獻藝的時候,劇本上的對話、劇作家創造的性格,以及布景、服裝、道具等等才獲得了生命。演員既是創作對象,又是創作本體。既是要創作的人物,又是創作人物的創作者、工具。所以演員的表演的確是一個復雜的勞動過程。新疆少數民族表演藝術中扮演角色的戲劇性質的表演,在維吾爾族麥西熱甫的小品小戲里、哈薩克族的阿尤畢(熊舞)、蒙古族的“跳布扎”里就有了。而作為戲劇表演藝術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成熟的戲劇形式出現以后才逐漸形成的。新中國成立之后,建立了正規的戲劇藝術院校,造就了眾多戲劇表演專門人才。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之后,由于思想的解放,視野的開闊,戲劇品種、風格的豐富,專業教育和藝術實踐的積累,各民族戲劇特別是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族戲劇都有極大提高,戲劇表演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縱觀新疆少數民族戲劇表演,我認為大體可以分為話劇式表演和歌舞式表演兩類。話劇式表演是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驗派”表演方法為基礎,從分析、體驗角色的性格、心理活動出發,結合本民族語言的特點和生活中動作的特點、并且按照舞臺藝術的要求而將角色彼時彼地的性格、心理在舞臺上表現出來;歌舞式表演的基礎也是分析、體驗角色的性格、心理,離開這個就沒有人物、沒有戲劇了,但在表演中融入了歌唱、舞蹈或載歌載舞的表演形式,這也是與能歌善舞的民族特點和生活方式緊密關聯的,是新疆少數民族戲劇表演的顯著特色之一。而這兩種表演形式在劇目中的運用又是靈活的,變化的,側重各有不同的,既具有鮮明民族性、時代性,又具有開放的、與時俱進的品格。
一、話劇式表演
話劇式表演主要指在話劇中的表演,以及歌劇中的有些表演。這種表演的特點是,演員依靠語言(獨白、對白、旁白)、形體動作、面部表情來刻畫人物之間的愛恨情仇,表達喜怒哀樂的感情,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它要求語言、動作的準確、明晰、生動,富有藝術性和感染力。話劇式表演在我國,演員主要接受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訓練演員的方式,所謂“體驗派”表演。它要求演員在深入理解和體驗劇本角色基礎上,從自我出發,設身處地地徹底化身為角色,在舞臺上,在角色的生活環境中,和角色完全一樣合乎邏輯地、有順序地去說話、去動作,去表達角色的思想、訴求、感情,和角色同樣地去感覺。演員的內心體驗越深,入戲越徹底,越能排除臺下的干擾,一心進入角色創造之中。
維吾爾族話劇《努爾太阿吉的故事》序幕寫努爾太阿吉6歲時,他家剛從城里遷到鄉下,房子漏雨,他媽媽阿依夏姆汗上房修補房頂,不懷好意的公社社長阿西木罵她是地主婆,讓她去積肥。阿依夏姆汗從梯子滑下來摔傷了,阿西木趁機要扶她,貼近她,她撥開他的手,走到旁邊。阿西木走近她,威脅說:“你今天非上工不可!我們就是這樣來改造你!”又假惺惺問道:“你小腿沒事吧?這兒不疼吧?”用手摸阿依夏姆汗的腿。她奮力掙扎,說:“別這樣,別碰我,阿西木阿洪。離我遠一點!”阿西木死皮賴臉地撫摸她:“不要這么厲害嘛!你已經是生過六個孩子的老婆子啦,我這樣關心你,你應該高興才是啊!”阿依夏姆汗抗拒,兩人廝打起來。她厲聲說:“滾開!別碰我!誰也休想碰我一手指頭!放開我!”她躲藏,逃開,阿西木追趕,又把她抱住。這時,努爾太手持鋼叉,邊跑邊大聲喊:“不要臉的阿西木,放開我媽媽!我要殺了你!”把鋼叉戳進阿西木的屁股。阿西木叫了一聲,放開阿依夏姆汗,對努爾太罵道:“你個該死的孤兒,我要擰斷你的脖子!”就撲向努爾太。阿依夏姆汗沖向努爾太,奪過鋼叉,對著阿西木喊道:“不要碰我兒子!不要靠近他!”逼得阿西木面對怒目圓睜的阿依夏姆汗,步步后退。這場戲,就完全是通過對話和動作、表情表現人物之間緊張的關系。對話富有感情,情勢緊張,內心活動和外形動作都很強烈,很有戲劇性和感染力。
歌劇以歌唱為主,也常有話劇式對白,但比話劇對白更精煉,富有詩意。在這一點上,新疆民族歌劇不同于西方歌劇的無有對白,完全靠唱。歌劇《帕爾哈特與西琳》有一場戲,寫巫婆奉赫斯魯之命毒死帕爾哈特,就主要靠獨白、對白和表演動作刻畫了巫婆的狠毒:崇山峻嶺中,巫婆彎腰駝背緩緩走來,陰險的目光四處張望。為了引來帕爾哈特,她凄厲地叫著“奧,公主!公主!”帕爾哈特聞聲匆匆跑來,問她為何呼喚?狡猾的巫婆瞪起驚恐的眼睛,神情夸張地說:“暴君赫斯魯帶兵搶占了米科利巴奴的國家,血洗城池,妄想娶西琳為妻,西琳忍無可忍……”帕爾哈特信以為真,急不可耐地追問:“到底怎么啦?”巫婆故意停頓片刻,做出不忍訴說、不勝悲痛之狀,垂下頭來,悲悲切切地說:“據說西琳因不愿嫁給赫斯魯而服毒身亡,還有人說西琳因思念你而一命歸天。”這些謊話像霹靂一樣擊碎了帕爾哈特的心。他痛苦不堪地叫著西琳的名字,雙手向著西琳的方向高高舉起,仿佛要把西琳攬在懷里,步履踉蹌地昏倒在地上。巫婆見狀,竊自心喜。她露出狠毒的目光,盤算著心計:“要徹底除掉帕爾哈特!”她端來一碗放了毒藥的水,挾起昏迷的帕爾哈特,把藥灌入他的口中。帕爾哈特從疼痛中醒來,知已上當,大喊“啊,西琳!”隨后便咽了氣。巫婆的臉上浮起冷酷的笑容,慌忙去找赫斯魯國王領賞。這是在歌劇中運用話劇式的對話和表演動作來塑造人物的成功例子。

維吾爾劇《帕爾哈特與西琳》劇照
哈薩克族歌劇《薩里哈與薩曼》主要通過歌唱來刻畫人物性格、表現人物關系的變化,但是也有對話用以交代情節、介紹人物,例如第四場,士兵抓來了騎馬人、女扮男裝的薩里哈的女伴托恩,黑熊摔跤手向鐵木爾報告“人已抓到,請你審問。”鐵木爾問托恩“你是什么人,跑進這荒山野林?假如你不說實話,就叫你一命歸陰。”以及托恩的回答、鐵木爾信以為真這段戲,都是由對話完成的。
話劇式的表演中還有一種喜劇場面的表演,是不同于正劇的。它要求語言和動作的幽默、俏皮、夸張、對比、滑稽、誤會等各種插科打諢的手法,引起觀眾的“笑”,無論是大笑、竊笑、善意的笑還是嘲諷的笑等等,這種劇場效果在接受美學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李漁在《閑情偶記·科諢》中稱之為提振觀眾情緒的“人參湯。”維吾爾族戲劇中這樣的場面很多。歌劇《古蘭木罕》中反面角色安蓋及其打手的丑態百出,話劇《奇妙的婚禮》里堅持“近親結婚、親上加親”的薩迪爾和阿依斯汗作為被嘲笑、批判的對象,都有這樣喜劇性的表演。這種性質的表演的安排,承繼了維吾爾的民族性格,是其戲劇的一個顯著亮點。
二、歌舞式表演

維吾爾劇《《蘊倩姆》》劇照
(1)在維吾爾族戲劇中,有一種形式被稱為“音樂話劇”,它以話劇通常的表演形式為主要手段,又插入歌唱和舞蹈,使之手段多樣,形式活潑,具有民族特色。而歌、舞的篇幅較之歌劇又少。這種表演形式,1942年創作的音樂話劇《蘊倩姆》即開始采用,因為觀眾樂意接受,“文革”后仍延續了這種表演方法。有一段戲寫努若木與蘊倩姆相遇、兩人一見鐘情,就主要通過歌唱和舞蹈來表現。努若木在花園一邊掄著坎土曼干活,一邊唱起了動聽的情歌:“杜鵑落在白楊樹上,見到戀人燒在心上。”蘊倩姆坐在南瓜架下,為歌聲所陶醉。她想把努若木叫到身邊,可是少女的羞澀使她不便開口。努若木似乎猜出了她的心思,便來到她的身邊:“你有話對我說嗎?”蘊倩姆把都塔爾琴遞給努若木:“好久沒有聽到你唱歌了,很想聽聽你的歌。”努若木提出:“如果你跳舞,我就為你唱歌。”于是蘊倩姆跳起了輕盈的“伊犁賽乃姆”,努若木也彈起了都它爾,唱起了情歌。當唱到“戀人的園中有百合花,不知她心中是否有我”時,蘊倩姆驟然停下舞蹈,皺起眉頭,噘起了小嘴。努若木沉浸在歌詞的情緒中難以自拔。當他猛地看見蘊倩姆的表情,他懵愣了,來到蘊倩姆身邊問道:“怎么啦?”蘊倩姆直視努若木,因愛不被理解痛苦不堪,說:“為要證明我的情意,非要把我的心掏出來嗎?”努若木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暗暗高興。其實,他剛才就是用民歌來試探蘊倩姆,但現在他卻以“這是民歌呀”為自己狡辯。蘊倩姆追問:“那你為什么對我唱?”努若木只好用玩笑的口吻坦率地說:“為了愛情嘛。”蘊倩姆羞得遮住臉,繼而舀起水來向努若木潑灑。努若木興致大發,迎著水簾去追趕蘊倩姆,兩人陶醉在初戀的喜悅之中。新疆歌劇團的男女主角在表演這段戲時,把話劇表演與歌舞表演有機地、自然地銜結起來,尤其在歌舞中表現他們之間互相試探、欲說又止,到最后表露真情,都演得層次分明,細膩傳神,盡顯了兩種表演形式的妙處。
(2)在歌劇當中,話劇式的表演雖然也有,但已不是主要的表演形式了。歌劇中的主要表演形式主要是歌唱、還有舞蹈、載歌載舞以及和表演動作的結合。歌唱與動作結合的表演形式是很多的。巴州歌舞團的蒙古族歌劇《魂系東歸路》寫土爾扈特部落東歸故事,沙俄要塞司令的女兒芙麗婭面對愛人要東歸,而她又不忍遠離父親,在這兩難抉擇時,有一段重頭唱段《留下吧我的親人》,運用了俄羅斯七聲“6”小調,委婉纏綿,起伏跌宕,唱盡了她痛苦的矛盾心理。哈薩克族歌劇《薩里哈與薩曼》第七場薩里哈的夢境:她與薩曼坐在秋千上,姑娘、小伙子簇擁著他們,這時,既有年青人歡樂的合唱,也有薩里哈與薩曼的對唱、二重唱,表現了薩里哈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幸福愛情的憧憬。
《艾里甫與賽乃姆》是維吾爾族一部演出時間最長、最有代表性的歌劇,1979年演出版在編導和表演上都達到了新的水平。這時的主演是艾坦木·玉賽因和瑪依拉·扎克爾,他們既擅表演,兼有一副好嗓子,就發揮所長,在第二幕第二場主要通過對唱、獨唱和形體動作,表現一對戀人生離死別的悲痛心情。幕啟,舞臺上是有著民族特色的城樓和街市,吆買呼賣,人頭攢動。幾聲沉重的鑼聲過后,喧鬧聲止,趨于平靜。艾里甫在宮廷衛士押解之下,身披枷鎖走出城門。稍頃,定神,亮相。然后緩步向前,凝視遠方,向舞臺中心邊走邊唱:“愛情的傷口流淌著鮮血,枷鎖沉重我步履艱辛。賽乃姆在悲切中嗚咽,貓頭鷹在詛咒這人間的不平。”蒼勁渾厚的歌聲和樸實無華的表演,抒發了艾里甫對賽乃姆的眷戀之情和對人間不平的義憤。當賽乃姆突然出現在城樓上,大聲叫著“艾里甫江”時,舞臺氣氛和舞臺節奏急劇發展。艾里甫一反舉步沉重的節奏,倏然轉身,疾步向前,撲向被困在角樓上的賽乃姆,卻被衛士阻擋;賽乃姆也悲痛欲絕,俯身,張開雙臂,恨不得撲進艾里甫的懷抱。這對難分難舍的戀人,一個俯身向下,一個翹首向上,中間有衛士阻擋,舞臺上籠罩著一片令人心碎的無奈氣氛。這時,賽乃姆含淚唱道:“賽乃姆等你,直到人老珠黃,縱然一死,我也要等在大路旁。艾里甫,我至死不渝,堅貞不二,何時啊,你才能返回故鄉。”艾里甫接唱:“只要我不永羈他鄉,死神沒有降落在我身上。只要我頭顱不遺棄在戈壁上,我會回來的,你切莫悲傷。”歌聲如泣如訴。賽乃姆因過分悲傷暈倒在角樓上。艾里甫急欲向前,被衛士驅趕,欲進不能,只得后退,仰望角樓,無奈,轉身向眾鄉親行禮告別。鄉親還禮,祝他一路平安。艾里甫走了兩步,轉身,用憂郁的目光搜尋角樓,慢步后退。衛士推他快走。他沉重地移動兩步,再次轉身,盯著角樓,尋找賽乃姆。當他被衛士推搡著將下場時,賽乃姆蘇醒,重立角樓,眼看艾里甫就要遠去,她伸出雙臂,凄聲呼喊:“艾里甫江!”大幕緩緩落下。這段表現兩人“離別”的戲就主要通過歌唱和緩步、疾步、后退、轉身、俯身等動作,揭示人物的內心波瀾。凄楚的木卡姆音樂,更增添了人物哀婉的感情色彩。
單純的舞蹈動作在歌劇中的運用并不多,一種是作為烘托氣氛的群舞,例如為了表現宮廷奢華生活而設計的宮女們的風格性舞蹈,或是為了展現民族文化特色、典型環境而設計的舞蹈,例如《魂系東歸路》里的《馬刀舞》《婚禮舞》;一種是主人公的或者眾人的有節奏、有動律的武打動作。在戲曲的“唱念做打”里,“打”是包括“舞蹈”的。這樣的打斗形式的“舞蹈”在舞臺常可見到。《艾里甫與賽乃姆》里有艾里甫與阿布拉夏特的決斗,《薩里哈與薩曼》里有薩曼與鐵木爾的摔跤、揮劍格斗。而作為刻畫人物、烘托環境氣氛的重要手段之一,歌劇里的舞蹈是常與歌唱結合的,形成了“載歌載舞”的表演形式。歌為心聲,舞為神形,二者相得益彰,相映生輝,使觀眾在清晰明了角色動機的同時,又欣賞到它浪漫的、超自然的、美妍的舞蹈形象,得到聽覺視覺的雙重滿足。在實際運用中,這種形式有時表現為集體的載歌載舞的形式。這時的歌唱或是由臺上演員擔當,或是由幕后伴唱參與其中。《薩里哈與薩曼》里在薩里哈的夢境中出現了婚禮的場景,這場戲都是在歌舞中完成的。先是男女青年的載歌載舞,“樹木要算柳樹枝最柔韌,守夜最熱鬧是管馬群(后略)”“矮山上的冰草長不高,吃冰草的馬兒長得好(后略)。”接著就是哈薩克婚禮上的程式性男女對唱“加爾加爾”和“揭面紗歌”,這些歌唱都是在舞蹈中進行的。這種設計,不僅展示了民族風俗、特色文化的畫卷,而且更重要的往往是起到了節奏變換、情緒對比的作用。在這樣的場景中,有時出現主人公,但也不是凸顯其性格的主要場面。
優秀的編導是不會忘記為主人公專門設計載歌載舞的場景的。這應視作少數民族歌劇的新穎之處。維吾爾族歌劇《熱比婭與賽丁》有一場戲,寫熱比婭的父親拒絕了賽丁的求婚之后,兩青年偷偷幽會,私定終身。這段戲里,他倆以一塊腰巾為道具,載歌載舞,歌舞并重,顯示了編導的獨具匠心:凌晨人們還在夢鄉,賽丁來到熱比婭院內,把熱瓦甫掛在廊柱上,把葡萄干緊包在熱比婭為他繡的手絹里,放在炕上。熱比婭憂郁地來到院里,看到炕上熟悉的手絹,立即拿起緊緊貼在胸口,激動萬分:她的賽丁來了。她環顧四周,看到廊柱上的熱瓦甫,跑過去,取下來,久久端詳著,仿佛賽丁就在眼前。這時賽丁果真唱著歌走來了,熱比婭高興異常。她跑進涼亭,捧起繡制的腰巾欲送賽丁,又害羞地遮住了自己的臉。賽丁似乎明白了熱比婭的心意,急于聽她親口說出,就唱著歌,抓住腰巾一端,請她說出心里話。熱比婭露出美麗的面容。他們唱著動人的歌,各執腰巾一角走下涼亭,伴著“賽乃木”的音樂節奏,款款舞蹈起來。時而輕盈地旋轉,時而舉起腰巾,深情對望,時而在腰巾的包裹中,熱比婭依偎在賽丁的懷抱。最后熱比婭欣喜地把腰巾系在賽丁的腰上。作為回報,賽丁為表達自己的愛情,也將母親留下的金手鐲戴在熱比婭的手腕。這段表演,以腰巾為道具,邊歌邊舞,聲情并茂,充滿詩情畫意。
要求主要演員“載歌載舞”是對演員的很高的期待。很多歌唱演員嗓子很好,卻不擅舞蹈;如果動作復雜,難度較大,演員費力,再想唱歌更是氣息難繼,心力不足。所以,無論中外歌劇,主要角色載歌載舞的情況都是不多見的,其時的舞蹈都較平和、舒緩,保持在可以完成歌唱的限度之內。在這個基本功上,有的戲曲演員是過得硬的。


音樂劇《冰山上的來客》劇照
三、音樂劇式表演
音樂劇形式19世紀末出現于歐洲,是由輕歌劇、鄉村歌劇發展起來的一種大眾化的、高度市場化的舞臺娛樂品種。戲劇故事、中心事件、性格沖突是它的創作基礎,音樂——歌曲、舞曲、序曲、間奏曲、背景音樂——是它的靈魂,而以舞蹈為重要表現手段,同時它又吸收、融合了美術、雕塑、影視、現代聲光電舞臺技術,把這些不同審美方式、不同藝術魅力的藝術門類高度綜合起來。因此,它樹立在舞臺上的作品是不受時空限制的,對于受眾來說是視覺、聽覺并重的,是立體的多維的審美。在這個前提下,音樂劇呈現了眾多的不同的樣式。《冰山上的來客》就是有新疆特點的民族音樂劇。新疆是多民族集聚的邊疆地區,生活素材、音樂、舞蹈及其他文化資源極為豐富,推出具有新疆民族文化、藝術特色的音樂劇,一直是新疆文藝工作者的熱切期望。該劇在創作之初就確定了“民族風格、時代特征、青春時尚、紅色經典”的創作宗旨,因而在表演上也顯示了不同以往的新追求。這種新追求不僅對今后音樂劇的創作具有借鑒意義,而且它彰顯的創新意識、與時代同行的精神更具有普遍意義。
音樂劇是一種更為大眾化的、易于為大眾接受的藝術。音樂劇《冰山上的來客》改編于大家熟悉的同名電影,《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等電影插曲從“文革”前流傳至今,無人不曉。所以,這是個很好的音樂劇題材。但是按照音樂劇要求,仍然需要進行很多創作。從表演上來說,交代情節、表達心情的對白、獨白大大減少了,音樂、歌唱、舞蹈的成分大大增強了。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一,突出了音樂劇的特點,在音樂上有很多很好的創造。它保留了影片中已經耳熟能詳的幾首歌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懷念戰友》《戈壁灘上的一股清泉》等,這些歌曲像音樂劇的骨架,確立了全劇高昂、悲壯的品格。同時創作了許多符合規定情境的、激越昂揚的、適于舞蹈的樂曲、歌曲、舞曲、間奏曲,這些音樂在旋律風格上,在氣韻上不僅符合規定的戲劇情境,而且也與原有的歌曲自然銜接,渾然一體,一次又一次地把情緒推向高潮,也展現了民族音樂劇的特有魅力。
第一場開場,阿米爾手捧玫瑰花苗上場,領唱合唱“翻過千層嶺哎,爬過萬道坡,誰見過水晶般的冰山,野馬似的雪水河?一馬平川的戈壁灘喲,放開喉嚨好唱歌。”就是原有的歌曲,立刻使觀眾聯想起經典影片,產生親近感。與楊排長四句對話之后,緊接了楊排長的詠嘆調《八一軍徽》和隨后戰士合唱的《馬刀閃亮》:“向前,向前!馬刀握在手上,戰馬四蹄飛揚。我們像雄鷹般翱翔,我們像雪山一樣堅強。(下略)”伴以雄偉矯健的“馬刀舞”,開篇就把戰士意氣風發的堅定意志盡情表現出來,為音樂劇奠定了保衛邊疆的主題和威武不屈的基調。而且前后銜接、過渡得流暢無痕。
在表現方法上,戲劇不同于影片的地方是要把角色的內心活動、糾結直接唱出來,而影片里通過角色的表情或簡短的獨白就可以說清了。所以,音樂劇中楊排長的詠嘆調《月光下的冰山》,阿米爾與假古蘭丹姆的二重唱《愛是什么》,古蘭丹姆、阿曼拜、卡拉的三重唱《快快離開這里》等等,這些剖析角色深層心理激蕩的地方就只能創作新的音樂段落來揭示。另外,有些表現解放軍英雄群像和軍民同仇敵愾的氣勢磅礴的合唱也是新創作的,例如最后一場《看刁羊舞》時的合唱,結尾時的混聲合唱《槍聲陣陣》,都是影片沒有而為音樂劇必須的表演手段,都是成功的。
第二,它在歌與舞的結合上也具有鮮明特點。主要是兩部分:一部分是表現解放軍戰士陽剛之氣的戰斗風格的歌舞,比如第一場在戰士的《馬刀舞》中,男聲合唱就屬于軍旅風格,歌聲伴唱中的舞蹈堅強、剛毅、勇往直前,動作也有相當難度。在以少數民族歌舞為主的新疆舞臺上,出現戰士形象的這類歌舞是不多的,令人驚喜。對于習慣民族舞蹈的演員也有相當難度,也提升了他們舞蹈表演的空間。另一部分便是塔吉克風格的歌舞,這在該劇中是彌漫在整個舞臺的,因為音樂劇故事是發生在帕米爾高原。最能炫示民族服飾、習俗、音樂、舞蹈光彩的就是婚禮了。在領唱、合唱、重唱《頭布纏起來》的歌聲中,是迎親隊伍的塔吉克風格的舞蹈,是向新人頭上撒面粉,是掀起新娘的面紗,是新郎新娘翩翩起舞。又如一班長犧牲前的雪花姑娘的雙人舞和犧牲后的冰雪舞蹈《雪花為你送行》,將民族風格與現代審美意識相糅合,兼有柔媚與莊重,悲情與堅毅,富有浪漫主義情懷,把觀眾此時的感受藝術地呈現在了舞臺上。它和緊接的戰士的歌舞《懷念戰友》一氣呵成,將悲憤的情緒推向新的高潮。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都是利用歌、舞、載歌載舞并將它們發揮到極致的這些音樂劇特別強調的手法,營造了異常熱烈、高揚的劇場氛圍。
還有一個可稱輔助表演手段的,就是利用現代舞臺技術所造成的新的表演空間。阿曼拜殺害假古蘭丹姆的情景,是通過投影見諸觀眾;剿滅匪徒的戰斗場景是利用原來影片的鏡頭。這些以往話劇、歌劇沒有用過的藝術手段,卻是音樂劇的習用手法之一。這也是音樂劇題材多樣、意識現代、手法靈活、異彩紛呈的體現。
總之,我區少數民族的戲劇表演,是源于本民族的生活和民族的文化藝術、民族的審美意識的,因而是具有鮮明民族、地域的特色的。同時它又隨著時代的進步,隨著人們審美意識的變化,創作人員思想的解放、眼界的開闊、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著、豐富著。這個發展過程是沒有終點的。在新的戲劇品種出現的時候,在編導的奇思妙想乍現的時候,在觀眾呼喚新的驚鴻一瞥的時候,演員是需要有更高的技巧來應對的。沒有演員水平的提高,戲劇的繁榮就無從談起。
(本文圖片由蔣建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