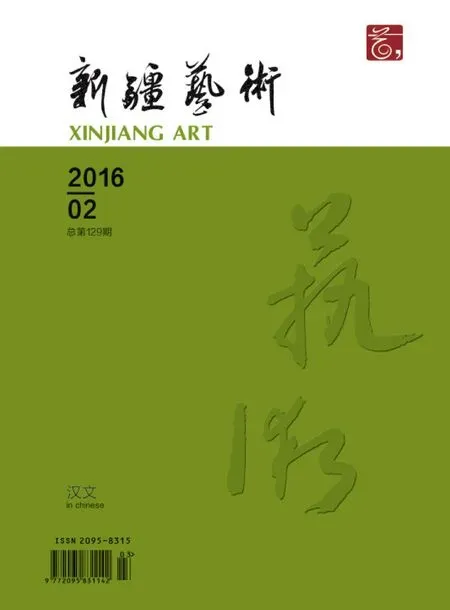六十年,《西部》與新疆文學
□ 黃永中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倏忽之間六十年光陰轉瞬即逝。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六十周年的喜慶日子里,《西部》一本伴隨著自治區走過近60年的新疆本土文學期刊也即將迎來自己的一甲子。《西部》的誕生和發展,是黨和國家關注和繁榮新疆多民族文學的最好詮釋。1955年10月,自治區甫一成立,《西部》的創刊即被列上了日程,一本新疆本土漢語文學刊物就誕生在這百業待興的繁忙日子里,足見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對新疆本土文學事業的重視。
自1956年創刊起,《西部》雜志的刊名經歷了《天山》《新疆文學》《新疆文藝》《中國西部文學》《西部》的多次更名,每一次刊名的更改,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當時新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一種文學層面的反映。可以說《西部》雜志伴隨和見證了新疆多民族文學事業走過了六十年的光輝歷程。有論者稱:“《西部》是新疆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本漢語文學刊物。”
六十年一甲子,《西部》經歷了初創期、成長期,至今依然呈現著勃勃生機。《西部》以其現代性、文學性、多元化為特征,展現著新疆燦爛的歷史文化、寬廣雄渾的自然地理、多彩的民俗風情以及各民族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辦好《西部》雜志不僅是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的殷切希望,更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六十年來,盡管《西部》也經歷了風風雨雨,但一代代《西部》人不懈努力,踏遍荊蓁,艱難和愉悅相隨、夢想與壓力相伴地一路走來。
西部文學的高地
要談論新疆當代文學史,不能不談到《西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西部》(其前身為《天山》《新疆文學》《中國西部文學》)幾乎就是新疆文學的代名詞。在《天山》之前,新疆的漢語文學刊物幾乎為零。《天山》的誕生,正值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提出,文藝正處在一個美好的黃金時期。《天山》創刊伊始,就秉承了繁榮多民族文學的重任,以翻譯、評介少數民族優秀文學作品為己任。很快,《天山》的周圍就聚集起并逐漸成長了一批新疆各民族優秀作家,如維吾爾族作家祖農·哈迪爾、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臺木、鐵依甫江、烏鐵庫爾、克里木·霍加、柯尤慕·吐爾迪等,漢族作家劉肖蕪、王玉胡、鄧普、周非、朱定、權寬浮、丁朗、霍平、吳連增、歐琳等;哈薩克族作家布哈拉、孔蓋·木哈江、郝斯力汗、庫爾班阿里,蒙古族作家巴岱、刊載;滿族作家沈凱、何永鳘;回族作家白練;錫伯族作家郭基南;柯爾克孜族作家阿曼吐爾等。他們成為新疆當代文學的開創者和奠基者。現在要回顧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新疆文學,不能不談到這些作家,也不能不談到《天山》及其后的《新疆文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山》文學期刊的創辦不僅僅是文學事件,它也是新疆社會進步、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完善的產物,體現的是建國初期新疆發展中的國家意志和文化訴求。其后,《天山》經歷了《新疆文學》時期(1962年——1973年),因“文革”動亂,《新疆文學》在1966年下半年至1973年曾一度停刊;1974年以《新疆文藝》刊名復刊的時期(1974年——1979年);1980年再度恢復以《新疆文學》為刊名的時期(1980年——1984年);《中國西部文學》時期(1985年——2000年);《西部》時期(2001年至今)。六十年來,《西部》一路蹣跚走來,經過彩虹,歷過風雨,但作為新疆多民族文學園地的初衷從未動搖過,它既是新疆漢語作家群成長壯大逐步成熟的主要園地,也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相互交流、共同繁榮的重要平臺,還是邊疆文學和內地主流文學交流聯系的重要渠道。
《西部》作為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園地和平臺,為文學運動的開展、文學流派的形成,文學思潮的引領,作家作品風格的確立和形成,都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如在1960年代初,編輯部迅即抓住中央調整文藝政策,使文藝環境有所寬松的短暫契機,迅速調整辦刊思路,提倡和組織反映真實現實生活的作品,提出題材、體裁的風格多樣化,注重藝術表現手法等方面的要求,對雜志進行了全新的改版,刊名也由《天山》改為《新疆文學》,改刊后的《新疆文學》一改自“反右”和“大躍進”以來日益僵化的文學風氣,刊發的作品中,表現人性、人情的東西多了,作家開始更加注重在文學本身層面的表現技巧,文學語言開始細膩、豐富了。在《新疆文學》的大力提倡下,在這一年的新疆當代文學中,出現了一批詩歌、小說、評論等在內容、主題、立意和形式表現上都比過去有較大變化的作品,這些作品可以說奠定了“文革”前新疆當代文學的堅實基礎。如在“文革”十年浩劫剛剛結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召喚下,雜志社的同仁以極大的勇氣和熱情,沖破“極左”思潮的禁錮,發起“開發者文學”征文,努力發現和扶持文學新人,倡導“新邊塞詩”,展開關于“中國西部文學”的討論,使新疆文學界逐步地掙脫捆綁,解放思想,開拓視野,新疆當代文學也終于進入了一個最好的發展時期。在《新疆文學》的大力倡導和推介下,到1980年代中期,一大批享譽新疆文壇乃至全國文壇的新疆作家紛紛涌現,如詩人周濤、楊牧、章德益、易中天、石河、李瑜、東虹、楊眉等;小說家艾克拜爾·米吉提、陸天明、唐棟、趙光鳴、文樂然、肖陳、韓天航、董立勃等;散文、報告文學作家豐收、矯健、孟馳北、張列等;評論家陳柏中、雷茂奎、周政保等。1990年代以后,又有劉亮程、沈葦、韓子勇、黃毅、王族、盧一萍、李娟、亞楠等一批青年作家、詩人、評論家借助《中國西部文學》這個文學平臺成長起來,有的已蜚聲全國。
“新邊塞詩”運動是在極左思潮肆虐中國十年之久的“文革”剛剛結束后,新疆吹向全國沉悶已久的文壇一股強勁的新風。“新邊塞詩”能夠在新疆興起并繼而影響全國詩壇,是《西部》一段值得銘記的歷史篇章。《西部》(時稱《新疆文藝》)在1978年9月號刊發了陳柏中、鄭興富的《詩苑新花迎春開》,評論了已開始在《西部》大量刊發作品的章德益、楊牧、周濤等人的詩歌創作,繼郭小川之后第一次以全新的內涵提出了“新邊塞詩”的概念,第一次對“新邊塞詩”代表人物進行了系統評介,“新邊塞詩”概念的號角一經奏響,隨即在新疆刮起了一股以其粗獷、雄奇、剛健、深沉、悲壯為藝術特色的詩風,在全國文壇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并引發了“新邊塞詩”的討論,“新邊塞詩”漸露雛形,蓄勢待發,呼之欲出。(這時已恢復為《新疆文學》)本刊除繼續大量刊發“新邊塞詩”作外,還組織刊發了為數眾多的“新邊塞詩”評論文章,從理論上為“新邊塞詩”鼓與呼。這不僅使“新邊塞詩”擁有一大批優秀的詩人,而且還涌現出余開偉、周政保等一大批優秀的詩歌評論家,新疆文學創作隊伍空前活躍。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中,在1980年代中期,《新疆文學》更名為《中國西部文學》,并將“邊塞新詩”欄目更名為“新邊塞詩”。在《西部》的大力倡導下,在新疆和西部詩人的創作實踐中,最終形成了一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詩歌流派——“新邊塞詩”派。在“新邊塞詩”初露端倪之時,《西部》就旗幟鮮明地打出了“新邊塞詩”的旗號,并對以周濤、章德益、楊牧為代表的一批詩人作品不遺余力地推介,并從而確立了其“新邊塞詩三劍客”的地位,為“新邊塞詩”派的形成鑄就了中間力量。縱觀八十年代,《西部》以全新的視野打造了“新邊塞詩”這一詩歌流派,成為西部詩歌的大本營,激活了新疆文學創作,改變了動蕩年代“萬馬齊喑”的沉悶格局,使新疆文學與新疆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共同走進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文學是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西部》狂飆突進式的文學運動,正代表了時代前進的方向。

首屆“西部文學獎”頒獎典禮2009年7月在喀什舉行

第二屆“西部文學獎”頒獎典禮2012年9月在伊寧市舉辦

第三屆“西部文學獎”頒獎典禮2014年6月在特克斯縣舉行。圖為獲獎作家為小讀者簽名留念

首屆“西部作家寫作營”2011年6月在天池舉行,參營作家在天池湖畔簽署了中國西部地區作家行為規范的“天池宣言”。
“新邊塞詩”詩派的形成和確立是和《西部》的大力倡導和推介分不開的,《西部》對“新邊塞詩”詩人群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可以說“新邊塞詩”作家群是在《西部》這塊文學園地中成長起來,從而走向全國詩壇的。
《西部》,尤其是近年來改刊后的《西部》,以更為寬廣的文化視野和多民族的文化背景贏得了讀者的一致贊譽。以海納百川的胸襟來吸引全國各地的優秀文學作品,使《西部》文學氣息與全國同步。《西部》憑借自身資源,實行欄目主持人制度,聘請了國內有影響的作家、編輯、學者參與到辦刊中來,為刊物的發展出力獻策,借助他們的資源和影響力,組織內地作家的優質稿源,有力提升了《西部》的文學品味。同時,改刊后的《西部》辦刊理念更加清晰、視野更加寬廣,在原有的小說、詩歌、散文基礎上,設置了“周邊”、“維度”等欄目,刊發文化評論,推介國外文學作品與著名作家。改刊后的《西部》,在網絡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讓新疆本土作家更有了一種危機意識,因為他們的作品將與國內優秀作家甚至世界優秀作家的作品共處同一個平臺。有讀者稱《西部》雜志是新疆文學界的“一桿旗幟”、“一個標竿”,對《西部》的發展給予了充分肯定。
《西部》六十年的發展歷程,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新疆大學教授歐陽可惺多年來專注于對《西部》的研究,并由此深入到新疆文學,尤其是新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研究,他認為,在這一方面,《西部》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他的學術成果集中體現在《區域文學的律動——〈天山〉流變與新疆當代文學》一書中,他由衷地贊嘆道:“(《西部》雜志)是新疆當代文學構成中最重要的期刊。”《西部》雜志對新疆各民族文學事業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
多民族文學的園地
《西部》是新疆多民族文學共同發展的產物,是展示新疆多民族文學成果的一個重要窗口。這是六十年來《西部》一以貫之的主線,它有時被稱之為“多民族文學”,有時又被表述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學表達”……不管如何界定,它們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致力于發展和繁榮新疆各民族的文學事業,打造具有西部特色的文化品牌,樹立新疆各族人民和諧、繁榮、奮進的文學形象。在新疆多民族文學發展史上,《西部》的作用不可小覷。
《西部》在1950年代創刊之初,就為自己明確規定了翻譯、推介、研究新疆少數民族優秀文學作品為己任的辦刊宗旨,這一做法成為了《西部》一貫的優良傳統。從創刊伊始就對早期的維吾爾族詩人黎·穆特里甫、鐵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薩克族詩人庫爾班·阿里;維吾爾族作家祖農·哈迪爾;哈薩克族作家郝力斯汗等的詩歌、小說、戲劇等進行了大量的譯介,對1970年代后涌現的維吾爾族作家祖爾東·沙比爾、艾克拜爾·米吉提、柯尤慕·圖爾迪、阿扎提·蘇里坦、買買提明·吾守爾、阿拉提·阿斯木等;哈薩克族作家夏侃·沃阿勒拜、朱瑪拜·比拉勒、夏里甫汗·阿布達里、葉爾克西·胡爾曼拜克等一代一代的少數民族作家的優秀作品不斷進行刊載、翻譯、評介,從而為新疆和全國讀者所熟知,他們從《西部》出發,走向了全國,有些甚至產生了世界性影響。
新疆各民族優秀的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更是通過《西部》大量而率先地譯介而逐漸廣為傳播,如中國三大史詩中的兩部——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蒙古族的《江格爾》,維吾爾古典文學經典《福樂智慧》《突厥語大詞典》,維吾爾古典愛情長詩《熱碧亞與賽丁》等,還有大量的維、哈、蒙、柯族的民歌民謠,民間故事,寓言笑話,諺語謎語,特別是《阿凡提故事》及其在新疆各地的變體《毛拉則丁的故事》《賽來恰坎的故事》等等在《西部》進行了大量的譯介,新疆各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通過《西部》這個平臺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西部》也成為新疆各民族作家相互學習、交流、成長的平臺,這種交流和學習也使新疆漢族作家獲益匪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多元文化的滋養,在其作品中具有了一種浪漫雄渾的西部氣息。很多少數民族作家也成為了用雙語寫作的作家,在扎根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用漢語這個工具,運用現代思維和理念,將自己的寫作和本民族的文化推向更為廣闊的空間。數十年來,《西部》一直是一個包容、開放的多民族文化園地,向世人展示著新疆多民族文化中最絢爛的一幕。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10年《西部》全新改版后,仍然秉承這個理念,相繼推出了“雙語作家”、“新疆少數民族作家專輯”、“新疆少數民族青年詩選”、“新疆作家作品研究”等欄目,集中刊發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達斡爾族、塔吉克族、蒙古族、回族作家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對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鼎力推薦,一批80后少數民族作家、詩人,如帕思安、艾多斯·阿曼泰、麥麥提敏等,他們的名字如耀眼的星星閃爍在西部的天空,他們的作品以新銳性、現代性而得到了人們的關注。持續關注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著眼于多元文化的發展,是《西部》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實踐證明,《西部》是團結各民族作家的橋梁和紐帶,也是各民族作家成長的搖籃和持續發展的平臺。
高品位文學活動的平臺
《西部》是一本具有擔當意識和現代意識的文學刊物,無論在各個時期,《西部》總是能夠體現新疆多民族文學創作的獨特價值和整體水平。《西部》是開拓者的家園,一代代《西部》人為辦好《西部》嘔心瀝血,盡最大可能擴大《西部》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西部文學獎”的創辦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證。
《西部》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六十年的歷程峰回路轉,跌宕起伏,《西部》的文學之路是艱辛而輝煌的。在2000年的中后期,《西部》在走過了一段艱難的市場化探索之后,重新回歸到純文學之列。其時的《西部》,文學聲譽和社會影響力都降到了最低點,而財務狀況更是窘迫,連刊物印刷費都無從落實。《西部》在泥濘中重新起步,如何才能讓人們盡快地知道《西部》的文學回歸,如何恢復大家對于《西部》、對西部文學的熱情和信任,盡快讓《西部》在文學場中“發聲”,這是當時《西部》辦刊人思考最多的問題。經過深思熟慮,舉辦“西部文學獎”成為《西部》人的共識,用頒獎慶典活動來高調宣示《西部》回歸文學后的新面貌、新成果。辦綜合性文學獎是幾代《西部》辦刊人想辦而未能實現的夢想,而這時的《西部》無論在經費、還是讀者認知度上,都處于最低潮,舉辦“西部文學獎”,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同時,對于曾經一度迷失了文學而今又重返純文學的《西部》,所起到的宣傳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西部文學獎”開啟了破冰之旅。在《西部》辦刊人鍥而不舍的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難,在喀什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在沒有使用上級財政資金的情況下,《西部》雜志創刊50多年來首個綜合性文學大獎——“西部文學獎”的頒獎慶典終于在2009年的7月在喀什成功舉辦。獲獎作品從《西部》2006年回歸純文學后至2009年間所刊發的各類文學作品中產生,有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報告文學、文學翻譯七個文學門類的24部作品獲獎。王蒙、阿來、舒婷、遲子健等二十多位全國著名作家蒞臨大會祝賀并為獲獎作家頒獎,近百位疆內外作家及喀什地區近千位文學愛好者參加了頒獎大會,可謂盛況空前。頒獎大會結束后,還舉辦了一系列作品研討會、文學講座、文學采風活動。這些活動的成功舉辦,無疑增加了《西部》在作家和讀者心目中的地位,給作家們提供了學習和交流的機會,擴大了文學的影響力。眾多新聞媒體連續地、多層面地報道,使《西部》文學精神廣為傳播。“西部文學獎”頒獎盛典成為2009年新疆文學、文化領域的大事件,對《西部》今后的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西部文學獎”成為《西部》高擎西部文學大旗的錚錚宣言,《西部》成為西部文學的強有力的發聲者。2012年9月、2014年6月,第二屆、第三屆“西部文學獎”分別在伊寧市和特克斯縣成功舉辦。

第二屆“西部作家寫作營”2013年6月在塔城市舉行
“西部文學獎”是《西部》雜志社為新疆多民族文學創作搭建的另一個重要平臺,在評獎過程中,堅持推薦民族作家、本土作家的原則,阿拉提·阿斯木、葉爾克西·胡爾曼拜克、麥麥提敏等少數民族作家都曾榮膺此項殊榮。目前,“西部文學獎”已成為新疆唯一面向全國的文學獎,獲得了文學界的廣泛認同。
《西部》在努力辦好刊物,認真辦好“西部文學獎”的同時,還盡量擠出時間去做一些有品質的文學活動,去做文學的普及和推廣活動,去做青年作家的培養和交流活動。2010年,《西部》雜志社組織了作家赴伊犁邊境農牧團場的文學采風活動,將文學的觸角伸向了邊境農牧團場,活躍了基層文化生活,加強了刊物、作家與基層文學愛好者的聯系。2011年,為獎掖文學新人,推動新疆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西部》雜志社聯合《綠洲》《伊犁河》雜志社策劃舉辦了“新疆新生代作家榜”的評選活動。經過多輪推薦、評選,46名年齡在40歲以下的青年作家上榜,10名作家被評為“十佳作家”。此次活動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有力地推動了青年作家的創作積極性,顯示出《西部》培養激勵本土文學新人、推動新疆文學事業持續發展的長遠眼光。2012年,《西部》雜志社與石河子大學文學藝術學院、《文藝爭鳴》雜志社在石河子舉辦了“全球化語境中的區域文化和文學”國際研討會。
2011年,《西部》成功地在天池舉辦了首屆“西部作家寫作營”采風活動,來自新疆、甘肅、青海、寧夏、內蒙、陜西、四川、重慶、廣西、貴州、西藏等西部省區市的作家,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地的特邀作家,共50多人參加了寫作營活動。這是一個有深度、有品位,有自己文學主張的文學盛會,參會作家們經過多次討論、修改,并最終共同簽署了涉及到文學與自然的關系、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作家責任、地域性與文學的多樣化、西部文學的超越等問題的《中國西部地區作家天山天池宣言》,在全國文學界也引起了廣泛的共識,被中國作協譽為當年“海拔最高的文學發聲”。2013年又在塔城成功地舉辦了第二屆“西部作家寫作營”采風活動。寫作營活動的舉辦加強了新疆與內地作家的交流互動,成為當年度新疆最為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贊譽。
回顧《西部》六十的發展歷程,我們有過彷徨、低吟、嘆息,但更多的是思考、探索、奮進……無論在什么時刻,《西部》都沒有放棄刊物的文學屬性及文化特征,努力把《西部》辦成一個融可讀性、包容性、輻射性、權威性為一體的優秀文學期刊,正是帶著這種信念,《西部》從一次次困境中重新崛起。《西部》六十年,為繁榮新疆多民族文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整個新疆文學創作起到了引領作用、助推作用,開風氣之先,這是為歷史所證明的。六十年的風雨磨礪,《西部》已經擁有了豐厚的文化積淀,呈現著新疆作家豐富而雄奇的文化想象力。《西部》是具有廣闊胸懷的具備了現代精神的《西部》,而不僅僅是新疆的一份省級文學期刊。要得到對《西部》的全面認知,必須跳出新疆看《西部》,跳出狹隘的文學觀看《西部》,甚至跳出西部看《西部》,《西部》早已走出新疆、走出西部,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歐陽可惺在《區域文學的律動——〈天山〉流變與新疆當代文學》中客觀公允地描繪了《西部》的生存發展之道,他說:“一個期刊的歷史就是特定的社會史、文化史,是社會思想、情感和理想、想象的歷史。”
(本文圖片由黃永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