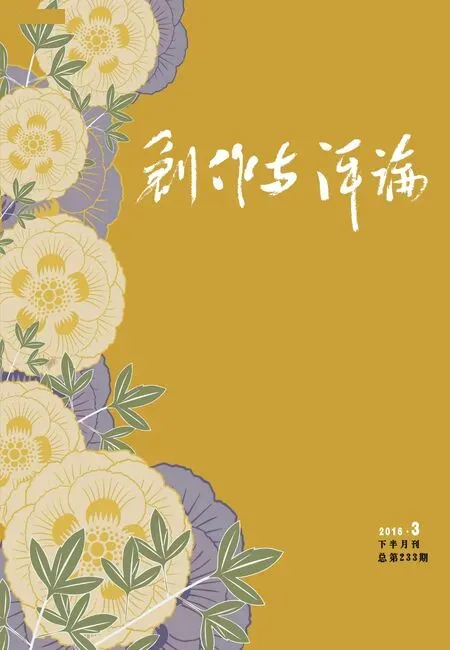作為方法論的和美學的『王小波』
——從房偉的『王小波研究』談起
○梁鴻
?
作為方法論的和美學的『王小波』
——從房偉的『王小波研究』談起
○梁鴻
1990年代后期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或者說愿意閱讀文學的年青人,有幾個沒有愛上過王小波?也許中年之后會遺忘,會批判,會有所疑問,但是,在青春最為激蕩,最容易被宏大話語制約,最容易被“理想”“時代”“夢想”之類的詞語所鼓動的時候,讀到王小波,那是怎樣的一種震動、震驚,或豁然開朗?
那天真而蠻荒的想象力,舉重若輕的反諷意味,性與政治的微妙辯證,它們組合成一種充滿趣味和獨特審美的文學語言,以最輕盈的方式穿透哪怕是最堅固的內心,讓你感受到人類存在的真相和時代精神內部的荒謬。而對于最缺乏個人意志和精神自由之感的當代中國人來說,那個“打不死的小強”,那個哪怕在最黑暗的時刻——被嚴刑拷打,跳樓自殺,游行示眾——也依然挺立的“小和尚”,猶如一個巨大的尖形碑,以滑稽而又莊嚴的方式給我們展現了生命的頑強和自由的美感。
房偉在他的《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王小波》(三聯書店)中稱王小波為“壞孩子”,這一說法雖然是感性的,但卻形象地把王小波與時代的關系,王小波存在的基本位置給展示了出來。他不按常理出牌,他挑戰、嘲弄權威,他不負責任,任性耍賴,在人人義正辭嚴的時候,他卻想著陳清揚的身體,在全國上下火紅一片,都在大煉鋼鐵之時,他卻把它想像為一場怪異抽象的戰爭,在賀先生不堪其辱憤而跳樓的悲慘時刻,他卻注意到賀先生的“小和尚”依然是挺直的。他總是能夠看到那些板著的面孔背后的漏洞,并且,就像一個班級的壞學生一樣,還生盡千方百計讓其它同學也看到那些漏洞,而全班同學發出的明了的哄笑聲就是對他最大的獎賞。這“哄笑聲”貫穿了王小波的所有創作。它是一種嘲弄,一種去蔽,對密布于我們生活內部的思想的突然陌生化,進而達到一種質疑——對最基本的概念、行動和觀念的質疑。而由于它的感性基礎,這一質疑變得真實、有力,幾乎達到一種澄清,很難再被遮蔽。
在王小波的小說中,“性”作為一種自然的元素,它與個人、生命力、自由相關,所相對應的是束縛、集體、政治、制度。“小和尚”不分時候、不分地點挺直在那里,既嬉笑怒罵、悲慘無比,又為所欲為,不聽使喚,哪怕是跳樓死亡,它也還在那里表演自己。王小波憑著直感找到反時代核心話語的核心話語,圍繞著此,喋喋不休,反復敘述,最后形成一種審美和美學,并擁有強大的消解和反抗力量。
這無疑是一種教育,關于個體生命,關于人類存在的限度,關于理性與經驗關系的教育。閱讀王小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是一場關于啟蒙的旅程。這與“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還略有不同。如果說“五四”時期的啟蒙更多地在于啟發民智,讓大家從愚弱中意識到作為一個民族存在的危機,是一種族群意識的警醒,里面包含著對個人權利的認知,在王小波的“啟蒙”里,以“族群”為名義的革命與權力恰恰正是需要反思的,他讓你看到革命、權威、道德如何以“正義”“集體”的名義摧毀個人,讓你看到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點自然性及這一自然性的力量。
自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王小波熱”一浪超過一浪,先是思想文化界,精英媒體界,然后是文學界,最后到達大眾文學愛好者和青年一代那里(這個排序本身很有意味),中間還有王小波的愛人,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的推波助瀾,關于王小波的一切——哪怕是他最不經意的一個動作和最私人的性愛(李銀河最近推出傳記詳細寫到兩人的性愛方式),似乎都已經被大家熟知,并被廣泛討論。
為一個已經被分析過度的作家寫傳記,應該是一件很冒風險的事情。在這樣一個全媒時代,掌握、收集資料,探聽故人的看法,尋找傳主生活過的地方,探查民間的聲音,似乎都不是難事,這就意味著,揭密式的、生平式的傳記都已經沒有多大價值。這給傳記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正是在這一層面,房偉的《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王小波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作為一位文學評論家和作家,房偉打通了雙重自我身份所產生的多重知識路徑和美學路徑。通讀全書,可以看到,房偉仍然以王小波的生平為綱——為尋找一丁點的蛛絲馬跡,房偉可謂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窮盡了一切可以窮盡的人,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有半年時間,為了約到北京與王小波相關的人,房偉在北京租了間房子,隨時待命。但是,他并非止于揭密式的描述,而是如抽絲般地梳理出王小波小說美學中的經驗來源和知識來源,他做的是一種倒置式的和互證式的闡釋,即,首先要對作家創作中的美學風格、思想方式和精神特征有最根本的把握,然后,通過對作家生平的回溯和探秘,找到其來源和生成方式。
這樣的寫法和結構方法,首先需要傳記作者對作家作品有深刻的領悟和獨特的認識。在此角度下,房偉充分發揮了他的專業優勢。作為當代文學的研究者,房偉不但對王小波小說進行理論探討,從王小波的接受學、美學和比較學等多個層面進行研究,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和學術專著①,同時,作為一名作家,在創作上,房偉也全方位實踐并探索王小波的美學思想。2012年房偉出版長篇小說《英雄時代》,在這部小說里,房偉讓當代和古代兩重時空同時并存,以一種王小波式的狂歡化、雜揉的語言對當代世界內部的虛空和荒誕進行了書寫,但是,它的多義性語言和黑色幽默卻又是房偉自己獨異的風格。這其中,自然有對王小波致敬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房偉把王小波的美學風格作為一種實驗,既實踐它,又創造出一種具有開放性和彈性空間的形式。
這正是王小波的核心:從來不提供固定的真理式的思想,他更樂于提出一種思維的方法和精神的形態,沿著這一方法和形態,每個人都會達到自己的方向。它強調一種通向真理的方法論,而非真理本身。
從房偉關于王小波小說的論述和自己的創作可以看出,他對這個作家的精神世界,對這個作家在當代中的位置及背后的象征性意義,對作家的美學風格,都有極具創見性的理解,能夠看到隱藏在作家作品中的多條路徑。同時,你也可以感受到,對于這樣一位作家,房偉有真正的欣賞和進一步探索的熱望。對于房偉來說,王小波是通向越來越深、越來越寬廣的遠方。
以學術研究為起點,再回到傳記研究,房偉要探討的是,王小波的作品,哪怕是一個最簡單的意象從哪里來。
在《三十而立》中,王小波寫道,“你能告訴我這只貓的意義嗎?還有那墻頭上的花飾?從一團雜亂中,一個輪廓慢慢走出來。然后我要找出一些響亮的句子,像月光一樣干凈……”“古舊的房子老是引發我的遐想,走著走著身邊空無一人。這是一個故事,一個謎,要慢慢參透。”
一個普通的讀者讀到這些話,可能很輕松地就滑過去了,只是不錯的句子而已。但是,房偉卻沒有放過,反而從最簡單的詞語“墻頭上的花飾”入手,回到王小波成長的生活空間和歷史場景中,去尋找這句話的來源,并且,由此出發,對王小波小說中的大量物質性詞語進行分析,進而闡釋其中的修辭風格和美學意味。
在第二章“頑童時代——孤獨的‘壞孩子’”中,房偉以“墻頭上的花飾”為起點,對王小波的成長空間進行了地理學和譜系式的考察。他追溯到王小波的祖輩父輩,作為大地主的祖父和作為革命青年及學者的父親,他們的生活方式、性格生成及命運軌跡,最后,回到王小波童年時代的“鐵獅子一號”:
該樓的主體是灰磚石結構,樓面上鑲著很多花紋和浮雕,樣式繁多,對稱而華美,有花和葉子,也有類似中國古典傳說中的夔龍等形象的圖案。主樓的大門是木質拱形黑木門,顯得非常大氣;副樓則有很多拱形回廊,綠色的立柱,以及造型歐化的路燈。……主樓和副樓相通,門窗和出入口很多,辦公樓下還有很多地下室,這些地下室,四通八達,“曲徑通幽”,給人以陰森神秘的感覺,據說當年的日偽特務機關,在此還設有水牢。王小平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到這里的水牢和王小波小說的“鐘樓情結”。……相比較紅色北京的革命化空間,鐵一號是“曖昧”的空間設置。作為革命者的后代,王小波及其同代人在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同時,生活環境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和成方街不同,“鐵一號”是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少了一點雜亂和粗鄙的快樂,多了幾分厚重的文化氣息。更特別的是,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政治空間,“鐵一號”對兒童的成長心理而言,卻更多體現為“神秘”的藝術氣息。曾經的輝煌,現實的衰敗,兩相對比,生發出一種歷史“幽靈”般的神秘主義力量。②
由此,房偉認為,“鐵獅子一號因此恰成為一種‘曖昧’的存在。它的樣式造型、內涵意義,都是‘非革命的’,然而,它也并全不革命的‘對立空間’。在它被中性化的外表下,展現出來的卻恰是‘革命之外’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豐富和復雜性。”這一成長的環境和空間,無疑會影響到作家日后的創作觀和創作美學風格傾向,王小波小說中對“革命”的叛逆和反思,審美的復雜性,可能都與童年的生活經驗和空間特征有關。也正如房偉所言,“王小波的成長空間,是一種革命北京的‘大院文化’。這種大院文化,既有別于王朔、姜文式的‘部隊大院文化’,也有別于傳統的‘市民胡同文化’。它屬于革命北京時空中,國家事業單位、高校團體的獨特空間。它既是革命北京的‘體制內產物’,又有一定的知識分子氣息,對‘軍事化的大院’有一定的疏離與反思。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從一個體制內紅色知識分子家庭誕生的王小波,最終形成了對‘革命北京’的深切反思。”③
以房偉的分析,我們返過來,再重新讀“墻頭上的花飾”,可能就不會覺得它只是一個蒼白、陳腐的詞語,而包含著一個幽微的空間,這一空間與大時代如火如荼的革命空間呈現一種出錯位的存在。這些“陳腐的、陰暗的”物質化詞語在王小波文本的大量使用,無疑增強了這一“幽微空間”的力量,并最終與“革命空間”形成對抗性和某種拆解作用,并形成一種美學風格。這也是我們在閱讀王小波小說時,雖然明明知道他在寫“革命”和“革命時代”,但又總感覺他的“革命”和“革命時代”和那一革命完全不同的基本原因。他會讓你猶疑,讓你頗費思量,進而產生思維上的晃動和真正的思考。
房偉非常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在這本書中,房偉對王小波小說里面最細微元素的來源都作了細致探討,這不單是對作家創作細節的把握,也是對小說美學元素的還原,猶如密徑,唯有仔細探察的人才能夠發現。
再譬如,王小波在《革命時代的愛情》中描述“大煉鋼鐵”的情形,“我順著那些磚墻,走到了學校的東操場,這里有好多巨人來來去去,頭上戴著盔帽,手里拿著長槍。我還記得天是紫色的,有一個聲音老從天上下來,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時時站下來,捂住耳朵,把聲音堵在外面。”
這顯然是一個兒童視角,與王小波本人的童年經歷相一致。1958年的人民大學的操場,和其他地方一樣,也工作著無數個小高爐和炒鋼爐。整個北京也陷入了“大煉鋼鐵”的狂歡。王小波以兒童眼光來看這一場宏大的運動,頭盔,長槍,巨人,這都是典型的童話式意象,也有著堂吉訶德式的夸張與滑稽,而紫色的天空,則成了夢境的代表,這些描述自然地把“大煉鋼鐵”變形化和夸張化。房偉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處理方式,它有效避免了生硬的說教和概念植入,將理性精神與美學超越結合一體,也避免了新時期以來形成的文學規范在意識形態和美學特征上的制囿……鐵獅子一號陰森恐怖的地牢已潛伏到了記憶深處,而廢棄的高爐遺址,成為王小波有關成長記憶的隱秘圣地。這里有童年的幻想,也有隱秘的傷害,這里有紫色的天空,巨人,長槍,鋼鐵。而這些東西,像流星一般出現在歷史,又很快被遺棄與遺忘,成為歷史的幽靈。”④而這些,也正是王小波小說美學的基本底色:怪誕、夸張和狂歡。
從作家對詞語的使用,回到作家的成長環境,再從作家的成長環境回到對詞語的分析和美學的形成,房偉這樣一種回環往復的考察,包含著對作家心理和性格成長的探秘,但更多的卻使我們對王小波的世界有更加感性的和深刻的理解。
這樣一種空間性的探討,從學理上講,并非完全是一種對位的關系,因為并非什么環境下一定生長出來什么人,而是同一環境下一定生長出不同的人。但它又具有意義,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作家成長內部的多種路徑。
從整體而言,《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不只是研究王小波的美學和成長,其實也是回到那個時代,重新還原歷史語境,探察那個時代的多條通道。以王小波為契機,房偉也在探討政治與人的沖突,生命的頑強與自我的選擇,進而探討文學以何種方式來達到一種澄清。
王小波對科學理性的推崇可能被所有讀者和研究者注意到。每每涉及此,王小波總是犀利尖刻,一針見血,但這一點,并非來自于皇天知識的培訓,而來自于作者對人類自身經驗的重視和肯定。這與他前面寫“大躍進”“大煉鋼鐵”的感覺是相一致的。真正的理性其實很簡單,尤其是對于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來說,就是“回到常識”。王小波的雜文里有一個“奶奶”的意象,即經驗和常識的象征。
他自己曾公開宣稱對智力和理性更感興趣,這一觀點也常常使王小波面臨質疑,認為他有很強的精英主義傾向。但是,如果把王小波放置到一個大的語境之中,就明白,這句話,幾乎是一種吶喊,背后有對我們這一國度最為匱乏的思維的焦慮。他的思想里有復雜的辯證成份。同時,最應該注意的,也是王小波最重要的地方,即,他對于所有事物的說理都并非是斬釘截鐵的,他只是通過藝術的形象來傳達。這樣,他所呈現出的藝術形象往往大于他想要傳達的,他的句子隨時隨地充滿著這樣的“溢出”,讓你有更多向度的感受與思考。也許,這正是文學的基本魅力。純粹的說理很難達到這樣的多重方向。
房偉對此的分析也很有意味。他沒有糾纏于王小波的“理性”是什么,沒有試圖幫讀者去確認王小波的正確性,而是依然回到文本中,分析它們之間的關系和在文學中的呈現方式,“對王小波而言,大躍進運動成為其樹立文學內涵和美學原則的一個出發點。正是大躍進運動,讓王小波看到了理性缺失的荒誕。有趣的是,盡管王小波在雜文中,不厭其煩地以大躍進為例,講解科學理性對中國人思維的重要性,但小說中有關大躍進的印象,卻成了一些更為悖論化的美學形象,所有那些荒誕景觀,都以‘兒童狂想’的美學形式出現。狂想之中,兒童對生命的好奇和對奇觀場景的探究,都在歷史的荒誕之中,顯現出了宿命般的美學魅力。一方面,歷史的荒誕成為理性缺失的反證,革命因違背常識付出沉重代價;另一方面,荒誕的歷史,又成為某種獨特的現代美學景觀,并被兒童視角賦予了‘奇幻’的生命激情”⑤。“革命活動”變為“荒誕景觀”,“大煉鋼鐵”則成了一場虛無怪誕的狂歡,這一意義指向本身就是一種批判和消解,這是王小波的美學形式所產生的力量。可以說房偉始終抓住經驗、生活與美學之間的關系對王小波進行分析,這使得他的結論可靠,讓人信服,同時,又能夠跟隨著王小波回到時代深處,重新去把握時代的內在脈絡。
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既是一本作家的傳記,同時,也借王小波的方法和美學,對中國當代思想史進行溯源式的回顧和梳理。王小波并非只是本體,還是方法論。
作為一個傳記作者,他和傳主之間到底該是怎樣的距離和關系?有人說,傳記作者太愛傳主容易形成誤區,容易諱疾忌醫,但是,反過來,如果沒有熱愛,又如何能夠如考古一般,匍匐在灰塵里,一點點找遺落在時間和空間深處的線索?不管如何,作為王小波熱愛者的房偉始終保持著一個學者的理性和嚴謹,沒有過于夸大王小波的文學意義,也沒有夸大王小波作為一名自由知識分子的行為及行為背后的意義。譬如王小波的辭職。房偉認為,這一行為在當時,并不是一個獨立于世的行為。王小波1992年從人民大學辭去教職,并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房偉在文中考察了同時期其他作家的辭職情況,南京作家韓東、吳晨駿、朱文都在同時期辭了職。辭職當然是某種精神的顯現,但同時,也并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實際上,1990年代初期,“自由撰稿人”“下海”這樣的詞語對知識分子的沖擊是今天難以想像的,它已然形成某種潛流和象征。并且,稿費的增加和報紙雜志的商業化,都給自由撰稿人的生存帶來一定空間。當然,相伴隨的,就是寫作上的自由度和獨立性。這樣客觀的、深入歷史語境的考察和結論并不會損傷王小波的獨立性,相反,它能夠使我們更全面地了解時代內部的精神狀態。它是一個學者的嚴謹態度所得,同時,也是對王小波形象的恰當敘事和還原。王小波是革命星空下的那個“壞孩子”,有他成長的空間、語境和特殊的話語形態,這些也造就了他寫作的基本內容。以此為起點,他把握時代、政治、人性和文學,他是在一定歷史空間中所誕生的叛逆者和破壞者。
在最后一章里,房偉以非常客觀和冷峻的筆法對王小波死之后的“王小波現象”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媒體、文青、李銀河、書商等如何共同參與,掀起了曠日持久的“造神”運動,而那些否定、批評王小波的聲音又如何此消彼長,始終存在。對此,房偉認為,“無論喜歡還是討厭,王小波在我們的社會,正在變成一個‘神話’被超越,在他身上,負載了太多復雜的社會信息,也負載了太多怨恨、憤怒、喜愛、沉靜與悲傷。”這一“造神”運動對于王小波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還很難判斷。但毫無疑問,房偉的《革命星空的“壞孩子”——王小波傳》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具有獨立價值的通向王小波世界的道路。
注釋:
①《十年:一個神話的誕生——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9期(《新華文摘》摘編);《雜文歷史小說:穿越歷史和現實悖論的一種可能——論魯迅<故事新編>與王小波的歷史小說》,《東岳論叢》2006年第6期;《在革命的星空下-王小波小說的“革命+戀愛”模式》,《東岳論叢》2012年第2期;《笑忘紅塵頑童夢》,《社會科學報》2012年5月31日(《新華文摘》摘編);《從強者的突圍到頑童的想象——魯迅與王小波之比較分析》,《文藝爭鳴》2003年第5期(人大復印資料轉載);《論王小波小說的三重形象》,《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另類目光與另類的生存——王小波同性愛題材小說研究》,《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論王小波小說敘述視角“復古”與“創新”》,《蘭州學刊》2008年第7期;《個人主義與群體否定——論魯迅、王小波文化邏輯之異同》,《藝術廣角》2007年第5期。專著《文化悖論與文學創新——世紀末語境下的王小波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
②③④⑤房偉:《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王小波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56頁、第112頁、第34-35頁、第32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欄目責任編輯馬新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