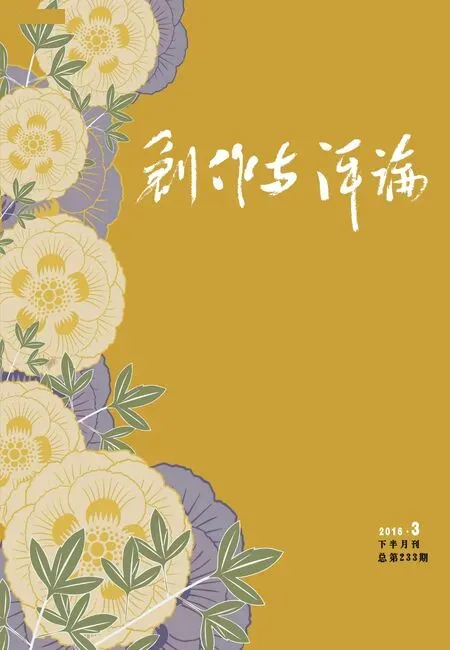寬廣·深刻·互動
——評房偉的文學批評
○劉文祥 賀仲明
?
寬廣·深刻·互動
——評房偉的文學批評
○劉文祥賀仲明
青年學者房偉,有著山東人最本色的“大漢”形象特征,舉手投足之間也透露著樸實與儒雅,顯現了齊魯文化的精神熏陶。業內人士都知道房偉的足跡橫跨批評與創作兩界,集批評家、詩人和小說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在多個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果,這在文壇是少見的。而正因為這種多重的身份,他的文學批評也具有了自己的顯著特色。迄今為止,尚不到40歲的房偉已經出版了多部批評專著,包括《文化悖論與文學創新——世紀末文化轉型中的王小波研究》《中國新世紀文學的反思與建構》《風景的誘惑》等,還有頗具影響的人物傳記《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王小波傳》。可以說,房偉已然成為山東文學批評界的后起之秀,也是國內青年批評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寬廣的關注面向
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指出:“批評應該被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知識結構中,從而使其研究更加系統,同時也在批評內為社會批評家和藝術趣味的代表建立起權威性”①。他認為批評者的視野應該寬闊,涵蓋所有與文學有關的學問和藝術趣味問題,惟其如此才能夠從全方位、立體化的角度開掘作品的內在意蘊,而不是流于某種單向度的解讀。毫無疑問,房偉在其文學批評中在自覺地踐行著這種理念,他不耽于某種文學現象和某個作家群,也不只是流連于文學本體批評,所有和文學藝術有關的現象作品都能夠點燃他的批評興趣,其領域也關涉到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等學科范圍。所以我們看到他奔走于文學批評場域中的各個角落,饒有興趣地梳理著林林總總,無論是文壇老將還是初生牛犢,無論是紅色敘事,還是網絡文學,無論是電視電影,還是小品文藝,都進入到他的批評視野中。
首先,房偉對文學的整體發展和走向有著自己清晰的理解。如在《作家身份結構與新時期文學》中,他認為當前作家身份結構是影響新時期文學的根本所在,當下的作家身份組織與認證結構呈現為由“核心”“次級核心”與“外圍”組成的同心圓式,作家身份是從“革命一體化”走向“后革命一體化”的“凝聚——耗散——重建”的動態過程,意識形態、商品性和審美性之間糾葛導致了多元身份選擇,這種選擇背后并沒有相應的“文化身份定位”。再如在《多元視野下的當代作家生存狀態研究》中,房偉歸納了當下作家的八大生存癥候:炫富性狂熱、偽中產階級趣味、炫貧性偏執、主旋律心態、虛擬封閉性生存、惡炒性癥候、弱勢化生存等……在這些論述中,房偉把握住了文壇的走向和弊端,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中國文學的經典形象在不斷淪喪,中國文學原創性的缺失”“泛一體化的文化體制的規訓力量,消除異端性寫作,建立均質性文化理想的決心是如此之大,令人憂慮。”②
其次,房偉關注的作家和作品領域非常廣泛,并能立足于寬闊的視野來進行關聯分析。其對單篇作品的論述異彩紛呈,也往往能夠以小見大,以近見遠。如從賈平凹《帶燈》中,他分析了女性在鄉土中國中的艱難行進和人性裂變,從《九月寓言》中,他發掘了張煒試圖構建的個性浪漫、又相對封閉自足的“寓言烏托邦”,在《兄弟》中,他討論了在先鋒死亡的“偽宏大敘事”年代里如何繼續寫作。在對作家的解讀上,房偉更能多方比較,深入細微,不同類型的作家他的筆下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論析。其中既包括活躍于1980年代的馬原,也包括新近崛起的青年新銳王威廉,還有具有強烈浪漫和異域色彩的海外作家郝譽翔,以及擁有山東平原精神氣息的散文家李登建,對漢語詩歌傳統努力探索的王長征……
除了文學,房偉的批評領域還延伸到電視和電影作品,顯現出房偉文化批評視野的廣闊和敏銳。如他指出電影《大話西游》中的模糊時空美學隱含著當代中國人的碎片化的生存語境,認為電視劇《武林外傳》實際上是對主流意識形態、市民倫理和知識分子心態之間的符碼重組。甚至對一些小品文藝,房偉也能夠做出準確的文化探析,如他曾細致分析趙本山從邊緣民間進入主流意識形態的喜劇演出軌跡,爬梳其尷尬的“農民形象”的被生產過程。
二、深刻的批評訴求
房偉的文學批評不僅僅流于面的梳理,同時更執著于深度的挖掘。從字數達到20多萬字的碩士論文開始,他就試圖挖掘王小波對魯迅思想的繼承與延展關系,體現出了一個不流于俗見,開拓自我批評領域的崢嶸形象。此后,房偉的這種精深的批評訴求繼續邁步前進,在當下一些充滿爭議或者早有定論的批評點上發出了屬于自己的聲音,展現了其獨立的思想特質。比如在人們爭論不已的《兄弟》上,他敏銳地感覺到在先鋒死亡的“偽宏大敘事”年代,余華拒絕進入宏大敘事的二元對立圈套,而是從個人化角度出發,自覺在文本中建構起一個想象性的個人化內心世界。只是在“宏大敘事”死而不僵的當下文學里,純粹的個人化敘事必然要失敗;在《論主旋律小說的內在構成形態》中,房偉又指出當下主旋律小說通過彈性處理,依靠“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族復興”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三重同心圓”的內在模式;在論述作家艾偉時,他敏銳地感覺到艾偉堅持人性與心靈的啟蒙立法的實質,是在逐漸從解構歷史走向“歷史的和解”,但是這種再歷史化的小說創作也存在內在困境和難度,容易賦予歷史“過量”的心理因素;在論述閻連科的創作中,他指出閻連科的小說存在一種經過純文學話語機制改造過的“奇書”模式,是新世紀以來純文學話語機制發展陷入困境的產物,容易產生極度抽象的寓言化、“惡”的絕對化等缺陷……可以說,這些論述都精彩而犀利,顯示出屬于房偉的質疑精神和深度思考。
此外,房偉對網絡文學的論述也頗具深度。當下的網絡文學創作可謂泥沙俱下,網絡文學批評中雖不乏批評實踐,缺的卻是理論建構,房偉的論述不滿足于單純的游戲性、大眾化、后現代性、民間性、自由性等研究視域,而是努力從文化深層進行開拓。如他以網絡穿越歷史小說為例,梳理了網絡穿越小說與通俗歷史小說的歷史淵源,認為在這些創作的背后折射出了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個人主義與共同體誘惑、歷史觀念的糾葛。這一觀點既有新意,也是富有據地形的。
作為一個批評者,房偉也不斷反思文學批評的現狀與處境,展現出屬于批評家的自我省察,而這也形成了另一種批評的深度,不僅僅是在關注文本,更注意關注文本介入者和自身構建的話語系統和標準。在論文《再造經典的難度與批評的失語》中,他指出當前的文學評價機制存在著很多缺失:其一是評價標準區隔與通約的匱乏,政治認定、文學精英認定、大眾認可相互糾纏,其二是政治標準、經濟標準和純文學標準等之間斗爭激烈,互相內耗,缺乏統一的元話語。這些對當前文壇現狀的把握既針砭其身處其中的批評界,也延及文學界整體,是有力量的自我認知。
三、與作家的互動體驗
新批評理論認為文學作品是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的藝術客體,是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很多時候我們的文學批評一直在隔靴搔癢、隔山打牛,作家不接受、讀者也不接受,只是因為沒有深入作品的肌理,取消了作家與批評家共同建構的藝術有機過程而已。真正的批評不是一味粉飾,也不是干預文學創作,而是同作家一起互動感悟、交流。
房偉最初的文學批評就體現出這種特色。他的文學批評是從王小波開始的,這得源于他在國企心酸尷尬的生活體驗,轉型時代對他個體、生命擠壓產生了綿延不絕的彷徨與苦悶,一個年輕人蜷伏在王小波的文字世界里得到寄托和指引,所以房偉鐘愛王小波,將王小波的創作視為一個頑童對著無趣、平庸時代開的玩笑。
此后的文學批評工作,房偉也始終能夠深入細微之處,同作家一起感覺和討論,形成一種互動式的批評。比如他在論述張悅然的小說的時候,對《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一個細節進行了饒有意味的把握:“它的花朵被剪下來。噴薄的青綠色的血液在虛脫的花莖里流出。人把花朵握在手中,花朵非常疼。她想躺一會兒都不能。她的血液糊住了那個人的手指,比他空曠的眼窩里流淌出來的眼淚還要清澈。”③很明顯,這種物我合一的精神痛感激起了房偉的共鳴,他油然地欣賞這種觸覺、味覺和色彩合一的文字所帶來的奇異力量。在與作家創作互動的基礎上,他也能夠得出自己的結論:張悅然這種描寫的背后已經從“青春”的角度進入了更深層次的人與世界關系的思考。
或許在很多時候,房偉是帶著作家與批評家的兩重面具來進行批評,或者是更深層的虛擬的再創作,在批評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與作家的情感互動乃至身份的置換。這一點在他對“70后”作家的批評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在評論瓦當的時候,瓦當作品中的青春、性、親情和友誼,連同背叛、懷疑顯然在不斷的召喚著房偉的記憶,似乎瓦當書寫的正是批評家房偉的歷史與過往,而批評家房偉也會“失控”的進入作家的精神領域,并下出這樣的斷言:“在另一批人眼中,它同樣是一地雞毛的無聊時代,是欲望泛濫的粗鄙時代,是理想主義窮途末路的時代,是兩極分化的時代,是眾神狂歡的解構時代。然而,那些都是表象,在那些人心淪喪的欲望故事背后,是人心秘密的探究。”④在論述張楚小說的時候,房偉也止不住自己情感的呢喃:“70年代人的尷尬在于,沒有60年代人的機遇和50年代人的生活經歷,也沒有80年代人的物質條件和精神解放。70年代人的青春期,其實也是一個過渡時期:革命宏大話語在慢慢解體,卻依然在發揮作用,物質欲望羞羞答答,但卻日漸理直氣壯。這個年代粗鄙混亂,又有蓬勃的人性法則。而我們這些‘過渡年代’的青年,趕上理想主義的尾巴和計劃經濟的尾聲,對過去充滿留戀”⑤。這種對生活經驗的唏噓感嘆,對文學創作的遙遠寄托也延伸到了他對“80后”創作的批評上,他以寬容的態度對待這些更年輕的作家,并以含情脈脈的方式撫摸著他們鐫刻的文字:“80后相對于70年代寫作和60年代寫作,寫作心態更自由舒緩。他們沒有60年代人強烈的形式創新焦慮,沒有70年代人欲望敘事之下的絕望破碎感,卻有對傳統文學的邊界更開放的心態。創新的焦慮和欲望敘事,不是不存在,而是變得更為平等、對話和自由”⑥。房偉的互動式批評,蘊含著強烈的平等姿態,也是心靈的自我投入。這種互動的批評方式,為構建新文學批評標準和范式提供了借鑒。
房偉的互動式批評中還蘊含著詩意,寓于更多的自我寄托,充分地展現了屬于文學的奧妙與原初本色。當下文學批評領域中充斥的是晦澀艱深的符號拆解、無聊臆測的能指嬉戲,很少有批評家能夠從自我的感覺出發為文學批評貼上更多的感性元素標簽,房偉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形成了一種反撥。他在《憂郁的抒情與傷感—張楚小說論》中這么評價張楚的小說:“在文學外殼下放縱自己內心如水草般無邊蔓延的虛無,以及那些如冰雨般鋒利無比的黑暗。我們在傷人的快感中傷害自己,在拒絕拯救的時候,拒絕抒情,嘲笑抒情,如同安慰我們對黑暗的恐懼”⑦。在論述瓦當的小說《到世界上去》的時候,又使用了這樣的語言:“他神奇的語言,猶如月光下的飛鳥,滑翔于幽藍的湖面,閃爍著流動的金屬光澤,又好似清水中的刀子,冷冽逼人,又熱情犀利。他將小說語言做成燦爛之極的煙火,卻只燃放在堆滿白雪的無人山巔,陪伴明月清風,為世界上最高傲又最美麗的人喝彩”⑧。從這里可以看出,身兼作家、詩人與批評家于一身的房偉讓文學批評擁有了更多的立體元素,詩性的語言讓我們不僅僅是在看,同時也是在聽,在感覺,一種玄妙而又觸摸可及的通感世界向我們敞開,一種浪漫主義文學批評格調呼之欲出,美麗而又飽含韻味。
概而言之,房偉在文學批評與創作領域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這與其扎實的功底、端方的態度、敏銳的藝術靈感有密切的關系,也得益于其受教于優秀的導師。從房偉不長的批評道路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迅速的成長,也可以看到他不斷的自我超越。他既有廣泛的文學興趣,又能夠不做蜻蜓點水的嬉戲,體現出了寬廣、深邃與互動的多維綜合。我們對這位青年批評家投去贊許的目光和更多的期待,期待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繁榮做出更醒目和更突出的貢獻——而且我們相信這是不會有任何疑問的。
注釋:
①弗萊:《批評的剖析》,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②房偉:《“原創性”焦慮與異端的缺失》,《藝術廣角》2011年第4期。
③⑥房偉:《永遠的青春永遠的夢——從張悅然小說看中國80后文學創作之路向》,《理論學刊》2011年第3期。
④⑧房偉:《一部70后人的青春成長圣經——簡論瓦當的小說<到世界上去>》,《南方文壇》2012年第4期。
⑤⑦房偉:《憂郁的抒情與傷感——張楚小說論》,《百家評論》2013年第2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