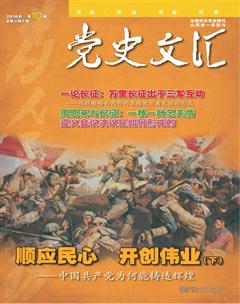遵義會(huì)議決議是如何形成的
李方祥+鄭崇玲
《中共中央關(guān)于反對(duì)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決議》是遵義會(huì)議期間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最重要的文件,一般稱為遵義會(huì)議決議,它首次系統(tǒng)地批評(píng)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的“左”傾錯(cuò)誤軍事路線。關(guān)于該決議的形成,一般認(rèn)為是張聞天在吸收了毛澤東在會(huì)議上發(fā)言的基礎(chǔ)上起草的,可是近些年有的學(xué)者對(duì)此提出質(zhì)疑,認(rèn)為上述看法“只下結(jié)論,不講根據(jù)”“很難令人信服”。①本文認(rèn)為,該決議的核心觀點(diǎn)主要來源于毛澤東,同時(shí)也融入了張聞天的認(rèn)知和理解,毛澤東關(guān)于紅軍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思想對(duì)張聞天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從而形成該決議。
一、遵義會(huì)議前張聞天已受毛澤東影響,這為他起草該決議打下基礎(chǔ)
張聞天在起草遵義會(huì)議決議前,實(shí)際上已受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影響。據(jù)張聞天妻子劉英回憶,遵義會(huì)議后的2月10日,在扎西開始傳達(dá)會(huì)議的精神,由張聞天作報(bào)告,他關(guān)于中國(guó)革命戰(zhàn)爭(zhēng)戰(zhàn)略問題的分析給劉英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說:“我本來只知道聞天理論強(qiáng),聽了傳達(dá),才知道他對(duì)戰(zhàn)略問題也有研究。后來聞天告訴我,這方面主要得益于毛主席。他同毛主席在長(zhǎng)征前曾在云石山一個(gè)小廟里同住過一段時(shí)間,長(zhǎng)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關(guān)于中國(guó)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略問題,他傾聽了毛主席的許多精彩議論。”
v
劉英在回憶中所說的毛、張?jiān)陂L(zhǎng)征前“曾在云石山一個(gè)小廟里同住過一段時(shí)間”,指的是1934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這段時(shí)間。很遺憾,2013年修訂出版的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沒有關(guān)于這段史實(shí)的記載,而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8月修訂版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有簡(jiǎn)略記載。②這也許是歷史的機(jī)緣,使張、毛兩人有機(jī)會(huì)聚在一起。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中,由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中央執(zhí)行委員、紅軍第十六軍軍長(zhǎng)孔荷寵叛變,并獻(xiàn)出他事先暗中畫的瑞金沙洲壩中央機(jī)關(guān)分布圖,從而使中央機(jī)關(guān)遭到國(guó)民黨“圍剿”軍的重點(diǎn)轟炸。同年8月,毛澤東隨中央政府機(jī)關(guān)搬遷至瑞金西面的云石山古寺,8月下旬張聞天在結(jié)束閩贛巡視后也搬至這里,這為毛與張進(jìn)一步增進(jìn)交往創(chuàng)造了條件。當(dāng)時(shí)的不少同志看到毛與張之間保持比較頻繁的聯(lián)系。毛澤民夫人錢希鈞時(shí)任中央政府黨總支副書記,因工作關(guān)系常到張聞天處匯報(bào)工作,她回憶:“毛主席住在祠堂里,他住在旁邊,吃飯都在一起。他經(jīng)常和毛主席在一起說說笑笑,談?wù)摴ぷ鳎芯繂栴}。”③其時(shí),毛多次與張交談,分析紅軍的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應(yīng)該說,毛的談話對(duì)張的確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據(jù)時(shí)任中央政府經(jīng)濟(jì)部長(zhǎng)吳亮平回憶,毛與張?jiān)驮S多重要問題細(xì)談過多次,雖無(wú)法知道每次的談話內(nèi)容,但知道談話的效果。有一次毛告訴吳,他和張長(zhǎng)談了一次,談的問題很多,在整個(gè)談話過程中,張是“全神貫注地傾聽他的意見”。而且張也對(duì)吳說,毛與他談話了,“談得很好”。④
此時(shí)的張聞天與黨中央總負(fù)責(zé)人博古、軍事顧問李德不同,他之所以能夠聽得進(jìn)去甚至初步接受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是因?yàn)樗麑?duì)中國(guó)革命的現(xiàn)實(shí)有了更多了解,且已有正反兩方面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的事實(shí)作鮮明的對(duì)比,這就使他逐步脫離了20世紀(jì)30年代初期的“左”傾教條主義,對(duì)毛關(guān)于紅軍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開始有了比較正確的認(rèn)識(shí)。他認(rèn)為毛“打仗很有一套”,“對(duì)毛澤東就很尊重”,“也常到毛澤東這邊來坐,兩個(gè)人談得很投機(jī)”。⑤另一方面,在廣昌戰(zhàn)役失敗后,張聞天對(duì)博古、李德的那一套軍事路線的錯(cuò)誤已有了切身體會(huì)和初步認(rèn)識(shí)。1934年4月27日,即廣昌失守的前夕,張為黨中央機(jī)關(guān)報(bào)《紅色中華》撰寫社論《我們無(wú)論如何要?jiǎng)倮窌r(shí),不指名地批評(píng)了博古、李德在反“圍剿”中所采取的“堡壘主義”與“分兵把口”的作戰(zhàn)部署,指出“這是單純防御的機(jī)會(huì)主義”的具體表現(xiàn),“這種傾向,實(shí)際上不但不能保衛(wèi)蘇區(qū),而且正便利于敵人的各個(gè)擊破。”文章還指出,“積極的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zhēng),把我們的基本游擊隊(duì)深入到敵人遠(yuǎn)后方與側(cè)翼去活動(dòng),是我們保衛(wèi)蘇區(qū)的最好辦法。而這種積極的活動(dòng),正是我們現(xiàn)在所極端缺乏的。”事實(shí)上,張預(yù)見的被敵人“各個(gè)擊破”的危險(xiǎn)局面,后來就成為事實(shí)。張同博古、李德的公開交鋒是在5月上旬召開的中革軍委關(guān)于廣昌戰(zhàn)役的總結(jié)討論會(huì)上,張同博古發(fā)生激烈爭(zhēng)執(zhí),批評(píng)廣昌戰(zhàn)役同敵人死拼是不對(duì)的,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以至遭受不應(yīng)有的損失。⑥
至于劉英回憶中所說的毛、張?jiān)陂L(zhǎng)征途中的交談和取得共識(shí),這些歷史情節(jié)早為史學(xué)界所知曉,此處不再贅述,只補(bǔ)充二則史料來說明:(1)錢希鈞在長(zhǎng)征途中有次去探望生病中的賀子珍,看見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一起蹲在地上看地圖。毛指著地圖說,這里應(yīng)該打沒有打,損失了多少人;那里不能打我們卻打了吃了虧等。張、王聽得心服口服,連連點(diǎn)頭。⑦(2)長(zhǎng)征初期任中央直屬縱隊(duì)政治部主任、負(fù)責(zé)保護(hù)照顧中央首長(zhǎng)的王首道回憶:開始長(zhǎng)征后張與毛、王經(jīng)常一起行軍、宿營(yíng),互相談心。他們談的中心內(nèi)容是王明路線在軍事上的嚴(yán)重錯(cuò)誤。張較多談到他同博古的爭(zhēng)論,毛則經(jīng)常耐心細(xì)致地分析“左”傾路線在軍事上的原則錯(cuò)誤。⑧
從上述情況看,張?jiān)谄鸩葑窳x會(huì)議決議之前,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在同毛的交流中認(rèn)可并接受了毛關(guān)于紅軍第一至四次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1943年12月16日,張?jiān)谘影舱L(fēng)筆記中也談到:“對(duì)于我個(gè)人說來,遵義會(huì)議前后,我從毛澤東那里第一次領(lǐng)受了關(guān)于領(lǐng)導(dǎo)中國(guó)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規(guī)律性的教育,這對(duì)于我有很大的益處。”這些思想自然凝結(jié)在遵義會(huì)議的決議之中。 遵義會(huì)議要弄清的最關(guān)鍵的問題是“什么是正確的軍事路線和錯(cuò)誤的軍事路線”,實(shí)際上也就是要通過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揭示博古、李德“左”傾軍事路線的錯(cuò)誤,只有通過總結(jié)才能夠確立毛澤東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及朱德、周恩來領(lǐng)導(dǎo)的第四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中毛澤東所確立的紅軍軍事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shù)。而這一段的歷史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毛在遵義會(huì)議之前已經(jīng)通過多次接觸交談告訴了張,從而說服了張,使他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cuò)誤和危害。endprint
二、從遵義會(huì)議出席者的發(fā)言看,毛澤東的長(zhǎng)篇發(fā)言是遵義會(huì)議決議基本內(nèi)容的最主要來源
遵義會(huì)議主要聽取了3個(gè)報(bào)告:博古作關(guān)于反對(duì)第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報(bào)告即“主報(bào)告”、周恩來作“副報(bào)告”和張聞天作“反報(bào)告”,此外重要的會(huì)議發(fā)言者還有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張聞天的“反報(bào)告”主要是批評(píng)博古、李德“左”傾軍事錯(cuò)誤路線,關(guān)鍵問題在于這個(gè)“反報(bào)告”的主要內(nèi)容是否與毛澤東討論過,或者說吸納了毛澤東的看法。遺憾的是,包括“反報(bào)告”在內(nèi)的上述3份文獻(xiàn)均已遺失。即便如此,一些遵義會(huì)議出席者的回憶史料,還是為大致弄清上述疑問提供了若干重要線索。據(jù)遵義會(huì)議出席者、紅三軍團(tuán)政委楊尚昆回憶,仍然“清楚地記得”張聞天“作報(bào)告時(shí)手里有一個(gè)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gè)提綱實(shí)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體創(chuàng)作而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主導(dǎo)的。”⑨1986年8月30日,楊尚昆在接受張聞天傳記組訪問時(shí)再次確認(rèn),遵義會(huì)議上張聞天的“反報(bào)告”中“總結(jié)長(zhǎng)征前面這一段,基本的東西是毛主席的。因?yàn)槟莻€(gè)時(shí)候他很尊重毛主席”。⑩也就是說,張的“反報(bào)告”不僅僅代表他個(gè)人的看法,實(shí)際上在遵義會(huì)議前他多次與毛、王討論過,接受了毛的正確意見,因而也可以說“反報(bào)告”同時(shí)代表了毛的看法。
遵義會(huì)議出席者基本上都發(fā)了言,批評(píng)博古、李德的錯(cuò)誤指揮,有的甚至聲色俱厲,比如朱德素來溫和寬厚但會(huì)上卻言辭激烈甚至提出要改變錯(cuò)誤領(lǐng)導(dǎo),“如果繼續(xù)這樣錯(cuò)誤的領(lǐng)導(dǎo),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輥?輯?訛在與會(huì)者的發(fā)言中,毛在張“反報(bào)告”后作的長(zhǎng)篇發(fā)言,給與會(huì)者留下深刻印象。據(jù)楊尚昆回憶:“這就講得比較厲害一點(diǎn)”,?輥?輰?訛“時(shí)間長(zhǎng)達(dá)一個(gè)多小時(shí)”。?輥?輱?訛毛的長(zhǎng)篇發(fā)言不僅綜合吸收了其他發(fā)言的看法,而且系統(tǒng)闡述了紅軍反“圍剿”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可以說是分量最重,內(nèi)容最全面,思想最深刻,對(duì)眾人最具說服力,給人的印象是“帶結(jié)論性”。李德的中文翻譯伍修權(quán)列席了遵義會(huì)議,據(jù)他回憶:“像通常一樣,他(指毛澤東)總是慢慢地先聽人家的意見怎么樣,等他一發(fā)言就幾乎是帶結(jié)論性的了。他講了大約一個(gè)多小時(shí),同別人的發(fā)言比起來,算是長(zhǎng)篇大論了。”
遵義會(huì)議上挨批評(píng)的李德在回憶錄中也承認(rèn)毛澤東的長(zhǎng)篇講話“實(shí)際上這是主要的報(bào)告”,遵義會(huì)議決議“實(shí)際上這是經(jīng)過編者加工的毛澤東的講話”。?輥?輲?訛他這“經(jīng)過編者加工”指的就是張執(zhí)筆撰寫,基本內(nèi)容來自毛的發(fā)言。李德在回憶錄中重點(diǎn)攻擊、污蔑毛,較詳細(xì)地引述了毛在會(huì)上的發(fā)言內(nèi)容。經(jīng)過筆者的文本對(duì)比、查證,發(fā)現(xiàn)他所引用的毛的發(fā)言恰恰就是決議的內(nèi)容。文本對(duì)比情況參見下表:
上述文本的對(duì)比分析表明,李德在回憶錄中所引述的毛澤東的發(fā)言內(nèi)容與決議不僅基本內(nèi)容一致,甚至不少文字表述也基本相同或相似。伍修權(quán)的回憶錄中并沒關(guān)于李德在會(huì)上講話、他做記錄的情節(jié),只是說李德坐在會(huì)議室門口處低頭吸煙,而且李德回憶錄又是在60年代末開始陸續(xù)撰寫,事隔30多年僅憑記憶怎能對(duì)毛的發(fā)言內(nèi)容記得如此清晰甚至有的文字表述幾乎完全相同?若從巧合角度解釋顯然難以服眾,筆者認(rèn)為最有可能的是,李德在引述的發(fā)言內(nèi)容時(shí)使用了決議的文本作參考。那么,在缺乏毛發(fā)言文本的情況下,為何用決議來代替毛的發(fā)言呢?最可能或合理的推理是決議主要內(nèi)容是依據(jù)毛發(fā)言內(nèi)容起草的。否則,若毛的發(fā)言內(nèi)容與決議沒直接關(guān)系或關(guān)系不大,那么李德在回憶錄中需引述毛發(fā)言內(nèi)容時(shí)也不可能去參考決議。此外,李德回憶錄中提到一個(gè)值得注意的細(xì)節(jié)是毛澤東發(fā)言時(shí)一反往日的習(xí)慣,作報(bào)告時(shí)手里拿著一份顯然是經(jīng)過詳細(xì)擬定的講稿。?輥?輳?訛多位遵義會(huì)議出席者的回憶均提到張聞天發(fā)言時(shí)有一個(gè)提綱性質(zhì)的材料,除李德此處的回憶外,其他人并沒提到毛發(fā)言時(shí)也有一個(gè)提綱。
遵義會(huì)議決議是張聞天在充分吸收會(huì)議上的發(fā)言意見的基礎(chǔ)上起草的,因而可以說是集體意見的凝結(jié)。其中,從會(huì)議討論和發(fā)言的情況看,毛澤東的長(zhǎng)篇發(fā)言是代表會(huì)議的主導(dǎo)性意見、傾向性意見,成為張起草決議稿的核心觀點(diǎn)的基礎(chǔ)。遵義會(huì)議決議的核心問題是明確指出并批評(píng)了博古、李德在五次反“圍剿”中存在著錯(cuò)誤的軍事路線,這是五次反“圍剿”中特別是長(zhǎng)征以來毛、張、王等同志揭露和批評(píng)的問題,也是毛長(zhǎng)篇發(fā)言的重點(diǎn)和中心,這是貫穿決議的一條主線,更是毛對(duì)決議內(nèi)容的形成做出的最主要的貢獻(xiàn)。在遵義會(huì)議精神傳達(dá)前,黨內(nèi)不少同志盡管對(duì)“左”傾錯(cuò)誤領(lǐng)導(dǎo)者的“正確性”產(chǎn)生過很大懷疑,但還未從根本上認(rèn)識(shí)到存在一條錯(cuò)誤的軍事路線,更不明確錯(cuò)在哪里、如何克服。此問題的“蓋子”,是在遵義會(huì)議上毛的發(fā)言以及決議里揭開的。紅五軍團(tuán)政委李卓然接到參加會(huì)議的電報(bào)通知后,趕往遵義時(shí)會(huì)議已開始,幾個(gè)報(bào)告已作完,他去見毛澤東時(shí)說此前“只知道仗打得不像樣,并不知道李德的什么路線”。?輥?輴?訛李維漢也指出,在扎西會(huì)議上聽了張關(guān)于遵義會(huì)議的傳達(dá)后,“解開了我思想上的許多疑團(tuán),比較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王明‘左傾路線的一些錯(cuò)誤,特別是在軍事路線上的錯(cuò)誤”。?輥?輵?訛
三、決議反映了張聞天的獨(dú)立思考,但闡述的具體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基本源于毛澤東領(lǐng)導(dǎo)下的紅軍反“圍剿”斗爭(zhēng)的實(shí)踐總結(jié)
在遵義會(huì)議之前,特別是廣昌保衛(wèi)戰(zhàn)到遵義會(huì)議期間,張聞天已經(jīng)開始從“左”傾錯(cuò)誤路線中逐漸分離出來,在一些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初步批評(píng)了“單純的堡壘主義”、“分兵把口”等“左”傾錯(cuò)誤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比如,1934年5月1日《紅色中華》發(fā)表《我們無(wú)論如何要?jiǎng)倮贰?934年9月7日《斗爭(zhēng)》第71期發(fā)表《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wù)》、1934年9月29日《紅色中華》發(fā)表《一切為了蘇維埃》。這些文章主要闡述了以下兩個(gè)問題:一是批評(píng)沒有抓住福建事變的有利時(shí)機(jī),打破蔣介石對(duì)中央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明確提出“要堅(jiān)決反對(duì)‘左的關(guān)門主義者”,“號(hào)召一切反動(dòng)營(yíng)壘中真正愛國(guó)的分子同我們?cè)谝黄馂橹袊?guó)民族的生存而戰(zhàn)”,?輥?輶?訛與個(gè)別上層分子有可能建立起統(tǒng)一戰(zhàn)線。二是指出“分兵把口,同堡壘主義……是單純防御的機(jī)會(huì)主義傾向”的具體表現(xiàn),批評(píng)了那種把“進(jìn)攻路線”簡(jiǎn)單幼稚地理解為“一種只是向上的,直線式的,不斷勝利的行動(dòng)”,提出“積極的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zhēng),把我們的基本游擊隊(duì)深入到敵人遠(yuǎn)后方與側(cè)翼去活動(dòng),是我們保衛(wèi)蘇區(qū)的最好辦法”。?輥?輷?訛endprint
實(shí)際上,彭德懷、聶榮臻等不少紅軍將領(lǐng)都對(duì)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提出過尖銳批評(píng)或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不滿,但能夠從理論層面初步分析和批判的,一是毛澤東,二是張聞天,這也反映出張?jiān)诶碚撍伎挤矫婢哂幸欢ǖ膬?yōu)勢(shì)及對(duì)蘇區(qū)斗爭(zhēng)實(shí)際有更多的了解。也正是由于張對(duì)“左”傾軍事指揮錯(cuò)誤有了深刻的認(rèn)識(shí),因而在起草遵義會(huì)議決議時(shí)融入、發(fā)揮了自己之前的認(rèn)識(shí)。但我們還應(yīng)實(shí)事求是地看到,此前張對(duì)博古、李德錯(cuò)誤指揮的批評(píng)還是很不夠的。由于他當(dāng)時(shí)還未徹底擺脫“左”的思想局限和完全認(rèn)識(shí)到博古、李德的錯(cuò)誤指揮是整個(gè)軍事路線的錯(cuò)誤。而且,張盡管肯定了一些具體的戰(zhàn)術(shù),但并沒從中國(guó)革命戰(zhàn)爭(zhēng)規(guī)律的高度提出紅軍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原則。所以,僅憑張上述發(fā)表的文章還不足以支撐起遵義會(huì)議決議批判“左”傾錯(cuò)誤軍事路線的系統(tǒng)觀點(diǎn)。而毛在這方面的思考、闡述和概括顯然要比張更深刻成熟,他在領(lǐng)導(dǎo)根據(jù)地反“圍剿”斗爭(zhēng)中逐漸探索總結(jié)出一套符合中國(guó)基本國(guó)情的紅軍作戰(zhàn)原則,在他的遵義會(huì)議長(zhǎng)篇發(fā)言中進(jìn)一步具體化和豐富發(fā)展了。張正是吸收了毛發(fā)言中的精髓,才起草了遵義會(huì)議決議。
從遵義會(huì)議決議可以看到,它所肯定的紅軍應(yīng)堅(jiān)持的一整套正確的軍事原則,比如“決戰(zhàn)防御”“集中優(yōu)勢(shì)兵力”“各個(gè)擊破敵人”“速?zèng)Q戰(zhàn)”“在運(yùn)動(dòng)戰(zhàn)中消滅敵人”恰恰是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時(shí)期及中央蘇區(qū)三次反“圍剿”革命斗爭(zhēng)實(shí)踐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特別是他親自領(lǐng)導(dǎo)的紅軍三次反“圍剿”集中體現(xiàn)了紅軍機(jī)動(dòng)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標(biāo)志著積極防御戰(zhàn)略理論和作戰(zhàn)原則的形成。尤其是第一次反“圍剿”,是紅軍從游擊戰(zhàn)爭(zhēng)發(fā)展到正規(guī)戰(zhàn)爭(zhēng)的偉大轉(zhuǎn)變所取得的首次勝利,郭化若在毛澤東的直接領(lǐng)導(dǎo)下參加了三次反“圍剿”,把第一次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的特點(diǎn)概括為以下4個(gè)方面: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zhàn)略方針,把敵人誘到我革命根據(jù)地內(nèi)打,以便發(fā)揮人民戰(zhàn)爭(zhēng)的威力;堅(jiān)持慎重初戰(zhàn),沒有準(zhǔn)備好不打,沒有把握不打;堅(jiān)持打運(yùn)動(dòng)戰(zhàn),堅(jiān)持打運(yùn)動(dòng)之?dāng)常粓?jiān)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zhàn),作戰(zhàn)方式是四面包圍敵人,主力從敵之后側(cè)攻擊。第一次反“圍剿”戰(zhàn)爭(zhēng)“開創(chuàng)了殲滅戰(zhàn)的典型,對(duì)以后幾次反 ‘圍剿作戰(zhàn)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輦?輮?訛在敵強(qiáng)我弱的嚴(yán)酷戰(zhàn)爭(zhēng)環(huán)境下,實(shí)施積極防御是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并發(fā)展壯大的最核心的問題,這同時(shí)也是毛澤東從井岡山革命斗爭(zhēng)到三次反“圍剿”期間逐步探索形成的紅軍作戰(zhàn)戰(zhàn)略原則。而這些積極防御戰(zhàn)略的軍事原則,在遵義會(huì)議決議中得到充分反映。中央紅軍長(zhǎng)征到達(dá)陜北后,毛澤東全面、深刻地總結(jié)了中國(guó)紅軍革命斗爭(zhēng)的歷史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發(fā)表了《中國(guó)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略問題》。他指出:“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yīng)當(dāng)時(shí)情況的帶著樸素性的游擊戰(zhàn)爭(zhēng)基本原則,已經(jīng)產(chǎn)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dāng)尺M(jìn)我退,敵據(jù)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到了中央蘇區(qū)第一次圍剿時(shí),‘誘敵深入的原則被提出來了,而且應(yīng)用成功了。等到戰(zhàn)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zhàn)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shí)是軍事原則的新發(fā)展階段,內(nèi)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的是從前的樸素性不見了,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gè)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括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括了戰(zhàn)略防御與戰(zhàn)略進(jìn)攻的兩個(gè)階段,在防御時(shí)又包括了戰(zhàn)略退卻與戰(zhàn)略反攻的兩個(gè)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fā)展罷了。”?輦?輯?訛
綜上所述,遵義會(huì)議決議的核心觀點(diǎn)來源于毛澤東(特別是毛澤東在會(huì)議上的發(fā)言),也融入了張聞天的觀點(diǎn)和實(shí)踐;同時(shí)進(jìn)一步證明了毛澤東在遵義會(huì)議這一重大歷史轉(zhuǎn)折關(guān)頭中所起的突出作用。
注釋:
① 何方:《黨史筆記》上冊(cè),利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頁(yè)。
② ⑥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頁(yè)、160頁(yè)。
③ ⑦ ⑩ ?輥?輰?訛 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200位老人回憶張聞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頁(yè)、60頁(yè)、40頁(yè)。
④ 《吳亮平文集》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頁(yè)。
⑤ 《劉英紀(jì)念集》編輯組、無(wú)錫市史志辦公室編:《劉英紀(jì)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yè)。
⑧ 《回憶張聞天》編輯組編:《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頁(yè)。
⑨ 楊尚昆:《追憶領(lǐng)袖戰(zhàn)友同志》,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頁(yè)。
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上,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頁(yè)。
《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頁(yè)。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guó)紀(jì)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頁(yè)、第123頁(yè)。
同上,第121頁(yè)。
轉(zhuǎn)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傳》,當(dāng)代中國(guó)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頁(yè)。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頁(yè)。
《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頁(yè)、第31頁(yè)。
《張聞天文集》一,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頁(yè)。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yè)。
竹內(nèi)實(shí)編:《毛澤東集》第5卷,北望社1970年版,第125-126頁(yè)。
(本文選自楊河、趙軍主編的《遵義會(huì)議研究——紀(jì)念遵義會(huì)議召開80周年》一書,此書2015年3月由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標(biāo)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目為“遵義會(huì)議決議存疑考證”)
(責(zé)編 孟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