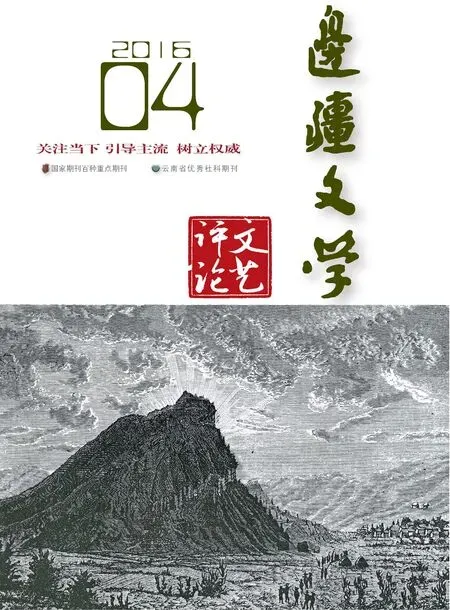接受美學:張愛玲的創作觀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
——以《金鎖記》《傾城之戀》為例
◎翟 悅
接受美學:張愛玲的創作觀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以《金鎖記》《傾城之戀》為例
◎翟 悅
二十世紀西方的接受理論富有啟示性地從讀者理解和接受的角度進行文學研究,實現了西方文論研究從“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讀者中心”的轉向。我們通過對張愛玲創作態度的了解,發現她的小說所呈現的特色與其接受美學相聯系的創作觀密不可分。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聯邦德國的康斯坦茨學派,著意于文學的接受研究,將文學研究的重點放在讀者的接受上。在接受美學看來,讀者對文本的接受過程就是對文本的再創造過程,文學作品不是由作者獨自生產出來,而是由作者和讀者共同創造的,可見讀者對作品并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具有能動的創造力,因此讀者的地位不容忽視。然而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滿足和期待是最常見的兩種心理狀態,它們的出現也使得讀者和作者之間產生一種張力,作者從中獲得了使用創作技巧的空間,讀者和作者的關系變得微妙起來。正如英伽登所認為的那樣,一部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物,必然和作者的生活經歷,思想意識和創作才能有關。但同時英加登也提出,作者在創作一部文學作品時,不僅僅是為了反映他的價值觀念,而且也是為了讓他創作的這部作品去接受讀者對它的具體化,由此可見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和作者的雙向互動使得作品的價值變得豐富起來。張愛玲小說之所以擁有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一方面得益于獨具匠心的創作手法,另一方面就是她“讀者至上”的文學創作觀。
一、創作觀里的“期待視野”
張愛玲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要迎合讀書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是說人家所要說的,二是說人家所要聽的。”可見她很在意讀者對文本的接受程度。而張愛玲小說擁有一批特定的讀者群,他們多半是上海小市民,傳統戲劇,通俗小說,禮拜六派的鴛蝴小說對他們的閱讀習慣產生重要的影響。所以張愛玲小說風格必然要迎合大眾的審美趣味才能獲得讀者的青睞。從這一點來看,不得不說她的創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讀者興趣的影響和限制。而讀者對文學類型,風格和語言的審美經驗實質上是他們的閱讀經驗所構成的思維定向,姚斯稱其為“期待視野”。接受美學認為,在閱讀活動中,與接受主體的期待視野相對的是接受對象即作品的客觀化。任何一部作品的產生,必須與一個客觀的標準相符,才能獲得接受,而這種超主體的客觀標準恰好又是期待視野。那么張愛玲在創作時就會盡力滿足觀眾的期待視野,說他們想聽的故事。因此她堅定地說道:“要爭取眾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眾興趣范圍的限制。”她深知大眾對文學作品的取舍并不完全基于文學價值,她也了解家傳戶誦的更多是感傷溫婉的小市民的道德愛情故事,她對自己的創作方向和風格清楚得很。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小說從形式到內容上都有著中國傳統小說的影子,中國傳統小說多根據悲歡離合的故事情節來安排內容且結構完整,人物形象生動鮮明。張愛玲小說也是如此,她筆下的人物命運,故事結局都交代得很清楚,內容上也多是男女日常家庭生活和婚姻愛戀等一系列故事,延續了舊小說的言情傳統。但僅僅符合讀者的期待視野又是遠遠不夠的,要想能夠吸引讀者并且使作品的藝術魅力得已長久的保持下去,就必須“此外再多給他們一點別的,作者有什么可給的,就拿出來。”張愛玲又似乎準備在大眾所要求的客觀標準內給他們的審美趣味多添些什么,而這點也正好是她的作品與傳統通俗文學作品的不同之處。張愛玲對她個人創作觀的細致把握使其作品受到大眾青睞,尤其是對小說中沖突環節的設計是她作品創作特色大放光彩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小說在描寫人物復雜的心理時,往往正是結合著動作化的敘述來進行的,可見在這里,張愛玲確實汲取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精髓,迎合了讀者大眾的審美期待。例如小說《金鎖記》向我們講述了家里開麻油店的曹七巧由哥哥做主把她嫁給了有錢的姜家二爺,可惜她的丈夫患有骨癆,嫁過去的七巧雖然有錢了,但是在姜家依舊遭受排擠并且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在她和三爺季澤的調笑中我們看見了她被壓抑的情欲,在對兒女生活無情的控制中我們看見了她被金錢扭曲的人性,曹七巧套在身上那“黃金的枷”把她的人性消磨殆盡。作者在《金鎖記》中設計了多個沖突場景,并且在描寫沖突中人物的狀態時恰恰就遵循了傳統小說從過程敘述中突出動作細節同時把人物的心理活動一起表現出來的手法。例如姜季澤和曹七巧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沖突是分家后的季澤日子過得開始沒落,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決定去找七巧幫忙,想利用七巧對他的感情來賣掉田地去買他的房子。在七巧的小心試探下,他的目的最終暴露出來,而曹七巧也惱羞成怒將季澤哄趕出去。文本中作者對曹七巧在金錢和愛情間糾葛的心理描寫可謂是下了一番功夫“他難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錢——她賣掉她的一生換來的幾個錢?僅僅這一轉念便使她暴露起來。”同時面對季澤的離去,七巧失魂落魄的心態通過幾句簡單的動作刻畫就變得更加生動起來。“七巧扶著頭站著,倏地掉轉身來上樓去,提著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絆絆,不住地撞到那陰暗的綠粉墻上,佛青襖子上站了大塊的淡色的灰。”這句伴隨著人物心理的動態化敘述,使人物描寫質感增強且富有神韻。當然,除此之外我們更多的是看見張愛玲的別具匠心之處,也就是她多給觀眾的那么“一點”。姚斯說過:“新藝術手法打破了舊有的小說傳統。小說中所表現的人物的道德判斷隱約流露于描寫之中,作者的主觀意志全然退入背景。然而,小說卻依舊能夠激化或提出新的社會生活問題……”顯然張愛玲小說中對人物心理精細的刻畫以及對中國傳統意象采取新的使用手法,將使讀者原有的審美閱讀經驗遭到破壞,群眾必須建立起新的期待視野才能重新認識和思考世界,同時換一個角度來看,她的創作特色也因此得到了體現。例如《金鎖記》中曹七巧的命運通過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心理刻畫以及意象象征的方式烘托出來。當七巧將蘭仙氣走后,她和季澤有了一次單獨對話的機會,七巧將心底對丈夫失望向季澤傾訴之后并質問到:“難不成我跟了個殘廢的人,就過上了殘廢的氣,沾都沾不得?”這里還有一段是對曹七巧身上配飾的描寫:“她睜著眼直勾勾朝前望著,耳朵上的實心小金墜子像兩只銅釘把她釘在門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標本,鮮艷而凄愴。”配飾其實象征著她生存狀態的一種表現,實心的小金墜子就像是黃金的枷鎖,將七巧牢牢的釘在遠處,她想得到愛卻無法靠近,她的命運會像蝴蝶標本一樣被永遠的束縛住,所有的欲望都將動彈不得。面對質問的季澤,作者給予了一段從男性視角出發的心理特寫,姜季澤雖心有所動,但是他把七巧為人看了個透,隨后便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可見七巧的愛是注定不會有回報,她的命運也是注定被金子永遠囚禁住。此外,小說中長安和七巧的幾次沖突也是通過人物復雜心理表現出來的,例如長安在多次聽到母親對她婚約的詆毀后經過幾番思想斗爭終于下定決心同童世舫解除婚約等。
在對中國傳統意象描寫時,作者也有新的突破,像鏡子,月亮和飾品等均融入了人物的主觀感受并且伴隨著他們出現,這樣一來物品就具有了暗示人物命運發展的特殊功效,使故事情節充滿了象征色彩。張愛玲在正面描寫戲劇沖突時所采用的心理描寫和象征手法等使故事情節變得生動起來,而讀者既能從中捕捉到人物的性格也能對劇情的發展產生更多的期待。在滿足了讀者閱讀期待的基礎上,張愛玲超越了大眾心中的客觀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她對傳統讀者大眾對于小說所期待的那種充滿理想主義的大團圓式結尾的突破,也是她獨有的創作風格。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我們會發現故事里的人物的人生雖然結束了,但故事仿佛不會結束。就像《金鎖記》的結尾,七巧在回憶過去的淚水里死去,而作者卻在結尾附上這樣一段話:“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又如《傾城之戀》的結尾:“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火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戀愛結婚、愛無回報、生老病死的循環在張愛玲的小說里好像真的是一輩子都寫不完,這樣的結尾讓人讀后感到回味無窮。同時,在讀張愛玲的作品時我們發現她的故事更多的會有一種“悲”的氛圍,而在組成中國傳統小說情節的喜,怒,哀,樂四個喻像中,張愛玲為何偏偏對“哀”情有獨鐘?這從她的創作觀中我們可以得知其中緣由。“快樂這東西是缺乏興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樂。所以沒有一出戲能夠用快樂為題材。”在她看來,只要是故事就須有點戲劇性,就要有沖突,有麻煩,還要有隱隱的悲涼感,否則就無從打動讀者,引發他們的情緒。在中國傳統小說里,人物雖然經歷了種種磨難但結局總是美好的。而張愛玲小說中的那些男男女女即使在歷經世俗情愛的折磨和苦難后,疾病和死亡的陰影也隨之而來。正如她所說的那樣:“生命即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了好。麻煩剛剛完了,人也完了。”可偏偏打動讀者的就是她給的這些沖突,磨難和蒼涼。她筆下的那些男女主人公們在歷經滄桑后大多都并沒有收獲到他們所期待的幸福,無論是《金鎖記》里的曹七巧還是《沉香屑 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她們的愛情和命運都像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輕輕一劃,便緩緩落幕了。即使是給予了圓滿結局的《傾城之戀》,讀起來還是能感受到一股子悲惘的冷勁,在時代洪流的涌動中,人是渺小的,他們的命運豈能由自己把握?那些過往無論是美好還是不堪,無論是否為爭取幸福而做過努力,戰爭都會在一瞬間將所有抹殺,最后留下的終究是悲歡離合,曲終人散。打破了傳統小說閱讀的審美標準,使人們既定視野和文本之間出現不一致,在增強閱讀感受的同時賦予人們新的感覺方式,產生“視野的變化”,張愛玲小說的藝術魅力據此表現出來。正如姚斯所說的那樣:“作品的藝術特性取決于“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審美經驗與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張愛玲對作品沖突的設計以及對所謂給讀者“多那么一點”的恰到好處,使她的小說即符合讀者大眾的審美期待又在結局時引發讀者沉思,從而主動去追尋作者想傳達的觀點和想法,形成了文本和讀者之間的有效互動,使作品創作的價值和意義豐富起來。
二、創作觀下的“召喚結構”
“召喚結構”這個術語是由接受美學派人物伊瑟爾提出來的。他認為文本和讀者之間沒有建立意圖的調節語境,兩者之間就產生了不對稱性,然而要克服這種不對稱性,讀者必須在一定范圍內由文本引導,而文本控制交談的方式是讀者和文本交流過程中最重要的方面,因此他提出“召喚結構”作為主要調節方式。
在分析張愛玲的作品時,我們依舊能夠發現,這位以“讀者至上”為創作理念的作家,巧妙地運用了“召喚結構”召喚讀者通過想象把小說中存有的不確定性或空白與他們的生活經歷聯系在一起,從而進行填充和解釋,使讀者在這樣的空間里享受閱讀的樂趣。而她本人創作風格也因使用“召喚結構”的方式而再次變得明朗起來。首先,張愛玲小說的題目大多都含有類似于像金鎖、紅玫瑰、 第一爐香、 茉莉香片等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所以看見題目時,讀者第一感覺就是很熟悉,他們自然就會把題目和生活中與這些事物相接觸時的經歷聯系到一起,從而進一步想知道作者為何會以這樣的日常事物為題,她擬設這樣一種看似與主題毫無聯系的題目究竟有什么目的?作品題目中所提到的事物是否就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那些事物…….讀者對于作者精心設置具有模棱兩可性的命題產生了好奇心,他們將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對文本進行細讀。在其閱讀完作品后,意識到小說題目其實與人物性格及其命運相聯系時,這就與讀者當初的設想多少有些悖離,因此便會產生對日常生活進行重新認識和反思的想法,這樣文本內容變得意味深長起來,“召喚結構”的作用得以發揮。
其次便是張愛玲對小說故事情節安排時“召喚結構”的使用。就像伊瑟爾認為的那樣,空白主要還在于聯系文本的不同部分,在大多數敘述中,故事線索突然中斷,又從另一個視角或預料之外的方向繼續下去,其結果造成意義的空白,有待讀者補充完成。《金鎖記》中曹七巧把來到姜家探望她的哥嫂送走后,回憶起自己還是黃花閨女時的往事,當筆觸延宕到床上睡著的沒有生命活力的七巧丈夫時,作者筆鋒一轉,緊接著出現的下一段便是描寫被風吹得搖搖晃晃的回文雕漆長鏡,鏡子里的翠竹簾子在第二次定睛看時早已褪了色,看鏡子的七巧也老了十歲。這里作者僅用鏡子等意象就把歲月流逝簡單明了的引了出來,顯然和前一段的小說內容產生了時間差,由此在文本中也造成了一定空白。同樣情況還出現在小說《傾城之戀》中,當白流蘇第二次去香港做了范柳原的情婦后,他們在巴而頓租下了一所房子,而此時范柳原回了英國,在空空蕩蕩的房間里,白流蘇被寂寞和空虛緊緊的圍著動彈不得。寫到這里,隨后的一段便是“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戰爭的爆發打破了白流蘇日日夜夜循環往復的寂靜和孤獨,然而作者在里有意添上了時間點,使得之前的敘述時間變得模糊起來,白流蘇究竟在這里住了多久是一個月還是一年使人不得而知,此后小說情節的敘述也開始加快,這樣一來也同樣使文本產生了空白。“空白”的出現將召喚讀者對文本進行不斷的探索和追問,從而調動自己的想象力和個人經驗去努力填補空白,使文本內容在閱讀過程中變得更加具體化。同時這些空白又服從于作品的完成部分,并在已經完成部分的引導下,使作品實現意義的建構傳遞出作者想要闡述的觀點。在分析張愛玲的創作原則時發現,她曾經說過自己喜歡參差對照的寫法,因為這種寫法在她看來是貼近現實的。那么通過對《金鎖記》《傾城之戀》《沉香屑 第一爐香》等閱讀,可看見張愛玲在塑造人物時有意加強了女性形象,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對男性形象的一種弱化。中國傳統道德中對女性的束縛是極為嚴厲的,尤其是對女性欲望方面的壓抑。傳統女性的貞潔保守的形象仿佛是一道標桿深扎于每個人的心里。但是張愛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無論是曹七巧還是白流蘇或者是梁太太,都與中國傳統意識中的形象大相徑庭。她們要么是伶牙俐齒,刁蠻善妒,要么就是主動追求異性,與男性在情感上展開周旋。男性形象大多都是遺老遺少,不論是《金鎖記》里的姜季澤和長白,還是《傾城之戀》里白流蘇的三哥,四哥,他們仿佛一個個都找不到明確的生存目標,不是吸鴉片逛窯子就是坐吃山空流連賭場,日子過得平淡無奇,在中國傳統父權制度“庇佑”下他們把生命消磨了個干凈。這種人物呈現的強烈反差,似乎否定了長期以來在讀者生存環境中占據統治地位的道德標準和社會規范,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對社會原有的價值體系提出強有力的挑戰。這就與伊瑟爾提出的另一種重要“空白”即由所謂“否定”引起的“空白”有異曲同工之處。而讀者在填補空白時,能夠獲得一種視點,通過這個視點來看那些曾經被接受的社會規范就會變得腐朽不堪了。因此好的文學作品在喚起讀者閱讀期待時更應該否定它,從而能使讀者從一個新的角度去重新審視生活,發現他生存環境中流行規范所固有的缺陷。從這個意上說,張愛玲“參差對照”的創作觀無疑會形成這種由“否定”造成的空白,讀者在填補空白時其實也是在改變過去既定審美觀念的基礎上對社會重新進行審視。
三、創作觀下的“審美交流”
在張愛玲談其創作時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所謂的“濫調”其實就是她筆下有關于飲食男女的衣食住行,婚姻戀愛等平凡簡單的一系列市民生活。作為這一類的普遍社會現象,作家安排什么樣的題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讀者是否能夠從那千篇一律的日常百態中有所領悟。“許多留到現在的偉大的作品,原本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事過境遷后,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現了新的啟示,是那作品成為永生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如果脫離了讀者的參與,是無法獨立產生意義的,作品的真正價值在于讀者所做出的各種不同的解釋和永無止境的解讀。所以張愛玲的創作理念最終還是希望通過文學文本達到與讀者進行交流的目的,通過對文本的構建去指引讀者發現她對生活的感悟,進而他們能夠根據自身的經驗獲得對個人的理解,也只有這樣她的創作才具有永恒意義。就像姚斯所認為的那樣一部過去作品不斷延續的生命是通過疑問與回答動態的闡釋而形成的并不是通過單方面永久的疑問或是回答。可見張愛玲“讀者至上”的創作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和姚斯的見解也是不謀而合的。為了使觀眾能夠通過作品的閱讀獲得對自身的一個理解,張愛玲想必也是考慮到她讀者大眾群的實際閱讀水平,所以創作時并沒有一味地采用繁復的技巧,相反在她的小說中我們往往更能看到一些自然樸實貼近市民生活的細節描寫,而這其實和她說過喜歡“素樸”的觀點是一樣的。用簡單的筆觸還原復雜的生存狀態是最容易走進讀者內心世界的方法,張愛玲對于生活細節的刻畫往往更能使讀者大眾深有感觸,并能夠更好地與他們形成交流。例如她對筆下男女人物服飾的精細描寫,不僅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和精神狀態,同時也暗含了作者想要表達的生存觀念。例如《金鎖記》中對曹七巧在不同時期裝扮的描寫:“一只手撐著門,一只手撐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條雪青洋縐綢手帕,身上穿著銀紅衫子,蔥白線香滾,雪青閃藍如意小腳褲,瘦骨臉兒,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 “世舫回過頭去,只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兩件不同風格的服飾,表現出曹七巧不同時期心理狀態的改變。顯然在第一句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的七巧剛嫁入姜家不久,色彩的精心搭配看還是很明亮的,這其實就能反映出她作為一個年輕女子內心的柔情。丈夫患有軟骨病,她缺乏情感的滋潤,但越得不到溫情就會越想要得到,內心欲望的不斷涌現也伴隨服飾的穿著表現出來。第二個句子中“青灰”“龍”等簡單的字眼就能展現出此時此刻七巧的生活狀態。青灰屬于暗色系,曹七巧服飾色彩從鮮艷到灰暗,說明她的精神狀態必然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暮年時期的她已經一無所有,她知道兒女恨透了她,也不再有什么情感上的欲望有的只剩下連自己也弄不懂的扭曲心態。服飾上的“龍”也能體現出七巧在家中地位的改變,她不再是受排擠者,而是生活在這個獨立門戶里的掌權人,可以操控著兒女的人生。從服裝款式和顏色的變化,暗示出七巧的生命逐漸褪去光彩,靈魂也漸漸被黑暗所吞沒。此外文中對長白長安服飾的描寫也頗有意味。“七巧的兒子長白,女兒長安,年紀到了十三四歲,只因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有七八歲光景。在年下,一個穿著品藍摹本緞棉袍,一個穿著蔥綠遍地錦棉袍,衣服太厚了,直挺挺撐開了兩臂,一般都是薄薄的兩張白臉,并排站著,紙糊的人兒似的。”長白長安身體瘦弱卻被安排穿上厚厚的棉袍把全身裹得嚴嚴實實,實際上這是七巧對兒女精神和肉體上的一種控制和約束,兩人即便是在“緞棉袍”“錦棉袍”華麗的裝扮下也依舊透露出一股“死氣沉沉”,像紙糊的人兒似的活著。有人說張愛玲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她看透了人們在奮斗過后得到的始終還是人生的虛無和幻滅。可即便如此在我看來張愛玲始終是個對生命抱有向往,對生存抱有信念的人。正如她自己所說“人生的結局總是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個悲劇,壯年夭折,也是個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張愛玲本人就像她在作品中反應出來的那樣喜歡色彩明艷的服飾,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談到她“愛刺激的顏色”,連房間布置都是“一種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是帶刺激性”。張愛玲對這種俗艷色彩的垂愛,其實就是她想傳遞給讀者的人生觀的一種折射。俗才是市民生存的本來面目,“俗人俗事”才會讓人感到熱鬧親切,在作品中她把角色對金錢物質迷戀以及愛欲肉體渴望的展現也正是對現代都市市民人生底子的還原,脫去華麗的服飾,俗就是他們真實而樸素的底子。也正是這些世俗間的俗事才是在末世文明的廢墟夾縫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最能體現生命永恒的力量。“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她想傳遞的信念就是在時代如影子般要沉沒下去時,每一個人要能夠坦然自若的面對死亡,同時也要活在當下,哪怕是以一種最低生活標準也要盡情的釋放生命精彩。張愛玲用細致的筆觸所描寫平凡市民的衣食住行,使文本扣動讀者內心最深處的弦,因此與讀者交流的過程中更好地產生共鳴,大眾在被作品中人物悲歡離合的情緒打動時,也能結合自身的審美經驗和生活經歷對故事內涵細細品味從而達到凈化心靈的目的,實現有價值的審美交流。
四、總結
接受美學認為,文學作品的價值常常是由兩方面構成,一方面是具有不確定性的文學文本,一方面是讀者閱讀過程中的具體化。任何文本都具有未定性,如果沒有讀者的參與,它是無法產生獨立意義的。文本意義的產生,只有靠讀者閱讀具體化才能實現。同時讀者的解讀也不能完全離開文本,要想發現文本的審美特征讀者就必須要依循著文本的引導和暗示,從而結合著自身經歷來發揮他們的想象,對文本進行再創造。張愛玲秉承“讀者至上”的創作原則,這對她的文本構造和創作特色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無論是“期待視野”還是“召喚結構”的使用,這都使其文學的接受效果即對社會常規慣例的否定以及讀者大眾的心靈解放得以發揮,也正是因為她的這份執念,使其小說的生命魅力一直延續至今并深受大眾喜愛,張愛玲本人也成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作家。
[1] H·R·姚斯 R·C·霍拉勃著,周寧 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2]朱立元著.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3]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M].上海三聯書店,2008.
[4]鄧如冰著.人與衣:張愛玲《傳奇》的服飾描寫研究[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5]李歐梵、夏志清、等著,陳子善編.重讀張愛玲[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注釋】
[1][3][4][11][12]張愛玲 .論寫作[J].雜志月刊第13卷第1期,1944.
[2][7][14] H·R·姚斯 R·C·霍拉勃著,周寧 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5][6][8][9][18]張愛玲著. 金鎖記[M].哈爾濱出版社,2005.
[10][15][19]張愛玲著. 傾城之戀[M].花城出版社,1997.
[13]朱立元著.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16]張愛玲. 寫什么[J].雜志月刊第13卷第5期,1944.
[17][22]張愛玲著. 流言[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
[20]殷允芃著. 那些年,這些人[M]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
[21]胡蘭成著.今生今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作者:云南民族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