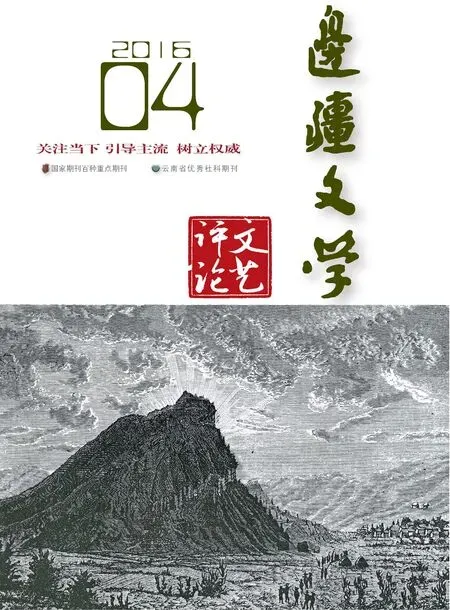論形象、情感與技巧、技藝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
◎蔡 毅
理論前沿
論形象、情感與技巧、技藝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
◎蔡 毅
主持人語(yǔ):文學(xué)是人學(xué),它要求的是寫(xiě)人,寫(xiě)“精彩人物”。所以,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人物的形象塑造與情感表達(dá)既關(guān)乎作品的品質(zhì),又決定著文學(xué)作品的命運(yùn);一部文學(xué)作品想要獲得成功,不光需要有好的創(chuàng)意、理念和情感表達(dá),還得有高超的技藝,文學(xué)所講的技藝其實(shí)就是作家對(duì)生活質(zhì)地的細(xì)膩感受和豐富觸覺(jué),是耳濡目染長(zhǎng)期用心琢磨積累的結(jié)果。當(dāng)作家有了好的創(chuàng)意、好的題材時(shí),如何將其敘述表達(dá)得精彩、生動(dòng)和深刻,靠的就是技術(shù)、技藝。
關(guān)于形象塑造與情感表達(dá)以及創(chuàng)作的技術(shù)、技藝通常是作家們經(jīng)常討論和研究的課題,然而,著名文學(xué)評(píng)論家蔡毅的這篇題為”論形象、情感與技巧、技藝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一文,引經(jīng)據(jù)典,借鑒許多國(guó)內(nèi)外著名作家的成功經(jīng)驗(yàn),詳細(xì)而生動(dòng)地論述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何表達(dá)人物情感以及文學(xué)創(chuàng)作技巧的把握等,相信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和文學(xué)愛(ài)好者都會(huì)受到啟迪。(蔡雯)
一、文學(xué)形象、情感的價(jià)值生成
文學(xué)創(chuàng)作大多是用形象與情感說(shuō)話(huà)的,形象中蘊(yùn)有情感,情感與形象相連,歷來(lái)就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種現(xiàn)象和規(guī)律。
青年作家王萌萌談自己的寫(xiě)作時(shí),講到她在支教生活中認(rèn)識(shí)一個(gè)貧困學(xué)生小美,就開(kāi)始資助她讀書(shū)與生活。一次次的接觸與共同生活,使作家與小美結(jié)下深厚的情誼,以致小美情不自禁地將作家稱(chēng)為“媽媽”。由于熟知小美的身世、性情、生活環(huán)境與成長(zhǎng)經(jīng)歷,所以她能順利地把自己看到與感受到的東西化為創(chuàng)作的素材和靈感,讓“小美”直接走進(jìn)小說(shuō)《大愛(ài)無(wú)聲》中去,并將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活靈活現(xiàn)有血有肉。王萌萌在回憶這一切時(shí),說(shuō)她與小美共同成長(zhǎng)的這6年,“表面看來(lái)是我一直在幫助她,實(shí)際上她給予我的更多。寫(xiě)作者常與寂寞冷清相伴,小美的堅(jiān)強(qiáng)樂(lè)觀(guān)和她對(duì)我的依賴(lài)支持著我克服生活上和寫(xiě)作上的道道難關(guān)。我的一部分根扎在小美家鄉(xiāng)的土地里,小美、素英姐和黃茅嶺所有心中有愛(ài)、有夢(mèng)想的親人幫我開(kāi)掘了那口專(zhuān)屬我的井。我與他們之間那些溫暖過(guò)我、感動(dòng)過(guò)我、激勵(lì)過(guò)我的點(diǎn)滴,為我的寫(xiě)作提供了豐沛的養(yǎng)分。”她用自己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經(jīng)歷透徹地說(shuō)明了寫(xiě)作與生活并不是各自分離的兩張皮,而是直接融為一體的同一件事。那就是創(chuàng)作就是應(yīng)將自己生命里最難忘、最獨(dú)特的經(jīng)歷相聯(lián),與自己內(nèi)心最深沉、最刻骨的情感相聯(lián),和表現(xiàn)書(shū)寫(xiě)對(duì)象結(jié)成親密無(wú)間的“母子”關(guān)系,這樣創(chuàng)作就能進(jìn)入形象、素材、情感與內(nèi)容源源不斷的良性循環(huán),跨入左右逢源如魚(yú)得水的佳境。
文學(xué)涉及的形象五花八門(mén)多種多樣,有人物形象、自然形象、動(dòng)物形象、植物形象、奇幻形象、神魔形象、普通形象、特殊形象等等,不論何種形象,其實(shí)都折射著作家自身的性格、情感、好惡與喜樂(lè)。作家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自己認(rèn)識(shí)的形象去創(chuàng)造,或是按自己心儀的對(duì)象、心目中的理想去塑造人物。形象一旦浮現(xiàn)或顯露,就會(huì)鼓動(dòng)作家去捕捉它,表現(xiàn)它,完善它。作家的認(rèn)識(shí)、期盼、向往和渴望,都溶合體現(xiàn)在形象的塑造上。
為了塑造一個(gè)美麗的形象,就取這個(gè)人的眼,那個(gè)人的鼻,再取另一人的唇,使之綜合化成,造出超群出眾的完美形象。為了塑造一個(gè)壞蛋,便將這個(gè)人的劣習(xí),那個(gè)人的壞事,加上其他人的惡毒,也移植到此人身上,讓人驚駭厭惡,從此遠(yuǎn)離躲避。當(dāng)然也可以把自己最熟悉的人當(dāng)作模特,或把自己直接寫(xiě)進(jìn)作品,目的皆是讓人感覺(jué)生動(dòng)真實(shí)可信。
王朔不喜歡知識(shí)分子,在他的作品中,知識(shí)分子常淪為調(diào)侃、嘲諷、打擊的對(duì)象。遲子建喜歡市井人物,“他們?cè)谖已劾锸俏膶W(xué)天空的星星,每一顆都有閃光點(diǎn)……每個(gè)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鏡,折射著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更折射著他們不同的生活側(cè)面。這里有生之艱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樂(lè)和詩(shī)意。”因此她樂(lè)于走進(jìn)小人物,為市井人物作傳,將筆墨伸向泥濘的街巷,伸向寒舍,伸向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普通人。情感在決定著作家選擇表現(xiàn)的對(duì)象,決定著作家的態(tài)度與立場(chǎng)。
史鐵生認(rèn)為:“寫(xiě)作者,未必能夠塑造真實(shí)的他人(所謂血肉豐滿(mǎn)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寫(xiě)作者只能塑造真實(shí)的自己。……你靠什么來(lái)塑造他人?你只可能像我一樣,以史鐵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陰暗去追查張三的陰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張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他說(shuō)得透徹,強(qiáng)調(diào)的是作家無(wú)論怎樣努力,超越或虛構(gòu)、馳騁或掙扎,最終還是得按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認(rèn)識(shí)、理解和體恤去表現(xiàn)和塑造,誰(shuí)也超不出“我”,逃不脫“我”,因?yàn)椤拔摇笔莿?chuàng)作最初和最終的根本依據(jù)。
比如牛漢先生塑造的雄鷹,其窠“筑在最險(xiǎn)峻的懸崖峭壁。/它深深地隱藏在云霧里”,“沒(méi)有羽絨或茅草,/沒(méi)有樹(shù)葉和細(xì)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樹(shù)枝”,然而誕生于此的鷹,“隆隆的炸雷/喚醒蛋殼里沉睡的胚胎,/滿(mǎn)天閃電/給了雛鷹明銳的眼瞳/颶風(fēng)十次百次地/激勵(lì)它們長(zhǎng)出堅(jiān)硬的翅膀,/炎炎的陽(yáng)光/鑄煉成它們一顆顆暴烈的心……風(fēng)暴來(lái)臨的時(shí)刻,/讓我們打開(kāi)門(mén)窗,/向茫茫天地之間諦聽(tīng),/在雷鳴電閃的交響樂(lè)中,/可以聽(tīng)見(jiàn)鷹群激越而悠長(zhǎng)的歌聲。/鷹群在云層上面飛翔,/ 當(dāng)人間沉在昏黑之中,/ 它們那黑亮的翅膀上,/ 鍍著金色的陽(yáng)光。”(《牛漢詩(shī)選》,1998)。他筆下的鷹,完全是一種人格化的形象,鷹似我,我似鷹,詩(shī)人已將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生命體驗(yàn)、美學(xué)理想、人格追求都賦予了它,堅(jiān)韌不屈悲壯英勇,使之成為一種人格操守和精神力量的象征。這形象與作家詩(shī)人是血肉相融,物我一體,無(wú)法區(qū)分的,它當(dāng)然就有理有據(jù)情濃意滿(mǎn)生命健旺,頗能打動(dòng)人感染人。
每個(gè)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和具體做法是各有千秋,并不一樣的。對(duì)于作家來(lái)說(shuō),能否創(chuàng)作出性格鮮明、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讓讀者牢牢記住,使之成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名成員,朋友、親人、榜樣,或是厭惡、憎恨的對(duì)象,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欲取得創(chuàng)作的成功,必須細(xì)致而廣泛地觀(guān)察各類(lèi)人,從中看到人類(lèi)的天性;通過(guò)閱讀和學(xué)習(xí)歷史與現(xiàn)狀,忠實(shí)地研究人類(lèi)的本性;必須將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集中在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集中在人格和情操的表現(xiàn),向著人性深處開(kāi)掘;以無(wú)偏私無(wú)成見(jiàn)的明亮眼光和包容一切的心胸看待人類(lèi),不受宗教情緒、意識(shí)形態(tài)偏見(jiàn)的影響,排除個(gè)人的自我中心、虛榮心、好惡和狂熱,懷抱深厚的同情心,透過(guò)邪惡看到善良,通過(guò)善良看出邪惡,才可望塑造出一個(gè)又一個(gè)讓人心服口服的生動(dòng)形象——讓人熱愛(ài)、崇拜和學(xué)習(xí),痛恨、警覺(jué)與遠(yuǎn)離,幫助讀者認(rèn)識(shí)生活。
莫言的經(jīng)驗(yàn)是:小說(shuō)“要盯著人來(lái)寫(xiě),貼著人的性格來(lái)寫(xiě)。”“盯”是觀(guān)察,是注視;“貼”是靠近,靠攏,縮小和消除距離。盯緊可以弄清人物行動(dòng)的來(lái)龍去脈;貼近可以探悉人物內(nèi)心的所思所想。目的皆是緊緊抓住和貼近人,在透徹認(rèn)識(shí)、深刻理解的基礎(chǔ)上,以心貼心的方式達(dá)到與寫(xiě)作對(duì)象的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只有如此,才可能寫(xiě)得準(zhǔn)確、生動(dòng)、親切與活潑。他在長(zhǎng)篇小說(shuō)《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后談內(nèi)心感言時(shí)說(shuō):“沈從文先生曾說(shuō)過(guò):小說(shuō)要‘貼著人物寫(xiě)’。這是經(jīng)驗(yàn)之談,淺顯,但管用。淺顯而管用的話(huà),不是一般人能說(shuō)出來(lái)的。我改之為‘盯著人寫(xiě)’,意思與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點(diǎn),這是我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決定的。”他說(shuō)他寫(xiě)《我們的荊軻》,就是寫(xiě)人,寫(xiě)人的成長(zhǎng)與覺(jué)悟,寫(xiě)人對(duì)“高人”境界的追求。汪曾祺則強(qiáng)調(diào):“小說(shuō)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dǎo)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huán)境描寫(xiě)、作者的主觀(guān)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lè)。作者的心要隨時(shí)緊貼著人物。什么時(shí)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huì)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chéng)意。”劉慶邦也表示,“所謂貼著人物寫(xiě),我理解,不是貼著人物的身體寫(xiě),而是貼著人物的心靈寫(xiě)……將心比心,以作者自己的心靈貼近作品中人物的心靈。”一個(gè)比一個(gè)表述得更清楚更透徹,這類(lèi)寶貴經(jīng)驗(yàn)要求我們對(duì)筆下的人物有充分的認(rèn)識(shí),詳細(xì)的了解和足夠的尊重,值得每一個(gè)創(chuàng)作者悉心體會(huì)、揣摩記取。
蘇童在講述自己的創(chuàng)作時(shí)說(shuō):“過(guò)去我也在努力塑造人物,但沒(méi)有能夠‘看見(jiàn)’他們;《黃雀記》的寫(xiě)作,是人物離我最近的一次,每一個(gè)章節(jié)寫(xiě)作中的相處,我都能感覺(jué)到他們的呼吸。寫(xiě)到某個(gè)對(duì)話(huà)時(shí),如果寫(xiě)得不妥當(dāng),人物會(huì)自動(dòng)糾正我:應(yīng)該這么說(shuō)話(huà)。”看得見(jiàn)看不見(jiàn)自己描寫(xiě)的對(duì)象,是創(chuàng)作能否順利展開(kāi)的一道重要門(mén)檻,看不見(jiàn),當(dāng)然就很難寫(xiě)準(zhǔn)寫(xiě)好,就不免會(huì)用許多猜測(cè)臆想之物來(lái)填充;看得見(jiàn)才可能寫(xiě)準(zhǔn)寫(xiě)清寫(xiě)好,在這基礎(chǔ)上若能感覺(jué)到人物之呼吸,脈搏之跳動(dòng),心心相印,然后進(jìn)行人物塑造,當(dāng)然就容易創(chuàng)造出形象鮮明逼真、栩栩如生,達(dá)到令自己和讀者都滿(mǎn)意的效果。蘇童認(rèn)為:“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態(tài)度,作家不應(yīng)陷入現(xiàn)實(shí)的泥潭,不能自拔,必須學(xué)會(huì)進(jìn)退有余,離地三公尺飛行。”他力圖使自己的作品面目復(fù)雜,而不是做一個(gè)簡(jiǎn)單地被一兩句話(huà)概括的作家。“倒不是有意樹(shù)立復(fù)雜多變的形象,我的創(chuàng)作一直想自我調(diào)整,設(shè)計(jì)一個(gè)模糊的未來(lái),設(shè)計(jì)所謂如何說(shuō)故事。過(guò)去的講述還沒(méi)有剖析到人物的靈魂深處;《黃雀記》不同,我很努力地寫(xiě)到最深處,像一道光,像一把刀,切入最深的地方,不能再往前走一寸為止。”他的態(tài)度和努力方向,顯然是值得肯定和提倡效仿的。
有的作家則是時(shí)常附體于筆下的各個(gè)人物,讓人物分享他的思想、情感和體溫,有時(shí)又突然抽身離去,讓人物自己去表演支配。一去一離,既有心心相印完全一致的體察,也有超脫逃逸的換位審視。在這方面,韓少功曾說(shuō):“作者對(duì)筆下人物的控制欲不能太強(qiáng),寫(xiě)作時(shí)需要丟掉所有的先入之見(jiàn),不是牽著人物跑,而是跟著人物跑,甚至什么時(shí)候被人物的表現(xiàn)嚇一跳。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要自廢思考,忙不迭地與理性撇清干系。”他主張盡可能讓人物形象按自己的性格邏輯行事,這樣可以避免淪為作家意志的傀儡。
形象從模糊到清晰,從混沌到成型,全靠作家不斷地捕捉與儲(chǔ)藏?zé)o數(shù)的情感、形象、詞匯和多種元素,并把這些東西儲(chǔ)存于心,讓其化合發(fā)酵,潛滋暗長(zhǎng),直到適當(dāng)?shù)慕M合時(shí)刻到來(lái),直到一切能夠結(jié)晶成一種新事物、新形象。
形象的塑造與作家的情感態(tài)度是直接連在一起的,對(duì)描繪形象有無(wú)情感,投入了多少情感,傾注了什么情感,那是非常關(guān)鍵不能含糊的。作家阿來(lái)說(shuō):每一次提筆,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都是一次情感的蓄積,這個(gè)過(guò)程就如一潭山谷間的湖泊,慢慢被春水盈滿(mǎn)。他認(rèn)為,寫(xiě)作相當(dāng)于這一湖水決堤而出,把所有情感的蓄積揮霍得一干二凈。“下一本書(shū),我得修好堤壩,等水再次慢慢盈滿(mǎn),再次破堤。一部長(zhǎng)篇的寫(xiě)作,尤其如此。”韓少功更是把文學(xué)創(chuàng)作視為一種嘔心瀝血的創(chuàng)造。他說(shuō):“在我看來(lái),好小說(shuō)都是‘放血’之作。這個(gè)‘血’是指貨真價(jià)實(shí)的體驗(yàn),包括鮮活的形象,刻骨的記憶,直指人心的看破和逼問(wèn)。我從來(lái)把這個(gè)東西看作文學(xué)的血脈。沒(méi)有這個(gè)東西,小說(shuō)就是放水,放口水,再炫目的技巧,再火爆或者再精巧的情節(jié),都可能是花拳繡腿。”用心血?jiǎng)?chuàng)作的東西比之用口水、清水或茶水之類(lèi)東西創(chuàng)作的作品價(jià)值自然就要高得多,兩者是無(wú)法相提并論的。
創(chuàng)作的價(jià)值很大程度就在于要為文學(xué)畫(huà)廊增添新人物新形象。因此能否專(zhuān)心致志于怎樣創(chuàng)造出新的人物形象,如何去雕琢民族的魂魄、時(shí)代的畫(huà)像,如何以正面的價(jià)值、正能量去影響人、改變?nèi)撕湾懺烊耍褪欠浅V匾枰钊胙芯康氖隆?/p>
塑造一個(gè)個(gè)感性的、活生生的、充滿(mǎn)喜怒哀樂(lè)的真實(shí)形象,靠的是作家用雙眼去觀(guān)察,用情感去浸泡,用生命去感悟。近年來(lái)如果說(shuō)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并未能給世人留下什么印象深刻、性格飽滿(mǎn)的成功人物形象,那么電視連續(xù)性到是創(chuàng)造出了不少讓中國(guó)人牢記和喜愛(ài)的人物形象,比如“兵王”許三多,一個(gè)木訥呆愣,卻無(wú)比地堅(jiān)韌頑強(qiáng),做出驚人成就的傳奇人物,他“不放棄不拋棄”的精神成為一種口頭禪,勵(lì)志語(yǔ),鼓舞人們勇猛精進(jìn),奮斗不息,他自己也成為一個(gè)讓人難忘的當(dāng)代偶像。還有《亮劍》中的李云龍,永不服輸,即使遭遇再?gòu)?qiáng)大的對(duì)手也敢于亮劍,即使失敗,倒下去也要成為一座山的英雄氣概,使“亮劍精神”成為激勵(lì)斗志振奮人心的民族精神,讓人感受到心靈和情感的強(qiáng)勁沖擊與震撼。在這類(lèi)放射著人性光輝和人性魅力的成功人物形象身上貫注著作家深厚的情感,融匯著時(shí)代、環(huán)境、經(jīng)歷、事實(shí)與作家的生命體驗(yàn),它超越一切概念的干癟和局促,以豐富生動(dòng)的生命氣息感染和打動(dòng)讀者。
形象塑造與情感表達(dá)既關(guān)乎作品的品質(zhì),又決定著文學(xué)的命運(yùn)。當(dāng)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能引起讀者的熱議、喜愛(ài)和共鳴,文學(xué)才會(huì)受重視,有位置;當(dāng)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虛假、變形、莫名其妙索然無(wú)味,根本引不起人們的興趣,文學(xué)的危機(jī)與麻煩肯定就到來(lái)了。
曾有不少作家以為創(chuàng)作就是寫(xiě)好故事,寫(xiě)出“精彩的故事”讓人過(guò)目不忘,這當(dāng)然有一定道理,但卻遠(yuǎn)遠(yuǎn)不夠。文學(xué)是人學(xué),它要求的是寫(xiě)人,寫(xiě)“精彩人物”,因此人和人物形象是勝于和重過(guò)寫(xiě)事、故事的。阿諾德·貝內(nèi)特說(shuō):“優(yōu)秀小說(shuō)的基礎(chǔ)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zèng)]有別的什么東西……風(fēng)格是有價(jià)值的,情節(jié)是有價(jià)值的,觀(guān)點(diǎn)的新穎獨(dú)創(chuàng)是有價(jià)值的,但是,它們中間沒(méi)有一項(xiàng)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樣有價(jià)值。”作家高滿(mǎn)堂則強(qiáng)調(diào):“故事是為人物服務(wù)的,人物的失敗就是故事的失敗”。這是入木三分的經(jīng)驗(yàn)之談,必須引起重視。任何一部稱(chēng)得上是優(yōu)秀或杰出作品的東西,一定會(huì)有一個(gè)或幾個(gè)鮮活、獨(dú)特、讓人喜愛(ài)或憎恨的人物存在,使你關(guān)注、牽掛或擔(dān)憂(yōu)他的一舉一動(dòng)、一顰一笑,進(jìn)而關(guān)心他的前途和命運(yùn)。因此,單純講個(gè)一波三折、精彩紛呈的故事并不足為奇,那是說(shuō)書(shū)人的本事,而非作家的重任。作家是由“說(shuō)故事”引出“說(shuō)人”,塑造人刻畫(huà)人和表現(xiàn)人的,人和人物形象,人的形、神、趣、魂及其活動(dòng)才是文學(xué)最關(guān)注的對(duì)象、最重要的任務(wù)、最核心的構(gòu)成。故事不過(guò)是為人服務(wù),依附于人的東西,決不能喧賓奪主。
寫(xiě)出生活之真、人性之美,追求文以載道,參與鍛塑民族魂魄,對(duì)時(shí)代和社會(huì)有著自覺(jué)的擔(dān)當(dāng),為時(shí)代畫(huà)像譜寫(xiě)一代民族的心史,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價(jià)值創(chuàng)造重要的任務(wù)。當(dāng)今文學(xué)面臨的是許多作家脫離生活,脫離時(shí)代和社會(huì)去創(chuàng)作,要么出現(xiàn)“假大空”、“驕奢躁”,寫(xiě)出的是虛浮蒼白的形象,要么是脫離生活的“外星人”、變形走樣的“四不像”,還有的是見(jiàn)事不見(jiàn)人,見(jiàn)人不見(jiàn)性格和精氣神,更糟的則是人妖不分,異怪混搭,虛情假意嘩眾取寵,令讀者很不滿(mǎn)意。
木弓在《文學(xué)人物畫(huà)廊就要關(guān)閉了》一文中提出現(xiàn)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很繁榮,但人物畫(huà)廊卻一直很寂寞,“文學(xué)是寫(xiě)人的,只有寫(xiě)人,文學(xué)才有魅力,才有力量。但是要塑造能夠流傳下來(lái)文學(xué)人物形象,永遠(yuǎn)是一個(gè)艱難的事情,永遠(yuǎn)是對(duì)作家的思想能力和藝術(shù)能力的挑戰(zhàn)。……如果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沒(méi)能為我們的文學(xué)人物畫(huà)廊增添新的人物形象,那么,說(shuō)這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很繁榮,總沒(méi)有那么足的底氣,總不那么讓人信服。……我們現(xiàn)在文學(xué)人物稀少奇缺,原因在于當(dāng)下文學(xué)反映現(xiàn)實(shí)的本領(lǐng)不夠用了、失缺了。開(kāi)始可能被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xué)思潮過(guò)度忽悠,以為現(xiàn)實(shí)主義過(guò)時(shí)了,寫(xiě)實(shí)技巧也可以丟棄了。所以都去玩自我、玩觀(guān)念、玩感覺(jué)。因?yàn)橥孢@些東西,可以不用到生活中去體驗(yàn),可以不必有深刻思想積累,可以不必嚴(yán)格修煉。以后玩的時(shí)間長(zhǎng)了,不會(huì)寫(xiě)他人了。失卻寫(xiě)實(shí)能力,也就是不會(huì)寫(xiě)人物了。由此,還發(fā)現(xiàn)我們的文學(xué)跟不上時(shí)代,有被時(shí)代拋棄的危險(xiǎn)了。”他的這番話(huà),言簡(jiǎn)意賅,語(yǔ)重心長(zhǎng),直接指明了人物形象化塑造的弱化與缺失,會(huì)嚴(yán)重制約中國(guó)文學(xué)質(zhì)量的提升,值得我們警覺(jué)與糾正。
二、文學(xué)技巧與技藝的價(jià)值生成
2013年4月,一部署名為羅伯特·加爾布雷特的偵探小說(shuō)《杜鵑鳥(niǎo)的呼喚》在倫敦面世,受到各方好評(píng)。此書(shū)手法嫻熟,在圖書(shū)排行榜上熠熠生輝,使眾多讀者對(duì)作者自稱(chēng)的新手身份產(chǎn)生懷疑,后經(jīng)有心記者不懈追蹤,終于搞清此書(shū)原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所作,是她自己主動(dòng)選擇一個(gè)隱蔽度很高的男性名字作為筆名,想看看丟開(kāi)盛名之后書(shū)寫(xiě)其它作品究竟能獲得怎樣的真實(shí)評(píng)論和反映。當(dāng)羅琳承認(rèn)她就是小說(shuō)作者后,在英國(guó)亞馬遜網(wǎng)站上,這部小說(shuō)的銷(xiāo)量排名從5076名陡升至?xí)充N(xiāo)榜第一名。此事充分說(shuō)明,當(dāng)一個(gè)作家的創(chuàng)作技巧和水平達(dá)到一個(gè)相當(dāng)?shù)母叨群螅齽?chuàng)作出的作品都會(huì)具有較高的質(zhì)量水準(zhǔn),散發(fā)出一股擋不住的光芒,即使換一個(gè)名字,還是會(huì)讓人辨認(rèn)出來(lái)。
技巧、技藝是一種實(shí)實(shí)在在的本領(lǐng),存在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各個(gè)階段、整個(gè)過(guò)程和最終結(jié)果之中。從話(huà)語(yǔ)的表達(dá)敘述、人物的描寫(xiě)刻畫(huà)到意象的營(yíng)造、懸念的安排、作品的結(jié)構(gòu)、布局以及審美渲染、意蘊(yùn)提煉等所有方面,都需要技巧、技法去強(qiáng)化、增生與升華創(chuàng)作的水平和價(jià)值。比如,人們經(jīng)常通過(guò)求師訪(fǎng)友、高人指點(diǎn)、名師傳授的辦法去獲取技藝水平的提高,通過(guò)作品研討會(huì)、創(chuàng)作座談會(huì)、學(xué)習(xí)班等對(duì)話(huà)交流方式,分析切磋如何尋找素材、提煉主題、塑造人物,編織故事和安排情節(jié),目的皆是為了通過(guò)研讀實(shí)習(xí)、心得交流和思想碰撞等多種方法,獲得實(shí)實(shí)在在的技能技藝的提高。
一部作品想要成功,不光需要有好的創(chuàng)意、理念和情感貫注,還得有高超的技藝為之服務(wù)。許多流傳不衰的經(jīng)典作品,除以真情動(dòng)人,以深刻感人外,還有一條就是精妙的藝術(shù)技巧讓人贊不絕口,嘆為觀(guān)止。小說(shuō)、詩(shī)歌、散文所有的文學(xué)作品固然要表達(dá)一定的思想觀(guān)念和人生內(nèi)涵,但支撐和表現(xiàn)這些觀(guān)念內(nèi)涵卻需要特定的技巧、技術(shù)和藝術(shù)。文學(xué)畢竟不是哲學(xué),不是思想,不是直白的闡述或說(shuō)教,而是藝術(shù)地?cái)⑹觥⒚枥L與表達(dá),因之?dāng)⑹龅姆绞健⒈磉_(dá)的技巧就是必須講求,絲毫也不能馬虎的。
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最個(gè)人化的事,它最需要才能,完全依靠個(gè)人的單打獨(dú)斗去打動(dòng)人心征服天下。因此技巧、技法、技能就顯得尤為重要。英國(guó)詩(shī)人蒲柏在《批評(píng)論》中寫(xiě)過(guò):“筆下的流利憑技藝不憑靈機(jī),/猶如學(xué)過(guò)舞蹈的舞姿才飄逸。/沒(méi)有令人不快的粗厲還不成,/要讓音韻聽(tīng)來(lái)像意義的回聲。”技藝就是技巧、技術(shù),它既要講“技”,技能、技巧與方法,也要講“藝”,主要指藝術(shù)和才能。技巧與藝術(shù),相輔相成相映生輝缺一不可。目的是要用高超的“技”,去追求高尚的“藝”與“美”,為世人為社會(huì)提供能娛人情志,提升精神境界的精品力作。
當(dāng)有了好創(chuàng)意、好題材、好故事、好內(nèi)容時(shí),如何將其敘述表達(dá)得高明、精彩、生動(dòng)、深刻靠的就是技術(shù)、技藝。比如故事從何說(shuō)起,從哪開(kāi)頭,怎樣展開(kāi)敘述,讓故事一波三折,起伏跌宕精彩紛呈;又如怎樣設(shè)計(jì)人物,讓人物如何登臺(tái),如何行事,與他人發(fā)生什么樣的瓜葛牽連矛盾沖突,那都是非常講究,極為考驗(yàn)人的。再如文章怎樣設(shè)置伏筆,安排懸念,怎樣起承轉(zhuǎn)合,首尾呼應(yīng),使結(jié)構(gòu)嚴(yán)密,因果邏輯清晰,那也是體現(xiàn)匠心水平的。青年作家蔣峰就很強(qiáng)調(diào)“不能你想到什么就說(shuō)什么,不然你說(shuō)出來(lái)的就是陳詞濫調(diào)。”他主張要嚴(yán)謹(jǐn)、節(jié)制,“我信奉一句話(huà),永遠(yuǎn)不要從故事的開(kāi)頭寫(xiě),我相信懸念是吸引人讀下去的東西。”他追求的是第一句話(huà)就把人抓住,如《為他準(zhǔn)備的謀殺》開(kāi)頭就是:“我去年11月特別想殺人”。《手語(yǔ)者》第一句就是:“我22歲那一年過(guò)得并不好,我可能一生都過(guò)得不好。”這樣的寫(xiě)作,一開(kāi)始就設(shè)懸念,埋伏筆,提出問(wèn)題,刺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為情節(jié)的逐步展開(kāi),調(diào)足了讀者的胃口,同時(shí)亦為今后的一層層揭秘,剝開(kāi)真相,露出謎底,做足了文章。所以即便是寫(xiě)愛(ài)情故事,他也要獨(dú)運(yùn)意匠,把它講述得充滿(mǎn)懸念,因?yàn)閼夷钍亲屓朔挪幌隆G不開(kāi)的動(dòng)力,運(yùn)用好懸念,便能讓普通小說(shuō)都具有推理小說(shuō)般非凡的魅力和吸引力。
文學(xué)所講的技術(shù)、技藝不是什么秘籍獨(dú)技,不是任何左道旁門(mén),也不是什么絕活訣竅,而是一種敘述表達(dá)的本領(lǐng),一種綜合調(diào)控的水平,一種師難傳徒,父難傳子的“玄妙之技”。 它既是一種對(duì)生活質(zhì)地的細(xì)膩感受和豐富觸覺(jué),是耳濡目染長(zhǎng)期用心琢磨積累的結(jié)果,非一蹴而就;又是別有慧心,需聰穎、才氣、秀巧、不斷漸悟或一朝頓悟的飛躍,包括對(duì)既往細(xì)致精微寫(xiě)作技法的鉆研;還是超常水平的發(fā)揮,對(duì)各種材料和關(guān)系的自覺(jué)領(lǐng)悟處理,以統(tǒng)一的思想操縱五花八門(mén)事物的能力。若非通人達(dá)士,學(xué)難及之。
譬如作品的色彩、情調(diào)、虛實(shí)與濃淡關(guān)系,那常常就是僅可意會(huì),很難言傳的技藝。高明的作家把最應(yīng)表達(dá)的表達(dá)出來(lái),而把應(yīng)掩飾的置于昏暗的沉默中,在該說(shuō)該寫(xiě)的時(shí)候一瀉千里,滔滔不絕,在不該說(shuō)不該寫(xiě)的地方一字不說(shuō),一語(yǔ)不露,使需表達(dá)的東西格外凸顯,不需表達(dá)的暗藏深埋,造成像繪畫(huà)那樣的陰影與留白,使作品呈現(xiàn)恰好的明暗、勻稱(chēng)而又有血肉的美。虛的地方空靈、輕逸、飄渺,實(shí)的地方扎實(shí)、厚重、沉穩(wěn),沉默時(shí)如空山深潭,喧鬧時(shí)如萬(wàn)馬奔騰,用纖秾適度,虛實(shí)交輝的方式,讓文字生出逼真酷肖的質(zhì)感,動(dòng)人心弦的氛圍和語(yǔ)少意豐的效果,令讀者擊節(jié)贊賞,大呼過(guò)癮,沉迷其中卻不知為何,因?yàn)榇祟?lèi)濃淡、虛實(shí)、明暗關(guān)系的處理確實(shí)微妙深?yuàn)W,誰(shuí)也難說(shuō)出個(gè)子丑寅卯。
常有人以為技巧、技術(shù)只不過(guò)是雕蟲(chóng)小技,是技工干的活,用不著勞神費(fèi)心,結(jié)果做出來(lái)的活毛毛糙糙,拿出來(lái)的作品根本就不合格,更別說(shuō)讓人喜愛(ài)、欣羨與驚嘆了。也有人認(rèn)為只要日復(fù)一日地苦苦修煉,孜孜不倦,重視技術(shù),勤于登攀,就不愁沒(méi)有長(zhǎng)進(jìn),可事實(shí)是許多人苦了一輩子,就是讓人感覺(jué)他尚未登堂入室,還在遠(yuǎn)處徘徊,旁人也沒(méi)法幫他教他。所以在我看來(lái),當(dāng)內(nèi)容、題材、追求目標(biāo)選定后,藝術(shù)或者說(shuō)是技術(shù)就是決定一切的,它之高下優(yōu)劣直接決定了作品的成敗,不重視“技”,不關(guān)注“藝”的人,根本就沒(méi)資格從事文藝。
古今中外的文學(xué)發(fā)展史早已證明,任何一部看似妙手天成的作品,或是仿佛率爾而為的即興之作,其實(shí)都有一定的技術(shù)因素、技術(shù)基礎(chǔ)作為它內(nèi)在的構(gòu)成和支撐。技術(shù)手段、技術(shù)難度和技術(shù)基礎(chǔ)看似無(wú)形,實(shí)則暗中主宰著作品的高低成敗和面貌品質(zhì),絲毫也不能忽視。技若無(wú)巧,技若不藝,作品便疙疙瘩瘩,粗陋不堪,不會(huì)放射光彩,也不可能打動(dòng)人感染人。換句話(huà)說(shuō),即使有了很好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材料和理念,若無(wú)精湛的技術(shù)技巧,藝而無(wú)“技”,藝而無(wú)“術(shù)”,那這些創(chuàng)作內(nèi)容依然會(huì)難以表達(dá)實(shí)現(xiàn),或根本達(dá)不到應(yīng)有的水平效果。
技術(shù)、技巧、技藝不是從天上掉下來(lái)的東西,而是長(zhǎng)期學(xué)習(xí)、磨煉和積累的結(jié)果。技術(shù)技巧很多時(shí)候像一把刀,能幫助你對(duì)混沌的生活進(jìn)行有力的切割。有時(shí)候像一根針,將經(jīng)驗(yàn)、素材、感知縫制成各式各樣的東西。有時(shí)候像一把火,將簡(jiǎn)單粗糙的材料煅造得渾圓晶亮,熠熠生輝。有名言說(shuō)技巧是“無(wú)數(shù)遍重復(fù)的成就”。無(wú)數(shù)次練習(xí),長(zhǎng)期的摸索實(shí)踐,熟能生巧、熟能生精,技術(shù)技巧就生出來(lái)了。
技術(shù)技巧不是用來(lái)取巧或作擺設(shè)的,而是用來(lái)提高作品質(zhì)量,增強(qiáng)其藝術(shù)魅力和感染力的。高爾基早就說(shuō)過(guò):“……你要想寫(xiě)得很好,就必須懂得各種技巧。” 學(xué)習(xí)和掌握技巧,既能使作品寫(xiě)得高明完善,也能提高寫(xiě)作速度和效率。他曾舉過(guò)一個(gè)例子,說(shuō)列寧格勒工人曾請(qǐng)德國(guó)技師來(lái)幫助安裝鍋爐,第一座鍋爐用了6個(gè)月時(shí)間,第二座由于俄國(guó)工人的幫助,提前一個(gè)月完成。第三座、第四座裝得更快,最后一座即第六座鍋爐,他們只用了6個(gè)星期就裝好了,這就是學(xué)習(xí)技巧的意義,也是熟能生巧的最好說(shuō)明。為此他說(shuō):“天才指的是對(duì)工作的熱愛(ài),就是說(shuō)要善于工作。您選定了一個(gè)目標(biāo),就應(yīng)當(dāng)為之付出全部身心、全部力量。”
譬如語(yǔ)言文字只是創(chuàng)作的材料,心靈和技藝才是使它發(fā)生變化的主宰力量,語(yǔ)言須提純提煉、安置妥當(dāng)之后才會(huì)變?cè)姵晌模庞绪攘蜕R虼讼嗤恼Z(yǔ)言材料,在不同人的手里,會(huì)生成千差萬(wàn)別質(zhì)地各異的東西,有的粗疏,有的精細(xì),有的平庸,有的精彩,有的是文字垃圾,有的卻是不朽精品。技巧能夠幫助作家寫(xiě)得既簡(jiǎn)練、準(zhǔn)確、樸實(shí),又高明生動(dòng)精彩。它能傳授語(yǔ)言塑造形象的技巧,教人怎樣安排材料、掌握情節(jié),告訴有關(guān)語(yǔ)言方面的許多“秘訣”,諸如內(nèi)容的虛實(shí)搭配,風(fēng)格的樸實(shí)明快,文字的簡(jiǎn)潔傳神,這一切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運(yùn)用技巧和匠心努力追求的結(jié)果。
俄國(guó)作家伊薩克·巴別爾在談他的寫(xiě)作經(jīng)驗(yàn)時(shí)說(shuō):“一段文辭出世能否成句,秘密就在于幾乎不易察覺(jué)的輕輕一擰。而扳手就時(shí)刻準(zhǔn)備好,隨取隨到,而你一次轉(zhuǎn)不到位,就沒(méi)有第二次機(jī)會(huì)了……修辭的秘密在于轉(zhuǎn)一個(gè)小的、幾乎看不見(jiàn)的彎兒。你要心中有數(shù)、一次到位,因?yàn)榫渥硬唤o你第二次機(jī)會(huì)……你須胸有成竹、有備無(wú)患,如不一箭封喉,再出手已成千古恨。”他把用兵之道作為自己的為文之道,強(qiáng)調(diào)擒賊擒王,攻人攻心,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講起文風(fēng),談到詞匯,他如同講起十八般兵器都得使用的軍隊(duì),認(rèn)為“沒(méi)有一種鐵能像一個(gè)恰到好處的句號(hào)那樣直刺人心。”主張用這樣的絕技,一次到位,一劍中的,絕不猶猶豫豫,拖泥帶水。這無(wú)疑是很高的語(yǔ)言表述和用字技巧,通過(guò)“輕輕一擰”,其實(shí)就是恰到好處的轉(zhuǎn)換、幻化、創(chuàng)造,無(wú)用的字就變得有用有價(jià)值,并生出光彩來(lái)了。這些就需要對(duì)某些稍縱即逝場(chǎng)景、情緒、人物精準(zhǔn)無(wú)比的描摹,舉重若輕的道破,體貼入微的辨識(shí),才能于無(wú)形中實(shí)現(xiàn)。
林斤瀾先生曾說(shuō)自己創(chuàng)作奉行的是“有話(huà)則短,無(wú)話(huà)則長(zhǎng)”,這是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技巧。誰(shuí)都知道,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中常說(shuō)的一句話(huà)是“有話(huà)則長(zhǎng),無(wú)話(huà)則短”。林先生等于是對(duì)之挑戰(zhàn),將自己推到一個(gè)相反的極端的境地,那就是別人無(wú)法開(kāi)口下手的地方,我偏偏要多說(shuō)多寫(xiě);別人常講愛(ài)寫(xiě)的東西,我卻盡量閉口不言。這樣才能講出不同凡響的話(huà),寫(xiě)出與眾不同的作品。這無(wú)疑是一種“擰著來(lái)”、反著來(lái),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技巧,肯定特別難能費(fèi)勁,沒(méi)有超常的追求,非凡的技藝是很難獲得成功的。而真正高明的作家,常常就是在別人無(wú)法下筆的地方下筆,在別人寫(xiě)不出字的地方寫(xiě)出長(zhǎng)篇大論驚世之作。
藝術(shù)作品中技術(shù)難度的大小、技術(shù)含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該作品的質(zhì)量和價(jià)值,從而也決定著它的生命與前途。技術(shù)高才能做到妙筆生花,化腐朽為神奇,“言情則沁人心脾,寫(xiě)景則如在眼前”,才能做到:“寫(xiě)鬼寫(xiě)妖高人一籌,刺貪刺虐入骨三分”。技術(shù)低則捉襟見(jiàn)肘,左支右絀,擺不脫平庸的泥淖,掙不出千篇一律的窠臼。有的作家能描述抽象,充分展示抽象,讓抽象熠熠閃光,這也是一種高超的能力。因?yàn)闆](méi)有一個(gè)作家滿(mǎn)足于具象、表象,他們都希望最后能飛升到抽象。作家在寫(xiě)作的時(shí)候肯定是有哲學(xué)和其它精神在后面作支撐,那些內(nèi)心的精神力量在他血脈當(dāng)中會(huì)幫助他突圍、沖刺、奮爭(zhēng)與騰越。
技巧技藝可以是拉長(zhǎng)或縮短的方法,是繁復(fù)或簡(jiǎn)練的本領(lǐng),是探幽索微一以貫之的追蹤,是精準(zhǔn)射擊一槍斃命的能耐。就像刀有刃才鋒利,刀無(wú)刃則什么也干不成。又像武功高明者能一以當(dāng)十出奇制勝,無(wú)技無(wú)術(shù)者,只有束手就擒,甘拜下風(fēng)。因此,不斷學(xué)習(xí)和嘗試新的技巧技法,挖掘更多的可能性,就能創(chuàng)造更多更高的價(jià)值,推動(dòng)文學(xué)向著高遠(yuǎn)的境界飛升。
作家藝術(shù)家肩負(fù)著促進(jìn)藝術(shù)發(fā)展的責(zé)任和重?fù)?dān),其中重要的一環(huán)就是要發(fā)展和促進(jìn)藝術(shù)的技巧、技術(shù)和技藝,將它不斷提高,日臻完善。許多時(shí)候,對(duì)技術(shù)的重視其實(shí)就是對(duì)藝術(shù)的重視,技術(shù)的使用和發(fā)展最終也是為了促進(jìn)藝術(shù)的完善。技術(shù)能讓內(nèi)容插上翅膀,技術(shù)能讓藝術(shù)更上層樓。忽視技術(shù),會(huì)令作品簡(jiǎn)單粗糙;忽視藝術(shù),會(huì)使作品短命。
巴金先生說(shuō)過(guò):“最高的技巧就是沒(méi)有技巧”。這話(huà)有人以為是否認(rèn)技巧,但其實(shí)我們又何嘗不能將它看作是高度地贊美技巧呢,因?yàn)樗呀?jīng)肯定和強(qiáng)調(diào)了“最高的技巧”的價(jià)值,那不是炫技,不是弄巧,而是將一切的經(jīng)歷、經(jīng)驗(yàn)、感悟、情感、知識(shí)、見(jiàn)解統(tǒng)統(tǒng)揉合熔化,使之成為一個(gè)嚴(yán)密的整體,讓你無(wú)從分辨哪是知識(shí),哪是見(jiàn)識(shí);哪是生活,哪是體驗(yàn);哪是技巧,哪是藝術(shù)。那不就是最高的境界嗎?!
當(dāng)然,凡事皆有例外,凡事也必須重視“度”,技巧再重要也得防止夸大它的功用。早就有作家談到技巧用多了會(huì)損害作品,會(huì)讓文章顯得生硬、炫目。電影導(dǎo)演康洪雷說(shuō)過(guò):“不能心機(jī)太重,惟有單純是制勝的法寶,只有單純才有奇跡的可能。”這想法和提醒是很必要的。
梁實(shí)秋先生在《文學(xué)的紀(jì)律》一文中提出:“文學(xué)的力量,不在于開(kāi)擴(kuò),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縱,而在于節(jié)制。”集中和節(jié)制其實(shí)也是一種技巧,因?yàn)橛芍宰拥姆趴v擴(kuò)張,會(huì)導(dǎo)致情感泛濫,分寸失當(dāng),破壞美感,令人生厭。而以理性駕馭情感,節(jié)制想象,才能把藝術(shù)的分寸、細(xì)微和精妙體現(xiàn)出來(lái),把藝術(shù)的光輝充分釋放出來(lái)。讓放縱的跑馬占地盡量減少,節(jié)制的精雕細(xì)刻盡量增多,真正的技藝技巧才會(huì)大放光彩。
在當(dāng)今眾多作家都分外重視技術(shù),喜愛(ài)談?wù)摵脱辛?xí)技巧之際,有必要提出:任何時(shí)候都需要把重“道”還是重“技”的位置擺正。“道”通常代表文學(xué)的內(nèi)容、內(nèi)涵和追求目的,“技”則指有效方法和便捷途徑。“道”大而無(wú)形,需長(zhǎng)期積累,苦心孤詣摸索,以求一朝領(lǐng)悟,獲得通達(dá);“技”小而實(shí),可研習(xí)秉承,有操作性推廣性。因技術(shù)技巧并不是一種獨(dú)立的東西,它們只是用于表達(dá)和揭示內(nèi)容的方法手段,是為思想、意蘊(yùn)、情感之類(lèi)目的服務(wù)的東西,必須與內(nèi)容、主題相符,而不能為技巧而技巧。因此我們既要警惕重技輕藝、重形式輕內(nèi)容的痼疾,也需要克服忽視、鄙薄技術(shù),輕視技藝的不良傾向。只要我們知道并重視技術(shù)、技巧、技法、技藝的研習(xí),用不斷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去更好地服務(wù)于新價(jià)值的創(chuàng)造,就不愁文學(xué)沒(méi)有遠(yuǎn)大的前程。
【注釋】
[1] 王萌萌:《愛(ài)讓生命寬厚,讓文字飛揚(yáng)》,見(jiàn)2013年6月4日《文藝報(bào)》。
[2] 徐建:《埋藏在人性深處的文學(xué)之光——作家遲子建訪(fǎng)談》,見(jiàn)2013年3月25日《文藝報(bào)》。
[3] 史鐵生:《病隙碎筆》第96頁(yè),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4] 莫言:《盯著人寫(xiě)》,載2011年第5期《作家通訊》第24頁(yè)。
[5] 劉慶邦:《貼近人物的心靈》,見(jiàn)2015年1月28日《人民上報(bào)》。
[6] 舒晉瑜:《蘇童:“香椿樹(shù)街”要寫(xiě)一輩子》,見(jiàn)2013年6月27日《人民日?qǐng)?bào)》。
[7] 《韓少功:好小說(shuō)都是“放血”之作》,見(jiàn)2013年3月29日《人民日?qǐng)?bào)》。
[8] 同上。
[9] 《弗吉尼亞·伍爾夫文集·論小說(shuō)與小說(shuō)家》第292—293頁(yè),瞿世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
[10] 高滿(mǎn)堂:《原創(chuàng)是天大的事》,見(jiàn)2014年4月4日《人民日?qǐng)?bào)》24版。
[11] 木弓:《文學(xué)畫(huà)廊就要關(guān)閉了》,見(jiàn)2013年4月19日《文藝報(bào)》。
[12] 行超:《蔣峰:拒絕無(wú)趣的小說(shuō)》,見(jiàn)2013年8月21日《文藝報(bào)》。
[13] 本章節(jié)參照了作者自己寫(xiě)的《不朽的魂靈——文學(xué)永恒性探秘》一書(shū)第125-128頁(yè),中國(guó)書(shū)籍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14] 高小立:《康洪雷:一次特殊的“推拿”體驗(yàn)》,見(jiàn)2013年8月21日《文藝報(bào)》。
(作者系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員、云南省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
責(zé)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