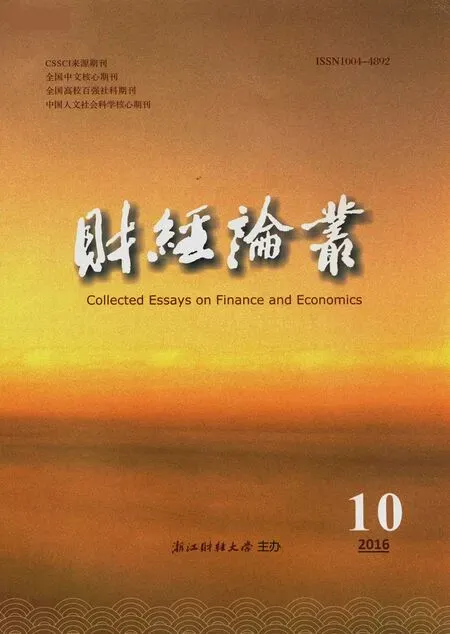中國環境規制如何影響了就業
——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的實證研究
閆文娟,郭樹龍
(1.西安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32;2.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天津 300222)
?
中國環境規制如何影響了就業
——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的實證研究
閆文娟1,郭樹龍2
(1.西安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西安710032;2.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天津300222)
本文從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FDI的角度,系統考察了環境規制對我國就業增長的影響路徑,并構建中介效應模型,以1999-2014年省份面板數據為樣本進行了計量檢驗。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就業不僅存在直接正向作用,還會通過三個中介變量間接影響就業。環境規制通過倒逼產業結構調整間接促進就業,同時,環境規制通過刺激技術進步和抑制FDI間接削弱就業,但環境規制對就業的總效應為正。本研究對實現環境保護和就業雙重紅利這一目標有重要啟示意義。
環境規制;就業;產業結構;技術進步;FDI
一、引 言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環境污染問題日益惡化升級,加強環境保護日益緊迫。相對高標準的環境保護,不僅可以滿足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需求,更是實現“雙中高”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引擎。然而,加強環境保護除了正向的生態效應以及不確定的經濟增長效應以外,涉及到的就業問題同樣值得關注,而與“環境和增長”問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環境和就業”問題得到的關注驚人之少[1]。十三五規劃的內容包括“五位一體”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個方面,其中就業增長是社會建設方面的一個重要內容,環境治理是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重要內容,環境治理和就業增長這兩項目標究竟會出現難以調和的“二元悖論”,還是會出現“雙重紅利”,具體的機制又是什么,回答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因為,環境規制唯有發揮出改善環境質量、倒逼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就業等造福民生的多重功效,才足以真正實現我們第一個百年的小康目標,只有正視環境規制對于民生的重大意義,社會發展才足以為環境保護注入巨大的動力[2]。
國外既有研究中關于環境規制就業效應的探討,就研究結果而言,可分為三類:(1)環境規制削弱就業。這類文獻大都基于企業層面進行分析,認為環境規制增加生產成本削弱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縮小生產規模會導致吸納的就業人數減少。Greenstone(2002)[3]采用倍差法研究表明1970美國清潔空氣法案(CAA)和1977美國清潔空氣法案修正案(CAAA)對就業有負向影響;Dissou(2013)[4]采用CGE方法研究碳減排的就業效應為負;(2)環境規制促進就業。這類文獻大都基于行業層面或者整個宏觀經濟層面進行分析:Gray(2014)[5]運用倍差法研究表明,通過減少制漿造紙業排放的有毒氣體和液體來保護人類健康的聚集控制法案對就業產生正面影響;Ira Altman(2015)[6]利用投入產出方法估算出利用碳捕獲和儲存實行低碳發電的項目對就業的帶動相當于新增了幾個就業吸納部門。(3)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不確定。如,Horbach(2013)[7]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依賴于技術創新的類型,生產過程技術創新促進就業增長,而末端治理技術對就業有負向影響。
國內關于環境規制與就業問題的文獻較為稀少。陸旸(2011)[1]以VAR模型為基礎模擬得出中國難以在短期內實現減排與就業的雙重紅利。陳媛媛(2011)[8]采用交叉彈性法,引入交叉項,檢驗環境管制的就業效應。閆文娟、史亞東、郭樹龍(2012)[9]構建面板門檻模型,檢驗了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與就業的非線性特征。王勇、施美程、李建民(2013)[10]基于行業視角,引入相關交叉項和平方項,研究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李夢潔、杜威劍(2014)[11]研究環境規制的地區就業效應及行業異質性。
既有文獻在分析環境規制的就業效應時大都集中于規模效應和替代效應這兩類直接效應,關于環境規制影響就業的中介效應分析相對缺乏,個別文獻引入產業結構或技術進步中介變量,但在研究方法上僅是將其作為控制變量進行考察,或簡單采用交叉項檢驗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研究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本文將環境規制、產業結構、技術進步、FDI、就業納入一個分析框架,理論演繹環境規制作用于中介變量進而影響就業的機制;在環境規制與就業問題的研究中,首次引用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環境規制對就業的作用路徑,從而豐富和拓展了這類問題的研究視角。
二、環境規制影響就業的機理分析
環境規制是指由于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政府通過制定和推行有關政策措施來調節企業的經濟活動,從而達到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環境規制類型可分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環保標準和必須采用的技術等),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稅費和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等)以及自愿性協議(環境協議和環境認證方案等)[12]。從環境規制對就業的直接作用來看,政府一方面采用稅費等基于市場的激勵型環境規制手段,對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征收稅費,增加三高企業的成本,抑制企業的規模擴張和市場競爭力,進而削減就業;另一方面采用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手段,如關停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或強制部分企業使用低碳技術等,而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適合技術創新,部分企業無法承擔治污帶來的額外成本增加,直接被市場淘汰,進而環境規制將直接導致就業減少。但在現實操作層面,這些現象不必然發生,因為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地方政府所得稅源來于營業收入,而非利潤,這就決定只要工廠生產,哪怕虧損,地方政府也有利可圖。同時這些被重點規制的企業很大一部分是產能過剩的企業,一般是當地最大的工業企業,為當地貢獻了巨大的GDP和稅收,同時也解決了就業壓力,所以現實經濟中,更大的可能性在于這些三高納稅大戶,在地方政府的保護下,維系原有產能或是增加產能,因而就業不減反增的現象會出現。除此之外,環境規制還可能直接增加就業,因為治理污染同樣需要勞動力。現階段直接關停三高企業以及增加三高企業的成本進而導致的就業削減效應會被中國特色的地方政府GDP競賽以及三高企業的一些特殊經營策略帶來的正向促進就業效應掩蓋。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環境規制對就業存在直接作用效應,且在現階段,這種效應為正。
環境規制不僅對就業存在直接作用效應,還可能通過產業結構、技術進步、FDI這三條路徑作用于就業。其一,環境規制水平的提高將倒逼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將帶動更多就業。根據遵循成本假說和環境競次假說,嚴厲的環境規制使得污染密集型產業承擔高昂的環境遵循成本,提升高耗能產業的生存門檻及市場進入壁壘,抑制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增長,進而向環境規制更為寬松的地區轉移;而服務業所受環境規制帶來高昂環境成本的沖擊較小,加上消費者越來越偏向于綠色產品,進而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根據庫茲涅茨定理以及配第-克拉克定理,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勞動力將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流動,第三產業有很強吸納勞動力的特性,第三產業吸收勞動力的比重將高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其二,根據波特假說,恰當的環境規制工具可激發企業技術創新,而企業改變現有的生產技術會對就業產生不確定的影響。就企業采用先進技術的發展階段而言,企業改進或引用先進的綠色生產技術,獲取技術進步的過程迫使企業擠占生產投資,剛開始會影響企業規模的擴大及市場占有率,從而削弱就業,隨著技術的不斷成熟,成本開始回收,企業綠色形象的樹立及消費者更加認可綠色企業的產品,主動采用綠色生產技術的企業將會贏得更大的市場份額,提供更多的就業。就企業采用技術的類型而言,企業生產型技術進步由于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對勞動力產生擠出效應,而污染治理型技術進步將會催生新的環保產業的發展,刺激新的就業需求。在中國現階段,筆者認為治污型技術進步的發展相對滯后,因而帶動環保產業發展動力不足,就業增加有限,而環境規制刺激生產型技術進步更為明顯,從而削減就業的現象更為突出。其三,嚴厲的環境規制會增加外國企業在中國的污染排放成本,尤其是高污染高排放企業將會尋求污染成本更低“污染天堂”,因而FDI將會減少將導致東道國資本存量的下降,減少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削弱了就業的吸收能力。另外,跨國公司所擁有的比內資企業更強大的“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為FDI通過示范效應實現治污技術外溢進而增加就業提供可能,而本地企業通過觀察模仿跨國公司的生產及治污活動獲得示范效應,但這種示范效應的發揮需要內資企業提高吸收能力和學習能力來配合,而環境規制增加了企業的污染治理成本,因而會減弱內資企業的吸收學習能力,所以環境規制減少FDI的流入,FDI治污技術的示范效應得不到良好的發揮進而減少就業的吸納。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環境規制通過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及FDI這三個中介變量對就業產生中介效應。環境規制倒逼產業結構升級進而促進就業,環境規制激勵生產型技術進步進而削減就業,環境規制減少FDI的流入,進而削減就業。
三、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的實證檢驗
(一)模型的設定及說明
在考慮解釋變量X對被解釋變量Y的影響時,如果X不僅直接影響Y,而且通過變量M來影響因變量Y,那么M是中介變量。中介效應的檢驗一般需要三個方程來完成。首先構建方程1:X對Y的回歸方程,如果X的回歸系數顯著,則構建方程2:X對M的回歸方程及方程3:X和M對Y的回歸方程,如果方程2中X的回歸系數顯著且方程3中M的回歸系數顯著,則中介效應顯著,如果方程3中X的系數不顯著,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應,如果方程3中X的系數顯著,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考慮到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環境規制上一期觀測值對下一期的就業人員發生作用這樣一種機制,且被解釋變量就業人員不僅受當期各解釋變量的影響還受上期就業人員的影響。因此,本文采用動態面板的方法進行回歸。
根據理論部分分析,環境規制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就業,還會通過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FDI三條路徑對就業產生影響,因此將上述三個變量設為中介變量,采用1999-2014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以環境規制為核心解釋變量,驗證環境規制對就業的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
以中介變量是產業結構為例,該中介效應模型設定如下:
Lnjyryit=a0+a1Lnjyryit-1+a2Lnzltzit-1+a3Lnwmycdit+a2Lnrlzbit+a2Lngdpit+ε1it
(1)
Lnscbecit=b0+b1Lnscbecit-1+b2Lnzltzit-1+b3Lnwmycdit+b4Lnrlzbit+b5Lngdpit+ε2it
(2)
Lnjyryit=c0+c1Lnjyryit-1+c2Lnzltzit-1+c3Lnscbecit+c4Lnwmycdit+c5Lnrlzbit+c6Lngdpit+ε3it
(3)
其中,i對應各省份的截面單位,t代表年份,ε1、ε2和ε3為隨機擾動項。Lnjyryit為地區i在t年規模以上工業就業人員平均人數,對應于被解釋變量Y;Lnzltzit-1為地區i在t-1年的環境治理投資,對應于解釋變量X;Lnscbecit為地區i在t-1年的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產值之比,對應于中介變量M,Lnwmycdit、Lnrlzbit和Lngdpit為控制變量,分別代表外貿依存度、人力資本和國內生產總值。
技術進步和FDI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模型設定方法同上,只需將產業結構分別替換為技術進步和FDI即可。篇幅限制,此處不再分別列出。
(二)變量及數據的選取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是就業人員(jyry,單位:萬人),用各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衡量。
2.核心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是環境規制(lfszl,單位:萬元/萬噸),目前沒有直接度量環境規制的指標,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廢水治理投資與工業廢水排放量之比”來衡量環境規制,為了避免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選取滯后一期的環境規制作為核心解釋變量。
3.中介變量:(1)產業結構(scbec,單位:%),選取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的比值作為產業結構的代理指標;(2)技術進步(zl,單位:件),采用專利授權量替代,由于專利授權量不能代表當期的技術進步水平,故選取滯后一期的專利授權量作為技術進步的代理指標。(3)FDI(單位:億元),選取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總額表示。
4.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gdp,單位:億元),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就業的重要驅動因素,采取平減后的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顯然GDP越高,經濟規模越大,能吸收的就業越多。(2)外貿依存度(wmycd,單位:%),采取進出口總額占GDP之比作為外貿依存度的代理指標。一方面,進口越多,對國內同行業的競爭壓力越大,可能致使一些經營不善的國內企業的就業人員失業;另一方面,出口越多,越能帶動國內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從而增加就業,兩者權衡的結果需結合不同樣本具體分析。(3)人力資本(rlzb,單位:人)采用“每十萬人口各級學校平均在校學生數之高等學校平均在校學生數”衡量。人力資本越高,在勞動力市場上越具有競爭力,較少的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會代替較多具有較低人力資本的勞動力,所以,人力資本對就業的影響理論預期為負。
本文的樣本為1999-2014年的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不包括西藏和海南。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0-2015),《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00-2014),《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0-2012),《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13-2015),中宏數據庫和ccer數據庫。在數據處理方面,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采用地區生產總值指數對各地區生產總值進行價格平減處理;為了統一貨幣單位,采用人民幣對美元年均價匯率將以美元計的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換算成人民幣;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以1997年的價格水平為基期對工業產值進行價格平減處理;對于部分年份缺失的統計數據,采用插值法處理。
四、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產業結構的中介效應
表1分三個步驟驗證環境規制通過產業結構這一中介變量對就業的中介效應。步驟1,以就業人員為被解釋變量,以環境規制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步驟2,以產業結構為被解釋變量,以環境規制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步驟3,以就業人員為被解釋變量,以產業結構和環境規制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各個回歸方程都加入了控制變量。先檢驗步驟1里環境規制的系數,如果顯著,進行步驟2,否則停止分析。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為0.0791,在1%的水平下顯著,進入步驟2和步驟3,如果在第二步中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和第三步中產業結構的回歸系數都顯著,那么中介效應顯著。如表1所示,兩個系數分別為0.00609和0.132,在1%的水平下顯著,所以環境規制經由產業結構這一中介變量產生的促進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同時,如果步驟3中環境規制的系數不再顯著,則完全中介效應顯著;如果環境規制的系數仍顯著,則部分中介效應顯著,表1步驟3中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為0.0768,在1%的水平下顯著,所以環境規制通過作用產業結構這一中介變量進而會對就業產生部分中介效應,這也為尋找及驗證其他中介變量提供了可能性。

表1 產業結構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N=435)
注:“* ”表示10%的顯著性,“** ”表示5%的顯著性,“*** ”表示1%的顯著性。下同。
上述包含了中介變量產業結構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1)環境規制對地區就業有直接正效應(步驟3里環境規制的系數顯著為正,下同),即環境規制促進地區就業增加,驗證了本文提出的第一個假說;(2)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有正向促進作用,但作用力度較小,彈性系數僅為0.00609。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和其他學者的研究,可知環境規制的強度和環境規制工具的選擇會影響產業結構升級。(3)環境規制通過產業結構升級進而促進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驗證了本文提出的第二個假說。(4)環境規制對就業的總效應為正(步驟1里環境規制的系數顯著為正。技術進步和FDI為中介變量的回歸步驟1同此。)。
此外,步驟1和步驟3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外貿依存度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外貿依存度對就業的促進作用較為穩健。在步驟1和步驟3里,人力資本對就業的影響顯著為負,說明人力資本對就業數量的削減作用十分穩健,隨著人力資本的提高,企業更傾向于雇傭高人力資本的工人,雇工的質量增加數量減少將會是一種趨勢。
(二)技術進步的中介效應
采用同樣的方法,可以對技術進步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步驟1,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為0.0791,在1%的水平下顯著,步驟2里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和步驟3里技術進步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228和-0.0278,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所以環境規制經由技術進步這一中介變量影響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同時第三步中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為0.0204,在1%的水平下顯著,所以環境規制通過作用技術進步這一中介變量進而會對就業產業部分中介效應,這也為尋找及驗證其他中介變量提供了可能性。上述包含了中介變量技術進步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1)環境規制對地區就業有直接正效應,即環境規制促進地區就業增加;(2)環境規制對技術進步有正向促進作用,但作用力度較小,彈性系數僅為0.0228。目前中國各個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水平尚有較大的上升空間,且存在地區差異,企業即使不進行技術革新尚有一定回旋余地,因而環境規制對技術進步的激勵作用較為微弱。(3)環境規制通過技術進步進而削減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驗證了本文提出的第二個假說。環境規制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業的技術升級,技術升級伴隨著大型高效機械設備的使用,會導致機械設備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因而會導致就業人員數量減少。根據前面理論分析,目前中國環境規制刺激的技術進步更多體現在生產技術的進步上,因而削減就業,而治污技術的進步尚不明顯,因而治污技術進步帶來的環保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就業的增長尚未凸顯。但地方政府為了贏得GDP和稅收錦標賽,會保護并維系三高企業的運轉,就業不減反增,當然,在技術升級大背景下,關停的三高企業往往是一些多元化經營的企業,其關停技術指標尚未達標的高污染行業的生產,轉而經營技術要求不高且監管較為寬松的其他行業,雖然高污染行業的就業人員有所減少,但是轉產可能彌補吸收更多的勞動力資源和其他生產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減輕高污染行業關停的損失,同時也向外界展示了一個良好的運營狀況,所以,雖然環境規制通過技術進步對就業的中介影響為負,但是總的效應依然為正。

表2 技術進步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N=435)
(三)FDI的中介效應
步驟1里,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為0.0791,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步驟2里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和步驟3里FDI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381和-0.370,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所以環境規制經由FDI這一中介變量削減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同時步驟3中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為0.0589,在1%的水平下顯著,所以環境規制通過作用FDI這一中介變量進而會對就業產生部分中介效應,為環境規制經由其他中介變量影響就業的解釋提供依據。

表3 FDI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N=435)
上述包含了中介變量技術進步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1)環境規制對地區就業有直接正效應,即環境規制促進地區就業增加;(2)環境規制對FDI有削弱作用,但作用力度較小,彈性系數為-0.0381,說明隨著中國各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水平提高,以及用工成本及政策優惠的變化,加上國際經濟低迷,FDI進入中國的數量有所減少,中國已然不再是發達國家的“污染天堂”。(3)環境規制通過FDI進而削弱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驗證了本文提出的第二個假說。步驟3里,FDI對就業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可能的解釋是隨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水平提高,進入中國的FDI就總量而言有所減少,因而中國的資本存量減少,經濟增長的動力減弱,削弱就業的吸收能力,加上FDI的結構偏向高技術型,這種技術進步的溢出效應更多體現在生產技術的進步而非治污技術的進步上,因而對就業有負向影響。還有一種可能是,環境規制增加了內資企業污染治理的成本進而削弱其吸收和學習能力,FDI對中國企業治污技術的溢出效應的發揮受到內資企業較弱的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的限制,因而治污技術進步帶來可能的就業增長被弱化。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系統考察了環境規制對我國就業的影響機理,并利用1999-2014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運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了檢驗,研究結論表明:(1)環境規制對就業有直接的正向促進作用;(2)環境規制通過產業結構作用于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環境規制倒逼產業結構升級,進而增加就業;(3)環境規制通過技術進步作用于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環境規制刺激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削弱就業;(4)環境規制通過FDI作用于就業的中介效應顯著,環境規制減少FDI進入,進而削減就業。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分析實現環境保護和就業雙重紅利的路徑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
(1)加大環境規制力度,倒逼產業結構升級,同時要因地制宜地選取恰當的環境規制工具,制定不同環境規制工具組合的規制方案;另一方面,還應重視影響產業結構的其他重要因素,以達到政策聯動效果。(2)促進生產型技術進步的發展,也要重視治污型技術進步的發展,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實現環境規制促進治污型技術進步,治污型技術進步帶動環保產業的發展進而促進就業。(3)完善外資企業投資的宏觀經濟環境,打造新的吸引外資的亮點;在FDI引入的結構方面,應重視高技術企業的引進,尤其是高治污技術企業引進,同時中國企業也要積極修煉內功,以配合外資企業在本國技術溢出效應的發揮,最終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實現環境保護和就業的雙重紅利。
[1]陸旸.中國的綠色政策與就業:存在雙重紅利嗎?[J].經濟研究,2011,(7):42-54.
[2]李志青.“十三五”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重點和展望[J].上海經濟,2015,(10):75-77.
[3]Greenstone M.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ial a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1970 and 1977 dments and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6) , pp.1175-1219.
[4] Dissou Y. , Sun Q. GHG mitigation policies and employment: A CGE analysis with wage rigidity and application to Canada [J]. Canadian Public Policy, 2013,(39), pp. S53-S65.
[5] Gray W. , Shadbegian R. , Wang C.B. Do EPA regulations affect labor demand? Evidence from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Management, 2014, 68(1) , pp. 188-202.
[6] Altman I. , Hunter A. M. The employment and income effects of cleaner coal: The case of futuregen and rural illinois [J].Clean Technologies & Environmental Policy, 2015, 17(6) , pp. 1475-1485.
[7] Horbach J. , Rennings K.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dynamics in different technology field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German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2009[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3, (57), pp.158-165.
[8]陳媛媛.行業環境管制對就業影響的經驗研究:基于25個工業行業的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11,(5):67-73.
[9]閆文娟,郭樹龍,史亞東.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與就業效應:線性還是非線性?[J].經濟科學,2012,(6):23-32.
[10]王勇,施美程,李建民.環境規制對就業的影響:基于中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的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13,(3):54-64.
[11]李夢潔,杜威劍.環境規制與就業的雙重紅利適用于中國現階段嗎?——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J].經濟科學,2014,(4):14-26.
[12]趙玉民,朱方明,賀立龍.環境規制的界定、分類與演進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6):85-90.
(責任編輯:風云)
How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Employment——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Mediating Effect Model
YAN Wen-juan1, GUO Shu-l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China;2.Business School,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222,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FDI,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hina’s employment. We establish a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test it empirically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different provinces between 1999 and 2014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not on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employment,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employment through the thre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promote employment indirectly by forc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Meanwhi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so reduces employment indirectly by stimula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restricting FDI. But the total effect is positive.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the double-dividend go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mploy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mployment;industrial structure;technical progress;FDI
2016-05-04
陜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項目(2016Z012);西安工業大學校長基金項目(XAGDXJJ15019);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58)
閆文娟(1984-),女,新疆哈密人,西安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郭樹龍(1982-),男,天津市人,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講師。
F061.3
A
1004-4892(2016)10-01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