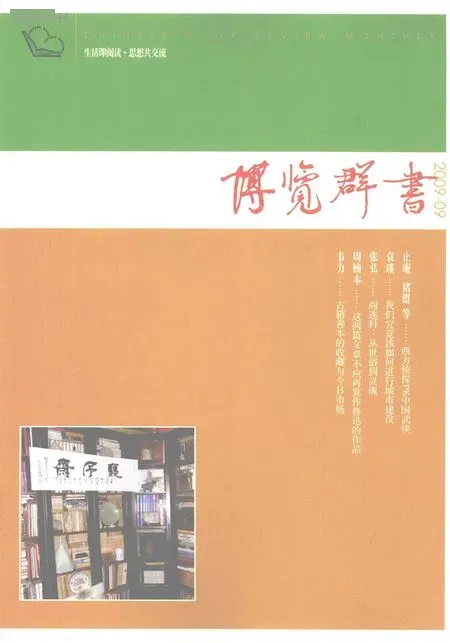開創者的缺點
樓正豪
《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研究》是目前國內唯一一部研究赴日唐人的專著,作者先后在浙江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學習研究,是此專業領域學術水平較高的青年學者。
全書共36萬字,分為緒論與正文三篇。在緒論中,作者指出以往的赴日唐人研究多偏重于赴日不歸的唐人,且多圍繞八世紀的鑒真、道璿等僧侶和九世紀的張友信等商人的個案考察,由于相關文獻資料的匱乏,對于赴日唐人綜合系統的研究尚不多見。而作者盡全力將日本正史《日該書紀》《續日本紀》以及其他相關史料中分散的相關信息進行整理、校異與補正,以宏觀的視角對七至八世紀整個赴日唐人乃至唐文化在日本的傳播,進行了一番研究。作者提出赴日唐人由于時代、地位身份各異,因此具有的才能和所做貢獻亦不同的看法,總結出七世紀的赴日唐人以使節和俘虜為主,八世紀的赴日唐人階層較為廣泛,而九世紀以商人為主的特點。關于未將九世紀赴日唐人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作者認為九世紀以商人為主的赴日唐人,已經難以判斷其來自哪個國家,研究九世紀以后的赴日唐人,需要新的視角與方法,故作為今后追蹤探求之課題。
該書正文第一篇《“唐人”用語的內涵以及唐人記事的成立》的論述重心在于探究日本史料中“唐人”一詞的含義和對《日該書紀》與《續日本紀》唐人記事的作者與內容進行文獻考證與史料批判。正文第二篇《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總論》是全書的中心部分,對七世紀與八世紀赴日唐人的名單、特點分而論之,七世紀的赴日唐人只有使節與俘虜,而八世紀階層廣泛、人數增加,而且已不是大規模集團性遷徙,多搭乘遣唐使船,在日本方面的招請之下赴日的。最后作者又對赴日唐人與日本古代國家內政外交的關系做了總結,將赴日唐人納入古代日本國家支配體制之中進行考察,通過對唐人的賜姓方式之分析,揭示了日本政府對于外國人的改賜姓均基于把其納入自己王權之下的“事大主義”思想,又對日本接待唐使與新羅使、渤海使時所使用的不同賓禮所體現出的雙重“中華思想”做了深入分析。正文第三篇《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個案研究》由“唐俘續守言、薛弘恪之研究”“唐人袁晉卿之研究”與“唐使沈惟岳等一行之研究”三部分構成。之所以能夠進行個案研究,是因為關于他們的資料相對豐富,并且身份相異,十分具有代表性。通過對這三類人物在日活動的考察,有助于我們窺探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在唐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縱觀全書,可以總結出如下的特點:
首先,資料豐富,旁征博引。中國方面關于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的資料幾乎為零,日本方面過于分散。然而作者除利用了《日該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后紀》《續日本后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這六部日本正史及部分佚文(《日本紀略》《類聚國史》收錄)之外,還征引了各類日本古典文獻,包括詩歌文集、律令格式、正倉院文書,甚至木簡、陶片等考古資料。凡是有一點關于他們的蛛絲馬跡,作者決不放過。例如2010年4月8日晚日本各大電視臺報道了奈良西大寺舊境內發現了書寫有赴日唐人皇甫東朝姓名的墨書陶器殘片,作者得知后于當月18日立即專程赴奈良目睹,一聽說正倉院寶物特別展展出了含有鑒真和尚親筆簽名的書狀,作者便前往考察。對于考證不定的文獻記載,作者怕有遺漏也不敢隨意舍棄,而是列出了一份疑似的八世紀赴日唐人之名單。應該說,該書所統計出的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名錄是目前最翔實完備的,而關于他們的資料收集也是最全面豐足的。
其次,考證綿密,條分縷析。為了得到最詳盡準確的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名單以及考察他們的赴日過程與在日活動,所有出現過他們姓名的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全都經過了作者嚴謹細密的考證分析,這樣的考據過程貫穿于全書始終,可以說全書就是由對各種問題的考證組成的。大體來看,作者的考證分為以下幾類:第一,對于用語概念的考證。例如開篇對該書題目中“唐人”一詞內涵的考證,指明日本文獻中的“韓人”“辛人”“漢人”“吳人”均不是該書的研究對象,界定出“唐人”的概念包括“唐俘”、“唐使”、《續日本紀》的“唐僧”和一部分表明為“唐人”之群體。還如關于混血兒稱謂的考證,作者指出日本男性與當地女性之后代被稱為“倭種”,不被視作唐人,第一代赴日唐人為“唐人”,而在日本所生子孫不再被稱為“唐人”。還有,作者首次對“陳袁濤涂”一詞做出了正確解釋,其實“陳袁濤涂”是春秋時期陳國的袁濤涂,為赴日唐人袁晉卿的先祖,糾正了日中學界稱“陳”為“南朝陳國”或“袁濤涂”是袁晉卿異稱的錯誤。第二,對于事件的考證。例如對七世紀唐使、唐俘與八世紀唐人、唐僧、唐使以及疑似唐人入唐時間與原因的考證。又如對唐人赴日方式、賜姓制度和在日活動的考證,還有對皇甫東朝與皇甫升女、薛弘恪與薛妙觀之間親屬關系的考證等。第三,對于文獻的校勘。例如作者考證出《續日本紀》中關于赴日唐使的官職“判官”應是“行官”之誤。又如作者指出了《續日本紀》里的“薩”姓實為“薛”姓之誤,由于“薛”之俗字“ ”與“薩”形似而被誤認,于是對七世紀赴日唐人“薛弘恪”“薛妙觀”的姓氏做了首次更正。
最后,分類合理,詳略有別。作者面對文獻中如此之多的赴日唐人姓名,必須先根據身份對他們進行分類才能進行論證。目前所發現的七世紀赴日唐人只有使節與俘虜,均是大規模集團的移動。太宗朝的唐使是高表仁一行,高宗朝有郭務悰、劉德高、司馬法聰、李守真等一行,被迫赴日的唐軍俘虜中可知姓名的有續守言、薛弘恪等。八世紀的赴日活動多為個人行為,且人數眾多,身份多樣。以往的日本學者們按照生存狀態將在日外國人分類為三類:其一,品部、雜戶、伴部構成人員;其二,一般人員;其三,專業技能者、僧侶和遣使滯留者。基于此,作者將其分為五類,第一類專業技術者,包括王元仲、李元瓌、袁晉卿、皇甫東朝等這些漢音教育與唐樂禮制的專家;第二類僧侶,指道榮、道璿以及鑒真僧團等;第三類唐使,為沈惟岳、孫興進等一行;第四類婦女,目前僅李自然一人;第五類其他人員,如一些信息不詳的赴日人員。根據文獻的多少,作者詳細論述了續守言、薛弘恪、袁晉卿、皇甫東朝、鑒真、沈惟岳等的詳細赴日過程以及對中日交流的貢獻,其他人員則只能簡而敘之。
依筆者淺見,該書亦存在一些問題如下:
首先就是作者試圖對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進行一番體系化研究的目標似乎并未得到很好的實現,最大的研究障礙就是資料太少,過于零散,因而一些綜合性的結論只是通過對個別人的考察而得出的,普遍性薄弱。例如作者在第二篇第三章《八世紀赴日唐人的諸問題》中討論“唐人赴日的動力與阻力”問題時,按身份分成唐使、唐僧、專業技能者三類進行論述。唐使僅取高表仁、趙寶英的例子,唐僧僅取鑒真、道璿的例子,而專業技能者稍微多一點,有蕭穎士、李元瓌、袁晉卿、皇甫東朝等,關于這些人物的文獻資料雖然相對較多,但他們身上的共性是否能夠代表整個八世紀赴日唐人應該得到深思。該書雖然盡全力整理出了八世紀赴日唐人的名單,展現出作者深厚的文獻考據功力,但是關于大多數人物的資料僅是寥寥數語,作者重點論述的無外乎還是少數的幾個人物。作者對所有資料進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已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史料的價值,但要從個人的遭遇中提取時代性的特征與規律還是略顯不足,大多數結論還是流于推測。
其次,該書在章節編排上存在一些問題。如第二篇《唐人皇甫東朝的赴日及在日活動》一節內容豐富,與其說放在《赴日唐人與日本古代國家的內政外交》一章下,不如作為個案研究置于第三篇更為合理。作者的考證有時又過于細碎,如第一篇《〈續日本紀〉所載的唐日關系記事與編纂者——以遣唐使上毛野大川為中心》一節和第三篇對續守言、薛弘恪進行個案研究時考證日俘入唐的內容似乎與該書題目的關聯不是十分緊密,這部分的論述或許可以精簡。
最后,該書研究的人物眾多,有時同一人物在許多篇章中皆有出現,雖然該書最后附錄中的圖表照片相當豐富,如再添入人名索引和關于重要人物經歷的圖表將更加一目了然,以方便讀者查閱。還有該書存在幾處錯別字以及繁簡字體尚未統一的地方。
雖然存在以上問題,但該書不失為七至八世紀赴日唐人研究領域的開山力作,為我們展現出一幅描繪異域唐人風景的壯闊歷史畫卷。我們期待著將來有更多相關史料被發現,以完善這一領域的研究。
(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學東海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