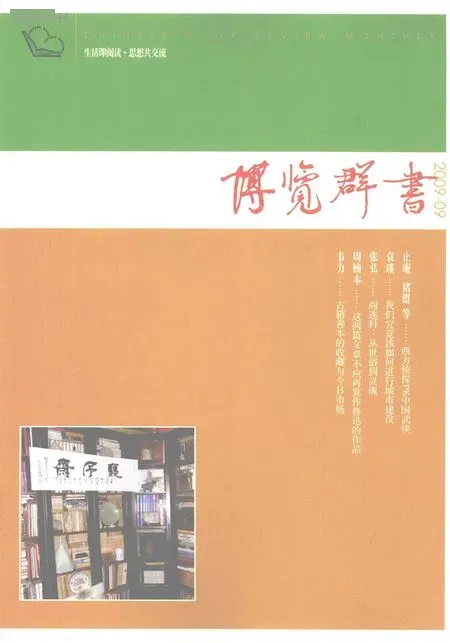關中書院:會當洙泗風,郁郁滿秦川
肖嘯+舒原
七寶閣書院特約刊出
歷史上的關中地區,不僅承載著漢唐之盛,還被稱為理學之邦。自周公集三代學術備于官師,《七略》述之,于是道學之統,自關中始。成康而后,孔門高徒秦子子南、南燕子思、石作子明、壤駟子從皆為秦人,承繼圣學,布道天下。北宋中期,橫渠先生張載崛起郿邑,勇撤皋比,倡明理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清之時,真儒輩出,關中書院建立,馮從吾、李颙前后掌教,化理熙洽,傳承關學。
【群賢薈萃建書院】
關中書院在陜西西安,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參政杜應占、閔洪學,副使陳寧、段猷顯等建于府治東南。是年十月,馮從吾與汪、李、陳、段等在寶慶寺舉行聯鑣會講,前來參與講會的文人學子多達數千人,日晡始別。臨別之時,汪可受等人對馮從吾說:“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馮從吾原本講學于城東寶慶寺已久,聲名遠播,聽講者甚眾,學者云集,佛寺已不堪容納。于是,汪可受等人在聯鑣會講的次日即開始籌劃于寺東小奚園建立書院,數月后落成,延請馮從吾講學其中,定名為“關中書院”。
書院地處幽靜的古寺之側,景致幽雅。創建之初,其建制規模相當可觀,有講堂六楹,講堂左右又各為屋四楹,東西號房各六楹,大門四楹,二門四楹。講堂之后建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岳也。講堂之前有方塘半畝,砌石為橋,豐亭于中。偏西南數十步掘井及泉,引水注塘,并覆以亭。可見,號房、齋舍、門廊、亭閣、池橋等應有盡有,規模宏敞。書院前后修葺數月,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風舞雩之意。
書院取名“關中”,講堂取名為“允執”,都蘊含著深刻的學術宗旨。馮從吾在《關中書院記》中寫道:“書院名‘關中而匾其堂為‘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中”這一理念,在子思《中庸》一書中闡釋得最為詳明。這是儒者安身立命的準則,也是他們所追求的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北宋理學家程頤曾有言曰“不偏之謂中”,所以“中”可以解釋為在修心處世的過程中需要遵循的一種不偏不倚的道德原則。按儒家對道統的構建,“中”的理念發自堯,而這也是堯得以統治天下的基礎,此后堯便將“允執厥中”授之于舜。在馮從吾看來,中與不中,難見于事,實根植于人心,這也是舜為何將中道傳給禹時又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擔憂世人求“中”于事而不知“中”深植于人心。在此,馮從吾將書院講堂取名為“允執”,就是希望在此入讀的學子可以體會到中道的內涵,研究盡性至命之學,體會無聲無臭之妙,以達到儒家所希冀的“天地位而萬物育”的至臻之境。
關中書院自創建之后,最輝煌的時期當屬明末馮從吾講學時代和清代康熙年間李颙重開關中書院講會,四方學者云集,從游者甚眾,使關中之學蔚為大觀,因而時人有詩贊曰:“會當洙泗風,郁郁滿秦川。”
【關西夫子設講筵】
關中書院的講學始于馮從吾在寶慶寺的“聯鑣會講”。馮從吾(1556—1627),字仲好,號少墟,明代西安府長安人。萬歷天啟年間關學的集大成者,人稱“關西夫子”。
馮從吾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后授御史。馮性情耿直,為官清正,嫉惡如仇,曾以一封《請修朝政疏》上書萬歷皇帝,指責其終日沉迷酒色,荒廢朝政,懈怠國事。馮從吾在奏疏中寫道:“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甚!”馮從吾一身正氣,冒死直諫,萬歷皇帝大發雷霆,當即傳旨對其“廷杖”。廷杖就是在朝廷上當眾用棍棒毆打被脫去衣裳的大臣,這是對官吏實行的一種酷刑。行刑之際,大臣趙志皋等人極力求情,聯名舉保,又會當太皇太后壽辰,馮從吾才幸免于難。在這之后,馮從吾借病辭官,歸養長安故里,三年后重被起用,任職長蘆鹽征。由于官商勾結,加上朝中宿怨已久,他再次被罷官回鄉。
馮從吾曾師事理學大師許孚遠,歸鄉后便杜門謝客,潛心治學,居家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直到天啟年間才又重新接受朝廷任職。家居期間,馮從吾除了繼續研讀儒家經典以外,還編撰《關學篇》,全面總結以張載為主的關中理學,其學術思想傾向于融合朱熹的理學和陸九淵的心學。
此間,馮從吾還間或講學于城東南寶慶寺。在冒死直諫事件之后,馮從吾的官德聞名朝野,而其學問又精深醇厚,前來聽講者日益增多,小小的寶慶寺門庭若市。偶爾的講學行為逐漸演變成定期的會講活動。為此,馮從吾撰寫《寶慶寺會約》,規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講學三次,并且對講學的內容、與會者的言行等皆有所規范。這顯示了明代講學最大的特點,即儒學詮釋的平民化。不僅是城鎮官府書院向平民百姓開放,儒學大師們還隨處講學,山林、寺廟都可作為其講學的場所,于是山林布衣、鄉村長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侶皆可前來聽講,甚至登堂講說。這是宋元時期罕見的現象,促進文化學術下移的同時,也體現了儒學與佛道的逐漸交融。
萬歷三十七年(1609)十月,馮從吾與汪可受等人在寶慶寺舉行聯鑣會講,而后學者云集,以致寺不能容,故而汪氏等人在寺東建立書院,取名“關中”,延請馮從吾、周傳誦等講學其中。馮從吾訂有《學約》《章程》,以為關中書院講學會講的規章制度。馮居院講學十余年,四方從游者五千余人,關中書院亦因此而成為關學的大本營,有詩贊曰:“出則真御史,直聲震天下。退則名大儒,書懷一瓣香。”馮從吾講學強調“躬行”“救時”,盡管有“會期講論,勿及朝廷利害、邊報差除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的《會約》規定,但“正以國家多事,人臣大義不可不明耳”,因此就要不計毀譽、得失去講學。于是講學自然就會涉及國家大事,這與東林書院相似,而馮從吾也是東林黨在西北的領袖。
明代后期,宦官魏忠賢專權,朝政腐敗,思想控制越來越強。因魏忠賢對“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東林黨人恨之入骨,下旨禁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而東林、關中、江右、徽州的一切書院,盡數拆毀。于是天啟五年(1625),關中書院毀于閹黨王紹徽、喬應甲之手,從學者皆被遣散。馮從吾遭此劫難,一病不起,于天啟七年逝世。崇禎年間,閹黨鏟除,關中書院得以重建,但影響已不及從前。
【海內真儒重開講】
明清之際,戰亂不止,關中書院遭到很大破壞,學子四散。清康熙三年(1664),巡撫賈漢復檄西安府葉承祧、咸寧縣知縣黃家鼎重修關中書院,擴建院址,增設楹廊。七年之后,在陜西總督鄂善的主持下,關中書院得以再次修復,關中大儒李颙應邀主院,重開關中書院講會。
李颙(1627—1705),字中孚,號二曲,陜西周至人,與黃宗羲、孫奇逢并稱為清初三大儒。黃宗羲之學盛于南,孫奇逢之學盛于北,而李颙之學盛于西隴。李颙自小聰慧過人,十五六歲時已博通典籍,十七歲時讀馮從吾《少墟集》,乃恍然大悟圣學淵源,于是潛心治學,研究經史。自此以后,志不事清為官,但以倡明關學為己任,關中人士翕然從師,問道之人接踵而至,被譽為“海內真儒”。李颙講學一生,以闡明學術為匡時救世的第一要務,其學批判繼承程朱之主敬窮理和陽明之致良知,主張“反躬實踐”“悔過自新”。他以明遺民自居,清廷多次舉薦,皆稱病拒絕,堅辭不就。官府甚至派人將李颙連人帶床抬到西安,行至南郊,他竟拔刀自刎,寧死不從,來人只得作罷。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巡幸關中,征召行在,李颙也固辭不見,只是遣子攜書前往。康熙無奈,特賜御書“操志高潔”匾額,予以表彰。
康熙十年(1671),李颙應常州知府駱鐘麟之邀到無錫、江陰、靖江、武進、宜興各地講學。駱鐘麟于順治年間曾任陜西盩厔(今周至)知縣,數次以師禮登門拜訪李颙,請教為學之要,李颙說:“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駱鐘麟銘記于心,因而在其升任常州知府后又延請先生前來講學。在無錫東林書院,李颙不僅展謁燕居廟、道南祠,還前往忠憲祠瞻仰高攀龍遺像,徘徊故地,不覺泫然,其后與高世泰會講,賢達環集。此次南下講學,李颙名播江南,亦可算作為他重開關中講會的學術預演。
康熙十二年(1673),鄂善在修復關中書院后,造士延禮,啟迪諸生,李颙三辭不得,應邀主院,并重開停于明天啟年間的關中書院講會。開講之日,總督、巡撫、將軍等各級官僚,并德紳、名賢、進士等文人學者,皆環席而聽,多達數千人,其盛況有如馮從吾時代。李颙極為倡導東林書院的自由講學之風,他說:“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轉乾坤,全在講學。天下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的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為了更好地組織講會,李颙還重新制定了《關中書院會約》十條、《關中書院學程》十一條,對講會的時間、內容、方法、目的及弟子日常禮儀規范等皆做出了具體規定。
關中書院自馮從吾之后,講會已停,李颙此次于關中書院重新開講,實是繼明代講會之“絕響”,無怪乎他自己在《關中書院學規》小序中也自譽為“當今第一美舉,世道人心之幸也”。
【愿承絕學共諸賢】
關中書院歷來是關學的大本營。關學,即關中地區的理學。在關學千年的發展史上,逐漸融合了二程洛學、朱熹閩學、陸王心學等理學學派特點,不斷創新,張載、呂柟、馮從吾、李颙、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儒者皆為中流之砥柱,倡道鄉里,傳承絕學。為弘揚關學,馮從吾曾梳理關中地區著名的理學大師四十三人,上至北宋、下迄明代,考證始末,總結學術特點,編訂成冊,是為《關學篇》。
橫渠先生張載堪稱關學之鼻祖,精思力踐,妙契疾書。早年喜談兵法,曾書治軍之法數條與范仲淹,范氏卻道:“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范仲淹斷定張載將在儒學上大有作為,因而勸其回鄉讀書。于是,張載潛心治學,遍及六經,而后在京師講《易》,端坐于虎皮之上,聽從者甚眾。一日,程顥、程頤二兄弟至,與之論《易》。二程為張載外兄弟之子,對其頗為尊重,然而張載卻心服二程,次日便撤掉虎皮,停止講學,對其門人曰:“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熹贊其為“勇撤皋比,一變至道”。北宋之時,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鼎足而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卻道關學為孔子嫡傳,可駕濂、洛之上。
然而在北宋理學興起之時,無所謂門戶之別,關中人士多師從二程。靖康之變以后,雖然關中大部分地區淪為金、元之地,然而楊奐、楊天德等關中諸儒與許衡互相唱和,傳承朱子之學,使理學在北方再次得以弘揚。
入明之后,容思先生段堅近宗程朱,遠溯孔孟,創建志學書院,倡明關學。而后涇野先生呂柟,為自張載后關學之集大成者,師從關中大儒薛敬之。在心學席卷大半個明朝之時,呂柟仍舊篤守程朱理學,《明史》贊其曰:“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呂柟入仕為官三十余年,仍舊堅持講學傳道,除了開講于開元寺、寶邛寺、崇寧宮以外,還建立云槐精舍與東郭別墅、東林書屋,聚徒講學,四方學者云集。呂柟之學不僅昌明鄉里,還遠播國外,朝鮮國曾上奏曰:“狀元呂柟……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可見,呂柟成為朝鮮士人學習理學的典范,廣受敬慕。
明代中期,渭南學者南大吉官居紹興時,曾修復稽山書院,并跟隨王陽明學習良知之學,而后歸鄉講學,建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于是關中始有陽明之學。數十年之后,王學興盛,關學之集大成者馮從吾,將程、朱、陸、王之學融而為一。
馮從吾之后,清代關學大儒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三人相繼續寫《關學篇》,增加馮從吾、李颙、王心敬、李元春等人學案三十三篇。王心敬師從李颙,其說近陸王,賀瑞麟師從李元春,李氏則篤守程朱之學,皆為清代關中地區理學的杰出代表,孜孜不倦地傳播關學。
作為關學大本營的關中書院,自明代以來就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關中學子,使得關中地區真儒輩出,他們潛心理學,布道天下。雍正十一年(1733),關中書院被定為省會書院,其陜西最高學府的地位再次得到確認;光緒三十二年(1906),書院提倡新學,再度興修,創辦“兩級師范學堂”,而后改制為陜西師范大學堂,為西北五省最高學府;民國初年,改為陜西省立師范學校;新中國成立后被列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恢復陜西省西安師范學校名稱。今天的關中書院為西安文理學院初等教育學院所在地。
如今的書院,依舊古樹參差,庭院深深,樓閣齊整,書聲瑯瑯。如今的關中,承載著歷史的厚重,延續著古人的傳奇,芳澤承續,弘揚關學。賀瑞麟曾寫道:“關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質直,而其士風亦多尚氣節而勁廉恥,故有志圣賢之學者,大率以是為根本。”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中,關中地區文化底蘊尤其深厚,陜西因而也成為當代中國的教育強省。關學就像歷史長河中不老的松柏,任憑水波翻滾,始終傲然峭立,又像是聳立的青山,其學綿延不絕,其精髓更是有待我們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