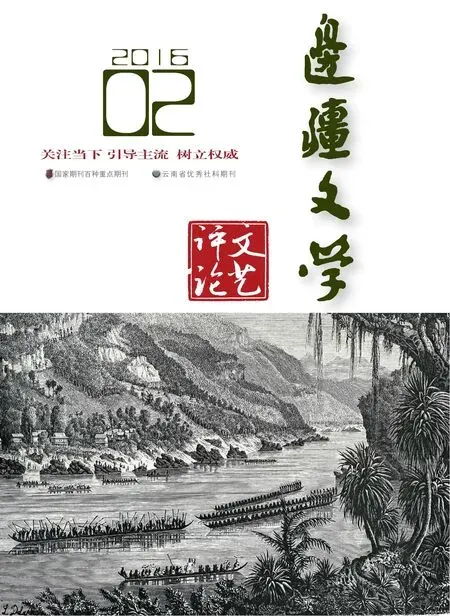劉大先:新一代人的探索
◎李云雷
劉大先:新一代人的探索
◎李云雷
我與大先認識很久了,但真正熟悉起來卻是最近兩年。大先的名字因為與“大仙”諧音,比較好記,所以在認識以前就早知道了他的名字,后來在各種會議上經(jīng)常見到他,也讀過不少他的文章,但私下交流卻不多。2014年夏天,東北財經(jīng)大學的韓傳喜邀請我們和賀仲明、方巖等人去大連開會,一起在那里待了幾天,這次會議人比較少,也就交流的比較多。傳喜很是熱情,請我們喝了不少次酒,在酒酣耳熱之際,大家暢所欲言,放浪形骸,交往也就輕松隨便了許多。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喝酒到深夜,又去一家海鮮燒烤繼續(xù)喝,那次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搖搖晃晃的,我還拍了不少大先與傳喜勾肩搭背類似同志的照片發(fā)到朋友圈,引起很多人的關注與調侃。在那次會上,我才知道,原來大先、傳喜和方巖都來自一個地方,安徽六安,他們那里出了不少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名人,如韋素園、臺靜農(nóng)、韋叢蕪、李霽野、蔣光慈、李何林等,當代作家中也有徐貴祥等人,現(xiàn)在做文學研究與評論的,一下又涌現(xiàn)出了像他們這樣的青年才俊,真是一個人文薈萃之地,這在全國也是很少見的,據(jù)說現(xiàn)在已有人專門研究“霍邱現(xiàn)象”、“文學蓼軍”,希望能早日見到。
跟大先聊天,聽他在會上的發(fā)言,給人最突出的一個印象是語速很快,很多復雜的理論問題在他的思路中被整理成型,以連珠炮式的語言噼里啪啦說出來,如果不認真聽他說話,很快就跟不上了,他思維的跳躍性很強,眼神很專注,語氣很堅定,同時伴隨著雙手不斷變換的手勢,看上去很有激情,有時講了七八分鐘,才說,“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接下來第二點、第三點,他也講得很流暢。在私下聊天時,說到暢快處,他還會爆發(fā)出一陣陣爽朗的笑聲,他的笑聲很大,很高亢,很有感染力,可以看出他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也是個爽快自然的人。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先有一張照片,好像是在什么論壇上演講,他西裝革履,雙手有力地伸出去,目光很有神,側面勾勒的身影,很有型,也很瀟灑,大先似乎很喜歡這張照片,不少地方在用,但在我看來,這張照片雖然神采奕奕,但不夠生活化,它所展現(xiàn)的只是大先的一個側面,真實的大先則更加豐富多彩。
我對大先最深的印象是他為人做事的爽朗痛快,在生活中是如此,在寫作上也是如此。在喝酒時,不少人總是磨磨蹭蹭、磨磨唧唧,能喝也不喝,非要被勸的不得已,才勉勉強強地喝一點,大先就不是這樣,他喝酒很爽快,從來不推脫,總是杯到酒干,不糾纏什么酒官司,也不說那些場面話與客套話,有時邊喝邊聊,聊到高興處,又是一陣爽快的笑聲。在寫作上也是這樣,有一次我約他寫一篇文章,批評某海外文學權威,我們簡單聊了幾句,看法正好相似,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很快就將文章寫好發(fā)給了我,后來由于某些原因,這篇文章過了很久才發(fā)出來,他也毫不介意,甚至從來也沒有問過我。
我和劉大先的研究與批評領域并不相同,他最初主要關注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我主要關注現(xiàn)當代文學,但有一點我們是相似的,那就是我們都是來自鄉(xiāng)村的農(nóng)家子弟,這讓我們思考問題的方法與視角有不少相通之處,主要是我們都注重現(xiàn)實問題或社會問題的現(xiàn)實感,注重從社會底層的角度提出問題,也注重將自身的生命體驗相對化與學術化,在此基礎上進行探索與研究。在他的文章中,當我讀到類似這樣的段落時,便會感到有所會心:“高中畢業(yè)的端方在干熱的夏日的愁緒,讓我不自覺就會想起高中時候的暑假,我和三弟每天中午都要割五百斤整整兩平板車的蘇丹草。其實,人在勞累的時候頭腦里是沒有什么愁緒的。三伏天的正午,一絲風也沒有,陽光當頭直射,我們兩個人就佝僂在一大片高如高粱的蘇丹草地里埋頭揮舞鐮刀,揮汗如雨。……1995年的夏天在我的記憶中炎熱無比,我背部的皮膚被曬脫了兩次,新長出來的黝黑發(fā)亮,刻寫下勞動的痕跡……”,這些段落出現(xiàn)在對畢飛宇小說《平原》的評論中,但又超越了具體作品的品評,而將個人深刻的生命體驗融匯其中,展現(xiàn)了他對人生與社會的感悟與理解,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他寫到,“一個鄉(xiāng)村少年要在當代中國完成他的社會化,其間經(jīng)歷的天人交戰(zhàn)和悲苦辛酸非親歷者無法了解。在這種社會化的過程中,他的融入與摒棄、他的妥協(xié)與堅守,唯有靠心頭一點點靈明。”這既是他對小說的理解,也是他對生命的感悟,正是由于他將自己的經(jīng)驗帶入對作品的理解之中,才讓一部作品真正活了起來。
如此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在一篇影評《朋友少年行》中,他寫到:“前幾天看《賽車總動員2》,又回顧了第一部,麥昆和板牙的故事,讓我想起遠方的朋友孫磊。孫磊是我的發(fā)小,我們老家地處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六安,非常蔽塞。在高中畢業(yè)之前,我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那個叫新安的小鎮(zhèn)。渾噩,迷惘,日復一日。但是,從學校破舊圖書館借來的《魯濱孫漂流記》、《遠大前程》,外出打工的人們帶回來大世界的故事、工廠的趣聞、都市里的謀生伎倆,啟蒙了我們對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出走的沖動。……高考一結束,我和孫磊就背上簡單的行裝,踏上去上海的長途汽車,在閔行一個小鎮(zhèn)上找了個臨時的工作。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坐輪渡越過黃浦江時的情形,江水浩蕩,濁流洶涌,如同兩個少年不平靜的心……”在他的筆下,個人的青春記憶有機地融入了對電影的欣賞與評論之中,我們在他的文章中,讀到的便不是干巴巴的死板文字,而是有情感、有溫度的文章。
現(xiàn)在的文學研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在研究中我們看到的只是理論的演繹或者材料的堆積,看不到作者的真知灼見與真情實感,這已成為了阻礙當代學術發(fā)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學院體制的束縛,不少人寫文章并不是有感而發(fā),而是為了發(fā)論文評職稱等,于是只能“炮制”一篇篇文章。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作者并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問題意識,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作者,他們的問題意識與思維框架仍然是他們老師那一代人的,因而他們也只能在師長們巨大的影響下做些細致的研究,而沒有辦法提出自己的問題,并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發(fā)展出新的學術思路。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學術。新的學術發(fā)展應該建立在新的問題之上,而提出新的問題,則需要研究者從最真切的生命體驗與時代的核心問題出發(fā),從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與前瞻性的命題,從而推進研究的新進展。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劉大先是青年一代學者中的佼佼者,他從個人的體驗出發(fā),不斷提出新的問題,也在向時代深處探索。
當然就研究與評論來說,僅有個人體驗不夠,還需要扎實的學術根基。劉大先的專業(yè)領域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已有《現(xiàn)代中國與少數(shù)民族文學》、《本土的張力》、《文學的共和》等著作出版。在《文學的共和》的后記,他說,“‘少數(shù)民族文學’一直是主流文學話語‘在場的缺席’,它的處境一直較為尷尬——雖然得到了來自文藝主管部門的支持,在學理性層面似乎一直存在著‘合法性’的焦慮。這背后自然有著種種可以分析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還是來自于文學學科內(nèi)部,之前的許多批評范式在面臨已經(jīng)變化了的語境時已經(jīng)失去了效力,而一種具有范例意義的批評方法和理念尚沒有確立”,“這當然并不意味著我鉆進了某個僻靜角落、挖掘偏門的材料,故作曲高和寡之態(tài)。事實上我一直都是將某個特定對象放入更為寬闊和立體的話語中進行討論,用俗白的話說就是‘跨學科’的嘗試與努力,并且也沒有放棄對于時代重大話題的關注和參與。我談論的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同時也是‘中國文學’,更是‘全球性的文學’。”在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大先的學術定位與追求。對于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我是外行,但在大先的論著中,我卻可以看到他所做的廣泛的田野調查,以及他在批評與理論建構上的努力。比如在《現(xiàn)代中國與少數(shù)民族文學》一書中,他以“歷史與書寫”、“主體與認同”、“差異與表述”、“地理與想象”、“迷狂與信仰”等角度,涉及到了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歷史敘事、身份與變異、譯介、空間、神話等各個方面的問題,讓我們看到了他的整體把握與思考。此書被國家社科基金外譯項目立項,譯為日文,這在青年學者的著作中很少見。
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之外,劉大先也涉獵頗廣,《未眠書》是他的書評或“讀書筆記”,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閱讀范圍的廣博,其中既有對《孽海花》、錢鍾書、劉慈欣等中國作家作品,也有國外作家如奈保爾、帕斯捷爾納克、安吉拉·卡特,還有理論家薩義德、阿多諾、詹姆遜、鮑德里亞、巴赫金等人,如此廣闊而駁雜的閱讀視野,讓我們看到了劉大先的理論根基及其對閱讀的興趣與喜愛,僅從這本書所勾勒的“認知地圖”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一種全球性視野確實是劉大先的內(nèi)在追求,在此書的“自序”中,他說,“阿多諾說,一個人在生活中所實現(xiàn)的,無非就是變換方式彌補童年的嘗試。我在鄉(xiāng)村的少年時代難得有讀書的條件,后來之所以選擇以學術為業(y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知識與思想的渴求,以及少年時代這種渴求不能滿足所產(chǎn)生的缺憾彌補心理。”
在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界,劉大先的特點就在于他與別人不同的視野,既包括少數(shù)民族研究視野,也包括全球性的文化視野,如果說前者讓他“比本土更本土”,那么后者則讓他“比國際更國際”,如果說前者來自于他的專業(yè)研究領域,那么后者則來自于他廣泛的閱讀及其在美國訪學的經(jīng)歷,這樣的雙重視野讓他在觀察與思考“中國文學”時,便具備一種他人沒有的目光。說到全球性的文化視野,不能不提到劉大先翻譯的《陳查理傳奇:一個華人偵探在美國》,此書對研究中國人形象在美國的接受與變化有著重要意義,史景遷說,“這是一部獨辟蹊徑、令人陶醉的書。它為我們提供了從中西兩個側面探討中國人的經(jīng)歷的嶄新方向。此書將徹底改變我們敘述這個爭議不絕卻又扣人心弦的故事的方式。”劉大先將此書譯介到國內(nèi),不僅填補了這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在文學研究之外,劉大先還先后出版了兩部影評集,《時光的木乃伊》與《無情世界的感情》,相對于專業(yè)領域的研究論文,他的影評大多采用隨筆的形式,更加活潑,更加隨意。閱讀這兩部作品,我們會發(fā)現(xiàn)劉大先看了大量影片,他的影評中有很多真知灼見,比如在一篇分析《十月圍城》的文章中,他尖銳地指出,“這里充分暴露了編導者自身的精神空間的狹隘,他們一直超越不了自己的局限,拘泥于世俗辛酸的日常生活之中,看不到人類在物質、肉身、情感的追求之外,尚有精神上的高尚、偉大,能夠為了陌生人蹈死不悔的利他的一面。他們自私而偏狹地以己度人,以為世上只有被領導的愚民和為利益追逐的動物,沒有主動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志士。他們理解不了革命,既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在殖民資本主義的溫床中誕生的人們,適逢小資產(chǎn)階級美學大行其道,于是在原本就薄弱的歷史記憶中再加入了這一股稀釋的渾水”,“消費與娛樂訴諸肉身與情感,所產(chǎn)生的后果讓人始料未及,有意無意地造成了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雙重傷害。是將革命戲說、抽象化和空洞化,以滿足公眾消費的需求,還是還革命一個公道,這是個問題。”在這里,劉大先在對影片做了細致的分析之后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這既是美學分析也是思想分析,直指問題的根本,讓我們看到了他的敏銳與犀利。書中類似這樣的分析所在多有。劉大先在《無情世界的感情》的后記中說,“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不認識任何一個電影導演、編劇、演員、放映機構人員,甚至影評人,一句話,不認識和電影相關職業(yè)的從業(yè)者。它們都是自在的產(chǎn)物,隨興所至,興盡則止。”我想正是這樣獨立寫作的姿態(tài)與自覺,讓他保持了一種良好的狀態(tài)。在《時光的木乃伊》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劉大先對少數(shù)民族題材影片的分析與把握,無論是國內(nèi)的少數(shù)民族電影,還是國外的少數(shù)族裔影片,乃至一些深層次的理論問題,他都能有深刻細致的分析,給人以啟發(fā)。
在70后一代的青年學者與批評家中,劉大先是少有的擁有清晰的問題意識并能不斷進行開掘的人之一,他扎實的學術根基和開闊的視野,讓他的閱讀與思考充滿活力,他通過閱讀與研究將自我與世界對象化、問題化與學術化,并以他的文章與評論將生命體驗升華,為這個世界的文化增添了色彩。可以說他的探索代表了一代青年人的探索,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探索,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青年批評家的創(chuàng)新,以及青年學者構建新的學術范式的自覺努力,我也希望他能夠長久地保持這樣的探索與心靈狀態(tài):
“寫到這里,我又回想起第一次去塔什庫爾干的夜晚。那天正好是漢地的中秋節(jié),我躺在床上睡不著。窗戶沒有窗簾,帕米爾高原的月光如晝,干燥冰冷的光輝打在屋子里,精神清明,光潔洞燭。坐起來從床上望過去,烏云中間一輪皓月高懸在山頂上。起伏的山脈如同鐵一樣沉穆,四周寂靜無聲,仿佛宇宙間唯有我一人存在。心靈在那時候變得飽滿、充實、盈潔、輝煌壯大,無可匹敵,沛然莫之能御。”
(作者系青年批評家,現(xiàn)供職于《文藝報》)
責任編輯:楊 林

柳浪聞鶯圖 桂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