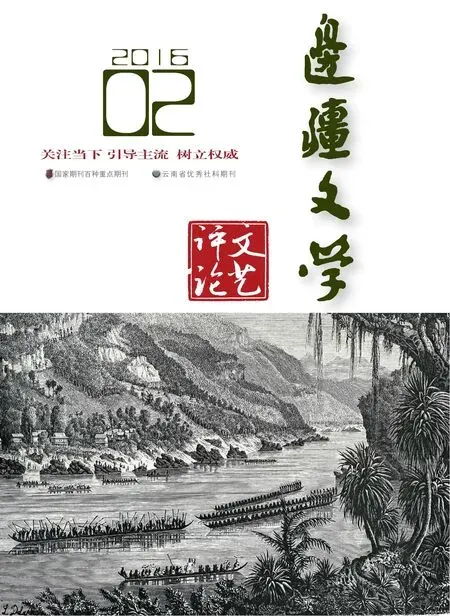在語言中構建一種更高的藝術真實
——甫躍輝小說淺論
◎朱彩梅
在語言中構建一種更高的藝術真實
——甫躍輝小說淺論
◎朱彩梅
第一次讀到甫躍輝的小說,是在2012年底第四屆高黎貢文學節舉辦時,作為八位提名作家之一,文學節作品集選入他兩部中篇小說《丟失者》、《動物園》的片段。因是節選,情節不免突兀,但讀了沒幾段,就能感覺到特別之處,其語言的清晰、簡潔、準確,字里行間的從容、平和、中正,與之前風行一時的很多80后偶像作家矯飾、油滑、戲謔,或是決絕、殘酷、任性的筆調,可謂大相徑庭。而且,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青年最易犯的傷感病——那種情感泛濫、語言夸張、裝腔作勢的唯美文藝腔和千篇一律、俗不可耐、毫無節制的成長敘事。對于一位年輕小說家來說,難能可貴。雖然還在探索階段,但作者具有強烈的敘事自覺和經典意識,其寫作是“取法乎上”的。
之后在昆明圓通影院會場上見到他,正和云南青年詩人符二聊得高興,一臉笑容淳樸、燦爛。現場交流時,談到復旦大學文學寫作專業導師王安憶對自己寫作訓練要求之嚴苛,他聲音沉穩,語調莊嚴,笑容不見了。可想見,導師對于他的寫作意義之重大。自此留了意,再看到他的作品,自然就特別關注些。之后又發現,他的創作量也很驚人,從2006年到2015年,每年持續發表多篇小說,先后出版了《少年游》《刻舟記》《動物園》《魚王》《散佚的族譜》《每一間房舍都是一座燭臺》《安娜的火車》等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且寫作視野日漸開闊,品質不斷提升。
小說的真實性
甫躍輝創作已十年,整體來看,他文學感受敏銳、細微,善于組織素材,能為呈現不同類型的故事、生活找到對應的敘事節奏、表達方式;詩化語言的適度運用,有助于經營意象,營造氛圍,在他筆下,一些細節被賦予了深厚的意蘊;若說其語調的自在、從容,有三分來自性格的溫和、淡定,倒有七分源自他對寫作永恒意義的堅定信念。這些元素、態度使得他的小說貼近生活,與現實世界息息相關、彼此照見,具有了可感知、可觸摸的真實性、生動性;同時,他又具有一種超越的視角——不斷審視生活,審視自己,時時反省、思考如何看待世界,理解世界。這種“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寫作,很有希望通往一種超越現實的、充滿力量的真實,那是更高的藝術真實。
好的小說,具有不可抵抗的召喚力。讀上幾句,深海般的吸引力會使讀者不由自主想進入它的內部世界,讀下去,一直讀下去。這種召喚力源于作品所創造的真實。所謂真實,不是內容方面單純的遵照現實,也不是寫作手法的照相式如實描摹。作家創作時,盡可展開想象,大膽虛構,但想象與虛構里面,須含有另一種更高的藝術真實。小說的生命之所在,正是這樣的真實。就像一個人的行事,只有當此事是其性格使然,源于內心深處的渴求,非外力強迫或對體制、權威的屈服,他所做的一切,才會煥發出活潑、迷人的光彩。小說亦如此,當它遵循自己內在的結構來運行,才會獲得真實性。真實蘊含人性的豐富、存在的無窮,真實使小說產生令人信服的動人效果。這樣的作品,不是向讀者講述、傳達什么,而是使讀者直接體驗。讀者身在書房,卻能經歷各種人生,享有豐富的生命體驗。
甫躍輝深知藝術真實的重要性。他的創作,正如其所言:“我所有的小說加起來,真實經歷的痕跡還占不到百分之十。但是,它們千真萬確又是真實的。它們是我想象中的真實。如果真實經歷是一棵樹,它們便是樹的影子。我的寫作更多的瞄準的是影子,在我看來,影子比樹本身更迷人,甚至,也更真實。”[1]的確,不管空間背景是鄉村、小鎮、城市,還是模糊的遠方,他都試圖在記憶與想象中構建關于它們的真實。《安娜的火車》腰封上這句話,可看作他的創作談:“我記得那些廣闊且沉寂的鄉村,混亂而蓬勃的小鎮,繁華也破敗的城市,陌生又熟悉的遠方;我也記得,在那些鄉村、小鎮、城市和遠方里,浮現又消失的面孔。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2]“我記得”,“我也記得”,一切關聯都源于記憶,記憶的海水深處,是龐大的感覺、情緒、經驗之冰山。它們“都與我有關”,這種相關,更多是作者的關切——對身邊事物、存在的深切關注。他的寫作,就是起于這些“與我有關”的物、事、人。在對這些息息相關之物傾注心神、筆力時,作者得以不斷構建外在世界與內心圖景的真實。
的確,真實是小說的生命之所在。當小說家遵循作品內在的情節邏輯和人物的性格邏輯,找到獨具個性的講述方式,其語言與內容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獨立自主的生命體,此時,小說是真實的。而真實在廣度、深度、厚度方面可作不同層級的區分,由此亦可辨別一部作品的藝術價值。甫躍輝的小說,雖不可單純以題材內容來劃分,但就“真實性”而言,他的作品在鄉土敘事和都市敘事兩個維度,卻明顯呈現出迥異的特質。
在黑暗中顯影:對鄉土世界的構建
鄉土敘事是甫躍輝寫作的一個核心,他一直圍繞這個核心經營自己的園地,多年來收獲的成果有《父親的手指》《紅馬》《雀躍》《初歲》《魚王》《鬼雀》《亂雪》《母親的旗幟》《滾石河》等。這類小說且不必細論其結構安排、人物形象塑造、人性挖掘等,寫作技藝對正在摸索“狐貍多知”[3]階段的甫躍輝來說,已達到實屬不易的程度。若要論成熟、完美,那是另一個需要交給時間來回答的問題。在此,只談他在鄉土敘事中所構建的“真實性”。
甫躍輝的鄉土敘事語言平實、故事樸素。他筆下的那些土地、景物、人,以及人物的話語、神情,都是鮮活的,敘述充滿了在場的實感,讀之如在眼前。他語言中的“有”之物,常能召喚出“無”的在場,氤氳出故鄉的氛圍。
這種在場、實感是有其深層來源的。一來作者具有云南邊地鄉村的生活記憶和家族背景,熟悉鄉土經驗。云南地理環境特殊,人們常年散居或聚集于山間平緩之地的村落,飽嘗山村生活之苦樂。即使是城市,也多基于群山環抱之中的一個個“壩子”經年累月慢慢發展起來,與大自然親密相依。自小生活于此的人,天然地保留著與宇宙天地渾然一體的整體感,他們成為作家后,作品里就自然地散發著一股活潑潑的生命氣息。這股生命氣息,在于堅、海男、雷平陽的詩歌和范穩等作家的小說中,是撲面而來的。這股生命氣息,在甫躍輝的小說中也揮之不去。他描繪的鄉土世界,充溢著來自民間、荒野的野性力量和神秘氣息,酣暢淋漓的生命元氣彌漫出蒼茫大地的混沌氣象。
二來作者身在異地,而對故鄉、童年常懷無限追憶。不管從地理空間看,還是從出生地與成長的意義上說,甫躍輝和當下的很多青年一樣,都是名副其實的流亡者。他從鄉村流亡到城市,從云南流亡到上海。如布羅茨基所述,“在促使一位流亡作家緊盯著過去的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追憶”,“追憶”會“使他不知不覺地受到稍感陌生的環境之觸動。有時,一片楓葉的形狀就足以使他感懷,而每棵樹上則有著成千上萬片的楓葉。……無論過去是愉快還是悲傷,它永遠是一塊安全的領地,這僅僅因為它已被體驗;人類復歸、回頭的能力非常之強,……這種復歸、回頭的能力簡直能使我們無視我們所面臨的現實。”[4]甫躍輝不斷追憶過去,追憶兒時的生活,成長的村莊,追憶村里的那棵香樟樹,那座小橋,那條河……“追憶”使他同逝去的歲月發生聯系。
懷著深深的追憶,甫躍輝在故鄉村莊與童年歲月中,構建起意味無窮的詩性言說空間。如頗具象征意味的《魚王》,外來者老刁承包了白水湖養魚,盡管他諳熟原住鄉民的生活習性與交往之道,但隨著鄉村文化形態中的原始性、自在性被打破,鄉民本性深處的排外、狹隘、盲目、跟風、貪婪、粗野統統被激發出來。矛盾、沖突終于演化出一場聲勢浩大的抓魚、搶魚事件,此時,“魚王”出現了。值得玩味的是,傳說中的魚王,只在孩子、老人、傻子的世界中存在。“魚王的傳說虛無縹緲,又實實在在,魚王無跡可尋,又無處不在。許多年后我們才知道,村里人年輕時無一不找尋過魚王,又都一一遭到挫敗。有一天,他們忽然明白,魚王是沒有的,他們便長成這個村子最最普通的一員了。可等他們輾轉一個大圈子,又漸漸地認為,魚王是有的,他們沒緣遇見罷了,那時他們已經是老人,快要離開這個村子了。”
魚王是什么?這個追問還得回到故鄉。云南各少數民族對神山神石、神樹神林、神泉神湖的敬畏,在世代生活中,與崇尚天人合一的漢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滲透,使得云南人至今還保留著敬畏自然,親近自然,尊重天地萬物,以及“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與共”的美好傳統,這傳統和人類童年的率性純真一起流淌在居民的血脈中。在云南,“人與宇宙萬物同處于大地上。人并不高于萬物。萬物各得其所。”[5]對甫躍輝來說,故鄉不只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飽含萬般生命情緒與體驗的生命場,自小浸潤在云南的多元文化中,使他對自然、神秘之物心懷敬畏。在這里,“魚王的傳說不知哪年開始的。父輩們小時候聽祖輩們說,我們小時候又聽父輩們說……”但隨著魚王被捕,魚王已死,“白水湖還是我們的,我們卻再也沒有魚王的故事講給那些很小的小孩聽了。”
海天離開時,帶走了魚王骨架上一根巨大的刺。甫躍輝離開云南時,也帶走了魚王骨架上一根巨大的刺。這根刺,流溢著云南大地粗獷、野蠻、原始的美。這根刺,能否承載他在現代都市中對鄉土世界的追憶、懷念?能否養護故鄉賦予他的生命元氣?這根刺,能否在他的文字中復活、生長為另一個“魚王”,喚醒讀者對自然、神秘之物的向往、敬畏?
記憶是一間漆黑的暗室,甫躍輝對鄉土世界的構建,就是在黑暗中,使故鄉的底片慢慢顯影。顯影歷歷在目、真實可觸,而追憶的視角,使其鄉土世界被懷舊的色調與氛圍深深籠罩。身在都市,卻執著于不斷地回頭、追憶,這回頭有著驚人的價值:“如果走運,它會聚集起強烈的感受,于是我們便真的可以得到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了。”[6]
在街拍中剪影:對都市異鄉人的透視
空間的改變帶來心靈的變化。鄉村生活與流動于山川、田野、河流之間的天地靈氣相貫通,身在都市,生活便捷、舒適,但世界的自然性、豐富性、差異性卻逐漸消失。現代化城市更改生命的存在方式,更改人們對世界、時空的感知系統。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原來星星點點稀疏坐落在大地上的小城,一夜之間變為龐然大物,轉頭吞噬四周的山川、河流、森林、田野。城市把人從自然之家中切割出來,將花草樹木小心培植在街道旁、公園里、陽臺上,將飛禽鳥獸豢養在動物園、鐵柵欄、鳥籠里。在鋼筋混凝土的人造世界中,城市景觀設計師總想保留一絲人類原始自然之家的氣息,但現代化科學技術能移植小橋流水的形、體、物,卻難以養護小橋流水的氣、神、魂;高樓大廈能滿足城市爆炸式增長人口的居住之需,卻未必給人以天井庭院那種天地人相通的自在、踏實。人們惶惶不可終日,莫名地焦慮、害怕。難怪當下的都市敘事中,常常流露出生命的茫然無措感、時空錯位感、身心分裂的疼痛感。
被窒息在密不透風的網中,談何營造生命的大氣象。甫躍輝也深陷在里面:“鄉村敘事中,我們還能看到天地萬物的影子。城市敘事中,坦然存在和恣意生長的天地萬物已讓位給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城市堅硬的現實長不出神話故事,也長不出鬼怪傳說。我自己也深陷在這現實里。”[7]深陷在現實里的甫躍輝,只能寄情、寄想象于動物園、猴子、巨象、老鼠、香樟樹……聊以慰藉無處安放的鄉愁、失落。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顧零洲們,大多從鄉村、小鎮而來,客居城市求學、求生。他們游離在異鄉,漂浮在都市,仿佛玻璃罩里的一粒塵埃,懸浮游蕩,無著無落,窒息而絕望。他們既難融入城市,故鄉也已回不去,一個個成了離土之樹、離水之魚,不得其所。在系統的高等教育中,顧零洲們獲得較為廣闊的人文視野,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別種別樣更加精致、奢華,更加富足、美好,更加自由、尊嚴的生活,但那種生活不屬于他們。他們是被故鄉放逐、被城市排斥的一代,內心充滿被擠在邊緣、排斥在外圍的無奈、焦慮、失落和隱秘的憤恨,以及對自己的卑微、渺小、碌碌無為、人生毫無意義的巨大恐懼。殘酷冰冷的現實、孤立無援的狀態、無足輕重的感覺……一起交織為難言的痛苦,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們,而他們又被自身的欲望重重包圍。向外,無力突圍,向內,難于據守。終于,不得不臣服于洶涌的欲望,成為傷害更弱小者的施害者。
中國正處于城市化、現代化的社會轉型中,作家面對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挖掘、處理社會現實提供的豐富素材,書寫這個時代。云南大學宋家宏教授在《重說文學創作的“思想性”》一文中指出:“急劇的轉型時期的生活為文學提供了空前的精彩與荒謬,數百年的人類歷史進程被壓縮成一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間轟然降臨于中國社會,它的豐富性、復雜性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這正是文學的用武之時,從社會現實狀態來看,正是出現偉大作品的時代。”[8]在這樣一個轉型期,無數個體都是這個時代的“顧零洲”,作者、筆者也都是其中的一員,小說人物的處境也正是我們自身的處境。顧零洲們將如何面對現代化、全球化對故鄉世界的摧毀?如何在警惕、審視、反省現代文明的同時,去發現、領會身處其中的城市之美?在現實困境中,這一代人是否能萌生出一種拯救自我的抵抗意識?在卑微、尷尬的境遇中,他們,也是我們,如何對現實社會的馴化、潛規則進行有效、有力的抵抗?……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的精神即復雜性。塑造人物是小說的核心問題,可惜在甫躍輝的都市敘事中,也許和作者自身的經驗、視角有關,這些人物大底單薄、空泛了些,他們是來自數碼相機的街拍剪影,聚焦是表面的,透視是淺層的。他們的卑微與渺小,孤獨與絕望,是作為局外人的旁觀所見,作者和人物內心雖有一些同感,但還是很隔離,所以小說敘述沒能很好地營造出人物活動那個“場”的氛圍,沒能發出人物靈魂深處的聲音,缺乏出自人物骨髓深處的切膚之痛。小說寫出了人物此時的狀態、困境,卻未寫出造成他們如此這般的復雜根源。到底是什么因素、際遇促使顧零洲成為現在這個樣子,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不得不臣服,不得不沉淪于欲望世界,難道僅僅因為他們出生在農村?小說寫出了人物的無奈、無助,卻還未寫出他們的命運。不過這倒并非作者無心于此,而是城市化進程中的這一代人,大都還年輕,他們的生活眼下是無望的,但依然充滿各種可能性。我們不知道,接下來他們將面臨什么,會做何選擇,他們的人生會發生什么變化。此時的一個個顧零洲,是繼續無力、無助地絕望下去,還是會出現另一種轉機?在充滿變數的生活中,什么力量會繼續強化或逐漸改變他們的性格,有沒有一種內在的心靈覺醒、精神支柱最終支撐他們走出生命的困境?
顧零洲應該是一個人物系列,而不是一種人物類型。他們是多樣的,復雜的,是充滿各種矛盾的。顧零洲們與其他一些作家,如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衛慧的《上海寶貝》、馬小淘的《毛坯夫妻》等塑造的人物,都是城市新人。對于這些人物未知的命運,讀者充滿好奇、期待。而甫躍輝與韓寒、張悅然、郭敬明、春樹、馬小淘等80后作家的家族背景、成長經歷都大不一樣,他具有書寫顧零洲的天然優勢,加之其不凡的文學才能、經典意識和寫作熱情,他筆下的顧零洲當會越來越立體、多樣,越來越豐富、飽滿。
兩相比較,“追憶”使甫躍輝的鄉土敘事真實可觸,那個遙遠鄉土世界里的人物、故事是從他的生命里流淌而出的,全出自他的內心,故而清晰、動人,但懷舊先天帶有理想化、純凈化的美顏、過濾功能。懷舊之鄉土與現實之鄉土的關聯、比照,是值得作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追憶”使他對城市文明保持警覺,同時也無法全身心融入城市,對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反而隔霧看花,故其都市敘事處于懸浮狀態,掙扎于都市邊緣的顧零洲們——這些具有時代特征和典型意義的人物新形象,顯得模糊、單薄,落不到實處,只約摸可見個影像。近年來,文學批評家關于鄉土資源與都市資源孰優孰劣的討論,一直甚為火熱。筆者以為,這不是鄉土與都市的問題,而是作者的生命、經驗、感受、體悟、思考和藝術的挖掘力、表現力能深入、拓展到何處的問題。切近的生活,與生命主體血肉相聯,若未經體驗、發酵,雖近,卻遠。記憶中的歲月,經過時間過濾,雖遠而更近,但在追憶、懷舊的光芒籠罩中卻容易失真,與現實脫節。所謂寫作,不管是數碼相機街拍的及時呈現,還是在黑暗中使生活的底片慢慢顯影,都需要作者敢于正視現實,敢于滲透自己的思考。
作為一位80后作家,甫躍輝有直面、關照社會的意識、勇氣,但他的筆墨間又常露出猶豫不決的神色,這透露出其內心的緊迫、焦慮,也呈現出技藝探索、打磨中的艱難。作家最可珍貴的,正是這種猶豫,這種對寫作的慎重。文學之存在,其意義不僅在于見證、描述一個時代外在的存在狀態,內在的人心世相,更高的意義還在于作品中蘊含的內省精神——那種基于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與意義對當下進行審視的內省精神,那種熱力——激發人向死而生、永不疲倦的生命熱力,那種力量——喚醒讀者、震撼其心靈的情感力量。不知甫躍輝能否確立起內在的主體性和真正的自我意識,能否打開視野、格局,回到現場,洞察社會與人生的差異性、復雜性,以文學的方式,有力地表達出這一代人對于自己生活于其中這個時代的思考、體驗和審視?筆者期待在他未來的小說中,感受到一個閃耀著內省精神、散發著生命熱望、充滿心靈力量的動人世界,那將是更高的存在之真實、藝術之真實。文匯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后記。
【注釋】
[1]甫躍輝:《時光若水,刻舟求劍》,見《刻舟記》,
[2]甫躍輝:《安娜的火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年10月版,腰封。
[3]甫躍輝引古希臘諺語“狐貍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表達自己的寫作狀態、路徑,見《刺猬,還是狐貍?》,《動物園》,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后記。
[4]【美】布羅茨基,劉文飛譯,《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或曰浮起的橡實》,《悲傷與理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29-30頁。
[5]于堅:《在漢語中思考詩》,《紅巖》,2010年第2期。
[6]【美】布羅茨基,劉文飛譯,《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或曰浮起的橡實》,《悲傷與理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30頁。
[7]甫躍輝:《魚王》,北京鐵葫蘆圖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12月版,序言。
[8]宋家宏:《重說文學創作的“思想性”》,《邊疆文學·文藝評論》,2015年第5期。
(作者系青年文藝評論家,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楊 林
青年批評家
主持人語:大先黝黑的臉上,永遠掛著笑容。那種感染人的、有甜味的笑。和大先在一起,無論是聊天,還是喝酒,總有他歡快的笑伴隨,也總被他的笑所感染。
可能愛笑的人,或者說活潑的人,文章也會受感染,大先的文章,無論是做電影研究、當代文學研究,還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都不呆板。理論文章讀起來,多少都會有生硬感,但大先的文章卻很潤,有暖暖的氣藏匿在文字間。
大先近年被批評界廣為稱道的是他一直行走在少數民族地區,潛心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提出許多有理論深度的見解。我曾和一位學界大佬聊天,他直言,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新的認知,都來自大先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提倡作家、藝術家要深入生活,卻很少說批評家要深入生活,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批評家面對文本就足夠了。這或許是我們當下的文學批評越走越窄的一個因素吧。以我之淺見,批評家中,目前只有大先,云南的冉隆中兩位才是真正深入生活的批評家。這是他們的批評文章有靈氣,接地氣的根之所在。
但正如批評家孟慶澍所言,從本質上說,大先是一個有情的、內心飽含詩意的批評家。(周明全)

劉大先(1978-),文學博士,生于安徽省六安市,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曾訪學及任教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雜志編輯部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已出版有作品《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文學的共和》《時光的木乃伊》、《無情世界的感情》《未眠書》《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合著)等六種,譯著有《陳查理傳奇:一個中國偵探在美國》,主編有《本土的張力:比較視野下的民族文學研究》等。兩部專著分別譯為日文和英文,多篇論文翻譯成哈薩克文、蒙古文、維吾爾文,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中國作協民族文學年度評論獎、全國青年作家批評家峰會“2013年度青年批評家”、第四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