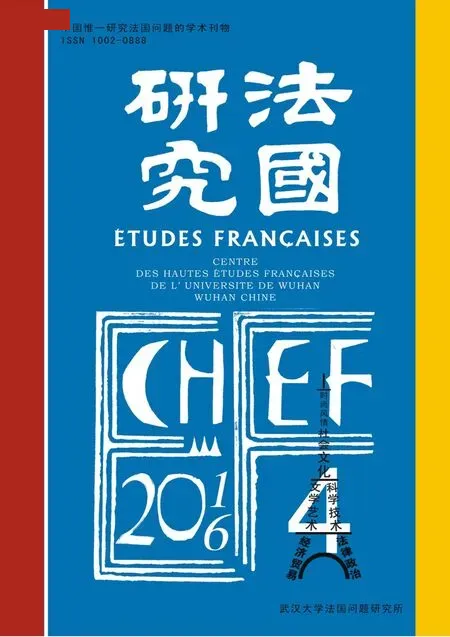亦步亦趨就是還原風格嗎?——羅新璋和郭宏安《紅與黑》第一章翻譯的比較
林維越 方麗平
?
亦步亦趨就是還原風格嗎?——羅新璋和郭宏安《紅與黑》第一章翻譯的比較
林維越 方麗平
本文以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第一章的中文翻譯為研究對象,選取羅新璋與郭宏安兩個譯本,比較二者在處理“存在多種理解可能性的內容”、“視聽表現”、“段落銜接”、“長句處理”、“抽象與具體轉換”幾個方面的異同。研究結果表明:翻譯處理方法的差異取決于譯者不同的翻譯觀,不同的翻譯觀導致不同的風格還原程度,而還原風格不應該局限于亦步亦趨。
《紅與黑》羅新璋 郭宏安 風格還原 翻譯觀
[Résumé]Ayant comparé deux traductions du premier chapitre dude Stendhal, nous trouvons que leurs différences se manifestent dans les aspects comme ? l’expression permettant aux multiples interprétations ?, ? la reproduction des effets audio-visuelles ?, ? l’articulation des paragraphes ?, ? le traitement des phrases longues ? ainsi que ? la transformation de l’abstrait au concret ?. Nous pensons que la divergence des méthodes de traduction résulte de l’écart des opinions sur la traduction, qui conduit aux différentes représentations du style de l’?uvre originale. Nous concluons que la représentation du style original ne peut pas être réalisée par la traduction à la manière du mot à mot.
引言
1990年代中期,《紅與黑》()的多種中譯本就像打擂臺一樣,幾乎同時出現在讀者面前,成為外國文學研究界和翻譯界的熱門話題。譯者們嘔心瀝血,對自己的譯文自然會頗為珍愛。但是,讀者作為譯本的接受主體,卻會毫不留情地批評譯本的質量高下。盡管大多數讀者既不能閱讀原文,也沒有受過文學欣賞的專業訓練,但他們的直覺判斷卻暗合了對“化境”的訴求。“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載錢鍾書:《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77頁。
在所有的《紅與黑》譯者之中,羅新璋與郭宏安都是享有盛譽的學者和譯者。因此,我們選擇了他們的譯本作為研究對象,以探討他們的翻譯藝術,進而探討翻譯的原則與策略。限于篇幅,我們的討論只觸及《紅與黑》上卷第一章的翻譯。[2]本文所比較的兩個中文譯本分別是2012年桂林漓江出版社羅新璋先生的譯本與2010年上海譯林出版社郭宏安先生的譯本。本文參照的法語原文版本為2000年巴黎Gallimard出版社 ? folio classique ?系列的Le Rouge et le Noir。一個譯本是否有個精彩的開頭,是決定讀者接受度的重要因素。這一章介紹了小說的發生場所Verrières小城,并引出重要人物de Rênal市長和Sorel老爹。作者筆觸清新自然,仿佛一位經歷豐富卻惜字如金的老人,難得坐下來給我們講述一個故事。其風格樸實而有力,聽故事的人并不覺得有什么生僻的字詞,可以愜意地跟隨他不疾不徐的節拍,從容地進入故事。
“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3]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載錢鍾書:《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78頁。譯者應該還原原文的風格,這是毋庸置疑的。風格是抽象而難以還原的,這是事實。另外,譯者的閱讀經歷與生活經歷不同,對同一種風格的感受和反饋也是不同的。一個中文基礎扎實,說話文雅的人,即使聽了一個語言平實的故事,也會自然地使用自己的語言,將故事再現出來。一個像大多數現代人一樣語文知識匱乏的人,能把一切表面樸素,實則用詞講究的故事說得索然無味,還爭辯說那風格本就是淡的。而對讀者來說,能夠聽到一個不走樣,像原文一樣不費解的故事,已是幸事。風格是抽象的,但風格還原的好壞,可以在具體的譯句中看到蛛絲馬跡。
本文將通過舉例對比,說明兩個譯本在貼合原文含義、視覺聽覺表現力、段落銜接、長句處理、抽象與具體轉換幾個方面的較大差異,而這些差異也決定譯文對原文風格的還原程度。
一、羅譯題詞更吻合章節的內容
《紅與黑》每個章節前都有簡短的題詞。盡管研究者們已經發現這些題詞大多是作者假借其他作家之名所做的個人創造,但它們對一章的內容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題詞翻譯的差異,也體現了譯者對原文內涵把握的差異。以下為第一章題詞:
Put thousands together
Less bad,
But the cage less gay
羅譯:置萬千生靈于一處,
把壞的揀出,
籠子里就不那么歡騰了?
郭譯:成千地,
把不那么壞的放在一起,
籠子里就不那么熱鬧了。
首先,英文原文本身就充滿多種理解可能性,“thousands”指什么?“less”是形容詞還是介詞?羅將“less”看作介詞,所以是“把壞的揀出”,郭將其看作形容詞,所以有“不那么壞的”。羅將原文中沒有出現的客體譯出來了,即“生靈”二字,郭則保留了原文的多義性與含混性。
題詞必定與章節甚至全書的內容有關。《紅與黑》寫的是復辟王朝的故事,批評了封建貴族專制,而第一章結尾提到小城的輿論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諷刺專橫輿論的愚頑。另外從文法上看,less bad與less gay形成對比,less應該都是形容詞。結合以上,我們的理解是:統治階級控制了人民的生活與言論,如此一來,他的統治就輕松了,對他來說壞處是少了(less bad),但這統治就像牢籠,統治者輕松的代價是被統治者的麻木與不自由,人民不快樂不幸福了(less gay)。這正是另一個譯本“千人共處,無惡,樊籠寡歡”所傳達的意思。郭的翻譯雖然保留了原文的多義性,但似乎與小說內容無關。羅的翻譯稍微具體了些,卻吻合章節內容。
二. 羅譯令讀者身臨其境
第一章正文開始是對小城風光的描寫,仿佛廣角鏡頭拍出的照片。司湯達(Stendhal)的語言簡潔,但畫面感十足:
La petite ville de Verrières peut passer pour l’une des plus jolies de la Franche-Comté. Ses maisons blanches avec leurs toits pointus de tuiles rouges, s’étendent sur la pente d’une colline, dont des touffes de vigoureux chataigniers marquent les moindres sinusites. Le Doubs coule à quelques centaines de pieds au-dessus de ses fortifications baties jadis par les Espagnols, et maintenant ruinées.
羅譯:弗朗什—孔泰地區,有不少城鎮,風光秀美,維璃葉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樓,聳著尖尖的紅瓦屋頂,疏疏密密,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壯的栗樹,恰好具體而微,斜坡的,杜河在舊城墻下,數百步外,源源流過。這堵城墻,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了。
郭譯:維里埃算得弗朗什-孔泰最漂亮的小城之一。一幢幢房子,白墻,紅瓦,尖頂,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壯的栗樹密密匝匝,了小山最細微的。城墻下數百步外,有杜河流過。這城墻早年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殘破不堪。
兩個翻譯都是成功的,語句通暢,都再現了原文的描畫。然而羅的翻譯更有畫面感,原文中由遠及近的鏡頭拉伸變化也表現得更突出。其中“星散”和“點出”兩詞用得尤其好。法文的“s’étendre”按照字典翻譯當然是“展布”,可是當法國讀者讀到此處時,并不會去想這個詞的具體詞義,因為詞語溶在句子中,句子溶在篇章中,成為完整的畫面。當我們遙望一座小城,那些彩色的屋頂不正像星星散落在夜空中嗎?對于中國讀者(讀者而不是所有中國人)來說,這樣的用詞并非許多批評家所說的“夸張”或“華美”,只是最平常的文學語言。郭的“展布”用得也好,但就畫面感來說稍顯不足,而“畫面感”是任何小說家都孜孜追求的。
相似的例子還有“點出斜坡的曲折蜿蜒”和“畫出了小山最細微的凹凸”。栗樹相對于山坡是小的,用“點出”一詞極妙,將“marquer”這一法文詞匯具體化了,符合中國人的語言習慣;而“曲折蜿蜒”正符合我們對不平直的山坡的印象,也是文學里極平常的語言。相比之下,用“凹凸”來形容山形比較少見,“畫出”竭力追求畫面感,但“小山”一詞本身不夠精確,此處講的是栗樹分布在山坡上,表現出山坡本身的崎嶇。可見要使譯文富有畫面感,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不因為某些突兀的用詞被迫跳出故事,需要譯者對篇章的總體把握。就像教師講課,并不是照著課本讀內容,而是事前先將書本內容消化成為自身的知識,再用自己的話講給學生聽。在這個講的過程中,教師本人的風格注入如果有利于學生把握整體內容,何樂而不為?郭先生強調還原原文的風格,但是讀者在閱讀原文時,并沒有感受到突兀的風格。當然羅先生的翻譯并非完美,比如“具體而微”這個成語錯用的嫌疑(具體而微指事物各個組成部分大體都有了,不過形狀和規模比較小,而非“具體而細微地”),“曲折蜿蜒”若簡化為“曲折”也許更能體現原作簡美的語言特色。
羅譯不僅令讀者在視覺上臨近,在聽覺上羅先生也頗為用心。比如原文第三段開頭部分:
à peine entre-t-on dans la ville que l’on estd’une machine bruyante et terrible en apparence.
對比之下,羅譯將聲音放在前,一進城,讀者還來不及從視覺上反應,就被盈耳而來的噪音震吵,之后,尋聲而去,才知道這聲音是一臺機器發出的。原文同樣強調聲音得“闖入感”,“on est étourdi par le fracas”。而郭譯卻將機器作為主要內容,聲音成了修飾語,好像旅人是先看到了機器,再聽見聲音,這與原文是不符的,也大大降低了原文的沖擊感。
羅譯的巧妙還體現在許多例子中,比如第三段將“fabriquer… de milliers de clous”譯為“沖出幾千個釘子”,第九段將“être frappé”譯為“劈面就會看到”都生動地還原了原文的精彩。
對原文視覺、聽覺甚至觸覺效果的還原對翻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讀小說的人必須首先進入情境,才能從文中各取所需。而要做到這點,譯者必定是爛熟文本卻不拘泥于文本。法文抽象,中文具體,翻譯得像字典解釋一樣“準確”,并不是讀者追求的“精彩”。羅先生對此有非常清楚地表述:“外譯中,非外譯外;文學翻譯,非文字翻譯;精確,非精彩之謂。”[4]羅新璋:《譯書識語》,載司湯達:《紅與黑》,羅新璋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436頁。“信從原文,不是教人拘泥原句,以外文律中文,作死譯文。”[5]羅新璋:《精彩未必不精確》,載司湯達,《紅與黑》,羅新璋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439頁。還原風格必須讓譯文“活”起來。
三. 羅譯的上下文連接更自然
第一章原文的描述連貫性非常強,先寫小城外觀,再進入小城,由進城處的機器引出主要人物市長先生,再由市長引出Sorel老爹,環環相扣,段落與段落間的銜接也自然合理。然而兩位譯者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有所不同,比如原文第四段的翻譯:
Pour peu que le voyageur s’arrête quelques instants dans, qui va en montant depuis la rive du Doubs jusque vers le sommet de la colline, il y a cent à parier contre un qu’il verra para?tre un grand homme à l’air affairé et important.
這一段是承接上一段的。讀者以旅人的身份進入故事,上一段他來到釘廠大街,這一段講的是在這條街上會看見de Rênal先生。原文“cette grande rue de Verrières”也表明讀者處在同一條街上,但郭譯的“維里埃有一條大街”卻將我們拉到另一條街上。這里的銜接不當會誤導讀者的思維,也反映出譯者對原文的不甚熟悉。
相似的問題還出現在原文第七段的翻譯上:

法語泛指人稱代詞on在中文里沒有對應詞,它的的具體所指要結合上下文判斷。上文寫旅人一路走到了市長先生的住所,這里羅先生將“on”理解為當地人非常恰當,因為當地人對當地的建筑了如指掌;再用“遇到”兩字與上文完美承接,將這個法語特有的詞翻譯成中國人可以接受的樣子。再看郭先生的翻譯,譯成“有人告訴他”,好像突然從旅人身邊冒出一個人跟他說話,讀者也許會反應不過來。
四. 羅譯對長句的處理使譯文更具可讀性
法文多長句,即多層次復合句,靠語法關系組合句子;中文多短句,即積累式分句,靠意思將分句連接成整體。譯者如何處理長句,將對法國人來說易于理解的長句譯成對中國人來說同樣易于理解的短句,反映譯者對原文的熟悉與掌握程度,而翻譯過程中是否句子不通則不罷休,時刻考慮讀者的接受,也體現譯者的工作態度。以下例子來自原文倒數第二段:
Pour arriver à la considération publique à Verrières, l’essentiel est de ne pas adopter, tout en batissant beaucoup de murs, quelque plan apporté d’Italie par ces ma?ons, qui au printemps traversent les gorges du Jura pour gagner Paris. Une tellevaudrait àune éternelle réputation de mauvaise tête, et il serait à jamais perdu auprès des gens sages et modérés qui distribuent la considération en Franche-Comté.
這一段由兩個長句子組成,充分體現法語分句多的特點。在這個例子中,兩位譯者的翻譯有明顯的差別。羅先生將原文斷為四小句,小句子中有停頓,不僅使句子有了羅先生所擅長制造的“韻律感”,也使通暢清晰。先介紹這幫新出場的泥水匠,再引出要獲得尊重和這伙人的關系。譯文不拘泥于原文的結構,卻將原文的邏輯關系理得非常清楚,這種清楚正是法國人讀原文時的清楚。反觀郭先生的翻譯,一方面將原本就長的句子譯得更長,全段只有一句話;另一方面,邏輯關系稍顯混亂。首先,在維里埃要造墻才能獲得敬重前文已經提過了,這里譯者好像忘記了,又重提一遍,而“要緊的是”跟前面的內容銜接也不好。另外,不要采用的是圖紙,將“每年春天經由汝拉山口去往巴黎的泥瓦匠帶來的意大利”作為定語,未免太長了;而泥匠以這種方式出現,也讓讀者納悶:“怎么突然來了幫泥匠?”也許郭先生為了重現原文的語言特點,有意保留句子結構,但卻帶來了法語中沒有的累贅和費解。在這一段中,譯者的差別還體現在對抽象名詞“innovation”的處理上。郭先生直接譯成了“革新”,用了意大利圖紙就是革新?未免太夸張了。其實法語中的“innovation”并不一定是“革新”“創新”這種抽象而強烈的意思,在生活里一個新的小想法也可以用“innovation”,只是法國人習慣了這種抽象的表達。但在中文里,則應該是羅先生的“新花樣”更符合原文的意思。相似的還有對“l’imprudent batisseur”的翻譯,中文中很少說“造墻者”,而結合原文,采用新花樣的其實就是“業主”。業主用了新花樣也不至于“魯莽”,“一時不慎”顯然更合乎邏輯。
五.“異國風情”不等于語句別扭
翻譯的目的是文化交流,我們不同意許淵沖先生將翻譯看作語言間競賽的觀點。然而“異國風情”體現在方方面面,包括新鮮的事物、別樣的價值觀、不同的生活方式等等,并不是指譯文的“別扭”。張成柱對此有清晰的表述:“翻譯腔就是‘洋腔’,而洋腔則是由譯者制造出來的,決不是什么‘洋味’(即民族特色)。‘洋味’包含在內容之中,而不是表現在文字符號之上。我們不能說用純粹中文譯出來的東西就失去了‘洋味’,同樣也不能說,似通非通、外文式的中文譯文就算是有‘洋味’”。[6]張成柱:《談羅新璋譯的〈紅與黑〉——兼談羅新璋的翻譯藝術》,載《中國翻譯》1996年第5期,28-31頁。
確實,如果譯文對于讀者來說沒有可讀性,不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讀者在感受真正的異國風情之前就拋棄譯本了。所以以“異國風情”、“洋味”為借口的“別扭”的閱讀感受是站不住腳的。以下例子摘自第一章原文最后一段:
Dans le fait, ces gens sages y exercent le plus ennuyeux; c’est à cause de ce vilain mot que le séjour des petites villes est insupportable, pour qui a vécu dans cette grande république qu’on appelle Paris.,! est aussi bête dans les petites villes de France, qu’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羅譯:事實上,這類聰明人言論霸道,令人生厭。大凡在巴黎這個號稱偉大的共和之都住慣的人,再到內地小城來棲身,就會覺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該到這個惡劣詞兒里去找。——無論在法蘭西的小城鎮,還是在美利堅合眾國,其愚頑都是一樣的。
郭譯:事實上,這些明智之士在當地施行著最討厭的專制;正是由于這個丑惡的字眼,對于那些在世稱偉大的共和國的巴黎生活過的人來說,小城市里的日子簡直不堪忍受。在法國的小城市和在美利堅合眾國是一樣地愚蠢。
這個例子中,我們要比較的是對“La tyrannie de l’opinion, et quelle opinion !”一句的翻譯。郭先生“輿論的專橫”可以說是亦步亦趨地翻譯了原文,是歐化的句子;但是對于習慣具體思維的中國人來說,必須將腦筋轉一個彎兒,才能理解;而羅先生所譯“專橫的輿論”則非常易懂,也并沒有更改原文的意思。另外,“輿論的專橫”后面緊跟的是“而且是怎樣一種輿論啊”,又突然將原本作為定語的輿論變成名詞,前后似乎有點矛盾,像是兩種思維在打架。羅先生的翻譯則沒有這個問題,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和諧。
結語
如果有一個詞能夠比喻風格,也許就是法國作家瑪格麗特? 杜拉斯所說的“音樂”:
大家都知道翻譯并不是文本字面上的準確,它或許恰恰需要離得遠一點,寧可說它循的是一種音樂的秩序,極度個性化的,如果需要還可以是異乎尋常的。
這要談起來是很難的,而有一點是我想做的,那就是嘗試著去說:“樂感上的錯誤才是最嚴重的。”
譯本總是由某個人的第一次閱讀開始的,這種閱讀和創作一樣富于個性,故而在任何情況下都抹不去譯者的痕跡。我們可否稱之為一種音樂的翻譯?我們只是做了音樂的詮釋而已。我們頗遺憾詞語的使用僅止于含義。一切就像是音樂被剝奪了意義,而不是文本。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難道沒有一種對文本的尊重,它反作用于文本的自由,它的呼吸,它的瘋狂?[7]瑪格麗特? 杜拉斯:《翻譯》,載瑪格麗特? 杜拉斯:《外面的世界二》,黃葒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43頁。
有人把造詣高超的翻譯比作原作的“投胎轉世”:“軀體換了一個,而精魂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翻譯出的東西。”[8]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載錢鍾書:《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77頁。我們通過上述一系列例子的比較,說明羅新璋和郭宏安二位先生譯本的差異。許多差異的產生也只是源自不同的翻譯觀點,然而這些差異還是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譯文對原文風格的還原效果。風格無處不在,卻不可將它僵化為語言的亦步亦趨。
(責任編輯:許可)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西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