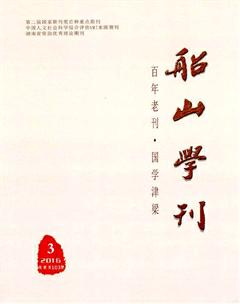論王船山以“公天下”為旨歸的價值理念與精神特質(zhì)
賴井洋
摘 要:王船山以“公天下”為旨歸的價值理念具有多方面的精神特質(zhì)。君子理想人格的追求與豪杰精神的挺立,“生民之生死,公也”的民本價值指向,“畛其族類”的民族振興情懷,以“古今之通義”升華的愛國主義精神等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xiàn)。這種精神特質(zhì)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普遍的道德原則性與引領(lǐng)作用。
關(guān)鍵詞:公天下;價值理念;精神特質(zhì)
王船山以“六經(jīng)責(zé)我開生面”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希橫渠之學(xué)”的志趣下,既賡續(xù)“天下為公”傳統(tǒng)思想又針對該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確立了以“公天下”為旨歸的價值理念。這種理念是船山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船山精神的重要特征,突顯出其以國家、民族、民本利益為最大公利的思想,從而展現(xiàn)出其“德功言”并建的核心價值觀和理想追求,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與個性特質(zhì)。
一、君子理想人格的確立與豪杰精神的挺立
“歷憂患而不窮,處生死而不亂”①的王船山,一生致力于追求“用天道”之“圣賢君子”的人格理想,強烈呼喚并挺立起“救人道于亂世”的豪杰精神。
1.“圣賢君子”的理想人格追求
王船山不僅贊賞圣賢君子,而且以圣賢君子為其理想人格。王船山指出:“君子無妄富,亦無妄貧;無妄貴,亦無妄賤;無妄生,亦無妄死;富貴而生,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貧賤而死,亦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以其貧,成天下之大義;以其賤,成天下之大仁;以其死,成天下之大勇。”②由此看來,王船山認為,圣賢君子具有無視貧富、無視貴賤、無視生死,用天道以成天下之大義、大仁、大勇之德性,這種德性實際上就是一種“公天下”“均天下”“平天下”的德性,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具有這種德性的圣賢君子就是王船山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而對于如何成就圣賢君子,王船山認為,君子德性的成就需要一個長期的道德修養(yǎng)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是志、情、意相統(tǒng)一的過程,即“君子之道,成身成
性以為功者也。”③
首先,王船山指出要成君子必須先成人,成人之道是身成與性成內(nèi)在統(tǒng)一.王船山分析說,“身”為“形色”,是“身色臭味之欲”,“性”為“德性”,是“仁義禮智之理”;“身成”就是用仁義禮智之理指導(dǎo)形色,使人之聲色臭味的欲望得到合理的滿足;而“性成”則是弘揚仁義禮智的德性,達到“昭然天理之不昧”的境界。他分析說:“蓋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則此與生俱有之理,未嘗或異;故仁義禮智之理,下愚所不能滅,而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俱可謂之為性。”④并進一步指出:“性者道之體,才者道之用,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湯、武身之也,即謂身而道在也。”⑤王船山認為,“身”與“性”是人固有的,“性”不能離開“身”。一個人只有在使身色臭味之“身”“順其道”,才可以“日以成性之善”,也才能像湯、武那樣成為圣人。其實,王船山的“成人之道”是儒家以高尚的道德君子為目標的“成人”思想的深入,是一個“成身”與“成性”的過程,是合理地滿足聲色臭味欲望與成就仁義禮智德性相互“為體”的過程,也是由此而實現(xiàn)道德的自我完善、達到理想人格的過程。所以他謂之為“君子精義研己而化其成心,所以為作圣之實功也。”⑥王船山認識到:人,就其一生而言,它不僅是一個自然生命成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人生價值的開拓、追求和實現(xiàn)的過程,是一個有意義的人生追求過程,是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tǒng)一過程。王船山的成人之道與人格理想追求是其“希橫渠之學(xué)”、對“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思想的體認與發(fā)揮,也是他所強調(diào)的異于理學(xué)家之“以身任天下”的精神特質(zhì)之一。
其次,為了追求與成就圣賢君子,王船山主張必須在修養(yǎng)上下功夫,修養(yǎng)的過程是“志”、“意”、“情”相統(tǒng)一以發(fā)揮道德主體的主宰作用過程。王船山認為,“欲修其身者為吾身之言、行、動立主宰之學(xué)”、“修身在正其心”⑦,就是要“以道義為心”、“以正心為主”,正心也就是正志,正志而后才能正意,否則“意之所發(fā),或善或惡,因一時之感動而成乎私。”⑧此為切實的“作圣之功”。因此,他指出:“《中庸》之言存養(yǎng)者,即《大學(xué)》之正心也;其言省察者,即《大學(xué)》之誠意也。《大學(xué)》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學(xué)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為主,而誠意為正心加慎之事。則必欲正其心,而后以誠意為務(wù);若心之未正,則更不足與言誠意。”⑨王船山認為“此存養(yǎng)之功,所以得居省察之先”,其“志正而后可治其意”所強調(diào)的是一種道德理性的作用。至于“情”,王船山認為:“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⑩王船山重“情”,在于他把情與性結(jié)合起來分析,“性情相需”、“性與發(fā)情,情以充性”。而“志”“意”“情”中,為重者當是“志”。他曾非常明確地指出:“身可辱,生可捐,國可亡,而志不可奪。”? “志”“意”“情”的統(tǒng)一是成就君子理想人格之必需。
可以說,王船山君子理想人格的確立充分展現(xiàn)了其“繼善”而志于天下、以身任天下的崇高理想追求。這不僅為后世樹立起一個追求“大義”“大仁”“大勇”及“以身任天下”、與天下人同苦樂的“圣賢君子”理想人格,而且指明了達到這個理想人格要求的“作圣之功”,從而使其的人生理想追求具有了時代的新意。
2.“救人道于亂世”的豪杰精神。
在確立理想人格的基礎(chǔ)上,王船山挺立起“救人道于亂世”的豪杰精神。王船山認為自古以來“未有圣賢不豪杰”,并指出:“能興即謂之豪杰。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興”是興正氣、興大義,即是“圣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賢,此救人道于亂世之大權(quán)也。”?由此可知,豪杰精神是一種圣賢精神,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是一種“救人道于亂世”的精神,它彰顯出“公天下”的圣賢氣象。
在明末清初時代,王船山為何要呼喚和挺立“救人道于亂世”的豪杰精神呢?因為王船山看到中國自古就有的豪杰精神到明代中葉時已式微,社會風(fēng)氣盡是“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于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shù)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而一般士大夫和讀書人的志趣,則是“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xué)快活過日。”?為此,王船山對庸人、俗人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們未能“承天盡己而匡天下”,以致大漢民族亡于滿清,“世道亂而人道失”。有感于此,王船山既繼承和發(fā)揮了儒家“匡濟天下”的精神,也肯認與贊揚了王陽明的“狂者”精神,以“公天下”為旨歸之價值理念為基礎(chǔ)挺立了“大公之理所凝”的豪杰精神。王船山所挺立的豪杰精神并非是“解衣推食”、“臨危一死報君恩”而盡忠殉死之私義,而是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力為其難”的勇氣與大義。因為“為其難,則欲愈淡而志愈篤,為其難,則氣愈剛而物愈無所待。”?為了國家民族利益,王船山結(jié)“匡社”、舉義兵,追隨明帝以抗擊滿清,充分體現(xiàn)了其勇當天下大義的豪情壯志。endprint
總之,王船山“救人道于亂世”的豪杰精神就是“生從道,死從義”、“為天下之大公”的道義精神,是一種成就圣賢的精神。這種精神“與灰俱寒,不滅其星星之火;與煙俱散,不蕩其馥馥之馨”?。雖是孤月之明,卻炳于長夜,光耀神州。
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民本價值指向
民本思想或民本意識自古有之,而在明末清初思想啟蒙時期的王船山,其以維護人的人格尊嚴為基點、以保護人的合理利益為目的的民本意識,則具有鮮明的時代與個性特質(zhì)。
首先,“天地之生人為貴”與“珍生”“載義”的統(tǒng)一觀。
王船山認為,在世間萬物中,人是“得天之最秀者也”,“天地之生人為貴”即說人是自然的最高等產(chǎn)物,人的生命也是最可寶貴的,因而要“珍生”。而“珍生”并非“畏死”,珍生的目的在于生命的存在能體現(xiàn)出道德的崇高,即能“載義”。由此,王船山指出說:“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珍生貴義是王船山所注重的,但是,在“生”與“義”、“生”與“死”之間,他重“生”,更重“義”,他認為生命不體現(xiàn)道德也就沒有其價值。然而,如果到了“生”和“義”二者不兼得的時候,他又主張舍生而存義,即要為堅持道德作出自我的犧牲。由于王船山珍重“生命”,所以他并不輕言“死”;即,倘若“義不當死,則慎以全身”,只有在“義不可生,則決于致命”?。可見,王船山主張在珍生與載義相統(tǒng)一的前提下使生命的尊嚴、生命價值得到體現(xiàn),這顯然是孟子所主張的當“生”與“義”兩者不可得兼時“舍生取義”思想的發(fā)展與提升。
其次,理欲合性,以理導(dǎo)性。
王船山的人性論是一種“理欲合性”自然主義的人性學(xué)說,這種學(xué)說基于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重視,從而為民利的保護提供了理論支撐。
王船山認為“欲”與“理”是人性中的兩大因素。他說:“蓋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則此與生俱有之理,未嘗或異;故仁義禮智之理,下愚所不能滅,而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而且“天以其陰陽五行之氣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為性。故有聲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義禮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聲色臭味,順其道則與仁義禮智不相悖害,合兩者而互為體也。”?由此,欲是人之生存與發(fā)展的自然需要,“有欲斯有理”,“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理則是協(xié)調(diào)個體關(guān)系之準則、規(guī)范,其作用在于保護群體之利益。當個體之欲與群體之利一致時,理與欲也是統(tǒng)一的。“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欲之或異”(21)。又說,“廓然萬物之公欲,而即為萬物之公理”(22)。不僅如此,王船山甚至把人對生存和發(fā)展的“渴望”之欲看成是人積極用世的動力之源。他說:“天下之公欲,即理也,人人之獨得,即公也。”(23)由“人欲”至“大公”,其前提是“人欲之各得”,即只有當個人合理利益得到滿足的時候,人欲才能轉(zhuǎn)化為公欲的實現(xiàn),也才能實現(xiàn)其“以身任天下”的宏愿。所以,他說:“吾懼夫薄于欲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24)由此可見,王船山的理欲觀是與其人性論思想一致的,也正是在承認理欲合性的基礎(chǔ)上,他主張“以理導(dǎo)性”來處理兩者的關(guān)系。這種對人欲尤其是人的合理欲望進行肯認的思想,不僅是對“存天理、滅人欲”的批判,更是對傳統(tǒng)人性思想的創(chuàng)化。
最后,“生民之生死,公也”的重民保民主張。
王船山以“依人建極”為基,從“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理欲合性論出發(fā),王船山提出了“生民之生死,公也”的重民保民主張。他說:“長民者,固以保民為道也,社稷輕而民為重。”(25)重民保民就是要珍重生民的權(quán)利、保護其合理之利益。
為此,王船山主張:第一,強調(diào)“自有其恒疇”,解決土地問題。王船山指出:“若土,則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yǎng)。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疇,不待王者之授之。”(26)這就是說土地是天地間本來就有的東西,農(nóng)民擁有土地是其維持生存的自然權(quán)利,這種權(quán)利不依賴“王者”,也不以“改姓受命”為轉(zhuǎn)移,而是要“有其力者治其地”。農(nóng)民擁有土地是其擁有財富、擁有利益的最大體現(xiàn)。由此,王船山明確地指出“王者雖為天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27)。即王者不能把土地據(jù)為自己之私有財產(chǎn)。第二,禁止兼并、減輕賦稅。對王者、豪強地主對土地的兼并、掠奪,王船山是堅決反對的,認為兼并、掠奪只會加重農(nóng)民的負擔(dān)。他說:“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搶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繁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向邇,吏胥之奸,不可致詰。”(28)由于賦稅制度的不合理和“吏胥之奸”致使土地兼并嚴重,從而也導(dǎo)致了“土滿而荒,人滿而餒”兩極分化現(xiàn)象。因此,在反對土地兼并的前提下,王夫之主張“輕其役,薄其賦,懲有司之貪,寬司農(nóng)之考”,使之“減賦而輕之,節(jié)役而逸之”。第三,王船山在闡述“土非王者之私”之后,對君民關(guān)系及君王之責(zé)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即“人君之當行仁義,自是體上天命我作君師之心,而盡君道以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當修之天職。”(29)即是“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思想的反映。實際上,在君與民之間,王船山主張以民為重,君主應(yīng)把關(guān)心民眾疾苦當作“第一天職”來履行,這也是“王道本乎人情”的要求,如果“君子不恤民之失其情,則情先睽絕于上”,最終導(dǎo)致“天下之情皆違”,因此,君王治政應(yīng)以民情為根本,違背天下之情實則是失天下之心,失民心者必將失去天下。王船山的“自有其恒疇”論和反對兼并的思想,既反映了他對農(nóng)民利益的同情和保護,又反映了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與控訴,凸顯出其民本思想的“均天下”個性。盡管王船山的保護民利思想帶有一定程度的“烏托邦”色彩,但確實是民主思想的萌芽與歷史的進步。
可見,王船山通過理欲合性立論,強調(diào)對人的價值與尊嚴的重視,從而主張對民利的保護,這種重民思想盡管源自傳統(tǒng)卻超越了傳統(tǒng)而具有了特殊的時代性。
三、“畛其族類”的民族振興情懷endprint
王船山的公天下價值理念在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表現(xiàn)就是一種“畛其族類”的民族振興情懷。
歷史上,因地域的不同、生產(chǎn)與文化發(fā)展的差異,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華夏”漢族把周邊少數(shù)民族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統(tǒng)稱為“四夷”,由此延伸出“華夏之國”與“四夷”的關(guān)系。“夷夏之辨”也就成了一個長遠關(guān)于民族關(guān)系的歷史問題。王船山的民族思想不僅突出了民族利益的至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時代新意。
他指出:“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xí)異,習(xí)異而所知所行篾不異焉。”(30)應(yīng)該說民族差別的存在是客觀的。但是,王船山在承認這種差別的同時,則主張民族之間的平等與和諧。因為“夷夏均是人”,所以各民族之間應(yīng)“各安其紀而不相瀆”。對于華夏,王船山主張“固其族類”,維護民族利益。歷史上管子曾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指出四維絕則國家就會由傾到危、由覆到滅。王船山則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其天、地、人的“三維”之論。他說:“人不自珍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珍以絕夷,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珍,人不能自珍以絕其覺,則人維裂矣。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31)王船山強調(diào)了以人為主體、以地域為界限所形成的文明與野蠻的區(qū)分,但是,其“三維”思想則體現(xiàn)了其要求華夏“畛其族類”、“自固其族類”的歷史深意。所以他指出:“圣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為之君長”(32),目的就是要“衛(wèi)其類”、“保其族”。同時,“固其族類”的思想,還表現(xiàn)了他的民族自信與自尊觀念。他說:“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yǎng)勵精、士佻栗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牟帶、仁育、義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33)所以,為了衛(wèi)其類、保其族,君王不能“以一人疑天下”,更不能“以天下私一人”,而必須“循天下之公”,“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此乃“古今之通義”,如果“族類之不能自固,又何仁義之云云”。他說:“保其類者為之長,衛(wèi)其群者為之邱,故圣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子,須于后圣,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34)由此可見,為了固其族類,王船山反對絕對君權(quán)的“私天下”,為了民族的生存和振興,他認為帝王之位也是“可禪、可繼、可革”的。
王船山對民族利益的重視與強調(diào)并非是對少數(shù)民族的歧視與偏見,而是針對少數(shù)民族貴族伺機離奸民族關(guān)系的警示及對專制主義的批判,其“夷夏均是人”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的民族平等觀。
四、以“古今之通義”挺立愛國主義精神
王船山以“公天下”價值理念為旨歸,以民族大義為“古今之通義”,挺立了剛毅的民族脊梁與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對“義”的層次區(qū)分,進而把“義”的內(nèi)涵提升至愛國主義的層面,是王船山思想中的一道亮光。王船山對“義”的分析是:認為義“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quán)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合則互千古、通天下、而協(xié)于一人之正,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35)。在這里,王船山把“義”區(qū)分為“一人之正義”、“一時之大義”和“古今之通義”三個層次。他把“一人之正義”和“一時之大義”歸屬為君臣之倫的行為要求,屬于“私”的范圍,而“古今之通義”則是“千古”、“天下”之義,是體現(xiàn)了國家、民族的“大公”之利。無疑,在封建社會里,強調(diào)忠君主、盡臣責(zé)的大倫之義是當然的,但是,它與國家、民族的“大公”之利相比,王船山強調(diào)的是“古今之通義”的大義,這種輕重區(qū)分卻是明顯的,并明確指出“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王船山毅然地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第一位,而把君臣之義置于第二位,并以歷史進化論為依據(jù),提出了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計,君王之位是“可禪、可繼、可革”的光輝思想。這就說明,王船山的的“古今之通義”論已超出了傳統(tǒng)的被視為天經(jīng)地義的忠君之倫理觀念了。
為了喚起和激勵保家衛(wèi)國的愛國主義精神,一方面王船山以極大的熱情褒揚了歷史上維護國家獨立而英勇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如:東晉桓溫維護民族統(tǒng)一是“伸天下之義”。公元347年,東晉明帝荊州刺史桓溫,“抗表”伐南燕,三次北伐為東晉收復(fù)部分失地,有人卻認為恒溫“篡政”,對此,王船山一反“惡其不臣”(36)之論,認為桓溫是“伸天下之義”,并嘆之曰:“嗚呼!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tǒng),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于戴異類以為中國主。”(37)而對東晉劉裕“抗表以伐南燕”、代晉稱帝,王船山認為他并未違背所謂的君臣之義,相反,確是符合“古今之通義”之為,因為他實現(xiàn)了百余年來東晉北伐的愿望。所以,王船山贊之曰:“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38)而另一方面,王船山對歷史上賣國求榮之人、之為則加以痛斥。如:對于漢朝騎都尉李陵降匈奴,王船山并不附和司馬遷之論,而指責(zé)李陵,“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zhàn),雖欲烷滌其污,而已緇之素,不可復(fù)白,大節(jié)喪,則余無可洗也。……其背逆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39)對于宋代的秦檜,王船山認為他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奸臣,罪不容誅;并指出宋高宗借贖母為名,向女真割地稱臣,是“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真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40)。并指責(zé)石敬塘將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是民族敗類。凡此,無不說明王船山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懷和熾熱的愛國熱情。他為使國家、民族不受外族侵掠,主張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必須樹立起自己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堅決維護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認為“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強也,智足自名也”,如果統(tǒng)治者不把國家變成“家天下”、“私天下”,而是勵精圖志,以“公天下”之價值理念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民族便“足以固其族而無憂”,國家便可“保延千祀”。王船山以厚重的“古今之通義”挺立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刻的價值意蘊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總之,王船山的思想既具有對宋明理學(xué)的總結(jié)性又具有對近代思想的開創(chuàng)性,其以“公天下”為旨歸的價值理念不僅推動了維新派的變革運動,同時成為開啟近代革命的精神力量。可以說,王船山以“公天下”為旨歸的價值理念是在對赤裸裸的利己主義以及對統(tǒng)治者“家天下”、“私天下”思想的批判與反思中得到萌發(fā)與確證的,它是“一種普遍的道德原則和絕對命令,又是一種同生民的生死及基本人權(quán)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核心價值理念”(41)。這種理念及其表現(xiàn)出的思想特質(zhì)正是拯救當下社會道德缺失的良藥,也是當下社會應(yīng)當繼承和光大的寶貴精神財富。
【 注 釋 】
①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114頁。
②⑩(24)王夫之:《船山全書》第3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74、353、374頁。
③④⑥⑧?????(23)(26)(31)(32)(33)(34)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61、128、161、189、479、479、139、128、121、191、551、501、500、501、519、503頁。
⑤?王夫之:《船山全書》第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52、363頁。
⑦⑨(21)(22)(29)王夫之:《船山全書》第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22、580、639、911、895頁。
???王夫之:《船山全書》第5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18、616、616頁。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11《顧季時行狀》.轉(zhuǎn)引自黃長義:《經(jīng)世實學(xué)與中國學(xué)術(shù)的近代轉(zhuǎn)型》,《江漢論壇》2005.12,第87頁。
(25)(27)(30)(35)(36)(37)(38)(39)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0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139、511、431、465、464、486、549、151頁。
(28)(40)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 第277、216頁。
(41)王澤應(yīng):《王夫之“古今之通義”的深刻內(nèi)涵與價值建構(gòu)》,《船山學(xué)刊》2015年第3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