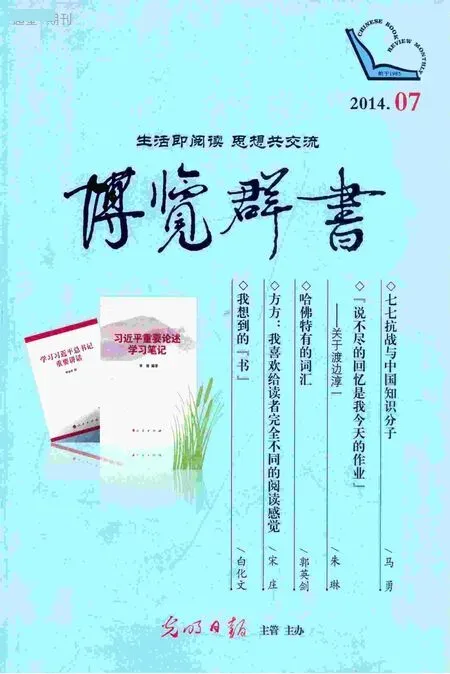上天留下我,就是讓我寫唐山
王家惠
一
1976年7月26日,當時我正在河北師院政教系學習,這一天為了配合中共黨史教學,集體組織在北京參觀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軍事博物館,整整一天,然后就是放暑假,各自回家。我訂的是當晚十點到唐山市的火車票,當時我的家在遵化,只是因為幾個唐山的同學約我去唐山玩兩天,一位男同學上學前當過工廠的采購員,和唐山市啤酒廠很熟,他說給弄一鐵桶散啤酒,夠我喝兩天的。一位女同學的父親當時任唐山市罐頭廠廠長,她說給我弄來些罐頭產品。當時副食緊張,買什么都要票,能夠吃到許多罐頭應該是一種殊遇。于是我就決定先去唐山玩兩天。晚上七點,我在北京叔叔家,正準備吃了飯上站,大院里傳呼電話來人叫我,說有我的電話。我去接,是一位遵化的司機,家在北京,他說他今天到北京拉貨,明天回遵化,奶奶讓他務必把我拉回去,不許回唐山,她想我了。我真不知道奶奶怎么會知道我要去唐山,怎么會知道此刻我在叔叔家。奶奶的命令不可違,于是我便騎上自行車到北京站,告訴同學們,我不能去唐山了。第二天坐上大貨車到了遵化,是下午兩三點鐘到的,和奶奶待了一會兒,晚飯后就去我原來的工作單位遵化農業機械廠看望老領導和工友們,很晚才回家。奶奶和母親先睡了,我等父親,父親12點以后才到家,沒吃飯,我又弄了幾個菜,陪他喝了點酒,將近兩點鐘才睡下。那天很熱,還沒睡著,地震就發生了。幸好遵化的地震不是很嚴重,房子沒倒,我們都跑了出來。父親母親穿起衣服就去了單位。我和奶奶則在院子里坐到天亮。天亮了,就聽說縣醫院來了大批地震傷員,我趕忙跑到縣醫院后門外的廣場上,那里的傷員已經躺滿了,醫務人員在露天忙著為他們洗傷換藥。我挨個尋找,沒有我的同學和親人。第二天,我放心不下,便和一位朋友一起搭了一輛去唐山抗震救災的貨車,去了唐山。我生在唐山,長在唐山,15歲離開唐山,唐山是我實際上的故鄉,那里有太多的人讓我掛念。下車之后,我簡直分不清東南西北,不知道身處何地,到處是廢墟,到處是死尸,到處是互救的人們。雖然事前聽說過唐山的慘狀,但我還是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心里是一片麻木,只是憑著直覺往前走,一直走到已經倒塌的大黃樓,才辨別出方向。由路北區走到路南區,道路越來越狹窄,兩邊是山坡似的廢墟,中間一條窄窄的道路,解放軍的軍車正往里開,極其緩慢,大量的受災群眾背著抱著傷員往車上擠,還時不時地有人喊:“解放軍同志,這里還有活的。”于是便會有一隊解放軍跑過去搶救。兩旁則是一個挨一個的尸體和傷員,我無路可走,只能踩著尸體和傷員的空隙往前走。那一種慘狀,簡直難以形容。這些東西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影視資料,據說當時河北省已經有了電視攝像機,而且派到了唐山,可是我多年后偶然遇見過當初扛機子的一位老同志,我問他當時的慘狀是否留有資料,他說沒有,當時有明確規定,不許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如果能留下來,至少可以提高人們對于地震災害的防范意識。
我要找的人一個也沒有找到,在建國路地道橋,我遇到一位舊日鄰居,他說你不用再去了,同院的人死了有一半,沒死的也都走了,他也是要到灤縣姥姥家待幾天。于是我便沒有到我的老院子去。我最擔心的還是我那幾個在北京剛剛分手的同學,雖然沒有找到他們的家,但是我想,他們也許都還活著,只是到了外地。直到開學到了學校,才知道幾個唐山的同學死了大半,那位答應給我弄酒的男同學死了,答應給我弄罐頭的女同學也死了。那位女同學是我們班的文藝委員,長得很漂亮,跳舞也很好,死訊傳來,全班一片唏噓。最讓人想不到的是,過了幾天,收到了北京頤和園攝影部給那位女同學寄來的照片,她穿著花裙子,倚在湖邊的欄桿上照的,日期是1976年7月26日。那一天幾乎全部是集體活動,自由活動的時間很短暫,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跑到頤和園照了這樣一張照片。那個時候女孩子不許穿花裙子,不帶花的裙子也不許穿,工農兵學員要保持工農兵本色,而工農兵不穿裙子。她在臨死前穿了一次花裙子,把最漂亮的容貌留給了人間。我拿著那一張照片半天沒有上課,躺在床上處于半昏迷狀態。那個時候我就想,生命為什么這樣脆弱,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脆弱的生命。如果沒有奶奶的一句話,我此刻怕是也和他們一起死了。此刻我們是否還在一起?我們是在天國還是在地獄?人是否有靈魂?如果有靈魂,是活著好還是死了好?如果沒有,活著又有什么意義?
從那以后,大地震就成為一個可怕的夢魘,揮之不去。我不敢想起它,可是它卻頑固地時時出現。但是讓我想不到的是,它居然決定了我以后的生命進程。
二
畢業后,我先是從事理論工作,不久轉行搞文學。1996年是唐山大地震20周年,唐山市政協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就組織作者采寫稿件,準備出版《唐山大地震百人親歷記》一書。我采寫了豐潤縣幾位老領導,集中寫了豐潤縣醫院在地震中如何救治唐山傷員的事跡。在唐山大地震中,豐潤縣醫院的全體醫護人員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苦苦堅持了三天,救治了不知道多少傷員。當時的藥品都用盡了,手術器械沒法消毒,就用鹽水煮一煮,輸血沒有血源,就把傷員的腹部積血抽出來再輸進血管,居然成活了幾例。非常的時期,常常創造非常的奇跡。這本書后來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1996年,唐山市民進又組織了一本書《唐山地震孤兒今日》,全書58篇文章,收入了我采寫的三篇。我采訪了五六位地震孤兒,毫不夸張地說,整個采訪過程我的眼睛時時浸滿淚水。
在唐山機車車輛工廠,幾位地震孤兒對我述說著他們的經歷。唐山地震過后,唐廠將二百多名地震孤兒接進廠里,成為正式工人。這是一些什么樣的工人啊,大的16歲,小的才9歲。廠里把他們安排進“五七學校”,他們開始讀書,也就是說,他們拿著全部工資和除夜班費之外的全部補助,免費讀書。不僅學雜費是全免的,就連衣服都是廠子統一給做。他們當中好些人由小學三年級讀到大學畢業,有的還到法國留學,人在法國,工資由廠里開。這樣的工人和這樣的學生,在全世界都是首例吧?
這些孩子大部分來自農村,又都父母雙亡,淘起氣來有些匪夷所思。他們在上課時就敢跑回宿舍打撲克,怕老師來找,把電線接在白鐵皮的門上。果然老師來叫上課了,一敲門就被電了一個跟斗。可是老師絲毫脾氣也沒有,依然隔著門和顏悅色地叫他們去上課。星期天,孩子們打籃球,老師們一人一個大鐵盆,一個搓板,坐在球場周圍,邊給孩子們洗衣服邊看著他們打籃球。放假了,孩子們要去探望親人,老師親手把車票、飯票、糧票用皮筋扎成小捆,放進他們的挎包,怕的是他們亂塞亂放找不著頭緒。他們開的工資,老師們一針一線地縫在他們衣服里面,怕的是半路丟了。親生父母能做的,他們都做了,唯一沒有做到的就是像親生父母那樣揚手打孩子一下,厲聲罵孩子幾句,因為廠領導給這些老師下了死命令:不許讓我們的孩子受一點委屈。
然而這還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這些老師大都經歷了地震,有的失去了孩子,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了妻子,有的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幾乎每一個家庭都破碎了,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有創傷,淌著血,發出陣陣疼痛。他們是把對死去親人的思念與愛都傾注到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身上,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平復孩子們心靈的創傷。
在一家藥店,一位已經做了副經理的地震孤兒對我講,他是開灤礦工的后代,在石家莊育紅學校長大,畢業后就到開灤上了班。他永遠忘不了上班之后第一個春節,那一天礦上沒有放假,他傍晚下班回來,簡易房顯得格外空曠,聽著窗外逐漸密集的鞭炮聲,他環顧四周,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個朋友,只有手里攥著的兩個燒餅和一袋海帶絲,這是他下班后買的,是他的年夜飯。此時,他實在難以抑制眼淚的奔涌。就在這個時候,有敲門聲,打開門,是住對門的大媽端著一碗剛出鍋的餃子,大媽說:“孩子,今兒是年三十,大娘沒別的,就給你煮一碗餃子吧。”他知道大娘的兒子工傷死了,兒媳改嫁走了,就他們老兩口拉扯著孫子過,日子也很艱難。看著那一碗餃子,他只有淚水噴涌,實在吃不下去。此時又有敲門聲,是礦工會的領導來了,拉著他來到礦工會,他一看,全體孤兒都到齊了,礦工會的全體干部也都沒有回家,他們和這些孤兒一起包餃子,一起過的年三十。從那以后,這成了慣例,每年的春節,都是礦工會的干部們和他們一起過,直到他結婚。
地震后的唐山人,用他們的大愛,筑起了世界上最雄偉最壯麗的新城。
后來,一家影視公司以這本書為素材,拍攝了一部電視連續劇《唐山孤兒》,播映后,攝制組全體成員回訪唐山,搞了一個儀式。在那個儀式上,我作為嘉賓接受主持人的采訪。我對他們講了以上的故事,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哭了,連飯店的服務員都哭了。講完后,影視公司的老板雙手掩面大哭著對我說:“王老師,謝謝您。我只想問您一句話,我能不能有幸接一個您的本子?”
1998年,我與關仁山一起接下了電視連續劇《唐山大地震》的創作。當時我們對于電視劇不是很熟悉,連提綱都做不好,光提綱就改了六稿,折騰了一年多。當時我們也有些氣餒,想撤退不干了。但是我想,如果這個題材唐山哥兒倆干不了跑了,讓外地人干出來,我們丟不起這個人,唐山也丟不起這個人。于是便硬著頭皮頂了下來,經過六年的反復修改,終于攝制成功,在南京和成都的衛視同時首播,幾集下來就創造了當地最高的收視率。后來的汶川地震當中,一位女士因為看過電視劇《唐山大地震》,地震發生時她運用電視劇中的地震自救方法,成功地保住了生命。我是在《文摘報》上看到這篇文章的,心中倍感欣慰。一部電視劇能夠挽救一個生命,值。
我們在這個本子的基礎上寫成長篇小說《唐山絕戀》,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書出來,唐山市新華書店搞了一個簽名售書儀式,在這個儀式上我說,也許這本書寫得有些沉重,但是面對24萬亡靈,我無法輕松。《唐山勞動日報》也約我寫了文章,我說,唐山大地震應該成為唐山作家的母題,就像二戰題材那樣,一代一代寫下去,也許最好的作品出自我們之后的作家。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我作為撰稿跟隨唐山電視臺的攝制組奔赴洛陽、沈陽等幾個城市,采訪那些地震當中參加過搶險救災的醫護人員。我不僅要擔當撰稿,還要作為主持人手持話筒采訪那些當事者。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一段段慘烈的回憶,使我的心情始終處于亢奮狀態。在沈陽一家醫院,采訪的人太多了,從上午一直干到中午12點還沒有結束。醫院送來盒飯,別人邊吃邊干,我卻不敢吃飯,怕吃了飯犯困,無法采訪,便一直餓著肚子挺著,一直干到下午三四點鐘才結束。
采訪結束,第二天就馬不停蹄地去了北京,參加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搞的一個紀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節目《震撼》。這個節目開篇就隆重推出了我們的長篇小說《唐山絕戀》,我作為作者,對于唐山地震幸存者的回憶一一點評。我在節目中說:唐山大地震是災難年代最后的災難,是新時代最初的曙光。
為什么這樣講?因為在大地震發生的年代,是一個人性、人情、愛情這些東西被漠視、被壓抑的時代,是一個階級斗爭的口號淹沒一切的時代,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當作敵人整治的時代。就是在那個時候,大地震發生了,唐山人在大片廢墟上面展開了慘烈的自救與互救,全中國的人民也伸出了救援之手,對唐山展開了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僅見的大救援。在這樣一場大救援中,我沒有聽說誰問過被救者的家庭出身與本人成分,人們把每一個唐山人當作一個單純的人來救治。我聽到過這樣的例子,在那些收治唐山傷員的外地醫院,嚴重對立的兩派在救治傷員的過程中捐棄前嫌,攜手赴難。這說明什么呢?說明了那種純粹的生命對生命的垂顧、人對人的關切,是確實存在的。當那樣一種真誠的、善良的、美麗的、純粹的人類之愛,在同一個瞬間,以爆發的形式,大面積地出現,一個充滿愛意的、和諧的、嶄新的時代的到來,還會很遠嗎?事實也確實如此,僅僅在唐山大地震發生三個月之后,中國歷史就發生了劃時代的巨變,中國人民走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絕不是一種偶然。
這個節目在當年的7月28日黃金時段播出。
后來,我又把這次即興的談話整理成文章,發表于2010年7月24日的天津《渤海早報》。
2010年,我與關仁山又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唐山大地震》,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小說出版后,在北京南鑼鼓巷一家書店里搞了一個新聞發布會,環境很幽雅,四面是書,每一個茶幾上都擺著我們的書,北京十幾家媒體派來記者參加,我們邊喝茶邊聊。那些年輕的記者提問極其敏銳,反復追問作為一個唐山人,我如何看待汶川人。我幾次都回避了這個問題,反復講唐山人的偉大,唐山人的情感之濃烈、高貴,唐山人在大地震中表現出來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說到動情之處,眼睛不免濕潤。散會之后,有一位中央美院的女研究生正利用假期在這家書店打工,她也眼睛濕潤著對我說:“我們這一代沒有您這一代的激情,您講得真好。”
這部長篇小說也被當年的浙江《長篇小說報》全文刊載。
作為一個唐山人,我親眼看到一座城市的毀滅與新生,親眼看到無數美麗的靈魂飄然而去,親眼看到無數掛滿傷痕的血肉之軀在大片廢墟之上挺立、搏斗。我無法不為這座城市感到驕傲,無法不為每一個唐山人感到驕傲。
前幾年,已經難以確定究竟是哪一年了,唐山南湖國際作家寫作營開營儀式上,來了幾位外國作家,其中一位這樣問我:“作為一個唐山作家,你怎樣看待眼前的新唐山?”我說:“作為一個唐山人,一個唐山作家,面對眼前的新唐山,我只有自豪,只有驕傲。因為新唐山恢復建設的資金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我們唐山人自己籌集的,每一個唐山人都參加了清理廢墟的義務勞動,我們是用雙手搬走了一座舊城市,建起了一座新城市。我無法不驕傲。”
三
2013年,唐山市召開首屆防震減災文化研討會,我向會議遞交了論文《信仰的力量——論毛澤東思想在唐山抗震救災中的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這可能是唯一一篇論述這個題目的文章。我在文中運用親歷親見親聞的大量事例,論述了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在唐山大地震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論述了當下信仰缺失的嚴重性和危險性,論述了重建信仰的可能性和操作路徑。理論是枯燥的,我這里只想舉出幾個我所親歷的例子。
我的家當時在遵化縣,地震中我家的房子沒倒,大家出來后,父親和母親穿好衣服就去了單位。當時父親是遵化縣委的主要領導,母親是縣針織廠的黨總支書記。父親到縣委之后,聽說了唐山的災情很重,便果斷下令全縣工業系統各個廠礦的干部職工緊急集合,開赴唐山地委機關、地委招待處等幾處重點目標搶險。母親也在工廠自己組織了一支搶險隊伍,開赴唐山某針織廠救援,那個廠和他們是長年的關系戶。剩下來的職工則在院子里搭起蘆棚,接待唐山傷員,每個人都當起了護理人員。
在整個抗震救災過程中,父親一直擔任遵化縣抗震救災工作的全面指揮,經手的抗震物資不計其數,母親的工廠也自有許多建筑材料可以利用,可是他們都不管家里,我家里竟然連一個像樣的帳篷都搭不起。當時我20歲,家里只有我和奶奶。白天還好辦,找個背陰的地方待著即可,晚上下雨,就不好辦了。幾個朋友幫助我在地上豎起四根木棍子,上面綁一張塑料薄膜,就算帳篷了。放進一張竹榻,讓奶奶搬進去,我們則圍著竹榻席地而坐,身子在帳篷里面,兩條腿卻露在外面被雨澆著。這樣還不能睡覺,要時不時地站起來把棚子頂上的積水捅出去,稍一耽擱,就會壓出一個鼓包,把頂棚壓破。這樣過了有兩三天的樣子,同院的一位大叔在縣供銷社工作,由單位借來一塊帆布,才搭起一張比較像樣的帳篷,兩家搬了進去。
當時我的哥哥在遷安大化工作,地震后他徒步走回家中,腳都走腫了。可是沒等他喝一口水,正好父親來家換衣服,見到他就怒了,問:“你回來干什么?”哥哥說不放心家里。父親說:“家里用不著你惦記,你馬上給我回去,去參加抗震救災,你這是逃兵,你知道嗎?”哥哥說找不到車。父親說:“你怎么走回來的,怎么走回去,現在就走。”幸虧我的奶奶說了話,說就是走,也得吃了飯再走啊。父親才沒再說話,換了衣服就匆匆走了。可是過了沒有一會兒,母親也回了家,見到哥哥也是一驚。哥哥對她哭,說他的戀人當時在唐山,也沒個人去看一看。母親當時也是大發其火,說:“唐山那么多階級弟兄都死了,你不哭,單為你的對象哭,你還有臉?你馬上回去,去單位參加抗震救災。”幸虧媽媽也是由家里拿了什么東西就匆匆走了。奶奶把哥哥留下來待了幾天。這幾天里哥哥始終躲著父母,他們回家的時候他就躲出去,不讓他們看見。
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如此,對待那些老同志的孩子則是另一種態度。父母自唐山解放就在唐山市工作,唐山市有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雙雙亡故,他們的孩子無處可去,就往我們家跑。有的吃一頓飯,換一件衣服,再去投親靠友。有的連親友都沒有,就在家里住下來,等唐山稍許安定了再返回唐山。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楚地震當中究竟有多少孩子來過我家,有多少人在我家吃過飯,睡過覺。反正是川流不息,接連不斷,把一個家搞成了接待站、公共食堂。還有幾位在遵化下鄉的北京知識青年,也都是老同志的孩子,他們無處可去,也都住到了我家,家里就每天人滿為患。沒有糧食吃,母親找了縣糧食局長批條子,買了好多打稻谷篩下來的碎米,那個東西可以不要糧票,屬于緊俏物資,需要走后門才能買到,我們就用那個東西弄飯吃。沒有菜吃,幾個下鄉青年就到城外的生產隊去買,弄了好些茄子西紅柿之類。后來我才想明白,那些嘎小子才不會花錢去買菜吃,肯定是到生產隊的菜園子里偷來的,后來他們也承認了確實是偷的。沒有衣服穿,母親就從廠子里買來一些碎布頭,把同院的幾位大嬸動員起來,把縫紉機搬到院子里為這些孩子軋背心褲衩。對于一些實在沒人管的孩子,父親母親是負責到底的,地震后安排工作,找對象,結婚,分家,都是他們來處理。這樣一種新型的人際關系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可是在今天,就很罕見了。
我在文章中說:“信仰的力量是強大的,尤其是在危難時刻,它的作用遠遠勝過所有物質的東西,這一點已經在唐山的抗震救災中得到很好的詮釋。一個人不能沒有信仰,一個民族更不能沒有信仰,信仰是文化的核心,沒有信仰的文化只是一具空殼,是沒有靈魂的文化。”
唐山人的最大特點就是敢于為了某種信仰犧牲一切,堅定不移。遠古時代的伯夷叔齊就為千百年來中華民族樹立了第一個堅守信仰的楷模。這種精神一直在唐山大地綿綿不絕。到了當代,唐山成為當代中國精神的最重要苗圃。李大釗的“鐵肩擔道義”的大釗精神,開灤工人“特別能戰斗”的開灤精神,遵化西鋪的“窮棒子精神”,沙石峪的“當代愚公精神”,都在當代中國的發展進程中發揮過無法替代的作用。唐山大地震發生,這許多精神匯聚成唐山抗震精神。這種精神成為唐山最重要的特色。
唐山又是一個有著大情大愛的情愛之城,大地震中無數感人事例,時時詮釋著這種人間摯愛,怎么寫也難以寫盡,怎么寫也難以寫全。
唐山因之成為文學創作的富礦,唐山大地震因之成為文學創作一個最具優勢的“母題”,唐山的作家應該一代一代地寫下去,也許能夠最深刻反映唐山大地震真貌的作品會出自那些根本沒有經過大地震的后代作家之手。就像蘇聯文學界寫二戰,直到第六代根本沒經過戰爭的作家出現,才寫出了《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那樣高度人性化的戰爭作品。
當年奶奶的一句話使我在大地震中逃生,我怎么想怎么像一種宿命,也許上天把我留下來,就是為了讓我寫這樣一場大地震,記錄這樣一場大地震。我的命運與大地震緊密聯系在一起,過去不能分,今后也不能分開了。
因此我說,唐山大地震深刻進我的每一道年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