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是否已到“拐點”
楊舸
中國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0%,相比發達國家動輒80%、90%的城鎮化率,中國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還遠未結束
近日,一組數據引發了輿論的關注。從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今年上半年陸續公布的常住人口數據來看,北京出現核心區人口減少,上海出現人口負增長,廣州出現人口增速階段性放緩。
比如,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15.27萬,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其中外來常住人口為981.65萬,減少了14.77萬。上海市流動人口的減少,引發了近年來上海的首次常住人口負增長。
而最近統計部門公布的一些數據,更引發了對人口流動的種種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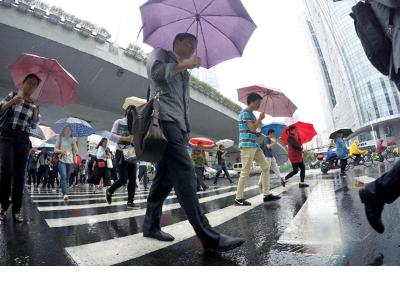
上海市流動人口的減少,引發了近年來上海的首次常往人口負增長
《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公報》顯示,全國人戶分離者2.94億,其中流動人口2.47億,比國家統計局在《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公布的數據減少近600萬。
如果數據準確的話,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出現流動人口減少的現象。
那么,從全國范圍來看,流動人口的“拐點”,真的到來了嗎?
中國的人口流動遠未結束
從全國數據來看,流動人口減少的結論有待商榷。
通常,數據的準確性需要從數據的內部一致性和外部一致性兩方面來評價。
嚴格來說,2015年與2014年的數據不能進行簡單對比。
數據變化趨勢應當具有連貫性。2010~2014年,流動人口年均增長高達800萬,而2015年突然出現負增長態勢,在沒有出現重大社會經濟事件、自然災害或政策調整的情況下,這一轉變是不成立的。
從數據的外部一致性來看,農民工規模、經濟增長率、工業產值增長率、城鎮化率、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等人口或經濟指標均不能支持流動人口減少的結論。
此外,國家統計局根據人口普查、經濟普查等大型普查數據對往年抽樣調查數據進行調整的情況屢見不鮮,因此不必著急下結論。
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流動人口規模減少或增速減緩,是地方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了“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基本思路。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地方政府面臨空前的人口疏解壓力,完成人口疏解任務的程度,已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工作考核指標。
為此,地方政府設置了人口調控指標,并主要以搬遷大型企業和批發市場、拆除違章建筑、清理群租房等方式疏解人口,政策效果也立竿見影。
不過,這些局部措施所帶來的影響,并不能真正反映總體的、內在的人口變化趨勢。
事實上,流動人口規模增速近年來確在放緩,但若論流動人口的拐點到來還為時過早。
2000~2005年、2005~2010年的流動人口年均增長率分別高達7.57%和8.49%。2010~2015年,流動人口年均增長率下降為2.21%,這主要是受人口形勢與經濟形勢的影響。但中國城鎮化率才剛剛超過50%,相比發達國家動輒80%、90%的城鎮化率,中國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還遠未結束。
越來越大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不是中國特有,人口的大都市化是世界潮流。
聯合國發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指出,超大城市(人口規模超過1000萬的城市)的規模和數量均顯著增加,超大城市的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全球已經有28個超大城市,數量比1990年翻了三番,超大城市居住了4.53億人口,占全球城市人口的12%。根據預測,到2030年,超大城市的數量將增長到41個。
人口向大都市集中是社會分工深度發展、人口城市化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人口、資本、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密集有利于產業分化,降低生產成本,促進技術創新,生產效率提高,這就是產業聚集的規模效應。而且,這種規模效應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方面,也同樣體現在居民生活、政府管理、社會化服務等方方面面。因此,人類不僅傾向于從農村遷往城市,也傾向于從小城市遷往大城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們追求規模經濟的行為促進了城市的形成、發展和壯大,規模越來越大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
但是,如果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很容易超出現有技術條件下的資源、環境容量,城市管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供給也會跟不上人口增長的步伐,從而導致交通擁擠、地價上升、環境污染等后果。這種情形下,人們又開始有回歸郊區來重新尋找生活質量的沖動,城市人口增速因此減緩,甚至出現人口郊區化。
隨著技術的革新、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管理方式的進步和住宅形態的變動,待城市空間秩序又建立起新的平衡,城市人口會再次穩定增長。
東京、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均經歷過人口發展如此循環往復的過程。
三大因素影響人口流動
影響人口流動的三大因素分別是人口變動、經濟發展和社會政策變革。當前的中國,這三大因素均面臨新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對人口流動產生怎樣的影響?
從人口因素來說,中國生育率已經下降,人口老齡化開始加速。改革開放初期的人口流動始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釋放,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減緩和農村新增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城鄉勞動力市場開始經歷“劉易斯拐點”,流動人口規模的增速隨之減緩。當前,中國人口政策正在經歷進一步調整和完善,生育率有回調的可能性,但這無法扭轉人口結構轉變的根本趨勢。
經濟因素將從三個方面影響人口流動的態勢。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將帶來重大影響;第二,產業結構的調整,特別是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有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有利于吸納勞動力就業和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第三,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出現端倪,國內制造業正在進行“雁陣”模式的轉移,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向中西部內陸地區移轉的趨勢,這將影響人口流動規模和方向。
國家對新型城鎮化建設和戶籍制度改革進行了頂層設計,陸續出臺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為實現這一目標,將采取兩個手段: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對大中城市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在傳統戶籍制度下,相關的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措施成了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壓抑了部分農民安居城市的意愿。未來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力度將可能顯著影響人口流動的意愿和流向。
人口流動新版圖
在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未來人口流動的新版圖將呈現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特大城市主動擴散,對周邊城市形成流動人口分流和輻射態勢。特大城市是社會財富和經濟能量高度集聚的場所,其所匯集和輻射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達到極大的規模,并由此產生相應的集聚效應或規模效益。一方面,特大城市不可避免地將面臨空間狹小、環境惡化等問題,在土地承載力和土地價格的制約下,一部分城市功能不得不向外圍地帶擴散,逐漸形成強勁的再分布態勢;另一方面,特大城市正在主動疏解人口、產業、功能等,這些將使得周邊城市或區域直接獲益。未來,特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將逐漸擴大到周邊城市或區域,形成更大范圍的都市圈流入中心。
二是三大城市群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依然強勁,并呈現進一步連綿化的趨勢。以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為中心的地區是流動人口的主要聚集地,這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國的四分之一,經濟總量占全國的四成,目前吸納了一半以上的總流動人口和八成的跨省流動人口。未來,這些地區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因此將繼續保持對流動人口的較強吸納能力。與此同時,山東半島、福建沿海和遼寧中南部地區的流動人口增長也十分迅速,未來將與原有的三大城市群連綿成片,并進一步強化成流動人口集中的沿海城市帶。
三是流動人口分布的“多元”格局初現,中西部城市群將成為新興人口流入中心。近年來,隨著長江經濟帶、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多個國家級城市群規劃的相繼出臺,中西部城市群成為全方位深化改革開放和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區域。數據顯示,以重慶、成都領銜的中西部城市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吸引流動人口的作用,2000~2010年,在城市流動人口規模排序中,重慶上升4位,成都上升13位,武漢、鄭州、西安、長沙、合肥等中部和內陸城市吸納的流動人口數量和比例大幅增長,排位顯著提升。未來,中西部城市群將崛起成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極,在產業集群發展和吸納人口集聚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得人才者得天下
隨著特大城市落戶政策的收緊和人口流動的普遍化,流動人口不再只是人們印象中的打工妹和建筑民工的形象,高收入、高文化水平、高技能的流動人口已經是流動人口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2010年,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到15.04%,比2000年增長了8個百分點,其中6.02%的流動人口擁有大學本科學歷,比2000年增長了6個百分點。
在全國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和戶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爭奪高端人才正成為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法寶。
到目前為止,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實施各自的積分落戶指標體系,其中教育背景、專業技術職稱、社保繳納年限等成為主要加分項,盡管指標各具導向、落戶難度不一,但主旨都是吸引城市亟需的高端人才。
在城市人才爭奪日趨激烈的情形下,資金補貼仍然不是取勝關鍵,留住人才還需要能發揮才智的平臺與機遇,城市需要有以知識經濟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透明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和現代化的舒適生活環境。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