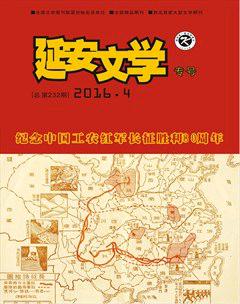回憶長征前后
1933年1月17日,我和博古一起離開上海。第二天,我們到汕頭住了一天,再坐火車到潮州,又坐船到三洋坎,然后坐小船到蘇區邊界,住在一個農民的家里。臨時中央從上海是分了三批走的,第一批是劉少奇,第二批是張聞天,我跟博古是最后走的。
到蘇區還不到十天,他們就搞了個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在瑞金開會,指責、批評羅明。反“羅明路線”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那時,我們很無知,跟著走,對那么大的事也沒有好好想想。總之,沒有像現在這樣清楚,什么是保衛蘇區。
在瑞金時,我住在總工會。那時根本不懂得軍事問題,所以也沒有聽到過什么反面意見。當時聽說,共產國際講毛主席的路線是右傾。但是我覺得,毛主席講話很有把握,而博古他們講的是“洋道理”。記得有一次在瑞金開會,葉劍英(當時是紅軍學校校長)、毛主席、任弼時都參加了。毛主席說這次戰爭要損失3000人,結果真是如此。長驅直入地打不容易。共產國際派來顧問,采取堡壘戰術。李德是1933年下半年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得中國的實情,又不懂得調查研究。當時,中國的實情是軍閥割據,不統一,為什么不能搞紅色根據地呢?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情況。
關于這個問題,周總理后來也講過,我們打不贏就插到敵人后方去,打運動戰。毛主席多次講過,不能拿主力去拼,應該打持久戰。那時我還不懂,去問過毛主席。后來在延安時毛主席寫了《論持久戰》,看后覺得有道理,明白多了。
長征一開始時是大搬家,這個我也有責任,因為我那時搞后勤。實際上哪能這樣做,應該先建立根據地。結果,一開始就搬家。當時,大家都說欠了總部一筆賬。因為李德他們瞎指揮,根據地圖來指揮行軍,說是走了280里,其實才走了四五十里,欠總部的賬了。他們不了解實際情況,腳不是鐵的。
那時,各軍團都有中央代表。8軍團的中央代表是劉少奇,9軍團是凱豐,我和劉伯承在5軍團。長征時紅5軍團打后衛,天天有戰斗,沒好好睡過覺。過湘江時,我和劉伯承在后面的13師,師長是陳伯鈞。14個師都過去了,但還有1個師沒能過湘江。葉劍英當過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記得過烏江時,他講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江。
黎平會議我沒有參加,當時我到3軍團彭德懷那里去了。我到洪州司時,博古約我和劉帥談話,告訴我們要改變方向走。當時不知道他們開會沒有。本來長征的目的是與2、6軍團會師,但后來發現不行,毛主席就建議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
長征路上,毛主席給王稼祥、張聞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說服了,再說服張聞天。是張聞天把這件事告訴我的。
紅軍在遵義停留了一個多禮拜。總結決議上寫的是1月8號,實際上部隊不可能一到就開會,記得是幾天后開的。遵義會議開了約5個下午和晚上是可能的①。
參加遵義會議的這些人員名單差不多。我當時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是委員長。說凱豐任宣傳部長不準確,他當時是青年團中央書記,到延安以后才是宣傳部長。那時宣傳部長是陸定一。李富春是否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我不能證實,但他當時任總政治部代主任是對的。林彪、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參加了會議,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董振堂、李卓然我接觸的時間短,印象就少些。9軍團是羅炳輝,記得沒有參加。我估計此外沒有其他人參加了。那時開會好像沒有人記錄,中央開會是不搞記錄的。
會上,博古作了報告,周總理作了報告,李德也講了話。會議討論的內容主要是軍事問題。只記得當時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里講到的那些。毛主席說:“路是要用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博古在會上說:“要考慮考慮。”毛主席說:“我贊成你考慮。但你要考慮的不是繼續留下,而是把職務交出來。”會上大家都發了言,一致擁護毛主席。
遵義會議后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總書記我記不清。
遵義會議后,我和張聞天一起去了3軍團彭德懷那里。在遵義時還成立了警備司令部,劉伯承是司令員,我是政治委員。司令部也是駐在一個公館里。遵義會議后我在總部,好像劉伯承也在總部了。在遵義天主堂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事,我不知道。各軍團設在市內,都是回去傳達的。但是,我記得會后開了一次群眾大會,毛主席、朱總司令講了話。我參加了這次會,具體講什么記不得了。
遵義會議后,成立了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有毛主席、周總理、王稼祥。中革軍委主席還是朱德。軍委總部下設的機構,羅舜初他們清楚。那時,一局局長是彭雪楓;后勤部長是楊至成,政委葉季壯。
遵義會議后,打仗就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非常靈活。過金沙江時,劉伯承是渡河指揮部司令,我也在那里。我們管6條船,保證不出毛病。渡河期間,劉伯承和周總理、毛主席在江對岸(四川)的石洞里指揮,我在江這邊(云南)負責指揮。渡江是非常困難的,船一過去很快又被沖回來,一定要有熟悉水性的船工撐船。我和劉伯承是大部隊過完江后最后走的。我們走后,敵人飛機還來轟炸過。
隊伍經過四川會理后,劉伯承跟少數民族首領歃血結盟。過瀘定橋時,劉伯承和聶榮臻在一起。
過瀘定橋后,中央開了會,決定要我去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因為那時白區的黨組織已經被破壞了。我離開時,劉伯承給我開了兩張證明,要我到他老家四川的弟弟那里去。在長征途中被派往白區的,還有潘漢年、嚴達人(真名叫嚴樸)、夏采曦②。劉少奇是長征到陜北后才到白區去的。我是1935年七八月間到上海的,當時先去找商務印書館的老朋友,后來是章乃器的弟弟把我接去住了一個多月。大家到上海后都覺得上海不能呆,正好共產國際派人來上海,就召集蘇區來的人一起到莫斯科。那時,王明、康生都在莫斯科。我們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結束,少共“六大”還在開。
另外,長征期間,我們對敵人的電臺密碼是能夠譯出來的。現四機部的王諍,懂得敵人的密碼,在當時起了很大的作用。還有劉英也懂。上海也訓練了一批人,是李強他們訓練的。王志剛就是在上海學習后送到張國燾那里去的。
注釋:①后經黨史學界考證,遵義會議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共三天時間。
②嚴樸(1898—1949),又名嚴達人,江蘇無錫人,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副部長。遵義會議后,被派赴重慶、宜昌組織交通站,后又被派赴蘇聯學習。
夏采曦(1906—1939),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長等職。長征途中奉命留在川貴交界的江門一帶堅持斗爭,后被派赴蘇聯學習。
(本文是陳云同志和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的談話。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原載《陳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