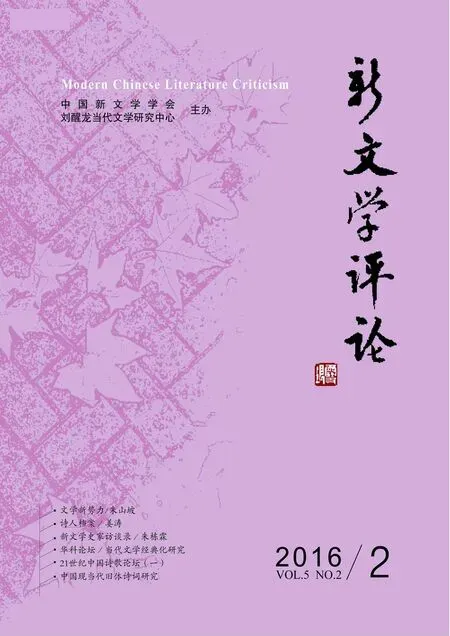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大儒陳詩》:古代知識分子的另一條巨流
◆ 湯天勇
?
《大儒陳詩》:古代知識分子的另一條巨流
◆ 湯天勇
客觀而言,《大儒陳詩》作為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并未深入到深廣的歷史時空,也未給亂世返本開新,其撰述的不過是主人公陳詩的成長史、生活史與功業史。小說封底如是說:“本書……重點描寫封建時代科舉制度之嚴酷,官場之險惡,世態之炎涼,勵志之艱辛。宣揚劉墉、錢灃、朱珪等名臣之正義,揭露和珅、劉國泰、蘇凌阿等貪腐者之奸兇,直言畢沅、章學誠等仕賢者之無奈。落幕之處,社會和人性回到它的起點。”誠然這些元素小說有所涉獵,卻非主道,頗有廣告的嫌疑,吸引讀者眼球的同時也誤解了小說寫作祈向。
《大儒陳詩》是否為一部好的長篇歷史小說,除了做文本符號學式解讀外,尤須將其放置于歷史小說的集合中,在參照對話中予以甄識考量。中國人素來對“史”較為看重和依賴,這也導致了歷史小說創作的經久不衰與閱讀興奮點居高不下。經由研究者總結,歷史小說的寫作模式有三種:一種可稱之為“以政治為中心意識的歷史敘事”。 在這類作品中,強烈的時代政治意識(或準政治意識)成了作家結構文本、塑造形象、傳達思想主旨的核心。第二種可稱之為“新歷史小說派”,這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隨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化與文學的輸入而蔚然成群的歷史小說“異類”。 原來政治性和道德倫理為主導內涵的意識形態被淡化及至消解,用泛化的歷史情境來虛構情節、宣泄自我對俗世及存在之意義的理解。第三種歷史敘事模式,即“文化歷史小說”, 從幾個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和這些人物所處的歷史時段入手,深入展示對傳統中國朝代興衰、文化基因、心理結構的穿透和自審①。三種模式的敘事視域,可以概括為政治、世俗與文化,尤其是文化熱興起與向傳統深處開掘的寫作向度,文化歷史小說備受到批評界與讀者的青睞。即便如此,諸多歷史小說始終逃脫不了一個基本敘事范疇:王朝的興盛更替,英雄人物的風云際會以及士人修齊治平的理想抱負。
巴爾扎克論及歷史小說創作時認為:“屬于這類小說的好作品,需要許多條件。首先,需要大力鉆研與工作,他必須有藏書家細讀一本大書的耐心,而得到的卻占只有一件事或者一句話。其次,必須有一種特殊的才能,能根據一大批書的零星材料,創造出來一個已經不存在了的時代的全貌。”②從寫作者的基本素養來看,甘才志完全具備。他在2012年受托后,查閱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身體力行地進行調研,盡可能占有寫作材料,《自序》中說為了考證陳詩故居遺址,訪老人,尋舊痕,足見其認真嚴謹。我們的歷史記述,無論是計時序列,還是紀事序列,從形式上看都是斷裂的,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被折斷。另外,對于人物,微言大義,一字褒貶,善惡雖未浮上地表,卻也隱而顯,直指意義評判。主人公陳詩在乾隆十二年到道光六年這八十年的歷史時域中,生活與事業的時空背景,呈現不假不虛,不走樣不離譜,由是觀之,作者的確“創造出來一個已經不存在了的時代的全貌”。 “陳詩是清代乾隆朝進士,因著《湖北舊聞錄》、《四書類考》被兩任湖廣總督尊稱為‘國士’、‘楚之大儒’,因主修《湖北通志》而被史界贊譽為‘湖北方志第一人’。”③但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陳詩是陌生的,并且他與風云詭譎、刀光劍影、沙場爭斗、宮廷秘聞相去甚遠,作者將這樣一個“知名度”不高、傳奇性不夠、花邊新聞不多的古代士人寫得形豐神聚,足見其寫作實力與駕馭能力。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儒陳詩》是一部較為成功的長篇歷史小說。
為何放棄傳記撰述,取之為歷史小說創作,作者已做說明,源于“資料不足很難開展”。用小說的方式講述歷史,歷史成為小說的題材;人們閱讀小說,以史鑒今,歷史成為具有鏡像作用的意象與符號。由此,歷史小說對于作家的考驗就在于史與詩的關系如何處理,也就是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問題。金豐在《說岳全傳·序》中說:“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于虛,而亦不必盡由于實。茍事事皆虛,則過于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實,則失于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甘才志在有限的“事事考之正史”情況下,更多是想象力的發揮,歷史是背景因素,是一個時代氛圍的整體性著色。巴爾扎克說:“光有對一個時代的這種一般看法,還是不夠的,因為這一切屬于歷史范圍,作者于此之外,還得添上小說家的才具、強大的創造力、細節的精確性、對感情的深刻體會等等。”④陳詩所能見諸史冊典籍的言論、書籍、地域風貌、性格特征、人生經歷,只能是小說家層層鋪排的內核。基于此,甘才志將陳詩一生風云歷程予以完整呈現,以時間為經,以空間為維,將陳詩的出生、求學、趕考、做官、辭官、婚娶、交際、教習與著述,始終貫通,脈絡清晰,詳略分明。作者的藝術想象,是在不失本相下的神游萬里,做到了合情合理。一是對于真實的歷史人物,符合歷史記載,藝術化但未無端戲說,比如小說中的朱珪、劉墉、和珅等,忠臣也好,奸佞也罷,符合歷史原貌。二是歷史情景、場面等,這是才情蓬發的地方,就如借助《清明上河圖》我們可以揣想臆測到宋朝的城市生活,陳詩逝世已逾180載,在沒有影像的前提下,作者只能充分發揮想象,近乎真實地再現了兩百年前檀林河岸、漢江與長江流域的風土人情。歷史不是抽象的概括,冷冰的詞句,而是日常生活的匯聚,是有溫度的,是動與靜的集合。甘才志將凝固的歷史,還原成真實的人生存在,其中有著活鮮的生命運動。
對于古代讀書人而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他們的人生信條和用世原則。布爾迪厄認為,知識分子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就在于統治者和尋常百姓之間,相對于西方知識分子更多強調與秩序或統治階層有意識的對立與獨立,中國古代知識層唯有依附與更隨,竭力入觳,“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⑤,尤其是鄉村讀書人,科舉入仕甚至是唯一光宗耀祖的手段。范進中舉,我們在批評封建科舉殘害人性的同時,也需對古代讀書人報以“理解的同情”,政治入仕為單向性選擇。倘若不能進入統治者的觳中,“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些追求皆是虛妄的白日夢。擁有知識,“業成早赴春闈約,要使嘉名海內聞”,方才有了進入統治階級的機會。陳詩伊始,如同大多數古代讀書人一樣,以求取功名為主要目標,在母親、外公、娘舅、岳父母等人支持下,砥礪前行,一路順利,金榜題名。金鑾殿以疏應策,慷慨激昂,胸納乾坤,書中寫道:“陳詩與眾多學子離席而出,胸中依然澎湃不已。取何名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卷若能當疏呈于天子,或被列為前十卷請皇上閱看,皇上也許會龍顏大悅,號令全國大治江河,大興水利,這該是一件多么有益于蒼生之妙計啊!”⑥本以為憂國憂民之心志得以如愿以償,殊不知策論縱橫捭闔之中含有乾隆皇帝生厭的內容,幸得阿蘭侍郎等人惜才,從中斡旋,陳詩方才得保全身,高中進士;若是遇到別有用心者,在文字獄興盛之時,陳詩連身家性命都堪憂,遑論進士及第。那時的陳詩,依然對皇帝頂禮膜拜,他所聽聞的,也多是圣主之說。后來蒙阿蘭侍郎的賞識與舉薦,陳詩被安排到為人正直、為官清廉的劉墉主政的工部,“履額外主事,視事三月,秩從六品”。原指望當個廉臣的陳詩,卻因為不懂官場游戲規則,不被直接上司重用。后陰差陽錯,內務府才華初顯,意外受到和珅賞識,欲囊括為棋子,薦舉上書房行走,課教皇子。皇子擾亂課業,后宮嬪妃明爭暗斗,稍有不慎,就有殺頭危險,謹小慎微的陳詩戰戰兢兢,以往的躊躇滿志復歸于平靜,又聽聞先前頗有好感的和珅實則累累罪惡,便逃離后宮這個是非之地。追隨劉墉查辦劉國泰等一干貪官污吏,雖是信心滿滿,最終也是空手而歸。此時的陳詩終于清醒過來,曾經的壯志凌云幻化為泡影,致仕歸鄉,孝敬娘親。歸鄉之舉,也曾惹來冷嘲熱諷、流言蜚語,陳詩不為所動,娶妻生子,恬靜過活。徹底醒悟后的陳詩,德業與事功正式揚帆,駐蘄州,留襄陽,居荊州,移武昌,教習學業,著書立說。業績斐然、功成名就后,返回蘄州,隱居大桴山,直至終老。
相較于其他文化歷史小說的主人公而言,陳詩的一生缺少跌宕起伏,有些波瀾不驚,缺少風花雪月,有些迂闊呆板,但正是這樣一個看似有些平淡的人物,卻樹立了古代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存在。在認識到與官場政治有些隔膜不合拍的時候,能夠急流勇退,在人生迷茫的時候,專心教習學生,傳道授業解惑,事功立言,成一家之說。從讀者的角度來看,看慣了爭權奪利、蠅營狗茍;看慣了殺戮戡亂、生靈涂炭;看慣了依紅偎綠、紅顏隕落,陳詩的塑造,是一份難得的干凈,難得的純粹。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嶄新的藝術創造,一個儒道互補、拘泥與灑脫雙具知識分子形象。
陳詩致仕后有兩次入仕的心動,一次是被云素和尚所勸,欲上武昌謀職,一次是為高為濟、畢沅所薦,有任赴襄陽學政之意,結果都失敗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在以政治為核心的價值體系中,“內圣”的目的是“外王”,飽受儒學浸潤的陳詩有些搖擺不定,人之常情。政治價值追求無望,經濟價值追求不屑,沉湎于天倫之樂又有些不甘,此時的陳詩,內心空虛無著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躑躅,尤其是自己空有一肚子學問不知售與誰?才有用則見,才無用則隱,陳詩萌生了出家的念頭。后在道人點化之下,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人生自此啟程。山中遇樵、仙人啟悟是否真有其事?或許有,或許無,這都無關緊要,別林斯基就說作家可以“違反歷史”,不一定要“忠于歷史的真實,卻極度忠實于人類的靈魂、人類心靈的永久的真實,忠實于詩情的真實”⑦。重要的是,作者以這些有些虛化的情節,讓讀者明白了陳詩何以找到人生真正的價值追求的。陳詩未糾葛于政治漩渦之中,于其本身,何其幸也,于荊楚教育、文化何其幸也!
歷史和小說的區別,既在于敘事上存在真實與虛構,也在于 “主題結構”與“情節結構”的各自凝聚。歷史往往通過事件序列呈示意義,歷史小說以人物作為舞臺核心。甘才志以特有的歷史敏感和較為豐富的小說寫作經驗,著力刻畫了那一時代的世情人生,人物的性格、心境、風貌較為圓滿地得到呈現。比如和珅“鱷魚的眼淚”,竟讓初入廟堂的陳詩頗為感動;章學誠的狂狷一展無遺,卻是真人至誠之人;云素和尚“六根未凈”,穿梭于紅塵內外,都給讀者以鮮明深刻的印象。當然,小說既然以陳詩為主人公,他塑造的成功與否,是可以作為衡量小說質量的重要標準之一。陳詩的成功在于其是個豐富圓滿的形象個體,在“楚之大儒”、“國士”的光環下,尚且有著俗世之心,有著矛盾、糾結之時;可以沖冠一怒,也可以唯唯諾諾;有時頑固執拗,有時圓潤赤誠。金榜題名,這是多少讀書人畢生追求,陳詩寒窗苦讀,欣喜若狂,春風得意自不待言,也符合其時人的心境。又為何辭官?在筆者看來,原因如下:一是自小失怙,母親含辛茹苦實屬不易,為人子當盡孝親;二是年齡已屆不惑,尚未完婚,“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家庭倫理的無形逼迫,尚有岳父一家恩情尚未報答;三是官場政治,權謀利益紛爭,傷人于無形,殺人于無名,以陳詩之膽略難以適應;四是仕途不如意,官場經驗闕如,尤其是耿直狷介的性格與政治權術的缺失,他經受不起廟堂風雨的沖洗。細究起來,前兩者是外因,后兩者才是內因,這對于心中駐留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子來說,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作出如此之舉。陳詩,說到底還是個讀書人,不是權謀家,不眷戀廟堂,實為自知之明的體現。作者也書寫了陳詩對于女性的渴望,由于道德的局限,陳詩并未放縱情感,于“自我”、“本我”方面內斂。在筆者看來,這是小說涓涓細流中的調皮浪花,迤邐富有生氣。情欲,在不少歷史小說得以充分張揚,既能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也能夠完善人物形象。作者處理極為妥帖,從生理與心理需要而言,陳詩對于賣唱女孩的心動與留戀合乎情理;作為一個道德主體而言,陳詩的決絕與舍棄堪稱得當,因為,情欲對于塑造人物,如果過于渲染,“任某一種情欲去支配,它就會顯得不是什么性格,或是乖戾反常、軟弱無力的性格”⑧。自此,我們可以看出,陳詩不是一個迂腐的夫子,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實在個體。
甘才志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小說寫作經驗,這不假,可多寫的是現代小說,尤其是官場小說。他從政多年,熟識官場各種情形,更熟悉各種官員心理及背后的官場文化。基于這種經驗,《大儒陳詩》中諸多官場人物,雖然只是側片或片段,卻也客觀冷靜不失公允,在陳詩的人生旅程中各自呈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主次交織,相映成趣,如和珅之專擅,朱珪之圓滑,劉墉之睿智,陶芥亭之奸猾,畢沅之無奈,高為濟之樂善,鄭靜山之真誠,張筠圃之知人,無疑推動著陳詩從一個夢想“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逐漸走上“一把戒尺走天下,四錢唾沫送乾坤”之路。一代大儒漸趨完型:撰《四書類考》,“考出一個四書的精髓來”;作《人名考》,“一一列注古代人名”,源流清晰可辨;著《六律正五音考》,“開創了音韻學之先始”;纂《古今韻類考》,“考通五千年文字之發音”;修《湖北通志》,遂成地方志第一人;繼而《湖北方域志》、《湖北舊聞錄》、《湖北金石佚考》、《湖北詩文載》“相繼付梓,一經面市,荊湖書屆即被轟動,洛陽紙貴”。陳詩何以成為“國士”、“楚之大儒”?黃庭堅《書幽芳亭》曰:“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學問博而約、宏而邃,通綜兼善,是謂大儒。“如何組合一個歷史境遇取決于歷史學家如何把具體的情節結構和他所希望賦予某種意義的歷史事件相結合。這個作法從根本上說是文學操作,也就是說,是小說創作的運作。”⑨歷史敘事尚且如此,何況小說敘事。小說雖然不是慣常理解的成長小說,其中足可以窺見大儒的修煉歷程,這個過程亦是歷史真實性與藝術必然性的結晶,其中既有大氣磅礴,又有蕩氣回腸,還有中正雅致,采摘于歷史的符合事實,藝術虛構的不失自然逼真,使得陳詩的一生并未因缺少大起大落、刀光劍影而生澀呆滯。這里,我們見出了作家的文學修養,見出了作家的認真的創作態度,見到了作家面對前輩先賢的虔誠。
甘才志的寫作取法古典小說創作,章回體是一例,分章別錄,主干枝節,清晰可見。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說植入詩、曲、民歌、典故、墓志銘,尤以詩為最,其中既有他人之詩作,多是主人公的吟誦之作,有助于我們領略他的冠時才華。此種植入,“無論是描述景物、人物與場面,還是直接敘述故事情節,往往多有省略、跳躍之處,需要讀者充分發揮想象與聯想,去填補其中的空白,連接各類意象。它的好處是能為小說營造詩一樣的意境,使讀者在閱讀故事的同時感受到詩意盎然,享受一種抒情情調”⑩。陳詩殿試返歸會館,哼的是蘄州人燈歌《八仙調》,此調輕快悠揚,輕松愉悅,當時陳詩是否唱過此曲,應是不可考了,但是,作者在這里用此調甚是妥帖:一是符合陳詩其時心境,殿試應對,一氣呵成,真知灼見,盡抒胸臆,奢想若能呈于天子御覽,自己治世妙計若獲得圣主青睞,豈不快哉?二是殿試順利,寒窗苦讀,終于要出人頭地,榮耀鄉里,不也快哉?三是所哼小曲為母親所教,春風得意之時仍未忘記苦熬在家的娘親,可作孝心解,一沒辜負娘親教誨,也與后面奉孝致仕前后呼應。明人李大年《唐書志傳演義序》稱“詩詞檄文頗據文理,使俗人騷客披之,自亦得諸歡慕”。清人毛宗崗《三國志演義·凡例》認為“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尤其在消費文化無孔不入、審美能力嚴重鈍化的今天,作者的這種努力無疑既進入了歷史,又豐富著讀者的精神世界。不過,隨之也產生了一個問題:作者植入詩詞后,往往會進行釋解,有時甚至長篇大論。小說畢竟是敘事,必然涉及敘事節奏和敘述進程,作者于此加入大量的考證與闡解,是否都合適呢?

注釋:
①吳秀明、夏烈:《現代人文觀照下的歷史敘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2期。
②巴爾扎克著,李健吾譯:《巴爾扎克論文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③甘才志:《大儒陳詩·自序》,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④巴爾扎克著,李健吾譯:《巴爾扎克論文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⑤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2頁。
⑥甘才志:《大儒陳詩》,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頁。
⑦ 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卷一),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37頁。
⑧黑格爾:《美學》(卷一),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302頁。
⑨ 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頁。
⑩劉曉軍:《雅俗文學文體的交融與悖離》,《明清小說研究》2008年第4期。

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