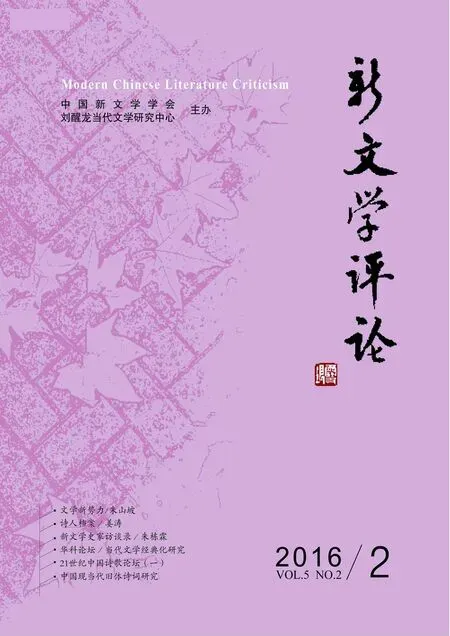從粵桂邊城出發(fā)的小說敘事
———朱山坡小說藝術(shù)新論
◆ 梁冬華
?
從粵桂邊城出發(fā)的小說敘事
———朱山坡小說藝術(shù)新論
◆ 梁冬華
朱山坡自2005年以“廣西文壇的黑馬”(《南方文壇》張燕玲語)之勢闖進(jìn)小說界迄今,已經(jīng)十年有余。十余年來,朱山坡由最初2015年第6期《花城》雜志“花城出發(fā)”欄目、2006年第2期《青年文學(xué)》雜志“新人展”欄目等文學(xué)刊物隆重推出的新人,到最近于2015年10月召開的“廣西后三劍客作品研討會”中的具有“個性鮮明,敘述十分有勁道”(北京大學(xué)陳曉明語)的劍客,已然成為當(dāng)前文壇頗具分量的作家,尤其在短篇小說領(lǐng)域占據(jù)重要席位。筆者一直關(guān)注跟蹤朱山坡的小說創(chuàng)作,分別于2008年、2014年發(fā)表了評論文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論朱山坡小說中的鄉(xiāng)土世界》①和《書寫鄉(xiāng)土世界中的尊嚴(yán)和靈魂——再論朱山坡的小說創(chuàng)作》②。在最早發(fā)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文中,筆者開篇便以“游走在粵桂邊城的鄉(xiāng)村敘事”為章節(jié)標(biāo)題評述朱山坡小說的藝術(shù)特點,可謂是較早從地域視角總結(jié)其創(chuàng)作的學(xué)術(shù)評論文章。近期,隨著朱山坡小說作品的不斷面世及其文學(xué)地位的逐步崛起,越來越多的評論家注意到了朱山坡的小說及當(dāng)中的地域性,將其小說風(fēng)格與廣西特殊的人文地理面貌聯(lián)系在一起。評論家邱華棟稱:“朱山坡發(fā)展了一種關(guān)注于和專屬于廣西的南方的小說文體,那純粹就是一種南方的小說。這種南方,不同于江南,是偏西南的瘴癘之地廣西的小說,是一種獨特的怪異的小說,就像螺螄粉和黃皮果的味道。”③陳曉明也在“廣西后三劍客作品研討會”上談到了朱山坡小說中的廣西文學(xué)性格。在這樣的學(xué)術(shù)背景下,筆者重返當(dāng)年評論的起點——粵桂邊城,結(jié)合朱山坡十余年的小說作品,從創(chuàng)作立場、作品美學(xué)風(fēng)貌等方面深入發(fā)掘粵桂邊城對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以求教方家。
一、朱山坡與粵桂邊城
作家朱山坡的故鄉(xiāng),是一個位于粵(廣東簡稱)與桂(廣西簡稱)邊界的邊遠(yuǎn)山村——廣西北流市那排村。朱山坡在此度過了人生最早的時光——童年和青少年,直到成年進(jìn)入城市工作后方才離開故鄉(xiāng)。如今的朱山坡,在城市待的年頭早已遠(yuǎn)超早年鄉(xiāng)村時光,但他卻難以忘卻曾經(jīng)的故鄉(xiāng)生活,多次提及“農(nóng)村是我的鄉(xiāng)土,是我心靈的故鄉(xiāng)”④。這種濃郁的故鄉(xiāng)情懷,并非朱山坡一個人所獨有,還出現(xiàn)在許多優(yōu)秀的作家身上,如沈從文對生于斯長于斯的湘西的眷戀、莫言所念念不忘的兒時密州等。對于他們而言,故鄉(xiāng)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符號,而更是一個生命出發(fā)的起點。他們在故鄉(xiāng)呱呱墜地,宛如一張白紙來到人間。正是在故鄉(xiāng),他們完成了從幼年到成年的成長蛻變,建立起對社會和世界的基本認(rèn)知,在白紙上勾勒出大致的人生線條和框架。此后,他們帶著既成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走出故鄉(xiāng)探索外在的世界,為白紙增添豐富的圖案和色彩。從這一意義上看,位于粵桂邊界上的故鄉(xiāng),佇立在朱山坡生命起點處,發(fā)散著巨大的影響力,不僅覆蓋其已經(jīng)走過的人生歷程,還將持續(xù)地輻射到其即將展開的人生道路。
假如說,故鄉(xiāng)對于朱山坡的影響,首先表現(xiàn)為其生命之初的認(rèn)知成長,而在離開故鄉(xiāng)進(jìn)入城市謀生后,故鄉(xiāng)則開啟了朱山坡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大門。在投身文壇提筆創(chuàng)作伊始,朱山坡便別有用心地將故鄉(xiāng)“朱山坡生產(chǎn)隊”這一地名直接轉(zhuǎn)換成其筆名“朱山坡”。他在文章《我的名字就叫故鄉(xiāng)》中說道,“‘朱山坡’是那排村的一個生產(chǎn)隊,那是我的故鄉(xiāng),現(xiàn)在成了我的筆名。只要別人輕輕叫一聲朱山坡,我首先想到的是故鄉(xiāng),然后才是自己。朱山坡現(xiàn)在與我渾然一體了,她就像老無所依的母親,比我的影子還要親密,我到了哪里,就把她帶到哪里,讓她與我風(fēng)雨同路,相濡以沫”⑤。“朱山坡”這一名字,成為作家從真實現(xiàn)實世界走向虛擬文學(xué)世界的通道。
在踏進(jìn)文學(xué)的大門后,朱山坡再次利用故鄉(xiāng)這一資源,構(gòu)建出一個以粵桂邊城為原點的文學(xué)鄉(xiāng)土世界。閱讀《我的叔叔于力》、《米河水面掛燈籠》、《陪夜的女人》、《靈魂課》等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當(dāng)中存在著一個由廣西米莊、米河、闕姓鄉(xiāng)民、廣東高州、販子等集合而成的文學(xué)鄉(xiāng)土世界。在這一虛構(gòu)的鄉(xiāng)土世界中,米莊位于廣西邊境,毗鄰廣東省的高州市,是一個原始、落后的農(nóng)村,“米莊古木叢生,這些樹沒人敢砍,它是用來阻擋四面撲來的邪氣的”,“就一條通往外面的路,路的盡頭是高州”⑥。而在現(xiàn)實世界中,“朱山坡其實只是粵桂邊上的一塊彈丸之地,像貼在山坡上的一張以明清民居為背景的郵票,群山抱繞,竹樹茂密,連房子也密密麻麻的,再也容不下別人插足進(jìn)來”,“朱山坡就一條通往外面的狹窄的泥路,路的盡頭是高州”⑦。對比二者不難發(fā)現(xiàn),小說中虛構(gòu)的鄉(xiāng)土世界實際是作者現(xiàn)實故鄉(xiāng)的藝術(shù)再現(xiàn),二者皆有著相似的粵桂邊城的地理坐標(biāo)和風(fēng)土人情。對于這一文學(xué)世界中的故鄉(xiāng)原型,朱山坡稱其為“寫作的根據(jù)地”,認(rèn)為“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精神故鄉(xiāng),對那里熟悉,有感情,有記憶,有痛感,他每次下筆都自然而然地想到那里,即使他的思緒已經(jīng)到達(dá)浩瀚的宇宙,但最終還會回到那里。這就是他的‘寫作的根據(jù)地’”⑧。從這一故鄉(xiāng)粵桂邊城這一根據(jù)地出發(fā),朱山坡在文學(xué)的道路上一走便是十余年。粵桂邊城給予朱山坡創(chuàng)作的靈感和素材,使其建立起立足鄉(xiāng)土的現(xiàn)代文明批評立場,形成邊緣、絕望、奇崛的作品美學(xué)風(fēng)貌,從而開創(chuàng)出屬于自己的一番文學(xué)天地。
二、創(chuàng)作立場:立足鄉(xiāng)土的現(xiàn)代文明批判
創(chuàng)作立場,是作家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中審視生活、處理創(chuàng)作素材、構(gòu)思人物故事時所處的位置和所抱的態(tài)度。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立場,往往受到其成長背景、生活環(huán)境、所受到的教育等多方面的影響。從粵桂邊城出發(fā)的朱山坡,帶著源自邊城的認(rèn)知和人生體驗進(jìn)入小說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建立起個人化的創(chuàng)作立場——立足鄉(xiāng)土的現(xiàn)代文明批判。
朱山坡在故鄉(xiāng)粵桂邊城生活的時間,大致是上世紀(jì)70年代至90年代,正值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變革的關(guān)鍵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以城市為表征的現(xiàn)代文明逐步崛起,借助市場經(jīng)濟(jì)的法則不斷擠壓傳統(tǒng)鄉(xiāng)土文明,鄉(xiāng)親們的利益受到巨大損害。朱山坡目睹了鄉(xiāng)親們所承受的多方苦難,感同身受地體會了苦難背后的酸楚和無奈。這一特殊的成長經(jīng)歷,投射到朱山坡日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活動中,使其自覺站在鄉(xiāng)土文明的立場,書寫那些被現(xiàn)代城市不斷擠壓慘敗破損的鄉(xiāng)村以及不堪重負(fù)茍延殘喘卻又不忘善之本性的底層鄉(xiāng)親,以此表達(dá)對現(xiàn)代城市文明的譴責(zé)和批判。
朱山坡小說中的現(xiàn)代文明批判,暗含“五四”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傳統(tǒng),同時發(fā)展出個人化的冷峻批判風(fēng)格。“五四”新文學(xué)形成的現(xiàn)實主義思潮,最顯著的文學(xué)特征之一便是使用人道主義作為武器進(jìn)行社會批判。老舍、夏衍為代表的“五四”現(xiàn)實主義作家,以人道主義關(guān)于肯定人的自由、價值和尊嚴(yán)的思想作為價值準(zhǔn)則,評判現(xiàn)實社會的正負(fù)面性,揭露底層民眾被剝削、壓迫、損害的命運,表達(dá)對受迫害者的同情。老舍小說中的車夫駱駝祥子,以拉上自己的洋車作為實現(xiàn)個人自由和幸福、擺脫被剝削命運的出路。然而,戰(zhàn)爭頻發(fā)、時局動亂的社會處境,并未給民眾提供任何實現(xiàn)個人幸福的機(jī)會。無論祥子做出何種努力,均以失敗告終,最后墮落為行尸走肉的街頭混混。老舍通過祥子的不幸人生,抨擊了當(dāng)時不為民眾謀幸福的政府和社會。夏衍則記錄了包身工失去人身自由淪為資本家掙錢機(jī)器的真實遭遇,以此批判資本家不擇手段追求金錢的本性。朱山坡繼承了“五四”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人道主義思想遺產(chǎn),同樣立足底層民眾,揭露底層苦難。但與“五四”作家不同的是,朱山坡的批判主體更為退后、批判視角更為隱匿。他并未采用“五四”作家站在臺前富于正義感的大聲控訴、譴責(zé)方式,而是退守至幕后嚴(yán)控批判主體的情緒,冷靜地將底層民眾的苦難一一敘述和呈現(xiàn),不做任何主體判斷,完全交由讀者評判。經(jīng)由朱山坡的冷靜描述,讀者與小說中的苦難世界面對面,得以直擊苦難事件,獲得親臨其境的感受,從而引起更大的震撼和更深入的反思。正是這種隱匿的批評主體和視角,使朱山坡的小說表現(xiàn)出一種嚴(yán)肅、冷峻的批判力量,力透紙背,發(fā)人深省。
朱山坡的現(xiàn)代文明批判,經(jīng)歷了從早期的經(jīng)濟(jì)層面批判到近期的拷問個體靈魂的轉(zhuǎn)變。
在早期發(fā)表的《米河水面掛燈籠》、《我的叔叔于力》等作品中,他著眼鄉(xiāng)村,通過描寫鄉(xiāng)村“米莊”與城鎮(zhèn)“高州”之間的故事,展示了前現(xiàn)代鄉(xiāng)土所遭受的現(xiàn)代城市侵害。米莊位于廣西境內(nèi),是一個古樸的鄉(xiāng)村,地理環(huán)境原始而閉塞,猶如與先民的上古世界相連,并且長期尊奉“人以食為天,食以米為本,以米立村”的古訓(xùn),固守以水稻種植為主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模式。米莊儼然是一個巨大的隱喻,暗藏人類童年記憶,意寓前現(xiàn)代鄉(xiāng)土文明形態(tài)。與米莊相鄰的高州,位于廣東境內(nèi),是一個得改革開放時代風(fēng)氣之先的城鎮(zhèn),推崇金錢至上的市場經(jīng)濟(jì)法則。在這一法則的推動下,高州人帶著大把的現(xiàn)金來到米莊,煽動人們放棄賴以生存的水稻種植,改為燈籠椒等經(jīng)濟(jì)作物。可就在鄉(xiāng)親們豐收在望的時刻,高州人卻因價格失利而逃之夭夭,將市場的風(fēng)險和損失直接轉(zhuǎn)嫁到了毫無防備的鄉(xiāng)親們身上,最終使米莊上演了豐收成災(zāi)的慘劇。高州人對米莊的入侵,從表層來看,是市場經(jīng)濟(jì)對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強(qiáng)勢植入。這些曾經(jīng)從鄉(xiāng)土走向城市的高州人,如今卻帶著城市經(jīng)濟(jì)的法則折返鄉(xiāng)土,并最大限度地攫取這片土地上的利益,破壞了傳統(tǒng)鄉(xiāng)土的寧靜及和諧。從深層來看,則是城市文明對鄉(xiāng)土文明的損害和遺棄,其嚴(yán)重性是無法言語的。由于前現(xiàn)代鄉(xiāng)土文明孕育了更高級形態(tài)的城市文明,鄉(xiāng)土也因而成為蟄居城市的現(xiàn)代人始終不能離棄的精神原鄉(xiāng)。如今,現(xiàn)代人卻以自己的貪欲和血淋淋的雙手將之破壞和損毀。長此以往,那些曾經(jīng)給與我們現(xiàn)代人生命和溫暖的精神故土必將不復(fù)存在,而膨脹著私欲的現(xiàn)代人也將陷入永無停泊之處的虛無境地。
如果說,朱山坡的早期現(xiàn)代文明批判還停留在宏觀的經(jīng)濟(jì)層面,那么,他近期的作品則把視角深入到了文明的載體——個體及其靈魂,通過個體的毀滅及其靈魂的歸宿深刻地抨擊了城市文明對鄉(xiāng)土文明的致命性打擊。在以《靈魂課》為代表的近期作品中,朱山坡聚焦城市,講述了進(jìn)城務(wù)工鄉(xiāng)親肉體和靈魂的悲慘遭遇,進(jìn)一步推進(jìn)了現(xiàn)代文明批判的主題。在《靈魂課》中,朱山坡的筆觸跟隨鄉(xiāng)親的腳步,從生養(yǎng)的鄉(xiāng)村一路追隨到了打工的城市。闕小安是故事的主角,他從米莊出發(fā)來到城市,與大多數(shù)進(jìn)城打工的鄉(xiāng)親相似,從事城市最繁重的體力勞動——摩天大樓的建筑工人。處在城市語境中的闕小安,很快便褪去了鄉(xiāng)土的質(zhì)樸而被熱鬧繁華、物欲橫流的城市文化所同化。他穿著表征都市流行文化的夾克牛仔褲,微笑地在財富廣場的大金元寶前拍照留念,并把照片寄給家鄉(xiāng)的母親。收到照片的母親看出了闕小安內(nèi)心深處被激發(fā)的強(qiáng)烈物質(zhì)欲望,更看出了其與鄉(xiāng)土決裂永待城市的決心。母親深感不安和焦慮,走了五六天的鄉(xiāng)路來到城市,試圖將日漸迷失的兒子帶回米莊。在母親進(jìn)城尋兒的情節(jié)上,朱山坡設(shè)置了重重障礙,使故事的敘述充滿了戲劇性和寓言性。母親的第一次進(jìn)城,尋找的是工作時不慎從五十樓摔下而死的兒子的靈魂。她徑直來到了一個名為“靈魂客棧”的地下旅館。這個靈魂客棧存放著大量死于非命的進(jìn)城務(wù)工鄉(xiāng)親們的靈魂。有的靈魂僅是暫時的安放,“等到過年回家了,等到死者親人的悲痛減輕了,或等到連低廉的房租都交不起了,才把他們帶回鄉(xiāng)下去”;有的靈魂卻企望長期安放于此地,“花花綠綠的城里的生活還沒過夠呢,房子呀,車子呀,還沒有買……不甘心半途而廢回到鄉(xiāng)下去”。在母親看來,兒子顯然屬于后者——死后的肉體雖然回到了米莊而靈魂卻固執(zhí)地停留在城市。因此,她喋喋不休地向靈魂客棧的骨灰盒管理員訴說“靈魂存在”的理念,希望以此獲得對方的認(rèn)同并幫助她找到兒子的靈魂勸其返回家鄉(xiāng)。極具戲劇性的是,就在管理員伸出援手協(xié)助老人的尋找并帶她到闕小安生前拍照和工作過的地方的時候,闕小安意外現(xiàn)身了。原來他還活著,摔死的是他的堂兄闕小飛。堂兄小飛的死,刺激了老人的神經(jīng),使她產(chǎn)生了錯覺和恐慌,才有了進(jìn)城尋兒的異常舉動。隨后,小安粗暴地把執(zhí)意要帶他回米莊的母親拖走,強(qiáng)硬終結(jié)了母親的第一次進(jìn)城尋兒之旅,僅余留下她凄慘顫栗的呼叫聲回蕩在城市的鋼筋水泥高樓大廈間隙間。半年后,母親再次進(jìn)城來到了靈魂客棧。與第一次尋兒靈魂回米莊不同,母親此行的目的是將意外從高空中摔死的兒子的肉體(骨灰)和靈魂一起永久安放于客棧中,以達(dá)成兒子生前期盼的“終于在城里安家落戶了,要買房子、車子,要娶妻生子,要光宗耀祖”的愿望。故事的最后,母親要求管理員預(yù)留緊鄰兒子骨灰盒的位置,以便自己死后能夠陪在兒子的身邊,給予死于非命的兒子以安慰。
讀完這一關(guān)于鄉(xiāng)親個體及其靈魂的小說,不禁讓人掩卷沉思。文明是人類活動和社會發(fā)展的產(chǎn)物。在文明這一龐大的系統(tǒng)中,個體是最小的單位。任何一種文明,都是由千萬個個體的知識、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習(xí)俗等匯聚形成的,同時也依靠這千萬個個體的傳承而得以延續(xù)。換句話說,沒有個體,就沒有文明的存在。然而,在朱山坡的小說中,以闕小安為代表的鄉(xiāng)土文明的個體,在進(jìn)入另一城市文明的語境后,卻遭受了死亡的厄運。尤其如闕小安,初入城時深以所從事的建造摩天大樓的工作而自豪——這一自豪感實際源于對自己作為城市建造者身份的認(rèn)同,卻未曾想在日后從工作崗位失足摔下而粉身碎骨、魂飛魄散。前后的巨大反差,形成了頗具深意的反諷——一心渴望融入城市的鄉(xiāng)親個體,最終卻被城市狠心拋棄。更甚者,被城市拋棄的鄉(xiāng)親個體,死后仍念念不忘生前的城市夢,一改葉落歸根的傳統(tǒng),而是囑咐家人將其肉體(骨灰)和靈魂長期安放在城市的某一角落,完全斬斷了與家鄉(xiāng)的聯(lián)系。可以想象,當(dāng)大量諸如闕小安般的鄉(xiāng)親個體進(jìn)入城市卻又慘遭城市毀滅時,鄉(xiāng)土文明猶如釜底抽薪,失去了維系其運轉(zhuǎn)及傳承的主體力量,逐漸空殼化直至最后的毀滅。或許,這也正是朱山坡書寫靈魂的意義所在。
三、美學(xué)風(fēng)貌:邊緣、絕望、奇崛
在粵桂邊城別樣風(fēng)情的浸潤下,朱山坡的小說呈現(xiàn)出獨特的美學(xué)風(fēng)貌——邊緣、絕望、奇崛。
粵桂邊城有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風(fēng)貌,給人以神秘、奇異之感。從地理坐標(biāo)上看,粵桂邊城位于祖國的東南部,南面臨海,遠(yuǎn)離政治、文化中心。長期以來,偏于一隅的粵桂邊城疏離中心,未受中心文明的馴化,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自我天性,再加上海洋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原始自然、性情率真、敢打敢拼的個性,與中心城市的明理守法、規(guī)整有序、按部就班形成了巨大差異。就氣候地理學(xué)而言,粵桂邊城屬于亞熱帶氣候,天氣炎熱,四季輪換并不明顯,山陵多,雨水充沛,常年潮濕溫潤。位于北方的中心城市則屬于溫帶氣候,四季分明,多為平原地貌,干燥遼闊。因此,對于北方中心城市的人們而言,擁有偏遠(yuǎn)地理位置和潮熱氣候特點的粵桂邊城是神秘、奇異的。而坐落在粵桂邊城的鬼門關(guān)及其傳聞,更是將這神秘、奇異推向極致。鬼門關(guān)又稱天門關(guān),《辭海》中的相關(guān)解釋為:“鬼門關(guān),古關(guān)名,在今廣西北流縣西,界于北流、玉林兩縣間,雙峰對峙,中成關(guān)門。”在古代,鬼門關(guān)是通往欽、廉、雷(今廣東雷州半島)、瓊(海南島)和交趾(今越南中北部)的交通沖要,也是朝廷流放、貶謫官員至南海、嶺南一帶的必經(jīng)關(guān)口。許多被貶的朝廷官員,由于不適應(yīng)潮熱的南方氣候,再加上處境改變后的抑郁落寞,往往不幸染病身亡客死南方,故將鬼門關(guān)視為人間與地獄的分界線,鬼門關(guān)以北是人間宜居之地,以南則是百草叢生、瘴氣彌漫、鬼怪作亂的蠻地。跨過“鬼門關(guān)”就相當(dāng)于進(jìn)入了陰森恐怖的陰界,生者難以復(fù)還。中唐名相李德裕過鬼門關(guān)時吟道:“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guān)。”宋代被貶文官蘇東坡,在獲得赦免返鄉(xiāng)途中,也以“養(yǎng)奮應(yīng)知天理數(shù),鬼門出后即為人”的詩句來表達(dá)自己重度鬼門關(guān)返回人間的喜悅。由此看來,無論是真實地理地貌、氣象氣候使然,抑或文人騷客的層層渲染,粵桂邊城猶如一位戴著面紗的異域女子,神秘莫測,卓然獨立于眾人之外。
從粵桂邊城生長起來的作家及其小說,同樣具有這座邊城的獨特氣質(zhì)。中國有句俗語“一方水土養(yǎng)育一方人”,揭示了生存環(huán)境與人的氣質(zhì)稟賦二者的密切聯(lián)系。法國理論家泰納的三因素說,將生存環(huán)境與人的聯(lián)系進(jìn)一步推進(jìn)到了人的創(chuàng)造活動及其產(chǎn)物——文藝創(chuàng)作和作品上。他認(rèn)為文藝創(chuàng)作是由種族、環(huán)境和時代三種因素決定的。這些理論觀點對應(yīng)到實踐領(lǐng)域,合理地解釋了為何一些作家的作品帶有其生長地的氣質(zhì)。就如同遲子建的作品,總能讓讀者從中感受到其出生地漠河北極村的純凈、成長地大興安嶺的厚重等性情。從粵桂邊城走出去的作家林白、朱山坡等人,也將生長地的神秘、奇異氣質(zhì)投射到其文學(xué)作品中。林白在早期創(chuàng)作階段,多次寫到故鄉(xiāng)粵桂邊城的鬼門關(guān)和河流。她在自傳體小說《一個人的戰(zhàn)爭》中寫道:“出生在鬼門關(guān)的女孩,與生俱來就有許多關(guān)于鬼的奇思異想……關(guān)于鬼魂的傳說還來自一條河,這條流經(jīng)B鎮(zhèn)的河有一個古怪的名字,叫‘圭’。在這個瞬間我突然想到,‘圭’與‘鬼’同音……圭河在別的縣份不叫圭河,而且一直向東流得很順利,到了B鎮(zhèn)卻突然拐彎向北流,過了B鎮(zhèn)再拐回去,這真是一件只有鬼才知道的事情。”另一作品《致命的飛翔》也有相同的表述:“在我的家鄉(xiāng)如果要尋找地獄的入口處,一定是那條向北流動的河流……傳說這條河就是地獄的入口處,凡是自動走進(jìn)去的人經(jīng)過地獄的熔煉會再次返回人間從而獲得順?biāo)煨脑傅膩硎馈!边@充滿靈異氣息的鬼門關(guān)和河流,在多部作品中反復(fù)出現(xiàn),如同文眼般點明了作品的整體傾向。與林白直接使用粵桂邊城的事物點題不同,朱山坡則在小說的技法藝術(shù)上下功夫,使其小說呈現(xiàn)出與邊城一致的絕望之風(fēng)、奇崛之氣。
朱山坡的小說具有邊緣、絕望、奇崛的美學(xué)特征。這一美學(xué)風(fēng)貌,實際是由其小說中非主流的人物、非常態(tài)的事件、令人意外的結(jié)構(gòu)等幾個方面整合起來后所呈現(xiàn)出來的。具體來說:
其一,朱山坡的小說主要描述非主流的底層民眾,體現(xiàn)出一種邊緣之美。
按照階層來劃分,人類社會由上層的領(lǐng)袖和英雄、中層的中產(chǎn)階級、底層的平民百姓三部分構(gòu)成。處于頂層的領(lǐng)袖和英雄,擁有偉岸的人格魅力、驚天動地的壯舉、標(biāo)榜史冊的人生意義,故成為眾多作家書寫的首選對象,由此形成英雄敘事的文學(xué)主流。在邊城長大的朱山坡,并未盲目從眾書寫陌生的英雄和領(lǐng)袖,而是著眼于身邊的底層鄉(xiāng)土民眾,將最熟悉的生活人物轉(zhuǎn)化為文學(xué)人物,立志“為民間野生人物立傳”⑨,從而使其小說體現(xiàn)出一種有別于主流敘事的邊緣之美。
朱山坡小說中的底層民眾大致可劃分為兩大類型:
一類是占據(jù)小說人物主體的農(nóng)村鄉(xiāng)民。
朱山坡的小說在最初亮相文壇時,就以成功塑造一系列邊緣、卑微的農(nóng)民而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最早發(fā)表的小說《我的叔叔于力》,其主人公于力是一個勉強(qiáng)掙扎于溫飽線之上的邊城米莊農(nóng)民。他與常人一樣有著最基本的傳宗接代、情感和歸屬的需求,渴望過上“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家庭生活。起初,于力試圖通過合法的方式實現(xiàn)這一理想,遂將自家種的芭蕉賣給廣東販子以賺回老婆本。但由于市場價格波動買賣未成交,于力的如意算盤落得一場空。之后,巧合之下,他遇到一個瘋女人并視之為“妻子”。初嘗家庭甜蜜滋味的于力,萌生出更高的需求——希望能夠治好“妻子”的精神病,“真正過上相互恩愛的令村里人嫉妒的夫妻生活”。為此,于力甚至干起了抬棺材和尸體的苦差以給“妻子”籌錢看病。但事與愿違,“妻子”康復(fù)病愈后恢復(fù)記憶,與其法律上的丈夫返回屬于她的上海,僅余下于力及其殘缺破碎沒有“女主人”的“家”。讀罷小說,于力的不幸遭遇令人動容,他手無寸鐵,無辜而善良,但窘迫的底層鄉(xiāng)村生存環(huán)境妨礙了其對幸福的追求,還不斷地遭受到來自城市的阻攔——市場經(jīng)濟(jì)打破了他的賣蕉掙錢夢、城市上海帶走瘋女人擊碎了他的家庭夢。于力可謂諸多生活在底層鄉(xiāng)村的苦難農(nóng)民的縮影。
自于力始,朱山坡的妙筆描繪了眾多性格鮮明、血肉豐滿的邊遠(yuǎn)鄉(xiāng)民形象。其中,有為改善生存狀況而用盡一切手段的鄉(xiāng)民,如《感謝何其大》中的何唐山及其妻子程銀香為實現(xiàn)戶口“農(nóng)轉(zhuǎn)非”付出了多方努力、《觀風(fēng)》中的未滿二十歲的觀風(fēng)因貪戀錢財嫁給了六十多歲的萬元戶王老董、《空中的眼睛》中的麻麗冰以自己的肉體換來飽腹的米飯和豬肉;有一心逃離鄉(xiāng)村融入城市生活卻不被接納的進(jìn)城務(wù)工者,如《靈魂課》中的城市建筑工闕小安、《推銷員》中的房地產(chǎn)推銷員盧遠(yuǎn)志、《躺在表妹身邊的男人》中因拒絕洗浴中心嫖客調(diào)戲而摔斷腿的表妹及其身邊躺著的連續(xù)加班過勞死的男人;還有的則是身處困境卻舍棄個人利益而無私幫助他人的鄉(xiāng)民,如《陪夜的女人》中陪護(hù)將死老人的陪夜女人、《爸爸,我們?nèi)ツ睦铩分卸啻螏椭四_女人的爸爸、《美差》中用母雞救回流產(chǎn)婦人性命的鬼村鄉(xiāng)親、《丟失國旗的孩子》中用自己珍藏的國旗挽救全村人不被批斗的張國寶老人、《天色已晚》中賤價賣肉給少年圓其電影夢和吃肉夢的屠夫老宋等等。這一個個生活在邊遠(yuǎn)鄉(xiāng)村的底層鄉(xiāng)民,置身于窮困、破落的生存環(huán)境中,遭遇苦難卻不忘善之初心,散發(fā)著溫暖的人性之光。
另一類是非農(nóng)身份的城市人。
朱山坡的小說,除了刻畫農(nóng)村鄉(xiāng)民形象外,還書寫了政府官員、知識分子、下崗工人等不同職業(yè)和身份的城市人。《逃亡路上的壞天氣》寫了一個因落入別人設(shè)計的受賄圈套擔(dān)心被判刑而出逃的副市長,在逃亡路上與蛇頭、殺人犯結(jié)伴而行,一路狀況不斷險象環(huán)生。最終真相浮出水面,受賄圈套的幕后主使——另一個圖謀鏟除仕途競爭對手的副市長被定罪,副市長因禍得福,榮升市長官職。而《信徒》、《驢打滾》、《天堂散》描寫的,則是大學(xué)教師、作家等高級知識分子群體。《信徒》中的大學(xué)副教授郭敬業(yè),既有體面的社會地位(擁有哲學(xué)博士學(xué)位頭銜的大學(xué)教師),亦有雄厚的經(jīng)濟(jì)實力(從哲學(xué)轉(zhuǎn)向風(fēng)水學(xué)并四處走穴賺大錢),卻一直遭受妻子的奚落和辱罵,最終奮起反抗殺死了妻子。《驢打滾》的主角是大學(xué)教師鹿小茸及其幾位同事好友。鹿小茸就職中文系,愛好詩歌,有著詩人特有的率性、沖動、瘋癲,因詩歌與同事馬朵朵結(jié)怨、出走阿富汗、沖擊諾貝爾文學(xué)獎等等,最后在與他人的糾紛和襲擊中過度精神緊張而精神失常,由文學(xué)意義上的詩人瘋子成為醫(yī)學(xué)意義上的神經(jīng)病瘋子。《天堂散》中的父親是一名才氣不高的作家,雖歷經(jīng)大半生的辛勤耕耘,卻未寫出引起眾人關(guān)注的作品,自然也就沒有獲得讀者的賞識和追捧。然而,一篇尚在構(gòu)思中的小說《天堂散》改變了父親不被人關(guān)注的局面,成功吸引一位來自石榴村的女人唐浩美成為其粉絲。最終,父親與其一生中唯一的知音——唐浩美——私奔到人間天堂杭州,合作完成了小說《天堂散》,發(fā)表后引起眾人轟動大獲成功。另外,《中國銀行》和《大喊一聲》則聚焦下崗工人群體,以近乎殘酷的筆法寫出了馮雪花、胡四等代表的眾多下崗工人被時代的改革巨輪碾壓而過的悲慘人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朱山坡的小說中,農(nóng)村鄉(xiāng)民或城市平民均有著共同的特點:利益被損害的一方。即便是高居副市長職位的政府官員,也沒有寫他官架子十足受人擁戴光鮮亮麗的一面,而是選取了其作為被人陷害的犯罪嫌疑人落荒而逃的狼狽一面。至于本來就已經(jīng)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城市下崗工人和鄉(xiāng)村農(nóng)民,其處境更是被毫無遮攔地裸現(xiàn)出來,讓人讀了倍感心酸、同情和憐憫。這些人物形象作為利益被損害的群體,處于權(quán)利和話語的邊緣,弱勢而受人欺凌,具有一種邊緣性。這一人物形象的邊緣性,使朱山坡的小說具有了別樣的美學(xué)面貌,從而遠(yuǎn)遠(yuǎn)區(qū)別于同是寫底層民眾的京派作家作品。京派作家老舍的《茶館》,所塑造的常四爺、王利發(fā)掌柜等京城百姓形象,雖然最末也走向了毀滅的人生道路,但他們始終有著一種皇城根下的驕傲自滿心態(tài),具體表現(xiàn)為對國家時政的關(guān)注、個人的報國抱負(fù)等。總的來說,朱山坡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以其獨特的邊緣性,豐富了當(dāng)代鄉(xiāng)土文學(xué)的人物長廊。
其二,朱山坡的小說大多講述非常態(tài)的極端生活事件,體現(xiàn)出一種絕望之美。
朱山坡曾說,“在寫小說的時候,我認(rèn)為世界本質(zhì)上是冷酷的,特別是表現(xiàn)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上,冷酷是常態(tài)”⑩。從這一冷酷文學(xué)觀出發(fā),朱山坡在進(jìn)行小說創(chuàng)作時,著重講述極端、慘烈的事件,把故事環(huán)境設(shè)定得極為貧瘠、落后、困頓,將人物推向不可挽回的絕境中,使其小說呈現(xiàn)出絕望的美學(xué)傾向。
朱山坡小說中的絕望,首先表現(xiàn)為人的絕望。《空中的眼睛》中的麻麗冰,為了能吃上白花花的米飯,喪夫后立即委身嫁給了碾米機(jī)房的闕富;為了能吃上使臉白胖、皮膚細(xì)嫩的豬肉,將自己的身體當(dāng)作交易籌碼給了肉行的屠夫;為了討好新來的鎮(zhèn)長,不僅賠上了身體、名聲還差點把兒子的性命給搭上了;為了生存,在攆出谷鎮(zhèn)后不得不靠撿垃圾為生,但最后還是失去了最疼愛的兒子。類似還有《米河水面掛燈籠》中的闕大胖一家,或被淹死、或被車撞死,或因故意殺人而被判死刑,隨處可見死神的足跡。假如說,《空中的眼睛》和《米河水面掛燈籠》主要表達(dá)的是個體的絕望,那么,《捕鱔記》所寫的絕望則超出了個體而屬于整個年代。小說以“我”為敘述視角,講述了饑荒年代中父子倆的捕鱔經(jīng)歷。父子高舉火把沿河蜿蜒而行,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能吃的東西,包括樹皮草根和鱔魚、蛇。待走到河盡頭,看見的卻是媽媽與眾人的一具具白骨。腹中無一物的父子倆,很快也餓死化成了白骨。從個體到年代的絕望,朱山坡逐一揭開了人類生存境況的脆弱、困頓、無助。

其三,朱山坡的小說結(jié)構(gòu)往往令人意想不到,體現(xiàn)出一種超出常理之外的奇崛之美。

朱山坡小說中的奇崛美,主要表現(xiàn)為結(jié)構(gòu)情節(jié)的大轉(zhuǎn)折。小說《等待一個將死的人》具有精心安排的起承轉(zhuǎn)合結(jié)構(gòu)。篇首的一段文字,言簡意賅。“春天剛過,突然來了一場洪水,把米河上的石拱橋沖垮了,還來不及修復(fù),便傳來闕越要回來的消息,村子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大人不讓孩子們亂跑,嚴(yán)令他們待在屋里。正在搭橋的人似乎也有些不知所措,中午時分,懶散地躲到山坡上的樹蔭下,等待一個將死的人通過他們草草搭起的浮橋。”當(dāng)中,洪水沖垮米河上的石拱橋、一個將死的人闕越要通過草草搭起的浮橋,這幾個詞語和句子暗藏豐富的信息量,不僅交代清楚故事的緣由和主旨——為什么(水沖垮橋)、做何事(將死的人要過橋),而且通過“來不及”、“嚴(yán)令”、“不知所措”等形容詞的使用渲染了緊張、慌亂的氣氛,為故事進(jìn)一步展開造勢。可以說,這段篇首文字作為整部小說的“起”部分,非常出彩,預(yù)示著后面精彩的故事情節(jié),成功吸引讀者的眼球和好奇心。在接下來的“承”和“轉(zhuǎn)”部分,作者承接篇首引出的事件,鋪設(shè)了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得了癌癥的闕越返村回家等死,另一條卻是哥哥出村到鎮(zhèn)上為患病母親購買救命的藥。這兩個線索,一條回村(往死),一條出村(往生),看似相互分離互不相干,但因二者都要趟過米河上的橋而發(fā)生交織、纏繞,推動故事情節(jié)向著出乎意料的方向發(fā)展。在眾人的幫助下,將死的闕越歷經(jīng)艱險渡過浮橋,如愿回到家中靜養(yǎng)等死,但沒想到奪去其生命的并非病魔,而是其兒子忍受不了父親對母親的辱罵后的槍殺。與此同時,哥哥出村到鎮(zhèn)上抓藥,發(fā)現(xiàn)藥鋪少了一味藥,放棄配藥無功返回村子,因與搭橋的人發(fā)生口角而不得渡河,便沿著河岸往南走,直到永遠(yuǎn)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外。小說的最后,兩條線索并行浮現(xiàn)——闕越死后其妻兒被一個身材魁梧的外鄉(xiāng)漢子接走、母親等不到哥哥及其救命藥的回來而奄奄一息,再次應(yīng)和篇首橋斷和人將死的主旨。顯然,橋與人均帶有深刻的寓意。橋是米莊人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橋斷,通道斷,意味著闕越、媽媽等米莊人生命的終止,而闕越妻兒被外鄉(xiāng)人接走又似乎預(yù)示著新的人生的開始。這一關(guān)于生命的深刻理解,鑲嵌在其小說結(jié)構(gòu)中,出乎意料且耐人尋味。
此外,朱山坡小說中帶有詭異之氣的結(jié)局,亦不失為一種極具個人化標(biāo)簽的奇崛美。小說《陪夜中的女人》的結(jié)尾,陪夜的女人按照當(dāng)?shù)仫L(fēng)俗,將垂死的老人背到堂屋。老人的離世標(biāo)志著女人陪夜工作的結(jié)束。這個名字和身份均未明的女人,如同第一次駕船來到村里般,也是自己開船離開村子的,“就在轉(zhuǎn)眼間,船消失得無蹤無影,只剩下浩瀚的江水和四向逃逸的霧氣”。同樣以“消失”作為結(jié)局的,還有小說《躺在表妹身邊的男人》。當(dāng)表妹最終意識到之前在車上躺在其身邊蒙頭大睡的男人是一具尸體時,頓時陷入無法自控的癲狂狀態(tài),“表妹滿臉驚恐,猝地扔掉雙拐,雙手拼命插頭發(fā),歇斯底里地往車站門外狂奔,但由于身體失去平衡,幾次摔了跟頭,甚至嘴巴啃了泥土,臉也摔破了,但她仍狂躁不堪,爬起來又跑。……只有一條腿的表妹像折翅的鳥,最后重重地摔倒在一道狹窄的臭水溝里,假如是夏天將會驚起一堆蒼蠅”。而在車上一直蒙騙表妹的小男人,則忙于指揮人們抬其表哥的尸體回家,“小男人肥大的西服披在他的身上看起來十分夸張、滑稽,寒風(fēng)將他的頭發(fā)吹成了雞窩。盡管他的左腿有點瘸,但他走得很快,一會便隨抬擔(dān)架的人連同擔(dān)架上的男尸一起消失在小巷盡頭”。這些小說文字,生動地為讀者呈現(xiàn)了謎一樣的主人公消失隱去的情景,極富鏡頭畫面感,為小說增添了幾分神秘、詭異的氣息,奇崛而不落俗套。
四、結(jié)語:邊城的苦難與溫情
或許是朱山坡幼年經(jīng)歷和觀察到的邊城生活過于艱苦,其從粵桂邊城出發(fā)的小說創(chuàng)作,往往與苦難有關(guān),殘酷、無奈卻又充滿溫情。

在經(jīng)歷了短暫的冷酷裸現(xiàn)苦難的創(chuàng)作階段后,朱山坡轉(zhuǎn)變了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他并未停留在展示苦難景象的層面上,而是深入到苦難的承受者——鄉(xiāng)親們的內(nèi)心世界,用悲憫的關(guān)懷、溫和的筆法來書寫鄉(xiāng)親們心底的善良和溫情,還給以鄉(xiāng)親們寶貴的人格尊嚴(yán)。

此后,朱山坡延續(xù)了對鄉(xiāng)親們善良和尊嚴(yán)的書寫。在《爸爸,我們?nèi)ツ睦铮俊芬晃闹校焐狡峦ㄟ^兩條敘事線索——一對鄉(xiāng)村父子與一位懷抱小孩的女人——的平行展開和交疊重合,編織了一個關(guān)于惻隱之心的故事。最初,互不相識的父子與女人因同坐一條船而發(fā)生交集,喪妻多年的父親察覺了女人的餓意和疲憊,掏出身上僅有的糧票相送,但女人拒絕了父親。隨后,父子與女人因船到岸的緣故而分開各趕各的路。在趕路的過程中,父親發(fā)現(xiàn)了女人瘸腿的身體缺陷,“似乎動了惻隱之心,幾次靠近她,但不知道應(yīng)該為她做點什么”。再后來,父子與女人在氮肥廠再次相遇,原來父親的兄長和女人的丈夫均被判了死刑且都在此處享用上刑場前的最后一餐。父親與女人為了讓各自的孩子與素未謀面的親人見上一面,不僅得花去原先預(yù)留買回程車票的錢,而且還得腳踏上人梯的肩膀才夠得著窗戶往里看犯人的用餐。在女人因為腿的殘疾無法踏到人梯肩上時,父親突破了向來懦弱的個性,果敢地從周圍冷漠旁觀的人群中挺身而出,先是用語言鼓勵女人,后用自己的身體艱難地幫助女人及其孩子完成了見面。見面結(jié)束后,父親與女人再次不辭而別各奔回程,父親此時卻因目睹了女人的不易而覺悟般地爆發(fā)了內(nèi)在的責(zé)任感,向兒子叫嚷著:“你沒看見她一整天沒吃飯了?你沒看見她的孩子病了?你沒看見她的左腿瘸成那樣……”“她是你媽媽……”“我們必須把她帶回家去……”這部作品通過描寫父親前后的變化——從惻隱之心到果敢?guī)椭俚綆Щ丶业呢?zé)任擔(dān)當(dāng)感,刻畫了一個同處困境卻不忘幫助別人的鄉(xiāng)親形象,同時也讓人們對這位父親體面而富有尊嚴(yán)的舉動心生敬意。此外,在《騎手的最后一戰(zhàn)》中,朱山坡化用了騎手的絕妙比喻,使用詩意與激情并存的語言,描寫了一位從鄉(xiāng)土走出來的老軍人在飽受病痛折磨的人生最后時刻與命運所作的搏擊——“父親騎著馬追隨火車消失在漫長而黑暗的隧道里,再也沒有回來”。這一充滿畫面質(zhì)感的精彩搏擊,樹立起一個偉岸的父親形象。他張揚(yáng)著挑戰(zhàn)困難的大無畏精神,散發(fā)著陽剛的男性氣息,給人以肅穆的尊嚴(yán)感。
仔細(xì)閱讀這些作品,不難發(fā)現(xiàn)朱山坡通常設(shè)置了生與死交界的特殊情境來凸現(xiàn)鄉(xiāng)親們的善良和尊嚴(yán)。或許對于朱山坡而言,底層鄉(xiāng)土的生存是艱辛的,處處布滿了苦難與不幸的陷阱,鄉(xiāng)親們終日疲于奔命應(yīng)付生活的困境,被裹挾進(jìn)生活的強(qiáng)大慣性中而暫時遺忘了人之初的善和人之為人的尊嚴(yán)。只有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才得以從容停下奔波的腳步,浮現(xiàn)心靈深處的善和尊嚴(yán)。也正因為這些善和尊嚴(yán)的書寫,朱山坡還原了一個更真實的邊城鄉(xiāng)土世界——不僅存在苦難的悲愴,還存在苦難所無法磨滅的人間溫情。期待朱山坡今后創(chuàng)作出更多讓人感動和溫暖的佳作。
注釋:
①梁冬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論朱山坡小說中的鄉(xiāng)土世界》,《南方文壇》2008年第3期。
②梁冬華:《書寫鄉(xiāng)土世界中的尊嚴(yán)和靈魂——再論朱山坡的小說創(chuàng)作》,《廣西文學(xué)》2014年第1期。
③邱華棟:《螺螄粉與黃皮果——談朱山坡的小說》,《文學(xué)報》2016年1月17日。
④孤云、朱山坡:《訪談:不是美麗和憂傷,而是苦難與哀怨》,《花城》2005年第6期。
⑤朱山坡:《我的名字就叫故鄉(xiāng)》,《廣西文學(xué)》2009年第8期。
⑥朱山坡:《米河水面掛燈籠》,《小說界》2006年第2期。
⑦朱山坡:《我的名字就叫故鄉(xiāng)》,《廣西文學(xué)》2009年第8期。
⑧唐詩人、朱山坡:《成為一個有情懷的作家——朱山坡訪談》,《創(chuàng)作與評論》2015年11月號下。
⑨李遇春:《為民間野生人物立傳的敘事探索——朱山坡小說創(chuàng)作論》,《南方文壇》2015年第2期。
⑩橙子:《朱山坡:從不同視角觀察新鄉(xiāng)土》,《南寧日報》2006年6月16日。







廣西藝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