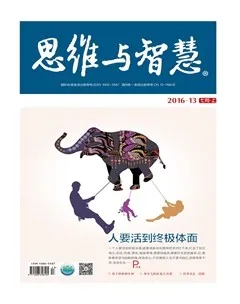山岡上,那輪明月
曹春雷
已是晚上八點(diǎn)了,孩子還沒有放學(xué),我在校門口徘徊,能做的,只有等待。陪我等的,是頭頂那輪月亮。閑著沒事,那就抬頭看月亮吧。很久沒有這樣認(rèn)認(rèn)真真看過(guò)月亮了。看著看著,就想起二十多年前,母親也是這樣站在校門口,頭頂一輪月亮在等,她等的,是我。
那時(shí),我在山腳下的一所中學(xué)里讀初一。學(xué)校很簡(jiǎn)陋,沒有宿舍,學(xué)生要跑校,讀完晚自習(xí)后回家。我家與學(xué)校隔著一座山岡,我家在山岡西邊,學(xué)校在山岡東邊,隔著五六里路。
晚上放學(xué)后,我急急跑出校門,一眼就能看到,在一棵老槐樹下,母親正靜靜地站在那里,等我。我說(shuō),娘,回家吧。娘應(yīng)一聲,哎,回家。于是,娘倆踩著月光下自己的影子,一路說(shuō)說(shuō)笑笑地,走在土路上。
要步行越過(guò)山岡。山岡上樹很茂密,是一些松樹或者柏樹。月光下,樹林幽深。時(shí)常有貓頭鷹“咕咕喵,咕咕喵”的聲音傳來(lái)。或者有山雞被明晃晃的月光照醒,夢(mèng)囈似的,咯咯咯地叫上幾聲,之后,樹林又歸于沉寂。
林子邊上埋有墳?zāi)梗滋鞎r(shí)遠(yuǎn)遠(yuǎn)看去,一座座饅頭似的土丘擠在那里。若是在夏天,墳?zāi)股系奈灮鹣x特別多。那時(shí),聽的鬼故事多,我總認(rèn)為那是鬼火,很害怕。每次經(jīng)過(guò)墳地邊,我都拽著母親的衣角,緊跟在她身后,話也不敢說(shuō)了。母親說(shuō),甭害怕,那是螢火蟲呢。可我還是害怕。
有一次,母親說(shuō),你唱個(gè)歌吧,唱什么都行。我哪能唱得出來(lái),心里只有害怕了。母親說(shuō),那我唱。她清清嗓子,就唱,唱的是《月亮走,我也走》,當(dāng)年很紅的歌曲,村里的大街小巷都傳唱。“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說(shuō)實(shí)在的,母親的嗓子有些啞,唱的歌并不好聽。但在當(dāng)時(shí),卻讓我慢慢放松了下來(lái)。
到后來(lái),母親不唱了,我開始唱。山岡上,我的歌聲浸染在銀色的月光里,灑在叢林里,飄到遠(yuǎn)處去。我總懷疑,如果月亮上真有嫦娥,那么她一定會(huì)聽到我的歌聲的。每唱一首,母親就為我鼓掌。
走著,唱著,山岡就翻越過(guò)去了,看到了村子里的燈火。到家了。
多年后,母親說(shuō)起當(dāng)年去接我時(shí),她獨(dú)自一人經(jīng)過(guò)山岡上那片墳地時(shí),也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害怕得很,即使是在冬天,手心也會(huì)出汗。我那時(shí)才想起來(lái),為什么我下了晚自習(xí)后見到母親,握著她的手時(shí),她的手心總是濕的。
如今,故鄉(xiāng)的山岡還在,山岡上的那輪明月還在,山岡下村莊的那處老宅里,母親還在等我,像二十多年前在校門口那樣,等我。只不過(guò),現(xiàn)在她是在等我從城市回家。
——我,該回家了。
(編輯 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