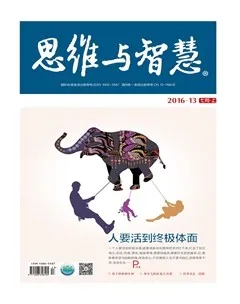人淡如菊
遠古的水草
是花必有色,且大抵有香,可以說,花是植物的升華,花開必為張揚,是花就必不能淡。淡的是人。人淡如菊,其實是菊淡如人。人或有以此意為名者,或曰淡人,或曰淡如,言外隱著一個“菊”字。
《詩品》曰:“落花無言,人淡如菊。”都是經歷后的靜水流深、絢爛后的平淡安妥,蕭疏如秋林,靜閑如秋云,就如愛它的陶令。陶淵明不是開始就歸隱的,他在失望后離開了,在那年的東籬,一叢菊安靜地開著,像一群忘歸的月光,深秋的月光。陶淵明因之悠然見了南山,見了自己。從此,菊又叫“陶家菊”,菊成了隱士花,被賦予了“高雅、堅貞、淡泊”的精神品格,被打上了“淡”的文化符號,如梅之于林和靖、竹之于王子猷,千百年來,相傳不疑有他。
然,菊是痛苦的,是等待的,熟悉中國隱士心態的人,或許能懂。
“隱”是體制外讀書人最有面子的生存方式,就像王猛、就如諸葛亮,進可以此兼濟天下,退可因此獨善其身,這是最后的尊嚴。就像季節已到深秋,尚且懷抱入世之心的菊,心知這是最后開花的時光了,飛霜不遠,開還是不開?它選擇了開放,但態度依然是不亢不卑的。我已經開了,招賢的官員來還是不來?如果來,花開就是迎賓;如果不來,開花就是一場風雅。
等來劉備的隱士畢竟很少,很多花事只是圈內人一次酒會,唱和的還是那幫子白衣或青衿。陶淵明掛冠而去后,衣食一直堪憂,便是風雅到重陽采菊時思酒,也靠江州刺史王弘派來白衣使者相送——但這不能改變中國讀書人的行世方式,毛遂不可能成為他們的榜樣,登臺演講永遠是古希臘人的方式。對中國讀書人來說,無論是以退求進的作秀,還是不合作的凜然,以菊為喻,都是一種悲壯。
“此花開盡更無花”,菊花的開,是一種“姑且如此”的態度,不抱必欲得到的堅決,因此難以熱烈,是一種站在秋風里遠眺的姿態,有固然喜,無不足悲,神情蕭散淡然,這是失意讀書人的心態,投放于菊,便是人淡如菊。
與霜雪相伴的菊,寧可抱香枝頭死的菊,成了他們的人生觀照,他們認領了菊。從仕進到退隱,退隱之后是若有若無的等待,就如從牡丹道菊花,再后面呢?是醒悟后的超脫,或希望后的絕望,或入佛,或入道,或儒釋道之間,代表的花是梅,決絕了人間溫暖,有鶴相陪,欲登仙籍——而眉間心上,依然有那種“淡”,菊的淡。它固定在菊的身上,影響了中國人,塑造著中國人特有的心理、情操和價值取向。它是劉伶的酒陸羽的茶張志和的三江五湖,是士人的狂狷,是女子的林下風致,李易安的“瘦”,是謝道韞的疏朗,是那種你我都有的骨子里的清冷。
(編輯 花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