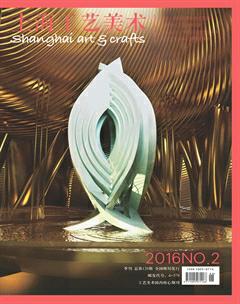技藝與審美的跨界聯合
朱煜宇



提起孫良,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位油畫家。他的油畫作品從“八五新潮”的中國前衛藝術時期開始,就不斷出現在國內外的藝術視野中。而同時,他也是一位頗熱衷于嘗試各種媒材甚至跨界合作的藝術探求者。從油畫到國畫、裝置,或是對復合媒材的使用,孫良的“好動”幾乎成為他創作的必然,玻璃藝術作品即是他這些多媒材嘗試的一個重要部分。
偶然亦必然的玻璃藝術創作之旅
孫良與玻璃藝術的交集源于藝術門畫廊主人林明珠在2002年左右引進大量的國際知名藝術家到上海舉辦展覽,其中就包括現已故的捷克國寶級設計師博雷克·西派克(Borek Sipek)。在上海參展的同時,博雷克也關注著中國藝術家們的創作動態。他在同孫良的碰面中直言,他認為孫良的繪畫最為適合玻璃藝術創作,也因此對孫良發出合作邀請。就在短短幾句言語間,孫良的捷克玻璃藝術之旅就這樣敲定了。也正是在博雷克的邀請及安排之下,孫良在捷克開始了最初但也是最為關鍵的玻璃創作時期,他不僅進行了新的媒材創作,更找到今后與他配合最為緊密的又一捷克玻璃大師——伊日·巴喬(JiriPacinek)。巴喬從著名的AJETO玻璃工廠開始,以出眾的才華、玻璃工藝制造的豐富經驗及藝術上的野心開創自己的玻璃品牌,并在捷克成立了自己的玻璃工作室。
孫良對玻璃藝術的興趣大概可以從早年去國外參展時接觸歐洲玻璃作品開始,如1993年他在威尼斯參加展覽購買了許多玻璃作品回國,而1996年其瑞典的藝術家朋友亦提出合作玻璃作品但未果,等等。雖然博雷克的邀請是偶然的事件,但在孫良的創作經驗里,對玻璃藝術的涉足也是必然。因而對當時毫無技術認知的玻璃藝術,孫良并沒有感到不安。
孫良坦言初到捷克時對要做什么、怎么做,都沒有太多的想法。但當他進入玻璃工作室看到滿柜的博雷克作品時,精良的工藝以及豐富的種類讓他驚嘆博雷克的創作力。博雷克玻璃作品的深入全面令人震撼,這也促使孫良必須思考:在幾乎所有的造型、設計都已被創作出的狀況下,他可以做些什么?在短暫的參觀和聊天之后,孫良就開始將平面繪畫中的具象造型轉化成設計草稿,并與巴喬等玻璃工藝大師開始腦力與手力的激撞。仔細觀察孫良的玻璃作品就可以發現作品充滿了動態的細節,如在局部的收尾處,孫良都試圖以干凈利落的弧度或仰角來達到某種穩定或飄逸的效果。這些細節要求對于一次成型的熱制玻璃做法提出了一定的技藝要求。而在日后與臺灣玻璃工藝合作的時候,孫良發現這些細節則相對難以實現,設計的造型也隨之變化,一方面必須符合在地文化的認知,創作諸如海星等符合臺灣自然人文環境的內容,另一方面也對工藝提出思考:在不同的工藝條件下,藝術與設計的融合能夠達到多大的效應。
藝術X設計>跨界
當代藝術家跨界進入設計、工藝美術已不再是新鮮事,大約最為著名的就是村上隆與奢侈品牌LV的合作,之后諸如周鐵海、楊福東、丁乙等中國當代藝術家也都加入此行列。在這種跨界越來越趨向于商業化操作的時候,藝術家與設計、工藝美術的跨界一定是成功嗎?在孫良的觀念中,只有“好的想象”和“好的技術”一同發揮創造力才有好的作品出現。
在文化結構和所專注的創作領域上,孫良和巴喬這兩個幾乎并無太大共同性的藝術家卻在合作中共同獲得各自創作上的提升。孫良在巴喬的精湛技術支持下,將他繪畫中最具符號性的神話形象,如鳳凰、人鳥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幻化想象,轉化至更具存在感的現實空間,也散發出更為濃重的超現實意味。孫良的奇思幻想得以實現,也離不開巴喬的藝術追求和極高的技藝。作品的難度不僅在于一次成型的熱制工藝,更在于手工藝者必須在制作過程中快速判斷和調整作品的局部呈現,這更要求手工藝者具有一定的審美感覺。正是在巴喬具有審美判斷力及精良手作的條件下,孫良的玻璃藝術作品如其繪畫作品一樣充滿了張力和想象力。
從架上繪畫二維空間的視角轉換到立體作品的想象與實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對孫良來說,顯然這并不是個難題。除了過硬的美術功底之外,孫良更透過顏色來實現空間互補,以此形成具有其強烈個人風格的玻璃藝術作品。孫良的油畫作品曾被形容在粉紫色或幽藍色的背景下透出“女性的柔媚”和“孩童的爛漫”,似乎與他外表所展現的陽剛男子氣全然不同。但在他的玻璃藝術作品中,鮮明的對比色或具高反差的互補色在同一維度中平衡進行,于是本就具有魔幻色彩的動物或人之形象更顯視覺沖擊力。綜觀孫良的各種媒材作品,恐怕所謂的“柔媚”或“精怪”,是孫良在對媒材和創作內容的造型處理中所挖掘出的這些材料和內容的本質特性,就如他初入玻璃藝術領域隨心而創作所獲取的能量一樣,并無特定營造某種神秘特質來彰顯個人符號,而是在筆下引領出這些個人色彩罷了。但孫良善于為不同媒材挑選出不同的設計造型,他試著了解不同工藝所對應的作品呈現可能性,因應手工藝者不同的文化認知。
孫良并不認同將他的玻璃作品以雕塑的概念去看待,他在談到作品形態的時候,實用性、造型、色彩都是他關注的重點。對他而言,玻璃藝術作品的創作并無藝術與工藝的嚴格限制,但作為玻璃藝術作品的屬性而言,它都具有融入生活并具有生活實用的功能,這也就是在孫良多數的玻璃作品中都從實用性的器皿形式出發,而造型形象則是在器皿基礎上的延伸和融入。于是,在孫良畫布上有些失重而奇特的生命,在他的玻璃作品中卻變得輕曼而無違和感。如果說畫布上的神話形象或各種生命是孫良對現實生活的嘲諷,那么在他玻璃作品中的生命卻是對生活的美妙探尋。
拋磚引玉:勤于創作的工藝美術發展之醒思
孫良對藝術與設計間的融合出于他對嘗試各種媒材和形式的創作熱情。但談起孫良與工藝美術的結緣,必繞不過他在上海玉雕廠的那段經歷。玉雕廠傳統工藝的師徒環境以及如蕭海春這些臥虎藏龍的鬼才都給孫良提供了更多元的創作奇想和感知。
捷克對傳統手工藝的保護與傳承在玻璃藝術中的顯現就在于這并非只是官方系統的強制介入,而更多是在于師徒化以人情味為基礎的技藝及人文傳承。回應到孫良在上海玉雕廠工作的時代與環境,這種匠心純厚、師徒互動的連結仿佛提供了孫良頗為熟悉和舒適的創作環境,也多少為他的玻璃作品提供了外在環境的動力。
回到今天的中國工藝美術發展,圍繞在創新或堅持傳統的創作層面的問題,都已經不再單純是創作大環境的變遷。在過去類似上海玉雕廠這種多樣性的工作或創作環境不再的情況下,“跨界”的興起似乎比彼時行業間的混入更難以實現。在跨界促使業界彼此邊界的消融之狀況下,藝術也好,工藝美術也好,都不再是一個限制的名詞。比起商業性的嘩眾取寵或是對藝術家知名度的炒作,跨界更需要扎實的技藝以及超前且獨立的藝術想法。而在中國工藝美術界中,扎實、精湛的技藝并不難尋,如何發揮藝術想象則是重點。
跨界合作在孫良過去使用多樣媒材及涉及不同技藝領域的作品中,都可窺探到孫良對此所持有的積極態度。而孫良在上海玉雕廠的豐富經歷提供了他對藝術與設計融合的更敏銳感知。孫良也不停指出,他的玻璃藝術創作選擇了“揚長避短”,將技術問題留給設計師來控制,而自己則把握造型設計和最后的呈現內容。這種并非獨攬全局的創作觀使得孫良的玻璃作品無論在技藝層面還是藝術內涵層面都更具說服力。從孫良的藝術創作方面來看,他將藝術性和設計元素加入到實用性的作品中;反向而言,對設計師或手工藝者而言,又需如何將實用性提升至更具審美感覺的層面呢?這也就是孫良所強調的“品味”問題。對于今天中國工藝美術的創作者們而言,對美感而非技術問題的探討顯得更為重要和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