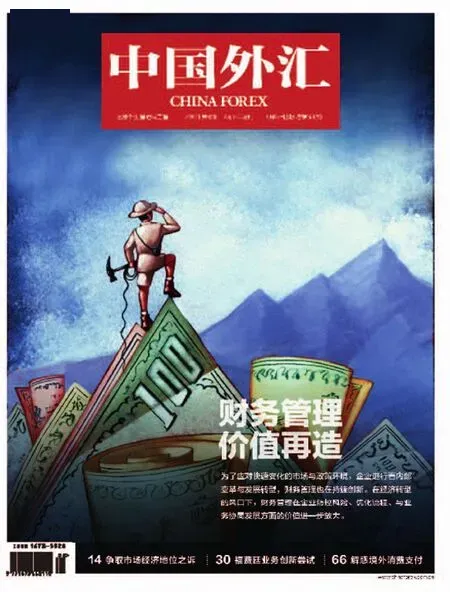決勝國際投資爭端
文/任清 編輯/丁小珊
?
決勝國際投資爭端
文/任清 編輯/丁小珊
為有效保護海外投資,我國企業在實施投資之初應妥善籌劃投資者國籍,在發生爭端后則應綜合運用最優的爭端解決方式,并在人力、預算等方面做好準備。
備受矚目的“菲莫亞洲公司訴澳大利亞案”于2015年12月17日暫告終結。仲裁庭當天做出“管轄權和可受理性裁決”(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裁決其對于菲利普?莫里斯亞洲公司(下稱“菲莫亞洲公司”或“申請人”)針對澳大利亞煙草平裝措施提出的訴請并無管轄權,駁回該公司的訴請。
事實上,近年來針對澳大利亞煙草平裝措施的法律挑戰頻頻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當中——烏克蘭、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古巴和印尼五國先后在WTO起訴了澳大利亞的煙草平裝措施;2011年12月,菲莫國際、英美煙草、日本煙草和帝國煙草等跨國煙草公司分別向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提起訴訟。
盡管菲莫亞洲公司在本仲裁案中以失利告終,但煙草系列案的最終結果尚不可知,且菲莫公司的“維權”行動對中國“走出去”企業有不少借鑒意義。
“菲莫亞洲訴澳大利亞”仲裁案
作為全面控煙計劃的一部分,澳大利亞于2010年4月開始醞釀、于2011年11月制定并于2012年12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1年煙草平裝法》、《2011年煙草平裝條例》(2012年修訂)和《2011年商標法修正案(煙草平裝)》,對卷煙、雪茄等煙草產品及其零售包裝正式實施平裝要求(又譯為“素包”),包括不得使用商標、地理標識,必須采用特定的卷煙紙、包裝材料、尺寸和樣式等。菲利普?莫里斯國際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卷煙生產公司。本仲裁案的申請人是該公司注冊于中國香港的子公司——菲莫亞洲公司。菲莫亞洲公司全資擁有注冊于澳大利亞的菲莫澳大利亞公司,而后者又全資擁有注冊于澳大利亞的菲莫有限公司(PML)。PML公司在澳大利亞從事煙草產品的生產、進口、營銷、分銷以及向新西蘭和太平洋島國的出口。
菲莫亞洲公司認為,澳大利亞煙草平裝措施禁止在煙草產品上使用其知識產權,使其全資子公司由品牌產品生產商轉變為大宗產品生產商,實質性地降低了該公司在澳大利亞投資的價值,構成對投資的征收。菲莫亞洲公司請求仲裁庭判令澳大利亞暫停實施相關平裝法案并賠償該公司遭受的損失。
2011年7月,菲莫亞洲公司基于中國香港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投資保護協定(下稱“香港-澳大利亞BIT”),向澳大利亞提交“爭端通知”。2011年11月,菲莫亞洲公司依據聯合國貿法會仲裁規則向澳方提交“仲裁通知”,啟動仲裁程序。仲裁庭由國際常設仲裁院(PCA)提供行政支持。2011年12月,澳大利亞表示將提出管轄權異議,并要求將管轄權作為初步問題先予審理。2014年4月,在經過多輪書面陳述和聽證會之后,仲裁庭決定分階段審理本案,即先審理仲裁庭是否對本案具有管轄權。2015年12月17日,仲裁庭作出裁決,以無管轄權為由駁回了菲莫亞洲公司的訴請。
國籍籌劃可以通過第三國轉投資,也可以將現有投資轉讓給位于第三國的關聯企業,還可以是將原來的投資者注入第三國關聯企業使其成為后者的子公司。
剖析裁決關鍵點
該案仲裁裁決的全文目前尚未公布。盡管尚無法知曉仲裁庭的推理和論證過程,但根據PCA網站公布的此案相關信息,并結合澳大利亞此前提出的管轄權異議,可以大致推斷仲裁庭做出無管轄權決定的基本思路。
澳大利亞在本案中主要提出了以下三項管轄權異議:
第一,投資未經批準。香港-澳大利亞BIT第1(e)條規定,在一方境內的投資應經該方依據其適用法律和投資政策予以批準。根據澳《1975年外國收購和接管法》,投資者應向財政部長提交投資申請書及補充信息,而財政部長有權在一項投資“有悖于國家利益”時禁止該投資。澳方認為,申請人在澳大利亞投資(收購菲莫澳大利亞公司的股份)的真實目的是為了獲得在BIT下起訴澳方的資格,而這一目的與澳國家利益相悖。申請人在其投資申請書中提交了“錯誤和誤導性”信息,由此而獲得財政部長不予禁止的決定。因此,申請人的投資申請書是無效的、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財政部長以此為基礎做出的決定在法律上應被視為“根本沒有決定”。申請人的投資因而不能滿足香港-澳大利亞BIT第1(e)條的要求。
第二,爭端先已存在。澳方認為,在申請人于2011年2月收購菲莫澳大利亞公司之時,澳大利亞政府已經先于2010年4月公開宣布將在2012年之前實施平裝要求,而PML公司及其最終母公司菲莫國際公司從2009年到2011年一直對此表示反對,因此爭端在申請人做出投資之前已經存在,進而不在香港-澳大利亞BIT第10條(投資爭端解決)的適用范圍之內。
第三,濫用權利。澳方認為,即使本爭端在BIT第10條的適用范圍內,申請人通過重組其投資以就“既存或合理可預見”的爭端獲得BIT的保護,也構成對第10條下權利的濫用。澳方稱,在申請人重組其投資時,爭端即使不是業已存在,也已經具有高度蓋然性而可以被合理預見。
仲裁庭可能綜合考慮了以上三項異議的合理成分,然后做出了無管轄權的裁決;而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很可能是“濫用權利”異議。
在既往的多起投資仲裁案例中,仲裁庭均以投資者濫用權利為由支持了被申請人的管轄權異議。如在Banco公司訴剛果案中,加拿大(非ICSID公約締約方)的一家公司將其在剛果的投資轉讓給在美國的關聯公司。鑒于在轉讓之時爭端已經產生,且美國公司受讓投資后幾天內就啟動了ICSID仲裁程序,仲裁庭裁決其對該案無管轄權。又如在Phoenix公司訴捷克案中,捷克投資者在已經與捷克政府發生爭端的情況下,為了獲得更好的BIT保護在以色列成立了Phoenix公司,并將其在捷克的投資轉讓給新成立的公司,且后者很快提起仲裁。仲裁庭認為,Phoenix公司的投資不是為了在捷克從事經濟活動而是為了起訴捷克政府這一唯一目的,構成對投資保護制度的濫用。
縱觀本案中相關事件的先后順序(見附圖),仲裁庭可能認為,在菲莫亞洲公司收購菲莫澳大利亞公司時,爭端已經存在或者可以合理預見,菲莫亞洲公司的收購行為(或者菲莫國際公司在集團內部的重組行為)正是為了獲得依據香港-澳大利亞BIT要求而起訴澳方的資格,因而構成權利濫用。

“菲莫亞洲訴澳大利亞”案相關事件簡圖
對中國“走出去”企業的借鑒
第一,綜合運用國內法院、投資仲裁和WTO爭端解決機制等多種法庭(forum)維護自身權益。
繼澳大利亞之后,愛爾蘭、新西蘭、英國、加拿大等國已經或正在考慮對煙草產品實施平裝要求,其他國家也可能跟進。多米諾效應可能對跨國煙草公司的利益產生巨大影響。正因如此,跨國煙草公司在多種法庭發起了法律挑戰。類似地,當中國“走出去”企業的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時,應綜合運用多種救濟途徑。
各種法庭各有其特點,所適用的實體法律和程序規則不同,在獨立性和中立性上也存在差異:
國內法院判決往往更為直接切中爭端要害且易于執行,但通常適用東道國法律且可能存在保護主義,因而不一定符合投資者的最佳利益。
WTO爭端機制主要解決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有關的爭端,但由于投資外延的廣泛性以及投資與貿易的日益融合,與投資有關的不少爭端也可以提交WTO。相比其他法庭,WTO爭端機制在程序上的一大好處是不收取訴訟費,但起訴方只能是WTO成員方的政府,因此投資者需要說服本國或其他國家的政府提出起訴。
投資者-國家仲裁近年來被外國投資者尤其是美歐企業頻繁使用,累計案件已多達600余起,且投資者勝訴的案件(含部分勝訴或和解)超過半數。中國大陸企業迄今提起的投資仲裁也有黑龍江經濟合作公司訴蒙古、平安訴比利時和北京城建訴也門等三起案件。
第二,投資者國籍應盡早籌劃和實施,避免因權利濫用被判無效。
在本案以及前述的Banco訴剛果和Phoenix訴捷克等案件中,投資者都是在爭端已經產生或者可以合理預見之時才進行國籍籌劃,最終被仲裁庭認定為濫用權利。
實際上,通過國籍籌劃而使投資者獲得更優的條約保護是被允許的。例如,在美孚公司訴委內瑞拉案中,美孚公司在委內瑞拉的投資原來是通過注冊于美國特拉華州的子公司實施的;在與委內瑞拉政府就所得稅等問題發生爭議后,美孚公司對其投資進行重組,在荷蘭新成立一家控股公司作為特拉華公司的全資母公司;在美孚公司完成重組后,委內瑞拉對美孚在委投資實施了國有化。美孚公司依據荷蘭-委內瑞拉BIT提起ICSID仲裁程序,獲得了仲裁庭支持。仲裁庭指出,對于“未來的爭端”而言,通過重組投資來獲得特定BIT的保護是“完全合法”的。
迄今,中國已與110多個國家締結了投資保護協定,在數量上僅次于德國,居世界第二。但由于很多協定簽訂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保護水平相對較低。如果投資目的國尚未與中國締結投資保護協定(未簽訂,或雖已簽訂但尚未生效)或者所締結協定的保護水平較低,則中國“走出去”企業應考慮盡早實施國籍籌劃以獲得其他條約的保護。
國籍籌劃的方式可以是通過第三國轉投資,也可以是將現有投資轉讓給位于第三國的關聯企業,還可以是將原來的投資者注入第三國關聯企業使其成為后者的子公司。國籍籌劃不能等到爭端已經發生或者可以合理預見時才進行,同時應遵守相關條約中“投資者定義”條款(例如有的條約含有“實質性經營”要求)和“拒絕授予利益”條款的規定。
第三,國際投資仲裁的專業性強、時間長、費用較高,投資者應及早聘請律師,并從人力、預算等方面做好相應準備。
很多BIT都有在國內司法救濟和國際投資仲裁二者擇其一的“岔路口條款”,如果投資者貿然在東道國啟動國內訴訟,很可能喪失國際投資仲裁的救濟途徑。
與國內訴訟和一般商事仲裁相比,國際投資仲裁的專業性更強,既涉及復雜的事實梳理、證據收集和損失定量問題,也涉及國際條約、習慣國際法以及東道國法律的解釋和適用,例如本案中涉及的爭端何時產生、國籍籌劃是否構成權利濫用、東道國投資審批的有效性、管轄權問題和實體問題是否應當分階段審理等。又如在Yokus訴俄羅斯案中,爭端雙方提交的書狀累計超過4000頁,同時還提交了8800份證據材料。
投資者應從爭端發生之初(甚至投資之時)即聘請國際投資法專業律師提供法律服務,以避免“走彎路”。僅就爭端解決而言,很多BIT規定中都有在國內司法救濟和國際投資仲裁二者中擇其一的“岔路口條款”,如果投資者貿然在東道國啟動國內訴訟,很可能會喪失國際投資仲裁的救濟途徑。律師的提早介入可以為投資者做通盤研究,制定最優的投資爭端解決方案,包括訴訟策略和時機。例如在平安訴比利時案中,仲裁庭駁回平安仲裁請求的主要理由是,平安在中比2009年BIT生效之前已經向比利時發出了“爭端通知”,因此該爭端不適用2009年BIT。
國際投資仲裁的另一個特點是時間較長、費用較高。在本案中,僅管轄權階段就用了四年時間,如果進入實體審理再考慮可能發生的撤銷程序,時長很可能翻倍。相應地,爭端雙方在仲裁庭費用、律師費、專家費和其他雜費等方面的支出也較高。因此,在重大權益遭受侵害時,投資者應具備“一戰到底”的決心和耐心,同時在人力和預算方面做好相應準備。通常來說,同時聘請外國律師和中國律師,可以顯著減少外國律師的工作時間,從而節省律師費支出。
作者系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