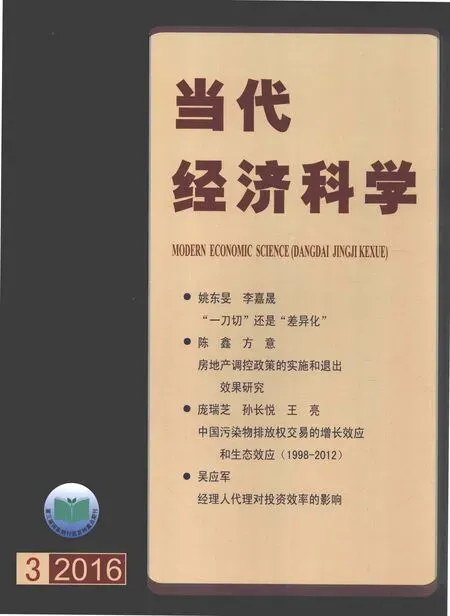并購行為與市場勢力:基于中國A股企業的分析
白雪潔,孫紅印,汪海鳳
(1. 南開大學 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 天津 300071;2.南開大學 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
并購行為與市場勢力:基于中國A股企業的分析
白雪潔1,孫紅印2,汪海鳳2
(1. 南開大學 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 天津 300071;2.南開大學 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
摘要:并購行為是否必然影響企業的市場勢力?在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市場有何不同?這是企業關心的重要問題。本文利用2007-2013年中國A股工業類上市企業面板數據,在新產業組織生產法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基于傾向得分匹配的雙重差分計量方法直接測度企業的市場勢力,考察企業并購行為對市場勢力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不同于其他市場上的顯著關系,在中國A股市場中,上市企業的并購行為與企業市場勢力的形成和變化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關鍵詞:并購行為;市場勢力;新實證產業組織
一、問題提出
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斷健全和經濟轉型的不斷深化,中國上市企業的并購活動日漸活躍,呈逐年上升趨勢。據統計,僅2014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企業發生并購事件超過4000次*數據來源:Wind資訊中國上市公司并購庫。。Weston認為從微觀視角來看,主導并購的企業發起并購活動的目標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解決委托代理中存在的低效率問題;二是獲得經營協同效應和財務協同效應; 三是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或者進行市場和資源再分配; 四是獲得被并購企業價值低估的好處; 五是獲得稅收優惠和傳送信息;六是形成并獲得市場勢力[1]。顯然,發起并購活動企業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通過并購形成并提高市場勢力,進而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可是,一個自然而現實的問題是,企業的并購行為真的能提高其市場勢力嗎?
目前理論界對這個問題并沒有統一的答案。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并購可以提高企業的市場勢力。Barton & Sherman[2]等人的理論分析表明,并購有助于主并購企業構筑進入壁壘,形成并提高其市場勢力。Vita and Sacher[3]等人的實證研究也顯示,企業的并購行為與其市場勢力存在正向關系,這種關系在計量上是顯著的。另一部分經濟學則認為企業的并購行為可能損害其市場勢力。Ellert[4]的研究表明,主并購企業希望通過并購獲得并提高市場勢力或者取得其它與公司規模擴大有關的非競爭性優勢的努力往往會遭到反壟斷力量的狙擊,因而不能實現其目標。Moeller[5]的實證分析顯示,并購有可能導致企業市場勢力被削弱,這或許是因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與職業經理人的目標不一致造成的。Focarelli and Panetta[6]利用銀行業企業數據的實證結果也表明企業的并購行為對其市場勢力存在負向作用。
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理論和經驗進行的分析,針對中國市場中企業并購行為的研究可以大致歸為三類。一類是上市公司并購活動的類型與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7-9];第二類是探討中國特色制度環境下企業并購行為選擇問題[10-12];第三類是中國本土上市公司跨國并購的績效分析[13-15]。顯然,在針對中國本土企業并購行為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獻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并購績效和并購類型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上,忽視了并購行為與市場勢力關系在中國市場上的表現。然而,正如Weston所言,企業并購行為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提升其市場勢力[1]。因此,基于中國制度環境下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并購行為與市場勢力的研究顯得尤為必要,這有助于科學評價中國市場上企業并購行為的得失利弊,對政府有針對性地制定經濟政策以及企業并購行為的選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為此,本文將利用中國A股工業類上市企業微觀層面面板數據,在新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實證模型,直接測度企業并購行為對市場勢力的影響,以此來探討中國市場上企業并購與市場勢力的關系。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具有以下特點: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在Konings et al.[16]模型的基礎上利用基于傾向得分匹配的雙重差分估計量方法測度市場勢力,有效克服了不可觀測因素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以及回歸過程中樣本選擇偏差和異質性偏差問題[17];另一方面,在結論方面與國外研究也有所不同,在中國市場中,企業的并購行為與其市場勢力的變動沒有顯著關系。亦即,企業通過并購實現提升市場勢力的目的并不一定能夠實現。因此,當企業希望通過并購提升市場勢力時,應該審慎。
本文余下的安排如下:第二章闡述企業并購與市場勢力的理論聯系,第三章構建測度模型并對樣本進行必要說明,第四章是實證結果及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作為第五章。
二、理論與聯系
企業的并購行為分為三種類型: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企業并購行為的類型不同,決定了其影響市場勢力的機制和路徑不盡相同。
首先是橫向并購,這種并購是指消費者相關、產品相互替代的企業合并在一起。橫向并購主要通過三條路徑影響主并購企業的市場勢力。其一,橫向并購導致的直接結果是在一定時期內減少了市場上的企業數量,在潛在進入者未進入市場之前,并購后的企業可以降低產品產量,而其他企業在短時間內無法提高產量。由此減少了產品在市場上的供應,從而提高了產品的市場價格,進而使其市場勢力得到提升[18]。其二,橫向并購能夠帶來成本節約。Lichtenberg and Siegel[19]等的實證結果表明,因為成本協作效應,橫向并購可以降低并購企業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借助成本優勢,并購后的企業可以降低產品價格至邊際成本,迫使其他企業因虧損退出市場。或者降低價格并保證價格降低幅度小于邊際成本的降低幅度,通過這種方式主動進行價格戰爭,而經營效率低下、無法有效降低生產成本的企業則無法跟進,從而失去市場份額,被迫退出市場。其三,橫向并購能夠實現并購后企業的規模經濟效應。Singal[20]的實證結果顯示,產品市場上并購后企業的市場份額達到一個較高的特定值時,就會顯著提升市場的反競爭效應,直接結果就是提高了企業的市場勢力。這是因為當并購后企業的市場份額足夠高時,一方面會顯著提升其對上下游企業的話語權,從而加大了潛在競爭者進入成本,形成進入壁壘,另一方面增加了合謀成功的可能性,進而提高其市場勢力。
其次是縱向并購,這種并購是指垂直的生產鏈中處于不同位置企業的合并。縱向并購影響企業市場勢力的脈絡同樣可以歸為三條。第一,如果一家企業并購了其上游企業(生產鏈中距離最終消費者較遠的企業)或下游企業(生產鏈中距離最終消費者較近的企業),那么企業可以向分銷商或需求方作出嚴格而可信的承諾:在未來提供穩定而充足的產品,即不會出現產品斷供和產品超額供應。因為產品斷供會增加分銷商的機會成本,給其聲譽帶來不利影響,而產品的超額供應會造成產品未來市場價格的降低預期,這會增加分銷商的盈利風險。因此,當上下游企業合并后,自然能夠在與分銷商的價格談判中占據主動,獲得較高價格,甚至有可能簽訂排他性協議,進而形成并提升自身的市場勢力[21]。第二,一個控制或影響了上游必需投入品價格的縱向并購企業,可以通過提高這種必需投入品的價格增加水平競爭對手的生產成本,進而將其逐出市場;也可以通過控制必需投入品的供應量將水平競爭對手至于不利境地,增加競爭對手的機會成本[22]。毫無疑問,無論是提高必需投入品的價格還是控制供應量都形成并提高了并購后企業的市場勢力[23]。最后,縱向并購可以避免經濟效率的損失。在發生縱向并購之前,幾家企業分開生產,那么每家企業都會擁有局部的市場勢力并可能獲得較高價格,從而降低了這幾家企業的總收入以及整個經濟體系的效率,在縱向并購的相關研究中,將這種損失稱為“二次邊際化”[24]。發生縱向并購以后,幾家企業變成了單一的決策主體,一些交易成本被節省,一些不利的外部因素被內部消化,這就降低了并購后企業的生產成本。成本優勢自然可以構成進入壁壘,一方面可以幫助并購后企業在水平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另一方面阻止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達到提高市場勢力的效果。
第三種是混合并購,這類并購是指產品沒有明顯替代關系和互補關系的企業間的合并。混合并購主要通過范圍經濟和降低交易成本來影響并購后企業的市場勢力。在混合并購后出現的多元化綜合性企業中容易實現范圍經濟[25]。因為這類企業具有運用相同的投入產品和生產線生產出一系列產品的能力,例如在可口可樂并購匯源后,可口可樂的生產線可以用于生產后者;同樣的市場營銷可以給企業生產的各類產品銷售帶來有利影響,并且一系列的廣告和促銷活動形成的品牌聲譽及忠誠度可以被各類產品分享;各類產品同樣可以運用企業的研發成果。至于交易成本,包括尋找原材料的搜索成本、供應合同的協商、監督和執行成本,特別是特殊的資產和知識密集型的資產交易時產生的交易成本,這些交易成本將在混合并購后被節省[26]。范圍經濟和節省交易成本提高了并購后企業的生產效率,顯著降低運營成本,保證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并形成市場勢力。此外,并購企業具有利用搭售或捆綁手段將一個市場中的市場支配力傳遞到另一個市場的能力和動機,從而形成進入壁壘,進行市場封鎖、形成市場勢力[27]。
三、模型構建
(一)基準模型
本文研究建立在Konings et al.[16]模型基礎上。Hall從標準生產函數出發,構建了最基礎的市場勢力測度模型,但是該模型不能排除不可觀測的生產率要素對投入產生的沖擊。Konings et al.[16]利用以價格為基礎的原始和對偶索洛余值的共同部分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得到了本文的基礎模型:
(yit+pit)-αLit(lit+pLit)-αMit(mit+pMit)-(1-αLit-αMit)(kit+pKit)=βit[(yit+pit)-(kit+pkit)]
(1)
其中,pLit、pMit、pKit和pit分別是工資、原材料投入、資本價格以及產出價格的增長率,βit是企業i在在時間t的勒納指數,本文用來度量市場勢力。
根據(1)式,只要獲得企業產出值(pityit)、勞動力投入(pLitlit)、原材料投入(pMitmit)和資本投入(pKitkit),就可以計算出市場勢力。
用dY定義方程(1)的左端,表示對偶索洛余值與原始索洛余值的差,用dX表示方程(1)的右端,再加上一個白噪聲誤差項υit,由此可得到一個簡單易用的方程:
dYit=βitdXit+υit
(2)
(2)式是本文實證模型的基礎。
(二)雙重差分估計模型
本文目的在于探討企業的并購行為對其市場勢力的影響。為此,我們將考察發生并購前后企業市場勢力的差異。但是在實證過程中,如果不加處理直接比較兩組企業,將產生兩個問題。一個是可能的選擇性偏差,因為企業的并購行為并非隨機發生,對非隨機樣本進行估計就會產生樣本選擇性偏差。二是異質性偏差,因為發生并購的企業與未發生并購企業的部分市場勢力差異可能源自企業的內生因素,這些因素不隨時間變化或者不可觀測,直接進行比較可能會產生異質性偏差。為解決這兩個問題,本文將采用基于傾向得分匹配的雙重差分法對樣本進行處理。

接下來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匹配的方法就是從對照組(Control)中尋找與發生并購的企業發生并購概率最為接近的未發生并購企業,以解決選擇性偏差。也就是說,如果不發生并購,這兩組企業市場勢力的時間變化路徑是平行的。本文選擇Rosenbaum and Rubin[28]提出的傾向得分匹配法來進行匹配。企業發生并購行為的概率公式為:
p=Pr{dmit=1}=Φ{Xit}
(3)
其中,p為企業發生并購行為的概率,Φ{·}表示一個正態累積分布函數。從這個方程可以得到每個企業發生并購的預測概率,傾向得分匹配就是將預測概率值p相近的企業進行配對[17]。在(3)式中,Xit為影響企業并購行為的因素,稱為匹配變量或協變量(Covariate),本文選用企業的營業收入、中間品投入、固定資產、流動負債和應付利息作為匹配變量。
再次,采用雙重差分法。在完成匹配之后,我們得到一個二維的虛擬變量dMit=[1,0],其中dMit=1表示i為發生并購行為的企業,dMit=0表示i為未發生并購的企業。同時,構造一個時間虛擬變量dT=[1,0],dT=1表示企業發生并購之后的時期,dT=0表示企業并購之前的時期。其中,T=1,2,3不同的取值,表示發生并購后的不同時期,以此考察并購發生后不同滯后時期市場勢力差異。最終,得到本文的回歸模型:
dYit=β1itdXit+β2itdXitdMit+β3itdXitdT+β4itdXitdMitdT+υit
(4)
其中,β4it體現了并購前后企業市場勢力的變化,是本文考察的主要變量。
(三)變量的度量和樣本描述
1.變量的度量。從企業的會計信息中可以得到本文實證模型所需要的企業層面的數據。我們用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度量PitYit;用企業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度量PLitLit;用企業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度量PMitMit;用固定有形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度量Kit;至于資本的租賃價格PKit,我們沿用HallandJorgenson[29]的定義,令Pkit=PI(rit+δit),其中PI為中國的年度投資價格指數,rit為每一時期的實際利率,用企業的利息支付與總負債的比值減去當期中國年度通貨膨脹率,δit是企業每一時期的折舊率,在有些文獻中,為這個變量賦值10%或15%,在本文中,我們認為企業每一時期的折舊率為15%*15%是文獻中最常用的資產折舊率,如Hall和 Mairesse(1995)、吳延兵(2008)等。。為實證方便,我們將在運算過程中采用上述變量的對數形式。
2.樣本描述。本文的樣本來自Wind資訊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了中國A股全部上市企業企業層面的微觀財務數據。本文采用的樣本包含了Wind資訊行業劃分標準中所有工業類上市企業的微觀數據,共712家,時間跨度為2007-2013年。
本文計算中所采用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均來自Wind資訊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數據庫,上市公司并購數據來自Wind資訊中國并購庫。
在對樣本的主要經濟指標進行統計性描述之前,先對樣本進行預處理。首先刪除明顯有問題的樣本和時間上有間斷的樣本,如營業收入、中間品投入、員工工資福利這三項中一項或幾項為零的樣本,接下來在留下的樣本中選取2007-2013年持續經營的企業作為本文要描述的樣本,共526家,主要經濟指標的統計特征由表1給出。

表1 主要經濟指標統計特征
本文主要分析并購行為對企業市場勢力的影響,從表2可以看出,本文實證所采用的2007-2013年樣本中,每年發生并購的次數超過了企業數量的10%,這說明并購行為已經成為企業做大做強的主要手段之一。從時間趨勢上看,除2009年外,本文采用的樣本企業發生并購事件的次數逐年上升,在7年間增長了近一倍。因為2010年處于本文所采用樣本中的中間期,因此,本文主要考察2010年企業并購行為。

表2 企業并購的年度分布
本文首先選取只在2010年發生并購事件的企業作為處理組(Treated),即2010年有22家企業位于處理組(Treated),dMit=1。對照組(Control)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與之匹配是的樣本中2007-2013年七年間一直未發生并購的企業,在對照組(Control)中,dMit=0。在本文中,將并購事件發生的當年,2010年作為并購前的時期,即dT=0,2011年及之后的時期作為并購發生后的時期,即dT=1,并且T的不同取值代表不同的滯后期。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傾向評分的匹配結果
本文選用有回放并且允許并列(ties)的k臨近匹配算法進行傾向得分匹配,取k=1。在本文考察的樣本中,2010年有22家企業位于處理組(Treated),190家持續未發生并購行為的企業將與之匹配。匹配之后去除未成功配對的企業,共有22家企業位于處理組(Treated),95家企業位于對照組(Control)。為了檢驗匹配結果是否可信,本文進行匹配平衡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匹配平衡性檢驗主要進行兩方面的檢驗,首先是考察在匹配前(Unmatched)與匹配后(Matched)處理組(Treated)和對照組(Control)的均值是否相等,在這里采用的是t檢驗。如果滿足平衡假設,那么在匹配之后t檢驗是不顯著的。其次考察匹配前后的標準偏差,通過計算配對前后匹配變量的標準偏差,來判斷匹配效果的好壞[17]。Smith and Todd[30]的經驗表明,標準偏差的絕對值越小,意味著匹配效果越好,Rosenbaum and Rubin[31]認為,好的匹配標準偏差在匹配后其絕對值應小于5%。
從表3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匹配后的t統計量并不顯著,相伴概率均大于10%,即所有t檢驗的結果不拒絕處理組(Treated)與對照組(Control)無系統差異的原假設,這表明匹配后處理組(Treated)和對照組(Control)均值不存在明顯差異。同時,匹配之后除中間品投入外,各匹配變量的標準偏差絕對值均保持在5%以內,而中間品投入的標準偏差絕對值為5.3%,接近5%,這也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的結果意味著本文選取的匹配變量和匹配方法是恰當的,估計結果是可信的。

表3 匹配的平穩性檢驗
(二)基于傾向得分匹配的雙重差分法估計結果
依據傾向得分匹配估計得到的處理組(Treated)和對照組(Control),我們運用2007-2013年的企業數據,采用雙重差分估計量法的回歸方法,考察了企業的并購行為對其市場勢力的影響,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歸結果
注:***表示顯著水平在1%以上,**表示顯著水平在5%以上,*表示顯著水平在10%以上,()中的數值為t統計量。
表4的結果顯示,企業的并購行為似乎沒有影響企業的市場勢力。在并購發生后的1-3年內(分別對應T=1,T=2和T=3), dXit×dMit×dT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91、0.272和0.161,但是這三個系數在統計上都不顯著。這意味著企業的并購行為與企業市場勢力的提高或者降低沒有必然聯系。企業希望通過并購提高市場勢力的目標可能也不會實現了。
本文的實證結果與眾多經濟學工作者的研究似乎存在矛盾,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實證探討,都表明企業的并購行為會對其市場勢力產生正向或者負向的影響。但是為什么在中國A股市場上出現了企業并購行為與其市場勢力相對獨立的現象?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應該是基于中國經濟轉型條件下的制度因素的分析。
首先,由于地方政府這一制度因素存在,導致企業的并購行為偏離了利潤最大化的軌道,地方政府出于財政收入和官員晉升動機而導致的“拉郎配”式的企業并購或者利用政府力量阻止優質企業出于經濟動機進行的跨地區并購[10]。一方面,政府干預下的“拉郎配”并購更多的是體現了地方政府“掏空”優勢上市企業的目標或者驅使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購本地“劣質資產”、減輕本身財政負擔的動機[32],而非企業主動發起的基于本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動機,顯然,此類并購行為無助于競爭優勢的獲得和市場勢力的提升[33]。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員更愿意鼓勵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企業并購本地的優質企業,而不愿坐看外地上市企業并購本地的優質資源以增強其經濟表現[11],這意味著可能提升市場勢力的并購行為被阻止或者加大了成本,從而削弱了并購與市場勢力之間的必然聯系。
其次,在中國A股市場上存在著多層次市場主體: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不同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發起并購的動機并非基于利潤最大化或者做大做強企業的經濟動機,而往往是出于個人升遷的政治動機[15]。因此,當國有上市企業主動發起并購時,選擇并購對象和并購類型考慮的是如何將企業規模擴大而非加強企業競爭力,這可能出現并購后企業大而不強的局面,從而造成了并購行為與其市場勢力的不相關現象。
再次,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有待繼續深化改革,目前還存在著與其他轉型經濟相同的不足:市場機制尚需完善、市場效率較低[34]。所以當企業出于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的發起并購時,往往被政府代替市場直接分配資源或者社會網絡越過價格機制分配資源的現實所阻礙,因為這造成了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增加以及企業整合的困難。因為市場機制不完善,資源配置背離了市場機制,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A股市場上企業并購與市場勢力相互獨立的現象。
此外,除了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制度環境外,委托代理問題的存在也可能是企業并購行為與市場勢力關系不顯著的原因。因為企業的所有者和職業經理人在目標上的不一致,基于個人利益的考慮,職業經理人有更多的沖動擴大企業規模[8]。Jensen發現,管理者和股東的目標不一致,管理者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盡可能的擴大企業規模[35]。職業經理人的報酬隨企業規模的增大而提高,而與企業的業績無關[36]。由此可見,職業經理人們發起并購為了擴大企業規模甚于提高企業競爭力和企業價值,這也造成了企業并購與其市場勢力的形成和提升無關的事實。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考察了2010年發生并購行為的上市企業的市場勢力的變化情況,為了進行穩健性檢驗,在這一節,我們選取2009年發生并購行為的上市企業作為考察對象。首先將發生并購行為的上市17家企業與樣本中190家持續未發生并購行為的上市企業進行傾向得分匹配,處理組有15家企業,對照組有156家企業。遵循上文的做法,將2009年設定為并購行為發生前的時期,即當年以及之前的dT=0;將2010年及以后的年份設定為并購后時期,則dT=1。利用匹配得到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探討企業并購行為對市場勢力的影響,輸出結果如表5所示。
表5的結果顯示,企業的并購行為與其市場勢力沒有顯著地相關關系。數據顯示,在并購發生后的1-4年內(分別對應T=1,T=2,T=3和T=4), dXit×dMit×dT項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8、0.555、0.121和0.256,這四個系數在統計上依然是不顯著的,這與本文上述回歸結果是一致的,這說明本文的實證結果是穩健的。

表5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注:***表示顯著水平在1%以上,**表示顯著水平在5%以上,*表示顯著水平在10%以上,()中的數值為t統計量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2007-2013年中國A股市場526家持續經營的工業類上市企業的企業層面微觀數據,在最新的產業組織模型——Konings et al.[16]模型的基礎上,利用基于傾向得分匹配的雙重差分估計量方法直接測度企業的市場勢力,通過比較并購發生行為前后企業市場勢力的變化,探討企業并購行為對市場勢力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在中國A股市場,企業的并購行為與其市場勢力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這也許是源于中國經濟轉型背景下的制度因素:中國市場體制尚待完善,企業的并購行為往往受到政府和社會關系網絡等非市場機制的干擾;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出于GDP考核激勵或財政考慮,有動機促成本地上市企業并購或阻止外地企業對本地優質資源的并購,無論是促成還是阻礙,都導致企業的并購行為偏離了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同時有可能加大了企業的并購成本;中國市場存在多層次市場主體,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發起并購有時是出于個人升遷動機而非經濟動機;以上三方面制度因素都會造成企業并購行為與市場勢力相互獨立。此外,委托代理理論也可以做出一定的解釋,因為企業的所有者和職業經理人目標不一致,職業經理人關心的是企業規模擴大帶來的薪酬水平的提升,因此在選擇并購類型和并購企業時背離了提高企業競爭力的目標。
本文研究帶來的政策含義在于:一方面,正確看待中國市場上的并購行為,并購并不一定導致市場勢力的提升,企業希望通過并購實現提高企業競爭力的目標未必能夠實現。產業組織理論認為,產品差異化是企業市場勢力的真正來源。產品差異化賦予企業在不失去全部顧客條件下提高價格的權利,消費者愿意為這種差異化多付成本。因此,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加企業利潤的核心是創新活動。另一方面,繼續深化改革,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持續深化改革,釋放制度紅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并購行為中的資源配置作用,減少和約束地方政府行政干預企業發展的行為,為企業發展創造一個公平有效的制度環境。
參考文獻:
[1](美)J·弗雷德·威斯通.兼并重組與公司控制?[M].唐旭等,譯.第四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2]Barton D M, Sherman R. The price and profit effects of horizontal merger: A case study[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84, 33(2):165-77.
[3]Vita M G, Sacher S.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not-for-profit hospital mergers: a case study[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1, 49(1):63-84.
[4]Ellert J C. Mergers, antitrust law enforcement and stockholder returns [J]. Journal of Finance, 1976, 31(2):715-732.
[5]Moeller S B, Schlingemann F P, Stulz R M. Wealth destruction on a massive scale? A study of acquiring-firm returns in the recent merger wave[J].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2):757-782.
[6]Focarelli D, Panetta F. Are mergers beneficial to consumers? Evidence from the market for bank deposi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152-1172.
[7]李善民, 曾昭灶,王彩萍. 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 世界經濟, 2004(9):60-67.
[8]韓立巖, 陳慶勇. 并購的頻繁程度意味著什么——來自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績效的證據[J]. 經濟學(季刊), 2007,6(4):1185-1200.
[9]李哲, 何佳. 國有上市公司的上市模式、并購類型與績效[J]. 世界經濟, 2007(09):64-73.
[10]唐建新, 陳冬. 地區投資者保護、企業性質與異地并購的協同效應[J]. 管理世界, 2010(8):102-116.
[11]方軍雄. 政府干預、所有權性質與企業并購[J]. 管理世界, 2008(9):118-123.
[12]潘紅波, 余明桂. 支持之手、掠奪之手與異地并購[J]. 經濟研究, 2011(9):108-120.
[13]裴長洪, 林江. 跨境并購是我國利用外資的新形式[J]. 中國工業經濟, 2007(1):29-36
[14]顧露露, Robert Reed.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失敗了嗎?[J]. 經濟研究, 2011(7):116-129.
[15]邵新建, 巫和懋, 肖立晟,等.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戰略目標與經營績效:基于A股市場的評價[J]. 世界經濟, 2012(5):81-105.
[16]Konings J, Van Cayseele P, Warzynski F. The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and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firms’price-cost margins: Micro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5, 87(1): 124-134.
[17]盛丹. 國有企業改制、競爭程度與社會福利——基于企業成本加成率的考察[J]. 經濟學 (季刊), 2013, 12(4) :1465-1490.
[18]林恩·佩波爾,丹·理查茲,喬治·諾曼.產業組織:現代理論與實踐[M].鄭江淮,等,譯.第四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19]Lichtenberg F R, Siegel D. Takeovers and corporate overhead [C ]. Cambridge, M A: M IT Press, 1992.
[20]Kim E H, Singal V. Mergers and market power: Evidence from the airline industr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83(3): 549-569.
[21]Normann H T, Snyder C M, Martin S. Vertical foreclosure in experimental markets[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32(3):466-96.
[22]Adams W, Dirlam J B. Steel imports and vertical oligopoly powe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4, 54(5):626-655.
[23]Chandler A 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7, 3(1):305-360.
[24]Riordan M H. Anticompetitive vertical integration by a dominant firm anticompetitive vertical integration by a dominant fir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5):1232-1248.
[25]Nathanson D A, Cassano J. What happens to profits when a company diversifies? [J]. Wharton Magazine,1982(24):19-26
[26]Teece D J. Toward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multiproduct firm[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2, 3(1):39-63.
[27]占明珍. 市場勢力研究[D]. 武漢大學, 2011.
[28]Rosenbaum P R, 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 70:41-55.
[29]Hall R E, Jorgenson D W. Tax polic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57(3): 391-414.
[30]Smith J A, Todd P E. Does matching overcome LaLonde's critique of non-experimental estimator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5, 125(1): 305-353.
[31]Paul R, Rosenbaum, Donald B, Rubin. 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J]. American Statistician, 1985, 39(1):33-38.
[32]陳信元, 黃俊. 政府干預、多元化經營與公司業績[J]. 管理世界, 2007(1):92-97.
[33]宋獻中, 周昌仕. 股權結構、大股東變更與收購公司競爭優勢——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財經科學, 2007(5):32-40.
[34]李善民, 周小春. 公司特征、行業特征和并購戰略類型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 2007(3):130-137.
[35]Ruback R S, Jensen M C.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3, 11(6):5-50.
[36]Schmidt D R, Fowler K L. Post-acquisi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11(7):559-569.
責任編輯、校對:鄭雅妮
收稿日期:2015-10-16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產業革命的發展方向、影響與中國的應對戰略”(項目編號:13&ZD157)。
作者簡介:白雪潔(1971-),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人,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孫紅印(1983-),陜西省西安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汪海鳳(1981-),女,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6(03)-01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