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56個民族的由來 讀《中國的民族識別》
文·圖 / 龍成鵬
?
中國56個民族的由來 讀《中國的民族識別》
文·圖 / 龍成鵬
學者們站在各自的立場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提出各種問題和看法。這些討論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細節和知識,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許多困擾。從做好民族工作的角度,我們應當去了解這些聲音,去了解這段歷史與當下的關聯。
一
“中國有56個民族”,這既是大眾熟知的常識,也是今天民族工作的基本前提。但這個說法,是怎么來的?1979年6月6日,國務院發布公告,宣布基諾族為單一民族,為第56個,之后就沒有識別認定新的民族,于是,我們有了“56個民族”的說法。
基諾族和很多其他少數民族一樣,起初并沒有現在這樣的名稱,也沒有被國家正式承認為一個民族,但在1949年之后,他們獲得了名稱、身份,甚至連名稱的寫法經過反復斟酌后被固定下來。促使這一轉變的工作,就是民族識別。
作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民族識別工作應該絕大部分已結束(云南是2011年才結束最后一批民族識別工作),但近些年人們對它的關注和討論,并沒有減淡,相反還越來越熱烈。學者們站在各自的立場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提出各種問題和看法。這些討論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細節和知識,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許多困擾。從做好民族工作的角度,我們應當去了解這些聲音,去了解這段歷史與當下的關聯。
2005年修訂重版的《中國的民族識別》對我們了解這項工作會提供很多有價值的信息。這本書由13位民族學者(主要來自各民族院校)集體完成,分6章24節,為我們勾勒了民族識別工作的基本面貌。該書編寫于上世紀90年代初,1993年完成初版。當時擔任該書顧問的學術權威——費孝通和林耀華都還在世,這兩位學者是1950年代最有影響的民族學者,也是民族識別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其中林耀華參與了1954年云南的兩次民族識別,今天多份識別報告里還有他的名字。
該書的主編是國家民委原副主任黃光學,和該書的大部分作者一樣,他也是民族識別工作的親歷者,因此,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關于民族識別,比較“正統”的評價和聲音。
二
《中國的民族識別》的第一章闡述了“民族”一詞的含義和發展規律。書中提及,中國古代文獻,并無“民族”一詞。這個詞漢語中最早出現是1899年,是梁啟超最先使用。1903年以后,“民族”才廣泛流行。對“民族”一詞的起源,實際上不止上述這一種說法,不過,都認為“民族”誕生于1900年前后,且與日本有關。
“民族”一詞的傳播和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的興起,意義非同尋常,這里要重點介紹一下。毫不夸張地說,它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促使中國改變了延續兩千多年的王朝模式,并轉而追隨西方,探索民族國家的現代模式。
這種探尋,落到實處就跟民族識別工作有關。因為中國并不是西方那種單一民族的國家,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并不是由某一個民族獨自完成,而是由漢族聯合其他各民族共同完成(為此他們提出了一個更有包容性的概念——中華民族)。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為了讓數十個民族參與政治,參與新國家的建設,就不可避免地要對各個民族的身份、狀況進行識別調查。
《中國的民族識別》把民族識別定義為“對一個族體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稱的辨別”。毫無疑問,這種辨別帶有政治使命,但同時也是學術工程。辨別的標準是什么,能否行之有效,是民族識別的工作前提,也是該書第一章和第三章關心的話題。
該書認為,中國民族識別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其中斯大林給民族下的定義,影響最為深遠。1913年,時年34歲的斯大林這樣說:“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這一定義,簡化之后,就變成了民族的“四要素”,即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質。
斯大林的這一定義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民族識別,是今天學者們還在討論的問題。不過,從實踐上看,中國學者并沒有完全照搬這套理論。
這套理論有很多難以被中國消化的東西。舉例來說,斯大林(列寧也差不多這樣)認為,民族是一個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才會出現的人們共同體(其靈感顯然源于歐洲歷史),所以,如果生搬硬套,那當時的中國幾乎沒有“民族”,而只能是一些發展程度更高的部族、部落甚至氏族。
但1953年,在一份重要文件中,毛澤東就明確表達了另一種觀點,他說:“科學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區分哪個是民族,哪個是部族或部落。”毛澤東的這個說法,跟絕大多數學者的主張一致。這一觀點,對民族識別有直接影響,中國民族,無論大小和發展程度,統一以民族命名(這無疑更體現了各民族的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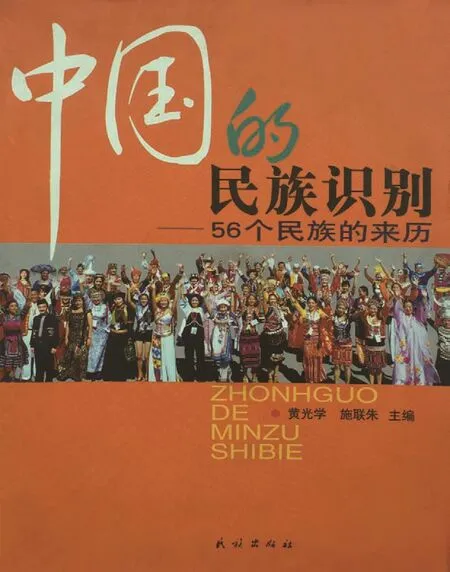
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要素”,在民族識別報告中,經常體現為一種論證策略,因為某某民族,具備“四要素”,所以,它是單一民族。實際情況比識別報告體現出來的更為復雜。早在1956年,民族識別還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費孝通和林耀華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署名文章就討論了“四要素”在具體運用時的困惑。他們坦言一些被識別為單一民族的族體,他們在語言地域等要素上,有的會缺一兩條。比如,景頗族的語言,就不止一種(《關于少數民族族別問題的研究》)。
從《中國民族識別》中列舉的情況看,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一直是很靈活地運用民族的“四要素”(等于說有時候可以不考慮“四要素”),而且,該書也注意到民族的名稱和歷史也是民族識別的重要因素。這點不難理解,中國是一個文獻和考據很發達的國家,所以民族的歷史盡管不成系統,但材料豐富(參看該書第二章關于民族名稱和歷史淵源)。
簡而言之,無論表面上表現得多么循規蹈矩,為了完成民族識別的工作,中國學者都一直小心翼翼地修改著斯大林提供的識別“依據”。下面這段話來自1958年云南的一份識別報告就是生動的詮釋:“五項(民族自稱、歷史、語言、習俗、民族意愿)尋找,必須建立在斯大林同志關于民族的經典定義的全面基礎上,并不是另外提出‘新’的民族定義。”(從內容看,這“五項”實際與斯大林的定義有些距離了)
三
相比理論闡述,《中國的民族識別》一書對識別的具體實踐提供了更為鮮活的資料。該書第三章把識別分成了四個階段來勾勒:第一階段(1949年—1954年)是發端;第二階段(1954年—1964年)是高潮;第三階段(1965年—1978年)是中斷;第四階段(1978年—1990年)是恢復。
該書還圍繞幾種類型,相對詳細地介紹了云南、廣西、貴州以及其他省份中比較典型的識別案例。其中有的民族被識別為單一民族,關鍵要素是它的歷史,比如畬族、土家族、達斡爾族等;還有的民族在識別過程中,民族語言成了重要參考,云南的彝族、哈尼族和壯族各支系的歸并,就跟語言學者的語言分類有密切關系,所以,語言這個要素,就相對凸顯出來。
該書的第四章和第六章對民族識別工作成績和意義進行了闡述,并列舉了部分民族識別的遺留問題。遺留問題,主要是部分族別的歸并引起爭議,比如四川的白馬人,西藏的僜人等。這里提供的數字并不是全部,因為以云南而言,克木人、莽人的識別也是當時的遺留問題。當然盡管有遺留問題,民族識別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
四
因為成書在20多年前,《中國的民族識別》一書未能反映近些年學界對民族識別議題的研究,但因為篇幅有限,我們這里就介紹其中的一次討論。
云南民族學者杜玉亭對基諾族民族識別40年的反思,比較有代表性。他是基諾族民族識別工作組的主要成員,某種程度上,基諾族被識別為單一民族,跟他的推動有密切關系。
但看到商業大潮沖擊基諾族社會之后,杜玉亭對基諾族的未來充滿焦慮。他預言,基諾族文化將在很短的時間消失(基諾族的一些老人對此也贊同)。這樣的文化變遷,杜玉亭認為跟基諾族作為單一民族被識別出來有關,所以,這促使他提出對“民族識別理論依據的再認識”。
杜玉亭指出,他(也包括國家)過去20年,為基諾族進行民族識別調查,是因為他堅信民族正如斯大林理論所描述,是一個長期而穩定的共同體(與國家齊壽)。但他沒料到的是,這些當初用來判斷基諾族是一個單一民族的文化要素,會在短短幾十年內走向消亡。
從基諾族身上,杜玉亭總結出中國的民族,在文化特征的維持上,應該分長期和非長期兩種類型,漢族是前一類,而人口較少的基諾族則屬于后一類。所以,他認為,只有保護好民族的文化,才能避免“族籍迷失”,使民族長久存在下去。
杜玉亭的反思不僅觸及到民族識別的理論問題,也觸及到當代民族共同面臨的發展問題。這些議題,可能不止有一種解釋,也不止有一種對策,但杜玉亭的反思,對我們依然是一個有益的提醒:我們當代的民族問題,跟我們之前的民族識別是否有著被我們忽略掉的聯系。
(責任編輯 趙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