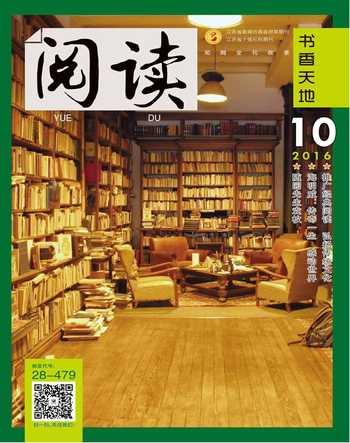北方男人
皮皮
我是個北方女人,在這里想很認真地說說與我可能毫無共同點的北方男人的一些小小方面,因為也涉及到了南方人,所以我收起個人好惡,在面對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時,盡力不喪失客觀的立場。我只要告訴您,我聽到的,我看到的,就足夠了。
長江和長城,都是中國最有名的有象征意義的存在,所不同的是長江使中國誕生了兩個內涵極為豐富的名詞,南方、北方。所以,在我還沒出世的時候,中國人就有了有天然差別的南方人、北方人。
一場爭吵
那是個陽光很好的秋天,葉子金黃,盡管有的已經開始飄落了。
我在十字街口的一側,等待被修理的自行車。午后的陽光讓人困倦,我靠在一棵樹上,不一會兒眼皮便合上了。眼皮下的那片紅光由明到暗,直到消失。
“咔嚓”,是一聲響亮的金屬撞擊聲,打開了我的眼睛:在面前不遠的地方,兩個騎自行車的男人撞在了一起。他們兩腿叉地,屁股還坐在鞍座上,便開始了爭吵。
“你怎么回事?”一個戴帽子的男人大聲問。
“你怎么回事?”另一個沒戴帽子的男人也這么問。
“我問你吶!”戴帽子的男人下了車。
“你沒長眼撞我了,還不認賬?”
“你罵誰?”
“罵你,不服啊?”
“罵我就不行。”戴帽子的男人說完,一拳打在對方下巴上。
這是兩個體格差不多一樣健壯的男人,他們扭打在一起,腦袋上方飛來飛去的是握得緊緊的拳頭。只有幾秒鐘,我便看見地上殷紅的血跡。
圍觀的人試圖拉開兩個怒火沖天的人,但收效不大。
他們又扭打了一會兒,終于分開了,戴帽子的男人順手從地上撿起一大塊石頭,一邊高喊“你別跑”,一邊朝對方猛沖過去。
圍觀的人攔住了戴帽子的男人,因為都看見了石頭。沒戴帽子的男人,一看對方手里舉著的石頭,也四處找石頭,但運氣不好。這時,高舉石頭的男人對拉住他的人大聲說:
“松開,不松開,我誰都砸!”
人們一聽這話,只好松開,躲到一邊。
因為“武器”的加入,戰斗很快接近了尾聲。石頭砸在了沒戴帽子的頭上,血流不止。戴帽子的男人見對方捂著流血的頭,蹲到了地上,便扔了石頭。他轉身要離開,他說:
“下次長記性。”
流血太多的男人已經不能再罵人了。
戴帽子的男人走到自己的自行車前,察看自行車,也看見了蹲在地上的男人和地上越來越多的鮮血,但他繼續檢查自己的車子。一分鐘后,他把自行車往地上一摔,撥開圍觀的人群,扯起那個蹲在地上流血的男人,大聲問圍觀的人:
“哪兒有醫院?”
我不由自主地跟在他們后面,一起去了醫院。那時我還小,孩子的稚氣還沒脫凈,要是現在我碰上這樣的熱鬧,無論如何也不會跟到醫院去,我會在前一自然段結束的地方擱筆。
到了醫院,戴帽子的男人把他的傷員送進了急救室。接著他便飛快地跑了起來:掛號、交款、取藥……等需要他做的一切都完成時,他摸摸鼻子下干涸的血跡,進了盥洗室。
大約半個小時,沒戴帽子的男人從急救室出來了。他的頭上包了白色的藥布,看上去有些可笑。戴帽子的男人連忙迎上去,他摘下帽子說:
“真對不起,我手太重,我……”
“別提這事了,我不也打你了嗎?”
“那是,可我……”
“你哪年生的?我1954年的。”
“我1956年的。大哥,從現在起,咱們就算認識了。我在×××工作,有事你找我。
“沒說的,老弟,不打不認識。我在×××工作,有什么我能幫忙的,別客氣。”
他們摟著肩膀,像親兄弟一樣離開了醫院,也離開了我,兩個北方男人。
我沒想笑,但還是笑了。
另一次爭吵
這次爭吵發生在長江流域一個以文明程度高著稱的城市,一個總下雨的城市,我們叫它x城吧。
我是在火車上聽說這件事的。親眼看見并參與這次爭吵的王先生,是我在火車上的鄰居,火車離開x城的時候,那兒依然下雨,而這雨已經連綿不斷地下了七天。
大家一直在喝茶,火車過了濟南,才感覺離潮濕遠了。王先生呷了一口茶說:
“到x城二十天,這是我第一次出汗。”
王先生是安裝電話的,他接著又說南方總下雨,糟透了。
“潮是潮了點兒,可南方人聰明。”一個老者說。
“沒錯兒,就是聰明,所以人家比咱富。”王先生停了停又說:“可能太聰明了,打架都不動真格的。”
“人家講文明,不愛打架。”我說。
“你什么地方人?”王先生問我。
“東北人。”
“沒搞錯吧?”
大家都笑了,王先生講了那次爭吵。
要不是下雨,那兩個x城人也不致于吵起來。那雨下得人心煩,恨不得咬誰幾口。
那兩個本地人是在彼此轉彎時撞上的。他們都是一手扶把,一手撐傘,撞得不輕。他們撞上以后,誰也沒道歉,馬上爭吵起來了。
他們吵什么,我聽不太懂,一句半句的。大約吵了十幾分鐘,仍然沒有進展。聲音越來越高,臉兒越來越白,但沒動手。
這真讓人發急,干打雷不下雨啊。不過,那天,我閑得難受,就想看熱鬧。我對旁邊一個本地人說,這要是在東北,三句話,就打得對方滿地找牙了。那人聽我這么一說,像躲瘟疫似的走了,到我對面看去了。
那兩個人火氣真不小,越吵越僵,絲毫沒有緩解的意思,最后終于動手了,他們每人手里都有一把黑色的長柄傘,收了傘,就用傘打了起來。
他們倆用傘劃來劃去,有點像外國人玩劍似的,可劍和傘不是一回事。那兩個人身子后傾,腦袋躲得老遠,皺著眉頭,像打掃垃圾時的表情。他們把身體的要害部位躲得遠遠的,各伸一條胳膊,在那兒瞎撥弄著兩把傘,動靜挺好聽,劈里啪啦,可誰也打不著誰,就像兩把傘干上了,你說這傘犯著誰了。
這兩把傘攪和的時間比爭吵的時間長,就是上不去層次,把我急得什么似的,終于忍不住了,就喊了幾嗓子。
“嗨,認真點腰部以上,直劈,別總側著身子,那樣使不上勁。”
我成了場外指導,可沒一個人聽我的。那些看熱鬧的像看猴似的看我。那兩把傘照打不誤,哎,你們說,急人不?哪有這么打架的?
我實在管不住自己了,沖過去,一把握住沒完沒了瞎攪和的雨傘,問那兩個還握著雨傘的男人:
“打不打?”
那兩個家伙怔住了,光看我不說話。
“要打就真打,懂不?”
他們還是光看我不說話。我氣急敗壞,大吼一聲:
“不打,滾。”
王先生說完,喝了口茶,對笑成一團又一團的聽眾,露出滿意的微笑。
火車還在山東境內努力地奔跑,大家終于不再笑了。我湊近王先生說:
“知道你這行為叫啥不?”
“叫啥?”王先生瞪大眼睛。
“傻。”
說完,我就去火車連接部了,是想透透空氣,但還是聽見了緊跟我背后傳來的那句話,是王先生說的:
“聽見沒?還是咱東北人,說話比他們打架還解恨兒。”
“真傻。”這話是從我嘴里溜達出來的,沒傳很遠就被列車的轟鳴湮沒了。
(摘自作家出版社《出賣陽光》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