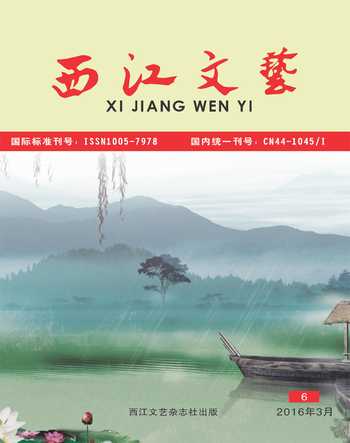地獄中的曙光
邵丹
【摘要】:曹禺的劇作對我國話劇文學的成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雷雨》的家庭悲劇到《日出》的社會悲劇,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形式上都走上了一個新的高峰。《日出》把目光投向三十年代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都市社會,通過人物之間的矛盾及自身的內心沖突為我們展示了資產階級的丑行,金錢化社會對人的毒化與吞噬。然作家并不止于控訴不公平的禽獸世界,而是積極從這黑暗中探尋一絲光亮,表露出對光明未來“日出”的熱烈期盼。
【關鍵詞】:曹禺;金錢;人性;掙扎;光明
曹禺的話劇作品代表了我國現代話劇文學的藝術高峰,受“五四”時代精神在文學領域的影響,其作品更加深刻集中的反映了反封建的主題。曹禺善于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尖銳的戲劇沖突,深入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日出》選取了陳白露的華麗休息室和翠喜的寶和下處兩個場所,真實的展示了人們“鬼”似的生活。讀完《日出》讓我深切的感受到資本社會金錢下人性的扭曲,人物內心的復雜斗爭,靈魂與肉體的掙扎,對黑暗社會的憎惡。但在落幕之時,并不會為此感到悲傷,反而有一種希望與力量—太陽出來了,黑暗就留在了后面。
一.金錢下人性的毀滅
在《日出》中,有種無形的東西一直在操控著整個社會,即是金錢。發財的貪欲和金錢的欲望把人們驅逐到人生的戰場上,它不但成為資產階級“最心愛的生活原則”,也使“一切熱情和一切活動都必須沉沒在貪欲”之中。金錢讓人們顛倒了是非黑白,可以說主宰了一切。《日出》中每個人物幾乎都是為錢而茍活著,在金錢的毒化下,喪失了人性。在第一幕里方達生要求陳白露和他一起離開時,陳白露問的卻是“你有多少錢?我要人養活,應酬要穿些好衣服,要花很多很多的錢”。而為了錢,陳白露竟然可以稱潘月亭為“爸爸,老爸爸”即使在她心里是那么的厭惡他。陳白露為了自身所謂的“快活”,不得不說她已經忘記了什么是尊嚴。顧八奶奶本是一個俗不可耐的胖女人,福升卻說:“人家有錢,您看,哪個不說她年輕”。而顧八奶奶的“情人”胡四,竟然向大齡丑陋的她求婚十二次,還像個小狗似的跟著她。福升的阿諛奉承,胡四的巴結,無不與顧八奶奶是個有錢人相關。這不正像馬克思經常援引莎士比亞的《雅典人臺滿》中所指的情形嗎?“黃金這東西,只要一點兒,就可以把一切黑的變成白的,一切丑的變成美的,一切罪過變成正義,一切卑賤變成高貴,把求婚者送給滿臉皺紋的老寡婦了”。在金錢的利誘下,將人性的毀滅發揮到淋漓盡致的莫屬李石清。他的心中充滿了恨,他恨自己為什么沒有一個好父親,生來就有錢,他罵陳白露是一個賤貨。他恨那些有錢人,可他又不得不去把那些有錢人當做祖宗一樣來奉承,他拿錢讓李太太陪“小姐太太”們打牌,不顧家中病重的孩子,最后兒子將要死去李太太打電話通知他時,他全然不顧。發財的欲望已使他發瘋,親情在他眼里早已不值一提。 在金錢統治的社會下,人類發瘋似的金錢欲望把他們的貪婪,狡詐,種種可怕的面孔暴露無疑。金錢支配著人們的每一個行動,尊嚴,親情,純真的愛情已蕩然無存,這些可憐的人們儼然成為金錢的奴隸,人性的善良溫純不復存在。赤裸裸的利害關系毀滅了人性,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被顯現出來。
二.靈與肉的掙扎
曹禺在談到《日出》的主題時,這樣說道:“《日出》希望獻與觀眾的應是一個鮮血淋淋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應為這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社會形態”。在《日出》中,陳白露可以說是貫穿全劇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是一個性格充滿了矛盾的小資產階級女性的代表。陳白露一出場時,對她的介紹就是“她愛生活,她又厭惡生活”。陳白露出身書香之家,是愛華女校的高材生。父親的突然去世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當人物出場時她已經是一個交際花,為了金錢寧愿犧牲自己的身體與各種各樣的人在一起鬼混。但她卻厭倦了這種“發瘋似的生活”。面對每天”鬼”似的生活,陳白露也確實做出了反抗。對于自身來講,她接受過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也渴望愛情。她與一個詩人結合了,但最終因為孩子的死詩人拋棄了她,他追尋自己的希望去了,追其根本還是她與詩人有著不同的人生觀。愛情上的失敗第一次對她造成了精神創傷。除自身之外,她也對黑暗勢力進行了抗爭,這莫屬救小東西的事情了,看到小東西的遭遇讓她心生同情。當聽說小東西把金八給打了時候,她不但沒有感到害怕,反而說“打的好,打的痛快”!這就更加看出她對以金八為代表的黑暗勢力的憎惡,大膽的進行了反抗。然而她的抗爭終究敵不過黑暗勢力的強大,小東西被送走,她和方達生竭力尋找也沒能找到。營救小東西的失敗讓她感覺自己永遠無法逃出黑暗,精神上自此也陷入了崩潰的境地。陳白露最后選擇了自殺,臨死前她說“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可見她已經從那醉生夢死的生活中清醒過來了,但她沒有力氣去繼續追求光明的未來了。關于陳白露其人,曹禺曾做過這樣的解釋:“方達生,陳白露是所謂的有心人,一個傻氣,一個聰明,他們痛心疾首的厭惡那腐惡的環境,都想有所反抗。然而,白露氣餒了,她一個久經風塵的女人,斷然地跟著黑夜走了。”④對于黑暗社會,陳白露努力掙扎過,但終究因為黑暗勢力的強大讓她在精神上垮了,正如曹禺先生所說,她斷然地跟著黑夜走了。
三.光明的旋律悄然奏響
方達生剛進城時是一個淳樸,老實卻有些固執的鄉下人,因為聽說陳白露變成了交際花便匆匆的趕來找她。看到陳白露就一心想要帶她去鄉下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但陳白露卻對此嗤之以鼻。他天真的以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感化陳白露。當被陳白露留在這兒多住幾天時,遇到了小東西事件,他決定幫小東西脫離苦海。然而小東西事件的失敗或許讓方達生對這個畸形的社會有了初步的認識,最后決定他一定要跟金八他們拼一拼!曹禺先生塑造的方達生形象看似是一個傻里傻氣的人,盡管后來他明知道金八等人勢力的強大,但還是決定留下來。方達生身上一直都有種救贖的人性,從對白露和小東西的救贖到最后決定和黑暗勢力拼一拼,自始至終他都在尋找光明,他不相信金八有這么大的勢力,他不過是一個人。方達生身上的救贖悲劇人性已經建立在圣人的位置上。只有像方達生這樣“傻氣”的人才能拯救這黑暗的吃人的社會。而這也恰恰是曹禺所說的聰明人,在金錢充斥,人性毀滅的都市生活中,方達生并沒有迷失自我,反而更加清醒的認識到要與這黑暗勢力做斗爭。這是日出的時刻,更是光明的開始。將要落幕之時,張喬治對陳白露說他做了一個可怕的夢,他夢見滿樓都是鬼亂蹦亂跳,但忽然哄地一聲大樓倒塌了,許多人都壓在了底下。他的夢冥冥之中也暗示著黑暗社會即將過去,光明將要到來。戲劇的結尾并沒有以陳白露的死就此結束,而是在砸夯工人們洪亮的歌聲中落幕。第二幕時砸夯工人的集體歌聲就與那些鬼似的生活的人形成強烈對比,砸夯工人高亢的《軸歌》始終洋溢著勝利的喜悅,傳遞著希望與力量。“日出東來,滿天大紅的日子”即將會到來。作家寫《日出》時也記錄了這樣的心情:“我要求的是一點希望,一線光明,人畢竟要活著,而且應當幸福的活著,腐肉挖去,新的細胞會生起來。⑤讀完《日出》,我并未感到消沉,相反獲得一種令人振奮的力量去同那黑暗勢力做斗爭,黑暗終究會過去,黎明會到來,我們每個人都將獲得新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221,236頁
[2]田本相:《日出》論 文學評論.1981.03.02
[3][4]曹禺戲劇集-論戲劇[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5]吳可:黑暗中重生 浴火中永恒—《日出》悲劇性的重新探討:吉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