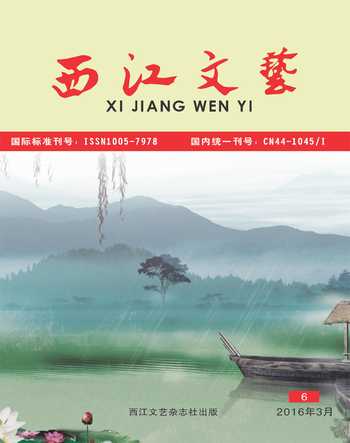淺論沈從文的精神流亡
張亞麗
【摘要】:薩依德說過,流亡是知識分子的命運。1949年新政權建立左右,意識形態全權話語與個人話語發生了沖突,沈從文不能自由地進行文學創作,選擇以“流亡”來堅守自己的文學理想和生命意識。他的這個抉擇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自救,為自己的生命在意識形態全權話語中找到的避難所。
【關鍵詞】:艱難的抉擇;精神的流亡;本心的堅守
沈從文,早年飲譽文壇,卻在建國后擱筆,轉向歷史文物的研究。對此,無數人為之可惜,把它稱為生命的消失,即所謂提前死亡。然而,金宏達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當世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遷之后,如同一道河流干涸,再無創作文字汨汨從他的流淌,沈從文重新出發,在另一個路口。不知道有多少人,為失去一個出色的作家惋惜,其實呢,‘洛陽親友若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1]沈從文退出文壇看似是個悲劇,實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正如他自己在美國圣若望大學演說,選擇歷史文物,是健康的選擇,而非消極的退隱。他的這個抉擇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自救,為自己的生命在意識形態全權話語中找到的避難所。
一、艱難的抉擇
“寫作不是職業,確是一種事業”[2],是“堅持到死去干的莊嚴工作”[3],“文學是一種事業”[4]等,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對待文學的態度:文學是事業,是信仰,也是宗教。在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為了維護文學的嚴肅性,多次參與了文學運動的論爭,其焦點都是反對文學與商業或政治結緣,維護文學的獨立性。沈從文在《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分析文學運動得失時,看到文學與政治或者商業結緣,表面上文壇是活潑熱鬧一片,實則其墮落傾向早已顯現。他反對“作品過度商品化”和“作家純粹清客化”,堅決維護文學原有的莊嚴性。當文學的嚴肅性受到威脅,并依附于自己厭惡的政治上時,他是堅決摒棄的,這也預示著沈從文建國后的人生選擇。
建國后,沈從文必然會走上流亡之路。“在人民意識形態話語進入社會存在之初,知識人面臨著一個是否放棄個體言說并認同于意識形態總體話語的自我抉擇,這也就是決斷自己是否流亡”[5]。新的政權要求文學不再是個人言說的表達,而是為政治服務。正如“新的時代要求于人的是‘忘我‘無我……而將‘我溶解于政治進程中,社會要求中。”[6]新時代將個人的文化活動引入政治,皈依政治并為其服務。沈從文面對這樣的新政權及其文藝要求時,出現了艱難的抉擇,是堅守自己初衷維護自己理想的文學夢,還是在意識形態全權話語中拋棄自己的個體言說與之妥協沉淪。在新政權全權專政中,他看到了意識形態全權話語對個人話語的擠壓,但讓他斷然放棄幾十年的寫作,這必然是個艱難舍棄和痛苦掙扎的漫長過程。在《父與子》的對話中,沈從文與兒子一起想象著、設計著“未來”的作家夢,還說要努力、好好地寫,創造20世紀新的經典;甚至為了靠近新生政權,他主動參加了建國初期的兩次思想改造等,這都表明在全權專政起初,也受到了沈從文的擁護和獻身。
但他手里的筆變得越發沉重,重到不知哪里才能停靠。之后他的思想不再是之前的透明、純真,開始變得隱晦、晦澀,越來越轉向精神內在。“經過了游移、徘徊、極端興奮和過度頹廢,求生的掙扎與自殺的絕望……反復了三個星期,由沸騰到澄清,我體驗了一個‘生命的真實意義。”[7]寥寥數語,把選擇抗爭還是沉淪時的矛盾與復雜心境呈現出來。原本磨刀霍霍,準備大干一番事業,寫他個一二十本,卻遭到迎頭棒喝。文學在新的全權專政下出現了轉折,“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成為‘綱領性的指導思想;文學寫作的題材、主題、風格等,形成了應予遵循的體系性‘規范。”[8]顯然,沈從文不能適應左翼文學對當代文學方向的預設與規范,認為“對土改,對文學從屬于政治,對文運活動的政治效果,我都感到懷疑,說過些毫不切合實際的空話。”[9]因為不能適應或者說不愿適應這樣“一尊獨霸”的文藝背景,沈從文選擇居于主流之外抗拒進行流亡。新政府成立初期,他抱有創作的希望,當某種話語全權意識形態化時,他對其意識形態全權話語產生了懷疑,甚至有這樣的發問“丁玲他們為什么去了,反倒沒有什么作品了呢?”[10]最終,他在自己的文學夢中哀婉凄絕。“20年30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11]正是由于“思”而非“信”,沈從文選擇主動擱筆,這其實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希臘小廟”,維護自己的文學尊嚴。
二、精神的流亡
“流亡是人的存在的一個生存論現象。”[12]分為可見的流亡即地域上的流亡和無形的流亡即精神上的流亡。1949年新政權建立左右,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面臨著地域上的流亡,還面對著精神上的內在流亡。阿多諾曾把知識分子釋為永恒的流亡者。薩依德也論述了知識分子流亡的相關說法。有著嚴肅的文學觀和生命意識的沈從文,面對意識形態全權話語壓迫個人話語,必然會為了個人的自由話語作出抗爭,在全權專政中進行精神流亡。
知識分子的圈外人身份,最能以流亡的情況加以解說即永遠處于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1949年之后的沈從文,一直處于邊緣和圈外。面對新政權的建立,“眼前的就永遠是不屬于我的。一切存在和個人都若無關系”[13]他人都沉浸在新政權建立的歡樂氛圍中,沈從文周身卻縈繞著寂寞、孤獨、疏離。通過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對新政權的深刻思考。他的知識分子批判意識使他對一切都存疑,不隨波逐流。新的政權建立,一切都得重新安排、調整和計劃,“人的犧牲還是萬難避免的事。出于個人問題,對現實或承認,或否定,總之隨處隨事都必然會有廣泛消耗與犧牲。”[14]知識分子在新的政權中如何凸顯,新政權又如何清算知識分子。他認為新政權“對知識分子莫取壓迫態度,實較賢明的措施。”[15]而“有些人是有問題,從一個新的制度新的尺標衡量下,看得出來的。問題正逼迫著他,不能不尋求明白簡單正確的答解,死或生。”[16]新中國成立前夕,關于知識分子如何自處于意識形態全權話語的問題,沈從文尋覓的答案是死,他“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17]這些舉動顯然可以看到他當時的決絕,以及徹底毀滅自我的決心。
從歷史的情形來看,流亡話語是政治迫害的結果。沈從文的自殺與其說是對新政權的膽怯,不如說是以決絕地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個人話語。“這個世界如不改造,實在沒有人能審判誰。凡屬審判,盡管用的是公里和正義作護符,事實上都只是強權一時得勢,而用它摧殘無辜。”[18]一旦某種話語全權意識形態化,個體性話語就不可能有容身之地。正如50年代,以延安文學作為主要構成的左翼文學,成為唯一的文學事實,開始對其他話語形式進行排擠。如郭沫若《斥反動文藝》、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1949年初北京大學校園里打出“打倒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標語,這都屬于意識形態全權話語。“某種話語類型與現實政治權力的結合,并導致對另一種話語類型的政治迫害,亦是話語本身的一種生存論規定。”[19]面對所有這些,沈從文清醒地發現自己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他選擇主動遠離文壇。所有人為新的政權歌功頌德時,他以“病”、“無知”來掩飾自己的精神處于異在狀態,默默地進行精神流亡。
三、本心的堅守
1949年,沈從文從創作轉向文物研究,看似前后沒有任何聯系,實則都是對本心的堅守。1949年之前,沈從文為了奪得個人話語權,參與幾次文學論爭,與當時“一尊獨霸”的文壇現象進行抗爭,希望重建自我話語的可能性。1949年之后,他由文學創作轉向文物研究,表面上看是其生命的消亡,甚至死亡,實質上卻是另一種生命形式的沖擊與重建,采用迂回的方式在全權專政中進行精神流亡,找到個人話語訴說的可能性。
在其精神流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一以貫之的生命意識。對生命的看法,使他不愿讓自己的生命受到外界的束縛,尤其是被自己視為信仰的文學。新政權要求新文學符合意識形態的要求。“我是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稱,和普通社會總是不合。一切來到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制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20]他否定現存社會的標準,選擇在社會變革中流亡。對于文學創作,他也曾說過“不是誰不準我寫,也不是誰規定我只能寫什么,而是自己心里有個限制。”[21]當某種話語一尊獨霸時,必然會與其個人話語表達發生沖突,流亡從而產生。沈從文無法在意識形態全權話語中找到個人言說的可能,他選擇退出文壇。退出文壇并不等于放棄了文學,而是選擇用沉默的方式來守護自己的文學理想。退居到文物研究,可謂是他在作最后的搶救與堅守,極力地保留最后一塊“思想文化自由”的天地。
總之,終其一生,幾度浮沉,毀譽盡成煙云。盡管建國后的沈從文沒有什么文學創作,但文物研究的成果碩碩,這早已彌補了建國后無作品的缺憾。他用自己的一生在實驗著自己塑造的邊城世界即“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參考文獻:
[1][10]王珞.沈從文評說八十年[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2.222.
[2][3][4]沈從文.沈從文全集·17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333,333,189
[20]沈從文.沈從文全集·12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46.94
[5][12][19]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M].北京:三聯書店,1996:258,261,265
[6][7][9][13][14][15][16][18]沈從文.沈從文全集·27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6,3,55,16,4,5,10,39
[8]洪子誠. 中國當代文學史[C]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5
[11]沈從文.沈從文全集·9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58
[17][21]凌宇.沈從文傳[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54,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