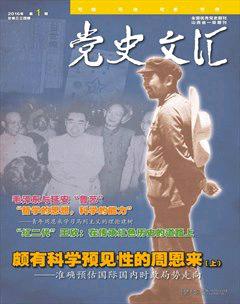劉亞雄:“我要走的道路正是參加共產黨”
芮原
劉亞雄是五四運動后三晉婦女參加革命的先驅者之一,1924年參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革命工作60余年。青年時代的劉亞雄,正直熱情,無私無畏,在斗爭洗禮中確立與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主張。
不守紀律的“壞學生”
1901年10月22日,劉亞雄出生于山西興縣黑峪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父親劉少白早年間曾考取清末貢生,后來在辛亥革命的大風暴中接受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成為一名有愛國心、正義感的開明紳士。作為長女,劉亞雄被家人視為掌上明珠,倍受關愛和疼惜。
一般的農家女孩,受封建禮教約束,在家專事女紅,大多極少拋頭露面。而劉亞雄在家人的嬌慣下逐漸養成了任性灑脫的性格,不僅對縫補刺繡毫無興趣,而且還和村里的男孩子們一起爬墻頭,嬉戲打鬧。
在8歲那年,劉亞雄被家人送到距黑峪村50余里的韓家截村的娘舅家里讀書。她的舅老爺是前清秀才,在村里辦有一間私塾,這里成了她接受啟蒙教育的地方。因舅老爺思想守舊,為人古板,每每上課,總會板著面孔端坐正堂,滿口之乎者也。其他學生正襟危坐,目不斜視地跟著先生讀圣賢書。“野”慣了的劉亞雄忍受不了這種沉悶的學習環境,也對整日吟誦似懂非懂的《百家姓》 《列女傳》《千字文》等陳舊詩書文章不感興趣,因而不肯用功。舅老爺雖屢次訓誡但仍不見其改觀,無奈地搖頭嘆息:“豎子不可教,朽木難雕也。”但劉亞雄絕非“朽木”,她反感的是呆板枯燥的舊學問,對新鮮活潑的觀點、事物興趣極高,對于父親給她買的新書愛不釋手,直到年老仍能默念其中的句子。
鑒于此,提倡興辦女學的劉少白將11歲的劉亞雄帶到太原,送進陽興公立女子學校讀書。小學畢業后入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學習。對此她曾撰文回憶:“在這所所謂的師范學校里,卻遇到各式各樣的管束,住校學生假日回家必須親屬來接,或委托他人拿上學校出入證來接,否則終年不得出校門”,“至于學生到校外參加社會團體的活動,如體育文娛組織也是不容許的,若帶有政治色彩,那就更不在話下”。
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劉亞雄與一些同學在校內辦起了一種油印刊物,在上面寫些愛國文章,針對時局發表議論。她的思想也逐漸發生轉變,更熱衷于接觸和了解各種救國思想和觀點,如宣傳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新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寫的書、資產階級文學家胡適的白話文等,在懵懂中尋求救國之路。當劉亞雄得知同學趙文靜等二人因無力抵抗封建婚姻而遁入佛門后,竭力勸說她們繼續學業,與包辦婚姻抗爭。但在劉亞雄勸說下返校的趙文靜等2人,學校不僅未給予理解和同情,反而以玷污學校名譽為由企圖開除她們,校長張理壽還氣勢洶洶地對規勸二人的劉亞雄指責道:“你目無校規,也太膽大包天了吧!誰叫你把趙文靜找回來的?這種傷風敗俗的人就不配做學生!”劉亞雄毫不示弱地反駁道:“女子也是人,憑什么遭受凌辱還要忍氣吞聲?為什么男子為所欲為卻要讓女子承擔痛苦?這算哪家的風,什么社會的俗!時代不同了,我希望校方注意潮流、識時務,改變這種不合理的校規,收回開除趙文靜二人的成命,否則被動的局面將不可收拾。”
張理壽理屈詞窮,鑒于大批學生的反對呼聲,不得不收回了成命。而劉亞雄這個不安分的“壞學生”則成了學校當局的眼中釘,在又一次因爭取學生正當權益而與校方公開談判的過程中被學校記了大過。
站在北京女師大 “驅楊”斗爭前列
1921年底,劉亞雄從省立女師畢業,在校期間與校方的抗爭經歷使她的思想得到進一步轉變,她希望從事教育事業,以此啟發婦女的覺悟,更好地幫助她們解除痛苦。抱著這種理想,她進入省立女師附屬小學當老師。一年后,為了更好地從事教育工作,她以高分考上了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大學(即北京女師大),并于1923年秋正式進入北京女師大文預科學習。
入校之初,劉亞雄潛心讀書,以期在學業上有所成就,但是現實使她的愿望落空。1924年冬,震動全國的北京女師大學潮發生。事情的起因是時任女師大校長的楊蔭榆思想守舊,專橫跋扈,在學校排擠進步教授,安插親信,限制學生自由,師生多有不滿和怨言。恰巧有3名學生因內戰動亂回家而未能及時返校遭學校開除。面對校方的無理決定,劉亞雄和趙世蘭、許廣平、蒲振聲、鄭德音等人挺身而出,組織學生召開會議成立學生自治會,多次與校方交涉,希望學校收回處理決定,并改變不合理的教學管理制度。但楊蔭榆不僅沒有接受學生的合理請求,還在1925年5月9日開除了許廣平、劉和珍等6名學生骨干,并封鎖了學生自治會辦公室。她的這一行為不但未能平息風波,反而激起廣大學生的反抗,學生會也封閉了楊蔭榆的辦公室,貼出大標語,不許她進校。學生集體罷課。5月27日,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知名教授聯名發表《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支持6名被開除的學生,指責楊蔭榆“混淆黑白”“偏私謬戾”。校方和學生的斗爭逐漸走向白熱化。與此同時,負責對外聯絡工作的劉亞雄和趙世蘭往來于學界名流、社會團體和新聞報館之間,積極尋求各方支持。在她們的努力下,中共北京市委派地下黨員夏之栩秘密入校指導學生運動,李大釗也公開為學生提供幫助。
當時的劉亞雄為了爭取學生的正當利益,工作起來廢寢忘食。晚上,她用報紙罩著燈泡,伏案刻寫材料并動手油印,常常整夜不眠;白天,她四處奔走,往來于兄弟院校之間,散發油印傳單,向同學們詳細介紹女師大學潮的始末,并與市學聯、《京報》 《世界日報》等報社團體建立了密切聯系。
一場“驅楊”學潮,逐漸演化為反對北京教育界獨裁體制和北洋軍閥政府的運動。感到事態日益嚴重的北洋軍閥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于1925年8月1日采取強制措施,下令封閉了女師大,并調集軍警把守校門,不準學生自由出入。幾天后,還停水停電,意在瓦解學生們的斗爭意志。被封鎖在校外的劉亞雄等人積極與北京學聯和各兄弟院校聯系,籌款購買饅頭、包子、燒餅、罐頭等食物和飲用水,用筐投進女師大校內,支援并鼓勵校內學生繼續抗爭。8月22日,無計可施的大批軍警沖入學校,逮捕住校學生40余名,反動當局也貼出告示,宣布解散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
這些柔弱的女學生并沒有因此而屈服,在中共北京市委地下組織的指導下,劉亞雄等人積極投身到了復校工作中。在北京宗帽胡同14號租賃民房,以魯迅為領導,成立學校委員會,聘請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知名教授,辦起了由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組織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魯迅、許壽裳、李石曾、易培基等進步教授和李大釗紛紛給學生義務授課。身為歷史系學生的劉亞雄,有幸聆聽了李大釗等教授所講授的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初步學習了馬列主義基本理論。12月,隨著北京革命形勢逐漸有利于民眾,易培基取代章士釗出任教育總長,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復校,劉亞雄等人回到原校,為期一年的女師大“驅楊”斗爭終獲勝利。
義無反顧走上革命道路
女師大學潮鍛煉和教育了劉亞雄,使她的思想由為受難同學出頭的“義憤填膺、仗義執言”,轉變成為爭取民族崛起而犧牲奮斗的“有理有據、目標明確”。在那段從事外聯的工作中,夏之栩曾多次給予她幫助和指導。她還認識了趙世蘭的弟弟、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之一的趙世炎,在相處中,趙世炎向她介紹了蘇聯的革命、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宣言》等馬列書籍。
在一次次運動和斗爭中,劉亞雄的思想日漸成熟,隨著對中國共產黨認識的加深,逐漸樹立起了追求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理想,她說:“我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不是枝枝節節所能改好的,沒有徹底的變革是不會有什么出路的,救中國只有共產黨,我要走的道路正是參加共產黨。”并正式提出入黨申請。1926年2月底,黨組織在經過考察之后批準了她的入黨要求。在隨后的黨組織生活中,劉亞雄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和認識水平,她以女師大代表的身份,被黨組織委派到北京學聯工作。劉亞雄終于以一名共產黨員的身份站到了學生革命風暴的中心,迎接新的斗爭挑戰。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學生為了抗議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在段祺瑞政府門前游行示威時,反動當局竟下令開槍鎮壓。47人被打死,150多人被打傷,史稱“三一八”慘案。沖突中,女師大學生代表劉和珍、楊德群犧牲,張靜淑受重傷。因病留守學校的劉亞雄幸免于難。聽聞慘案發生,她悲憤、焦急地立刻帶領部分留守同學趕到慘案現場,希望救援遇難同學,但反動當局卻封鎖現場,不準她們接近。經過激烈交涉,劉亞雄等人終于在當晚搶出了犧牲同學的遺體和受傷同學。25日,女師大舉行悼念活動,追悼劉和珍、楊德群二人,魯迅撰文稱她們是“真的猛士”,并發出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的怒吼。
然而,事情并沒有完結。“三一八”慘案后,奉系軍閥張作霖進占北京,瘋狂鎮壓進步勢力和愛國運動,殺害《京報》社長邵飄萍,查封市學聯,最后還以教育部的名義開除了20多名北京學聯執行委員會成員的學生學籍。劉亞雄名列其中。她后來回憶說:“從1924年鬧反楊運動起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被開除,我的思想變化很大,開始我看問題是直觀的、簡單的,漸漸認識到社會的不平,階級的矛盾,斗爭的復雜、尖銳。在這一年半內,親眼看到帝國主義如何蹂躪侵略中國,軍閥如何賣國欺壓人民,反動走卒如何助紂為虐。親身體會到人民對敵人的仇恨,反抗斗爭的堅決,認識到國家要獨立,人民要翻身,就要斗爭、要革命。”
面對北京的嚴酷斗爭形勢,劉亞雄等4人受黨組織委派,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在那里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這讓她把所經歷的鮮活斗爭實踐提升到了更高的理論層面,同時也讓她有機會接觸和學習到更為具體、生動的革命經驗,成為指導她一生從事革命工作的寶貴財富。劉亞雄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強剛毅、信念堅定的共產主義革命者。1928年底,中國國內形勢急劇逆轉,中共黨組織受到嚴重沖擊,急需共產黨員回國參與斗爭。根據黨的指示,劉亞雄中途輟學回國,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責編 孟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