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鄉村記事
羅賓·吉爾班克 胡宗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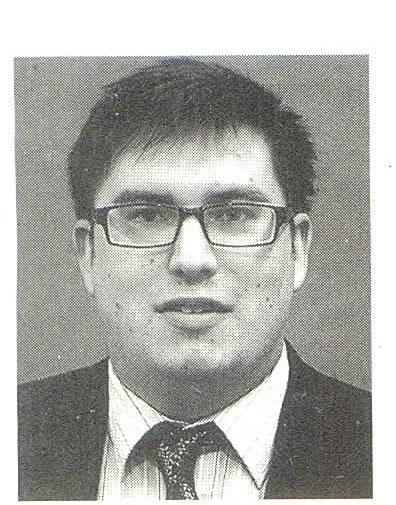
農民是不朽的中國。在西安的陜西省博物館里,人們可以看到一尊漢代墓葬的石雕,是一個人趕著牛拉的獨角犁在犁地。在城外,也可以看到被上演了兩千多年的這一幕景象。在田野里,一群群的人彎著腰,在沒完沒了地辛勞著……不論到哪里,不論人們用什么工具,風景里永遠是草帽下彎著腰的人。
——引自芭芭拉·W·塔奇曼著《來自中國的函件》第17頁
四十年前,在毛澤東和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打開僵局會晤的前夕,美國有名的歷史學家芭芭拉·W·塔奇曼對中國進行了一次調查性的訪問,目的在于讓自己的同胞對這個國家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陜西可能以其豐富的古跡和當代中國西部糧倉的聲譽被選為她造訪的地方,她的分析帶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塔奇曼著眼于拂去當地復雜的歷史塵埃,把以前受奴役的農民和“被解放了的農民”后代分開了。前者是受自我認識束縛,被孔子稱為是“小人”,是維持這個龐大帝國螻蟻般的蕓蕓眾生。而后者則是接受了宣傳和教育,認為每動一锨土和每種一粒糧都會使自己更加靠近社會主義理想。實際上,老百姓長期以來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無休止地勞作。在我心里,毛姆在引用莊子語錄的時候,對此做過更加精辟的闡述。他說:
“在中國,馱負重擔的是活生生的人,‘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引自毛姆著《在中國屏風上》“馱獸”
這種觀點現在早已過時了,現代的鄉村男女把自己從父輩的生活困境中解脫了出來。
關中平原的現有人口超過了兩千五百萬(比澳大利亞全國的人口都多),但除了西安、寶雞、咸陽和渭南等城市外,到處還是彌漫著農村的氣息。沿著高速公路前行,映入眼簾的一切新穎而別致。忽然就冒出了許多獨立的和半獨立的住宅,屋頂上通常都裝著小型的太陽能設施。唯一高點的地方是丘陵、黃土高坡和古代皇帝們的墓冢。單調的平川地帶上,點綴著瓷磚裝飾、古香古色的樓房。農民新建的房子幾乎都是不協調地裝著兩扇大門,每扇門上都鑲著門套和很大的門環,上面有主人喜歡的標志。很少有麒麟,因為人們不期望有不吉利的訪客。大多數人家的門口寬大,可以讓電動車和農用拖車出入,農用拖車晚上就很安全地停放在院子里。
生死輪回在這里不可避免地上演著,在地上的角落和田野的空間都可以看到一簇簇的墓碑,好像各有各的特色。簡單一些的就只有一個墓堆,而在有的地方則有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有與逝者有關的后人名字。新墳不難辨認,普通的花圈通常都是一個大的同心圓,周圍是紙做的花和彩帶,中間掛著挽聯。在我看來,這些多姿多彩的花圈怪怪的,讓人會聯想到射箭用的靶標。不管如何,仔細一想,城里人的生死極限既安全又衛生。在西安的一些特定的地方,特別是在文昌門里邊附近的花卉街和買戲衣的街道,還有人在做花圈。但這些商品很少見到與死亡相關,在毛澤東時代,城市里就在嚴格執行火葬,這一點從未變過。火葬場和墓地都是建在遠郊。
只要是到了鄉下,就會親眼看到對逝者的敬畏依舊是那么隆重。葬禮的色調是白色,而不是黑色。從人去世到最后下葬,有七天的哀悼日。禮儀規定逝者的親屬要從頭到腳都著白色,頭上戴的帽子和平時醫生和年長的穆斯林女人戴的一樣。悲痛與日俱增,當一個人的最后一位父母離世的時候,其子女有責任盡孝,一舉一動都要表現得無比悲痛,連日常事務都沒法打理,比如要趿拉著鞋,不能全穿上。
我的一個朋友,家住在秦嶺腳下,他給我講過一個傳奇故事,說他們一大家為了哀悼長輩和高壽的姑奶奶,沿用舊禮儀,姑奶奶卻死而復生了。他姑奶奶當時已九十多歲了,還保留著新中國建立前女人愚昧的“三寸金蓮”。她不用人扶,可以戰戰巍巍地走到幾米遠的木凳跟前并坐下來。一天早晨,她的侄女發現姑姑窗前的百葉窗沒有被掀起,遂進屋一看,發現她一動不動地坐在墻角里。下葬前安排有七天的哀悼日,放靈柩的是上個世紀的一張老長桌,旁邊堆滿了白玫瑰和康乃馨。鄰居們來的來,去的去,所有來的人都是給一碗面,但大多數人都沒有動。幾天過去后,姑奶奶的面容變得更加扭曲和不起眼了,不像桌子上方黑白照片中的她那樣相對富有活力了。于是人們決定應當再給她的臉上蒙一層遮面的薄紗,這樣既可以讓人看清她的臉,但卻不至于露出她沒有表情的面容。當面紗接觸到她的額頭時,姑奶奶的眉毛抽搐了起來。由于不清楚這是不是人死后的罕見反應,其侄子和侄女都退到了邊上。過了一分鐘,她的喉頭也動了,接著便咳嗽了一聲,“復活”后,老太太又活了兩年。在她最終離世后,家里人花錢從城里請了兩位有經驗的醫生過來證實她確實是“不在了”。
在關中農村,孝道和迷信在人們的心里根深蒂固。正如弗朗西斯·亨利·尼科爾斯所言,從嬰兒一來到這個世界,勉強糊口的父母就會絞盡腦汁地想,怎樣才能讓自己的孩子避禍祛邪:
陜西孩子的脖子上戴一個用繩子拴著的“長命鎖”,認為這可“鎖”住其魂,不讓厲鬼偷走。孩子特為此自豪,只要跟人一認識,就會常常拿起來讓人看。雖然孩子的名字來自于“起名手冊”,但父母很少叫孩子的名字,而是經常給孩子起一個低級動物的小名,如“癩疙寶”或“亥娃”。這也是為了防找孩子魂的厲鬼,鬼不會對一個叫“癩疙寶”的孩子像對其他叫真名的孩子那樣有興趣。陜西的男娃幾乎剛會走路,就會把頭頂剃光,只留一小撮頭發,預備以后編辮子。
——引自弗朗西斯·亨利·尼科爾斯
《穿越神秘的陜西》第134頁
以前,嬰兒死亡率很高,人死后無子乃是最大的不幸,故做父母的認為采取這些古老的做法很管用。
儒、釋、道的融合以及本土信念形成了老一輩人對宇宙和周圍環境的認識。家家戶戶都有神龕,供奉的是父母的相片、太上老君或是土地公。土地公的名字就意味著他是“地神”,其長相接近圣誕老人——是一位慈眉善目,白須像餐巾一樣垂肚的老人。土地公掌管土地及其生長的萬物,土地公和土地婆偶爾也有收禮的嗜好,要是有人家慶祝大豐收,讓門邊喜洋洋的神像同樂也沒有什么壞處。畢竟農民是靠土地在過日子,其歸宿也是腳下的黃土。土地公既不用神權報復人,也不反對人們以他的名義,修建華麗的廟宇祭祀他。
英國傳教士和英語教師威尼弗雷德·加爾布雷斯注意到:“對中國人生活比任何宗教影響都大的是對土地的觀念和鄉土生活的重要性。”(見加爾布雷斯著《中國人》第四章)泥土氣息是關中民間文化和幽默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許多荒誕的笑話都和夫妻生活有關,如夫妻為了要孩子而產生的誤會。由于一大家人都是睡在同一個炕上(炕就是用土坯壘起來,底下有加熱通道的床),于是就有了各種各樣的黃色笑話。常常是新娘渴望有一個真正的愛人(陜西方言稱之為老漢),但卻命中注定和一個比自己小得多的男孩訂婚,有一首歌謠表達的就是這種黃色但卻辛酸的情景:
十八大姐八歲郎,
晚上睡覺抱上炕,
年齡太小不是郎,
說是兒子不叫娘,
等到郎大妹又老,
等到花開葉又黃。
新娘的這種感受顯然是以前的事情了,國家現在法定的結婚年齡是女性二十,男性二十二。即便如此,這種泥土的氣息又有了新版本。一個有名的笑話是,縣上的領導去看一個村長,領導非常想知道經濟發展對農村人生活的影響,就直接問:“村里的GDP有多少?”村長仿佛既迷惑不解,又很尷尬,滿臉通紅地說:“天啊!那當然是太多了,我們能不能先開始數馬的和牛的?”用陜西話說GDP(這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外來詞)聽起來跟“雞的P”一樣。GD就是英文的chickens(雞的),而P就是指母雞身上的生殖器官了。
關中鄉村和城市之間的關系是很奇特的,在有些方面是共棲的。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青年人離開農村的家,去打工和追求高等教育。這些人也許依舊保持著對家里人的孝順,給家里很大方地寄自己的工資。然而,實際上除了過年和節假日,沒有幾個人重回黃土地。年輕人的愿望是能拿到一個城市戶口,長期在那里待下來,并成家立業,像城里的西安人一樣享受教育、福利和其他一切。
類似版本的故事在無數次地被演繹著。在公交車上和生人說話,人有時感到這并不是在聽某一個人的身世。現在,這樣的故事少了。過去十幾年來,鄉下又成了人們休閑和創業的地方。原先人們覺得活在鄉下是個恥辱,而現在卻成了自豪的象征。要是愿意,你可以想象一下這個情景:在火車上,一位衣著光鮮的城里人不得不坐在一位邋遢的生人對面,其身上還帶著一絲肥料味。火車導軌的時候,他們的膝蓋就會碰在一起。那位鄉下人從他的臟短褲口袋里掏出一個響鈴的蘋果手機,他對面的人驚訝得都不會說話了,于是屈尊問人家:“你是農民嗎?”對方的鄭重回答是:“不是,我是農夫。”接著便會拉起袖子,露出自己的瑞士手表,那也許值城里人一個月的工資。坦率地講,他想傳達的信息是他是個農民企業家——一個找到了賺錢竅門的人,用不著每天都去種地了。
旅游指南和日常生活中現在最“火”的詞是“農家樂”,不好翻譯成英語。政府的媒體傾向于用帶有美國味的蹩腳縮略語“agri-tainment”(是把農業和娛樂兩個詞合在了一起),其他的翻譯有“joy in the farmhouse”(農舍里的樂趣)和“merry farm-hostel”(快樂農家旅館)。我個人喜歡有基本元素的“country fare”(鄉村行)。這個詞包括圍繞著鄉下農戶的多種活動,如鉆樹林、進田地、嬉水和爬山。十年前,農村人的年收入大約是在9000 至10000元人民幣(900-1000鎊),要是家里可以提供釣魚、摘果、采菇和教一些傳統手工藝,其收入也許可以翻十倍。“農家樂”剛開始就是搞個活動,或者是個農家小飯館。一旦開始源源不斷地賺錢,下一步就是把外面的房子改為可以過夜的住處。渴望一年毛收入達到十五萬到二十萬的農民,就會想著搭個臺子唱秦腔或跳民間舞。
也有嚇人的故事,說外國人興高采烈地摘了半天核桃,等把袋子拿去一稱,才發現不得不交幾千塊錢。一般說來,“農家樂”讓人舒適,甚至讓人有一種懷舊感。食品摻假在城里是個炙熱的話題,最近的謠言說市場上有為了看起來鮮黃,被硫黃熏過的生姜,和被撒上了石灰粉的柿餅。好多客戶,從厭倦了生活的企業高管,到沒有孩子拖累的父母在周末終于有了空閑,這些人便陸陸續續出門,去品嘗從不遠處的地里和窩里拿來的東西所做的飯菜。
我初次感受陜西的鄉村味,是到旬邑縣一個種蘋果的村子——唐家村,那兒是咸陽的管轄區,但還是開車在危險的山路上走了整整三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邀請我的幾個同事和熟人的是咸陽文物局的副局長龐聯昌先生,當他聽說我是英國人時,就很遺憾地說他才上任幾個月,錯過了隨“兵馬俑”去倫敦的機會,“兵馬俑”曾在大英圖書館被短期展覽過。他特別感興趣的是“秦始皇兵馬俑”當時的展出情況。我告訴他那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墓葬展覽后最吸引人的一次展覽。因為游客都想和“兵馬俑”面對面,主辦方就采取了一個很有創意的辦法。他們在古老的像蜘蛛網形狀的閱讀室書桌上面裝了現成的地板,來支撐“兵馬俑”和青銅器的重量。對英國人來說,這個空間意義非凡,因為過去有無數作家曾在那里做過研究。卡爾·馬克思就是在那里完成了《資本論》。龐先生感慨道:“啊,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締造者聚在了同一所屋檐下。”
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詞,那次的一日游是典型的“農家樂”游。在看了幾處上百年的老磚房和玻璃柜臺中做工粗,價格高的手工鞋、繡花鞋墊和坐墊后,我們就被帶到了路邊的飯店里。
這次旅行物有所值不僅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到農村,也是我第一次為中國酒陶醉了。穆濤先生是西安有名的文學編輯,他伙同另一位教授想用當地的酒使我上臉,把我灌醉。這種酒一般為45度,而且一次干杯要喝三小杯,這個任務沒法推辭。
穆先生的一個強項是引經據典,內容總是帶色,說話的方式重在嚇唬人。他問我知不知道晉朝的王羲之,這在英國的綜合院校里不是必修的課程,但我喜歡他其雄逸矯健、中和典雅的書風,其書法如人所言“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穆先生說的軼事如下:“有一本文人雅士作于紹興蘭亭的詩集,王羲之以行書為序,原作上有四十枚精美的印章。此作為歷代人所敬仰,三百多年后,唐太宗尤愛,特想得到原作,便派一大臣向珍藏原作的和尚索要。這當然不容易了,那個大臣化裝成一個潦倒的書生,與和尚閑聊,并從其眼皮下騙走了這一寶物。當然,人若知之為寶皆想盜也!但實際上,這不過是一場風雅聚會的產物。當時有四十二位文人雅士在蘭亭‘修禊事也,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一觴一詠。我們可以想象這些名士“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直到酩酊大醉。清醒后,王羲之又寫過多幅,均無第一幅的神韻。還有人說王羲之養鵝,根據鵝的體形及行姿練習執筆和運筆。”穆先生有意吸了吸鼻子,咳嗽了一聲,扶了扶眼鏡,左手拍了一下我胳膊。然后右手像鴨脖子一樣扭了扭就端起了酒杯,他人若是這樣就顯得有點“娘娘腔”了。
隨著一聲“干杯”就要一飲而盡。中國人,尤其是陜西人飲酒的禮數可以追溯到《周禮》。《周禮》成書的時間也許在周后幾百年,但卻是中國文化的基石經典。鄉飲酒禮在《周禮》中是單列出來的,為了表示對主人和同伴的尊重,大家要一起共飲三杯,然后是桌上的人逐個相互敬酒,根據人的職務或年齡打關。有時候酒到一半,也有不守規矩或至少是走樣的。如沒有任何理由,我都要和龐先生與穆先生各喝三杯。在大口吃雞蛋的間隙(這被證明能化解酒),我的肚子開始不舒服了。有人把這比作是喉嚨上了火,但讓外國客人多喝點的習俗還是沒有變,直到把瓶子喝干。
如果說我的消化道已經對我的嘴不滿意了,那我的“下水道”還不知道下來會發生什么?一打聽,村子里的衛生設施就是在外屋放一個鐵通,用一個布簾子遮著。雖然味道不大,但當時桶里的黃銅色液體已經快滿了,大概是好多人膀胱噴涌的結果,只要再加一點,就會溢到地面。我猶豫著揮了揮手,便又把手插進了上衣口袋。這時,布簾拉開了,是穆先生,他的臉紅紅的,那是因為喝酒,而不是因為尷尬。到今天我也不清楚,他到底也是來尿的,還是來看外國人能不能像當地人那樣蹲坑。
那個屎尿桶的景象盤踞在我的腦海里,直到我們來到一個果園,我才幸運地在附近找到了一處堆滿了干草的田地,這就方便多了。每個排隊的游客都有兩箱自己從樹枝上摘來的大紅蘋果,一位胡子焦黃的老漢(胡子可能是被一直吊在嘴角的煙頭熏黃的)在用膠帶封上箱子前都要檢查一下。他從眼鏡上瞄了我一眼說:“我看,你是第一個來旬邑的外國人,你回去以后宣傳我們的產品很重要。”“我中午喝了18、21,有可能是24杯酒。”我說,“我也有可能是死在這里的第一個外國人。”
如果習慣了鄉下的簡樸和舒適,那就是有很好的機會來清洗被西安的空氣所污染的肺了。我去農村最多的一個避難所是寶雞東邊鳳翔縣的一個村子,鳳翔有幾處值得推薦給游客的特色去處。這里曾經是被城墻圍著的雍城,從公元前677年到383年是西周人的首都,現在上了五十歲的人還能想起城墻完好時的情景。與后來的漢長安城不同,雍城的城墻歷史更加悠久,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了。方圓三公里的土地不再有任何防衛的意義,城里邊到處是搭建的破舊房屋,農民們不得不躲避冬天的寒風。偶爾,也有附近著黑衣的農民,放下手中的農活,與家人一起到這里來。也許他們是想看看從孔子時代就留下來的這片古跡,也許這種長途跋涉會使他們很容易地蹭口饅頭或苞谷珍子。
今天鳳翔馳名的東西有四樣,每一樣都各具特色。據傳說,六營村的名字來源于明朝初期駐扎在那兒的一支部隊,其士兵祖籍乃中國陶瓷工業的中心江西。隨著與當地婦女的通婚,士兵們教自己的鄰居做泥塑,以便增加收入。泥塑的動物或面具風干后,再在白色的表面涂上鮮艷的色彩,以大紅、大綠和黃色為主。
西鳳酒是陜西名酒,這兒人的酒量能把人的肝喝爆,一般都是一邊打麻將或撲克,一直喝到深夜。當地的一句話是“鳳翔的老鼠也能喝二兩”。西鳳酒中的高端產品“華山論劍”系列就針對的是消費者的男人氣概。其包裝獨特,酒瓶是一個圓球體,瓶底凸顯的浮雕是道教圣地華山。在參觀了“兵馬俑”之后,阿諾德·施瓦辛格被聘為“華山”的最新代言人,所以一路上的廣告牌里都是他的形象。
鳳翔的另兩個產品也和家畜有關:一個是吃的,一個是裝飾品。毛驢一旦過了出力的年齡,就會被宰殺,驢肉經過加工就成了“品牌特產臘驢肉”。驢皮被剝下來,加工成薄片,用來制作傳統的“皮影”。在屏幕后邊用燈照著,輔助纖細的竹棍,這些連接在一起的“皮影”就可以演繹傳奇和古典的浪漫。在西安的書院門,就曾經有一位姓梁的女士纏了我大半個小時,讓我掏三百元錢來買她的一張“皮影”,說她父親是“皮影大王”,曾為外國元首及其家人表演過。她說的最多的是二十年前,希拉里就曾接受過她父親贈送的“皮影”,并答應回國后“試玩”。“你想想,先生,希拉里女士都拿著這只龍在白宮和克林頓與他的朋友們一起樂呢!也許布萊爾首相和你們的女王也會看到。”雖然讓“州長俠”飲幾杯“華山論劍”還說得過去,但讓前第一夫人和現在的國務卿脫掉鞋子,蹲在地上在白宮表演動物的陰影就讓人難以置信了。
喝酒(無法避免)是我在隱居鄉下四重奏中日常唯一不變的節目。在胡奶奶家的時候。生活的節奏慢了下來。永遠好客的女主人怕我冷,會給我加好幾床被子,并用柳枝趕走毛毛蟲。在秋天,村里的街巷上都是為冬天做準備的農村婦女,她們忙著把玉米剝開,再用這自然的包裝把玉米緊緊地綁成可以掛起來的串。垂直掛起來的金色玉米串和瀑布般下垂的紅辣椒串相映成輝。
當我躺在一間與世無爭的房間里時,不論是窗簾掛得比窗戶高三十厘米或六十厘米,還是門楣和門框配不配套,我的腦海里縈繞著兩個思緒:一個是沒完沒了的面條,從早晨、中午到晚上。年逾八十的胡奶奶一定為她的長輩做了五萬鍋臊子面,接著又為自己的丈夫和子孫做。二一個是為什么歷史的影子在鄉下是那么悠長,胡奶奶在2013年去世的時候,前來悼念和送挽聯的有作家、詩人和大學里的領導,這也顯示出了其住在城里的子女所收獲的人脈。然而,她被安葬在了村委會指定的墓地里,在土地被分田到戶的三十年后,她依舊是生產隊里的一員,這就是一位普通農村婦女的宿命。
紐帶:鄉下的儒教
2012年,根據陳忠實小說 《白鹿原》改編的電影開篇展示的是茍延殘喘的帝制華夏時代。關中一個村里的人集體站在祖宗的祠堂前,齊聲吟誦孝道。在那個時代,每個家庭都秉承家訓——有遺傳下來的家規或代代相傳的至理名言。這些有的出自《論語》,有的已經變得無法考證了。
這部電影大體上講的是地方上兩個家族——白家和鹿家的命運變遷,這兩個家族之間的密謀、爭斗以及欺騙可以說驗證了一句老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白嘉軒和家族里的其他老者堅守傳統,而教師出身的鹿兆鵬則參加革命,成了共產黨人。劇情的高潮是革命者為了破除舊習,搗毀了鹿家最神圣的祠堂。祠堂中供桌上的鹿被掀翻打碎在地上,意在表明和過去決裂。對祖先的敬重雖然沒有上升到宗教的地位,但實際上卻一直是中國最流行的崇拜儀式。同樣,革命者為了顯示反抗封建統治,剪掉了自己的辮子。
古典儒家思想的痕跡依然閃現在《白鹿原》中,彌漫在中國鄉下的角落里。在陜西,地處渭河北岸的渭北包括大荔、澄城與合陽等地,這些地方的殷實人家對傳統道德規范的堅守就是杰出的例證。
渭北一個比較大的地區是蒲城,縣城坐落在具有清朝風格的達人巷,很有十九世紀的獨特景致。這里有學子參加科舉考試的清代考院。一千三百年來(從公元605年到1905年),除了十二世紀簡短的中斷外,嚴格的科舉考試一直是人們進入政府機構的萬能鑰匙。雖然每一個朝代都有自己的科考項目,但一成不變的概念就是(以圣人之言)人不分貧富貴賤,只要有才華就有機會出人頭地。
雖然蒲城考院早就被改造成了一所私塾,但其兵營式的建筑里依舊保留著幾處文生參加科考的狹窄“號舍”。在參加考試的三天兩夜里,考試文生的吃喝拉撒睡都在“號舍”里,直到寫完高質量的“ 八股文”。考生所帶的東西,諸如菜肴、饅頭和取暖的木炭都要切成不到三厘米,以防作弊者藏匿夾帶。在有些地方的博物館,如“半坡博物館”(實際上是指西安半坡博物館和上海嘉定博物館聯合舉辦的“中國科舉文化展”——譯者注)里就展有一件作弊的麻布坎肩,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有預備答案好幾萬字。由于檢查的人不會對考生進行全裸檢查,所以有些無恥的考生便會不用紙做夾帶,而是在外套下穿件切身的短袖坎肩。潛在的回報之高讓考生覺得值得一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能通過考試成為“舉人”,然后再參加下一輪的“會試”,直到京城參加“殿試”。
蒲城人的后代有一個他們渴望效法的榜樣,那就是出生在達人巷的王鼎(1768-1842),他走出了渭北的死水,成為一代名家和高官。王鼎在位時,曾主持政府的幾大工程,如用現代方法治理河南的洪水。然而,他讓人記憶頗深的是對清政府有學者良知的外交家林則徐(1785-1850)的影響。林則徐在國際舞臺上展現出了其“忍”(為了大眾利益寧愿放棄個人的舒適)的性格。在道光皇帝令其監管廣東的海關時,正是他發起了大規模的收繳鴉片和煙槍。他也在輿論上反對英國,發表了致維多利亞女王的公開信。在倫敦的《泰晤士報》得到消息刊登此信后,也一定是最終引起了女王陛下的關注。林總督在信中說:
王其詰奸除慝,以保乂爾有邦,益昭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
大家可以猜想英國的編輯覺得這封信有新聞價值,是因為林則徐目空一切的口吻,而不是因為害怕憤怒的東方人報復。不久,正直的林則徐就被描繪成了倫敦舞臺上的滑稽人物。諷刺雜志《笨拙》出現的是他的辮子和雞爪似的手指,而杜莎夫人蠟像館里也出現了同樣形象的蠟像。
林則徐的光輝形象很快就消失了,他被指責明知英國海軍要發動進攻,但卻沒有及時提醒當地的江浙總督。他周圍的政敵意識到他即將倒臺,而清朝的皇帝則又像以前那樣保守,讓不明就里的改革者成了“替罪羊”,林則徐被發配到了離中英海上沖突最遠的新疆伊利。1845年,雖然不如以前風光,他再次成為總督。他任陜甘總督(后來由左宗棠接任)的時光留在了今天鳳翔縣東湖岸邊的大柳樹上。
林則徐的老師王鼎卻從沒有看到林的官復原職,在聽到林則徐被發配的消息后,王鼎在失望之中,想到了后來被孔子贊揚的春秋戰國時的史魚,便于1842年六月八日自縊于圓明園。他死后81天,《南京條約》就被簽訂了,割讓香港給英國155年。王鼎的政敵向皇上隱瞞了其自縊真相,皇上還以為這位老臣是“卒暴”了。
從蒲城沿著去鄰省山西的高速路走一個多小時,人們便會再次回到黃河旅游線上來。韓城北邊的黨家村有一百多處的明清民居,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古老的的四合院兩層樓,中間有院子。一小部分人家里也有家族的祠堂,通常是墻上掛著幾十年來的相片,或者是裝在相框里掛在祭桌的上方。香和季節性的裝飾,如一盆櫻花顯示出人們對逝者的記憶依舊鮮活。
游訪此處的最佳季節是早秋時候,這時早霜還未降臨,空氣中彌漫著明顯的花椒味道,樹枝上掛著像布袋一樣熟透了的柿子。要是不介意像母雞那樣蹲在路邊的青石邊上,就可以花一兩元錢吃一碗用麥面做的,帶有芫荽湯的“魚魚”。我第一次享受這種禮遇時,遠處傳來的一陣鞭炮聲差點讓我把勺子埋到了碗里,把碗扣在地上。那是村子的另一頭在辦婚禮,胡同小巷里到處撒的是紅紙屑,紙屑塞滿了路上的石縫,沾到了大門上的黃銅門環上。五彩紙屑飛到了公雞的爪子和尾巴上,溜進了路邊的菜園里。園子里蓬松的牡丹、萵苣和巨大的白蘿卜在繁星纏繞下旋成了一片花浪。沒有人在意紙屑讓自己化成了“紅人”,也許是又一個黨家人嫁給了賈家人,也許就在我們吃飯的時候,一個朝代的聯姻正在進行。從那些洗碗人喜悅的臉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別的,唯一離開舉行婚禮大院的鄉親也許是因為他們要排隊去領賞錢。
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普遍認為黨家村的人屬于當地的有閑階層。他們的先輩用從黃河上運木頭積攢的錢修起了這些磚砌的古典而宏偉的院落。每家的木門檻都如膝高,因為據說在地上拖著腳走路的野鬼翻不過這樣高的門檻。但從偶爾出現的戲臺和藝術雕刻來看,人們也不清楚這里的家家戶戶到底信奉的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滿足,還是孔夫子的節儉。其中的門庭家訓有:
心欲小 智欲大 行欲方 能欲多 事欲鮮
言有教 動有法 晝有為 宵有得 息有養 瞬有存
無益之書勿讀 無益之話勿說 無益之事勿為 無益之人勿親
行事要謹慎 謙恭節儉擇交友 存心要公平 孝悌忠厚擇鄰居
事能知足心常愜 人到無求品自高
傲不可長 欲不可縱 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
動莫若敬 居莫若儉 德莫若讓 事莫若咨
富時不儉貧時悔 見時不學用時悔 醉后失言醒時悔 健不保養病時悔
歲月流逝,美德凝固在了高大的碑林里。在村校園的中心有一座“文星閣”,那里供奉著圣人孔子以及其10位高徒的牌位。村里人說這兒也藏有“避塵珠”,保護村民不受塵暴的侵擾。沿著操場走,又會解開另一個謎。不論是在門檻旁邊,還是在花圃里,大多數人家都有一堆灰燼,這么多的灰不可能是因為燒香或燒紙錢。小學里的公廁(也許各家各戶也一樣)是斜坡式的一個坑,各家里掏出來的灰是為了掩蓋糞便及其臭味,并以防糞便散落到街道上。
最宏偉的一座建筑是上個世紀的,當時清朝政府受“八國聯軍”的威脅,慈禧太后和宮里的人逃往西安時曾路過這里。慈禧太后御駕逃難留宿的地方在華北有好幾處,都是忠臣的營地,而且周圍的自然環境和防御必須安全。河北的驛站“雞鳴驛”給人印象頗深的是其鋸齒狀的圍墻,但慈禧太后給這里的御賜顯然不及給陜西的主人。她給黨家村忠實的臣民親賜了“福”和“壽”兩個大字,第一個字瀟灑開放,即便是被雕刻在大理石也是如此。第二個字筆畫纖弱,仿佛賜字的慈禧太后也對自己能否躲過一劫而心有余悸。相形之下,光緒皇帝卻想的是表彰臣民的婦德。“節孝碑”就是他下令為黨偉烈的夫人牛孺人而修的。實際上,對于知道內情的人來說,碑上的銘文說的是牛孺人一生所受的艱辛。說到底。她就是一個傳統封建婚姻的犧牲品。
黨家村人的事業心和商業頭腦也許肯定擋不住這兒的發展。像臨近的韓城一樣,這個古老的村莊也在計劃建一個保護區。在旁邊的山上,已經開始修建現代化的水泥住宅和娛樂設施。在磨面機的軋軋聲停止后,伴隨著從大廳后面的屋子傳來的麻將聲,游客依舊能感受到這個古老鄉村那寧靜而黝黑的夜景。與此同時,當地人也過上了現代農民的生活,坐在豪華的沙發上喝著“娃哈哈”。我們離開的時候,在“新村”鵝塘碰到了三個80多歲的老人。其中一位老婦人(她說自己88歲了)用她彎曲的拐杖戳著黃土地說:“你們看到太史第門樓了嗎?你們知道安樂居碑嗎?你們知道不,我是小姑娘的時候,那些石頭刻的老虎把我嚇得亂叫。我覺得現在沒有那些胡里花哨的東西也行,把老玩意放在外面就是在招賊。”她的話被證明是有先見的,2015年11月的一條電視新聞說有一個叫黨瑞的家伙被捕入獄,他從韓城附近的門邊偷走了幾百個石獅子,想拿到黑市上去賣。顯而易見,這個“哈慫”(陜西方言意思為“壞小子”)沒有把儒家對祖先的崇敬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