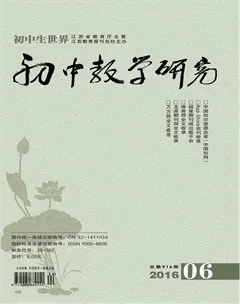取“道”景安
像任何一所“新貴”名校一樣,如東縣景安初級中學迎來了四面八方的前來學習取經的人們;也像到其他任何一所名校學習取經者一樣,從景安初中“滿載而歸”的人們有相當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得其形而失其神,這不,在有些學校,“問題伴學”成了一時熱詞,“圍聽”現象亦蔚為壯觀……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畢竟,相比于死水一般的教學生態,能讓課堂活躍起來、熱鬧開去,總是一種變革與進步。當然也不能聽任徒(多)有其表、無(少)有其實的情形延續下去,因為,“孩子的名字叫‘今天’”。
得其形固然可以,得其神更有必要,如果鑒于學校原有基礎和現實情況,難以或無需在形上心追手摹,那么,適當地“轉到現象的背后”,體悟、領會和化用“景安之神(獨到的實踐精神、內在的行動意蘊)”,倒也無妨,甚至,它才是關鍵之所在。“神”亦可謂“道”,荀子有言,“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學習先進,追步景安,說到底就是要取“道”景安,進而以景安之“道”來“兼物物”(規律性地“派生”一些積極因素),建設、辦成更多更好的優質學校。
那么,景安之“道”是什么呢?這里,我主要從自己數次踏訪景安初中進行課堂觀察和參與其他一些研究活動所獲出發,就“道”(景安初中課堂改革所賴以開展的支撐性理念)與“器”(他們的具體行為策略和技術)之間并更趨近于“器”一端的區間談談我的理解。在某種意義上,“說器”也是在“釋道”。我所擇取與言說的都是我頗感興趣、“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因素或方面,還嘗試用自己過去概括和闡述“課堂之道”的一些語詞來“指涉”它們。這些“道”都“著我之色彩”,是我所認為、認定而未必“名副其實”的“景安之道”——
其一,“獨學優先”。人們早就“看慣”了(公開課上)太多合作、過盛討論等情形,教師問題指令甫一發出,學生便“條件反射”,把頭湊到一起,頓時眾語喧嘩、人聲鼎沸,很顯然,這樣的課堂既容易湮沒學生的自主意識、獨立能力,也容易陷入碎片化思維以及失序、無效等的困局之中。我曾寫下《“重申”幾個“優先”》一文,其中第一個便是“獨學優先”。景安初中“問題伴學”有六個環節,“問題設計”之后便是“問題初解,基于獨立的思考”。他們也以“獨學(獨立的思考)”為先,這看似是時序安排使然,而實際上,“獨學”卻是全課的奠基之舉、扎根之為,其作用、權重亦處于最優位置。須知,景安的課堂是以追求真實、深度的合作為其顯著特征的,他們為此還申報了一項省前瞻性教學改革項目,在此情形下,依然著力踐行“獨學優先”,這不能不說是他們在行動哲學方面的理智辯證和明智廓清,其意義與價值不可小覷。
其二,“最好的學是教”。差不多十年之前,我受如東高中一位文科狀元不吝教同學數學、在高考中他幾乎獲得數學單科滿分的事實所啟發而說出這句話。今天從“百度”里可以很容易地搜索到與它有著緊密意義關聯的網頁,這里也會涉及“學習金字塔”理論(各種方式的學習所得在兩周后的平均存留率以教別人學的方式為最高,可達90%)。景安初中一直倡行“最好的學習方法是教別人”的理念,無論是小組合作還是全班展示,學生都有做“小先生”的資格和許多機會,他們的自立性以及“交互主體性”(胡塞爾語)得以充分彰顯。
其三,“學習策略教學”。這是我在幫助一位高中物理教師總結教學經驗、提煉教學主張時“原創”的一個概念,意即在教知識之外更多地教方法(策略)。鐘啟泉教授認為,學校知識大體包括實質性知識(即知識技能)、方法論知識和價值性知識三個方面,而素質教育區別于應試教育的一個標尺就是關注方法論知識和價值性知識,從實質性知識向方法論知識進行重心轉移。景安初中認為,“教師最重要的是教給學生方法”,譬如,每周平行班級中有一個班在階梯教室的舞臺上上課,其他班級則在臺下聽,不僅同步學習相關內容,更可以發揮“旁觀者清”的優勢,從中學到他班、別人優秀的學習方法,或者發現、省思其中所存在的相關問題,進而“反身而成”(從和他人的學習方法比較中取長補短,成就自我的“最優學習法”)。
其四,對課堂教學、學習活動進行“玩化改造”。我非常贊成郭思樂教授“將教轉化為學,把學轉化為玩”的主張,并與市內、省外各一所小學合作開展“學會玩的動課程”建設。我們旨在“與兒童的天性合作”,旨在讓“學活于嬉,智啟于動”。同其他初中學校一樣,受制于中考壓力,景安初中也“無時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但他們執意探索“化學為玩”的新路徑,譬如別出心裁的假期作業布置,譬如豐富多彩的社團課程,再譬如策劃開展的“我們的課堂在路上”的活動,等等。“用徐梅的話說,學生是‘在玩游戲中學習’。”自然,這是殊難達成的境界,“景中人”也未必都能,但“有心向玩”的學校,他們的課堂、課程以及教學、教育行為一定能淡化、驅散令生命窒息的氛圍,賦予師生更多一份有情有意、有趣有味的生命亮色。
還有更多。我召喚“生本問題”(學生遇到困惑或主動探究過程中所生成的問題),認為“帶著來”的也能“帶得走”;我倡導“在結構之中教知識”……這些無一不可以在景安初中的課堂里發現許多鮮活的“原型”,獲得無數生動的“注腳”。我這樣說,無意于自詡,也不敢掠美,是想表達兩層意思:其一,“沒有他人我也無法思想”(巴西教育家弗萊雷語),“景中人”就是這樣的“智慧他人”;其二,真正的思考者、探索者和研究者,都會“走到一起來”。
景安之“道”是他們實踐出來的。學者徐長復說,“思想也可以算一種實踐”,那么,這“道”也是他們“思想”出來的。他們更以“校本實踐性理論”的形式將之呈現。我很少見到有農村學校像他們一樣成型、熨帖和近乎完美地表達真正屬于自己的思想,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理論。思想與理論即是“道”,而形成、表達、深化,尤其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切實踐履同樣是抑或更是一所學校自強圖治的“大道”所在。思想與理論基于現實而又超越現實,它的超越性即它的理想性,理想性引領人站得更高、走得更遠,這未必是為了被世界看到,但一定是為了看到世界。今天我們取“道”景安,最需要借取的也許正是這樣的理想性,它使景安初中既“是其所是”,自信地趟出一條“弱校崛起”的振興之路,也“非其所是”,以一種高度清醒的教育自覺不斷地發現與修正自身的弱點和不足,勇敢地登上一脈向上向善的超越之徑。
取“道”亦即“取道”。今天的景安初中本身也是“景中人”向規律靠攏、跟科學對接,走向明天“最好的自己”的一個必由站點,他們也要“取道”于自我。那么,我們呢?
(作者為江蘇省特級教師,江蘇省南通市教育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