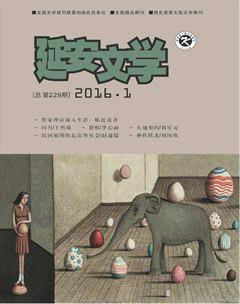恐懼
李心麗,山西呂梁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當代》《中國作家》《清明》《天津文學》等,著有長篇小說《師范女生》,中短篇小說集《棉花在棉被里盛開》《流年》。
廣播播了一半的時候,火車轟隆隆地開過來了,火車幾乎就在麻春連家的屋頂隆隆著開過。這條鐵路不僅能通向西安,北京,還能通向上海,烏魯木齊,聽說還能通向很多很遠的地方。前面的一個村子設有站臺,所以往往這個時候,火車的速度就降下來了,但到站的鳴笛聲卻格外地長久,一天里,火車的鳴笛聲要響好多次,這個聲音一響,村子附近的其它聲音都被它蓋住了。
麻春連大致聽明白了廣播的內容,快過年了,村委給村民發米面,這次還有油,讓大家早飯后拿戶口本去領。村子大,發一次福利要發好幾天。麻春連家有五口人,三個兒子,大兒子成家了,有了兩個孫子,所以他們家現在是八口人,八口人至少能領八袋面,兩大袋大米,四桶油。這么好的福利和待遇附近的村子也沒有幾家,自從鐵路占地,大學、中學占地之后,村里人一下子就有了福利,中秋節發,過年發,有時端午節也發,發棕葉和紅棗。麻春連的幾個兒子可不愁媳婦了。村子在外的好名聲遮蔽了他們家的窮困。任誰說他們家也不該是窮困戶,除了照看孩子的媳婦和兩個孩子,他們全家人都有一雙能掙錢的手,會窮到哪兒去?
門口摩托車的聲音響,之后大門被摩托車前輪撞開了,門是虛掩著的。三兒子付小軍回來了,車尾巴上還捎著他處的對象。麻春連說今天不忙嗎,得空嗎?付小軍拉著姑娘的手進屋,說不忙。麻春連說飯快好了,我給你們做飯吃。付小軍說我們在城里看好了一套房子,一間半,一個月租金四百五十元,準備這兩天就搬。麻春連看著兒子,又看了看姑娘,姑娘不看她,看窗臺上那盆快要開花的君子蘭。麻春連的眼睛里有許多話要說,但她說出來的只是一句,租金是不是太貴了?里面都有些什么家具?兒子說有兩只衣柜,還有一套沙發,但沒有床。麻春連邊說邊瞅姑娘的腰身,她沒有瞅出什么來。兒子說廚房里有廚柜,但得自己帶電磁爐或者買罐裝的煤氣,還得買鍋碗瓢盆,缺的東西還不少呢。麻春連想說,住城里是城里的開銷,還沒結婚就住一起,多出許多的開支,到什么時候才能準備好結婚的錢呢?但她說不出口,不住城里住哪里呢?上次姑娘不是提出來要結婚嗎?院子里有三孔窯洞,姑娘說,我們想結婚,你們指給我們一孔窯洞吧。麻春連和她男人付成平都反感了這個姑娘,姑娘是逼著他現在就分家呢。三孔窯洞一孔大兒子一家住著,另外兩孔打通串在一起,隔出來廚房客廳和臥室,三兒子和二兒子一個臥室。他們夫妻占了一個臥室,分明看著指不出一孔窯洞給他們住,姑娘不說話了,眼看著再有怎么巧的嘴也說不出一套房子來,付成平說等有錢了在這三孔窯洞上加層,不愁沒有房子住!可是說話的當兒就去加層,哪就變出能結婚的房子來?擱了兩年,村里發出了通知,舊窯洞上一律不允許加層,現在加層也變成空的了。
兒子和姑娘現在都不說結婚的事,麻春連也不能提。如果他們要提,她就會說,等等吧,等你二哥結了再給你結。老二也已有了對象,帶回來給她看過,她隱約聽說租了房子住在了一起,按說,他們都剛到二十歲,還可以緩一緩。她以為她不給他們張羅他們就會等著,可不知不覺他們帶著自己的對象同居了。
吃過飯,她要去恒大打掃樓房,比往常的出工時間遲了一小時了,她要走的時候,三兒子說,修理廠現在開不了支,手頭緊,問麻春連能不能給他點錢。麻春連家里只放著昨天恒大給她結算的一千塊錢,從立柜里掛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來,給了兒子。這錢她本來是要還欠款的,現在只能給了兒子。麻春連說我得趕緊走了,已經遲到了。她走的時候,兒子帶著他的對象去看侄兒侄女了。
恒大是一家房地產公司,主要開發高樓。這家公司駐扎在他們村已經有幾個年頭了,一棟一棟的樓修好,有的剛打地基的時候就已經把房子預售出去了。立秋前十六號樓封頂,之后立即開始裝修,現在高層的房子都已裝修好,雇工打掃,一天一百元。麻春連夏天的時候給這家工地的工人做飯,現在又給這新修的樓打掃,主要是清理裝修后不用的廢棄物,擦拭廚房和衛生間。她倒是一個勞動的好手,可是這一上午,她的心空當當的,像是一個空心人,麻木地擦拭著三十層的衛生間。
她在休息的間隙突然有點后悔把錢給了兒子,這錢她本來是要還給外甥的。大兒子結婚的時候,家里的錢不夠,她沒處去借,就去城里工作的外甥那兒借錢,借錢的時候她說結完婚就還,收好禮錢就給他送來,也就是借十天半個月的工夫,外甥借給了她三千元。結果大兒子的孩子都已經兩個了,那錢她還沒有還上。她本來是想攢夠三千元的時候把那個賬務清了,早該清了,現在又落空了。
村里像她家這種境況的人家幾乎沒有。她嫁給付成平的時候,付成平家窮,但付成平的父親給他們分了一孔窯洞,和另外能修兩孔窯洞的地皮。莊戶人家能做到這樣也就不錯了。況且她嫁來的村子是遠近有名的好村子,國道依村而過。之后她先后生了三個兒子,付成平會濾粉,就在村子里的粉房里打工。那時一份地基才五十塊錢,生了兒子的人家都交錢在村里批了地基。她對付成平說我們也早點批幾塊地基吧,付成平總是說,交了錢批了地基,我們也沒錢修,沒錢修批地基干什么呢?這話說著的當兒,地基每年開始漲價。等兒子們長到十來歲的時候,一份地基要大幾千元。付成平說批地基干什么呢,有錢就在我們家的窯洞上加層,想加多高,加多高。付成平的話讓全家人踏實下來。
什么時候有錢呢?等到什么時候,麻春連不知道。該批地基的時候沒有去批,后來地基逐年漲價。后來倒是有錢了,村里的地一下子被全部征用了,給了一筆錢,那錢付成平說買一輛大車吧,買了車拉沙,拉料,不愁翻不了身。麻春連覺得付成平說得在理,錢就讓他做了主張。要不買車,后來村里集資房子的時候,集兩套樓房還是夠的。錢買了大車了,兒子們結婚用的房子還在半空里懸著。麻春連想,結婚去住哪兒呢?這成了她一直思慮的問題。
地全部征用以后,麻春連不用下地了。靠近城市的村子,本來地就不多,現在純粹沒有了。原來齊整整的院子,在下一個春天來的時候,麻春連用籬笆扎出了一片菜地,種一些菜蔬,種一小片西紅柿和黃瓜。那時孩子們上學,村里還沒有這樣集中連片地開發。她去大路上的一家小飯館打零工,賺點家用。付成平還是付成平,想出車的時候出車,不想出車的時候,車就放假。村里的低層住房已經開始了拆遷,村委開始開發房產,廣播通知到結婚年齡沒有房子的去村委報名,村里修家屬區,還說陸續要改造現在的窯洞,要進行新農村建設。麻春連喜歡聽村里的廣播,聽完之后去街巷里議論一番。消息靈通的人說一平米按成本價八百元集資,還是比較劃算的。麻春連算了一下,一平米八百元,一百平米就是八萬元,回來和付成平商量。付成平說八萬元可以在我們的窯洞上蓋兩層,何必讓他們修呢?我們自己就能修。麻春連知道這個機會又誤過了。果然,隔了五年,兒子們的結婚年齡逼近的時候,集資房就不是八百元,而成了一千八百元了。
他們家的三孔窯洞,還是三孔窯洞。
三個孩子初中都沒有上完,就陸續不上了。大兒子學了開車,跟著付成平開。二兒子不上學之后去城里學了修車。隔兩年,三兒子也不上學了,也去學了修理。這個家,短暫地安靜了下來,二兒子和三兒子都當學徒工,那兒管吃管住,不給工錢。那兩年他們緊巴,還得麻春連貼補他們。學徒工干到第二年,就有零花錢了。麻春連囑咐他們,不要亂花錢,自己的媳婦還得靠自己娶。到后來她也不知他們到底是否有了積蓄,他們的錢從來沒有讓她保管,他們有自己的卡。卡也在他們身上帶著。
好像都一下子自立了,吃喝用度自己管自己。大兒子結婚的時候,要求買一臺電腦。村里的孩子結婚都要求有電腦。麻春連說電腦有什么用呢,又不像電視和冰箱。她不知道電腦有什么用,但除了她,家里的另外幾個成員都支持買,她也就不好反對。過年的時候,除了她,他們幾個在電腦桌跟前排隊,玩游戲,有時候甚至還有打架的時候,付成平和孩子們也擠作一處,輪不到他玩的時候,耳刮子就上去了。麻春連覺得那耳刮子像打在她臉上一樣不舒服。
她看到,那電腦,除了能玩,再沒有別的什么好的用途。欠了的債還沒有還上,他們卻買了那樣的一臺東西玩,這個家麻春連主宰不了,但她一直希望這個家有她想要的那個秩序,該干嘛干嘛,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該修房子的時候修房子,該娶媳婦的時候娶媳婦。大兒子二十歲的那一年,村里有人提親,說姑娘倒是很好的姑娘,只是她的娘是一個啞巴。麻春連說等等吧,日后提親的人少不了,不要著急。兒子還是偷著去看了,不久就帶回來給她看。姑娘會說話,姑娘的娘啞著,外甥說這一代沒有遺傳,隔代遺傳也是有的,這樁親事要慎重。假如生一個啞巴怎么辦?是啊,誰想生一個不會說話的孩子,她把她的擔憂說出來,兒子卻與姑娘熱乎上了,什么話也聽不進去。第一個孩子生下來的時候,她眼巴巴地等不得她說話。第二個孩子也是這樣。好在,沒有什么可怕的隔代遺傳,她可一直后怕著呢。
第一次娶媳婦,她和付成平都盡了力的周全,聘禮,首飾,家電,新衣,一切新媳婦進門要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備好。兒子出車工錢結算不了,她和付成平給買奶粉,看孩子。媳婦有時還管她要錢,說,娘,沒有洗衣服的肥皂了;娘,沒有穿的胸衣了。一個娘一個娘地叫,她的錢能不往出掏嗎?可是到她沒有錢的時候,他們的錢依然沒有結算下來。只一年的工夫,小米從三元漲到了六元,一切要經嘴的東西,嘩啦一下都漲價了。能把嘴吊起來嗎?媳婦能不娶嗎?可是房子呢,新媳婦往哪兒呢?
麻春連就在這個上午,忽然間體恤起兩個小的兒子來。沒有房子住,他們只好在外面租房子。沒有錢結婚,他們只好現在同居。小小的年紀就同居在一處,讓她說什么好呢?同居不好,結婚是好的。那給我們張羅著結婚。這話就在嘴邊等著,一下子就能嘣出來。上次三兒子回來商量結婚,說肚子里已經有了,聘禮送過去就能結了。付成平說山上的姑娘偏貴,我們這兒不時興這么高的聘禮。一句話就擋住了。后來兒子再回來,不提結婚了,說不著急,肚子已經空了。
難過的是麻春連。
現在村里娶一個媳婦得好幾萬元。不種地之后,賺來的錢都買了一切該買的東西,日用花銷都是一筆很大的開支。有時為避著花錢,她去山上把母親地里種的瓜菜一袋一袋拉回來。度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媳婦沒有錢,電話中和兒子吵,鬧,孩子要過生日,要買換季的衣服,事兒一堆一堆。誰讓她不僅當了娘又做了奶奶呢?
她和崔秀娟說她的這些愁煩。崔秀娟邊擦洗衛生間的墻壁邊和她接腔,崔秀娟說你這個做奶奶的,也太嫩了。你才四十多歲就做了奶奶,我都比你大兩歲,我這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做奶奶呢。你這么年輕,又這么大的輩份,總該得讓你吃些苦頭呢。麻春連說你別羨慕我,我是逼得沒辦法。崔秀娟說一家有一家的難處。你的兒子倒賺上錢了,我的兒子一個月一個月還得給他打錢。如果還要考,誰知道哪一天我才能花上他給的錢?
你說怎么辦呢?兩個兒子都等著要結婚。房子沒有,要有錢也算,可是錢也沒有。麻春連說。前面開了一家彩票店,要不去打彩票吧。崔秀娟說,你缺的錢可不是一筆小數目。麻春連說打彩票也是白扔錢,哪有好事能落到我頭上呢?崔秀娟說也只是說說,這年頭,誰不缺錢呢?樣樣都得花錢。你看著我兒子有出息了,上了大學,可是壓力也大呢。畢業后不想回來我們這地方,回來也不好就業,還要繼續考,還想留北京。北京的房子聽說一平米就得幾萬,想都不敢想。麻春連說上大學也是一樣的,事事也得父母給操心呢。崔秀娟說操心也是瞎操心,什么忙也幫不上。
聽聽崔秀娟的煩惱,麻春連的心不那么脹脹地痛了,短暫地得到了緩解。假如付成平聽她的,她覺得也許不是現在這樣子。付成平什么也太不當一回事了。可是現在,不消說付成平,就是自己生的兒子,他們的主意還是他們自己拿,誰又愿意聽她的話呢?想想他們各自在外租房子住,她就有種無來由的恐慌,接下來怎么辦呢?她該拿他們怎么辦呢?
隔幾天,付成平回來,她把她的恐慌說出來。她說現在馬上就過年了,年過后,得張羅著先給二兒子結婚了,都租房子外面住上了。付成平說他們想住就讓他們住去,都租房子住上了還怕什么,還怕姑娘跑了不成?麻春連說也到結婚的年齡了,他們覺得合適還是早點張羅著把事辦了。要不,肚子里有了怎么辦?付成平說有了就讓生下來得了,領一個證,省得辦事。麻春連說你怎么這樣呢?你這次結算了工錢說什么也得攢起來。如果我們早幾年加層,說不定就能住了。現在村委通知不讓加層了。付成平說,不讓加層可能是要拆,拆了還不好嗎?拆了就可能賠我們三套樓房,我倒是現在盼著他們拆呢。如果賠三套樓房,一個兒子一套,我們就隨便哪兒租一個房子住。麻春連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這家什么時候能像她想象中的一樣起興呢?
過年的時候,付成平沒有結算回工錢,開回了一輛二手的豐田,說老板抵賬給他的。這是他和大兒子付小偉一年的工錢。歇工回來的幾個兒子圍著車看,麻春連也圍上去看。車倒是還不錯,她聽他們說跑了近十萬里路了。她說要車干什么呢?付成平說不要車也要不來錢,誰知道拖到什么時候才能結算呢。所以我和小偉商量,還是先把車開回來。付成平又說,聽說去火車站拉人生意還不錯呢,這車不僅能家用,還能當出租車用。麻春連說黑出租你也敢跑?還是把車賣掉吧,孩子們都該結婚了。付成平和兒子們都說,賣掉干什么呢?自己家有一輛車,有急事,就不用再和別人家去借了。
因為是年前,火車站人流量大,付成平說他試著去拉拉人。那兩天,運管也不是太緊,可能忙,也查不過來。付成平的生意確實不錯,一天,三四百就賺回來了,賺到的錢他就直接買了年貨,吃喝水果,對聯鞭炮,一種殷實的假象。
麻春連在廚房里忙,晚上還得給鍋爐里加幾次煤。年過后,春節人流還是高峰,付成平就去火車站上班,有時候到飯點了,他正在遠路上跑。麻春連給他打電話,他說在火車站吃了一籠包子。他仿佛很投入。麻春連想要是這個活兒能長期做下去,也還是不錯的。但沒多久,付成平就被出租車司機舉報了,盯著他,他跑黑車也只能偷偷摸摸,再后來,積極性就大大下降了。
媳婦沒有錢,就開始和付成平要。付成平有,就給一百兩百。媳婦就帶著孩子去巷子里的小超市買吃的。小超市里什么都有,有泡芙,有英國宮廷糕點,有時候小軍和小偉見孩子哭鬧,就帶去小超市,回來提一大包吃的東西。那些小吃的東西,價錢一點也不便宜。后來小孩子讓麻春連帶著去超市的時候,直接就在貨架上拿。麻春連結算的時候,才知道價錢高的嚇人。不給買,孩子哭著不走,麻春連生生地怕帶孩子去了。
年一過,歇工的人都開工了,付成平開著那輛豐田車,出租也不跑了,說鄰縣一家粉房雇大工,工資不錯,他去那兒做。麻春連說你一個打工的人,用得著開一輛車嗎?要我說,還是把車賣掉,張羅著給兒子娶媳婦吧。付成平沒理會麻春連的話,開著車走了。麻春連的心,空得像冬天的荒地一樣。冬天的荒地還等著春天的到來呢,她能等到什么呢?
小孫子急性肺炎,要去住院,家里沒錢,她去和鄰居借。她走后,聽到鄰居家的親戚說,他們家養著大車小車,怎么還借錢呢?麻春連真是羞憤死了。
春節過后,麻春連又去工地打聽什么時候開工,照看場子的人說工人馬上就來了,麻春連說那我還來灶上做飯。孫子住了一場醫院,家里又有了虧空,她得趕緊出來做活把虧空補起來。現在麻春連太怕花錢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只要這一天沒有花錢,她的心就會一陣輕松,沒有花錢這一天也捱下來了,米甕滿著,面甕滿著。付成平有時會問,有吃的喝的,錢都花到哪兒去了?
冬儲菜剛一開春就吃完了,菜窖里白菜沒有了,土豆沒有了,蘿卜也沒有了,麻春連就決定去山上看看母親,順便再捎一兩袋菜回來。去的時候母親正害牙痛,在炕上躺著,說前一晚上覺都沒有能睡,兩個腮幫子腫得像嘴里塞了兩顆大棗。麻春連看著母親因牙痛而蒼白的臉,狠了狠心說,趕緊走,我帶你找醫生看看去。
鄉衛生院的牙科大夫就是他們村的,見母親的牙都松落了,滿口的牙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幾顆,說得鑲牙,要不僅剩的幾顆牙負擔太重了,經常會痛。那就鑲幾顆吧。大夫檢查之后,給麻春連推薦他們牙模上的牙,麻春連問鑲一顆牙多少錢?大夫說有五六百的,有三四百的,最便宜的一顆也得二百多。麻春連身上只有幾十元,說那你先開點消炎藥吧,我今天不帶著錢,過兩天我們再來。
麻春連心里盤算了一下,鑲最便宜的牙,一顆二百元,鑲十顆就得兩千多元,她上哪兒去找呢?真沒想到鑲個牙也這么貴。把母親帶回家里,吃了藥,麻春連就給付成平打電話,問他能不能給她打點錢回來?付成平說老板的粉還在庫里壓著,還得等幾天。付成平以為麻春連是因為孫子住院的事要錢,麻春連就把電話擱上了。之后他就給小軍打電話。小軍不是冬天還和她要過幾次錢嗎?沒想到小軍接通電話之后,很不耐煩,說他在醫院呢。這話讓麻春連的心一下子揪緊了,說你在醫院干什么呢?誰怎么了?小軍說在婦產科,人工流產呢。還說一會兒做完流產手術,我把她送回去,你照顧幾天。我們修理廠這兩天忙,我沒有時間。麻春連說你們不準備生嗎?老做流產手術可不好。小軍說要生也總得結婚吧?不結婚她不愿意生。麻春連說那你們商量商量,就咱們家這個條件,將就著先結婚。擱了電話,麻春連沒心思再給誰打了。
母親吃了藥,睡了,睡夢中因疼痛,呻吟聲從臥室那邊傳過來,麻春連又一次陷入了惆悵。媳婦帶著孩子從外面回來了,孩子叫喚著,讓麻春連很煩亂。
怎么能變出錢來呢?麻春連一直想這個問題,忽然看到了桌子上的那臺電腦。那臺電腦應該能賣兩三千吧?現在她就只有一個想法:實在沒錢,就變賣家里的東西。她不想再去和誰借錢了,即使變賣家里的東西,她也要給母親去鑲牙。
村子里有好幾家網吧,那兒電腦多,興許那兒收電腦。麻春連出門了,出門的時候還狠狠地想,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花大價錢買回來,真到要用錢的時候一個子兒也沒有,創造不了一點利潤的東西,為什么要花錢買回來呢?麻春連現在一點也想不通這些家人,她想不通這些不是必需品的東西為什么要擺在他們家?還有付成平開的那輛二手豐田,一個出去打工的人,開著車,家里卻窮得四處伸手借錢。可是為什么她的幾個孩子都和付成平一樣的想法呢?他們都以為這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嗎?
母親睡著,她出門了,媳婦問她干什么去,她說出去看看。她徑直來到附近的新時代網吧,她還是第一次來網吧,網吧里光線很暗,一個保安朝她走了過來,問她干什么?她問你們這兒要不要電腦?保安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說你是賣電腦的?她說不是,她說我家里有一臺電腦,用不著,想賣掉。你們這兒收電腦,我就把它抱過來。保安說這兒不缺電腦。她四處看了看,網吧里的人不多,見他們不要,她也就出來了。
麻春連又來到根據地網吧,這次她還沒有進去,保安就把她攔在了門口,問她是不是找人?她說我有一臺電腦要賣,看你們這兒要不要?保安說不要,這兒的電腦大都空著,還想賣幾臺呢。麻春連本來滿懷希望,沒想到四處碰壁,料峭的春寒讓她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已近傍晚了,春天的寒風從高樓巷里席卷而來。她環顧了一下四周,整個村子里高樓林立,國道上車輛一輛接一輛呼嘯而過,之后不久,火車的鳴笛聲從遠處傳來,麻春連在春天的夜幕下打量這個村子,已經沒有當初剛嫁過來時的模樣了。原先的耕地上,現在都變成了高樓。
小軍回來了,麻春連看了看,兩個臥房里全不見姑娘的影子。麻春連說就你一個人回來了嗎?小軍說你能不能去城里照顧幾天,麻春連說做了嗎?小軍說做了,不做還怎么著?麻春連說既然不準備要,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呢?小軍沒有說話,麻春連說你外婆牙痛,我今天剛把她從山上接下來,還是想籌錢給她鑲牙,我走不開。你明天還是把她送回來。小軍說那你能不能再給我點錢?麻春連說我現在一個子兒也沒有,工程還沒有開工,我也沒有賺錢的地方。你倒是天天賺著錢,你賺的錢呢?小軍說安家得花錢,置辦鍋碗瓢盆得花錢,流產一次也得花錢。麻春連說你們現在怎么這樣呢?小軍說什么怎么樣呢?麻春連說等結婚再住一起,還沒有結婚早早地住一起,不是多出來很多不必要的開支嗎?小軍說人家都這樣,現在就這社會。
麻春連說實在沒錢,就扛出去把這臺電腦賣了。你說這臺電腦能賣多少錢呢?她問小軍。小軍說為什么賣電腦呢?電腦也賣不了多少錢。麻春連說不賣電腦花什么?家里一分錢也沒有,電腦又不能當錢花。只是我剛才去網吧問了,網吧里不收二手電腦。小軍說賣了就可惜了,不賣還能用。麻春連不理解地瞪了兒子一眼。
崔秀娟知道了她的難處,說我借給你兩千,你先給你娘鑲牙是大事。麻春連說不用。崔秀娟說你和我還客氣什么?晚上崔秀娟就送來了兩千塊錢,可是麻春連說什么也不肯收。她的胸中有一股氣頂著,讓她對這個家有了無法自控的怨恨。到底怨恨誰,她也說不清楚。怨恨付成平嗎?怨恨兒子們嗎?村里大部分的人家有了電腦,有不少人家有車。這是一種潮流,為什么他們家不能有?麻春連呆呆地想這些混亂的事,她一年四季從母親那兒拉菜吃,到頭來母親用得著她出一次力的時候,家里卻一分子兒也沒有,這讓她氣憤和羞愧。
麻春連的大腦里一片混亂,無數憤怒的蟲子爬向她的全身,涌向她的胸口,她覺得自己都快要窒息了。崔秀娟說工地快開工了,趁這兩天還有時間,你先給你娘看病,工地開了支你還我還不是一樣的。麻春連說錢窟窿多得補也補不起。你看這樣行不行,你如果能用得著,你就把我家的電腦扛走吧。崔秀娟說那怎么行?麻春連說怎么不行,窮得連看病的錢都沒有了要電腦干什么?你說這勞什子有什么用?我就不明白這東西有什么用?
崔秀娟看到麻春連的神情里有一種很陌生的東西,她被絕望撕扯著,仿佛有一只獸在她的身體里。麻春連說這臺電腦我兒子結婚時買的,也就是三四年的光景,當初花了五千七百元,發票我還保管著,我找給你看。崔秀娟說不用看,我自己愿意借給你錢,不是想要換你家的電腦。但她擋不住麻春連,麻春連不一會兒便從抽屜里拿出了發票單,指給崔秀娟看。崔秀娟說不用看我也知道,你以前說過。麻春連說現在我覺得這電腦兩千塊錢也值,你兒子不是一直想要一臺電腦嗎?這下他回家就不用去網吧查資料了。崔秀娟說他現在又不在家。
崔秀娟走的時候說什么也不肯把電腦帶走,麻春連第二天就給她送到家里去了。崔秀娟說無非就是借給你兩千塊錢嘛,你不必這樣啊。麻春連說我也想過了,電腦你如果用得著,就留著;用不著,等我還你錢的時候我再抱走。這樣誰也不欠誰的,就這樣定了。崔秀娟被麻春連的一種陌生的神情震懾住了。
拿錢給母親鑲好了牙,麻春連就把母親送回了山上。母親要她拿一些白菜和土豆,麻春連沒有拿。她發著恨沒有拿。為什么要拿呢?養著大車和小車,卻還要啃老。媳婦說,娘,家里沒有菜了。麻春連說有什么吃什么吧,沒有我們就不用吃了。媳婦看著麻春連很怪異,這可不是平常的麻春連。平常,麻春連會說,沒有菜我出去買點去,現在麻春連說沒有我們就不用吃了。一副不想過日子的神情。
工地開工后,麻春連問工隊的頭頭,讓他幫著打問賣那輛二手車。別人問她為什么賣呢?麻春連說燒不起油。確實是,付成平開著車去一趟鄰縣,加的油錢比坐班車還貴。付成平開回來就沒有開走,車就停在院子里,又礙事,又礙眼。倒是有人來看了幾次,說這車半舊了,最多也能賣五萬元。麻春連就給二兒子打電話,問這車五萬元賣劃算不劃算?兒子說為什么賣呢,麻春連一下子就生氣了,說為什么賣呢?難道你不準備結婚了嗎?兒子說結婚與賣車有什么關系呢?麻春連說窮得連婚都結不起,不賣放家里裝大款嗎?她的氣又一股一股從胸腔里竄出來。
家里沒人同意賣車,麻春連出去自己張羅,張羅來一撥一撥人到院子里看車。有人開車出去還試了幾次,要看車的手續。麻春連就問付成平,付成平說什么也不賣,說賣五萬太虧了,還罵麻春連是敗家子。想買車的人見他們意見不統一,看看也就走了。有人就問麻春連,你家到底誰做主,麻春連說我做主啊,你以為我做不了主嗎?我要給兒子娶媳婦,娶媳婦是大事。你如果想買,你就拿五萬元來,把錢放下,車你開走。麻春連想,家里的事我不能再這樣聽之任之地下去了,再這樣下去什么時候是個頭啊。
鎮上一個年輕人,來看了幾次車,說錢準備好了,問麻春連車手續準備好了沒有?麻春連就在電話中問付成平,向他要手續。付成平生氣了,說車手續還在上家車主手里,人家壓根兒就沒有給。還說當初他們有一個口頭協議,等工隊的那個老板有了錢,就拿錢把這輛車換回去。付成平說你趕緊打消了這個念頭,你是不是窮瘋了?
麻春連聽著付成平在電話中咆哮,一句話也不說。她聽著他的聲音,那么虛無。那聲音仿佛是風從遙遠的地方吹來,一會兒近,一會兒遠。那聲音已經沒有了實質的內容,就只是一個分貝,進入她的耳膜,又飄散到無限遙遠的地方。麻春連聽著,甚至有些出神。這時候,火車進站的鳴笛聲呼嘯而來,麻春連的思緒從遙遠中回到了現實。無限喧囂的聲浪淹沒了她。
院子里什么時候一個人也沒有了,一個人也沒有了,麻春連回過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坐在院子里的臺階上。她不記得她怎么就坐在了臺階上,一坐坐了老半天。
天黑的時候,她聽到一個聲音,說她的二媳婦要去醫院做流產,她的三媳婦也要去醫院做流產。她想,她們怎么能這樣呢?會把命送掉的。于是她就給二兒子小龍打電話,二兒子說沒有啊,你聽誰說的?她說村里有一個人說的,被她聽到了。二兒子說瞎說呢,沒有的事。她又給三兒子小軍打電話,小軍說已經做了,不做怎么辦呢?她說為什么不生下來呢?說著,她就把電話掛了,也不用小軍回答她。
她這樣在電話中反復問了他們幾次,絮絮叨叨就是一句話,你們不要騙我,村里人都說了好幾次了,說你們又要去醫院做人工流產,我都說過幾次了,那地方不敢去。起初,小龍和小軍都說,你聽誰瞎說呢,誰說的?她說有人說的。小龍問她到底是誰說的,她說你問了要干嘛,莫非還要找人家去打架?
付小龍覺得母親很奇怪,就把這事說給了和他一起租房的一個醫生。醫生說你媽病了,得了幻聽癥。小龍從來沒有聽過還有這么一個病,趕緊回去把母親接來。經醫生診斷,說麻春連得了輕度精神分裂癥。如果不及早治療,會變成精神病人。
那晚回去,小龍沒有走。半夜的時候,他聽到開門的聲音,一看,是母親出門了。他問母親干什么去,母親說墻背后有人又議論她們家的事,她得出去看一看。小龍就任她出去了,他也跟隨在母親身后。別的聲音他沒有聽到,只聽到母親的聲音:你別瞎說,我兒子說沒有的事。我回去問問我兒子,問問就知道了。付小龍聽到他母親又說,你等等,等等我仔細問問你。她邊說,邊朝著鐵路橋蹾的橋眼走去。
連續兩晚上,麻春連都要在半夜出一次門。小龍問她,她說,墻外面老有人議論咱們家的事,她想出去問個究竟。可等她出去的時候,他們又走遠了,她也不知為什么他們不愿意當著她的面說一說,讓她弄清楚。到底他們是聽誰說的?
第二天晚上,麻春連回過頭,看見小龍就在她身后。她問小龍聽到了沒有?小龍說沒有聽到。她說,那么高的聲音你怎么會聽不到呢?
麻春連得了幻聽癥,家里人誰也理解不了,好端端的一個人,怎么會得這么奇怪的病?
責任編輯: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