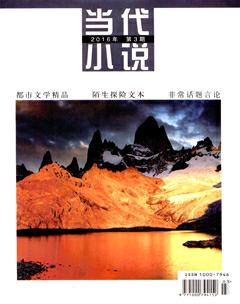玻璃上的城市(短篇小說)
劉愛玲
1
山東劉、河南王、黑龍,我們在社會層面上組成了新的血緣關系——兄弟。在威海一家鴿子房里,我們被黑龍的驚叫聲再次嚇醒。黑龍渾身是汗浸泡在棉被里,七八級地震般撞擊著上下三層的單人床,高喊著:“快閃開,快!”被高喊聲激起的還有一長串撕心裂肺的貓叫,以及滿身迅速伸長的貓毛,那是我們的貓,被我們取了名字叫“城市”,是被上一個租戶遺棄在此的。
黑龍又一次從夢里把那輛車開到了現實里,相同的是,每一次都是夢境,不同的是從夢里飛奔而出的車子,有時是桑塔納,有時是比亞迪,有時是東風雪鐵龍,最貴的一次是豐田越野型,更狠的一次是公交大巴車,黑龍醒了的時候跟山東劉和河南王說過,再這樣下去,總有一天,他可以完全控制夢和現實了,因為他在夢里的威海大道上瞄準車輛的時候很費心思,他需要考慮撞壞后修車的成本,所以,他每一次都選擇便宜些的車子,然后,把正在駕駛座上開車的主人拽出車外,自己坐上去,加油門,直沖,開始準確無誤地選擇在人行道上的行人,在飛行的速度中,他依然要把握超強的控制力,在行人中選擇最彰顯富貴的人,這樣才能,才能……但是,每一次在即將撞向目標的時刻,他都無法繼續堅持下去,就這樣高喊著,震顫著,依然是靠控制夢的能力,脫離夢境……
而真正現實中被撞擊的是在二層和三層床鋪上睡覺的山東劉和河南王。山東劉,就是我,我和河南王幾乎能夠一字不落地把黑龍夢里的喊叫背誦出來。不用說,黑龍又做了那個關于開車撞人的清醒的夢,他的夢越來越頻繁。在夢里無法實現的事情,黑龍只有再次留到現實里一遍一遍地過嘴癮,“撞一個人,賣掉一套植入物,再撞一個人,再……”黑龍說到“再”的時候就已經心生恐懼,他從來就沒想過,生命可以這么輕,而在他輕飄的生命中,他也有著這樣一副黑暗而骯臟的靈魂,致使他不斷下墜。于是,他只有再次選擇退到夢里去,他才能勇敢地去實踐,誰他媽知道到底是夢里是真實的現實,還是現實是夢的假象?
其實,沒有黑龍隔三差五的驚叫聲,我和河南王,也會在每天迫近的早晨惴惴不安地醒來,糾纏在我們身體和心靈上的夢魘不比黑龍弱,我們曾經站在街道的路口,詛咒過眼前的行人和車輛,“如果那個人,那輛車出了車禍,那我們的接骨板就……”我們有一陣子甚至想念120急救的車鈴聲,每當聽到那種救命的聲音,我和河南王都會滿足和得意,充滿激動,那將與我們的接骨板產生不可分割的聯系。我還時常產生幻覺,看見對面一個行人在我面前突然間跌倒,跌壞了腿骨,我會緊抓住河南王的手臂準備向那個人奔去,河南王在疼痛中把我喚醒,我發現,我身邊走過一個無比健康強壯的男人,他甚至自在地對著我們吹口哨。
這些骯臟的念頭令我們同時也被下了詛咒,我和河南王的睡眠也不盡如人意,只是黑龍比我們更富有想象力,畢竟,他是中文系畢業的,并將白日夢在夜里反復付諸實踐,而我們只有在內心里承受這種糾纏的煎熬。那種糾纏變成一根直線的兩個方向,一頭兒直指剛剛過去不久的大學生活,其實,他們那已經是三年前的時間了,但是,渴望回歸那種一塵不染的荷花池般的大學生活的意念太過強烈,所以,渴望縮短了時間。而眼前的現實,就是一潭荷花池里的黑色淤泥。是的,黑色淤泥,深陷其中的混濁不清的當下,還有模糊難辨的未來,像現在這個鴿子籠子一樣散發著三個男子漢的臭氣。
另一頭兒直指模糊不清的次日早晨,模糊是個最令人厭惡的詞匯,它總是在每天早晨的銷售例會上,被我們公司經理清晰地吐到我們三個面前,“再是‘0售,就把你們自己售了!”那模糊決定著我們在此生存下去的幾率以秒的速度遞減,就這樣周而復始下去,我們三個強壯的男人,在半年的時間里,將承載著夢想的世界越縮越小,小到眼下這間鴿子房,甚至消失。
2
“外面下雪啦?那是雪吧?”河南王被震醒了,他已經不厭煩黑龍的夢了,他甚至在狂歡。他在最上方第三層床鋪上爬起身子翹起腦袋,穿過玻璃窗最上方的那塊肱骨接骨板的玻璃望向外面的城市,城市半空正下落著雪片,仿佛那雪片都變成了肱骨接骨板的狹長形狀,在長方形拐彎的地方還呈現優美的弧形,就像人體那根真實的肱骨的流線形。每落下一片,都像是準確無誤地植入人的身體里,植入人的胳膊里,不,現在是大地的身體。
我多少有些興奮,這該是今年冬天威海的第一場雪。但我不愿意抬頭,我懷疑河南王的視覺,我甚至將腦袋再次縮進被窩里,我閉著眼睛都能看見河南王那雙布滿眼眵的小眼睛,如何把最上方的那塊長條玻璃看成是一塊形似的肱骨接骨板,他把它深深植入樓體里,也算作他的一次銷售業績。
從我們三個歷經山東、河南、黑龍江,劃了中國北方的大半圈兒,鬼使神差,齊頭并進,來到中國最東端這個海濱小城的這家醫療器械公司,趟過筆試、面試那些面子工程般的虛設花樣,正式成為公司里的銷售部的業務員,然后,結為兄弟并一同生活在這間不足十五平米的屋子里,河南王就選擇了最上鋪。那天,他就是帶著滿眼的眼眵主動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選擇的主要緣由后來我和黑龍才知道,有一天我們從公司之外的碩大世界瘋跑了整日回到這個鴿子籠子,河南王猴子一樣躥到三層的床鋪上,貓著腰,就像今早那樣從那塊接骨板里望出去,他說:“你們知道我為什么選擇高高的上鋪嗎?”當時下鋪和中鋪沒人理會他,我們已經被一天的銷售工作累斷了腸子,累出了小腦萎縮,我們在床鋪上閉著眼睛迷糊,他獨自在三層床鋪上自我陶醉,“我喜歡漂浮在上面的城市,高空中的城市,脫離了低俗與車尾氣、腳丫子的城市。”我記得我聽見黑龍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那是空氣!”并準確無誤地從自己的枕頭底下抓出一本書,我就是進入夢鄉也能猜到那本書是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從第一天開始,黑龍的枕頭底下就沒離開過那本書。這個看不見的城市被昏睡中的黑龍再一次準確無誤地向天空拋去,飛到河南王的枕頭上。河南王一只手就抓住了,“你們懂什么,看什么都不能只看其形,要向高處看,就像漂浮的城市,在云端。”長久以來,其實,我們共同相處了半年多,漂浮的城市的真相是因為河南王永無休止地長眼眵,像我老家房檐上的燕子窩,窩里窩外流淌的白色的燕屎,所以,他看到的世界總是糊了一層窗貼,又充滿粘稠。
不過,今早卻是下雪了,因為聽見隔壁房東家的小孫女在敲打每一個租戶的房門,并一一告知下雪了的消息。我才把腦袋再次鉆出來,在每個周惟一的一天休息日里,起床,去干該干的事情。
黑龍多少被夢里的真實嚇到了,被他嚇到的還有“城市”,“城市”蜷縮在窗臺上拱著腰身看著他,它那一身虎皮花紋充滿憂郁和懈怠,損耗了本該有的王者風范,它看著他的腿還在哆嗦,耷拉在床下邊,從床幫上拽過一塊毛巾捂在臉上。他穿著三角褲頭走到他的T形加壓鎖定板那扇玻璃前,一聲不響地看被雪片遮住的街道、樓頂、行人、天空、法桐、青松,街道上那些緩緩開動的車子,沒有一輛是他從夢里開出去的。遠處的大海、身負國恥的定遠艦、劉公島,海中央的燈塔……
“起床吧,鴿子們!”
我從二層床上跳下來,隨后是河南王,他一邊跳一邊用河南的豫劇唱著,“城市,城市,漂浮的城市,云端的城市……“城市”聽到這種怪腔,把身體緊緊貼在窗戶最下邊靠右的那塊T形加壓鎖定板玻璃上,那一塊是我的,我和黑龍在當初選了整扇窗戶下方三大塊中的左右兩塊兒,那位置適合我們視覺的高度和寬度,有些近似長方形和正方形,更近似我們銷售的T形加壓鎖定板,所以,我們的窗玻璃就這樣被命名。最重要的是窗戶是這間鴿子籠的希望,每天,陽光可以從這里走到我們的床鋪上、腦袋上,甚至腳趾上,我們也可以從這里望出去,望到威海的正面,望到城市東邊的大海,望到人們常常掛在嘴里的那個叫“希望”的東西,起到短暫消解詛咒和噩夢的作用,面對剩下的兩塊玻璃,一塊和上方河南王的緊靠著,一塊在我和黑龍的中間,河南王曾經問過一個問題:“如果把這個城市按照這個上二下三的方式切割,你希望得到哪一塊兒?”
無論是當時和當下,我倆都沒理會他,只是把我們中間的那一塊留給了“城市”。而現在,雪終于盼來了,其實,我們并不清楚盼望下雪究竟僅僅是盼望下雪本身嗎?還是應該繼續盼望河南王所說的那些云端的、看不見的東西?我們盼望的究竟是什么?我們三個,擁擠在“城市”的那塊居中的大玻璃上向外望,雪花完整地從天而降,在離地面十公分的時候,就已經被融化,所以,一早上的時間望下來,這個城市連一層雪都無法在大地上存留,連一層衛生紙的薄度都沒有,它們直接就被車輪和腳掌帶走了。
3
我們行走在威海大道上,通往恒瑞房產的路途很遙遠,從我們所處的西文化小區向東,要過兩條威海大道這么長的街,還要向南拐三個彎,才能到達,我們要到那里去做另一份工作。我們選擇走路,因為今天的時間我們說了算,不用趕早班車到單位報到,也不用像一條野狗穿梭在城市的角落里,比如醫院、門診或者醫療器械代理商,我們可以喜歡走正步就走出整齊的正步,扭成模特步也可以。我們可以慢下來,由高到低依次排開,最高大的黑龍排在第一,我居中,河南王最后,我們仔細看看這座城市的每一個縫隙,想找到點那些看不見的東西,甚至還可以回頭看看我們那間七樓的鴿子籠子,聳立在飄雪的城市的半空會不會別有一番景象。在這里,人們都稱這樣的合租形式叫鴿子籠子,貧困點的房東,像我們的房東老太和老頭兒,就會把他們那棟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分割成五間臥室,分租給五個租戶,客廳、衛生間、廚房公用。富裕點的房東,就會把臥室的數量減少,盡量擴大客廳的面積。無論怎樣,都是一種群居生活,就像一個被規范分割的大鴿子籠子,名字由此而來。
我們三個立在鴿子籠子對面的威海大道上望我們的鴿子籠子,黑龍說:“看見‘城市了嗎?”我們三個一出門,“城市”就要獨自呆在那里等待著我們。
我朝著七樓的那扇窗戶揮揮手,中間那塊屬于“城市”,玻璃后面沒有任何風吹草動,我想它去小便了。河南王搓搓眼眵,再一次想到了他那些云端的東西,“我們在城市中,向著窗戶里面望。”黑龍不斷向前面走去,他帶著一鞋底的雪水,極其嚴肅地回頭,“那將是看不見的城市!”
雪還在下著,因為是周末,路上的行人極其多,尤其是小孩子,都用腳丫子踩即將落到地面上的雪,用兩只擴成心形的手接住半空的雪片,他們和我們一樣,發現雪花只能用眼睛看,一接觸到人就會消失,所以,他們不停地在路上跳躍著。河南王羨慕他們,也在雪地上蹦跳一陣子,“看看,看看城市這些人,中國人上數三代,誰家不是農民,不就是把農民的身子放在城市的軀殼里嗎?有什么呢?”他在向我們強調,人跳起來的樣子都是一個樣,像無數只青蛙。我和黑龍已經把河南王落得很遠了,我聽到他在那里自言自語,路過的人都要仔細地看上他幾眼。我回頭招呼他,“快點,那你不蹲在你的村子里,跑到城市里來干什么?”“看路燈!”我覺得河南王說得挺真實的,其實我們,包括這些城市里的人,根本就沒搞清城市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它和我的老家三十里鋪村子沒太大的區別,除了春節的夜里才亮起的路燈,在這里可以每晚都會發光,而且,數量比村子里的多。其他的,就是多出的路,多出的房子,多出的人,這樣想下去,我有個驚喜的發現,我們已經開始走進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了,我們在找城市的內在,城市的精神呢。我們就這樣各自抱著自己的大腦,繼續穿行在迫近恒瑞房產所在的那條青島路上,帶著從未有過的興奮和激動,感激雪。
恒瑞房產已經開門了。這一整條街都是靠賣房子吃飯的小公司,而我們就是靠賣房子公司撒出去的宣傳單吃飯,對,就是發房產廣告宣傳單,每發一次大概半天,三十元,這是我們那個并不景氣的骨科醫療器械公司最忌諱的一條,所有的員工都不得在外做任何兼職,包括非醫療行業的兼職,也就是說,公司能夠決定每周休息一天,已經冒著億萬損失的巨大危險,為的是讓員工們的腦袋在這一天里放空,好開始新一輪的工作。
我們三個是冒著被清除出局的危險做這份工作的。同時,也是為了隨時可能失掉的工作做一個最低保。那個終日里讓我們惶惶不安的銷售工作,在這里獲取一種短暫的安全。房產公司的李經理已經在桌子上放了三大摞印好的“新城名居”的宣傳單。工作簡單到只要有手有腳即可,取了單,發出去,回來領三十元,當然,李經理在街道上也會有很多雙眼睛。
從恒瑞房產出來,我們三個就需要各走各的路了。我和黑龍知趣地把最繁華的那條步行商業街讓給河南王,那里有他的“玻璃上的女孩兒”。我與黑龍背道而馳,我向著華聯商廈走去,黑龍向著相反的方向大潤發走去。
雪,還在繼續下,比起初的要大些,溫度在人群逐漸聚集下卻向著低溫爬去。三個人占領著各自的道路,逐步向著恒瑞房產這個中心點再次聚攏,給過路的行人發宣傳單,每發一張,都要伴隨著一堆解釋和祝福,我覺得我們說了很多謊話。河南王越來越不夠專心,他幾乎畫地為牢,站在一個地方直到發完全部的宣傳單。那個地方叫“慧心美視園”,光這名字在第一天就把河南王迷住了,以至后來這個名字不斷在我們的鴿子籠子里彌漫。這個“慧心美視園”就在步行商業街上,一個時尚飾品店,應該是和我們同齡的一個女孩兒,獨自一個人在那里整理她的各種飾品,那個貓耳朵的小店是屬于她的。她那么靜,大多時候就坐在店門口靠窗的位置,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鋼琴曲從那扇窗里流淌出來,匯聚到嘈雜的商業街上。
一直以來,河南王連進店的勇氣都沒有,我和黑龍裝作顧客進去過一次,得到一連串的微笑和問好,我們把那些都帶給了河南王,河南王從此陷入復雜的自我陶醉中,“真美,美得像云端!”“美個屁,連愛情都是從玻璃上看過去的!”聽了黑龍的話,河南王就會暫時恢復常態,“現實面前,也得留點浪漫,理性和浪漫不沖突!”然后,端著一大摞宣傳單繼續發。
今天,河南王和往次一樣站在店門口前的街道上發他的傳單,他發幾張就要回頭看一看那扇窗戶,雪還不夠大,還構不成對視線的威脅,是逐漸降臨的寒冷,寒冷讓那扇窗戶上糊滿了白色的熱氣,里面的人影成了仙人。河南王無法靜心發傳單,他把一大把傳單塞到路邊停靠的一排轎車擋風玻璃上,再次返回店門口,窗戶依然布滿了模糊的白色。他就在門口前方圓十來步遠的距離里轉圈,每轉一圈兒,遇到些玩雪的小孩子,他就把一大把傳單塞進孩子的書包里。今天的傳單無比的多,但,那扇窗戶無可抗拒地繼續變白,結果白過了河南王嘴里的云。河南王有些心慌,他把扣在頭上的棉頭套一把捋下來,用一只手狠狠搓自己的眼睛,眼眵義無反顧地獻身,整個眼睛都被疊加的眼眵弄花了,那扇窗戶越搓越模糊,越搓越遙遠。河南王正要把兩只眼球也摘下來,他的眼球里出現一個極其熟悉的面孔。
“王強?是王強?”來人把自己的臉從河南王的眼珠上拔下來,沖著越下越大的雪發問。
河南王的眼睛立刻清晰了,“是你小子王強?”站在眼前的不是那個女孩兒,而是我們的公司經理李前進。他的身后站著一個一身貂毛的女人,一只手拎著一個同樣是一身貂毛的小女孩兒,一家三口在這個惟一休息日里逛雪景。
面對李前進,河南王的嘴失去了所有浪漫的詞兒,他變成一個速凍的雪人,凍僵在“慧心美視園”門口,李前進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走出去不遠,等把他心里的氣憤消化掉,他回過頭來對雪人說:“周一上班領了你上個月的工資,滾蛋!你們三個!”
4
我的宣傳單已經發了一大半,就見河南王慢吞吞地朝著我身后的華聯大酒店走來,他確實像一個雪人,失去筋骨般軟塌塌肥膩膩地堆在我身后,“出事了!”在此之前,我和黑龍在結束自己的戰斗后,總要去找他這個拖后腿兒的。
“還剩那么多,不趕緊發,看看這天,陰下來了,大雪馬上就來了!”我在匆匆走過的人身邊尋找著縫隙,能夠裝進一張宣傳單紙角的縫隙,比如伸過來的兩根指頭,沒有足夠精力推掉我而倉促伸過來的大手,挎包的拉鏈處,自行車的車簍里,還有烤地瓜的小攤販的三輪車斗里,轎車的門拉手……
“出事了!”
“你怎么把你的帽子摘了?周六的同事們總是喜歡逛街!”
河南王把滿懷的宣傳單摔在雪地上,“我們玩完了!”
河南王把剛剛過去的一幕從頭講到尾說一遍。“那你最后看沒看到窗戶里的女孩兒?”我從來沒看見河南王那樣懦弱過,我甚至想一拳兒把他捶倒,他在搖晃著那顆永遠裝著云端和美的腦袋,“沒看見,你摘什么帽子!”
已經無法挽回什么了,我和河南王去找黑龍,街上的行人在迅速減少,幾近中午,加之雪下得過緊,溫度過低,路面開始鋪上一層雪片了。天越來越低,向著地面壓下來,我如果是黑龍,我會挺直一米九的身軀,再把一只胳膊舉起來,就能夠到天。但是,在陰沉沉的天空下,我和河南王看到黑黑的黑龍正在努力將自己的身體向下彎,他幾乎半蹲在地上,正在被孩子們圍困,因為他從頭到腳穿得像一個蜘蛛俠,孩子們將自己的小手在蜘蛛俠的臉上摸一下,取走一份傳單,他們取走之后,在路上興奮地叫喊著,“蜘蛛俠在發小廣告!蜘蛛俠!”
我在蜘蛛俠的后背拍了一下,蜘蛛俠那一雙擠成縫隙的眼睛盯著我和河南王,“你們發完了?”那一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剩下的所有小廣告扔進垃圾桶里去。我們穿成這個樣子,穿成蜘蛛俠的樣子,把自己一層層,從頭到腳包裹起來,躲避的就是一張張同事們的臉,還有碰見李前進后要承擔的后果。我們都清楚李前進的為人,他已經對我們忍無可忍了,一個不能為公司做出什么貢獻的人,沒有任何價值。
河南王結結巴巴把那一幕又說了一遍,我們等待著黑龍的爆發,照黑龍的性子,他會把河南王打到半空上去,或者埋進雪地里去。黑龍沉默了一會兒,拉著我們朝華聯大酒店那條街跑去,火熱的大潤發向著我們身后飛速退去,我們幾乎是狂奔,像拋棄了所有那樣狂奔。
這個時間,向著那個方向去無疑是自尋死路。如現實該走的路線那樣,李前進帶著他的美麗夫人和洋娃娃般的千金正走在華聯商廈十七樓的望海餐廳的路上,他們每一次去那里吃大蟹子,都被我們用層層包裹的眼睛看見過。
這一次,黑龍直接把他的蜘蛛俠頭套摘了,恭敬地端著一大摞宣傳單,站在華聯商廈三十層臺階上,對迎面爬上來的李前進問了聲好,“請看一下‘新城名居,威海經濟區新建的住宅區,有三室兩廳,有兩室兩廳,戶型齊全……”我和河南王看著黑龍真的將傳單分別遞到經理的手里,經理夫人的手里,經理孩子的手里,然后,轉身一階一階邁下三十層高的臺階。
不用商量,我們朝著恒瑞房產公司的方向一路發下去,走過來的路上除了厚積的雪,就是到處凌亂的宣傳單,剛剛發出去,瞬間會被扔在地上,我們又重新撿起來,重新發出去……我們極其認真地把那天的傳單全部發完,并每個人領到三十元錢,我們把恒瑞房產的老板炒掉了。
我們輕松極了,在大雪中,我們朝著我們的鴿子籠子飛奔。那條需要拐三個彎,再過兩條大道的路在大雪中消失了一般,雪把一切,城市、行人、車輛、高樓、燈火,全部變沒了,你可以重新在這一片白上面建造一座你心目中的城市,你所想象的世界。
雪夾著風擋住人的視線,讓人沒有過多的時間想象,你會看到雪地里,有些人捉著D5頭那樣的相機,對著這個世界瘋狂地按快門。河南王在風雪中的視覺為零,在這個時候只有牢牢地抓住我的胳膊。黑龍跑在最前面,他把自己當成了風箏,他過度輕松,像斷線的風箏一樣,在拐彎處突然間不見了,我看到黑龍一身強健的肌肉在隨后的一秒鐘里,軟得像海綿,或者像彈簧,或者像一只斷線的風箏,從一輛車前玻璃上空飛過,到遠處墜落……黑龍的夢實現了,可惜的是,他沒有控制好車輛的成本,也沒有控制好被撞物,撞他的是一輛甲殼蟲般的破舊奇瑞車。
5
黑龍被撞傷了右胳膊和一根右小腿骨,脛腓骨和肱骨骨折,身體里植入一塊脛骨近端加壓鎖定板和一塊肱骨近端鎖定板,也就是如河南王每天望向外面的那扇長條形的玻璃窗的比喻物,只是黑龍一下子把那兩塊比喻物全安在了他的身上。他在即將昏過去的時刻,咬著牙告訴醫生,一定要用我們方正醫療器械公司的植入物,但是,在這個權威的骨科醫院里,只有一家壟斷性的醫療器械公司的產品。在此刻,在黑龍醒來的第一時刻他面帶微笑,當時,我們既恐懼又緊張,我們叫著黑龍的名字,他滿臉堆著笑,發不出一點聲音,我們一致認為他被撞傻了。但是,他從手術臺被推到病房里,醫生暫時離開之后,悄悄對我和河南王說:“我一下賣出了兩套植入物!”他又笑了,然后閉上眼睛休息,他的聲音太脆弱了,像一只蚊子叫,但,他沒有停止叫。
黑龍在骨科醫院里呆了三個月就出院了,中途,他還需要回到醫院里拆線,所以,那間鴿子籠子被留了下來。黑龍的父親陪伴了一陣子,就趕著回家去了,近年關了,他得提前回去收拾收拾,還要照顧黑龍癱瘓在床的奶奶。
我和河南王把黑龍搬回了鴿子籠子。那三個月我和河南王又找了一家房產公司發宣傳單,臨時過渡到新年,準備過了新年再做打算。我們三個進鴿籠子的時候,房東老太和老頭兒給包了黑龍最饞的白菜豬肉水餃,房東的孫女為黑龍畫了一幅蠟筆畫,畫上是一個蜘蛛俠在高高的樓梯上攀援,地面上全是大雪,厚厚的大雪,大到足夠可以堆起一個雪人了,于是,小孫女在雪地上又添了一個雪人。我說,那不是河南王嗎?
這個在威海度過的第一個冬天,連續下了幾場大雪,聽房東老頭兒說是五十年不遇。后來又聽我們隔壁另一個鴿子籠里的租戶說,他們服裝廠的廠房頂都被大雪壓塌了。看來真的是五十年不遇,而我和河南王都忘記了在頻繁的大雪中,我們發出去了幾千份甚至幾萬份房產宣傳單,在白雪覆蓋這個城市的時候,我們還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內心里重組了這個城市。
在一個夜晚,鞭炮聲陸陸續續開始響起,從城市的各個角落里響起。我們仨聚在一起。外面依然下著雪,“城市”從早到晚就沒離開過中間那塊玻璃,它一直向外望雪中的城市,神情嚴肅而低沉,也許,它望到了什么東西。
我和河南王從樓下的小店拎了幾個現成的小菜,一捆啤酒,提前吃個年夜飯。“城市”被請到了黑龍的床上,也許它嗅到了分離的氣味兒,緊緊靠在黑龍的另一條腿上。靠著黑龍的床鋪,我們支起一個小方桌子。黑龍打破了患病期間不許喝酒的禁忌,他用那顆犬類的尖牙把啤酒蓋咬開了,還分別為我和河南王各咬開一瓶。
黑龍獨自喝了幾大口,他說:“到現在,我還后悔呢。”
“后悔來這里?”
“我怎么也沒選個豪華轎車,比如奧迪A6或者奔馳、寶馬,賠得可觀些,既然自己是被撞物!”
笑聲一過,河南王前所未有地嚴肅,“黑龍你可飛得真高!”
黑龍真想從床上站到屋子中央,他那根吊著的大腿晃了晃,還是回到了原位,“我翻過那輛奇瑞車的時候,你猜我看見啥了,我看到了半空里漂浮的城市,就是河南王說的上面的城市,那卻是挺美的,上面的城市,有鳥的飛翔感,有云的漂浮感,還像空氣,看不到,抓不到,但它卻是存在著!”
我們仨碰了一下酒瓶子,清脆的撞擊聲在屋子里回蕩了好久,“城市”的叫聲把我們驚醒,它讓我們想起一件必須解決的事,這個“城市”又將面臨再一次被遺棄。它蹲坐在我們身邊,它持續地咩咩地叫著,像一只羊羔。
黑龍問:“過了年都去哪?”
河南王卻說,“遺憾,連大海都沒看清楚。”他層出不窮的的眼眵還是無法解決掉,“繼續唄!世界這么大!還有那么多看不見的東西呢!”
我挑逗他,“比如,河南王的眼眵!”
黑龍蹬蹬他的腿,朝著我倆動了動腳趾,“生命不息,運動不止!”
我們一起間歇地朝著玻璃窗外望一望,“那將是看不見的城市!”外面有時很模糊,好像虛幻,可再過不久,窗內的生活也是虛幻的,也將不存在,所有的事情有時清晰,有時會有倒影,有時就是夢。
我們獨自喝了一陣子,誰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還是黑龍,這個中文系里走出來的人,倒是比我和河南王腦子靈,“看到威海的路兩旁并不整齊的法桐,現在就差鋪滿白雪了,像哪里?”黑龍自言自語說:“真像澳大利亞!”
我和河南王起身,到窗戶底下朝著外面的夜路看一看,樓前那條寬闊的威海路被路燈照亮,發出橘紅色的光,路兩邊的法桐樹一直長到遠處,超出人的視線。我回頭問:“你想去?”
黑龍說:“澳大利亞連雞都禁止屠殺,我喜歡。”
我在搜尋我即將或者想要去的地方,“新加坡,不去為好,華人太多!”
河南王叫嚷著,不到一瓶啤酒,他的脖子已經紅到了根兒,不用眼眵的出現,他已經在啤酒中呈現微醉的狀態,“我要去法國,我要去盧浮宮,看看那金碧輝煌的雕塑!”
我和黑龍把嘴里的酒都笑噴了,異口同聲,“你想那個玻璃上的女人了?”
這最后一夜,我們忘記很多東西,也記下了很多,我們記得河南王在那一夜兩只眼睛紅紅的,臉上呈現兩個奶白色的圓圈兒,從未有過那么多眼眵糊住了他的雙眼,就像京劇臉譜,只有他自己知道,眼眵后面藏著多少焦慮與火氣,才能夜夜熬出這么粘稠的奶白色來。
第二天,我和河南王先走了,黑龍背地里竟然把腦袋低到胸膛里去,抽噎起來,那細小的抽噎聲從他的胸腔里抽出來,像拔絲地瓜的糖稀,他剽悍外表下包裹的文人的細膩終于凸顯了。
他一瘸一拐走到窗戶口目送我們,玻璃窗上有一小塊兒被他的鼻氣焐熱,模糊了一片,那模糊之外,我和河南王每個人拉著一個塑料行李箱,在雪地上拖出兩道痕,河南王比我多一個背包,那本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在里面,“城市”也在里面,露著腦袋。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