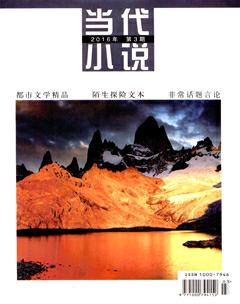導火索(短篇小說)
柳小霞
那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樣,獨自在報社加班。說是加班,偶爾我也會看看閑書,或者看看電影什么的。我在藝術部工作,每周負責兩個版面。活不像新聞部那么繁重,但也不見得輕松到哪兒去。不能繞圈子,不能老調重彈,不能跟風使舵,幾乎每一次都面臨著打破常規,從零開始的全新挑戰。時間久了,我的精神有點吃不消了。我總是會做同一個夢:我在一幢大樓里獨自行走,樓內有許多房間,我不停地打開門,看到房間里空無一物,心中充滿了莫名的恐懼,我不明白自己在尋找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得不停地找下去。夢境里光線非常亮,我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背后沒有影子。每次,我從這樣的夢里醒來,總是渾身冒汗。夢里的恐懼感在醒來后依然會持續幾分鐘,直到完全清醒過來,恐懼感慢慢退去,繼之而起的是一種蒼白虛弱的悲涼感,似乎我再也沒有精神來應對生活中的任何問題了。壞情緒會一直持續到天亮。并不是初升的太陽帶給了我情趣盎然,而是我必須得把自己壓到一系列生活的傳輸帶上去。就這樣,新的一天開始了。
為了緩解精神壓力,我一度迷上了電影。每天下午,同事們走完后,我便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辦公室里看電影解悶。我沒有太高的藝術品位。對于電影我只求畫面好看,故事精彩,什么愛情片、武打片、槍戰片、動畫片我全看。我惟一不看的是偵破片,不知為何,偵破片會加重我的精神焦慮。
那天,我沒有出去吃午飯,從中午就開始看起了電影。我先看了一部平淡無奇的都市言情劇,看看時間還早,我又看起了日本影片《羅生門》。這部電影我上大學時看過,沒怎么看完。只記得里面沒完沒了地在下雨,煩得很。而此刻,影片的畫面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空蕩蕩的辦公室,空寂荒蕪的心境,再加上空空如也的肚子,看這樣一部濕潤的影片,真是再合適不過。
我幾乎一動不動,盯著電腦顯示屏看完了整部影片。時間肯定不早了。我低頭看了一眼手機,屏幕顯示是下午四點半。
沒想到過去這么久,差不多了,到了該回去的時候了。
我迅速合上電腦,抓起包,向電梯走去。
總覺得哪兒不對勁,可我一時鬧不清楚。我走到門口關了燈,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外面一片昏暗,不知幾時起,下起了傾盆大雨。冷峻的風裹著雨水拼命沖刷著窗玻璃,而且屋子里有些冰冷。我起身的同時,連著打了好幾個噴嚏。盡管時令已進入了初夏,可這是在青藏高原,世界的屋脊,無論什么季節,只要一起風,一下雨,氣溫馬上就會轉冷。前兩天,天氣很熱,氣溫已臨近三十度了,只隔了一天,又一下子跌到了三四度。我能看見自己嘴里呼出的哈氣。
這么冷的天,我身著單衫如何出得去。
于是,我又坐回了辦公桌前。我想等這場暴風雨過去再回家。我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單身貴族一個,回不回家對于我來說,也僅僅是一個概念而已。
我有個男朋友,叫陳喬生,半年前我們訂了婚。陳喬生好幾次想盡快舉辦婚禮,可我想再等等。我喜歡盡善盡美的感覺,尤其是婚姻,我不愿意有太多的瑕疵。
今天,整個新聞大廈好像都了無人煙。可能是外面雨聲太大了,我聽不到任何人發出的聲音。電梯被我按到了二十九層后,便一直停在那兒。
這太不正常了,難道新聞部、專刊部都沒有人上班嗎?納悶歸納悶,出于一種職業習慣,我并不愿意去查看別的部門辦公室。
巨大的孤獨伴隨著徹骨的寒冷包裹著我,我的心情毫無征兆地難過起來。我想找個人說說話,想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了什么。也許會有人來給我送件棉衣吧。我翻遍手機通訊錄,沒能找到一個能雨中送炭的人。
陳喬生顯然不合適。我愿意嫁給他,可我不愿意讓他知道我的艱難困苦。這是我一個女孩子的尊嚴。再說,我已經不是女孩子了,一個三十掛五的女人,算什么女孩子。我更愿意帶著我的驕傲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不是一身傷痛,讓人虛偽地憐惜。我早已過了讓人憐香惜玉的年紀了,有什么困苦,我情愿自己抗著。我并不喜歡有人來分擔我的悲歡。風雨同舟的感覺于我有些隔膜。在未來的人生里,我希望陳喬生能給予我足夠的信任和尊重。
我沒有給陳喬生打電話。在如此的暴風雨面前,他也沒想著問問我的安危。這樣的信任的確有點沉重了。不過,我能抗得住。
可我孤獨。我被一種荒漠般的空洞感吞噬著。我感到了傷痛。
天空越來越暗。我起身打開了所有的燈。找人聊聊的沖動已經過去了。很多不開心的往事不知怎么全跑了出來。沉重的傷痛感壓迫著我。生命的悲劇意識越來越重地向我砸來。我想起《羅生門》里行腳僧說的那句話:人都是自私的。我的過分強硬未嘗不是一種自私。我的自我保護欲太強了,以至于別人無法介入我的世界。我三十五歲了,還孤單一人,一定是我的性格造成的。可是,讓我尋求一種保護,我又辦不到。我不知道拿自己身上的這個性格包袱怎么辦。
傷痛是明顯的,而我又不具備放下傷痛的能力。我不懂溫柔之道,不會撒嬌,甚至不知道拿別人的關心怎么辦。我是陳喬生的未婚妻,而我有麻煩時,我總是回避他。
生活到底是什么東西呀,風雨同行真的能減輕一個人的痛苦嗎?我找不到答案。人生無意義。忽然這五個字蹦了出來。我吃了一驚。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用我最大的意志力控制著思想上突然出現的洪水猛獸。如果任思想信馬由韁下去,天知道我會做出什么事來。
沒有電話。陳喬生不知在忙些什么。電梯依然停在二十九層上。時間在一秒一秒地過去。空無所有的世界給我造成的精神壓力很快變成了恐懼感。《羅生門》小說原著的場景浮了出來。一個巫婆在一根一根拔著死人的頭發。一樣的雨幕中。她的心中還有希望嗎?如果沒希望,她就應該從羅生門跳下去。她拔頭發干什么!是的,她想生活下去。行腳僧最后不是說了嗎:生活還是有希望的,只要你肯走下去。可那場景未免太恐怖了。像焊住了似的雨無休止地下著,窗外一片黑暗。我覺得我的身邊布滿了尸體。它們一個個張著嘴在喊:給你頭發,給你頭發。
我再也抵抗不住了。我沒有關燈便跳進了電梯。
在那種情形下,我是沒有勇氣關燈的。我甚至不敢望窗戶一眼。我害怕“人生無意義”這五個字會摧垮我所有的意志,使我的人生一去不復返。我明白,我所有的堅強都是虛偽的,是不堪一擊的羅生門。
還好,電梯并沒有壞,只是窒息依舊在繼續。盼望有人進電梯的愿望徹底落空了。我孤身一人走出了新聞大廈。我回頭望了一眼電梯,那上面的數字“1”慢慢變暗了。外面昏黑一片。雨比我想像的要大得多。幾乎無法冒雨而行。街上四面八方全是急湍的流水。路燈還沒有亮起來,流水透著冰冷的白。回看樓內,依舊空無一人,連門衛室也上了鎖。街上一樣不見行人,只有滾滾車流沖開流水,急速前進著。沒有空的出租車。我在門檐下約摸站了半個多小時。
出租車越來越少了。雨勢越來越猛。我的單衫早濕透了。雨似乎夾雜著冰刺透了我的肌膚。沒有空隙的雨,連呼吸都感到了困難。人行道上的水流已漫過了我的腳踝。馬路是過不去的,已經有汽車陷在了流水中。
這不是荒原,而是一座城市,我相信我能找到人煙。
這是青藏高原初夏的雨,帶著還沒有退盡的冬日嚴寒擊打著每一寸路面。低洼的地方,水漫到了膝蓋。我就這樣頂著雨大約走了五六分鐘,終于來到了一個燈火明亮的所在。
這是一家帶有藏式風情的酒吧。里面一定開著空調,因為我在跨進旋轉門后,身上便開始冒起了水汽。
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帶著一臉的快樂走了過來。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繼而引領我坐到了靠窗戶的一張小沙發上。這是個四人座的小隔斷。我的對面沒有人。
坐定后,我便明白自己身上發生了什么。我渾身濕透了,頭發全粘在臉上,向下淌著水,而我的腋下竟然夾著一把折傘。
我記不得自己怎么拿的傘。我逃一樣跑下二十九樓時,怎么會那么理智地找傘呢。也許傘就在我手底下,我僅僅是出于一種本能拿上了吧。反正我是腋下夾著一把傘,頂著雨艱難行走了七八分鐘,最后一身水汽,出現在了酒吧里。
服務生走了過來。我要了一壺熱奶茶,一口氣喝了兩大杯,身上的寒氣總算有所減弱。
我的衣服太濕了,讓我很不舒服。我斟酌再三終于很不自在地問服務生有沒有干的衣服。他看上去很和氣,想了想,說有,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暫時穿著。
衣服很快拿來了,是一件供演出穿的藏袍,而且是男式的。
比之寒冷,我情愿暖和。我真誠地道過謝,去洗手間換上了演出服。我將濕透的外衫干脆洗了洗,擰干后掛在了衣帽架上。
服務生一臉笑意,說,你這個人真有意思,看見你真叫人開心。繼而他問我需不需要把濕衣服烘干一下。
我再次道了謝,把外衫遞給了他。
我又要了一壺奶茶,一份煎牛排,一份面條。
接下來的時間里,我一直悶著頭吃飯。酒吧里很安靜,沒有任何人喧嘩。我想,在這樣的雨夜,我肯定是這兒惟一的客人。
時間過去不久,服務生又出現了,拿著經過整燙的外衫。他告訴我,衣服不礙事了,不過還有點潮氣,應該掛一掛就干了,酒吧間里空調很熱。
這次我說真的非常感謝。
我繼續坐著喝茶。雨有力地沖刷著窗戶。城市的燈已經亮了起來。
偶爾地,我會想起陳喬生。在這樣的暴風雨面前,他在干什么,他的生活受到了影響嗎?我的手機上依然沒有任何來電,連短信都沒有。就像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與我相熟似的。暴風雨與他們無關,而世界與我無關。我甚至起過念,想重新選擇一下婚姻。也許風雨同行才是適合一個女人的生活吧。然而,另一種不完美感馬上滋生了起來。我怕失去自己。
服務生端來一小碟開心果,說是免費品嘗的。我收下了。我不太愛吃堅果一類的食品。
服務生問我介不介意和別人拼一下桌,因為他們酒吧客滿了。現在又來了一位客人,別的桌都是幾個人一起的,只有我是單客。
我環視了一下大廳,沒看見人來人往。不過我懶得較真,于是說沒關系的。
服務生說,那個客人是個男的。
我說,沒什么的,雨停了我就走。
服務生說,這雨恐怕一時半會兒停不了,我們酒吧是通宵營業的,你可以坐到天亮再走。
我心想,難怪這兒消費如此之高,原來是可以過夜的,只是這沙發未免太小了點。我得混到什么地步,才有可能在酒吧里睡覺啊。
服務生說,如果冷,這兒有毛毯,不過是收費的。
拼桌就拼桌,何苦一下子扯上這么多廢話。虛偽的關心!我心里狠狠罵了一句。
我說,謝謝,真的不需要。
來人一看就是位游客,一身旅行裝束,身后背一個黑色背包。像西部草原上的游牧民一樣,他頭上戴一頂褐色禮帽。這兒飛機場到處出售這種帽子,結實而不實用。
這位旅者脫下禮帽,向我問了一聲你好,然后將帽子直接掛在了我的衣服上面。
在這樣的一個雨世界里,許多堅定的事物被分散瓦解,人心很容易會變得惺惺相惜。我放下在陌生人面前固有的冷傲,點點頭,回了聲你好。我盯著帽子看了幾秒鐘,沒有表示異議。
暴風雨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帽子和衣服掛在一起又有什么要緊。
我明顯感到一種微妙的患難情分滋長蔓延了起來。
這位旅者頭發濃密而混亂,至少有一個月未經打理了。
他的眉毛也很濃,一雙眼睛冷靜而無助。
出于一種禮貌,我問他要不要先喝一杯奶茶,正熱著呢。
他沒有絲毫推辭,說好的。
服務生給他倒了一杯,然后等著他點餐。
旅者看了一眼菜譜,說就和她的一樣,反正我也不懂。
服務生問奶茶也上嗎?
旅者說也上,越熱越好。
看著服務生走遠,我低聲說這兒面條不太好吃。
旅者說只要熱乎就行。
雨水“嘩嘩嘩”地順著玻璃往下流。城市的燈光越來越亮。酒吧對面的樓層閃起了霓虹燈。
寒冷徹底退去,我的身體感到了溫暖。剛才辦公樓內急驟而起的悲涼感沒有了,我的心態恢復到常態上來。
我盼望著雨停,好打車回家。
陳喬生似乎與我的生活沒有任何關聯。我不明白自己為什么要和這樣的一個男人訂立婚約。
我和陳喬生是曾經的同事,在電視臺采編中心共事了四年。我調到報社后,昔日的上司介紹我和陳喬生重新認識,于是我們訂立了婚約。一切就這么簡單。毫無章法。也許在他的眼里,我永遠是個同事,只是同事關系從辦公室調整到了婚約內。不敢想像我會將什么心事向他和盤托出。他不是個傾聽型的人。我擔心他分不清我和新聞人物的區別。
上司說,不要心高了,人穩當就行,聽過來人的話沒有錯。
這就是一切。我得承認,陳喬生是這樣一種人:不善言辭,工作賣力,長相普通到你永遠記不住。他可是電視臺出了名的老黃牛。我總覺得他長得也像一頭牛。風雨襲來,穩如磐石,風雨過后,喜歡反芻。
旅者坐定后,我習慣性地又看了一眼手機,上面除了時間,什么也沒有。
旅者問我幾點了。
我說八點多。
旅者說,想不到青海這么冷。
我說,昨天還很熱,只是因為下雨才冷的。
旅者問我是不是藏族。
看來他一點兒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有些唐突。出門在外,拼桌吃飯沒什么,哪能隨意問及陌生人的身份呢。
出于一種雨水浸潤下的涵養,我友好地說不是,我僅僅是因為冷,借了店里演出服穿。
旅者沒有看出我回答前的遲疑,自顧自地繼續問我,據說藏族很厲害的,人人都帶著刀是嗎?
這話明顯過于突兀了。不過,窗外下著大雨,人又很無助,這點突兀似乎也能遮掩得過去。
我說,那得要看是什么情況,如果吃肉,必須得帶刀,這兒人都喜歡大塊吃肉,得一邊割一邊吃。刀是生活必需品。
旅者表示了理解,他又問藏族好相處嗎?
我問他是什么意思。
我很反感一個人因為好奇而沒完沒了問問題,把自己的無知抖摟得一覽無余。我望了望窗外,心想著是不是該冒雨而行。
我要去黃南工作,旅者仿佛看出了我的不快,帶著解釋的語氣說,我想了解一下那兒的風俗習慣。
是這樣啊。我心中的不快沒有了。我說,我還以為你是來旅游的。
旅者沉思了一會兒,似乎在想合適的措辭。顯然他看出了我剛才的排斥情緒。他帶著一種不情愿的語氣說,不是,我要去河南縣稅務局工作,我剛剛考取了那兒的公務員。
的確有點意外,我不由自主地說,你怎么會想到去那里工作?
他說,那兒遠,我喜歡遠天遠地。
我問他遠是指什么。
旅者說,我原來是中學老師,教英語的,不想當老師了,想到處走走,就考了過來。我家是青島的。
這太不符合常理了,所以我問,你從青島考到河南縣工作?
他說,是的。想了想,又說,我在青島曾有過一個家。看來他是鐵了心要向我訴說心語了。
我望了望掛在我衣服上面的帽子,問他,你沒有去過河南縣吧?
他說,沒有,沒去過,面試是在西寧市,我知道那兒很艱苦,面試時省局的考官已經告訴我了。可我不怕,任何艱難困苦我都不怕。越苦我越喜歡。
我帶著理解點了點頭,河南縣荒涼的草原徹底擊退了我對陌生人的心理防線。我說,如果你真的喜歡荒涼,那可真是個不錯的地方。
旅者用中氣十足的聲音說,哪兒都一樣,只要心不荒就行。在青島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和我沒什么關系。
是個藝術型人物,我心想,難怪他要來青海,他需要用一無所有來構建自己的新世界。我斷定他在青海待不長。
菜端上來了。旅者開始埋頭大吃起來。他的吃相不太文雅,有些過于放縱的粗糙。他滿嘴含著食物咕噥著讓我喝茶隨意。
我說,我已經喝了好幾杯了,再喝我自己成奶牛了。
這話說得很沒有分寸,幾乎是在調情。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會突然冒出這么一句粗鄙的話。
旅者的心思顯然全在牛排上。他津津有味地吃著,大聲咂著嘴,一個勁兒地說好吃,說奶茶也棒極了。
一種濃郁的生活情調升了起來,空氣變得有些濕潤。我說,這些怕就是你以后的主食了。
他說那敢情好。
現在,我們的面前只剩下了一壺茶,兩只杯子。服務生撤下了所有的空盤。
忽然感到有些不自然。這不像是拼桌,而像是一場蓄謀已久的約會。
雨看來是停不下來了,街上的車流聲根本聽不見。只有遠近明暗的燈光證明著我們身處在一座城市里,而不是萬物沉寂的荒原。
我說,這個時節青島也不熱吧。
他說,熱,今年大旱,三個多月沒下雨了,氣溫高得很,今天有三十五度。
我說,是夠熱的。
我們看著窗戶上的水流,異口同聲地說,要是把這些雨下到青島該有多好。
這是始料未及的。我們都不免有點詫異,繼而尷尬地一笑。兩個人都不再說話。
酒吧里隱約有人聲在飄動,隔著老遠,有人在唱生日歌。聲音很輕,明顯是壓著嗓子唱的。不是一桌人,而是兩個人在過一個有情調的生日。
少男少女的游戲。我心想。
我問他,青島很美吧?
他說,是很美,可這輩子也不想回去了。
我又問,你不是在青島有家嗎?
他說,是的,是有個家。半年前老婆死了。那個家也沒了。
他沒說老婆是怎么死的。不過,這種事情足夠有力量把一個青年男子從青島弄到青海來。他有他足夠的理由。
我說,河南縣可不是找老婆的地方。那是青海最艱苦的地區之一。人少。
我稀里糊涂說出了這樣一句話。我的好心和尖刻攪在一起,都分不出伯仲了。
對于我的一再冒犯,旅者并沒有介心,而是平定地說,只要能找回自己的心,心不再荒就行了。
我請他喝奶茶。我說,這壺茶算我的,我請了,飯錢你自己掏。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從來不會無端地慷慨。
他說,謝謝,茶真的很好喝。
我終于卸下了所有的武裝,帶著聊天的口氣說,加班晚了,下這么大雨,根本打不上車,回不了家,所以來了這里。
他對我的話題漠不關心,而是自顧自依然說自己。他說,幸好飛機沒晚點,不然這么大的雨如何是好。
我望了望窗外的雨幕說,今天應該有閃電吧。
他說,是的,那時候我已經下了飛機了。我在飛機場坐了兩個小時,我一直在下決心,是轉飛機回去,還是留下來。后來開始閃電打雷,暴風雨越來越大,所有航班都取消了,于是,我打車進了城,看見這兒燈光亮著就進來了。
旅者眼中的疲倦和愁容都消散了許多。他的鼻子長得很好看,挺直而有力量。
我說,在牧區工作幾年,可以調到西寧的。
他說,還沒有想到這一步。我現在是今天不想明天的事。活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空氣有點靜寂。我心里想著陳喬生。旅者似乎在回味往事。他從沉思中抬起頭來,又問,那兒真的人人都帶著刀嗎?
我實在想不明白他為什么總是糾結這個問題,有點心煩,又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我說,吃肉的刀家家都有,隨身帶刀的也很多,為了生活方便嘛。
服務生走過來,問我們,想不想來份手抓羊肉,這兒的招牌菜,剛出鍋。
我趕緊說,不需要了,謝謝。
旅者來了興致。他要了半斤。
羊肋骨很快端了上來,是一整塊的,旁邊放著一把刀。
服務生問是由他們切開,還是客人自己切開。
旅者說,我自己來。
他很笨拙地對付著肉,幾乎把所有手指頭全用上了。
我看不下去了。我說,我來吧。我一根一根分開,你再吃。
他有點固執,沒有聽從我,繼續切著肉。終于剖開了。
他吃了兩根,滿意地咂著嘴。
剛進門就遇見的那個快樂的小伙子出現了,他抱著一把六弦琴走到我們桌前,問要不要聽歌。
聽這種歌是要付費的。我慌忙制止。
旅者問怎么個聽法。
小伙子說,一百塊錢五首歌,二百塊的話,就可以隨便點,直到客人滿意。
旅者拿出兩張百元的人民幣,遞給小伙子,請他隨便唱。
小伙子的嗓音很干凈,不亮吭,而是一種低沉的男中音。這樣的嗓子唱藏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他先唱了一首很干凈的祝酒歌,然后一支一支唱起了藏族情歌。
有一首歌是用漢語唱的,應該是小伙子向心儀姑娘的求愛歌。這樣的歌適合在有月亮的晚上,在姑娘的窗下唱。歌詞里有這樣幾句:
姑娘走過的地方,
一路鳥語花香。
那是春天的使者,
我心中的姑娘。
小伙子唱歌時,眼睛深情地望著前方,仿佛他的眼前是一方明澈的湖水,水邊開滿了鮮花,而他的姑娘正在向他走來。歌聲的感染力非常強,讓人的心不由得對愛情充滿了憧憬。
旅者忽然問我,這世界上真的有鳥語花香嗎?
我有點吃驚,不知如何回答。我想到了陳喬生。他和鳥語花香這四個字離得太遠了。我說,歌兒總得深情些才好。
旅者臉上露出一種疲倦的笑容。他望了望前方,用手支撐著桌子站起來,然后向洗手間方向走去。
我的衣服干了,我站起身,取了下來。
我對唱歌的小伙子說,不要再唱了吧,聽多了傷感呢。
小伙子一臉不解,納悶了十幾秒鐘,走開了。
服務生走過來說,如果雨不停,你就在沙發上睡吧,我給你免費送一條毯子過來。
我心情異常沉重起來。不知何故,剛剛美妙的歌聲似乎帶走了生活中的溫情,而將不美好的一面抖了起來。我覺得自己什么東西都抓不住了。
我定了定神,說,不了,謝謝,我等著雨停,會停的。
旅者一直沒有回來。我等了很久。這個酒吧衛生間外廳是男女混用的。我想等他回來,再進去換衣服。
奶茶已經涼了。窗外的雨似乎小了起來。雨順著玻璃流動時“嘩嘩嘩”的聲音聽不見了。
酒吧里混亂起來。很多人跑來跑去。原來真的有很多人在這里就餐。
我對面的人一直不見回來。我看著他的帽子孤獨地掛在衣帽架上。
這次向我走來的人不是服務生,而是酒吧經理。
他問我認不認識對面的旅者。
我說,之前不認識,明明是你們安排我們坐在一起的嘛。
他又問,真的不認識?
我說,真的,他怎么還不出來,我等著換衣服呢。
經理說,他出不來了,我們在等警察呢。
難道他是逃犯?我心下一驚,慌忙看了一眼我的手包。
我說,他明明看著像游客啊。
經理說,可能吧,不過現在他死了,你得跟我們走一趟。
男衛生間的地上全是血,旅者臥在血泊中,他的胸口插著那把切羊肋骨的刀。
與其說是震驚,還不如說是受到了傷害。我雙腿拼命打起顫來。我厭惡陌生人和我開的這個玩笑。他用最極端的方式告訴我:美好的事物轉瞬即逝。我的眼前仿佛看見世間一切用最丑陋的方式狂奔而來,沖向了鳥語花香之地。
很快,警察來了,是一老一少兩個男警察。沒想到這座城市的出警速度如此之快。
像所有的事故現場一樣,他們里里外外忙亂了一陣子,最后在衛生間四周拉起了一圈彩色警戒線。
旅者依舊躺在地上。沒有救護車來。看來也沒有人打算把他移到別的什么地方去。我這才發現,不清不白的死亡竟會讓人如此心生厭惡。
我為旅者深感惋惜。我覺得他那樣躺在衛生間地上有點不體面。死亡總歸還是潔凈些才好。
兩個警察大概已經聽完了酒吧經理和服務生們的陳述,沒過多久,我被帶到了經理辦公室。他們愚蠢地認為我是這場意外死亡事件的導火索。就這樣我接受了平生第一次涉案問話。
你的姓名?
杜贊。
哪個贊?
杜甫的杜,贊頌的贊。
什么杜?
杜鵑花的杜。
年齡?
三十五。
家庭住址?
沒有家。租住在微波巷39號公寓。3單元208室。
你是藏族嗎?
不是。
哪你為什么穿成這樣?
這不是我的衣服,是借酒吧里的。
那么你自己的衣服呢?
這很重要嗎?
是的,凡是我們問到的問題,你必須正面回答,這也是為了你,如果你和本案真的無關的話。
為了我!我想你們問錯人了,我只是因為下雨,沒辦法回家,碰巧來這里吃飯,那個旅者也是碰巧進來的。
旅者?你怎么知道他是旅行者?
憑裝束,難道你們看不出來嗎?
現在那個人死了,情況不一樣了,你是惟一的目擊者。
不,你們弄錯了。我壓根兒沒有目擊到什么。我和所有這兒的客人一樣,是后來才知道的,而且是經理親口告訴我,我才知道的。
可他死前一直和你在一起。
再說一遍,我們只是在一起吃飯,而且這是酒吧安排的。
那么,你自己的衣服呢?
這時候,那個唱歌的小伙子將我的衣服遞給了我,然后向警察解釋了我為何換衣服。
老一些的警察問酒吧經理,你們還有這種服務嗎?
經理讓小伙子出去,說,這是惟一的一次,傍晚她進來時,衣服完全濕透了,所以下面的人自作主張拿了演出服給她。
好吧。老警察又轉向我說,衣服問題先到此為止。你們兩個到底說了些什么?
我聽出了這句話的潛臺詞:以至于人家要去衛生間自殺。
我說,能說什么,無非是閑扯。
請你冷靜一下,不要抵觸,這是警察問話。你的所有話都會記錄在案的。
下大雨,我沒辦法回家。只好來這里喝茶,想暖和一下。后來那個人也來了,服務生說客滿了,安排我們坐在了一起。
警察看了經理一眼,問,是這樣嗎?
經理說,是的,因為實在沒有空閑的小隔斷了,只有他們兩個是單客,所以安排坐在了一起。拼桌是常有的事。
兩個警察用眼神交流了一下看法,其中一個問我,那么你們吃飯時說了些什么?
他說他是青島人。
然后呢?
他說他以前是老師。
噢。
他說他考取了河南縣的公務員,要去那里工作。
太不可思議了,然后呢?
他說他老婆半年前死了。他沒說是怎么死的。
老警察的口氣和緩起來,意味深長地說,你們談得很深啊,都趕上警察查戶口了。
我解釋道,沒有,我想是因為下雨,他想訴訴煩惱吧。
因為下雨,他就向一個陌生姑娘談自己的生活,而且連死了老婆的話都說?
我想是的,人有時候會很脆弱,這很正常。他是個常人,并不是警察,沒必要非要有鋼鐵般的意志。
年齡大一些的警察明顯聽出了我話中的譏諷味道,又轉換話題,問我的一些基本情況,如家里有什么人,兄弟姐妹幾個。我干脆將自己徹底介紹了一下。我的記者身份顯然起了作用。警察和經理的態度都有了明顯的改善。服務生甚至給我倒了一杯水。我再次重申了一下我和旅者之間的所有事,最后表明了我的態度:這一切都和我無關。他們無權質問我。而且,這件事情讓我受到了傷害。
看著警察一臉的疲憊,和無意間流露出的對死者的厭惡表情,我做出了讓步。我用解答讀者疑惑的語氣說,人在極度孤獨的情況下,會邁不過心靈的坎,出現一些異常舉動很自然。
老一些的警察點了點頭,說,沒有任何事情是不自然的,如果他一時痛苦殺了你也是自然的。任何犯罪都有一個順應自然的過程。
我說,他沒有犯罪,他僅僅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警察說,對于警察來說,結束自己的生命和結束別人的生命是同一種性質,我們都得出警,都得履行所有程序。
我又說,那個旅者只是在向我訴說苦衷,我也僅僅是出于禮貌耐心地聽了,這就是全部。
老警察沉默了一會兒,年輕警察刷刷地在本子上做著記錄。
老警察帶著疑問的語氣又重復了一遍我的話:一個男人向一個陌生姑娘談完了心事,然后把自己了結在了衛生間?
我說,我想是的。據說有些男人會患膀胱空虛癥,上完廁所精神會處于極度荒涼狀態,非常容易產生自殺情緒。
老警察說,想不到你小小年紀,竟然懂得犯罪心理學。
我說,我大學學過心理學。女性也一樣。人很容易耐不過空無所有的感覺。這也叫心理上的空洞現象。
老警察說,有點意思,你有沒有覺得他是早有預謀的。
我反問,預謀自殺?
老警察說,是的。
我忽然想起下午辦公室里的一幕,對自殺者產生了些微的同情心理。
我說,下雨天人的想法會很奇怪的。
奇怪是什么意思?
奇怪就是奇怪,想什么自己也弄不明白。
你是說他是來河南縣工作的?
是他自己告訴我的。
可他的背包里只有身份證、錢包,他連手機都沒有,而且也沒有剃須刀。這不奇怪嗎?
我想他是想從頭開始吧。
開始什么?一個出遠門不帶剃須刀的男人,不可思議。
我想應該是想重新開始認識生活吧。
記者同志,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我們眼下不想討論哲學問題。
我終于明白旅者何以三番五次過問刀子的事了。他怕生活中出現刀子,怕一時性起管不了自己而結果了自己。他其實是想邁過坎重新生活,又怕自己邁不過去。他太了解自己了。不帶剃須刀正是為了保護自己。
那盤羊肋骨。那把刀子。我明白了他何以要自己切肉。他那是在考驗自己的控制力啊。
我說,我很同情旅者。他肯定有他的不幸。
警察說,你再仔細想想,他還說了什么?
我說,他說奶茶好喝,羊肉好吃。對了,他還問藏族人是不是總是帶刀子。
這句話顯然觸及到了警察的敏感神經。老警察果然很警惕地問我,他真的提到了刀子嗎?
我想早點結束這場讓我很不舒服的談話,所以說,是的,他問了兩次,我一直以為是他好奇來著,他自己也說是想了解一下那邊的風俗民情。
沒想到話又兜了回來,老警察又問我,他去衛生間前,你們到底說了什么?
我說,我們一直在聽歌,是他請的客。聽了不少,全是情歌。后來他問我世上到底有沒有真正的鳥語花香。我給他說了有。然后他就起身去了衛生間。他臉上一直微笑來著,我不知道他幾時拿了切肉的刀子。我一直在等他出來,好進去換衣服,然后回家。
依你說,他是受了歌聲的刺激才尋思著自我了斷的?
我想是歌聲讓他覺得生活很悲哀吧。
那么,你相信他說的話嗎?
什么意思?
你有沒有覺得他在說謊?
我想不會,他犯不著。他不是已經死了嗎,將死之人,還用得著遮遮掩掩?
你結婚了嗎?
沒有,這個問題我剛才已經告訴過你們了。
真沒有?
沒有。
不知為何,我不想在警察面前提陳喬生。
老警察看了我一眼,干巴巴地說,好吧,另外送你一句忠告:千萬不要輕易相信出門不帶剃須刀的男人的話。他的身份證顯示,他并不是青島人。
這讓我很吃驚,一時不知所措,我愚蠢地問道,他為什么要對一個陌生人說謊?
老警察說,他為什么要對一個陌生人講真話?
這時候,我產生一種沖動,我想把旅者從地上揪起來,問他個一清二楚。他讓我蒙受了羞辱。我對他最后的一點敬意消失殆盡。
陳喬生的電話恰到好處地響了起來。我從暫時的尷尬境況下掙脫了出來。
陳喬生問我回家了沒。
我說,沒有,在外面和幾個朋友在吃飯。
兩個警察立刻面面相覷。
陳喬生說,外面好像在下雨,最好早點回去。
我說,你一直沒出去嗎?
他說,沒有,一直在采編室,今晚我值班。
他的采編室不臨窗。我理解了他,心里釋然了許多。
我說,是下雨了,不過現在停了。
陳喬生又問我在哪兒吃飯。
我說了酒吧的名字。
他說,好吧,早點回去吧。
兩個警察耐心地聽完了我和陳喬生的對話。我問他們是不是可以走了。
不料,老警察問我剛才打電話的人是誰。
我壓了壓心頭一躥而起的火,說,我男朋友。
他說,你男朋友?你為什么不說實話?
依這個老頑固的理解,我應該哭哭啼啼向陳喬生求助才對,而不是如此輕描淡寫地遮掩。
我說,我沒有說謊啊。我想他沒必要知道這些閑事吧,他忙得很呢。
老警察說,你和死者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你為什么說不出口?
我的火再也壓不下去了。我說,夠了,警察叔叔,我厭惡坐在這兒和你們閑扯。如果我哪天不想活了,你們就是導火索。
兩個警察明顯愣住了。“導火索”三個字的威力震住了他們。我終于從審訊中解脫了出來,回到了家中。
原以為事情到此為止了。然而,第二天,陳喬生找到我,向我詳細詢問昨夜酒吧里發生的一切。不愧是新聞工作者啊,事情還沒有眉目,就嗅到了異樣空氣。
我從陳喬生的詢問里,大意知道了昨夜暴風雨事件的另一個版本。這個版本俗套得跟所有的花邊新聞一樣。連陳喬生都相信,那個旅者和我是舊相識約會,因為言語不和,其中一個走上了不歸路。
血淋淋的現實擺在那兒,我孤家寡言,誰會相信?
陳喬生最關注的一點是:我為什么說謊?
我以為他指的是打電話一事,我說,也不是想隱瞞,主要是天晚了,不想讓你擔心。
他說,不是這個,而是我和旅者之間的談話。
我告訴他,關于那場談話,我說的句句是實。
陳喬生說,你沒有任何理由去酒吧避雨,你完全可以打電話給我,讓我來接你。我問了很多人,都說昨天的雨并沒有大得寸步難行。另外,你那么有潔癖的一個人,你竟然會穿酒吧的演出服,把自己弄得跟個演戲的角似的。你也沒有任何理由讓那個男人請你吃飯,除非你們早就認識。
我說,他并沒有請我吃飯,我僅僅是看他冷,請他喝了一杯茶。茶還是服務員為他倒的。我想這是人之常情。
陳喬生說,那么,大小姐,你昨晚吃飯花了多少錢?
我恍然明白了。昨夜那頓飯我并未付賬。我最后離開時,服務生也未向我提及飯錢。我不知道旅者是什么時間結的賬。一個人在臨死前竟會想著結清賬目,這讓我對旅者又生出了一份敬意。我再也不愿意任何人去玷污他了。
我說,請你尊重一下死者,不要亂說一個已去往天堂的人好嗎?
陳喬生笑了笑,說,你心疼了?你到底瞞了我多少事啊!難怪你一直拖著不結婚。我怎么會和你這樣的人談婚論嫁?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那頓暴風雨陪襯下的晚餐終于成了我和陳喬生分手的導火索。我的心里并未產生太多的不痛快,反而覺得這樣也好。那之后,我心中再也升不起對任何事物的熱情了,荒涼就像暴風雨一樣時時敲打著我。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明白那位旅者到底是何許人也。我沒有勇氣去向任何人查證此事。后來,我因為逐漸加重的精神衰弱離開了原來的單位。我的生活開始動蕩不安起來。
責任編輯:劉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