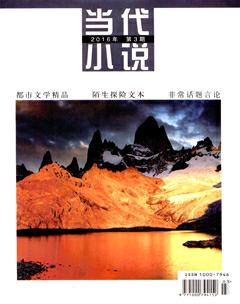我們(短篇小說)
王開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現在的朋友,當時他跟我說,他能將科學與巫術完美地結合,制造出很多神奇的東西。我嗤之以鼻,認為他在吹噓,我說,你這種人遍地都是。我沒有直接稱他騙子,畢竟第一次見,不留一點情面太不禮貌了。后來,我發現他的話挺靠譜,便加深了交往。
一天,我和朋友說,我再也忍受不了這樣的日子了,你幫幫我吧。他手杵著下巴,歪著腦袋,不錯眼珠地盯著我。我鄭重地向他保證,這事兒不是開玩笑。他搓搓手,不太情愿地嘟囔,好吧。不過我要賠錢的,給你做,我得選上等原材料,讓它最大限度接近人性,還要降低收費標準。我說你放心,一個子兒都不會少你。于是,我們的這樁買賣就算成交。
過一段時間,朋友通知我去驗貨。在他充滿詭異氣息的店鋪,我看到另一個我。怎么樣?朋友問道。她和我簡直是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找不到一點兒破綻!我叫起來,真的,我很滿意。那一刻我對朋友欽佩之極,沒想到他手藝絕佳,連我也快分不清哪個我是我了。朋友說,我可是費了好大勁兒呢。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掏出錢包,按照預定價格加倍付款。你知道,干他們這勾當的,心生了銅臭,哪怕爹媽求他辦事,也得丁是丁卯是卯,撈夠便宜還扮出一副苦相。
為了另一個我,我花掉一大筆錢。但我覺得值,我圍著她轉來轉去,上下左右的打量,她的發型、五官、衣服、神態舉止,與我一模一樣,她和我對話,聲音毫無二致。我高興極了,為了讓她更逼真,我把我的愛好、習慣、缺點毛病全告訴她,防止她不注意漏了餡兒。我和她,也就是另一個我,做了充分的交流,然后正式進行角色轉換——她替代我工作和生活,而我呢,抽出身來,去干一些平常想干卻干不了的事情,盡可能地放松自己。
她接替我從忙碌的早晨開始。
六點鐘,她被手機鬧鈴驚醒,睡眼惺忪地進衛生間,簡單洗漱一下,再去廚房做飯。六點二十分,她把我女兒從床上拽起來,催她去衛生間、洗臉,坐在餐桌前吃早飯,背上書包上學。這期間,她還要打掃一下房間,騰出空來往臉上涂各種化妝品,拔掉韭菜一樣鉆出來的白發。總之,她應避免猥瑣、窩囊相,使自己不至于在公眾面前慘不忍睹。整理一番,她坐下來喝杯牛奶,吃幾片抹草莓醬的面包,這個過程大約耗時十分鐘。然后,她進臥室換衣服,同時召喚還在熟睡的米斤:水燒開了,藥片在桌子上,呆會兒別忘記服用。米斤是我丈夫,他身體不好,單位不好,多年不上班,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上網斗地主,拖著僵硬的腿出門遛彎兒。
我擔心她能否適應這樣的生活,一直在小區大門口等她。看到她走出來,我急忙迎上去。她朝我微笑。我頓時釋然,看樣子,我的擔心有點多余,她比我想象的能干。我也微笑著望著她,目送她背著我的包徒步去上班。
一晃多日過去,她那邊沒什么動靜,我有點兒沉不住氣,我想,得找她了解一下情況,摸一摸她的心理。于是,我約她去一家茶館聊聊。
你越來越像我了。我倒了一杯泡好的菊花茶,推到她面前。
這兒的環境不錯,與你優雅孤傲的性格匹配。她輕輕啜一口茶,品咂菊的清甜。
我笑了,問她,過得好嗎?
生活就是一天又一天的重復。工作嗎,嗯……你挖掘的那個典型,我已經整理好材料上報,領導表示滿意。
選樹典型這件事,弄好了是你的成績,更是領導的成績,你一定要積極對上爭取。
你的工作蠻有意思的,動動腦子,動動筆,一切齊活。又輕松又體面。
我沒想到她居然這么看待我的職業,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不過,既然她滿懷熱情融入我的世界,盡管讓她干就是,我樂得悠閑。
又過些日子,她主動約我了。確切說,她去我的住處找我。那些天,我正沉迷一篇小說,我給它起名叫《制造業發達以后》,講的就是一個科學家兼巫師的人,利用他的手段大量仿造人類,給社會帶來深刻變化的故事。她來的時候,我寫得正起勁,如果換成別人,絕不會開門。
你女兒似乎談戀愛呢,影響了她的學習。她扔下包,順勢坐在地板上,垂頭喪氣地跟我說。
你不妨和她談談,教導她明白利害。
她白了我一眼,你一點不意外,難道你原來就有所察覺?
我眨眨眼睛。女兒談戀愛我確實知道,但我的勸告全打了水漂,我滿心指望她代我履行職責,讓女兒專注學習,考上重點高中。鑒于這個原因,我壓根兒不能跟她坦白,她會認為我跟她撒了謊。
米斤,你丈夫,更令人……焦躁。焦躁,你懂嗎?!
她的情緒有些激動,沖著我嚷嚷起來。
糟了,她說到最難堪的事。我想制止她,別提這茬兒,拿了一只蘋果遞給她,新疆產的,你嘗嘗,口感特別好。
她的火氣已經躥上來,一掌推開蘋果,瞪圓眼睛喊,米斤不是男人,他給不了我性愛!我更受不了他像女人一樣墊衛生巾!
我沉默了。我沒預料到一個仿造的人也有如此強烈的感情需求。米斤患腦血栓十年余,住院幾次已然記不清,錢流水般扔進醫院。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病情愈顯嚴重。兩年前,他再次入院,花掉二萬多塊錢,人倒是站起來了,無奈發生病變,下體經常鮮血滴瀝,只好墊衛生巾保持內褲的干燥。米斤的病,累積成壓在我心頭的一塊巨石,搬不走,砸不碎,悶得我透不過氣,夜夜噩夢。更可悲的事情,在于我享受不了夫妻生活的歡愉,饑渴感令人崩潰。而我為了維護面子,硬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欺騙自己,欺騙眾人。米斤自知愧對我,每天低三下四,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討我歡心,完全喪失他從前的囂張。
米斤年輕時開了一個加工廠,專門從事木材加工生意。平心而論,米斤人不笨,尤擅長擺布人際關系,加工廠因此辦得紅紅火火,他儼然財大氣粗的老板。米斤屬于狗肚子里裝不下二兩香油的主兒,一有錢就窮得瑟,呼朋喚友,吆來喝去。光這也沒什么,男人在世面上混,沒幾個哥們朋友的也真成了窩囊廢。問題是米斤跟不正派的女人掛扯到一塊兒,甜哥蜜姐的黏糊,并和其中一個黏上床,迷得神魂顛倒。米斤在外面找女人的事,我是最后知道的,那天我憤怒地去加工廠找米斤,那女人正巧在,她坐在米斤辦公室的椅子上,面對我的質問,不卑不亢,不急不慌,端詳著剛畫完的指甲,直眉瞪眼地說,你誰呀?我是米斤老婆!哈,原來你就是米斤老婆,我正要找你呢,哎,有事兒想告訴你,我懷孕了,米斤的。你看,你是不是應該給我騰地方呀?你妄想!妄想不妄想的,你說了不算,咱們走著瞧吧。我氣極了,撲上去摑她的臉。她那張臉太他媽不像臉了。那女人靈巧地一閃,我撲了空,等我再出手,便和她絞在一起。米斤得信兒進門時,我和那女人扭成一團。米斤像老鷹拎小雞似的一手一個,把我和那女人分開,說,你們他媽干什么呀,嫌這兒不夠亂咋的?米斤,你還當我是你老婆嗎?我聲嘶力竭。喊什么喊,你給我滾,回家喊去!米斤根本不正面回應我。那女人抱著肩膀,在一旁洋洋自得。我的肺都快炸了,眼淚涌上來,甩門而去。
痛苦中的我想到離婚,考慮女兒米奇太小,缺爹少媽的怪可憐,只好忍了。米斤抓住我的軟肋,更加肆無忌憚,和那女人打得火熱。后來我知道,那女人沒懷孕,她純心拿話擠對我。再后來,米斤的加工廠虧得一塌糊涂,一直惦記著要跟米斤結婚的那女人連影子也沒有了,背著一身債的米斤著急上火,患上血栓病,臥床不起。米斤生病的那段日子,吃喝拉撒全由我來照顧,他感激涕零,懺悔曾經的荒唐,期望得到我原諒。米斤的德行讓我非常討厭,我由此想到,人得意時是狼,落魄時喪家犬都不如。
米斤初病的時候,夫妻生活尚能勉強維持,慢慢地,他舉而不堅,直至成年累月軟塌塌地,像只霜打的茄子。米斤為了那點最后的尊嚴,多少個夜晚試圖進入我的身體,卻無一例外的失敗。他想借助手指安慰我,喚醒他自己的能量,可我不希望也不滿足那種應差式的做法,由煩躁漸漸冷漠,日子久了,兩個同睡一張床的人,誰也不碰誰,失去性愛的纏綿與溫情。
但這些細枝末節我絕不會和她——另一個我交實底,反過來,我也不允許事情繼續蔓延、發展,這樣下去太危險了,沒準兒會出別的什么麻煩,我得設法平息她內心起伏的波瀾,以免破壞我的計劃。我對她說,一個家庭中,總有種種不如意,你要諒解、遷就,倘若凡事較真,日子一天也過不下去。我還拿我舉例,你看,我和米斤就這么過的這些年,不也沒什么嗎?假如米斤生龍活虎,常在外面花紅柳綠,你受得了嗎?啊,堅決不行,我會殺了他!另一個我叫起來。所以呀,他給不了你,同樣也讓你省心,現在這年月,哪個男人鐘情一個女人?為了讓她相信,我給她講了我親眼見的事情:朋友家裝修,她找的木工其中之一是啞巴,啞巴活干得細致,人實誠,朋友很感慨,說如今這樣的男人快絕種了,把老公的半舊名牌衣服褲子送他好幾件。收工那天,木工比劃著問朋友,剩余的零碎木板怎么處理,朋友知道木工住平房,以為他想帶回家燒火,表示送給啞巴。啞巴十分高興,掏出手機發了一條短信。幾十分鐘后,一個啞巴女人敲開朋友家的門,啞巴木工一見她,指著堆在地上的早已捆好的碎木板一通比劃。啞巴女人眉開眼笑,配合啞巴木工將碎木板裝進袋子里,扛起來轉身下樓。我和朋友被這一幕驚呆了,面面相覷,云山霧罩。再問其他木工,原來啞巴女人是啞巴木工的情人!啞巴木工和他的老婆、啞巴女人經常結伴上街,購物、吃飯,親親熱熱如同一家人。但在一開始,兩個啞巴女人也打架,見面就往死里掐。不知道啞巴木工施了什么招,竟使兩個女人化敵為友,親如姐妹。
有趣嗎?我講完這個故事,詢問她,也就是另一個我。
太他媽神奇了。另一個我脫口說道。
這就是我們——人的世界,你明白嗎?
我有點兒恐懼感。她說。
我知道說壞事兒了,急忙挽回,這世界也有美好的事物啊,你每天看到的河流,樹木,花朵和太陽,鳥兒和天空,多么純粹明朗,如果你不做人,這些是體驗不到的。
可也是。她附和我。
接著,她想起什么似的,沮喪地叫道,噢,你的工作害得我傷透了腦筋!
你不是很喜歡我的工作嗎,怎么啦?
一周以來我連續挨訓!她哭喪著臉。
怎么啦?
她說,近期全市各縣區衛生拉練檢查,我們區不合格,區委劉書記把她劈頭蓋臉好一頓訓。為整治好衛生環境,她心里窩著火,起早貪黑挨著鄉鎮街道轉悠,見著哪里堆放垃圾,立即與當地干部聯系,要求即刻清理。她這邊累得頭暈眼花,那邊市領導微服私訪,結果逮個正著。區委書記臉上更掛不住了,損的她鼻青臉腫,限定日期全面改善全區衛生環境。她說,我這些天吃飯不香,睡覺不穩,做夢都踅摸垃圾堆。這么大的范圍,幾萬人不停地造垃圾,今天清理完,明天就堆滿了。加上人力、財力不足,群眾素質不高,要立竿見影,短期內的變化翻天覆地,談何容易。
這事兒真不怪她,實際上,提倡美麗中國人人擁護,環境美了,人格外長精神。問題是,雖然各地區配備了保潔員,但我們的群眾養成胡亂丟棄廢物的壞習慣,俗話說惡習難改,急于一招奏效很難。我覺著,想徹底加以解決,需要行政部門的長期堅持,同時提高群眾素質,培養他們的公德觀念。另外,我十分納悶,衛生環境整治已經開展多年,全區情況始終不樂觀,為什么今年領導這么上心?她嘆道,唉,我聽說,區委書記有調任市里的跡象,衛生整治是市委書記親自抓的,搞不好,他調走的事就涼了,能不急嗎?
我笑了,我猜準了。
對于劉書記那個人,我一向印象不佳。甚至,我和他之間存在深層的矛盾。一年前,區里調整科級干部,我琢磨著,在文明辦的位置干五年了,該挪挪窩了。我這樣想絕非自不量力,因我有一定把握,論資歷,年頭夠了;論工作,勤勤懇懇,我也不過高要求,能給我換個干實質工作的崗位就滿足了。你知道,務虛的工作沒油水,沒前途,誰都不愿意干。于是,我選擇合適的時間,向劉書記遞交了歷年工作總結,談了具體想法。誰知,劉書記和顏悅色地說,小陳呀,你的工作做得不錯,但有些方面尚需加強。我聽明白了,劉書記沒有調整我的意思。我說,劉書記,我不敢說我的工作干得最出色,起碼也是有目共睹,我只想走到干實質工作的崗位,干什么都行。劉書記說,小陳呀,你的政治思想覺悟還有待提高,你先等等,下次再說,好吧。我心說這他媽的哪兒跟哪兒呀,我政治思想覺悟怎么不高了?不就我寫幾篇小說,有人對號入座了嗎?我覺悟不高,婦聯主席就高嗎,文化局長就高嗎,他們要么沾法院院長老子的光,要么和某領導關系曖昧,我呢……除了一腔熱忱,其余什么也沒有。談話不歡而散,自然也沒換崗位的下文,我繼續在現在的椅子上耗著。
當然,與劉書記的過節我仍得對另一個我隱瞞,否則她會責怪我,劉書記狠狠批她是受我的牽連。我說,工作么,難免挨點批評,受點挫折。換一角度看,這是好事,對自己是磨練,說明領導眼里有你,如果他看都不看你,你什么價值也沒有了——我把場面話一點兒不差地用在她身上。勸解果然奏效,她想了想,認為我說得有道理,心里一松,情緒好多了,在我這兒呆到很晚才離開。
哄走了她,我越發贊賞自己的別出心裁,由另一個我頂替我應付這一切,多么英明啊。我厭倦了做人,尤其做我自己,我想躲得遠遠兒的,看著人們表演,就像頑皮的孩子對著上帝的惡作劇鼓掌。我喜歡當觀眾,再不必卷入其中,無需討好誰,防備誰,伺候誰,不用怕得罪誰,我想走就走,想睡就睡,任意揮霍時間,享受逃離壓抑的喜悅,這多愜意!
話說回來,我也隱隱擔心,她半道兒給我撂挑子,出我的洋相。
消停一段時間,我的擔憂變成現實——她又來找我,這次一見我就哭,哭得肝腸寸斷,我都忍不住快掉眼淚了。在我的追問下,她抽抽嗒嗒地跟我說,她愛上一個人,愛得快死了。我大感驚訝,我從未想過一個雙重技術催生的人還有如此豐富真摯的情感,這太不可思議了。她讓我想起那條可愛的白蛇和聊齋里的女妖女鬼,我納悶,上帝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安排上下三界的雌性都忠誠于愛,而雄性總顯得自私自利、不負責任。我被她哭得十分難過,同情她,竭力勸慰她。可她痛苦得根本聽不進我的話,一味絕望地哭,反復說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必須離開我的家。我蒙了,倘若她真的這么做,米斤、我女兒誰來照料呢,那樣的話我得重返蝸居,像一根不知疲倦的發條,咔噠咔噠地浪費生命。不行,這絕對不行。我挺直身子,告誡她冷靜,并提醒她,我朋友制造她是需要她負起責任的,而且我也花了錢。誰知,她不怕我的威脅,反過來挑戰我的底線——如果不能實現愿望,寧愿拆毀體內的精密設置尋死。我真的恐慌了,這幾個月里,我越來越依賴她的存在,有了她,我悠閑自在,正計劃遠游呢,她一死,我豈不亂套了。
聽著,我理解你的心情,真的,這世上除了愛情,其他什么都是可控的。你給我點時間,容我想個辦法,好嗎?
她抽泣著說,請你盡快,我一天也等不下去了。
我向你保證!
等她走后,我望著她漸漸離去的背影,突然冒出一個念頭:跟蹤她,看她愛上什么樣的人。基于這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悄悄盯她的梢。沒費什么力氣,我就在我請她喝茶的地方發現她的秘密。當時,我幾近暈厥——萬萬沒想到,她要死要活愛上的人,竟是我的舊情人。他們坐在那里,擁抱著彼此,情意纏綿的樣子。這情景讓我回想起從前,那時候,我的情人就這樣擁抱著我,親吻、做愛,我一整夜在他的懷里,感覺他的溫暖,呼吸,他的胸膛那么寬厚,胳膊那么有力,把我裹在里面,像一只冬眠的小蟲子。春天,他喜歡開車帶我去鄉村,欣賞沿途的美麗風景,我記住流淌的小溪,萌芽的樹木,漫山遍野的燦爛桃花。冬天,他在夜里給我打電話,讓我看窗外的雪。他總是穿得干凈整潔,看上去俊朗瀟灑,而他的性格又務實穩健,待人誠懇。我們好了多年,最終分道揚鑣……我不愿碰觸傷心事,一碰,就如一把刀子割我,每一寸神經都疼。那年秋天,我懷了他的孩子,可他堅決讓我打掉。他決絕的不像是他,在我最需要關心的時候,跟我冷戰,不理我。為了孩子,我給他打電話,每次他都態度堅決,不容商榷。我承認我太軟弱,無條件順從了他的意思,但走進醫院的那天起,我就開始憎恨他,再沒有跟他聯系。事后,他曾短信說,給我適當的補償,我拒絕了。我認為這不是他償還良心債,而是怕我盛怒之下于他不利,采用這種方式討價還價,堵住我的嘴。時隔多年,他居然與她打得火熱,難道他誤以為她是我,與我和解了嗎?還是他把對我的歉疚和思念寄托在類似我的人身上,表現得一往情深?看著她的幸福,我嫉妒得要死,恨不能沖上去拽開她,告訴我的情人,你摟的不是我。但我抑制住自己,我在心里說,如果你現身,一切都穿幫了。你的情人永遠離你而去,一絲一毫的念想都沒有了。你的同事、領導、朋友、同學,乃至不相干的人,一齊將矛頭指向你,出軌、濫情等等一盆盆污水潑向你,讓你沒法見人。忍了吧,你。
我傷心地離開茶館,把自己關在臨時租住的房子,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大聲罵我的情人王八蛋,摘下手腕的表往墻上摔——那只表是我的情人送我的,我一直小心呵護,多年不曾損壞,一點擦痕也沒有。
醒來的時候,我渾身癱軟,撿起地板上的表,握在手心,癡呆呆地犯傻。
你不開心啦?她在我身邊蹲下來,歪頭問我。
你怎么進來的?我給她嚇一跳。
這你不用問。告訴我,誰惹你不開心啦?看你悲傷欲絕的樣子,一定是感情方面出了問題。只有愛使人瘋狂。
我揪住她,目露兇光,你給我滾,滾遠點!
好啊。我就是來告訴你,我要嫁給他。
什么?
我要嫁給他。
她平靜地看著我,并不回避我的兇相。
媽的。她變得強硬了,王八吃秤砣鐵了心了,我可怎么辦呢。一想到那個死氣沉沉的家,把活蹦亂跳的人折磨成植物人的工作,我就害怕了。我緩和語氣,試圖勸她打消念頭。但她毫不妥協,重復嫁給我舊情人的決心,恨得我牙根癢癢,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氣。談到最后,我答應她,找我的朋友拿主意。
我跟朋友講完一系列的變故,他擺出哲學家的架勢,說,愛讓人成神,也讓人成魔。我說,先別管神呀魔的,你趕緊想法兒幫我渡過這關。他慢悠悠地抓起一只玻璃瓶,拔出蓋子,倒出里面的粉末,與酒精攪合,立刻,我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我掩住鼻子,催問他。再做一個。他說。成全她嫁給你的情人,第二個繼續替你扮演社會和家庭角色。這主意不錯。我說。但這樣一來,我又要花一筆錢,我心疼。朋友說,在錢和自由、現實與理想之間,你必須做出選擇,別夢想著兩全其美。實際上,你活的過程,就是不斷選擇的過程。沒辦法,我忍痛割愛,又花掉一筆錢,仿造了第二個我。看起來有點亂,是不是?然而事實就是這樣。朋友趁機又宰我一次,他跟我訴苦,什么原料漲價,稅率提高之類。我知道他蒙人,像他這種黑店,稅務部門查都查不著,要么私下串通好,給征稅員好處,免除納稅。總之,有各種逃稅的辦法可操作。
第二個我造好了,接替第一個我進入我的家庭和工作圈,她盡心盡力地料理我那個家,對米斤和我女兒毫無怨言。之所以她脾氣好得出奇,因為朋友在這方面下足功夫,有意淡化她的生理功能。也就是說,減少了她情感需求的程序設置。朋友說,這是他在設計上的進步。第一個我如愿以償,嫁給我的舊情人。婚后,他們搬到遙遠的城市去,在那里買了房子。他們生活得相當美滿,生了三個孩子,一女孩,兩男孩,個個聰明伶俐。第一個我改行當了教師,溫柔賢惠,樂于為丈夫和孩子奉獻。我的舊情人干他的老本行,成為一名出色的畫家。人們說,他的畫畫出了世界的靈魂,不管是人,還是花草樹木,山川河流,都飽含著一種無法言說的東西,那東西就是靈魂。人們自以為看懂了他的畫,給予各種高度評價。其實只有我知道,我的舊情人畫的,是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時光。
第二個我沒有辜負我的期望,她勤勤懇懇地工作,容忍,機敏,有自我消化委屈的本事。領導和同事喜歡這種人,因此,她干上去了,當了官,手中握有實權。不過,她非常繁忙,連我的電話都不接了。我認為她在故意躲避我,很顯然,如果她和我見面,免不了談米斤,而她和米斤沒有歡愛,她不需要,米斤有心無力。家庭對于她來說,無非是個擺設,她更在意一呼百應的感覺——情愛的缺失,必定使她熱衷權力的追逐。反過來說,她迷戀俯瞰眾生的高高在上,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情感,于她云淡風輕。但她對我女兒管教嚴,在她的監督下,我女兒以優異的成績考上重點高中。大家夸她是位好母親,這一點我承認,但我覺著,大家忽略了她的性格,她表面隨和,骨子里很好強,假如我女兒考不上重點高中,她更多顧及的是面子,而非孩子的前途。但這一點瑕疵,不影響她成為卓越的女人,我坦白,我不具備她這種舍我其誰的爺范兒。
說起來,這些事仿佛就在昨天,可它們分明過去多年。現在,我們各自相安,各有各的快樂。她倆一個熱愛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一個穿梭官場,而我呢,背著包獨自旅行,沒有目的,沒有終點,陶醉古文明的尋找與發現。倘若我在家,寫文章,喝點兒葡萄酒,點著燭光吹簫,就是美好生活了。
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