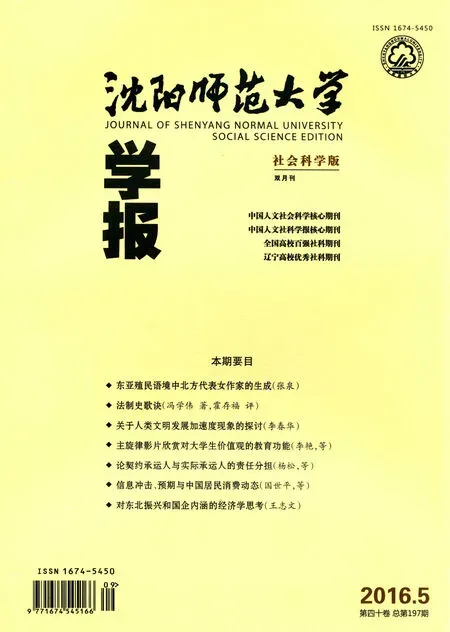“中國夢”的傳統文化根源探析
吳雙,韓立坤
(1.沈陽建筑大學學生處,遼寧沈陽110168;2.沈陽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部,遼寧沈陽110044)
“中國夢”的傳統文化根源探析
吳雙1,韓立坤2
(1.沈陽建筑大學學生處,遼寧沈陽110168;2.沈陽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部,遼寧沈陽110044)
中國傳統文化中,從先秦時期儒家的“大同”“小康”、道家的“小國寡民”開始,每個時代都會出現反映當下社會現實的集體信仰和社會理想。回溯中華民族傳統中信仰精神的各種闡述,對古代思想辯證分析、批判繼承,不但能為“中國夢”的提出提供歷史性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借鑒,展現中華民族的信仰精神和社會理想的發展脈絡和歷史邏輯,還可以幫助我們反省傳統文化中關于社會發展理論的空想、誤讀和歧路,為我們堅持“中國夢”、研究“中國夢”、實踐“中國夢”提供幫助。
傳統文化;社會理想;中國夢;哲學基礎;實現路徑
在中華大地上,肇始于先秦,各民族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共同浸潤和影響下,形成了共同的宇宙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也形成了共同的社會發展理想和美好愿望。近代以來,西學東漸,面對異樣文明,許多思想家和哲學界深刻比較中西文明,并揭示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在天人關系、人與人關系及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等方面,中華文明都呈現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殊之處。這些特殊之處就是中華民族專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并歸屬于中華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可以說,中華民族特有的社會發展理念和愿望,形成了中國文化中特有的“社會理想”,體現了中國人對于社會發展中的政治、經濟、道德、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終極發展理想,而這種社會理想在當下的最集中體現就是“中國夢”的提出和踐行。回望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資源,特別是古圣先賢對于“社會理想”的重要闡釋,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夢”的深刻內涵,并發揮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關鍵時期凝聚社會價值、社會理想和社會共識的作用,將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一、古代文化中的“社會理想”及其演變
(一)先秦時期的“社會理想”
周朝時期的禮樂之制,形成了“周文鼎盛”的局面。而春秋戰國時期發生巨變,穩定統一的社會秩序被破壞,“禮崩樂壞”,“道術將為天下裂”,諸侯之間為了權力和財富的爭斗不但粉碎了社會共同體的法律體系、道德體系,更直接導致當時信仰體系的崩塌。思想家們為了應對這種社會現實,提出了各自的社會理想,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如老子主張回到原始生存狀態,提出“無為而治”的觀點,宣揚“小國寡民”的社會理想[1]。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2],以更久遠的夏朝作為自己的理想社會藍圖。孔子提出“復周禮”的主張,其核心是要實行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和等級制度,從而建構起“愛有差等”的社會秩序。“復周禮”是要求人們都“行禮”,“禮”不僅僅指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等五倫的合法標準和道德規范,還是保證理想社會實現的禮節習俗、禮儀規定的規范。基于對禮法社會的理解,孔子在《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3]一段的表述是對先秦時期社會理想的經典概括,其既涉及國家政治、經濟,也涉及社會福利、倫理道德,成為先秦時期社會發展的最完整的構想,也為后世歷朝歷代的國家發展和政府治理提供了社會發展的理想模型,“大同”和“小康”這兩種社會形態也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信仰和追求的生活目標。
(二)秦漢魏晉之際的“社會理想”
秦漢時期所追求的“大一統”的國家信仰和社會理想,被東漢末年開始的起義和長期的群雄割據所摧毀。長期的戰亂帶來的困頓不安和流離失所,促使知識分子從國家和民族信仰的角度轉到思考個人精神信仰。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不再關注前人以禮樂政治為框架的社會理想模式,而是關注個人生命精神的自在與自由,將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落實到每個人的精神自由和心靈安頓上來。對于魏晉時期的哲學家而言,自由無為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心境才是人們追求的生存理想。對于如何處理社會理想和個人理想這個重大關系,引發當時對“名教”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如王弼繼承了先秦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認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經濟、技術,也不是道德,而是人精神層面的自由。雖然社會法制和道德“名教”對于國家社會的政治穩定和有序發展是必要的,但“名教”根本上是為了維護皇權社會等級尊卑的統治秩序,其本身是大道離散的結果。與其設定禮儀規范、制度等級來規范人們的生活行為,以此打造人人向往的理想社會,還不如返回天道“自然”,從人性的自然基因來凝練生存信仰和社會理想[4]。阮籍在思想成熟期同樣主張理想的生存狀態或生活目標是超越現實“名教”的羈絆,而復歸精神本源的自然和安寧。與阮籍很相似,嵇康也是在對現實社會政治的無奈下,試圖超越現實中的限制,而求得自我的實現。他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拋開虛偽名教的束縛而遵循自然本性[4]282-285。
(三)唐宋時期的“社會理想”
隋唐時期,外來的佛教思想深刻影響到社會各階層關于宇宙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方面的認識。佛教借鑒儒家和道家關于理想社會的具體描述,結合佛教的教義和修持方法,構造出永恒不死的西方極樂世界。這種外來宗教不但沖擊了中華文化以儒家、道家為核心的傳統信仰系統,更站在塵世生活的對立面。當時的哲學家為了重建儒家的信仰系統,不得不吸收道家甚至是佛教的相關思想資源。禮法傳統僅停留于世俗性的社會道德層面,就缺失了對人的精神境界和價值理想的建構,生活中的道德實踐也就缺乏,故必須在天道心性等形而上學領域有所建樹,才能真正維護儒家的價值世界。為此他們延續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方式,通過本體論的重構,將天與人、人與人、人與物納入到一個彼此關聯、和諧共存的宇宙之中,將天道、天理與儒家的價值原則和人倫規范聯系起來了,他們既視儒家的價值原則和人倫規范為天道、天理的體現,以維護儒家價值原則和規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時,亦視儒家的價值原則和人倫規范都出于人本身所具有的仁義之性。他們的基本思維方式是從宇宙學說中尋找社會理想、揭示人生境界。如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著名論斷[5],描繪了一個萬事萬物彼此緊密關聯的宇宙大家庭的理想。“民胞物與”的思想解決了如何從個人的立場來看宇宙,又如何運用這種對宇宙的觀察來安頓社會、人生的問題。這一思想與傳統儒家的“禮運大同”的社會理想一脈相承,代表了這一時期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
(四)明清之際的“社會理想”
從明末開始,在延續儒家為主流的個人道德心性的修養模式基礎上,關于國家、民族的整體思考和討論成為知識分子的思考重點。可以說,從明末經清朝、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幾百年中,在新的歷史時期和思想語境下,對于《禮記·禮運》篇中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國家和社會理想的當代建構,成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命題之一。明清之際的黃宗羲主張,要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這個“天下之法”不僅僅是行政上的法律,它還應包括軍事、土地、教育、禮樂、賦稅制度等一套完整的社會制度,這樣才能養民、利民、求民、保民。黃宗羲進一步提出要建構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社會整體是由眾多的個體組成的,君臣關系是一種師友關系,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沒有絕對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君臣共同擔負起治理天下、服務天下的重大職責,這種社會治理模式的具體措施就是實行平民議政,而學校則是平民議政的最佳場所[5]193-195。
清朝中后期,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和學習逐漸深化,以科學文明和民主制度為特點的西方現代文明強烈地沖擊著閉關鎖國的清王朝的合法性。面對進步、科學的西方社會,國人不得不改造并重建新的社會理想,以此適應現實社會的發展規律。19世紀后期,中國的哲學家、政治家面對著一個科學、進步、強大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課題促使國人從科學、政治、精神三個層面系統展開自我變革。
二、20世紀之后“社會理想”的重構
(一)西學東漸與民國時期“社會理想”的實踐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學說的傳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興中會的活動一開始便和傳統的王朝更替模式區別開來,而具有新時代的特點。1911年,在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同盟會領導下,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在中國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以西方資產階級制度為藍本的中華民國。然而中華民國成立后,孫中山所期望的三民主義并未實現,國內連年軍閥混戰,中國社會并沒有如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期望的那樣,變成西方歐美國家那種政治民主公開、工業技術發達、經濟發展進步、社會生活安全穩定、人民道德素質良好的理想狀態。
(二)馬克思主義傳入與共產主義理想
隨著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傳入中國。十月革命后,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大批知識分子開始研究并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以至于組建專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人民為實現國家的統一、民主、富強進行不懈奮斗。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社會理想的重新探索和實踐亦由此開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從此開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征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真正掌握了自己的政治命運和經濟命運,這使得在中國建設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有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但是在隨后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時期,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經驗和教訓也是慘痛的。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
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鄧小平提出了黨在現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鄧小平正確地認識到中國仍然是一個“落后型”的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應該是“三步走”:20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21世紀用30到50年時間再走第三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三、“中國夢”是當下“社會理想”的集中表述
(一)“中國夢”的具體內涵
在當今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就表現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形態——“中國夢”。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第一次闡釋了“中國夢”的概念。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對建國幾十年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的整體認識,“中國夢”是通過頂層設計的方式提出的新時期的執政理念和社會發展理念,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社會理想的科學統一,是對中國國家民族發展目標、前進方向、情感信仰的高度概括和總結。“中國夢”本質上是國家、民族、個人三個層面的理想信仰的總稱,是精神取向和社會理想的現實表達。
具體來說,“中國夢”的兩個階段: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也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中國夢”的實施手段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中國夢”的具體表現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就從國家、民族、個人三個維度設定了中國共產黨未來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需要達到或實現的目標。同時,“中國夢”的三個維度也為檢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府管理在制度建設、市場調控、文化傳承、倫理培養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標準。與以往單純以經濟建設和經濟指標為中心、專注社會硬指標的建設不同,“中國夢”將經濟發展與民族文化振興、人民生活幸福納入到統一的有機體之中,提出了中國發展的軟指標,認為任何一個方面的進步而輕視甚至阻礙其他兩方面發展的國家治理模式都是片面的、不科學的。
(二)“中國夢”的哲學基礎
“中國夢”思想的正確性在于,它遵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物質和意識、量變和質變、客觀規律和主觀能動性等關系的基本規律。“中國夢”的思想是對中國當下客觀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道德等領域的辯證認識和正確把握,“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論斷為我們揭示了中國未來發展的三個維度和領域,符合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的基本規律。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根據社會現實提出了不同的社會發展理念和建設要求,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到“中國夢”,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和現實性特點。“中國夢”是從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成就出發展開的論述,充分考慮到經濟成就的積累、民族精神的培育、人民幸福感的逐漸提升等重要方面的準備過程,并提出具體的階段性目標,符合量變到質變的哲學基本規律。“中國夢”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精神層面的全新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預定了明確的旗幟和目標。“中國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在精神意識維度方面的科學判斷,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三)“中國夢”的具體要求和實現路徑
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為了實現中國夢的目標,習近平提出“三個必須”的要求,即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明確指出了作為中國人特有的“夢”,需要符合中國社會的特點和現實,符合中國文化的精神與信仰,符合中國民族的利益和訴求。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無疑正確揭示了“中國夢”的精神信仰維度。“中國夢”繼承了古代信仰和價值傳統的科學性元素,又將國家信仰、民族信仰、人生信仰的實踐路徑統一表述。“中國夢”是在辯證批判吸收古代優秀信仰精神基礎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成就、發展階段的正確認識和科學想象,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精神信仰與社會理想的頂層設計理念。由此,“中國夢”必將成為凝聚全民族理想信念的強大精神支柱,為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產生巨大的作用,其必然成為激發和強化中國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奮發圖強意識,成為鼓舞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歷史性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
[1]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2001:357.
[2]張雙棣.《淮南子》校譯: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199.
[3]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92-193.
[4]馮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78-279.
[5]馮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50.
A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Origin of Chinese Dream
Wu Shuang1,Han Likun2
(1.Office of Students’Affairs,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168;2.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866)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even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period’s Confucian“great harmony”“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or“small country with less population”of Taoists,each era reflects the collectivism belief and social ideals based on social realities.Backtracking the explanation of the believes in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ancient thought can not only provide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guide for the Chinese Dream and show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belief of spirit and social dream of Chinese,but also be reasonable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imagination,misreading and forked roa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which should be helpful for there search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ream.
traditional culture;social ideal;Chinese dream;philosophical foundation;realizing path
G 03
A
1674-5450(2016)05-0063-04
2016-07-01
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立項(20151s1ktzijyx-19);遼寧省高等學校杰出青年學者成長計劃項目(LJQ2014051)
吳雙,女,遼寧沈陽人,沈陽建筑大學講師,設計藝術學碩士,主要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韓立坤,男,黑龍江綏棱人,沈陽大學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
【責任編輯:趙穎責任校對:趙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