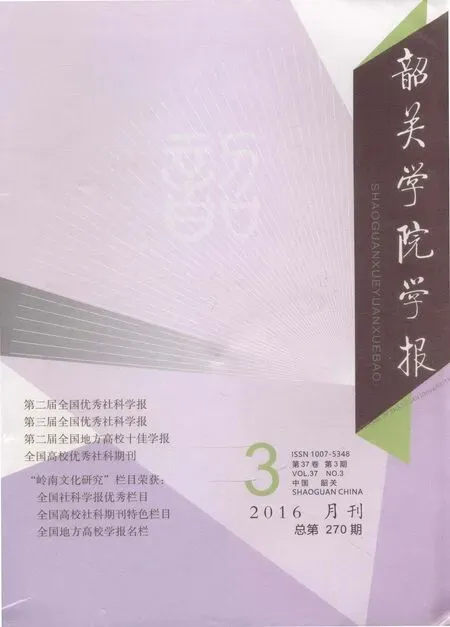論文本外因素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周瓊(韶關學院外語學院,廣東韶關512005)
?
論文本外因素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周瓊
(韶關學院外語學院,廣東韶關512005)
摘要:從“翻譯即操控”角度看,《圍城》英譯本的成因及其影響,除小說文本的因素之外,還受到譯入語的社會意識形態、詩學環境、翻譯目的、讀者期待以及贊助人等多種文本外因素的操控。從文本外因素的視角切入,對于深入分析《圍城》譯本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文本外因素;《圍城》;英譯本;操控
錢鐘書的小說《圍城》發表于1947年,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狀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情態,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最有趣,最細膩或許還是最偉大的小說”,創下印數392萬冊的歷史記錄,期間國外學界對錢鐘書的關注和研究也急劇增長[1]。1979年由珍妮·凱利(Jeanne Kelly)和茅國權(Nathan K.Mao)合作完成的英譯本《圍城》面世,在海外漢學界中反響甚為熱烈。該譯本被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評選為1980-1981年間的卓越學術著作,2005年被收入選材標準嚴格且在英語界影響力巨大的英國企鵝經典文庫。到目前為止,該小說沒有出現第二個英文譯本。《圍城》英譯本取得的巨大成功,除去作者和小說文本本身的因素之外,還受到多種文本外因素的影響。
一、文本外因素在翻譯中的地位和作用
傳統的翻譯活動一直被看作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過程,翻譯研究因此也歷來是圍繞語言分析和文本對照進行的。對原語和譯語文本進行對比,以及對翻譯標準的制定和遵守成為傳統翻譯活動最主要的研究部分。20世紀80年代,認識到文化對翻譯的制約作用,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勒弗維爾和巴斯奈特跟從佐哈爾(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認為文化中蘊藏著驅動和制約翻譯的本質性的東西,也就是文本外因素,會影響或決定翻譯的走向,因此該派主張將翻譯行為放在文化的大語境下來考察,將翻譯的研究重點從原作轉向譯作,從作者轉向譯者,從源語文化轉向譯語文化。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維爾在合編的《翻譯、歷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一書中提出,翻譯不僅僅是復制和模仿,而是文化的協調和操控。1992年,勒弗維爾出版的專著《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強調歷史意識和文化觀點,聲稱“翻譯即重寫”,“重寫即操控”,這種操控使得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續。在他看來,一切重寫,不論其意圖如何,都反映出譯語文化的某種思想意識和詩學[2]211。
文化學派強調文本外因素在翻譯活動中的作用,顛覆性地把翻譯的基本單位定位成“文化”,而不是傳統的單詞和句子,認為基于詞語對等或者篇章對等的“忠實”根本不存在。當下的翻譯研究意味著與翻譯有任何關系的任何東西,是各種社會力量用來“操控”特定社會、建設所需文化的“主要”文學手段[2]211。這一觀點使得翻譯作品的地位大大提高,同時使“翻譯”作為翻譯本身而存在的學科屬性日益模糊,為當代的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新維度。
二、文本外因素對《圍城》英譯本操控的表現形式及成因
《圍城》于20世紀40年代寫成,沉寂到70年代末才被譯成英文,而英譯本卻受到追捧和好評。這除了與該小說文本本身的語言因素相關外,還需要將視野放大到整個譯介文化大環境,綜合考量當時譯入語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分析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主流詩學環境,譯者的翻譯目的,讀者的期待以及贊助人等文本外因素對該小說的影響。
(一)主流詩學環境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韋努蒂在其《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The Translator’s Visibility---AHistoryof Translation)中統計出的數據顯示,在1982-1984年間,中文英譯的作品分別為159部、148部和163部[3]。中國最為西方所熟知的作家有魯迅、茅盾、郭沫若、郁達夫等等。跟整個西方文學界其他語種的文學作品譯介相比,中文的譯作是較少的。一部外譯文學作品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系統要得到歡迎和重視,其作品主題必須符合譯入語的社會文化和詩學環境,也就是在一個文學系統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學寫作手段和功能。譯本作為外來文學,能否成功被引入某一詩學,甚至改寫這個詩學,就取決于該譯本的主旨和詩學是否和目的語的詩學環境相融合。
美國當時的主流詩學環境,讀者對歷史不感興趣,他們注重趣味性、時效性和現實關注度,欣賞快捷、直觀和行動性。這固然與美國在政治、經濟及文化等方面的領先地位所導致的國民驕傲心理有關,同時也跟美國讀者的閱讀偏好以及價值取向有關系。前期英譯的中國文學作品,主題大都集中表現人民對于歷史造成的苦難和貧窮的承受,或者是對政治主張的說教式宣揚。中國文學偏重歷史性,主題集中在貧窮、戰爭和農村生活,因而缺乏吸引力[4]7。因此,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譯介在美國一直處于邊緣化生存狀態。《圍城》的題材和主題不在此列,該小說創作淵源豐厚,既有民族文化與文學的基因,又有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有割不斷的聯結。可以說,《圍城》的視野一開始就是世界性的,這無疑讓外國讀者耳目一新,為他們了解當代中國文學提供了新穎的素材。
(二)意識形態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翻譯從來都不是可以隨性而為的私人事務,而是受到各種權力話語的左右和操控。勒弗維爾認為,意識形態決定了譯者基本的翻譯策略,也決定了他對原文中語言和論域有關的問題的處理方法。而弱小民族的文學譯介,多半體現“以譯入語文化為主導地位”的翻譯策略。賀顯斌曾說過:從使用人數上看,中文一定不是小語種,可是和長久以來占霸權地位的英語相比,中文是弱勢的。因此,在英譯中國文學作品時,“西方讀者優先”是譯者一直奉行的原則。對于讀者來說造成理解困難的地方都被隨意刪去,很多刪節有時都是隨意和不公正的[5]。譯者處于特定時間的特定文化之中,他們對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響他們翻譯方法的重要因素。
Julia Lovell(藍詩玲)認為,和同時代的日本文學作品相比較,中國的文學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度范圍要窄許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國二戰后試圖重振日本以作為自己的跳板,進而遏制共產主義的中國。因此大量日本文學作品被譯成英文。而這些作品中所描繪的日本,充滿了詩情畫意和異國情調,和戰前那個軍國主義盛行,好戰挑釁的日本形象大相徑庭。其中最炙手可熱的作家包括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樹[6]。意識形態對文本類型選擇的操控力度可見一斑。
20世紀70到80年代,由于中國在美蘇爭霸中的戰略地位,中美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也日漸頻繁。政治上的互通必將促進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與先前在美國知名度較大的作家作品不同,西方讀者開始關注新的面孔和作品。錢鐘書的作品外譯正是處在這一階段。
(三)翻譯目的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傳統翻譯研究的劣勢之一是譯者在文化上被看作中立者。功能翻譯學派代表人物諾德(Nord)曾說,如果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在目標讀者中實現某種功能,那么任何阻礙這種功能的翻譯都屬于翻譯錯誤[7]。《圍城》英譯本的作者珍妮·凱利和茅國權正是本著推薦優秀中文文學作品給西方讀者的目的。在他們看來,《圍城》這部語言機智幽默,諷刺辛辣又不留情面,內涵深意豐富。在英譯本的introduction部分,兩位譯者花了近20頁的篇幅,傳記式地介紹了錢鐘書的生平,包括其教育背景、工作經歷以及錢鐘書的一系列代表作品,還對小說《圍城》作了一個綜合和全面的總結性評價,并發表自己的見解,可見譯者的翻譯目的是推薦錢鐘書及其作品給西方讀者。
譯者茅國權在譯者序中寫道:他們希望通過《圍城》的英譯本激發英語讀者對錢鐘書及其作品更大的興趣[8]3。基于此出發點,他們在翻譯的時候盡量考慮譯文讀者的感受,使讀者在已有的知識和文化范圍內更好地理解原文。對譯文進行恰當的歸化和異化處理,在盡量使譯文通順流暢、符合譯文讀者的閱讀習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向譯文讀者傳遞中國文化。
在譯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歸化翻譯策略,例如:
“蘇小姐一向瞧不起這位寒磣的孫太太”。
譯: Miss Su has always scorned the poor and simple-minded Mrs Sun.[8]5
文中“寒磣”被譯成“poor and simple minded”,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揮較大,只考慮了譯文讀者的感受和接受力,這樣的翻譯策略顯然是服務于譯者本人的翻譯目的的。
又如:“不免像黃梅季節的墻壁”中的“黃梅季節”是中國特有的表達方式,指的是每年4、5月長江中下游地區梅子成熟季節連續的下雨潮濕天氣。而放在西方文化里,沒有地理文化背景知識作為支撐,讀者是會感到困惑的。所以,譯者用“rainy season”這個對于西方讀者來說一目了然的表達方式,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當然,譯者有時為了更好地傳達原作,促進文化交流而采取的異化翻譯策略例子也不勝枚舉。如:“井水不犯河水”這樣的中文俗語,被譯成“keep the river water separate from the well water”,完全保留了中國俗語對于讀者的陌生度,如果譯者想要找到英文對等的表達方式,或許用“stay out of my things”或者“don’t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等等,更能幫助譯文讀者理解原著。這樣歸化與異化靈活運用的翻譯策略,恰好體現了譯者翻譯目的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四)讀者期待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譯作是為特殊的目標語讀者群而創作的,在翻譯過程中必須時刻考慮他們的接受心理,盡量照顧讀者的期待,從而避免譯作成為無人讀沒有意義的東西。不論翻譯目的如何,譯文都要能給讀者或傳送新的信息,或勸服讀者,或娛樂讀者。而作為能閱讀外來譯作的讀者來說,他們對于譯文中的洋味和新事物做好了心理準備。
對于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來說,現代中文小說里提到的中國文化和典故對于他們是陌生的,因為前期英譯中國文學的匱乏使得讀者缺乏對中國文學一脈相承的認識,這影響了他們對中國小說的理解和欣賞。英國學者Q.D.Leavis總結為以下幾點:美國一般知識分子讀者(非文學研究者)喜歡文學性強且非常引人入勝的小說;不喜歡沉湎于凄慘的情感;不喜歡晦澀難懂、含蓄的寫作方式;不喜歡壓抑、前途灰暗,令人絕望的小說,無論其文學技巧如何高超[5]36。而小說《圍城》的主題擺脫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主流題材的桎梏。在長達20多頁的英譯本的序言部分,譯者將原小說描述成幽默的流浪漢小說和學者小說,并指出該小說引經據典,涉及中外文學、哲學、法律、邏輯學和教育等學科,這便注定該英譯本的讀者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群體。而這一群體,剛好是樂于接受新文化、新理念和新價值觀的群體。所以《圍城》英譯本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讀者的期待和接受能力。
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不斷平衡著翻譯目的和讀者期待兩個方面。只有讀者接受譯作并作出符合譯者預期的反應,才能說明翻譯活動的成功。《圍城》英譯本受到的好評恰好說明了譯文是符合讀者期待的。
(五)贊助人對《圍城》英譯本的操控
翻譯的發起者是隱藏在翻譯行為后的驅動力,對翻譯也會有一定的影響。勒弗維爾所說的贊助人指的是任何對于某作品的流通和宣傳有積極或消極影響力的力量。闡釋學、翻譯學派代表斯坦納認為任何翻譯活動都始于譯者對原文本和作者的信任,相信其待譯作品是有意義的[9]。而《圍城》譯者對錢鐘書及其作品的高度贊揚充分體現了譯者對源語文本和作者的信任。根茨勒(Gentzler)認為,贊助者對翻譯的影響遠不止譯本的選擇這一方面,它通過思想意識、經濟和地位這三種因素左右著譯本形成的整個過程[3]21。中國文學作品的研究和閱讀在美國僅限于大學層面,對于大眾讀者的影響甚微[6]32。從《圍城》英譯本的序言中可以看出,為該小說英譯本推波助瀾的大多都是華裔學者和錢鐘書的個人崇拜者。所以,這些贊助人有著自己的學術或文學影響力,能夠促進譯本的形成或者影響譯文的走向。
三、結語
文學作品的譯介屬于翻譯活動中較難的部分,因其承載的文化內涵遠遠超出其他文本形式,只對文本語言作機械的復制和轉換是無法充分傳遞文學作品所蘊含的文化意義的。文學作品的譯介需要譯者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協調和操控。優秀的文學作品會得到讀者的喜愛,但是僅僅靠文本本身的質量無法確保其譯文在譯入語語言文化系統中能獲得同樣的反響。而這正是因為文本外因素多維度地左右著譯本的形成和影響力。
前人對《圍城》英譯本的研究多如牛毛,得出的結論褒貶不一。究其原因,是由于研究的角度只關注文本語言本身,側重探討該譯本的具體翻譯策略和技巧等。而《圍城》英譯本的成功,不僅歸根于作者錢鐘書的個人影響,也不僅是因為該小說文本本身的魅力,而且還受到當時譯文語言的社會意識形態、詩學環境、譯者的翻譯目的、讀者的期待以及翻譯過程中贊助人等因素的操控。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了該譯本的形成時間以及讀者對譯文的態度。當時的詩學環境影響著譯者對題材的選擇,進而促進了譯者對該小說的選擇。譯者的翻譯目的左右著翻譯過程中具體的翻譯策略和技巧,最終決定了譯文的語言形式和接受度。讀者期待也影響著譯者的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取舍。贊助人則推動了譯本的形成,提高了譯本的影響力。由此可見,只有結合文本本身因素與文本外因素來對《圍城》英譯本進行研究,才能全面闡釋其譯本的真正內涵,給譯文一個客觀全面的評價。
參考文獻
[1]葛校琴.《圍城》英譯底本考證[J].外語研究,2013(6):63-66.
[2]李文革.西方翻譯理論流派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
[4]崔艷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小說在美國的譯介與傳播[D].長春:吉林大學,2014.
[5]賀顯斌.論權力關系對翻譯的操控[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6]Lovell,Julia.Great leap forward[EB/OL].[2005-06-11].http://books.guardian.co.uk/print/0,3858,5212214-110738,00.html.
[7]趙彥春.翻譯學歸結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67.
[8]Kelly,Jeanne,Nathan K M. Fortress Besieged[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3.
[9]孫穎琳.從翻譯四步驟看珍妮·凱利、茅國權譯《圍城》[J].異域文苑,2012(2):33-35.
(責任編輯:廖銘德)
On the Manipulation of Extra- textual Element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icheng
ZHOU Qi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Translation is manipulation”,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ichengand its influence are not only decided by its content,but also manipulated by the extra-textual elements like ideology,poetics,translation purpose,the expect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as well as patronage. Research from the above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eper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Key words:extra-textual elements;Weicheng;English translation;manipulation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348(2016)03-0107-04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簡介]周瓊(1986-),女,湖南湘潭人,韶關學院外語學院助教,碩士;研究方向:翻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