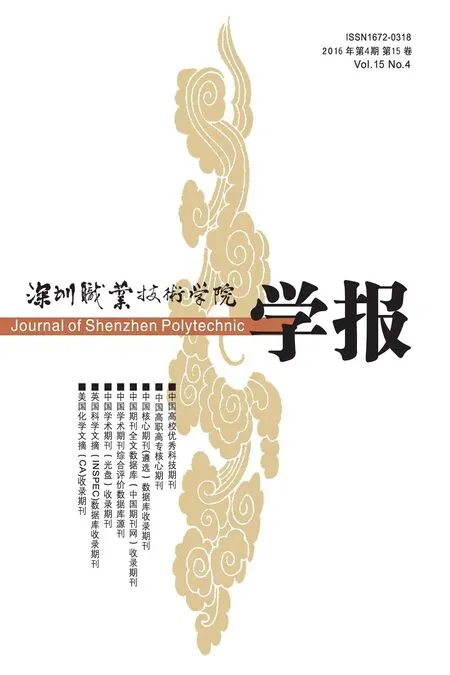對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不可抗力的反思
姜 平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507)
對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不可抗力的反思
姜 平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507)
環境侵權責任因其特殊的無過錯歸責原則和因果關系的認定,“不可抗力”一直以來都是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但是,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和高新科技的廣泛性運用,“不可抗力”是否應該作為免責事由引起學術界的爭論。從全球環境倫理的價值背景看,重新審視和考量這一法律制度,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是不適宜的。本文結合對“不可抗力”這一免責事由相關問題進行探討,進而為其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議。
環境侵權;不可抗力;免責事由
近年來,隨著全球污染問題的加重,環境污染折射出的問題很多,有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但從法律層面講,主要是環境侵權損害的問題。從現行國內法的角度來分析,環境侵權的制度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41條的規定;其次,是一些單行法規,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42條、《大氣污染防治法》第37條和《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3條的規定;最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關于環境污染致人損害責任的規定,以及第70條的民用核設施致人損害責任的規定都是與此問題相關的制度。這些相關的制度不僅規定了環境污染應當承擔的責任,而且也明確規定了可以免除責任的理由。
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就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災害、受害人過錯、第三人的過錯和戰爭行為。”[1]231-232還有的學者主張免責事由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第三人過錯、受害人同意、受害人故意、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依法執行公務”[2]549-580。民用核設施致人損害責任的免責事由只有兩種,即戰爭和受害人故意,并沒有把不可抗力作為免責條款。可見,民用核設施的免責事由是非常嚴苛的,作為一種高科技和高度危險的能源,“不可抗力”不能免責所體現的不僅僅是法律上的正義,更為重要的是表達了對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為什么有如此的不同呢?是因為環境侵權比民用核設施的損害更小,還是因為我們的制度本身存在問題呢?毫無疑問,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絲毫不亞于一次大的核事件所造成的損害。所以,環境損害與民用核設施在免責事由上的不同,不是因為二者的損害后果不同,而是因為制度本身有缺陷。
鑒于本文主要問題在于解決環境侵權中的“不可抗力”所存在的制度瑕疵,再加上民用核設施的侵權問題相對來說規定的比較明確和完善。所以關于民用核實施的問題,在這里就不在做過多的論述,我們主要圍繞環境侵權中的“不可抗力”可否作為免責事由展開。
1 “不可抗力”作為一般民事侵權責任免責事由的理由
作為一種侵權責任的免責事由,“不可抗力”制度的設計主要基于這樣的考量,即侵權損害的發生,遠遠超過了人類所能認識和控制的范圍。更加準確地講,致害源何時何地出現,出現后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在人類現有的技術能力范圍內是不可預見和避免的;或者說,雖然事前預見到了將要出現損害后果,但是人類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是無法改變和避免其后果發生的。對于這樣的事件,如果還要行為人承擔損害后果責任,則會失去法律正義,所以免除行為人的法律責任。這就是不可抗力作為一般民事侵權責任免責事由的理由。為了深入的分析環境侵權中“不可抗力”的制度問題,在法律邏輯之下,有必要對“不可抗力”作為一般侵權責任的免責事由進行探討。
關于“不可抗力”的經典規定,主要是體現于《民法通則》第153條:“不可抗力指的是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現象。”當然這樣的規定,是相當抽象和模糊的。這個范疇僅僅從性質上規定了“不可抗力”的法律內涵,并沒有指出具體的內容和類型。有些學者則補充認為:“不可抗力是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包括某些自然現象(如地震、臺風、洪水、海嘯等)和某些社會現象(如戰爭等)”[3]135。此中補充一定程度上具體化和明確化了不可抗力的內容和類型,但還不是很完善。
從上面可以看出,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的免責事由主要分為正當理由和外來原因兩大類。正當理由是從行為的規范根據上所進行的分類,是指行為人實施了損害行為,但該行為如果是合法的、正當的,行為人可以免除侵權責任。換句話說,行為人雖承認其行為造成了損害的原因,但主張實施該行為時具有合法的根據。正當理由一般包括“依法執行公務、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自助行為、受害人同意”[4]658。而外來原因則是從因果關系的角度進行分析,其一般是指因行為人之外的原因而造成的損害,行為人據此可以免除或減輕侵權責任,即行為人否認損害是其行為造成的。外來原因包括“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過錯、第三人過錯”[4]662。這是目前我國法學理論中對一般侵權行為的免責事由比較完整的論述。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不可抗力”作為一種免責事由,僅僅是侵權行為免責事由體系中的一種而已。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新的免責事由會不斷出現,免責事由體系也會逐漸完善和多元化。然而,很多時候人們在使用這個范疇的時候,往往忽視其中因素變化所帶來的差異,撇開具體的法律關系來適用免責事由,使其適用泛濫化,嚴重脫離了法律思維的軌道。
2 “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的不合理性
環境侵權及其構成要件、歸責原則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免責事由的特殊性。目前,學界有的學者對“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持支持意見,但也有些學者認為環境侵權中,“不可抗力”不應該作為一種免責事由。實踐層面,全世界的許多案例,如“切爾諾貝利事件”,“印度的毒氣泄漏事件”,以及 “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都將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予以排除,這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免責事由應與環境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具有相同基本價值取向,“即這一原則應立足于公平地保護受害人權益,并最大可能地彌補受害人遭受的損失。”[5]總之,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面臨挑戰,其制度的不合理性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環境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和因果關系。環境侵權中的歸責原則和因果關系是環境侵權中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歸責就是確定責任的歸屬,是“負擔行為之結果,對受害人而言,即填補其所受之損害。”[6]272歸責原則“指在行為人因其行為和物件致他人損害的事實發生之后,應以何種根據使之負責,即法律應以行為人的過錯還是應以發生的損害結果,為價值判斷標準,亦或以公平等作為價值判斷標準,而使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7]173歸責原則解決的是確定責任的根據,為責任的成立尋找依據。
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是確定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根據和標準,也是貫穿于侵權行為法中對各個侵權的歸責立法指導方針,體現了侵權行為法的立法價值取向和價值功能,在侵權行為法中處于核心的地位。我國環境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現行立法明確為無過錯原則。在環境侵權責任中,“在不可抗力存在的情況下,致害人無過錯或只有部分過錯且致害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必然存在因果關系或相當因果關系,不可抗力本身才是損害的發生的主要原因”[8]171。在環境侵權中,因果關系的認定也有特殊性,一般認為是必然因果關系說,即因果關系的認定不是抽象的,主觀臆斷的,而是符合自然的社會的經驗法則[8]172。因此,因為不可抗力,認為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而免責,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會說不通的。
第二、工業革命以來,工具理性主義和科技革命推動所帶來的現代文明,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肇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巨大的推動了全球的工業化浪潮。歐美主要國家的生產力獲得飛速發展,經濟的繁榮伴隨著對自然地征服和對環境的極端破壞,文明陷入了可怕的“二律背反”。經濟的發展應該具有的樣態是人類生活環境的美好,但是,工業化的帶來的卻是人類環境的巨大損害。現代文明應當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是人類生存的終極價值。人類賴與存在的環境一旦受到毀滅性的破壞,人類滅亡也就不遠了,畢竟,目前為止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平衡,最終會招來自然地報復。于是各國權衡利弊,一方面在承認環境損害的事實的基礎上,另一方面采取相應的機制來增加自己的社會責任,以求效率與公平。在此背景下,各國在環境侵權責任中,大多規定了無過錯歸責原則,讓企業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因果關系上采用因果關系推定和舉證責任倒置。但是,由工具理性的主導下的經濟行為,很多國家,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好。可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凌駕于全球環境利益之上,嚴重阻礙了全球環境利益的維護。
第三、環境侵權行為人本身的行為是一種經濟上獲利行為,而且政府也是利益相關方,政府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以經濟的發展來樹立的。政府不僅是一種政治組織,還是社會組織,承擔著應有的社會責任。環境侵權者主要是企業組織,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必然會伴隨著對他人和社會環境的損害,所以,讓其承擔與其相應的無過錯的社會責任也是非常公平的。企業的經營行為威脅到公共利益的時候,其承擔的“公法責任”也不可避免。政府是公權力的代表,主要承擔的主要是過錯責任,本質上是一種監管責任。但是,當損害是在合法的情況下,或者無法追查侵權人的情況下,政府也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這種責任由政府的公共性質決定的。而且在侵權中,企業的經營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具有功利主義的目的,這種目標的實現與他人生存的環境利益緊緊相關。企業強勢的地位決定了,在無過錯的侵權中,本著正義價值取向和社會責任,讓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也是理所當然的。王利明教授就認為:“如果某些高度危險責任屬于無過失責任,就不應以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不可抗力雖然表明被告沒有過錯,但損害在事實上又確與被告的行為和物件有關,若完全免除被告的責任,將使無辜的受害人得不到任何補償,從而不能達到對損害進行合理分配的無過失責任的目的”[7]317-318。
第四、要求“不可抗力”下,環境侵權行為人不免責,有利于增強其注意和謹慎義務,也有利于引導社會行為,充分發揮制度的指引作用。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在微觀層面上的企業,企業的物質生產維持著人類社會的延續。大規模的企業行為,本身具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發展和環境保護問題是一對矛盾,我們既不能只要發展,不要環境,也不能只要環境,停止發展,關鍵的是如何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環境侵權實行無過錯原則本身的立法精神是值得贊許的,但規定“不可抗力”使其免責事由無疑使這個制度失去了本身立法價值。要求“不可抗力”下環境侵權行為人不能免責,可能有的企業認為很不公平,但其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層面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它可以在更寬廣的領域使行為人甚至更多企業樹立環境意識,倡導環境倫理,引導良性環境行為。
第五、我國的相關立法也規定并不是所有的環境侵權中的“不可抗力”都是免責的,而只是將不可抗力的范圍限定在某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第46條,《環境保護法》第41條,《水污染防治法》第56條,《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3條都將不可抗力規定為免責條款,而《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噪聲污染環境防治法》則未將“不可抗力”規定為免責事由。從上述有關規定看,我國在環境污染損害中,就自然現象引起的損害僅限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作為法定的免責事由,而且該法定免責事由在作為引起損害時,被告必須在自然災害發生時及時采取救濟措施,以免造成環境污染。2008年新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5條第2款規定:“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損害的,排污方不承擔賠償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新《水污染防治法》把“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的范圍進行了擴大。這說明立法者的在特定情況下,已經將“不可抗力”排除在免責事由之外。
第六、當今世界,環境問題已成為世界性的“全球問題”,實行無過錯為基礎的環境侵權領域,不可抗力成為免責事由可能會違背全球環境倫理的價值目標,也與環境哲學的理念相去甚遠。全球化使地球成為一個“地球村”,使各國密切聯系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一員。每個國家的行為已經不僅僅是單個的行為,而是與我們整個人類的行為密切相關。當我們將民主視為全球的普世價值時,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與環境和諧相處。發展是各國普遍追求的現實目標,但發展不是以技術理性無情的征服環境為代價,而是與環境相平衡、適應的發展。功利主義哲學所倡導的工具理性破壞了人類與環境的和諧關系,恩格斯早就指出,人類對環境的征服,早晚會得到環境的懲罰。現在,這個懲罰終于來臨了,“全球變暖”,“臭氧層空洞”,“極端惡劣天氣”,“生物多樣性缺失”等等問題,已嚴重威脅到了人類的存在。“全球問題”終究要靠全球治理結構的完善來解決,一個國家不能解決所謂的“全球問題”。況且,很多環境問題已經超出了一國控制的范圍,如果將“不可抗力”視為免責事由,會導致各國在環境問題上相互推諉,消極不為,最終受害的將是整個人類。
綜上所述,在環境侵權中,“不可抗力”不適宜作為免責事由。但現行制度還是將不可抗力作為有限制條件的免責事由,為行為人的免責留有余地。這樣的規定也有其相對合理的一面。如果絲毫不考慮侵權后行為人的積極作為,一概認為“不可抗力”不免責,其后果是什么呢?行為人選擇就很明確,只會消極不作為。因為積極作為防止損害擴大和消極不作為,法律后果都是不免責,那行為人當然會袖手旁觀,受害的只能是受害人的環境利益。
可見,目前的制度有進行相應的完善的必要性,使其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內更具有可操作性,更符合法律正義。
3 環境侵權中“不可抗力”免責事由制度的完善
綜上所述“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在理論和實踐中面臨質疑和挑戰。其根本原因歸結于環境侵權中特殊的歸責原則和因果關系。對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思考可行的解決方法。一方面,改變其特殊的歸責原則,即把無過錯責任原則改為其他的歸責原則,以求與相應的侵權責任構成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將“不可抗力”從免責事由中剔除出去,實行“不可抗力”不免責的責任原則。
這兩個思路,前一種做法,很明顯是不可能達到的。首先,立法層面是不可能得到支持,會遭到立法機關的“凍結”。法律制度出了問題,只能通過立法解釋或者司法解釋來解決,但這種解釋不會違背其立法精神。現行制度總體上還是比較合理的,為了個別條款而廢除整個制度不太可能。其次,在理論層面,無法站得住腳。環境侵權中,選擇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是立法機構和法學家們經過大量的思考和總結實踐經驗得出的,有其社會和理論基礎。利益權衡選擇的無過錯原則比較好的保護了受害者的環境利益,而其他的歸責原則是制度設計中摒棄的 “次品”。最后,在實踐層面,無過錯原則有現實可操作性,有利于彌補因環境侵權造成的損害賠償,而不至于使普通民眾因侵權而無法得到賠償的制度尷尬。現實生活中,很多的環境侵權合法進行,另外,許多侵權無法找到行為人,或者說行為人是一個不確定的群體,這些都為受害人尋求救濟和維權造成困難。而實行無過錯歸責原則,可以避免這樣的局面出現,最大程度上維護受害人的利益。
第二種思路,我們可以嘗試將“不可抗力”適當地清除出免責事由的體系。也就是說,在“不可抗力”的背景下,盡管行為人采取了積極的措施,仍沒有防止損害結果的發生,行為人不可以免責。此制度的變化與現行制度的最大區別在于,不考慮行為人的主觀上的積極努力的因素,只要出現了“不可抗力”造成的損害,行為人都應當承擔責任。這樣設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行為人將承擔更加嚴苛的責任,其間接的效果在于可以增強行為人的注意和謹慎義務,在生產中積極地采取相應措施,將“不可抗力”的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同時也有助于培養行為人的社會責任感和環境倫理意識。但是這種制度設計的缺點也是很大的,例如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來說,當不可抗力來臨時,其無法預測災害的何時到來,也無力采取完備的措施來預防。假如在此次事件中,東京電力公司沒有絲毫的過錯,也無法阻止災害的發生,但卻要承擔巨額的賠償費,這也是法律正義所不允許的。這樣的后果就會使行為人負擔巨額的賠償金,大大阻止人們開發和從事經濟活動的欲望和動力。另外,將“不可抗力”排除其“免責事由”體系,也會使行為人消極不作為,其法律和社會效果更加有害。相比較而言,第二種思路可能會更加合理,因為該制度的價值在于保護受害方的利益,但我們不能完全接受第二種思路。我們應結合現行制度,對第二種思路進行反思,使“不可抗力”制度趨向于完善,實現“修正的正義”。
首先,在法律的范圍內,應當嚴格界定“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一個相當模糊,沒有明確界定的范疇,適用到具體案件中,產生爭議不可避免。法律不明確會使人們陷入可怕的奴役狀態。“不可抗力”指“不可避免,不能預見,不能克服”的自然和社會現象。自然現象主要指地震、海嘯、暴雪、泥石流、火山爆發等自然力,這些涉及到自然知識的范疇;社會現象包括戰爭、暴動、罷工等社會現象。并不是所有的自然和社會現象都可以成為法律意義上的“不可抗力”,成為法律意義上的不可抗力需要我們的技術支持和社會理性標準。也就是說,需要專業的權威的技術部門來認定不可抗力的內容,例如:不可抗力的程度、不可抗力構成法律意義的臨界點、不可抗力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影響等等,這些因素對行為人是否應承擔無過錯責任,承擔多大的責任具有重要的意義。據此,我們可以嘗試建立專業的“不可抗力鑒定機構”,司法機構可以建立,民間有資質的也可以建立,并在財政上和制度上保障其運行。此種機構的建立,可以更好的鑒定“不可抗力”的諸種具體因素,具有更公正的法律效果。
另外,在不可抗力發生以后,行為人“及時采取合理措施”的“及時”和“合理措施”如何認定?目前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對此缺陷,在制度設計時,最好能有法律或法規、規章對此作出較明確的規定,但一定要鼓勵行為人的積極作為和利益平衡為宗旨,這樣才能在司法實踐層面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法律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司法人員也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的判斷標準。
其次,對“不可抗力”的界定,還應以現存的科學技術水平為依據。任何法律范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受到具體社會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可抗力”的法律價值和意義不能脫離現存的條件抽象地去談,而要以當下的技術水平為支撐。此外,“不可抗力”要以一般大眾的認識水平來判斷,而不能以專業技術人員的立場或行為人的立場來界定,專業技術領域的人員有很豐富的自然技術水準,以他們的眼光來界定“不可抗力”,對行為人太過于苛刻,不利于公正;而以行為人的立場來界定,他們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釋,也會失去公正。
最后,在進行制度設計時,必須進行價值分析。價值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主體自身需要和滿足,二是客體固有的某種屬性。價值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主客體之間一種價值評判關系,價值關系隨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價值的核心問題是主客體之間的實踐基礎上的關系,體現了主體與自然的關系,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主體和自身的關系。價值關系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作為價值屬性,既取決于客體又取決于主體的需要和主體的實踐活動,即主體的對象化和客體的人化。
近代世界以來,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科學和理性是現代性最主要的特征。科學合理性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這種價值體系下,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充斥著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人類運用技術征服自然,但是卻忽視了人類終極價值。人類的終極價值在于“有家”,在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告訴我們,在進行制度反思時,必須以環境倫理思想為指導,將環境價值與人的價值統一起來,將“不可抗力”的免責事由放在人與環境的價值關系中來考量。
“不可抗力”一直是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這與現代的環境哲學和環境倫理相違背。從理論和實踐層面來考慮,環境侵權領域不可抗力不宜作為免責事由。但是,結合我國的現行的法律制度,將不可抗力完全排除在免責事由的體系之外,也違背法律的正義。只有結合具體的歷史的實踐,對現行制度進行修正,嚴格規定“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適用的相關制度,才可能實現“修正的正義”。
總之,環境侵權由于特殊的構成要件、歸責原則,決定了其免責事由的特殊性。而不可抗力究竟能否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還值得進一步的探究。為了更好地保護受害者的利益,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必須進行相關的制度設計,明確“不可抗力”和免責事由,嚴格限制“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適用范圍。這樣才能發揮這一制度的法律價值,最大程度上保護受害人的利益。
[1] 周珂.環境與資源保護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 王利民.侵權行為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 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4] 郭明瑞.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陳太紅.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免責事由探析[J].礦業安全與環保,2002.
[6]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五)[M].臺北(自版),1987.
[7] 王利民.侵權行為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8] 李偉濤.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責任免責條件的探析[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3,23(6).
Force Majeure—the Excuse for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al Tort
JIANG Ping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07,China)
Due to the special principle of “no-fault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 tort, “force majeure” has always been an excuse for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high-technology, “Force Majeure” caused academic debate as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be used to plead for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ed issues of “force majeure” in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ystem.
environmental tort; force majeure;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D923
A
1672-0318(2016)04-0032-06
10.13899/j.cnki.szptxb.2016.04.006
2016-03-02
姜平(1979-),女,山東平度人,助理研究員,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