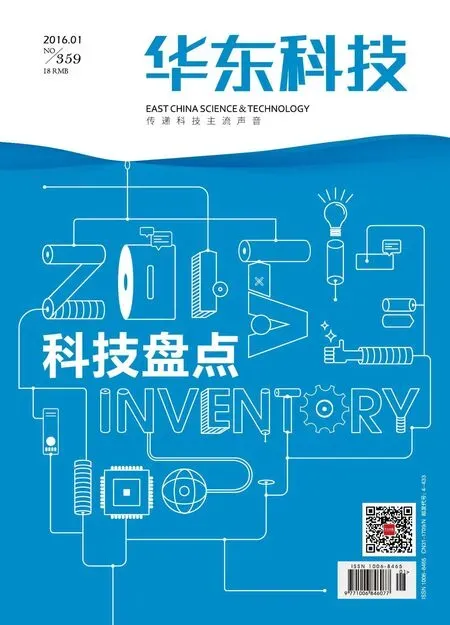尼葛洛龐帝一位理性的“預言”大師
文 林云志
?
尼葛洛龐帝一位理性的“預言”大師
文林云志

20年前,一位被媒體譽為“數字化預言家”的投資人、教授、研究者等,身兼多重身份叫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的人,出版了一本叫《數字化生存》的書籍,這本書種下了許多對于現今社會的預言。20年后,里面的那些預言都在現實里開花結果,為這本書的可信度作了見證。
尼葛洛龐帝出生在美國紐約,是希臘船東的兒子。當然,目前結果來看,他沒有延承家業,而是在1968年一口氣鉆到當時還很新鮮的數字媒體界去了,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畢竟那時候的互聯網和媒體這一概念屬于“冷手山芋”,尤其是與他選擇從政的哥哥相比,他相中計算機這一在那個年代被認作還是比較“娘氣”的行業,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對未來的自信和前瞻意識。
20年前的預言皆成現實
這個人對新鮮事物有著獨特的迷戀,人家不是說了:為什么美國有這么多創新?答案很簡單——那些新想法都來源于差異化,差異化存在得越多,兩股勁頭擰不到一塊,反而相互擦出靈感的火花。但如果你在一個特別同質化的國家,人與人之間沒有太多差異,那差不多等于拔掉創造的輸氧管。與他人人生方向的不同,對新事物的好奇而非恐懼,造成了他的特異性,以及他總是對未來產生的暢想。
不過據他本人的說法,他對未來所作的推測其實根本算不上預言,只是把他自己的工作成果呈現到大家面前而已。他的預言,更多針對其可行性與合理性方面,其背后旋著嵌入現實的邏輯結構。與微軟的“未來智能生活館”一樣,這位外界盛名的預言家,一直在他的腦海中搭建自己的“未來世界”。
比如,從1960年開始,他和團隊就開始著手研究40年后的觸摸式顯示屏技術。結果就像我們現在清晰地看到的,蘋果的出世開始顛覆世界的電子產業;又如在1989年,他預言,到2000年互聯網的用戶將超過10億人,這在網絡普及的年代聽上去不算新鮮,而1989年人們的預估值其實僅壓在4000 萬-8000萬。
尼葛洛龐帝對新新事物似乎總是保持自信,他在TED 30周年時曾提到過:“當新事物新科技出現時,人們常常低估它們的威力。”他的自信不是空穴來風,新事物總有它的價值,但怎樣挖掘它們好的一面,方式卻是大相徑庭,如何把一件事物最好的一面從中“掏出來”,是他預言背后深藏的基本指向,他說過:“預測未來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創造出來(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他的理論與其說是預言,不如說是對未來提供更多的 “可行性”。
這位外界盛名的預言家,一直在他的腦海中搭建自己的“未來世界”。
可行性有時候是比較矛盾的,尤其是當它還披著“一切未知”的面紗的時候,它的實現往往是在接受一遍遍失敗的洗禮之后才得以完成。好比馬云在創業初期找不到合作商,因為人們無法理解和接受一個網絡的支付系統可以替代傳統的face to face支付模式。一個新興行業總是充滿未知,波動,危險。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越是危險的東西,卻越是機會,這是對于一部分人來說的——敢于冒險的人對未知躍躍欲試,隨波逐流者卻忌諱于此,而當它成為可能,擁有了實體,到最后散發利益的香味,后者才會急匆匆趕上末班車,可這時候市場對他們已經換了冷臉,趨于飽和。
尼葛洛龐帝自然屬于前者,作為一個有著多重身份的人物(他樂于冒險的精神,自然使他敲開其他領域的大門),天使投資人便是他的另一重身份。他曾把眼光瞄到中國市場,在1996年中國對互聯網還腦海一片空白的階段,他便帶著“全世界都會被套進互聯網”的理念,將他的大筆資產,如火如荼地投入了當時在中國仍是十分生澀的互聯網行業。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市場沒有飽和,沒有很多人共同搶占一個東西,而是有很多可以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的人。”
當然,投資行業里,預言的魔法是很難維持的。要是在投資領域還能靠預言長盛不衰,那便不再是預言,而是實打實的超能力了。市場的瞬息萬變的節奏與預測有一定程度上的關系,但終究,它不會停留在預測的結果層,它是流動的,甚至以捕風捉影來形容亦不為過,好比你可以摸到大象的肚子,卻抓不到松鼠的尾巴。這位預言大師說過:“你每投資10美元,就會損失9美元,這是一個規律。我做10個投資,會有9個投資是賠錢的。我是一個高風險投資者,所以對失敗也就習以為常了。”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
那些預言,是他對這個世界存在的無限可能的期許
為何一個麻省理工大學的媒體教授,會搖身一變成為投資人,且在10比1勝率的環境下,越挫越勇?
這一點,需從他的童年說起。從小醉心于藝術和數學的尼葛洛龐帝,卻有閱讀困難癥,他不喜歡閱讀,3歲起他隨父母游走世界。毋庸置疑,他的童年比一般的孩子要好,家庭富裕使他能在不同國家學習和生活。也許人們會覺得,家境好,父母優異的腦基因才是決定他最終成才的根本。但他的閱讀困難和搬遷這兩者在時間點上完全重合的段落里,卻讓人想到了另外兩個人——我國自古留名下來的思想家孟子,以及同是科技界的大亨級人物,也是尼葛洛龐帝的好友斯蒂芬·喬布斯。
這兩人與尼葛洛龐帝有類似的經歷,孟母三遷的故事自不必說,喬布斯也曾因為自覺國中時期他與校園氛圍無法融合,而要求其養父母供他上貴族學校。這兩人童年的家庭背景與尼葛洛龐帝可謂相去甚遠,簡直如同被置于M型社會的兩端,卻都有過不滿于現存環境而最后“遷途”的過程。比起在其他地方尋找新的生活空氣這一點,“遷途”本身似乎更耐人尋味。
人是社會動物,而本質上來說,更是環境動物。對抗環境往往是困難的,即便最后成功,也會消耗掉自身的大半力氣。但聰明人會想辦法繞過它,或者說,不斷修正以找到最能適應自己的環境,而不是自己去適應環境。人們總覺得與環境磨合是好的,其實并非如此,不好的環境本身帶有損耗性,磨合只是最被動的過程。而處于被動,人便很難知道自己要什么,環境會帶動你,帶你到或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而你置身其中亦是被催眠到毫無方向。
可以說這三個人在年輕時代都有顛沛流離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卻提供了很多變通和多面性的選擇,以及不同環境下更為多元的文化輸出。可能,尼葛洛龐帝不論在事業選擇的分叉點,或在動蕩不穩的投資波瀾中,還能持續保持對陌生事物的熱情,很大程度上還是受到童年時期環境轉化的影響——這個世界不只是我們所處的生態圈,它擁有更廣的維度,所以可以去嘗試,而非磨合,把磨合的心態壓平,嘗試便可以越來越大膽,直至把不可能拉進可能。
由此亦可見,他的那些預言,是對這個世界存在的無限可能的期許,而非停留在“眼前的事物”和周遭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大環境。就像你可以想方設法讓環境去適應你一樣,現實世界也充滿著各種“可置換性”,只要你對新鮮事物存有好奇,以及,比這個被常理意識拖慢腳步的世界快一步的直覺。回到開頭,尼葛洛龐帝口中的差異,或許便是針對這個世界所處的模棱兩可的均衡,而那些均衡里微弱的分裂,想必才是預言以致達到創新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