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化成與國家建構
任劍濤
?
人文化成與國家建構
任劍濤
一般而言,現代國家建構都會遭遇到一個雙重難題:走出傳統國家,建構現代國家。之所以說這是一個雙重難題,是因為傳統的力量會極大左右現代國家的建構;同時,現代國家建構自身的種種難題也橫亙在建國者面前。所有國家在致力建構現代國家之前,都有其歷史文化積累的負載問題,這一積累究竟是建構現代國家的動力還是牽絆,確實是個需要分析的問題。這是人類建構政治體的文化處境所注定的事情。《易經》有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易經·賁卦》。仰觀天文,理解自然變化;俯察人文,知曉社會變遷。唯經文化審視,才能理解作為人文現象的國家建構。倘非如此,人們就只能浮淺觀察到國家作為強制政治力量的一面,無以深刻理解國家建構的文化驅動力量。
建構現代國家,必須為其聚集文化資源。源遠流長的文化積淀與嶄新的文化資源,是現代國家必須同時聚集的兩種資源。這兩種資源既可能是相互支撐的,也可能是相互沖突的。相互支撐的文化資源,需要建國者自覺利用歷史文化饋贈,并與現代建國的文化需求巧妙對接;相互沖突的文化資源,需要建國者化解兩者之間的對立,以求為現代建國清理文化地盤,提供文化動力。因此,現代國家建構中需要建國者致力解決的文化問題至少有兩個:一是歷史積累的文化怎么處置,二是為現代國家建構聚集的相宜文化資源如何保障。就前者言,深厚的歷史文化積累對現代建國必定有利,需要辨析;相應地,磽薄的歷史文化積累對現代建國必定造成不利,有必要分析。就后者論,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是取一種嚴格的排斥性立場,還是取一種開放立場,并以對建國發生的效用來決定去取,需要慎重對待。在現代建國的復雜政治事務面前,聚集雄厚的文化資源,使之成為現代建國的動力,是相關論辨凸顯的宗旨。圍繞這一宗旨,需要具體分析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文化與政治是國家建構中的兩種動力,但兩種動力不至相互消解,而能相互支撐,是為問題的關鍵。在現代國家建構中,凸顯了三種文化類型。這三種文化類型既是現代建國呈現出來的類型,也是與現代建國互動的文化狀態。文化與政治兩種因素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交互影響,是具有主次之分的: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因素是決定性的。文化決定論對現代建國有害無益。借助這些分析,確立起如何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的合理認知。
一、文化與政治:國家建構中的兩種動力
在現代建國的實際進程中,一切社會要素都綜合地作用于建國事務,沒有哪一種社會要素可以單獨決定建國進程。但在分析的視野中,將各種社會要素對現代建國發揮的影響離析出來,或者將某些要素的關聯作用作為分析論題,則是幫助人們理解現代建國的研究需要。斷言文化與政治是現代建國的兩種關聯動力,就是在影響現代建國諸要素中,選取兩者對建國發生的交錯影響,以期幫助人們理解兩種社會要素與現代建國的緊密關聯。②就這一論題的近期推動者而言,塞繆爾·亨廷頓發揮了重要的推進作用。不過,它不是在一個國家建構其現代國家形態的視角立論的,而是在國際關系的角度分析問題的。他指出當代的國際沖突,不再是政治與經濟原因所致,而是文明-文化導致。這引起國際政治學界對文明-文化因素的集中關注。參見[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增訂本)》,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335~336頁。版本下同。這一分析,需要從三個方面具體解析:首先需要確認“現代國家”(the modern state)的含義,其次需要厘清現代建國的文化所寄,再次需要對現代建國的政治-文化動力進行關聯分析,這樣才足以說明現代建國中政治與文化兩種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并對建國狀況發揮重大影響。
現代國家,自然是與傳統國家比較而言的概念。由于兩個概念的復雜性,很難給出一個簡略定義,大致只能在比較描述中呈現兩個概念的差異。傳統國家是指一五○○年以前存在并運行的國家形態。這類國家形態,呈現為城邦國家(city state)、帝國(empire)和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等具體形式。這些國家形態大致都依托于農牧文明,依靠軸心期文化理念為其提供正當性支持。在國家權力形態上的分化程度不高,主要仰賴政治權力和宗教信仰提供統治支持。從政體的角度講,傳統國家以專制政治為主,間中出現一些民主共和政體。不過即便是民主共和政體,也不是現代國家那種高度發達的立憲民主政體形式。“從古代國家產生和發展道路來說,無論是東方文明古國還是西方的希臘羅馬,起自君主制和終于專制主義可以說是共同的歷史軌跡,所不同的是,極少數古代東方國家的原生國家形式是貴族制或共和制,而希臘羅馬則在其間插有貴族制等特別是民主與共和制的發展階段。民主與共和制長期存在,且得到高度發展,確是構成了希臘羅馬世界一些國家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特殊的現象。”①施治生等編《古代民主與共和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5頁。共和制,在傳統國家的政體形式中綿延時間最長,影響最為深遠。共和制是一種混合政體,包含了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的不同成分,因此并不是一種明晰的政體形式,其蘊含的三類政體形式各自發展的充分程度因此受到限制。進入中世紀階段,以基督教支撐的世界社會與各個王國實行的封建制度,讓這一時段的國家形態頗為獨特:一是教權與王權之間的爭斗持續不斷,促成了神權與王權分而治之的憲政雛形。二是王權與封建之間的磨合,齟齬不斷,從世俗領域推進了分權而治的立憲政體發展。但古代的憲政僅僅著眼于限權,而從未呈現保護個人自由的面相,更未獲得強大經濟動力的驅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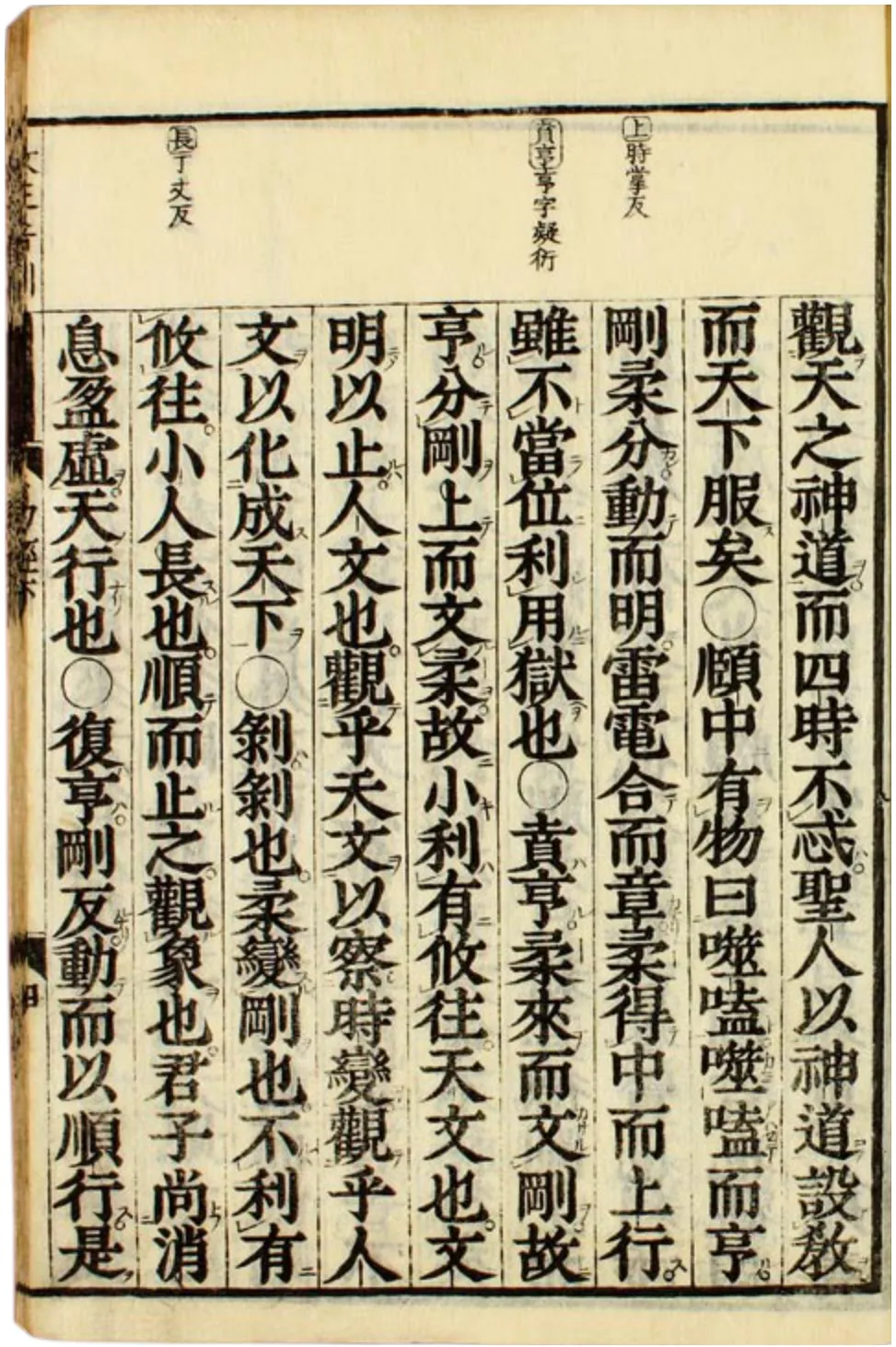
易經
就世界范圍來看,現代國家是一五○○年以后逐漸成型的國家形態。其前史非常漫長,可以直接追溯到上古政治體草創時期。這正是國家史研究中人們習于從古希臘羅馬統治史中分辨現代國家源起的理由之所在。但其正史并不悠久:以其形式結構而言,民族國家的蓬勃興起是在十六世紀;以其規范結構而言,立憲民主國家的世界進程起始點在十八世紀。民族國家是伴隨著世界社會的解體,而在歐洲率先興起的現代國家形式。但這一現代國家形式所采用的政體結構大為不同,有民主政體,也有獨裁政體;有專制政體,也有共和政體。就規范的現代國家結構而言,民族國家的形式結構為其表,立憲民主政體的實質結構為其里。這樣的國家形態以個人自由為核心價值取向,以平等精神安排國家基本制度,以國家與社會的分流運行為其總體框架,以法律主治作為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典型的現代國家結構,絕對不可能在古代國家中尋其蹤跡。
現代國家的建構,依賴于多重動力塑造而成。暴力與征服是現代國家興起的直接動力。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現代國家建構的標志性事件。但暴力征服的目的,不在于政治控制,而在于經濟掠奪。國家力量的對內保護與對外防御兩種基本功能,可以換算為對內的政治統治與對外的暴力征服。這是一個國家功能的良性發揮與惡性膨脹一物之兩面的顯現:一旦國家權力不能落到規范的憲政法治平臺上,國家權力就會成為對內施暴的工具;假如國家權力受到國內立憲民主的規范,權力不能對內施暴,但因為國內法不能自然延伸到國際社會以規范國家主權,因此很可能讓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大肆掠奪。這是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先行國家基本都有一段殘酷的殖民史的原因。以征服的經濟力量掀開的現代建國進程,與分權引導的國家權力制衡機制掀動的政治建國進程,構成現代建國總體進程的兩個面相。比較而言,在這一總體進程中,政治史淵源比經濟史淵源更為深遠。卡爾·馬克思對現代國家興起的解釋,無見于前,有見于后。但在政治經濟緊密互動上的解釋,卓爾不凡,超過諸家。在現代建國的世界史進程中,一二一五年《大憲章》簽署以來的政治史,是一部現代國家建構演進的復雜政治史,因為我們理解的是國家,其間處理的問題是限制權力和分享權力的問題。這是硬碰硬的政治建國問題。經歷數百年的漫長歷程,分權制衡的國家權力體制,以及以權利限制權力、以社會限制權力的現代國家國內政治框架,才呈現在世人面前。①參見[美]托馬斯·埃特曼《利維坦的誕生:中世紀即現代早期歐洲的國家與政權建設》,郭臺輝譯,導論,尤其是導論的第三部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32頁。同時,十六世紀全面掀開的全球貿易史大幕,讓現代先發國家以全球財富掠奪的行徑,成為迅速集聚財富的富裕國家,進而為后發強國示范,推動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讓一國經濟體系不再成為自足的經濟類型,國家的開放式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刺激國內經濟發展的市場經濟模式,由市場逐漸掀開的工業革命序幕,造成現代世界經濟疾速發展的局面。這對改變國家面目,推進現代國家成長,提供了強大的物化動力。②一個國家致力于營造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環境,對經濟是否發展、發展快慢,具有決定性影響。但在國際經濟環境浮現之際的國家舉措,則對一國走向富裕或停滯貧窮具有重要影響。參見[美]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門洪華等譯,第3章、第11章,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39~56、199~221頁。

托克維爾
但現代國家的興起,并不只是政治與經濟等硬力量(hard power)推動的結果。文化這樣的軟力量(soft power)對現代建國也會發揮重要的作用。③何謂“文化”,是一個很難給出簡明答案的問題。作為一個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概念,它大致是指人類活動的創造物。寬泛意義上的文化,則是指與勞動閑暇相關的習慣、習俗和態度,其高級形態,是受教育者的實踐與理解結果;其普通形態則在社會成員身份上體現。Roger Scruton, The Palgrav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Thought, 3rd edi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2007, p.159.因此,作為文化界面的現代國家的興起,構成作為政治界面與經濟界面的現代國家建構之另一面。作為文化界面的現代建國,具有三個重要內涵:一是價值觀念、尤其是文化基本價值觀念,在現代建國進程中會發生廣泛、深刻而持續的影響。比如說限制權力的價值信念,就與限制權力的現代建國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構成限權政治嘗試的兩種動力。堅信限制權力的正當性,并且甘冒風險投入限制權力的政治行動,確實有利于實現限制國家權力的現代建國目標。與此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凡是那些缺少限制權力的傳統信念的國度,寧愿依附權力而獲得可憐好處的民眾,他們確實很難相信自己的限權努力會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后果。因此,他們對限權付出的努力就顯得十分不夠。文化價值信念,是文化因素影響現代建國最深層的方面。二是文化態度,這樣的態度直接影響政治體成員的政治參與、參與方式與參與后果。當一個國家的成員習慣受制于國家,并且拒斥政治生活,與國家權力處在一種長期的疏離狀態,并且不愿意以自己對該政治體的參與來改變某些令自己不滿的現實,認定即便是自己參與某些政治行動,也不會收到任何效果,那么,這樣的政治文化態度,勢必造成一種專斷的政治權力機制。反之,如果公民懷抱一種積極參與的政治態度,并認為唯有在自己積極參與的情況下才會改變令自己不滿的政治現實,那么極大可能會生成一種民主的政治權力機制。三是心靈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也就是體現在一個國家國民日常生活中的習性,其體現的方式,不是經過教育的塑造、抑或是耳提面命,而是不經意之中表現出來的國民個性。這是一個托克維爾命題。最早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得到闡述,美國社會學家們對之進行了驗證性的研究,確證托克維爾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對美國人心靈習性觀察的近期演變。他們一致認為,“家庭生活、宗教傳統和對地方政治的參與造就了美國人,是我們能夠保持同更大范圍的政治共同體的聯系,并進而維護自由制度的生存。”①[美]羅伯特·N·貝拉等《心靈的習性:美國人生活中的個人主義和公共責任》,翟宏彪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2頁。正是一種堅信私人積極介入公共生活就可以維護自由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構成美國現代建國的深厚文化土壤。
文化因素如何影響甚至制約現代建國,需要從不同角度分析。首先,現代國家建構一定會受到歷史傳統文化的影響。這是因為,歷史文化傳統所積淀的、最深沉的精神文化傳統,會對人們的行為發生持久的影響。一方面,一個國家的精神文化傳統,通過文化傳遞,由長輩塑造晚輩的基本價值信念,盡管偶有改變,但一個國家的精神文化絕對不是當世者不假外力的當下創造,一定來自于代際傳遞。當然,代際傳遞的精神文化傳統、尤其是基本價值觀念,既可能是動力,也可能是負擔;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但由文化傳統傳遞下來的價值理念,毫無疑問地會影響甚至左右該群體成員的價值偏好與行為習性。另一方面,經由代際傳遞的價值觀內化為人群的生活習性,呈現為日常生活中某種觀念的排斥性和接納性,使人們在不經意之中展現出某種行為定勢。這是一種行為的文化信號,指示人們從中離析出理解相應行為背后的文化意涵。再一方面,由于人之為人的重要標志在觀念先行,先行的觀念當然主要得自傳統。盡管理性判斷對人們的政治決斷發揮著最重要的指引作用,但是,得自傳統的先行觀念,會對人們的政治判斷發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其成為與理性交互作用的政治行為動力。
其次,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發揮重大作用的歷史文化傳統,直接呈現為傳統制度文化對現代建國制度決斷的影響。傳統的制度觀念、制度安排、制度運行、制度績效,或顯在或潛在地左右著政治成員的制度思維。制度的歷史積淀就此具有發揮現實效能的通道。這一方面是制度綿延的時間維度所注定的,人們一定沿偱從過去、經現在到未來的時間線索展開行動,不可能存在橫空出世的現在。古希臘人對民主制的實踐,盡管并不直接成為現代民主制的實踐方案,但很顯然,在西方國家建國的基本制度選項中,人們對民主的歷史熟悉感,使之成為現代國家基本制度建構的重要參照系。而對民主的政治實踐完全隔膜的民族,在建構現代國家的時候,是很難從歷史文化中汲取民主滋養,走上民主政治的軌道。盡管這并不構成西方以外的國家拒斥民主的理由,但確實構成西方以外的國家建構民主政體難度的成因。而對那些長期處在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制約下的民族來講,由于他們完全不熟悉現代國家的立憲民主規范制度,相反習于接受專制統治者的高壓統治,因此,接受其來有自的、源自集群生活傳統的民族國家這一現代國家的形式結構,是相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建構其所陌生的現代規范國家形態,也就是立憲民主政體,相對就困難很多。而且,在民族國家形式結構轉向立憲民主規范狀態的過程中,總會存在因為傳統制度思維的干擾不斷回流的可能。在現代建國進程中,也存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②諾思指出,“路徑依賴—從過去衍生而來的制度和信念影響目前選擇的路徑—在這種靈活性中起著關鍵作用。那些過去的經驗使人們以懷疑和憎惡的態度來看待創新性變化的社會,與那些文化遺產為這種變化提供了一個適宜環境的社會形成鮮明對照。構成這種不同文化遺產的潛在原因在于每一種情形下參與者共享的心智模式。”[美]道格拉斯·C·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鐘正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0頁。諾斯明確指出,路徑依賴與其說是一種慣性,還不如說是過去的歷史經驗施加給現在選擇集的約束。見同書第49頁。的問題。盡管路徑依賴不能被理解為路徑宿命。

《利維坦》
再次,在現代建國進程中,一個致力建國的民族之源遠流長的生活方式,對其建國嘗試發揮著最不經意、但卻最深沉的影響。對一個農耕民族來講,如果長期生活于一家一戶的散漫狀態中,中間又未曾經歷過任何革命性的變化,那它是很難一下躍進到講究規則的公共生活世界的。換言之,這樣的民族在建構立憲民主國家的時候遭遇到的困難,肯定會比長期生活在商業民族環境中,習于政治博弈,慣于限權嘗試的民族要大。原因很簡單,在日常生活中對政治博弈完全生疏的民族,基本上也就是與政治、尤其是國家高層權力政治處在一種疏離的狀態。即便將其安頓在一個需要即刻開始權力與權利博弈的政治處境中,他們也會完全不知所措。因此他們完全缺乏相關生活經驗,甚至完全缺乏相關行動的關注。只有那些千百年來浸潤在從未間斷的政治博弈環境中的民族,才具備基本的政治博弈技能,也才具備經由討價還價形成政治妥協的技巧。當然,這并不是說政治變遷就無以促成新的集群生活方式,只不過這樣會使人們為了適應新的集群生活方式償付更多代價而已。
既然在現代建國進程中,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在建國進程中激發文化資源的效能,就成為一個需要進一步辨析的問題。無疑,取決于現代建國的兩個構成面,即建構民族國家與建構立憲民主國家,首先需要聚集有助于形成統一民族意識的文化資源,以便為現代建國凸顯形式結構提供條件。現代“民族國家”概念中的“民族”,不是指的一般意義上的民族(nation)、族群(ethnity)或種族(race)這類由歷史因素自然造就的集群結構,而是構成國家建構的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或國族(state nation)。這樣的民族建構,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現代國家建構而言,不是什么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但對于“多個民族、一個國家”(multi-nations, one state)的現代國家建構來講,就涉及到分析意義上的、先行國族建構與后起國家建構的問題。這就無可避免地會遭遇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難題,進而遭遇多個民族的政治統一基礎上建構國家權力體系的難題。于是,就前者言,需要處理原生的民族、族群或種族如何統一為一個有助于建構統一民族的文化難題。就后者論,需要處理有助于建構統一民族基礎上的統一國家的政治歸屬問題。

《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
將多個民族建構成統一民族、也就是國族,就必然涉及民族共同體的想象問題。其間,極大可能出現國族建構中悲劇性事件—種族清洗。①近期,美國社會理論家對之進行了最為系統深入的考察,值得重視。參見[美]邁克爾·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嚴春松譯,第1章“論點”,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1~42頁民族之作為想象的共同體,乃是一個多民族形成統一的國族時必然遭遇的問題。這個問題還可以轉換為另一個提法,一個后發的民族國家興起之時,要建構一個與先發民族國家一樣的集群主體結構,就不能不仿照先發民族國家那樣建構一個統一民族。于是,民族之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的問題就凸顯出來。“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者,有人會傾向于使用能夠表現其多重意義的另一個字眼,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適當地理解這些現象,我們必須審慎地思考在歷史上它們是怎樣出現的,它們的意義這樣在漫長的時間中產生變化,以及為何今天它們能夠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我將會嘗試論證,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被創造出來,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復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它們就變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到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頁。版本下同。本來,論者將民族歸之于文化產物是正確無誤的,但當他進一步給民族下定義的時候,卻給出的不是一個文化定義,而是一個直接的政治定義: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第6頁。這樣的定義,是為了給論者自己斷言民族主義乃是歐洲殖民者激發殖民地國家民族想象的結論,提供便利的說辭。但確實已經偏離了民族的文化性,而凸顯了它的政治性。不過,其論斷有助于人們在文化創造物的基點力理解何謂民族。
在此基礎上,國族建構的民族根基與政治驅動力交互作用,推動民族國家的建構。于是,文化的歷史要素和建國的政治要素,強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國家的興起與興盛。在此,論者所說的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便不再成立,民族轉而成為一個基于歷史共同體的文化想象與政治建構合一的產物。民族轉換為國族,政治的驅動力主要呈現在國家統一建制上面,而文化的驅動力則主要通過價值觀念、歷史經驗、語言文化、傳統習俗的力量呈現出來。這恰好構成安德森民族定義的另一面相,即民族是“共同體的想象”。不是基于共同的經歷,共有的語言、文化與習俗等等相同的社會生活體驗,是無法憑空展開所謂民族的想象的: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念,不足以將不同族群整合為國族;缺乏共同的歷史經驗,不足以使不同族群交流互融;沒有相同的語言文化,不足以促使不同族群形成文化認同;缺乏相近的傳統習俗,不足以將不同族群融合進一個生活空間。在民族的自然同化進程中,這些文化因素的作用推動小族群成為大族群。但在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政治的動力作用日益明顯。但總的說來,它們還保持了對國家建構發揮文化影響力的文化特質。③參見牙含章:“論民族”,載氏著:《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85~97頁。
在民族共同體建構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為民族國家聚集文化資源,還需要將文化共同體提升為政治共同體,以期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化動力與政治動力水乳交融地發揮作用。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作為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的整合建構,民族構成國家這一政治機制的行動主體,國家構成民族這一文化共同體的政治建制。今天人們習慣于將民族國家的國家權力建制思維政治化的處置,其實這對國家的規范屬性發生了局部的遮蔽作用。在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合二為一的規范現代國家結構中,早期的國家命名,顯然比當下流行的“民族國家”命名要更為準確。Commonwealth是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用來命名國家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字面含義就是“共同財富”。它標示的是現代國家依約建立,其宗旨就在于保護每一個成員的權利,因此國家成為對每一個成員而言的共同財富,而不是某些擁有特權的成員用以謀求私利的工具。而且關鍵的是,形成這樣的國家機制,不是依靠什么人的意志或恩惠,而是依靠制度來達成的。④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Volume 1): A Comprehensive Selection of Crucial Idea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Enlightenment, ed. Michael Curtis, Harperperennial modernclassics, 2008, p.341. 以及[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等譯,第17、18章,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28~142頁。因此,民族國家必須保有一種讓每一個成員依制度建制認同的基本功能,才足以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這就使民族國家的文化根基,呈現出一種政治-文化合宜互動的特征。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民族成為一種本質上是“政治的”共同體的特質,民族國家也就成為本質上是文化與政治交相促成的國家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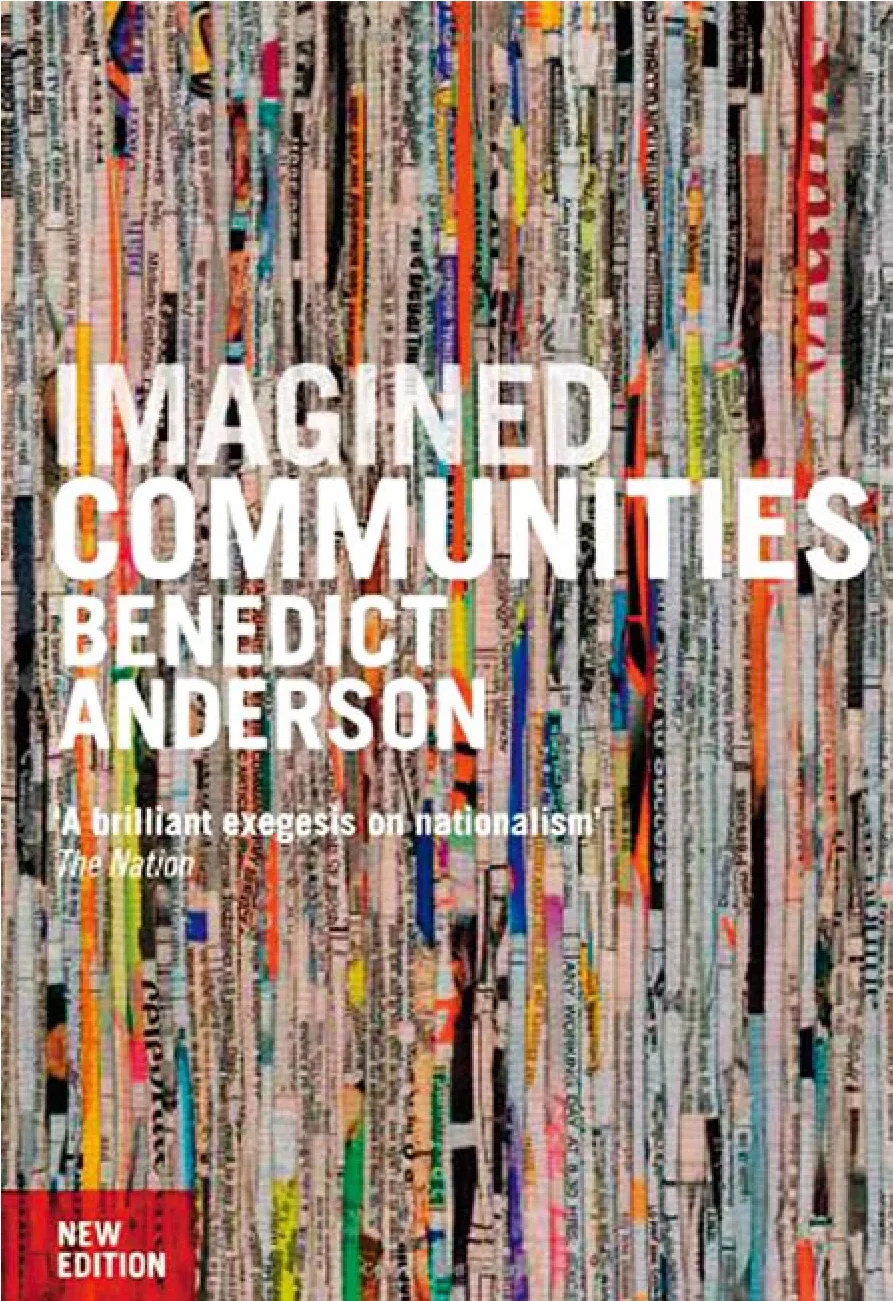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二、現代建國的三種文化位勢
在現代建國進程中,既成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有助于建構現代國家的文化資源,是既相互聯系又具有重要區別的兩個文化構成面。因為兩者在發生關聯的時候,既有相互順暢貫通的方面,也有彼此明顯緊張的方面。兩者之間能夠順暢貫通的方面,是一種可以歸結為雙贏狀態的方面,那就是既成的歷史文化傳統有利于現代建國的推進,而現代建國有利于承接和發揚傳統文化。但彼此之間也可能處于一種明顯緊張的狀態:既成的歷史文化傳統、尤其是自陳的歷史文化傳統當下承載者,發揮著阻礙現代國家建構的作用,因此成為現代建國的文化羈絆,并突兀呈現出新舊文化沖突的僵局—新文化非祛除舊文化而不能構成現代建國的文化動力,結果歷史文化傳統成為博物館的文化遺存。與此同時,在現代建國的政治進程中,因為種種不幸的緣故,歷史文化傳統成為現代國家的對立面,因此新生國家必須清理文化地盤,以期形成與現代建國相吻合的文化機制。在這種相互沖突的狀態中,既成的歷史文化傳統缺乏現代生機,而新生的現代國家相應缺少文化背景條件的支持。這是一種雙輸僵局。尋求現代建國與激活傳統的對接,是實現雙贏的必須;避免現代建國與摧毀傳統的對峙,是保證雙贏的支點。但傳統文化與現代建國究竟處于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狀態,并不受當局中人主觀意愿的控制。原因很簡單,文化演進的某種趨勢與現代建國的某種定勢,會成為注定兩者關系最強有力的力量。趨勢與定勢的用詞,并不代表一種宿命的看法。它們僅僅指示了某種非主觀意愿的客觀處境:文化的千百年漸變過程,豈是人們的當下愿望所能左右?現代建國的復雜博弈,安能受某種善良愿望的線性引導?處于某種承接傳統與政治建國的狀態中的人們,必須首先清楚既成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現代建國的順逆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嘗試以積極主動的舉措,促使文化與政治有效互動,讓傳統文化對現代建國發揮良性的軟力量動能,讓現代建國激活傳統文化在當下的生機與活力。這是理解現代建國與傳統文化關系問題的兩個指向。
在現代建國進程中,文化的自身變遷邏輯,構成人們理解建國舉措與文化傳統兩者間關系的重要方面。既成的歷史文化發展,當然會形成自身的演進邏輯。它因此才能構成影響自身所在的國家的政治變遷。如果文化僅僅是政治的副產品,那么政治局勢一有改變,文化面貌也就驟變。文化之成傳統,就在于它不是隨政治局面的瞬息萬變而流動不居,因此才成為傳承有致之文化統緒。傳統文化具有不同于政治變遷急遽性的相對穩定性,這正是傳統文化足以影響現代建國的理由之所在。只有在勾畫相對穩定的傳統與政治互動中凸顯的某種機制,才足以認識清楚某種具有自洽性維續能力的文化傳統,其所呈現出來的流變情形,以及這中間所蘊含的某種調適現代建國與激活傳統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勾畫在現代建國中傳統文化與政治嘗試兩種力量對之發揮的不同作用,以及可以尋找到一種什么樣的整合機制,促使兩者共同構成現代建國的強大動力。
從前一方面來看,文化與政治的既成關系結構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西方國家從政教合一到政教分離的政治-文化類型。這樣的關系,本應放在政治與宗教的關系角度來審視。但為何在政治-文化的視角來觀察呢?原因在于宗教文化在整個古代社會中乃是統納文化諸要素于其中的文化形式。尤其是在早期宗教階段、中世紀宗教高度發展的階段,鮮明呈現出宗教對文化的吸納性特點。宗教之所以能夠顯現一個文化體系的特質,是因為它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與日常生活模式有效整合為一個文化體系。理解西方文化的演變,必須拿住宗教這把鑰匙,才能開啟進入西方文化的大門。
在西方的長程歷史中,西方的政治-文化關系,呈現為兩個長過程:一是古代歷史階段的政教合一演化出來的政教分離,二是中古階段一直持續到現代階段的政教合一演變而出的政教分離。就前者看,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文化,早期就是政教合一的文化形態。家庭宗教是古希臘早期政治權力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共同供給者。家庭圣火,是所有帶有社會性的組織得以綿延的象征性標志。“將古代家庭的各個成員聯絡起來的,是一種比出生、情感、體力更大的力量,那就是對家火及祖先敬禮的宗教。此宗教將家庭中的生者與死者結合為一個整體。古代家庭不是一個自然的團體,而是一個宗教的團體。我們因此將會看到,女子由于婚禮才有資格參與家庭的祭祀,并成為家中一員。相反,繼嗣者雖無血統的關系,卻因它加入了家庭的宗教,反成了家庭的真正成員。法定的繼承人若不肯參加家祭,也要被剝奪繼承權。還有,家庭關系及遺產的繼承權,并不是按照出生,而是按參與祭祀的權利來規定的。可以肯定地說,宗教雖沒有創立家庭,卻是家庭的組織與維持的原則。”①[法]庫朗熱《古代城邦—古希臘羅馬祭祀,權利與政制研究》,譚立鑄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2頁。版本下同。古代史學者大都指出了這一特殊現象。“每個希臘和意大利城邦都有它的保護神和一個高度組織起來的國家崇拜機構。外在形式上,每個公共或私人會所至少是一個宗教社區,并不是少數人將崇拜神作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宗教儀式:希臘人的住宅通常包含赫斯提亞(家宅的保護神)的祭壇,羅馬人的住宅通常有拉爾(家族守護神)和佩那特斯(家神)的神龕。每種崇拜都要經歷興衰,一種宗教的替代品是另一種宗教。”[英]M·J·卡里等《希臘羅馬世界的生活與思想》,郭子林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61頁。可見,在古希臘羅馬的社會組織方式上,即使是政治,也被宗教化了。宗教文化成為總體文化,將一切社會要素籠罩其中,構成一種原初意義上的政教合一結構。但隨著希臘晚期發生的幾場革命,政治與宗教內在勾連起來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革命將緊密連接在一起的政治與宗教切割開來,促成了新生的社會政治機制。之所以會出現顛覆政教合一機制的新機制,是因為人類思想的自然演進,舊有的思想自然而然在發生變化,負載這些觀念的社會結構也處在演進之中。同時,也是因為社會的不同階層或集團在利益上的紛爭,其各不相同的利益取向,逐漸瓦解傳承久遠的城邦制度。第一場革命便將政權與教權切割開來。第二場革命使家庭組織發生重大變化,氏族結構解體。相應地,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體制不再能夠維持。第三場革命讓城邦不再成為貴族活動的空間,平民大批進入城邦。法制改革、公共利益與選舉勃興。第四場革命呈現為民主制度的蓬勃成長,窮人有所依,富人有所懼,新的政治機制浮現出來。②庫朗熱《古代城邦—古希臘羅馬祭祀,權利與政制研究》,第四卷“革命”,第228頁及以下。這樣的政治機制,是西方世界第一次展現出來的世俗機制,它跟宗教的關系之疏遠,完全與家庭宗教主導政治生活的時代全然不同。

《古代城邦—古希臘羅馬祭祀,權利與政制研究》
隨之在羅馬政治演變的進程中,晚期羅馬權力腐敗與人民腐敗交錯呈現,權力方面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惜一切代價為民眾提供耽于淫樂的縱欲方式,結果讓人的神圣價值無所依托,人成為酒池肉林中的低級動物。結果,基督教的興起,讓世俗政權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高度緊張。在數百年的持續爭執之中,羅馬帝國終于承認基督教的國家地位。③參見[美]布賴恩·蒂爾尼等《西歐中世紀史(第六版)》,袁傳偉譯,第三章第7節“基督教與羅馬國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1~45頁。從此,西方世界再次進入政教合一的千年定局。不管中世紀政教合一是合一于教、抑或是合一于政,政教雙方活動的正當性,都由上帝所賦予。即使這樣的狀態持續的時間不算太長,歷史學家指認的歐洲基督教社會歷史只有三四個世紀,但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紀典型社會結構中,基督宗教是所有政治、一切社會生活形式的正當性來源與合法性判準。在“雙劍論”最終落定在“上帝的事情歸上帝,凱撒的事情歸凱撒”的節點上之后,教皇選舉的失敗,教會內部存在的貪腐,以及世界社會遭遇的民族認同挑戰,新的社會經濟因素的興起,政教的分離已經是大勢所趨。現代社會-國家因之呱呱墜地。而在第二次政教分離的過程中,社會諸要素的分化發展,已經將社會塑造成諸要素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宗教等互動的復雜體系,國家建構不再以某種單一社會要素支持。于是,社會文化、而非政治文化或其他文化形式,與現代建國的關系,成為人們觀察人文化成與國家建構關系的確定視角。
在世界史范圍看,除開西方世界那種政教合一與政教分離的文化與建國的聯結方式,還有兩種文化與政治的關聯結構:一是政治與教化合一的建國模式。盡管這樣建構起來的國家類型還僅只于古典國家形態,未能浮現出相應的現代國家結構。但這已經足以用來表明與西方世界形成的文化與政治關系結構不同的比較類型了。這種古典建國模式的典型形式,就是中國的儒教式國家。這里的儒教,不是世界宗教那種由神圣信仰、宗教制度與生活儀式結構起來的嚴密宗教,而是由社會教化支撐起來的公眾信念體系。儒教將國家建立在君臣、父子、夫妻、弟兄與朋友的倫理基礎上。家庭的基本倫理,決定了國家的建構原則。換言之,傳承久遠的倫理文化成為國家建構所依賴的正當性資源,國家的長治久安也依托于倫理文化的井然有序。在邁向現代建國的初始階段,由于倫理文化與現代建國的對峙處境,因此,有論者發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①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載林文光選編《陳獨秀文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5頁。由此凸顯一種傳統倫理文化與現代建國的高度緊張狀態,以至于現代建國總是缺乏強勁的文化動力,而傳統文化的現代活力也完全無法展現出來。
二是在現代挑戰日顯嚴峻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固有的宗教文化傳統,拒斥建構現代國家。一些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可謂典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在文化-政治上曾經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在希波戰爭終局之前,中東、北非地區發達的農牧文明,對發源階段的西方世界形成強大的壓力。中古階段,這一地區的伊斯蘭文明與西方基督教世界延續了幾近千年的沖突。進入現代階段,尤其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崩潰之后,這一地區與西方國家爭勝的勢頭,大為衰變。但這一地區及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尤其是奉行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國家,堅持以教會法治國,也就是堅持依伊斯蘭的宗教文化傳統作為國家治理的根據。因此極其敵視千年宿敵西方國家,甚至宣稱要與西方國家展開圣戰。兩個世界的沖突,構成伊斯蘭社會政治運轉的一個主調。②參見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本)》,第九章第二節“伊斯蘭與西方”,第186~194頁。這一沖突的未來尚未可知。但很明顯的是,伊斯蘭文明-文化與基督教文明-文化之間的劇烈沖突,導致伊斯蘭世界自身的現代國家建構遲滯,以至于成為今天全球范圍內發展政治顯著滯后的國家或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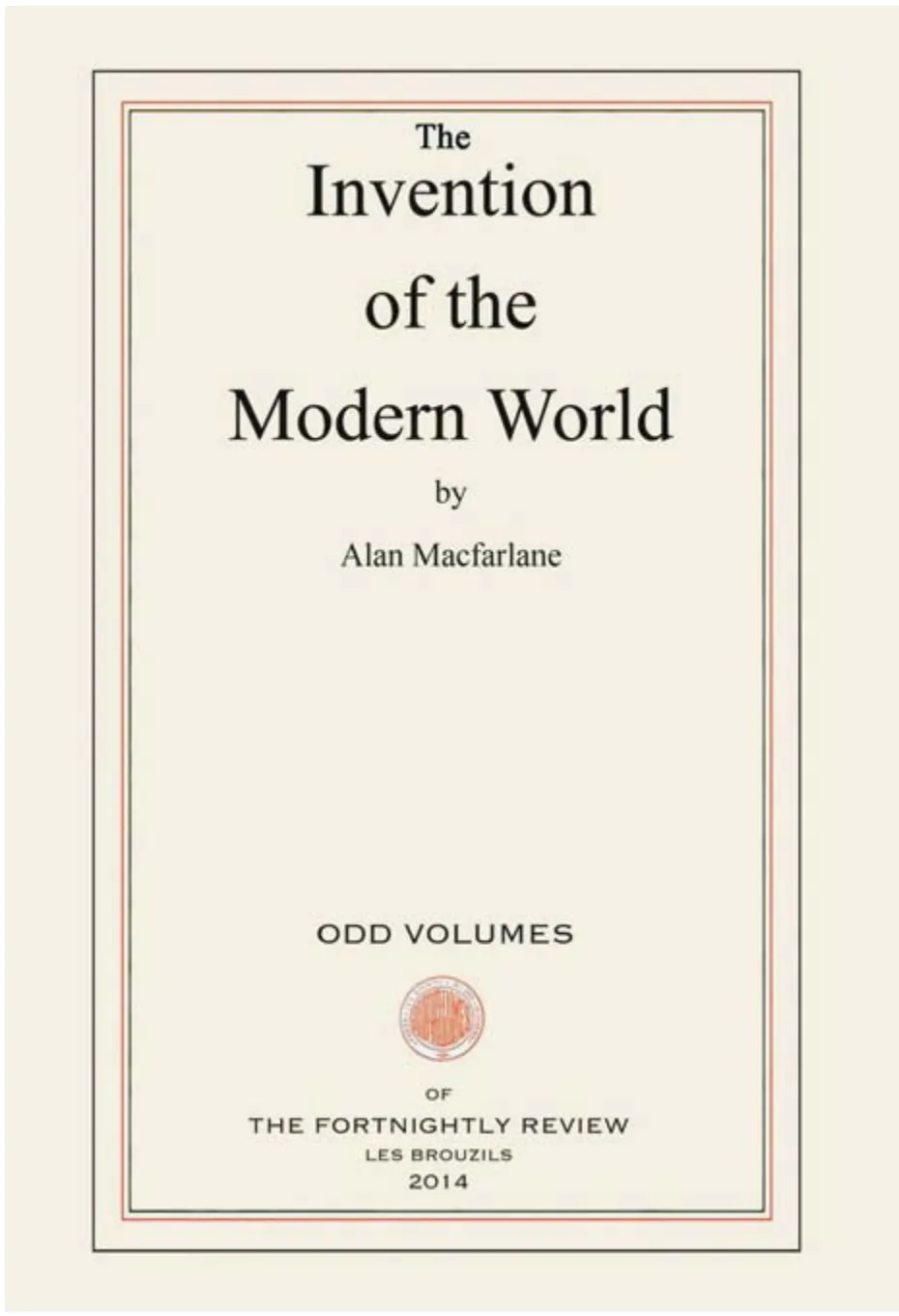
《現代世界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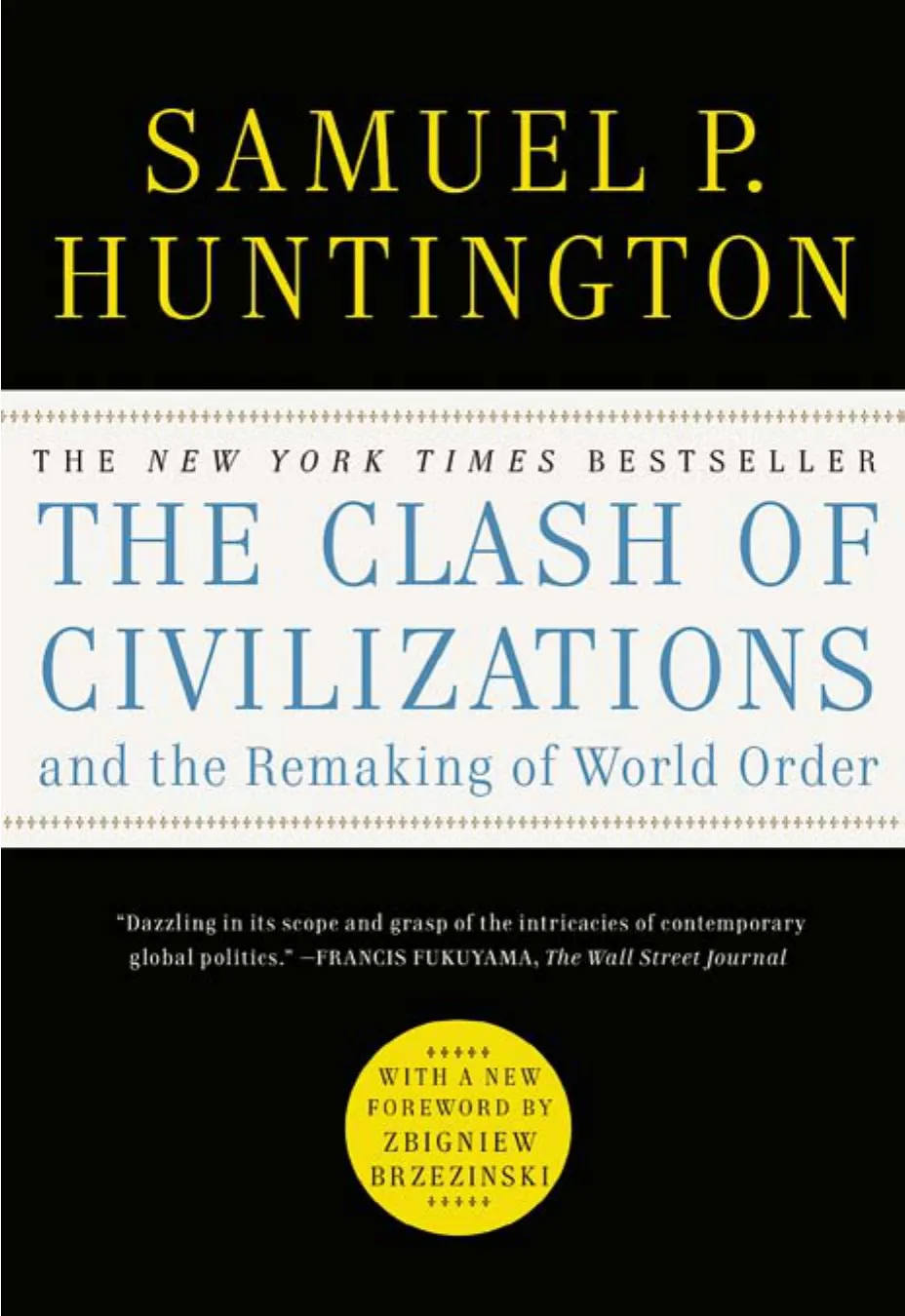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后兩種政治-文化的關聯結構,是作為西方世界處置文化-政治建國關系的參照系得到勾畫的。如果將論題集中在西方國家內部來看,如何在文化的流變中處置傳統文化與現代建國的關系,也自有其張力。對表現這種張力的不同狀態進行分析,也許對人們理解現代建國進程中文化與政治的關系更具啟發意義。根據西方國家邁進現代國家的文化嬗變狀態,可以將之區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英國模式。英國在漸進的文化演變過程中,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從而將文化傳統與政治建國理順為相互促進的關系,因此將傳統文化重塑為現代文化,將傳統國家塑造為現代國家。二是法國模式。法國舊制度的力量在革命風起云涌之際,成為現代建國的障礙,因此,掀動文化革命的啟蒙主義領袖與推動政治革命的領袖集團,發起了一場旨在蕩滌舊文化、構造新文化,以便打造與現代建國完全一致的嶄新的文化體系。這是一種全新文化與全新國家的搭配。三是德國模式。德國所走的現代建國道路與法國正好相反。面對法國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建國大革命,德國人嚴加拒斥:實際拒斥、婉轉接受現代國家方案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們,主流觀念呈現為一種國家主義的立場;直接拒斥并回首傳統價值的浪漫主義者,以一種民族的歷史文化情懷引導,建構了完全屬于德國的國家觀念。這都將德國導向一個危險的國家崇拜境地。
這是值得具體分析和比較的三個典型案例。先看英國。英國的現代建國歷程頗為漫長。如果從一二一五年貴族與約翰王簽署《大憲章》算起,截止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坐實君主立憲或虛君共和的現代政體,幾近五百年時間。在這期間,英國點滴積累起有助于現代建國的文化基礎。從總體上講,新文化的漸進累積,與現代國家要素的逐漸聚集,成為英國波瀾不驚的現代建國過程一個相互推進的過程。在這中間,最有利于現代國家建構的個人主義、妥協精神、責任擔當等文化因素得到有效積累,其與現代國家的分權制衡、憲政法治等制度安排頗為融洽地相伴成長。首先,個人主義的降生,在英國不是一場觀念革命的產物。它不像在多數后起現代國家那里,是因為認識到個人面對國家,乃是國家呈現其現代特質的文化-政治建制基石,因此以一種觀念革命的方式為之激情呼喚。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興起乃是傳統家庭理念與行動方式逐漸松動的結果。從十三世紀起,英格蘭就不承認家庭共同財產權,子女不能天經地義地繼承父母財產,父母可以將財產留給他們喜歡的人。只要打破了家庭共同財產權,也就會激發子女自謀生路。事實上,中世紀晚期英國的家庭,不論貧富,都得在少年時節開始學習自己謀生。父母子女之間養育與贍養的直接勾連關系終結了,家庭僅僅需要在夫妻之間盡責。①[英]艾倫·麥克法蘭主講:《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秾譯,第八章“家庭、友誼和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9~158頁。版本下同。該作者另著有《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管可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對這里簡述的英國個人主義的興起,有更為詳細的敘述。因論題所限,不對之作詳盡的重述。這樣的家庭結構,有助于形成大社會,相應也就有利于促成公民社會。血緣的社會機制終結了,人造的社會機制勢必取而代之。基于廣泛分工合作的市場機制的興起,伴隨著的必然是合作性的社會機制的興起。個人與國家的關聯關系浮現出來,取代了以前以集體跟國家打交道的模式。當然,個人與國家打交道的方式,是借助于獨立個人建立的社團組織來實現的。這樣,國家與社會的現代關系結構就凸顯出來。英國中世紀后起逐漸形成的普遍結社風氣,尤其是公民謀生性的結社轉而為政治性的結社,有力地維護了興起中的個人自由,從而讓國家很難借助強權限制公民自由。②艾倫·麥克法蘭主講:《現代世界的誕生》,第八章“家庭、友誼和人口”,第159~178頁。這對國家與社會各有畛域的現代觀念與實踐,發揮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英國素有貴族文化傳統。貴族,并不是今人簡單定位的豪門世族。換言之,貴族起碼不只是一個關系到財富多寡的社會集群,除財富多寡這一指標以外,它還有一個代行社會責任的集團載體的含義在。當國王以權力行事的時候,貴族便以社會代言人行事。前者的強權印痕是明顯的,后者的公共責任擔負也是顯著的。貴族并不是替所有人擔負公共責任的群體,而是在國王試圖專權的情況下,以限制權力、維護權利的名義呈現其公共責任擔當的。③論者指出,16、17世紀“這一時期的英國貴族與其他時候和其他地方精英的區別,是他們相對溫和的財富和權力欲,以及其中一些貴族表現出來的相對社會責任感。”[英]勞倫斯·斯通《貴族的危機1558-1641年》,于民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貴族文化轉變為紳士文化,對英國建構現代國家發揮了重要的文化奠基作用。這是十六、十七世紀英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明顯的變化。紳士(gentleman)本來與貴族之間是存在壁壘的。但這一時期文化氛圍的變化,讓紳士的文化氣質與新生的國家機制更為協調。紳士風度,因此成為最足以顯示新興文化的特質,且與虛君共和的現代建國恰好匹配。紳士是貴族與大眾之間的一個中間階層。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勿需從事體力勞動來謀生,其出生并不一定高貴,關鍵的是有社會責任心。“一位貨真價實的‘gentleman’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一個堪當大任的可敬的人,一個正直無私的人,一個能夠為了他所領導的人們挺身而出,甚至犧牲自己的人;他不僅是一個高尚的人,而且是一個盡責的人,他內在的卓越天資被正確的思想方法所鞏固,他的行為不僅天然地正確,而且在美好原則的指導下更加正確。”④艾倫·麥克法蘭主講:《現代世界的誕生》,第100頁。這個階層不僅是維系整個社會機制最關鍵的階層,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階層體現了英國開放的階級結構,不至于讓階級集團之間陷入一種突兀的對立狀態。社會階層間的溝通與合作,由此變得順理成章了。一種融進了競爭因素的良性社會合作便由這樣的階層集團結構所預制。或許在這里,人們就能理解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何以發生在英國的緣由了。“英格蘭和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這就是傳統上人們認為的英國孵化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的時期,不過英國并不是在做什么全新的事情,而是在已發生的分流的基礎上,變得更加富裕和更加城市化。其過程涵蓋一五○○至一八○○年,到了這個時間段的末尾,英格蘭成為了第一個工業國家。”①艾倫·麥克法蘭主講:《現代世界的誕生》,第345頁。
法國的情形與英國明顯不同。本來,法國大革命以前,法國現代社會文化的積累完全不弱于英國,而建構民族國家的資深國家歷程,甚至勝于英國。但法國的文化發展與現代建國,總是處在一種緊張狀態,因此最后不得不借助人頭落地、腥風血雨的大革命,直接催生一個全新的現代法國。曾幾何時,法國的政治史并不是那么令人激越,相對讓人平靜,甚至讓法國人感到驕傲。因為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上,法國曾經長期領先整個歐洲。但統一的民族國家落定在封建制度、君王專制的平臺上之后,法國的社會政治結構演進就幾乎停頓了。法國的民族國家這一現代國家的形式結構,向立憲民主國家這一現代國家的規范結構的前進,幾乎可以被忽略掉。君王的小恩小惠不是沒有,甚至多到遠超歐洲其他國家。譬如農奴制的廢除、擁有土地的農民比例,都在當時歐洲處在領先位置。然而,王朝國家那種腐朽統治的態勢,一直伴隨著實行君主制的第一個重要民族國家。法國人、尤其是法國農民承受的賦稅之重,不僅是繳交給政府的賦稅讓農民怨恨,地產主的貪婪也讓他們憤懣。這足以激起人們的普遍不滿。而且由于這些不滿竟然嚴重缺乏發泄渠道,因此長期郁積起來,讓整個社會亟欲找尋爆發機會。“管他干什么,處處都有這些討厭的鄰人擋道,他們攪擾他的幸福,妨礙他的勞動,吞食他的產品;而當他擺脫了這幫人,另一幫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現了,而且奪走了他的收獲的絕大部分。請設想一下這位農民的處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計算一下,若你能夠的話,農民心中郁積了多少仇恨與嫉妒。封肆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范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②[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73頁。版本下同。這種由怨恨主導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絕對只有在大革命的風暴中才能得到徹底釋放。但這樣的釋放,卻很難將國家引上規范發展的軌道。
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場缺乏自由約束的、追求民主的革命,主旨自然是建構規范意義上的現代國家。這不僅是因為法國早就具備了現代國家的形式結構,也就是民族國家的結構。而且是因為法國人心中無比強烈的憤恨君主專制所蓄積起來的強烈民主愿望。但也正是因為法國人指望一場革命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將這場革命推向了一個徹底顛覆秩序的極端境地。“法國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要變革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社會結構,因此,它必須同時攻擊一切現存權力,摧毀一切公認的勢力,除去各種傳統,更新風俗習慣,并且可以說,從人們的頭腦中蕩滌所有一貫培育尊敬服從的思想。這就產生了法國革命如此獨特的無政府主義特點。”③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第48頁。無政府主義的流行,塑就了一種與建構現代國家秩序相悖反的政治氛圍。因此,試圖重建國家秩序,就不得不花費比革命前建設國家還多的成百上千倍功夫。問題的關鍵還不在多花或少花功夫,而在于即使花費了這些功夫,其效果也不如人意。法國落定在現代國家的規范平臺上,此后經歷了一百五十來年的波折。可見,現代建國不能建基于現代文化的空中樓閣上。斷送一切文化積淀的現代建國,肯定會將建國自身也斷送掉。
法國大革命確實激起了人們以政治手段改造一切,白手起家創制現代國家的想象力。“從特別意義上來說,法國大革命根本上就是‘政治的’。新政治修辭的發明和政治實踐中新象征形式的出現改變了時人關于政治的觀念。政治成了改建社會的工具。法國人相信,他們能夠建立一個與過去不同的、以理性和自然為基礎的新的民族共同體。這些崇高的抱負需要新的政治實踐去實現。于是,為了法蘭西民族的復興,群眾性宣傳、下層階級的政治動員、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等策略應運而生。這些策略也很快成為界定大革命經驗的要素。”④[美]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汪珍珠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4頁。版本下同。但由于以政治方式摧毀了一切穩定的東西、尤其是千百年凝聚起來的文化機制,因此,它造成的后果,一定是促使人高度警惕的政治不確定性。這是文化與政治惡性循環的機制,值得建構現代國家的所有國度吸取教訓。“大革命一直迷惑我們至今,因為它催生了這么多現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它不僅僅是現代化會引起暴力和不穩定的一個例子,或走向資本主義的關鍵一步,或極權主義誕生的環節之一,雖然我們可以認為它促成了所有這一切。關鍵是,它應該是一個時刻,就在這一時刻,人們發現政治是蘊含巨大效力的活動、意識轉變的代理人,以及性格、文化和社會關系的鑄模。從此,人們可以從這一發現中演繹出不同的結論,事實上也確實出現了許多不同結論。托克維爾雖然對這次經歷中‘陰暗惡兆的’一面感到懼怕,但還是總結道:‘所以,法蘭西人民立刻成了所有歐洲民族中最輝煌也最危險的一支,在其他民族的眼里,法蘭西人民最有資格被膜拜、被憎恨、被憐憫,或者說,法蘭西人民成了一種預警—一種絕對不容漠視的預警。’”①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第267~268頁。一種期于絕對嶄新的文化和完全沒有缺陷的政治之完美的對接,這種病態的社會心理,也絕對無法帶給深懷這種期待的國家以內心強烈期望的結果。而且結果常常是恰相反對的。法國大革命之后,國家建構陷入長期的起伏波折,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讓·皮耶爾·烏艾勒 攻占巴士底獄
與英國和法國不同的是,德國既沒有在長久的文化發展中積淀有利于現代建國的文化要素,也沒有掀起一場全方位的文化革命,以便為現代建國清理地盤。德國走上了一條只想基于既有文化傳統,建立有益于維護民族自尊心、贏得民族成員內在認同的國家。但與法國早期的建國類似,德國的現代建國進程,很快落定在民族國家的現代國家形式結構上,但卻遲遲難以落定在立憲民主的規范現代國家平臺上。而且中間也經歷了無數的國家災難,最后不得不在一次準殖民的經歷中才確立起立憲民主政體,勉強躋身規范的現代國家行列。德國呈現出的文化與政治關聯,展現的文化懷舊與現代建國間過于緊密的勾連關系,不僅讓站在現代門檻外的德國人陷入一種文化自閉,而且讓致力建構現代國家的德國人無法確知現代國家的規范結構。結果,德國陷入了一種雙失局面:以對傳統文化的眷顧冒充世界情懷,以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卻被真實世界所排斥和打擊;以對國家的絕對忠誠來建構現代國家,最后形成國家主義和國家崇拜的畸形建國后果,因此注定了多舛的國家現代命運。
德國的文化傳承與現代建國關聯,循兩條線索演變,一是浪漫主義的線索,一是歷史主義的線索。浪漫主義直接受到英國浪漫主義先驅的啟示。一種將歷史想象得美侖美奐、完全自足的文化理念,在英國人休謨和伯克那里也許是有根據的。因為英國正是在潛移默化、風波不興的歷史漸變中,為現代國家集聚深厚的文化資源。但對德國來講,現代建國是后發外生型的,是通過法國以戰爭手段推銷給德國的。德國的現代建國急促性之強,完全無法在歷史文化的漸變中有序推進相應進程。因此,德國是無法再現英國經驗的。但偏偏德國卻毫無疑義地走上了英國保守主義的文化道路。這就使文化的既定軌道與現代建國的實際處境出現了嚴重的錯位。德國的浪漫主義者如席勒、施萊格爾兄弟和諾瓦利斯,借助小說、詩歌、戲劇和美學作為表達手段,語言形象、富有詩意、感染力甚強,但表達的不外是政治訴求,試圖以此抗擊侵略者,凸顯一條德國實現自由的道路。這樣的表達,在德國的愛國主義思想家費希特、阿恩特、雅恩及科爾那那里,就更是將愛國主義闡揚成為一種炙熱的民族情感。①參見[澳]慕哈特·舒爾慈《浪漫主義:歐洲浪漫主義的源流、概念與發展》,第五章“浪漫主義與政治”,香港: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76頁及以下。像赫爾德這樣的學者,則通過自己對德意志民族的語言、文化與歷史的研究,將國家歷史直接視為普遍歷史,并從中汲取無窮的精神力量。在這樣的思考進路中,回首德國自身歷史進程的普遍精神吁求,將反對普遍主義的歷史主義推向了引導德國建構現代國家的前沿。民族性因此成為戰勝世界性的最有力武器。“赫爾德的《人類歷史哲學觀念》表現為一個遼闊強大的海洋,雖然并不是不停歇地劇變著,卻持續不斷地同時為順流和逆流推動著。因為在關注偉大的集體性個體時,他那輝煌莊重的個體發展意識和個體完美意識特別地占據著主導地位。他的卓越之處在于按照各民族及其民族精神來進行思考的能力。”②[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歷史主義的興起》,陸月宏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第387頁。版本下同。這樣的思考,既可以說將啟蒙精神的干癟理念豐富化了,但也可以說窒息了啟蒙的現代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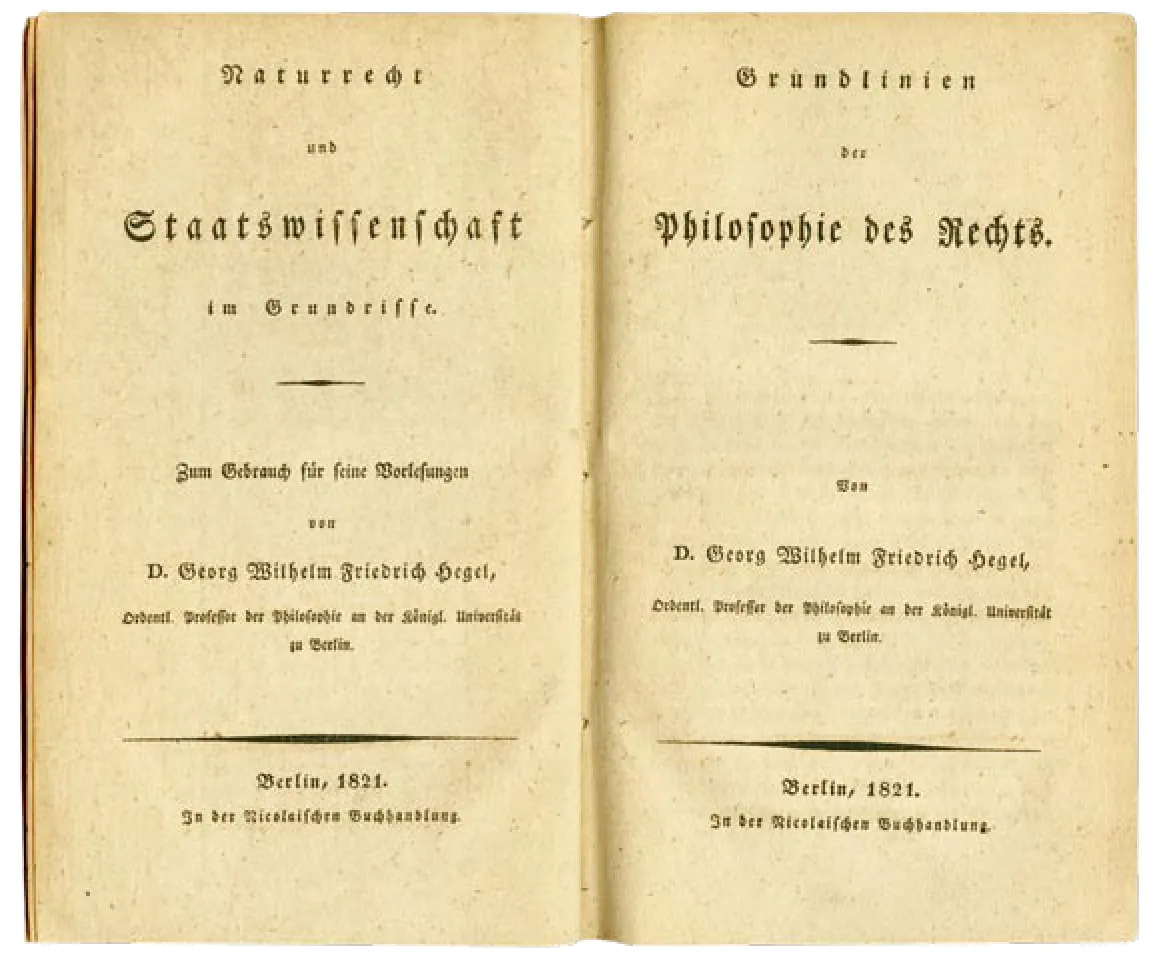
《法哲學原理》

黑格爾
黑格爾的國家主義理念,可以說承接了浪漫主義的民族國家觀念。③梅尼克指出:“萊辛在包含于1780年《論人類教育》的發展觀念中,科學地為通向黑格爾的偉大德國運動準備了道路。萊辛選擇的道路也許很可能通向黑格爾,但很難說通向歌德或蘭克。因為《論人類教育》深奧的核心觀念不是歷史主義高舉的個體發展觀念,而只是來自業已在萊布尼茨中表現出來的完善觀念,它在啟蒙運動中也以粗陋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歷史主義的興起》,第259頁。但他顯然給予國家以更加崇高的期許,因此自然而然地將國家視為神造之物。黑格爾明白無誤地剖白:“我們不象希臘人那樣把哲學當做私人藝術來研究,哲學具有公眾的即與公眾有關的存在,它主要是或者純粹是為國家服務的。”①[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8頁。版本下同。在他確立的這一基本原則基礎上,黑格爾首先將國家提升到個人之上。“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因為它是實體性意志的現實,它在被提升到普通性的特殊自我意識中具有這種現實性。這個實體性的統一是絕對的不受推動的自身目的,在這個自身目的中自由達到它的最高權利,正如這個最終目的對單個人具有最高權利一樣,成為國家成員是單個人的最高義務。”②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53頁。依此設定,黑格爾將國家作為目的性的存在,它并不需要行使保護公民個人自由的職責,相反公民個人必須以國家為歸宿,才呈現出自身的客觀、真理與倫理規定性。這樣就完全逆轉了英國人為現代國家設定的旨在保護其成員權利的工具性特質。接著它再將國家提升到市民社會之上。說起來,市民社會本就是私人的活動空間,因此當國家置于個人之上的時候,也就置于市民社會之上了。與國家是個人的歸宿一樣,它也是市民社會的歸宿。市民社會是蕓蕓眾生特殊利益的聚集之所,只有國家才代表了普遍利益。因此,國家必定是市民社會倫理規定性的供給者。“自在自為的國家就是倫理性的整體,是自由的現實化;而自由之成為現實乃是理性的絕對目的。國家是在地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識地使自身成為實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為它的別物,作為蟄伏精神而獲得實現。只有當它現存于意識中而知道自身是實存的對象時,它才是國家。……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國家的根據就是作為意志而實現自己的理性的力量。在談到國家的理念時,不應注意到特殊國家或特殊制度,而應該考察理念,這種現實的神本身。根據某些原則,每個國家都可被指出是不好的,都可被找到有這種或那種缺陷,但是國家,尤其現代發達的國家,在自身中總含有它存在的本質的環節。但是因為找岔子要比理解肯定的東西容易,所以人們容易陷入錯誤,只注意國家的個別方面,而忘掉國家本身的內在機體。國家不是藝術品;它立足于地上,從而立足在任性、偶然事件和錯誤等的領域中,惡劣的行為可以在許多方面破損國家的形相。但是最丑惡的人,如罪犯、病人,殘廢者,畢竟是個活人。盡管有缺陷,肯定的東西,即生命,依然綿延著。”③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58~259頁。黑格爾的這些論述,似乎將國家完全置于非歷史的絕對理性之自我實現的辯證進程中,人們完全無法直接從中看到他對現實國家演進歷史的爭辯。其實,只要注意到他在申述民族與國家的關系時,將日耳曼民族安頓在調和與解決一切矛盾的高位,他的理想國家指向的現實蘊含就昭然若揭。一場關于國家的復雜哲學思辨,不過是他最終想將自己所在國家加以神化的嘗試而已。就此而言,黑格爾的國家理念,與浪漫派的國家想象,相差其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他們都不過是將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看作是建構現代國家的當然前提罷了。
三、文化與政治的交互影響:文化的次級效能
在復雜的現代建國世界史進程中,各個國家處置建國中的文化與政治關系,在進路與舉措上,都大為不同。但就前述三個西方國家而言,可以看出不同模式的共同點與差異性。在共同點方面,三個國家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進程中都遭遇了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問題,而且文化與政治的交互影響都非常明顯。但相互間的差異性也非常顯著:像英國那樣實現文化與政治的良性互動,有力促進現代建國的驚人成就,堪稱典范,可望而不可即。而像法國那樣出現文化與政治的惡性互動,難以坐實建國目標的驚人事實,實為教訓,讓后起國家極力規避。至于像德國那樣尋求發揚光大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并試圖以此促進民族國家建構的,不可避免地會走上國家主義的道路,盡管這樣的道路并不直接與希特勒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接通,但一種文化自戀主義的自閉狀態,是無法開辟出現代建國的陽關大道的。德國后起的建國曲折,也許就在文化與政治的畸形聯通中注定了。

大憲章(1215)
現代建國進程中文化與政治發揮的作用,明顯是不同的。這正是兩者需要互補的原因之所在,也正是兩者作為社會要素一直糾纏在一起發揮效力的社會結構狀態所致。文化與政治對現代建國的交互影響,就此呈現出來。這種交互影響,可以從三個角度得到確認:一方面,文化內蘊的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國民心態、傳統習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確實會影響甚至制約人們的政治行為,讓人們在建國關鍵時刻的態度與行為受其左右。另一方面,現實政治狀況,尤其是一個國家內部諸政治力量的對比關系、各方的處境與實力、各方對某一政治舉措的得失判斷、究竟是以政治妥協還是你死我活對待政治決斷、以及如何衡量政治終局等因素,會對建國中存在的各種政治力量發生巨大的引導作用。再一方面,當政治與文化成為建國進程中特定的分析關聯結構時,既成文化究竟如何影響現實政治抉擇,反過來,現實政治變局如何塑造與之相宜的文化氛圍,成為人們理解文化與政治對建國發生交互作用的綜合視角。這就像人們在分析經濟發展與文化傳統的關系時,需要確認一種交互性的分析視角,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單純決定一樣。文化與政治關系呈現出來的三個面相,都可能誘導三種完全不同的處置兩者關系的立場:第一方面可能引導出文化決定論的立場。這一立場敦促人們認定是文化而不是其他因素,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現代建國績效與成敗。第二方面可能誘導一種政治決定論的立場。這一立場教導人們,由于政治是一種強有力的力量,因此它足以單獨或自主決定國家建構的績效高低與成敗前景。第三方面則引申出一種對等看待兩者作用的立場,認為文化與政治都不是自足的社會要素,它們相互作用,形成兩種等值的結論:“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淪。”①引自塞繆爾·亨廷頓等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頁。版本下同。假如人們相信文化與政治不是自足自主的作用于現代建國進程,因此只能以一種交互作用的方式影響現代建國進程,那么,為文化作用更為重要進行辯護,因而顯得保守的主張,與為政治作用更加重要進行申辯,因而顯得開明的兩種主張之間,是不是可以持一種從兩端出發逼近均衡作用的綜合性立場呢?從邏輯上講,這樣的綜合性立場是可以推導出來的。因為既然兩者是交互作用的,甚至無法區分誰的作用究竟更大,那么就勿需勉強區分作用的大小,轉而尋求一種對應性作用機制,促使兩者對現代建國發揮疊加的積極作用。
在西方國家的現代建國進程中,文化與政治的交互作用,以及對建國發揮疊加推進作用的典型案例,當屬英國。文化與政治兩個社會要素對現代建國交互且疊加發揮推進作用,最佳的狀態是人們已經無法嚴格區分究竟是文化還是政治、抑或是兩者共同對現代建國發揮了什么樣的積極作用。但從現代建國的上佳結果上可以推知,文化與政治同時對這一過程發生了有效推進。否則,現代建國就成為一項失敗嘗試。在現代建國中可以分辨清楚究竟是文化還是政治要素明顯推進了建國進程的情形,已經是一種令人擔憂的狀態。因為這就顯示出要么是文化影響政治發展,要么是政治改變文化土壤的偏倚情形。在英國幾近五百年的現代建國史上,文化與政治都處在漸變狀態,因此文化與政治的交互影響促成一種均勢狀態:文化的妥協性演進,促使政治力量各方適應一種妥協性局勢。遠在一二一五年現代建國肇始階段,英王約翰面對貴族的進逼,與貴族達成了《大憲章》。盡管這部憲章對現代英國的興起具有的象征性意義遠大于它的實質性作用,但它卻襯托出英國人在自治習慣、也就是自我管理的文化與國王權力之間的博弈,對英國開啟現代建國歷程所具有的重要價值。當時英國都市的自治、鄉邑的自治,已成為都市居民和鄉村居民的習慣。自治已然成為一種英國的社會文化習性。鄉紳的興起,甚至比貴族發揮的社會政治作用還要大。因為他們的社會基礎更加深厚,更能動員社會基層力量:紳士協理公務,以及對代表制重要性的認知,都構成一種現代立憲民主制度建構的社會文化動力。②[英]屈勒味林《英國史》(上冊),錢端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94~196頁。即便是英國國王,也受制于社會長期形成的習慣:國王向社會索要的服務、捐納金或承襲金,都不能比習慣的更多。封建主義養成的反專制主義習性,以及與國王進行武裝對抗的傳統,都是《大憲章》最終得以簽署的前置條件。這正是《大憲章》兩個對等重要條款受到后世重視的緣故:一是國王對人民自由權的確認。“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等地位之人依據這塊土地上的法律作出合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形式的損害。”③《大憲章》第39條。引自齊延平《自由大憲章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7頁。版本下同。盡管論者對這一條款究竟是否現代自由權的憲制規定存在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英國社會已經足以要求國王保障人民的權利了。二是明確規定貴族具有限制乃至于廢黜國王的權利。“如余等或余等之法官、管家吏或任何其他臣仆,在任何方面侵犯任何人之權利或破壞任何和平條款而被上述二十五位男爵中之四人發覺時,此四人即可至余等之前—如余等不在國內時,則至余等之法官之前—指出余等之錯誤,要求余等立即設法改正。自錯誤指出之日起四十日,如果余等或余等不在國內時余等之法官不愿改正此項錯誤,則該四人應將此事決于其余男爵。而此二十五男爵即可聯合全國人民,共同使用權力,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與壓力,諸如奪取余等之城堡、土地與財產等等。務使此項錯誤最終能依照彼等之意見改正之。”①《大憲章》第61條。引自齊延平《自由大憲章研究》,第329頁。這是社會力量限制國王權力的明確規定。盡管執行起來受到諸多阻滯,但這一條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僅從《大憲章》的達成以及相關條款來看,英國在現代國家的初始階段,就已經形成了一種以社會文化習性對抗國王權專制權力的機制,這對此后英國立憲政治獲取文化與政治的雙重動力確立了方向。
此后英國立憲民主政制的發展,一直邁進在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互動的健康進路上。如果以《大憲章》不斷的簽廢、再行頒布的線索審視英國現代建國的歷史,可以進一步了解這兩種建國動力的交互作用。一二一五年簽署《大憲章》不久,約翰王就因拒絕出席后續程序碰頭會,遭貴族宣戰。約翰聯合教皇,宣布《大憲章》無效。內戰中約翰去世。繼位的亨利三世一二一六、一二一七連續兩年承認大憲章。一二二五年又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大憲章》進行了刪改。這個文本,成為此后歷代國王確認該憲章的正式文本,從而讓《大憲章》具備了國家基本法的地位與功能。《大憲章》由此成為保護權利、規范權力的法案:貴族與自由民以此爭取和保護自己的權利,國王方面也據此緩解不滿、防止反抗、維護權力。雙方各得其所。正是由于《大憲章》具備這兩種功能,所以它才具有綿長的生命力。到一二九七年,隨著愛德華一世基于財政需要,將《大憲章》加蓋印璽,頒發各級官員,并要求嚴格遵守,使得《大憲章》成為英國的一部成文法典。“自此以后,英國社會每遇社會危機,英王一旦為了戰爭籌集經費向臣民施加壓力,臣民提出冤情一旦被延擱,自由大憲章就會被抬出來。尤其是它的第三十九章更是成為了英國乃至人類一切暴政和司法不公的天敵,成為了英國乃至人類法治與憲政制度衍生的‘基因性’條款。”②齊延平《自由大憲章研究》,第191頁。此處對《大憲章》演進過程的概述,多依據該書。尤其是該書第六章“自由大憲章訂立后的確認與發展”、第七章“自由大憲章在近代的復興”。可見,在社會領域里行動的臣民,樂意將《大憲章》作為自己習于認知與援用的政治文化依據;而在權力領域行動的國王、法官與行政官員,愿意遵守憲章的諸條款,作為施政的理據。因此,憲政文化與依憲施政緊密結合,相得益彰。后經十四世紀的完善,尤其是對《大憲章》加以確認、進行解釋和修改完善,讓其成為保護權利和規范權力的重要法案。中經十五世紀以后長達二百年的蟄伏期,《大憲章》在英國正式落定現代國家建制時,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詹姆斯一世試圖將英國法制體系改變為成文法,而律師們極力維護普通法的較量中,《大憲章》的重新闡釋,使其再次發揮出引領英國現代建國的重要作用。在首席大法官科克爵士對《大憲章》的輝格黨解釋中,它真正發揮了確立現代政治自由的決定性作用。其時,議會、法官、教會、大學均依據《大憲章》來為自己的自由權辯護,從而有效捍衛了幾個世紀以來“王在法下”的傳統。一六二八年的權利請愿書、一六七九年的人身保護法、到一六八九年權利法案,讓《大憲章》的基本精神與部分條款,成為現代英國立憲文化與立憲政治齊頭并進的標桿。截止今天為止,《大憲章》的九個條款,仍然存在于英國的法令全書中。
在文化與政治對現代建國發生均衡影響的英國進程中,很難區分清楚究竟是文化因素還是政治因素對立憲民主國家建構發生了更為重要的影響。如果一定要分辨兩種因素的重要性差異,那就必須將之放到現代建國這一主題上來衡量。這樣的衡量,一方面是在英國現代建國兩種動因的實際效能上進行的甄別,另一方面則是在國家間的比較中進行的估價。如果說前一方面的甄別可以與國家間相關狀態的總體特征一并審視的話,那么,后一方面的刻畫反倒具有了某種優先提供參照的論述必要。
誠如前述,在歐洲建構現代國家的進程中,法國與德國的狀況,與英國的差異比較明顯。法國同時創制革命文化與現代國家的嘗試,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德國將自己的民族文化置于創制現代國家的優先位置,從而顯現出明顯的保守性。實際上,法、德兩國建構現代國家時,也很難清楚明白地離析出究竟是社會文化因素、還是現實政治因素對現代建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兩種因素,也像英國建國進程中那樣緊密糾纏在一起。但兩個國家建構現代國家時,傳統文化、新生文化與現代建國的吻合關系,顯然不及英國。
法國以革命因素的明顯積累,掀動現代建國的驚濤駭浪。因此,法國建構現代國家的關鍵階段,也就是大革命前后五十年左右,傳統文化的衰頹非常顯著。在啟蒙運動中,啟蒙領袖人物堅信,正是超越歷史與文化的理性精神,才是引領現代法國的強大觀念。由笛卡爾創制的建構理性主義哲學,勢不可擋地侵入歷史哲學,成為啟蒙領袖重建社會政治世界的時代精神。啟蒙領袖期望一個全新的、平等的政治世界展現在人們面前。啟蒙運動自然有其展現于整個歐洲的總體特點。“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有許多,但是啟蒙運動卻只有一個。當時,從愛丁堡到那不勒斯,從巴黎到柏林,從波士頓到費城,一群松散而非正式且完全沒有組織的文化批評家、宗教懷疑論者以及政治改革家,這些啟蒙思想家組合成為一支喧囂的樂團,當然他們中間容或存在著不和諧的聲音,但是更令人訝異的則是他們之間的和諧一致。這些啟蒙運動的啟蒙思想家以一種巨大企圖心的姿態結合在一起,支撐他們這種姿態的不外乎世俗主義、人文精神、世界主義,以及各種不同形式的自由—杯葛獨裁作風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貿易的自由、實現個人才能的自由、從事美學活動的自由,一言以蔽之,一個道德人在這個世界上實現自我的自由。”①[美]彼得·蓋伊《啟蒙運動(上):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劉森堯等譯,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第24頁。這是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完全撼動了中世紀以來形成的精神世界和政治世界。這是現代興起,尤其是歐洲大陸現代興起所必須借重的力量。但這也是一股令人震驚的摧毀性、破壞性力量。其理論的建設性甚強,其社會政治的建設性內涵十分微弱,而且極其浪漫,很難收到實效。
而在法國,啟蒙運動助長的政治浪漫主義更加突出。由于法國啟蒙運動缺乏思想市場的內在激蕩,因此,崇尚理性的精神甚少受到反對理性精神的洗滌,即便有盧梭對伏爾泰的抗拒,也就是情感對理性的抗拒,但盧梭本人的思想并不構成促使單純的理性精神趨向成熟的動力,相反提供給理性以激情的動力,將理性塑造成為由情感激蕩起來的、徹底重造社會的力量。一種期于道德理想國的強烈愿望,正好與盧梭反對的法國啟蒙領袖所主張的理性王國精巧匹配,構成嶄新國家與嶄新文化聯袂出場的合二而一的強大動力。此時,傳統文化自然成為徹底蕩滌的對象,因為它的承載者君王、以及君主政體,已經成為腐朽沒落文化的同義詞。新生的革命文化則完全屬于服務于建構嶄新國家需要的產物。文化與政治同時成為建構嶄新國家的工具性因素,對等地作用于理想王國的建構。“雖然革命的政治文化從定義上來說總是變化和發展的,但仍有其連貫性和統一性的源頭。革命者將理性和自然作為新的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基礎,從此導出一整套的共同期望。他們認為,成功的職業生涯靠的是能力,不是出身,不應該有任何世襲的、團體的或地方的特權,應該向廣大公民開放通過選舉和擔任公職來參與政治的機會。簡而言之,他們相信,新秩序應該以理性為基礎并覆蓋全國。這些自覺的政治原則都來自啟蒙思想家的著作,為一般受過教育的法國人所熟知。革命者的出眾之處在于他們隱含的修辭學假設。指導他們行動的信念是:復興后的民族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新共同體,是建立在透明的社會和政治關系這一理想基礎上的。所以,他們認為所有職務、甚至服裝上的不同都沒有必要,最極端的想法是認為任何代表制度都是不必要的。新共同體不需要政客或政黨,議員和官員只是暫時性地行使職權,而且要服從民眾的意愿。”②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第244~245頁。法國大革命終于淹沒在普世性價值的頌揚中,對法國自身的現代國家建構來講,國家性特征就此隱沒了。本來,一個現代國家,應當在其有效解決自己國家建構的同時,為其他國家提供普世經驗。但法國大革命將之打為兩截,現代觀念與現代國家身首異處,無法融為一體。而就文化與政治對現代建國的關系來講,既成的傳統文化完全隱而不彰,新生的革命文化又完全成為政治建國的工具。因此,文化完全喪失了規訓或引導政治建國的功能,變成了囂張跋扈的權力將自己野蠻行為正當化的托辭。一個期于平等精神的現代建國反而導出了一個血腥的專制政體。橫空出世的現代法國,不僅沒有兌現它給所有法國人基于理性的平等承諾,相反將法國誘入無邊的苦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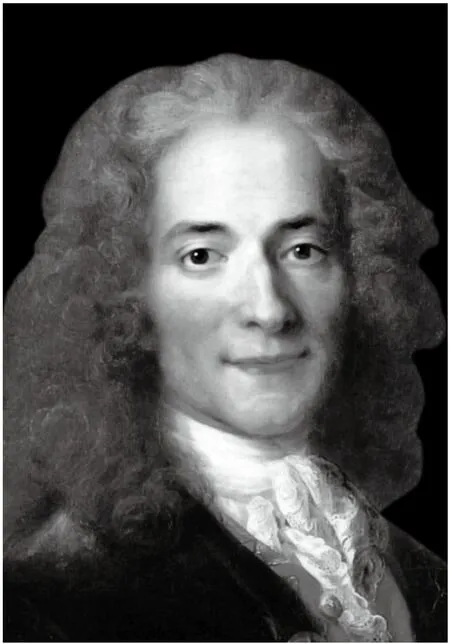
伏爾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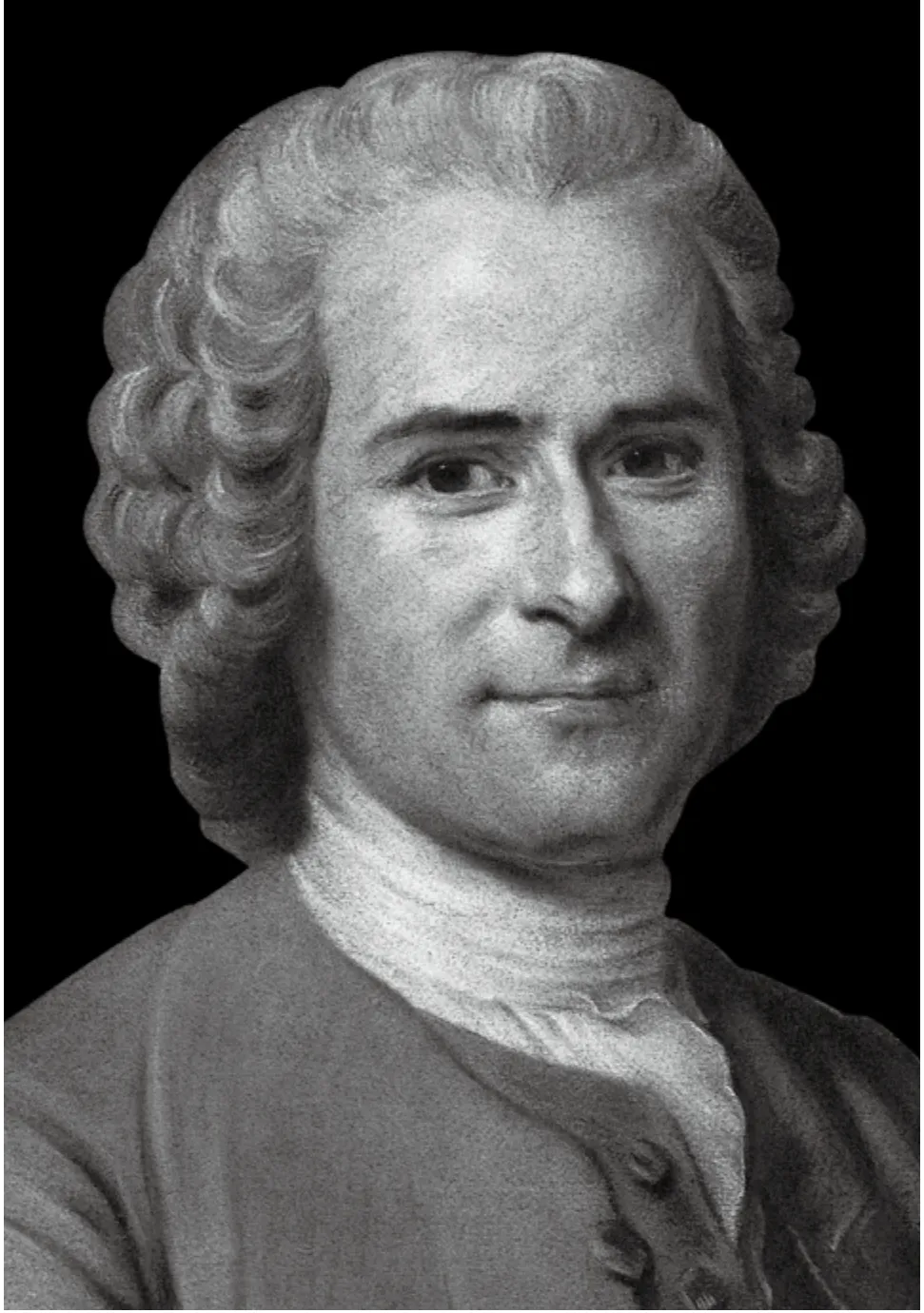
盧梭

康德

洪堡
德國的情形又有所不同。德國的啟蒙運動較法國微弱許多,而承接啟蒙的方式依靠的是玄而又玄的哲學,在直接扎根于德意志民族經驗生活的歷史、語言與文化研究面前,明顯顯得蒼白乏力。既成的傳統文化,明顯在德國的現代建國進程中發揮了強勢作用。“德國的啟蒙運動是自我意識的覺醒而自治,是德國人在審美或是精神上所作的準備,而非有針對性的對現代政治生活的訓練。德國人對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持更加肯定和積極的態度,他們拒絕在政治上采取法國式的暴力,而是更傾向于服從國王和國家的穩定。基于此,他們集體表現出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懼而寧愿選擇專制的統治。在德國人看來,法國構建自由的過程威脅到了自由與權威、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平衡。從路德的‘因信稱義’到康德的‘智慧之人’以及洪堡的‘自然發展’之人,固執的德國人將自身束縛于君主的統治和自我犧牲的公眾生活的理念中。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宗教信仰自由,深受哲學的啟迪,蒙受社會的教育,有義務為鄰居和國家服務。”①[美]史蒂文·奧茨門特《德國史》,邢來順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139~140頁。這是一種由德國文化預制了的政治習性。由這種政治習性驅使德國人拒斥革命、服從秩序,這對后起的現代建國來講,無疑增加了不少困難:一種難于松動的服從性文化,很難提供給權利主導的現代建國以強勁動力。從威廉父子絕對主導國家進程,到俾斯麥鐵血統一德意志,以至于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勃興,都可以看出德國人過于看重秩序所導致的政治臣服。
在英、法、德三國建構現代國家的進程中,文化因素與政治因素確實是交互作用于建國事務。在實際的建國進程中,試圖區分兩種因素究竟誰發揮的作用更大,也許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但在分析的視野中,區分兩種因素對現代國家發揮作用的大小,則極有必要。這是因為,人們常常就此引申出現代建國不同后果的導因之文化決定論和政治自主論兩種觀點。前者認定,一個國家之所以跟另一個國家相比,在建國的結局上呈現出鮮明的不同,就是因為文化緣故所致。后者確信,不是所謂的文化因素決定現代建國的不同結果,而是實際政治博弈導致了不同國家現代建國后果的懸殊差異。兩種形式的決定論說辭都有失偏頗。但兩種論斷都推動人們審視文化與政治對現代建國相較而言的重要性問題:這種比較,既推動人們審慎對待文化決定論與政治決定論,又促使人們在作別單一因素決定現代建國的基礎上,比較兩者對現代建國所發揮作用的重大不同。相比而言,后者更為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就現代建國這一論述主旨來講,文化因素的作用,肯定不會比政治因素的作用更加重要。因為現代建國本身就是以政治事務為核心的綜合工程。如果僅僅以現代建國主要是政治事務來斷言政治因素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似乎有些循環論證的意味。試圖確認政治因素對現代建國發揮了這樣的作用,需要將各種社會要素對之發揮的作用羅列出來并加以比較,才足以顯示究竟是那種因素更加重要。同時,還需要從理論上論證,何以政治的因素才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其他的社會要素則無法發揮同等重要的作用。前一論說進路,并不需要真正將各種社會要素一一羅列出來,只需采取一種接近理想實驗的方法,就可以說明問題了。對現代建國來講,國家權力建制是核心問題。比較這一核心問題,諸如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傳統因素、習俗因素等等對現代建國發揮的再怎么重要的作用,就都是外圍因素。經濟、文化、傳統、習俗無論對國家建構發揮怎么重要的作用,它們都無法直接生成國家權力建制。試圖建構完成現代國家機制,還必須展開政治力量各方的直接博弈,才能凸顯由各方提出、磨合、妥協并接受的權力機制。這種不可替代性,注定了政治因素對現代建國所發揮的作用,是其他社會要素不可比擬的—如果沒有英國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對現代建國的臨門一腳,人們完全無法設想英國如何落定在現代國家的平臺上;如果沒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人們也無從想象大革命的種種文化嘗試因何浮現;如果不是德國長期無法坐實現代建國目標,僅從德國浪漫主義和古典哲學的成就,人們完全有理由認定德國早該建成現代國家了。
就此而言,僅就文化與政治兩種要素對現代建國發揮的作用來進行比較,政治要素肯定是影響其結果的首級要素,而文化要素則只能是影響建國結果的次級因素。取決于這點,需要人們自覺拒斥流行于現代建國解釋中的文化決定論。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文化決定論形式,大致有三種,一是思想文化的觀念決定論,其認定思想文化是能夠貫通古今的決定性力量。因此,現代建國也逃不出被先定的思想觀念決定的圈套。二是政治文化的價值決定論,其認為一切政治行動都是行動者政治價值偏好的副產品,因此,先在的價值觀念決定后起的政治行動。三是社會日常生活的習慣決定論,其堅信社會生活的習性決定一切相關的選擇,政治建國之高端事務終究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低端事務中呈現成敗得失。從總體上講,三者都體現出“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文化決定論特質。它們都確信,既定的或專門的文化狀態決定了現代國家的建構狀態。“不同的文化區域的存在,具有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后果,有助于形成從人口出生率直到經濟行為的種種重要現象;……它們影響到民主體制的形成。對于民主而言,各文化之間的差異的一些重要方面尤其起重要作用。我們將看到,各社會的一大區別在于有的社會強調‘生存價值觀’,有的則強調‘自我表現的價值觀’。強調后者的社會成為民主社會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強調前者的社會。”②[美]羅納德·英格爾哈特:“文化與民主”,載《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第126頁。這樣的論證旨在區分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建構現代國家時文化發生的不同作用。但很顯然,它不足以解釋西方國家內部、譬如像英、法、德三國現代建國中的文化與政治對建國事務的不同影響。極而言之,僅以價值觀解釋現代建國,也就是建構立憲民主政體的國家,是不足夠的。
文化決定論的三種形態,都不構成阻擋或促進現代國家建構的決定性力量。這是因為,現代建國進程中政治發展的自主性力量更加重要,而文化只能對現代建國發揮次級的效應。具體說來,一者,在現代國家政治變遷中,文化確實有塑造具體國家形態的作用,不同的文化體系所建構起的國家確實具有不同的文化面相。但文化面相的背后,并不是文化自身對政治生活的決定性塑造,只不過是對打造一個具體政治結構發生一種正當化效力的重要因素。它既不是單一因素,更不是決定性因素。一國的政治體系,不管是權力歸屬、權力結構、用權方式、利益分配機制,還是公民認同狀態、國家-社會互動結構,才綜合塑造國家的政治面相。二者,在政治變遷狀態中,文化受到重新塑造。一種既定的歷史文化狀態中斷以后,尤其在外部政治力量中斷以后,它會在新的政治運作模式中,產生新的文化價值理念、制度安排和心靈習性。因此,文化并不具有文化決定論者認定的絕對自主性。三者,文化與政治的交互性作用,還受制于其他社會要素的相互影響。因此,在復雜的國家建制中,任隨哪一個要素也不足以對建國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政治、經濟、文化三種基本社會要素而言,它們不斷地因時、因地、因事對建國發揮不同作用,其對國家的塑造結果或微妙或顯著。因此,試圖理解現代建國的完整狀態,就必須借助社會要素的交互影響才能實現。僅僅借助于文化的單一要素,是不可能理解現代建國這一事件的。
在現代建國中,文化只具有次級效能。這不僅是從政治與文化兩種社會要素比較角度講的,也是從文化自身的狀態而論的:文化是一種軟力量,而非硬力量。軟力量的綿延性很強,發揮作用依靠潛移默化,因而它的長期作用遠遠勝過當下見效的經濟力量和風雷激蕩的政治革命,但后兩者的作用是及時的、當下的、有力的。持衡的力量和當下的力量,當然可以是交疊性力量。但緩不濟急的文化效能始終被當下政經急務所左右,因此對現代建國發揮作用的文化力量,始終是次級性的、背景性的韌性力量,而非首級性的、前臺化的現實力量。文化不可能發生直接塑造國家的作用,只可能發揮潛在影響國家走向的功能。
四、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
如前所述,在現代建國進程中,政治因素與文化因素交互發揮著作用。在實際的建國進程中,兩者的作用無法切割開來處置。在分析的框架中,兩者的功能需要分別對待。分析的結論是,文化對現代建國發揮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但這一作用對現代建國不是決定性的,相對于政治因素對現代建國發揮的作用而言,文化的作用只是次級性的、背景性的、潛移默化的。這樣的結論,讓人們在作別現代建國的文化決定論基礎上,高度重視文化所發生的重大作用。而重視這樣的作用,體現為現代建國進程中對文化資源的有效聚集。
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著眼點自然在于推進現代國家的建構。因此,凡是那些有利于促成現代國家的價值觀念,無論是以宗教、哲學、道德、傳統、習俗、慣例的形式,還是借助教育、媒體、代際傳遞或同輩關系等方式形成的信仰與觀念,都應當聚集起來,并將之付諸建國進程中諸社會要素的積極互動,從而營造出一個有效推進現代建國進程的文化氛圍。至于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的進路,則需要強調三個基本原則:其一,這樣的聚集工作,既不是基于文化精英的主觀信念,讓他們以一種為民立命的方式替民眾確立某種文化信念;也不是基于政治精英的建國偏好,由他們為政治共同體成員提供一套政治生活準則和制度安排。現代建國既然已經成為所有成員參與其中的事務,就不排斥成員或成熟或不成熟的政治理念、制度訴求與生活方式。因此,促成一種精英階層與社會公眾參與其中的文化建設狀態,是最有利于現代國家建構事務的。其二,這樣的聚集工作,既不是完全因應于當下政治的亟需而對文化資源的隨意調遣,以至于將文化徹底工具化,變成建國政治事務的奴婢;也不是執著于既成文化傳統,拒斥一切文化發展契機,拒絕以開放的胸襟讓既成文化傳統與外來文化有效融匯,以至于窒息文化生機,造成現代建國中過于重視文化反倒妨礙其發揮積極作用的悲劇性后果。現代建國不再是宥限于一國境內的孑然孤立事件,而是以先期呈現出來的現代國家之規范內涵來塑造后起致力建構現代國家的國度。因此,后起現代建國必須承接先行現代國家的文化理念,并勉力與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有效對接。對自己國家內在傳承的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入,不宜采取偏廢態度—即要么固守傳統文化而拒斥外來文化,要么開懷擁抱外來文化而盡棄傳統文化。這兩種態度都會造成現代建國所需文化資源的可怕稀缺。其三,這樣的聚集工作,既不是以文化決定建國的文化決定論來引導的,以至于將現代建國的重要政治事務處理為一場文化批判或建構運動;也不是拒絕讓文化發揮本應有的作用,將之抑制在政治立規與制度設計之下,以至于讓新生的現代國家規則難以發揮效力。現代建國需要激活所有的文化資源,但不是因為文化自身發展的理由,而是基于建國的政治需要。這不是一種政治實用主義的態度,而是一種促進文化發展且有利于現代建國的雙贏目標需要。如果僅僅著眼于文化自身發展需要而將文化置于現代建國事務的絕頂重要位置,那不僅會遮蔽建國的要務,而且會窒息文化發展的社會生機。
據此,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乃是一種守成型態度與開放性立場兼綜的理性行動。英國的狀態當然是一種近乎理想的狀態。所謂近乎理想,是因為英國實現文化與政治雙向健康作用于現代建國,在結果狀態上堪稱理想;但在過程的漫長性上,是其他所有國家所無法償付的代價。因此它的成功具有不可模仿性。換言之,英國之外的所有國家,無法再次將文化與政治安置在緩急功能相應的適宜地位上,即便是模仿英國建國的美國,在提供現代建國的文化理念上,也表現出相當的急促性。好在漫長的自治傳統緩解了急促的文化上位造成的建國緊張,讓美國意外地實現了創制國家與創制文化同獲成功的奇跡。至于在歐洲范圍,事情就不那么順利了。法國實際上是因為承接英國的現代建國進路,而與本土的政治與文化發生直接沖突,因此不得不付諸激烈的政治革命,并由革命領袖集團開創嶄新文化統緒,來制造一個嶄新國家和嶄新文化,并使之相互匹配。但很顯然,在文人政治思維的作用下,意識形態化的辭藻,橫空出世的文化理念,完全不足以營造出現代建國所需要的文化機制。結果,不是文化與政治在現代建國中的雙贏,相反造成文化與政治在建國進程中的雙輸。守成不足,創新有馀,結果可悲可嘆。德國的情況正好與法國相反。德國人畏懼疾風暴雨的革命與革命文化的搭配方案,選擇了一種守護既成秩序、膜拜國家權力的保守建國進路。結果同樣是慘不忍睹的建國敗局:不斷肆虐的專制主義,讓德國人深陷國家崇拜而不能自拔,最后只能讓希特勒將德國引向政治深淵,在幾乎亡國的處境中被加予現代國家機制,如此才勉強坐實在現代國家的平臺上。

《自戀主義文化:心理危機時代的美國生活》
英國不可學,法、德不可期。缺乏國家歷史積淀的美國,創造性模仿英國而迅速躋身現代國家行列。但美國也不是其他國家所可以效仿。這不僅是說美國明顯例外,而且是說美國幸運地出現了一批旨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領袖集群,他們在政治觀念、制度理念、民主生活方式上都能表現出一種因勢利導的建國才能,成為往古今來罕見的、既具有公心又能靈巧施展政治家技藝的建國之父。這種幸運本身,只有在例外論的解釋中才得以自洽。盡管對美國例外論的解釋,似乎堵塞了其他國家像美國那樣迅速創制現代國家的道路。但不能不承認,美國經驗即使不是完全例外的,起碼也是很難模仿的。至于法國和德國的狀況,確實不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原因很簡單,急驟革命不僅無法讓國家落定在規范平臺,而且后續難題之多,出乎人之意料。法國不僅沒有在革命中縮短建國進程,相反似乎明顯拉長了建國的時限,付出了更為高昂的建國代價。至于德國,扭曲的文化理念、甚至畸形的文化自戀,①文化自戀是各種自有源流的文化體系無可避免的文化心理定勢。這是一種文化體系之能自我維持而不至于崩解的必需。但是,如果一種文化體系完全陷入文化自戀陷阱,以至于拒絕開放的文化交流,拒斥文化更新,那么,這一文化體系就會自毀前程。參見[美]克里斯托弗·拉什《自戀主義文化:心理危機時代的美國生活》,陳紅雯等譯,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1~5頁。帶給德國人至今尚難克服的國家觀念障礙。好在德國從未成為世界范圍的現代建國典范,因此其惡性影響尚未擴展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這樣一來,似乎堵死了其他國家走向現代國家的進路?那也未必。如果設定現代建國避走極端的前提,即:既不嘗試像法國那樣借助激進革命鍛造新國家與新文化,因此將政治手段從諸種社會要素結構中抽離出來,作為建國的唯一倚重;也不嘗試像德國那樣自陷傳統文化窠臼,陷入一種文化自戀主義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為文化能夠將國家從專制中拯救出來,那么,一個國家是可以走上一條健康現代建國道路的。因為“叩其兩端,執兩用中”,就可以凸顯一條激活既有文化資源,限定革命建國目標,構造規范現代國家的建國之路。如果進一步將這樣的努力限定在后起現代國家的范圍,那么,革命建國與文化建國既然都是此路不通,那么,這些國家尋求一種雙向著力的建國進路,在不疾不徐的嘗試中,實現現代建國目標,也是可以期望的。盡管這樣的說辭有相當的烏托邦色彩,但也不是完全的向壁虛構。因為像非西方的國家如日本那樣,就走通了一條類似的現代建國道路。盡管日本也付出了像德國一樣的代價,但從結果上看,日本的文化傳統與政治建制,今天可算是相得益彰,對其維持一個民主政體的國家建制,發揮了堪稱適配的作用。如果說日本不是一個西方國家,而是一個西方化國家,而且僅僅是一個孤立個案,似乎不足以用來證明現代建國中重視文化而不至于操之過急,慎重建國而不聳動革命的原則,更不足以用來證明巧用文化資源與政治手段促進現代建國的話,那么,拋開這一個案,進入一種政治理論的分析,仍然可以凸顯一種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的適宜進路。
設定建構現代國家是所有尚未成為這一類型國家的國度都必然經歷的舉國大考,那么,這些國家在積聚現代建國的所有重要資源的時候,都需要審慎處理既成的文化狀態與建構的新型國家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避走法、德兩國的極端,是一個首要原則。這是失敗的提醒,而非成功的召喚;懂得仿效英美的困難,是一個接著需要重視的問題。這是成功的自限,而非失敗的警懼。在此原則之下,促成一種借重政治因素建構現代國家但不尋求革命,依托文化動力但不自賤自戀的雍容氣度,并且不求兩種狀態的理想值,僅求兩種狀態的持續性,那么,營造一種有利于推進現代建國進程的態勢,是完全可能的。為此,需要那些致力建構現代國家的國度,盡力做到下述三點:
首先,營造一種有力促進社會進步的文化變革態勢。文化本是長期積淀的結果,絕對不可能是當下急促功利需要的產物。因此,在現代建國需要文化提供動力的情況下,一者不能將文化作為工具化的手段使用,避走法國大革命那種以革命塑造文化,亟欲將文化作為政治時局需要的強有力手段。二者不能將文化作為抗拒社會變革的手段,從而窒息文化的時代生機,戕害文化發展的長遠未來。因此,需要避免像德國那樣將其傳統文化作為抗拒規范現代的手段,妨礙現代建國順利推進。在激進的文化革命與保守的文化僵化之間,以現代建國為軸心,推動形成一種促進社會變革的活性文化狀態,對文化與政治雙方都具有好處,進而讓兩者都能成為現代建國的強勁動力。就此而言,一個致力建構現代國家的國度,需要在保守文化還是變革文化之間做出決斷,著力防止文化陷入停滯,保證文化發展具有活力。
論者指出了具有活力的進步文化與僵化死寂的停滯文化之間的十個重要差別。“1.時間取向:進步文化強調未來;停滯文化強調現在或過去。面向未來,意味著一種進步的世界觀—影響自己的命運,讓美德在今生得到回報,主張雙贏的經濟學。2.工作:它在進步文化中是美好生活的關鍵,而在停滯文化中卻是一種負擔。在進步文化中,工作構成日常的生活:勤奮、創造性和成就不僅帶來經濟上的回報,而且帶來安慰和自尊。3.節省:它在進步文化中是投資之母,也是財政保障之母;它在停滯文化中卻被視為對‘平等’現狀的威脅,人們往往認為一方之所得即為另一方之所失。4.教育:在進步文化中是進步的關鍵,在停滯文化中卻只對精英階層重要。5.在進步文化中,功績是地位上升的關鍵;在停滯文化中,地位上升是靠關系和家族。6.社群:在進步文化中,人們彼此之間的認同和信任半徑超出家族范圍而達到廣大社會:在停滯文化中,家族局限著社群,認同和信任半徑狹小的社會較易出現腐敗、偷稅漏稅和任人唯親,較難推廣慈善活動。7.在進步文化中,道德準則一般比較嚴格。在透明度國際的‘腐敗感指數’中,發達民主社會(除了比利時、臺灣、意大利和韓國以外)均名列前二十五位之內,而前二十五位之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只有智利和博茨瓦納。8.在進步文化中,人們普遍期待得到正義和公平待遇,不以個人感情為轉移。在停滯文化中,公正待遇跟地位上升一樣,往往取決于你認識什么人和付得起多少錢。9.權力:在進步文化中趨向平行和分散,在停滯文化中則趨向垂直和集中。……10.世俗生活:宗教機構對公民世俗生活的影響,在進步文化中不大,而在停滯文化中往往很大。進步文化中,宗教等方面的不同意見受鼓勵,而在停滯文化中受鼓勵的是思想正統和順從。”①[美]勞倫斯·哈里森:“促進社會進步的文化變革”,載《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第429~430頁。這是一個基于扎實的實證研究得出的比較結論。無疑,這樣的結論更多屬于類型學意義。但對為現代建國聚集文化資源的國度來講,不能不從中看到文化選擇的重要性。凡是有助于現代建國的文化,一定是尋求進步的文化。在這里,保守文化傳統不是一種僵化的態度,而是為了讓文化傳統保持活力的方式。凡是阻礙現代建國的文化,一定是陷入停滯的文化。在這里,保守傳統文化是一種僵硬的姿態,不是一種真正捍衛傳統生命力的主張。正是因為如此,那些在時間、工作、節省、教育、升遷、社群、道德、公正、權力以及生活狀態上悖反呈現的態勢,凡屬積極的,就是進步的、變革的、進取的文化,都有力于推進現代建國;凡屬于消極的,就是停滯的、僵化的、退守的文化,都會阻礙現代建國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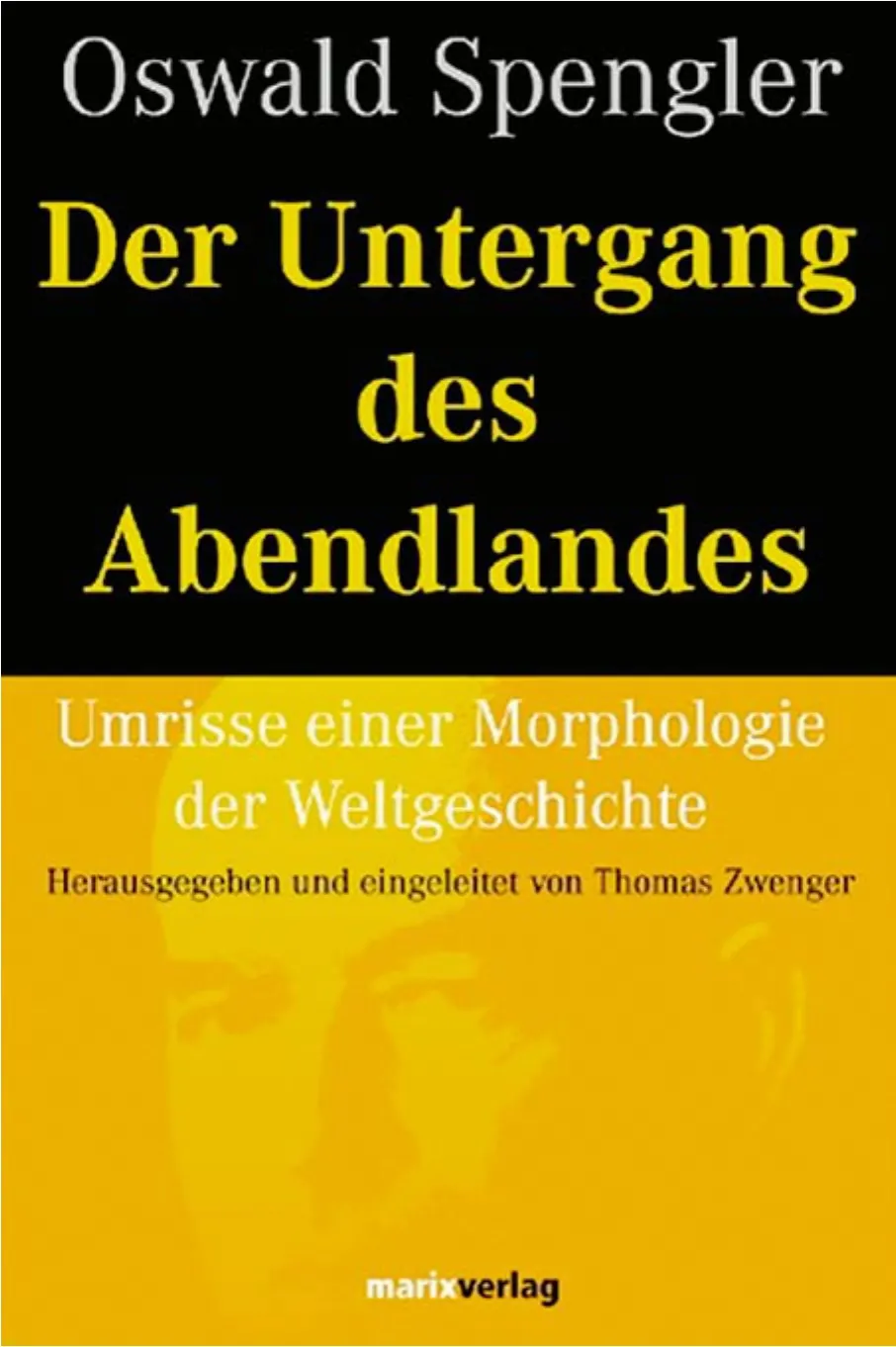
《西方的沒落》

《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
其次,逐漸創制一種有利于分權制衡的政治妥協機制。如果說營造一種積極進取的變革文化氛圍,是為現代建國提供充分的文化動力的話,那么,創制分權制衡的政治妥協機制,這是為現代建國積累制度資源。分權制衡,并不來自于掌握國家權力人群的良心發現,也不可能一腋成裘、一蹴而就。集腋成裘,才能解決現代國家制度資源的短缺問題;漸進推進,才能穩妥實現現代建國目標。因此,一個嘗試建構現代國家的國度,需要在政治上絕對杜絕好勇斗狠的政治風氣,促成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尊重、相與協商,并就此達成國家基本價值與基本制度的高度共識。為國家確立基本的規則,達成憲法共識,頒布實施憲法文件,將國家權力與公民行動都約束在憲法之下。借助于這種立憲民主的政治運作機制,反過來促進社會公眾以一種容忍、協商、妥協的方式,進入國家政治生活世界,從而習慣與國家權力討價還價,達成一致。不至于讓公眾陷入失望、乃至于絕望境地,隨時隨地表現出一種決絕的政治姿態,以至于跟國家權力勢不兩立、魚死網破。如此就讓國家權力與社會公眾、文化因素與政治因素處在惡性循環之中。尋求國家權力與社會公眾、文化發展與政治進步之間的良性互動,需要趨近于立憲民主政體的有序進展,來為社會公眾的國家認同、文化的善性積累創造條件。那種以政治上的絕對不妥協造成的、彌漫于全社會的對抗氣氛,是極不利于現代國家建構的。一旦國家陷入權力與社會的直接抗衡,并且雙方都不愿意后退一步,那么就只要訴諸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激進方式來重構國家與社會,國家就此陷入長期的動蕩不安。進而言之,在圍繞國家權力是否有序運行的政治爭端上,應當將其嚴格限定在政治世界之中,而不能隨意將之擴張到社會世界范圍。避免涉及國家權力交替的政治爭端泛化為社會公眾的全面對抗,構成現代建國不至于泛化為徹底革命的災變之前提條件。如此,政治的歸政治、文化的歸文化—將政治事務限定在國家權力的和平、有序、按周期交替上,將文化事務限定在社會領域的漸進創制上,從而保證政治與文化兩種因素都能綿綿供給現代建國的優質資源。
再次,以國家的繁榮帶動國民心態的積極向好發展。國家的實際處境是向好還是向壞的發展,直接影響到一國的國民心態與從眾行動。簡言之,當國家發展向好時,國民心態是健康向上、積極進取的。當此狀態下,國民不僅能夠主動介入國家事務,成為國家良性發展的動力,而且也能夠忍受一時的困難,與國家權力方面共擔、共謀,推動國家克服困難,走向一個新的發展境地。當國家發展向壞時,國民心態即是扭曲的、心地陰郁的,國民不僅拒絕參與國家決策,不愿貢獻自己的心力與智慧,而且不愿為國家分憂、擔責,因此讓國家權力顧此失彼、陷入混亂。國家的繁榮,就是國家向好發展的明顯標志;國家的貧困,則是國家向壞變化的顯著象征。這兩種狀態下的國家境況,是大不相同的。“貧困能損害人的志向、希望和幸福。在這方面,貧困的影響無法衡量,卻感受得到。大量的文獻表明了較高的收入有助于積極進取,寬厚待人,支持公民自由權,對外國人持開放態度,對下屬持正面關系,養成自尊心,對個人能力有信心,愿意參與社群活動和國家事務,保持人際信任,以及滿意于自己的生活。”①[美]邁克爾·費爾班克斯:“改變國民的心態:致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載《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第391頁。雖然說這樣的比較斷言有可能失之于簡單化,但總體結論不會乖離真實狀態太遠。
而為了實現國家的繁榮,有必要促成一個旨在繁榮國家的社會政治氛圍。為此,有必要展開國家與社會各方營造健康國民心態的工作。圍繞這一工作,需要國家權力方面制定有效的發展戰略,推行有效的變革舉措,形成自覺的變革緊迫感,理解戰略的范圍并加以適當的選擇;同時,需要社會各方形成高瞻遠矚的眼光,建立新的關系網絡,廣泛傳播新的思想;進而,在國家權力與社會公眾之間,促成富有成效的聯合,讓大家及時獲知成功的消息,促成一種變革的體制,評估變革的得失并形成變革的共識。②參見[美]邁克爾·費爾班克斯:“改變國民的心態:致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同上書,第392~404頁。如此一來,激發國家權力體系與社會公眾各方投入促進國家繁榮的進程,達成政治權力與社會文化兩種要素積極互動,有力促進現代國家的興起興盛、持續走強。
有論者對文化、傳統與現代建國的關系做出過先知般的預言,盡管其表達所包含的反對現代大眾民主、專家政治的意向非常明顯,甚至飽含一種反現代的英雄主義沖動,但啟發人們從傳統中透觀未來的提點,則不無教益。“許多古老而偉大的傳統遺留下來,許多古老而偉大的歷史‘道理’和經驗繼承下來,注入了二十世紀各民族的血液之中,獲得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力量。對我們而言,創造性的虔誠,或(用一個更基本的術語說)脈動,從最初的源頭傳到我們,只是依附在那些比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更為古老的形式上,這些形式是生長出來的,而不是制造出來的。它們的每一種殘馀,不論多么微不足道,只要能在任何一種自足的少數派的存在中保存下來,不久就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價值,并將引起至今仍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歷史效果。舊的君主政治、舊的貴族政治、舊的上流社會的那些傳統,只要它們仍健康到足以抵御職業的或專家的政治,只要它們還保有榮譽、克己、紀律、對偉大使命的真正意識(亦即,種族品質和訓練)、責任感和犧牲精神—它們就能成為把整個民族的存在之流結合起來、使其比這個時代活得更久的中心,并能使這存在之流在將來有其歸宿。‘合乎狀態’就是一切。我們將生活在一種偉大文化有史以來最艱難的時代。保有其形式的最后的種族、最后的活生生的傳統、最后的具有這兩者作為支撐的領袖,將作為勝利者度過這個時代并繼續前行。”③[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二卷·世界歷史的透視》,吳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405~406頁。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信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