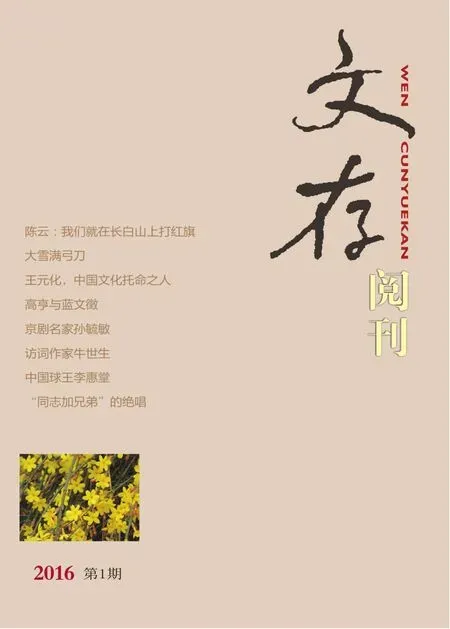中國文化托命之人
□許紀(jì)霖
?
中國文化托命之人
□許紀(jì)霖
王元化

王元化先生不僅留下了不朽的文字、永恒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精神,一種擔(dān)當(dāng)了文化傳承的精神。在今天這個不再有英雄的時代,卻依然需要先生那樣的“文化托命之人”。
過去的我,有一個習(xí)慣,每年的11月30日都會從日程中留出來,留給王元化先生。這天是先生的生日,這天晚上,與先生最親近的學(xué)生、朋友都會相聚一堂,為老人家祝壽。起先是輪流做東,后來先生年歲大了,走動不便,便固定在他常住的慶余別墅小餐廳里。順便說一下,我妻子的生日也是11月30日,對我個人來說,這很有一點家宴的感覺。
先生是1920年生人,與我父親同歲。家父走得太早,一次意外的腦溢血,就離開了人世。我是一個遺腹子,父親只在照片上,在家人的描述中,習(xí)慣成自然,也因此形成了我特立獨行的性格。直至在我四十歲的時候,遇見了先生。因為心靈的相契,漸漸走得很近,我感覺自己似乎有了一個父親,一個精神意義上的父親——雖然在先生生前,我從來沒有向他袒露過內(nèi)心的這一秘密。
我不想用慈祥來形容先生,那是先生給外人的形象。先生的晚年,慶余別墅那個名為“清園”的小小客廳,每天先生被各路訪客包圍簇?fù)恚舯娦枪霸隆O壬腥烁竦木薮篦攘Γ蠹页缇此矚g聽他談學(xué)問、論思想。他也來者不拒,有教無類,越到晚年,越喜歡熱鬧,對陌生客有求必應(yīng),從簽名題詞到介紹關(guān)系,給人以如浴春風(fēng)之感。
不過,對身邊熟悉的人,先生卻有另外的一面,他很嚴(yán)格,嚴(yán)格到有時不盡人情。我與先生來往多了以后,他對我的要求逐漸變得嚴(yán)厲,記得九十年代末,我曾經(jīng)一度迷戀文化評論,報紙副刊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我的名字。先生每次見到我,都疾言厲色地批評我:“你少寫報屁股文章!好好做你的知識分子研究!”我知道他對我有所期待,但又有點失望。但以我自以為是的個性,很難聽進(jìn)先生的話。倒是有一次在閑談中,先生講自己的心得體會,說:“做學(xué)問要能夠沉得住氣,善養(yǎng)大氣。如果一有點感覺,迫不及待就放掉了,最后是成不了大氣的。”我心頭一驚,恍然有悟,從此收斂了許多。
與先生走得比較近的學(xué)生、晚輩,大都可能都被先生罵過。有一天上海某出版社老總,突然很沮喪地打電話給我,說先生為了一本書的排版和裝幀問題,對他大發(fā)雷霆。我知道先生眼界很高,有完美主義的癖好,容不得一絲瑕疵。我對這位朋友說:“恭喜你,先生已經(jīng)不把你當(dāng)外人了!不過他不會放在心里,說過就過了,老兄千萬不要生氣啊。”
到了晚年,由于治病打針有副作用,身體里的激素失衡,先生的脾氣變得急躁,時有爆發(fā)的時候。但先生的難得在于,事后意識到自己過分了,會自我反思,有所補(bǔ)救。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間里打了幾個電話,聲音干擾了他寫信,他對我發(fā)了一通火,讓我立即走人。那個時候我已經(jīng)非常了解先生,覺得是自己的不妥,沒有放在心里。沒有想到,第二天先生專門打電話給我,對我說:“對不起,我昨天脾氣大了一點,向你道歉。”我驀然驚呆,不知說什么好,為先生的誠懇感動。人常常會犯錯,亦會失態(tài),圣人亦是如此。然而,德性高尚之人,乃是能夠直面自己,承認(rèn)錯失,尤其在晚輩面前,更是難得的德性。試問天下諸君,又有幾人能夠企及?
先生是圣人,亦是凡人,亦圣亦凡。圣人可尊而不可學(xué),凡人則不值得學(xué)也。但亦圣亦凡的先生之于我,則是一個令我敬畏又可親近的精神父親。西諺云:“仆人眼中無英雄”,這話不錯。但我更喜歡俄國的一句諺語:“鷹有時候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yuǎn)不可能像鷹飛得那樣高。”
先生離開我們七年了,他在世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他對于我與這個世界有多么重要。但在先生告別儀式結(jié)束的瞬間,當(dāng)我看到平時非常熟悉的身影被推走送去另一個世界,永遠(yuǎn)不再回來的時候,我突然泣不成聲,無法自己,感覺內(nèi)心崩塌了很大一塊。我終于意識到自己失去了精神的父親,那是我人格上的引路人。他越是離我遙遠(yuǎn),我越是感覺到他的存在。有時候當(dāng)自己無法在兩難困境中做選擇的時候,我常常會這樣想:假如先生在的話,他又會如何做呢?以我對先生的了解,我知道他會如何做,于是我也就豁然開朗,知道自己該選擇什么了。
先生走了之后,對我來說,這個世界寂寞了許多。這種感覺,不僅屬于個人,也屬于先生生前所在的這所城市。上海的知識界,從此再無精神領(lǐng)袖,中國的知識界,也少了一位旗幟性的人物。先生離開我們越久,越加感覺他存在的意義。我常常在想,王元化先生,對于中國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我曾經(jīng)將他與李慎之一起,視為中國“最后一代士大夫”。所謂的“士大夫”,乃有著家國天下情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視天下為己任。但他所擔(dān)當(dāng)?shù)模烤故鞘裁矗渴亲杂芍髁x嗎?在世紀(jì)之交,有“南王北李”之說,有人認(rèn)為王元化與李慎之是一南一北自由主義的精神領(lǐng)袖,但將先生定位于自由主義者,寬泛地說,也不錯,在他的身上,的確具有蔡元培、胡適式的自由、寬容和多元,對民主社會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倘若簡單地將先生定位為某某主義,似乎很違背他的初衷與原意,他的生前,非常不滿自己被劃為某個主義的符號,反對打大旗、搶山頭,他說:“我不想?yún)⒓邮裁椿ブM、合作社,我一直是單干戶!”這個單干戶,乃是在各種對立的思想與潮流面前,不輕信,不盲從,不相信任何版本的“某某主義才能救中國”。他奉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信條,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么,不喜歡簡單地歸隊為某個類。雖然經(jīng)過痛苦的反思,先生從崇拜魯迅轉(zhuǎn)向佩服胡適,但假如只是將他解讀為某種形態(tài)的自由主義,顯然又將他思想的豐富性、復(fù)雜性和矛盾性遮蔽了,將他超越各種主義的開放胸懷說小了。

1981年,王元化在上海寓所。
這幾年,我一直形容自己是“思想界的蝙蝠”。其實,這個說法最早來自于先生。他生前對我說過:蝙蝠是哺乳性鳥類,但它一直很尷尬,不受歡迎。去鳥類那里開會,鳥兒們對它說:你是哺乳動物,不屬于我們。它去參加哺乳動物大會,又被趕了出去,視它為異類。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異常堅決地說:“我就是蝙蝠,我愿意做到處不受歡迎的蝙蝠!”我知道,先生自稱蝙蝠,是有點悲涼的,因為晚年的他,多少受到各方面的不待見。原教旨派因為他是思想解放運動和新啟蒙運動的旗手,而視之為“自由化思潮”的頭面人物,而啟蒙陣營那邊又因為先生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反思,肯定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又以為他發(fā)生了“轉(zhuǎn)向”,成為章太炎式“屁股向后轉(zhuǎn)”的保守主義者,時有冷嘲熱諷。在激進(jìn)與保守的二元思維之中,先生成為無法歸類之人。但無法歸類、不愿站隊,正是先生的本意所在,當(dāng)眾人紛紛挑邊站隊、抱團(tuán)取暖的時候,孤身群外,側(cè)身而立,“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很需要一點勇氣的。
先生在“一二·九”運動中加入革命,在日本人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提著腦袋干地下工作。在仕途最得意的時候被打成胡風(fēng)分子,文革后復(fù)出位居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未滿一屆又提前下野。長期豐富的黨內(nèi)經(jīng)歷、半個世紀(jì)的坎坷人生,令先生的政治閱讀能力遠(yuǎn)遠(yuǎn)超乎于一般自以為“懂政治”人之上,每每聽他解讀錯綜復(fù)雜的黨內(nèi)歷史,都有一種庖丁解牛、老吏斷獄般的快感。先生不僅是帷幕中人,而且對歷史、哲學(xué)與人性有深邃的理解,因此他的觀察和思考有高度,也有深度。那一代人的政治情結(jié)本來是很濃厚的,他們的一生都與政治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他們熱烈地投身于政治之中,政治又內(nèi)化為自己的生命,成為一代“政治人”。比如李慎之先生就是這樣,晚年他有強(qiáng)烈的文化關(guān)懷,但無寧說,對文化的關(guān)懷是從屬于政治目標(biāo)的。
然而,元化先生在那代革命家之中,似乎有點另類。他的父親是清華外文系教授,他從小在清華園長大,耳濡目染,打下了書生的底色,革命隊伍中的知識分子,其實有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有文化關(guān)懷的“游士”,但充滿了政治意識與熱情,另一種是有革命情懷的知識人,雖然投身政治,但骨子里還是一個文化人。先生屬于后一類,他年輕的時候是個文青、乃至憤青,對魯迅頂禮膜拜,北平淪陷后逃難南下,懷里藏著的,是一張魯迅的畫像。來到上海之后,在江蘇文委做地下工作,以青年理論家在黨內(nèi)小有名氣。建國之初,三十歲出頭就出任上海文藝工作委員會文學(xué)處處長,用先生的好朋友、夏衍的秘書李子云的話說:王元化當(dāng)年飚得很!但突如其來的反胡風(fēng)運動,將他打到十八層地獄之下,也打回了書生的原點。先生讀書最多的時期,是1956年到1966年那十年。有郭紹虞這樣的學(xué)術(shù)大家保護(hù)他,又有熊十力等多位大師指導(dǎo)他,他精讀黑格爾,專研《文心雕龍》,翻譯西書,學(xué)術(shù)基礎(chǔ)因此打得非常厚實。有一次先生與我閑聊這段經(jīng)歷,我對他說,您是因禍得福!假如當(dāng)時您沒有成為“胡風(fēng)分子”,到文革才被打倒,多做十年的官,您在學(xué)術(shù)上大概就被毀了。先生點點頭,頗同意我的看法。他說:“人在陷入困境的時候,只要不自暴自棄,是自我完善的最好時光。”
先生的性格里面,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兩面,但究其底色,政治是用,文化是體,是他的終極關(guān)懷。到了生命的晚年,特別是2004年之后,他似乎已經(jīng)看破一朝時政。每次去看先生,告訴他一些傳聞,先生似乎都心不在焉,興趣索然。反而每每抓住我,與我談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大問題。先生之憂慮,乃是感到這個世界出了大問題,問題不在政治,也不在經(jīng)濟(jì),而是最深層次的文化。當(dāng)代人沉湎于物質(zhì)、沉湎于世俗而不自知,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世界陷落了,世界的意義、人生的價值無人關(guān)心了,這世界不再令人著迷。先生常常半夜醒來,再也睡不著,為此而心焦,憂慮兩三千年的世界軸心文明,包括中國文明、古希臘文明、基督教文明,是不是會毀在我們這一代人手里?
當(dāng)我追隨先生的憂思,思考中國與世界大問題的時候,我逐漸明白了,先生對于中國來說,乃為“文化托命之人”。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世界文化,在抽象的精神背后,都有其肉身的寄托,從而顯現(xiàn)出文化的主體性,這個文化主體,就是自覺擔(dān)當(dāng)和傳承文化的那些人,故曰“文化托命之人”。文化就是通過一代代托命之人薪火相傳、舊邦新命,得以創(chuàng)造性傳承的。
余英時先生在《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中,分析了“文化托命之人”的遠(yuǎn)古源頭。在先秦軸心文明誕生之前,文化主要保存在巫師那里,巫師知曉天命,唯有他才能與天溝通。但巫師缺乏文化的自覺與人的自覺,既匍匐于天命,又從屬于政治權(quán)力,沒有從宇宙、王權(quán)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知識人。公元前五百年的軸心文明大突破,誕生了孔子、老子,最早的“文化托命之人”出現(xiàn)了。這些文化先知與巫師們不一樣,已經(jīng)獨立擔(dān)當(dāng)了文化,文化系統(tǒng)與宇宙系統(tǒng)、權(quán)力系統(tǒng)發(fā)生了分離,成為了獨立的道統(tǒng)。孔子說:“士志于道”,這個“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道不再神秘,在天命面前人也不再被動,而具有了能動性。天道與人道,天理與人心已經(jīng)相通,文化來自于天命,又獨立于天命,知識人成為了“文化托命之人”。
張灝先生強(qiáng)調(diào),中國古代有雙重權(quán)威,天子代表政統(tǒng),士大夫代表道統(tǒng),雙重權(quán)威皆來自天命,究竟孰高孰低?儒家認(rèn)為道統(tǒng)高于政統(tǒng),文化高于政治,一代代中國士大夫雖然承擔(dān)著“為生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人間使命,但是比政治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使命,是“為天地立心”、“為往圣繼絕學(xué)”。
這種將自身與文化融為一體、擔(dān)當(dāng)文化天職的精神自覺,到了近代中國,為王國維、陳寅恪、梁漱溟等知識人所繼承。1927年,當(dāng)北伐軍兵臨城下,王國維投湖自盡,一時猜測紛紛,許多人認(rèn)為王國維是殉清而死。但王國維在清華國學(xué)院的同事陳寅恪敏銳地指出,王國維并非殉清、乃是殉中國文化。他在悼念王國維的文章中如此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必受苦痛亦愈甚。”陳寅恪與其說是解王國維,不如說是夫子自道,表明心跡,自己立志以中國文化為己任,成為“文化托命之人”。
先生對清華有揮之不去的感情,先生所認(rèn)同的清華,不是那種校友或子弟式的母校崇拜,而是純粹精神性的,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他所理解的清華靈魂所在。從王國維、陳寅烙,到王元化,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傳統(tǒng):為文化之憂而憂,自覺地?fù)?dān)當(dāng)文化復(fù)興的使命。
凡是“文化托命之人”,內(nèi)心都有一些狂氣,熊十力、梁漱溟狂在臉上,王國維、陳寅恪與先生狂在心里。但他們都狂而不妄。抗戰(zhàn)時期的梁漱溟,香港淪陷之后步行逃亡回內(nèi)地,一時沒有消息,輿論驚呼:梁先生失蹤了!幾個月以后在桂林出現(xiàn)了,大家對梁漱溟說,我們都在為你擔(dān)心。梁漱溟頗不以為然,說我怎么可能會死?我如果死了,天地將為我變色、歷史將為我改轍,那是不可能的!梁漱溟自認(rèn)擔(dān)當(dāng)天命,天命擔(dān)于一身,天理在我心中,故無所畏懼,敢于在天廷向天子諍言。假如沒有一點擔(dān)當(dāng)天命的狂氣,一般凡夫俗子是扛不住的。
陳寅恪與先生在“有所為”上不及梁漱溟,但他們一生都做到了“有所不為”,哪怕泰山壓頂,也不肯隨聲附和,不說一句敷衍的假話。先生因為胡風(fēng)案件被隔離審查的時候,組織對他說,你只要承認(rèn)胡風(fēng)是反革命,你就解脫了。但先生偏偏認(rèn)死理,不肯說違心話。他回答:“說胡風(fēng)有思想上的錯誤,我承認(rèn),但說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沒法認(rèn)。”因為不肯說違心話,本來不是胡風(fēng)小圈子的王元化,被認(rèn)為態(tài)度最惡劣,而列入胡風(fēng)分子,被打入另冊。
孔子曰:“狂者進(jìn)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進(jìn)取”之狂者固然可敬,但一生守住“有所不為”的狷者,豈非與一時之“有所為”同樣難得,甚至更難?先生很喜歡孟子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家客廳一直掛著先生為我書寫的這三句話。三個“不能”,皆是狷者之道,但唯有自覺意識到“文化托命之人”,背后有一個超越的信念支撐。才能守得住人格的尊嚴(yán)。
說到以文化復(fù)興為己任,不要以為這些“文化托命之人”念念在茲的文化,只有中國,而無世界。陳寅恪有言:“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xué)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句話乃是文化自覺之最準(zhǔn)確表達(dá)。是的,陳寅恪、王元化這些“文化托命之人”,固然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但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文化,不是封閉的,與世界文化相對抗;而是開放的,盡量“吸收輸入外來之學(xué)說”。他們是文化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天下主義者,關(guān)懷整個人類的命運,思考整個世界的文化。
與陳寅恪先生一樣,王元化先生對中國古典學(xué)術(shù)有很深的造詣,義理、考據(jù)、詞章皆有所通,同時對西方學(xué)問也下過苦功,黑格爾、莎士比亞、俄國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都是他精通的領(lǐng)域。我記得,先生對研究中國古典的學(xué)生,時時叮囑他們英語一定要學(xué)好,多讀西方的經(jīng)典;而對他欣賞的從事西學(xué)的有為學(xué)者,又常常感嘆:他要是能懂一點中國的歷史與思想,就不得了!像先生這樣從民國過來的一代學(xué)者,絕無中學(xué)、西學(xué)的門戶之見,他們的視野是超越中西、打通古今。古今中西,皆在法眼之內(nèi)、掌握之中。在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在《讀書》雜志發(fā)表過追憶先生的文章,篇名用的是先生的一句話:“我是十九世紀(jì)之子。”十九世紀(jì)是博大的,開放的、多元的,東海西海,心同此理,不是東風(fēng)壓倒西風(fēng),也不是西方壓倒東風(fēng),而是古今中西,八面來風(fēng)。先生所心儀的十九世紀(jì)俄國文學(xué)是如此,晚清的康有為、梁啟超、嚴(yán)復(fù)、章太炎這些大師們,關(guān)懷的也是超越古今中西的人類共通的文化命運,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在上個世紀(jì)末,思想界流傳“南王北李”的同時,在學(xué)術(shù)界還有一個“南王北錢”的說法,這兩種說法的同時并存,表明先生跨越了思想與學(xué)術(shù)兩界,大概很少有誰能夠像他那樣,在學(xué)術(shù)上與錢鍾書比肩,思想上與李慎之各領(lǐng)風(fēng)騷,雖然先生對這兩個說法都不以為然。九十年代以后,思想與學(xué)術(shù)斷裂,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部分循入學(xué)院,甘為某細(xì)微領(lǐng)域的專家,孜孜于學(xué)科內(nèi)部的雕蟲小技,不再有超越碎片化的大關(guān)懷;另一部分則活躍于媒體,成為職業(yè)型的“知道分子”,但常常“公共太多、知識太少”,游談背后,無學(xué)理支撐。針對這兩種極端的分化與弊端,先生提出了“有思想的學(xué)術(shù)”與“有學(xué)術(shù)的思想”,意思說,學(xué)問者要有思想的關(guān)懷,思想者須有學(xué)理的背景。學(xué)術(shù)與思想本來就不該兩分,合則共美,分則兩傷。先生自己所追求的境界,正是“有思想的學(xué)術(shù)”與“有學(xué)術(shù)的思想”。他一生寫了不少學(xué)術(shù)文章,這些文章絕對不是純粹的談玄理、玩考據(jù)、弄詞章,背后都有很深刻的關(guān)懷和思考。只是有些明顯,有些隱晦,一般讀者看不出來而已。他晚年也喜歡用訪談的方式發(fā)表自己對中國與世界、文化與社會的看法,但這些談?wù)摰谋澈蠖加兴綍r積累的學(xué)理背景,有歷史的深度和跨文化的廣度。
上個世紀(jì)末的上海,是一個大家如云的文化大都會。我當(dāng)時就特別注意到,不少學(xué)問大家,見到先生時都非常尊敬,可以發(fā)現(xiàn),那是一種從內(nèi)心發(fā)出的由衷敬佩。假如按照專業(yè)成就,馮契先生的哲學(xué)、章培恒、錢谷融先生的文學(xué)、陳旭麓、朱維錚先生的史學(xué),可能都在先生之上,為什么他們還是在學(xué)問上那樣真誠地佩服先生呢?一開始我不太明白,后來慢慢清楚了,因為先生是跨學(xué)科、打通文史哲的大師。他就像一個體操全能冠軍,在單項成就上可能不及馮契、章培恒、朱維錚等先生,但他的研究是將義理、考據(jù)和詞章貫通了的。
中國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雖然有經(jīng)史子集之分,但四部之學(xué)從來都是分類不分家,學(xué)問上都是打通了來研習(xí)的,然而到近代之后從西方借來的學(xué)科分際,使得文史哲之間、人文學(xué)科與社會科學(xué)之間壁壘森嚴(yán),即使在同一學(xué)科內(nèi)部,也是互為溝壑。有些名氣很響的專家,只要一出本學(xué)科,便天下無人識此君,而大部分學(xué)者的活動空間,僅僅限于二級學(xué)科乃至三級學(xué)科的狹隘領(lǐng)地。先生生前是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中國文藝批評專業(yè)的博士生導(dǎo)師,還是國務(wù)院第一、二屆中文學(xué)科的評議組成員,但我聽到他講過好幾次:“我又不是搞文學(xué)的,我是一個雜家!”
我的理解,這個“雜家”,并非學(xué)無所本的文人之學(xué),乃是貫通文史哲的大家。這乃是五四一代的精神遺傳,與他所崇敬的魯迅與胡適在風(fēng)格上有相通之處。如果說魯迅是文學(xué)家,魯迅先生聽到以后必定不屑一顧,他給兒子留下的最后遺囑就是“不可去做空頭文學(xué)家”。胡適先生是什么家?也很難定位,“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寫了半部,“水經(jīng)注”做了一半,“紅樓夢考證”開了一個風(fēng)氣,如果按照專業(yè)的成就,都比不上他的學(xué)生輩馮友蘭、顧頡剛和俞平伯。不過胡適是一個“但開風(fēng)氣不為師”的跨學(xué)科人物。1953年大陸為了批判胡適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xué)術(shù)思想,在幾乎所有的學(xué)科里面都對他發(fā)動了圍剿: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社會學(xué)、政治學(xué)、法學(xué)……幾乎所有人文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的最頂尖學(xué)者都被迫站出來批胡適,肅清其在自己專業(yè)上的流毒,在學(xué)術(shù)上與他劃清界限,足見胡適在民國學(xué)術(shù)界巨大的跨學(xué)科影響。對于元化先生在中國學(xué)術(shù)地圖上的定位,似乎也可作相應(yīng)的理解。是的,在今天這個專業(yè)化時代,要找一個學(xué)有專攻、成就斐然的專家不算難,但要找到一位像先生那樣的學(xué)貫中西、打通古今、縱橫文史哲、對自然科學(xué)與社會科學(xué)也有所涉獵的大家,太稀罕了。

王元化(前右)和周揚(前左)等合影
先生不僅學(xué)問好,最重要的是有智慧。智慧像一把撒在湯里面的鹽,看不見,找不到,卻融化在知識里面。許多專家徒有專業(yè)知識,但缺乏大智慧,就像一鍋缺鹽的原湯,淡而無味。先生健談,縱橫天下,上下千年,思想在各個領(lǐng)域自由奔馳。記憶之好,知識之淵博,在我認(rèn)識的前輩學(xué)者之中,幾乎無人可比。但最難得的是先生的談吐中有大智慧、大見識。他的客廳經(jīng)常高朋滿座,很多人慕名前來享受智慧的沐浴。有一次我陪一個企業(yè)家去見先生,這位企業(yè)家也算結(jié)交廣泛,出門后對我感嘆說:“我見了不少省部級領(lǐng)導(dǎo),許多老干部退下來之后,世態(tài)炎涼,過去圍著他轉(zhuǎn)的人都不見了。王先生從部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后,還是門庭若市,還更熱鬧了,王先生真是一個有大智慧的智者啊!”我很有同感,權(quán)力是有保鮮期,過期就作廢,但一個人擁有了智慧,即使肉身化為泥土,文字背后的智慧,卻與日月同在。知識也會過時,但智慧將超越歲月,化為人類永恒的文明遺產(chǎn)。
先生倘若不死,明天(2015年11月30日,編者注)是九十五誕辰,我們將再次聚會在一起為先生祝壽。如今白云蒼狗,先生駕鶴遠(yuǎn)去,我們只能在先生的墓前相會了!人間再無大智者,世界也因此荒漠許多。然而,先生不僅留下了不朽的文字、永恒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精神,一種擔(dān)當(dāng)了文化傳承的精神。在今天這個不再有英雄的時代,卻依然需要先生那樣的“文化托命之人”。只要這一精神還在,中國文化就不會亡,人類命運就有希望。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xué)紫江學(xué)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wù)副所長,華東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yè)博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