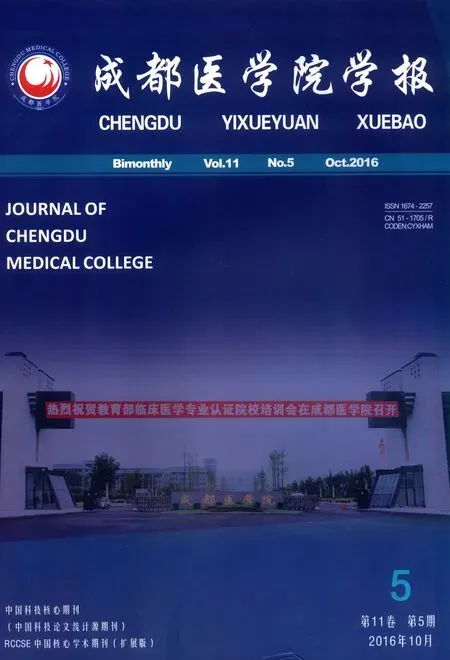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慢性肝病相互關系的研究進展*
黃思思,周 艷,左 羅,李小安
成都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消化內科,消化系腫瘤與微環境四川省高校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500)
?
·綜 述·
腸道菌群與慢性肝病相互關系的研究進展*
黃思思,周 艷,左 羅,李小安△
成都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消化內科,消化系腫瘤與微環境四川省高校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500)
肝病;腸道菌群;糞菌移植;腸-肝軸;益生菌
1 腸道菌群
人類腸道菌群種類非常復雜,其中包括大約1014個細菌,107個病毒,以及一定量的真菌、寄生蟲和古細菌等[1]。正常腸道菌群有500~1 500種不同細菌種類[2],其中絕大多數為厭氧菌。腸道菌群在人體的生理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參與機體的代謝功能、增強免疫系統及促進腸黏膜上皮細胞的發育[3]。在正常情況下,腸道菌群的種類和數量保持著動態平衡。
2 “腸—肝軸”
研究[4]表明,肝病的發生、發展與腸道菌群的變化關系緊密。腸道菌群與肝臟通過門靜脈在解剖及功能上有著密切聯系,它們的病理生理學聯系被稱為“腸-肝軸”。肝臟的門靜脈是腸道各種抗原、毒素、腸道菌群及其產物侵入的第一道防線,這種關系賦予了肝臟重要的代謝、免疫及解毒功能。腸道、肝臟及免疫系統的相互作用是確保肝臟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慢性肝病與腸道菌群紊亂的關系
慢性肝病時,20%~75%的患者會出現腸道菌群失調[5],且菌群失調的嚴重程度和肝病嚴重程度相關[6]。當肝臟受損后,其解毒功能下降,不能清除來自門靜脈的細菌及其代謝產物,如腸源性異位細菌及內毒素等;另外,某些肝病可出現腸黏膜屏障功能受損,加重細菌易位和內毒素血癥[4]。因此,腸道菌群失調與慢性肝病息息相關,可促進慢性肝病的發生發展。
3.1 酒精性肝病(ALD)
ALD是由于飲酒導致的慢性肝病。研究[7]表明,腸道菌群紊亂在ALD的病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長期飲酒導致腸道菌群紊亂、腸黏膜通透性增加,促使腸道菌群及其產物異位,促進肝臟促炎癥細胞因子聚集,引發炎癥級聯,進而加重肝損傷。研究[8]發現,飲酒者腸道菌群較正常可發生改變。Yan等[9]采用動物模型發現,ALD模型的腸內需氧菌和厭氧菌都過度生長,且肝細胞出現了脂肪變性及炎癥反應,證明酒精與腸道菌群紊亂之間的關系。近期,有1項研究[10]給無菌小鼠分別移植了伴有肝臟炎癥和不伴有肝臟炎癥(對照組)ALD患者的腸道菌群,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移植了伴有肝炎ALD患者的腸道菌群的小鼠肝臟出現了更加嚴重的炎癥反應,有大量的T淋巴細胞及自然殺傷細胞浸潤,且腸黏膜通透性增加,出現了細菌異位,提示腸道菌群的改變可促進ALD患者肝臟炎癥狀態。Bull-Otterson等[11]研究也發現,慢性酒精攝入者的腸道內,擬桿菌門和厚壁菌門數量下降,革蘭陰性菌變形菌門及革蘭陽性菌放線菌門數量增加。
目前,通過補充微生態制劑改善ALD的研究已經取得一定進展。其原理主要是通過補充益生菌,抑制致病菌繁殖,進而恢復腸道菌群平衡來治療ALD。Yan等[9]報道了益生元可改善小腸細菌過度生長(SIBO)及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癥狀。Kirpich等[12]給予ALD患者雙歧桿菌加乳酸桿菌治療5 d后發現,腸道中益生菌增加,血清中谷草轉氨酶 (AST)和谷丙轉氨酶 (ALT)水平下降,提示給予益生菌治療后,可減輕肝損傷。
因此,長期飲酒主要表現為腸道優勢菌數量下降,致病菌過度繁殖,導致腸道菌群紊亂,促進 ALD 的發生發展。越來越多證據[12-13]支持,恢復腸道菌群紊亂或許可延緩或阻止ALD患者肝臟病變。
3.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NAFLD是一個用來描述與肥胖密切相關的一類肝臟疾病,包括肝臟脂肪變性,伴或不伴有肝臟炎癥,甚至肝硬化[14]。腸道菌群紊亂及形成的腸源性內毒素血癥在NAFLD的發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腸道菌群紊亂和腸道通透性增加,使肝臟暴露于腸源性細菌產物內毒素。有研究[12]通過實時定量PCR方法分析NAFLD患者糞便菌群,結果顯示,NAFLD患者糞菌內的擬桿菌門類細菌與單純非酒精性脂肪肝及正常健康人相比,明顯下降,提示腸道菌群的差異在NAFLD的發展中可能具有一定作用。Cani等[15]發現,給予高脂飲食小鼠的腸黏膜通透性增加,血漿內毒素水平上升。另有研究[16]選擇了2個對高脂飲食不同反應的小鼠,A小鼠出現了高血糖及高濃度的促炎細胞因子,B小鼠并無上述改變。把兩只小鼠的糞便菌群分別移植到一批無菌小鼠體內,一定時間后,接受A小鼠糞便菌群的小鼠出現了空腹高血糖及胰島素抵抗,肝細胞出現脂肪變性,而接受B小鼠糞便菌群的小鼠并無上述改變,且兩組小鼠糞便菌群在門、屬、種各級別出現了明顯差異。這證明腸道菌群的不同組成可影響全身的糖代謝及肝臟脂質代謝。由于NAFLD發病的多因素,有報道[17]指出,SIBO及Toll樣受體4(TLR4)在NAFLD的病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TLR4能特異性識別脂多糖,激活炎癥相關基因的活性。為明確其中關系,有研究[18]選擇NAFLD患者完善十二指腸鏡檢查,發現有37.5%的患者出現了SIBO,且以大腸埃希菌為主;伴有SIBO的患者較不伴有SIBO的患者出現了較高水平的內毒素血癥及TLR4蛋白的表達。該研究對于SIBO及TLR4在NAFLD的病理過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直接證據。此外,楊雪敏等[19]研究顯示,SIBO及小腸運動功能紊亂多發生在伴有肝損害的NAFLD患者中。
上述研究說明,腸道菌群紊亂可通過多種途徑調節NAFLD進展。因此,早期診斷和生活方式的干預,并在此基礎上給予調節腸道菌群治療,可能會阻止或延緩NAFLD的發展。
3.3 慢性乙型肝炎(CHB)
我國是一個肝病大國,其中,CHB是我國最常見的慢性肝病之一,其炎癥遷延不愈,可發展為肝硬化、肝癌等疾病。Xu等[20]通過對CHB感染患者及健康人的糞便進行分析顯示,感染CHB患者的腸道內雙歧桿菌數量明顯下降,且伴有條件致病菌的生長。陳萌萌等[21]檢測了CHB患者糞便中的幾種菌群含量,結果顯示,與正常健康人相比,CHB患者腸道內的雙歧桿菌、乳酸桿菌、擬桿菌屬等益生菌含量減少;而腸桿菌科細菌、腸球菌等致病菌明顯增加,證明了CHB患者體內存在不同程度的腸道菌群失調現象。白細胞介素17A(IL-17A)是一種新型促炎性細胞因子,可以促進白細胞介素-1、白細胞介素-6、腫瘤壞死因子-α、前列腺素E2等表達,引發組織細胞通透性增加,甚至壞死[22]。研究[23]顯示,CHB患者體內腸球菌與IL-17A呈正相關。腸球菌迅速繁殖,可產生大量趨化因子,介導肝臟發生炎癥反應,進而加重肝臟的炎癥反應和損傷[24]。
由此可知,CHB患者體內存在不同程度的腸道菌群紊亂,其體內過度繁殖的腸球菌與IL-17A共同參與肝臟炎癥反應過程,可導致肝功能受損。
3.4 肝硬化
肝硬化是慢性肝病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肝纖維化的過程可促使腸道菌群紊亂及腸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礙的發展。肝硬化患者的門靜脈血流速度慢,可直接導致腸道通透性增加[25]。另外,肝功能受損,膽汁酸合成下降,腸道動力障礙,導致SIBO,從而促使腸道菌群紊亂。腸道菌群紊亂是肝硬化患者發生自發性腹膜炎、腸源性內毒素血癥等并發癥的重要原因。
動物實驗[26]表明,隨著肝硬化程度不斷加深,腸道菌群紊亂程度、肝臟炎癥反應和腸道細菌異位也隨之加重。Chen等[27]研究顯示,在大鼠肝臟纖維化過程中,出現了腸道菌群紊亂、腸黏膜屏障受損以及菌群異位現象,進而導致肝臟的炎癥反應加重及肝臟進一步受損;而調節腸道菌群,抑制細菌異位后,肝臟組織炎癥明顯減輕,肝臟受損程度得到改善。另有研究[28]顯示,與對照組相比,給予實驗大鼠益生菌治療后,明顯降低了實驗組大鼠的細菌異位、肝臟的炎癥狀態,改善了回腸的黏膜屏障功能及炎癥損傷。黃曉宇等[29]研究表明,菌群紊亂的程度和肝硬化患者肝功能Child-Pugh分級程度有關,與肝功能Child-Pugh A級的肝硬化患者相比,肝功能Child-Pugh C級的肝硬化患者腸道菌群紊亂的程度更嚴重。而益生菌可以調節腸道菌群,改善腸黏膜屏障障礙及免疫功能,防止肝硬化細菌易位的病理過程。 綜上所述,腸道菌群紊亂在肝硬化患者的病情演變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且菌群紊亂程度與肝功能狀態、Child-Pugh分級密切相關。改善腸道菌群紊亂有助于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的恢復。
3.5 肝性腦病(HE)
HE是由于肝功能障礙導致神經精神功能障礙綜合征,其中,輕微肝性腦病(MHE)是指無明顯HE臨床癥狀,但用精細的智力試驗或神經電生理檢查,可發現輕微異常的HE。HE可受腸道菌群代謝的直接影響,因為腸道菌群是腸道氨產生的關鍵因素。隨著各種基因測序技術的發展,近來研究[30]發現,MHE的發生與腸道菌群紊亂有著密切聯系,主要表現為厭氧菌數量下降,需氧菌和兼性厭氧菌數量增多。
Montgomery等[31]研究表明,MHE與腸道菌群紊亂密切相關,特別是與因菌群紊亂引起的內毒素血癥有關。Shukla等[32]研究顯示,MHE患者腸道中有害細菌大量繁殖,產生大量內毒素;與不伴有MHE的肝硬化患者相比,伴有MHE的肝硬化患者腸道菌群的生物多樣性發生了明顯改變,且其腸道菌群的豐度和物種數降低;兩組肝硬化較正常人比較,鏈球菌數量增強,伴有MHE的肝硬化患者更明顯,且鏈球菌的數量與血漿氨呈正相關[33]。這揭示了腸道菌群紊亂可能是肝硬化患者發生 MHE 的原因,特別是與氨增加相關,暗示了腸道鏈球菌可能作為預計MHE 肝硬化患者降氨療法的生物標記物 。
臨床研究[34-35]顯示,微生態制劑可以改善MHE患者的認知功能、降低血氨以及逆轉MHE的作用。給MHE患者加用合生元治療后,腸道大腸桿菌和葡萄球菌減少,乳酸桿菌等厭氧菌數量增多;血氨水平、內毒素水平下降,可逆轉HE,且肝功能Child-Pugh分級好轉。
綜上所述,在HE的發生發展中,腸道菌群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對HE患者除了常規綜合治療外,調節腸道菌群可作為重要的輔助治療。
4 調節腸道微生態
腸道菌群紊亂在慢性肝臟疾病的發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調節腸道菌群從而改善腸道微生態對慢性肝病的治療具有很大價值。近年來,研究[36]顯示,針對腸道微生態的調節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4.1 胃腸動力藥
促動力藥可協調胃腸運動,防止腸內食物潴留,減少SIBO的發生。動物實驗[37]表明,肝硬化大鼠存在內毒素血癥及細菌異位,可促進SIBO,增加腸黏膜的通透性;加用西沙比利治療后,增加了腸道傳輸功能,改善了腸黏膜的通透性,減少了SIBO及內毒素血癥。
4.2 抗生素
利福昔明是一種非氨基糖甙類腸道抗生素,具有低的細菌耐藥性,不良反應少,大量運用于臨床。Bajaj等[38]發現,ALD患者口服利福昔明能減少腸道革蘭陰性菌的數量,降低血清內毒素水平,同時改善其臨床肝損傷指標。Gangarapu等[39]研究發現,與對照組相比,給NAFLD患者加用利福昔明治療后,患者的體質量指數、血清內毒素、AST、ALT以及谷氨酰轉肽酶(GGT)改善明顯。Kimer等[40]一項Meta分析發現,利福昔明可降低HE患者病死率。此外,2010年美國FDA批準利福昔明用于治療HE。
4.3 微生態制劑
微生態制劑可調節腸道菌群來維持腸道微生態的平調[41],還可恢復免疫平衡,改變腸黏膜通透性,降低腸道pH,促進氨排泄,對于肝病的治療具有重要意義。微生態制劑主要分為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元。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對預防治療慢性肝病、內毒素血癥、感染等方面有著積極作用。Vajro等[42]研究顯示,給予NAFLD兒童乳酸桿菌治療后,ALT在8周后改善明顯。Aller等[43]也證實,當患者給予乳酸桿菌及鏈球菌治療后,血清轉氨酶水平明顯改善。雙歧桿菌已被證實可改善血清內毒素水平及肝脂肪變性[44]。最近一項關于肝臟疾病及肝移植的系統評價[45]顯示,與對照組相比,益生菌治療組可明顯減少感染發生率及住院率。益生元是不被腸道吸收的物質,進入腸道后,可刺激腸道菌群發生改變,從而治療肝臟疾病,其常見的種類有單糖(果糖)、雙糖(乳糖)、低聚糖(乳果糖)、多元醇(山梨醇)等。其中,乳果糖在控制和預防HE中具有確切的治療作用。另有一項隨機對照試驗[46]表明,實驗組給予低聚果糖后,血清轉氨酶明顯下降。合生元是益生菌和益生元的聯合制劑。目前,臨床上使用合生元改善腸道菌群的研究較少。
4.4 糞菌移植(FMT)
FMT是指將健康供菌者的糞便經處理后,獲得其中的功能菌群,通過多種途徑,將其糞菌移植到患者體內,達到重建患者的腸道菌群以治療相關疾病的一種方法。近年來,隨著腸道菌群紊亂性疾病的高發及現有治療方式的缺陷,FMT逐漸被應用于各項臨床治療。以往的動物實驗[47]表明,腸道菌群異位可導致肥胖及胰島素抵抗。FMT關于肝病的治療目前還未見報道,但是荷蘭一項實驗[48]表明,當肥胖者接受瘦者提供的大便制成的菌群后,肥胖者的胰島素敏感性得到明顯改善。因此,從理論上推測,使用從健康人糞便提取的含有大量活性菌的物質改善肝病患者菌群紊亂,從而治療疾病是切實可行的,但其確切療效需進一步臨床研究來證實。
5 總結
慢性肝病與腸道微生態中的腸道菌群息息相關,二者互為因果,互為影響。目前,許多研究[10,16,27]表明,當腸道菌群紊亂時,腸道菌群及其產物可影響肝臟疾病。雖然其確切機制尚不明確,但是通過抗生素、微生態制劑、糞菌移植等方法改善腸道菌群紊亂,對肝病的治療具有重要作用。
[1]Hooper L V, Littman D R, Macpherson A J.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icrobiota and the immune system[J]. Science, 2012, 336(6086):1268-1273.
[2]Lozupone C A, Stombaugh J I, Gordon J I,etal. Diversity,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J]. Nature, 2012, 489(7415):220-230.
[3]Maynard C L, Elson C O, Hatton R D,etal. Reciprocal interactions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immune system[J]. Nature, 2012,489(7415):231-241.
[4]劉春光, 毛德文. 腸道菌群失調與肝硬化[J]. 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 2014,23(26):2959-2961.
[5]蔣彩鳳, 陳岳祥, 謝渭芬,等. 腸道微生態在慢性肝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J].中華消化雜志,2013,33(12):814-816.
[6]Chen Y, Yang F, Lu H,etal. Characterization of fecal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J]. Hepatology,2011,54(2):562-572.
[7]Purohit V, Bode J C, Bode C,etal. Alcohol, intestinal bacterial growth,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to endotoxin, and medical consequences: summary of a symposium[J]. Alcohol,2008,42(5):349-361.
[8]Mutlu E A, Gillevet P M, Rangwala H,etal. Colonic microbiome is altered in alcoholism[J]. Am J Physiol Gastrointest Liver Physiol,2012, 302(9):G966-G978.
[9]Yan A W, Fouts D E, Brandl J,etal.Enteric dysbiosis associated with a mouse model of alcoholic liver disease[J].Hepatology,2011,53(1): 96-105.
[10] Llopis M, Cassard A M, Wrzosek L,etal. Intestinal microbiota contributes to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alcoholic liver disease[J]. Gut,2016,65(5):830-839.
[11] Bull-Otterson L, Feng W, Kirpich I,etal.Metagenomic analyses of alcohol induced pathogenic alterations in the intestinal microbiome and the effect of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treatment[J]. PloS One,2013,8(1):e53028.
[12] Kirpich I A, Solovieva N V, Leikhter S N,etal.Probiotics restore bowel flora and improve liver enzymes in human alcohol- induced liver injury: a pilot study[J].Alcohol,2008,42(8): 675-682.
[13] Stadlbauer V, Mookerjee R P, Hodges S,etal. Effect of probiotic treatment on deranged neutrophil function and cytokine responses in patients with compensated alcoholic cirrhosis[J]. J Hepatol,2008,48(6):945-951.
[14] Brunt E M. Pathology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J].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0,7:195-203.
[15] Cani P D, Bibiloni R, Knauf C,etal.Changes in gut microbiota control metabolic endotoxemia-induced inflammation in high-fat diet-induced obesity and diabetes in mice[J].Diabetes,2008,57(6):1470-1481.
[16] Le Roy T, Llopis M, Lepage P,etal. Intestinal microbiota determines development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mice[J]. Gut, 2013,62(12):1787-1794.
[17] 曹毅, 沈峰, 徐雷鳴, 等. 腸道菌群和內毒素血癥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J]. 實用肝臟病雜志,2012,15(2):163-165.
[18] Kapil S, Duseja A, Sharma B K,etal.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and toll-like receptor signaling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6,31(1):213-221.
[19] 楊雪敏, 呂宗舜, 王邦茂, 等. 小腸細菌過生長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關系的探討[J]. 天津醫科大學學報, 2013,19(3):223-226.
[20] Xu M, Wang B, Fu Y,etal. Changes of fecal Bifidobacterium species in adult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induced chronic liver disease[J]. Microb Ecol, 2012,63(2):304-313.
[21] 陳萌萌, 鄭吉順, 劉艷艷, 等. 慢性乙型肝炎以及肝硬化患者腸道微生物研究[J]. 安徽醫科大學學報,2015,50(5):648-652.
[22] Zhang X, Angkasekwinai P, Dong C,et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interleukin-17 family cytokines[J]. Protein & Cell, 2011, 2(1): 26-40.
[23] Semedo T, Santos M A, Martins P,etal.Comparative study using type strains and clinical and food isolates to examine hemolytic activity and occurrence of the cyl operon in enterococci[J].J Clin Microbiol,2003,41(6): 2569-2576.
[24] Zhang J Y, Zhang Z, Wang F S,etal.Interleukin-17-producing CD4(+) T cells increase with severity of liver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J].Hepatology,2010,51(1): 81-91.
[25] Gunnarsdottir S A, Sadik R, Shev S,etal. Small intestinal motility disturbances and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and portal hypertensio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2003,98(6): 1362-1370.
[26] Gómez-Hurtado I, Santacruz A, Peiró G,etal.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is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and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 mice with CCl 4-induced fibrosis[J]. PLoS One, 2011, 6(7): e23037.
[27] Chen Y X, Lai L N, Zhang H Y,etal. Effect of artesunate supplementation on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and dysbiosis of gut microbiota in rats with liver cirrhosis[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6, 22(10): 2949.
[28] Sánchez E, Nieto J C, Boullosa A,etal. VSL#3 probiotic treatment decreases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 rats with carbon tetrachloride-induced cirrhosis[J]. Liver Int,2015,35(3):735-745.[29] 黃曉宇, 李剛平,寇繼光,等. 肝硬化患者腸道菌群失調與Child-Pugh分級的關系[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5,31(3):392-395.
[30] Bajaj J S. The role of microbiota i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J]. Gut Microbes, 2014, 5(3): 397-403.
[31] Montgomery J, Bajaj J. Advances in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J]. Curr Gastroenterol Rep, 2011, 13(1):26-33.
[32] Shukla S, Shukla A, Mehboob S,etal. Meta-analysis: the effects of gut flora moduation using prebiotics, probiotics and synbiotics on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J].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11,33(6):662-671.
[33] Zhang Z, Zhai H, Geng J,etal. Large-scale survey of gut microbiota associated with MHE Via 16S rRNA-based pyrosequencing[J]. Am J Gastroenterol, 2013, 108(10):1601-1611.
[34] Liu Q, Duan Z P, Ha D K,etal. Synbiotic modulation of gut flora: effect on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J]. Hepatology,2004,39(5):1441-1449.
[35] Agrawal A, Sharma B C, Sharma P,etal. Secondary prophylaxi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cirrhosis: an open-labe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lactulose, probiotics, and no therapy[J]. Am J Gastroenterol, 2012,107(7):1043-1050.
[36] Haque T R, Barritt A S 4th.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liver disease[J]. 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 2016, 30(1):133-142.
[37] Zhang S C, Wang W, Ren W Y,etal. Effect of cisapride on intestinal bacterial and endotoxin translocation in cirrhosis[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03, 9(3):534-538.
[38] Bajaj J S, Heuman D M, Sanyal A J,etal.Modulation of the metabiome by rifaximin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nd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J].PLoS One,2013,8(4):e60042.
[39] Gangarapu V, Ince A T, Baysal B,etal. Efficacy of rifaximin on circulating endotoxins and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J].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5,27(7):840-845.
[40] Kimer N, Krag A, M?ller S,etal.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the effects of rifaximin in hepatic encephalopathy[J].Aliment Pharmacol Ther,2014,40(2):123-132.
[41] Han D W. Intestinal endotoxemia as pathogenetic mechanism in liver failure[J].World Gastroenterol,2002,8(6):961-965.
[42] Vajro P, Mandato C, Licenziati M R,etal. 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strain GG in pediatric obesity-related liver disease[J].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2011,52(6):740-743.
[43] Aller R, De Luis D A, Izaola O,etal. Effect of a probiotic on liver aminotransferases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atients: a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Eur Rev Med Pharmacol Sci,2011,15(9):1090-1095.
[44] Malaguarnera M, Vacante M, Antic T,etal. Bifidobacterium longum with fructo-oligosaccharides in patients with non 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J]. Dig Dis Sci, 2012,57(2):545-553.
[45] Sawas T, Al Halabi S, Hernaez R,etal. Patients receiving prebiotics and probiotics before liver transplantation develop fewer infections than control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015, 13(9):1567-1574.
[46] Daubioul C A, Horsmans Y, Lambert P,etal. Effects of oligofructose on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results of a pilot study[J]. Eur J Clin Nutr, 2005,59(5):723-726.
[47] Turnbaugh P J, Ley R E, Mahowald M A,etal. An obesity-associated gut microbiome with increased capacity for energy harvest[J]. Nature, 2006,444(7122):1027-1031.
[48] Vrieze A, Van Nood E, Holleman F,etal. Transfer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from lean donors increases insulin sensitivity in individual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J]. Gastroenterology,2012,143(4):913-91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705.R.20161027.1711.076.html
10.3969/j.issn.1674-2257.2016.05.029
四川省教育廳科研項目(No: 16TD0028);成都醫學院校級課題(No: CYX12-029)
R575
A
△通信作者:李小安,E-mail:4354456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