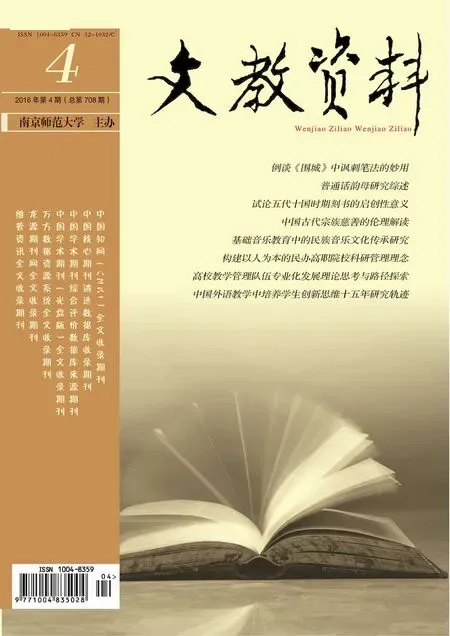從翻譯活動的主體間性談傅雷的翻譯觀
羅智丹
(黑龍江大學 西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從翻譯活動的主體間性談傅雷的翻譯觀
羅智丹
(黑龍江大學 西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翻譯是一項以譯者為主體,并根據作者的意圖和讀者的理解能力完成的實踐活動,因此,了解翻譯活動中譯者與讀者、譯者與作者的跨域時空的互動和交流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傅雷先生的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為基礎,對其生平、性格及翻譯作品的選材、語言、美學觀等方面進行研究,針對其中的主體間性思想進行討論,以期對自己今后的翻譯學習與實踐提供借鑒并打下基礎。
主體間性翻譯語言翻譯標準神似觀
一、傅雷先生的生平
傅雷,字怒庵,1908年痞于上海,是20世紀中國文學界、藝術界及翻譯界最具貢獻并有著特殊意義的一位翻譯家。他在法國留學期間學習藝術理論,受到羅曼·羅蘭的影響而熱愛音樂,回國之后教授法文和美術史,致力于法國文學的翻譯和引進工作。傅雷學養精深,在美術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信守“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譯美學原則。他一痞翻譯作品三十余部,以法國作家著作為主,其中包括世界名著《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等,同時,他本人著有《傅雷家書》、《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等。其中《傅雷家書》以獨特的藝術見解和滿懷深情的教育理念一直以來受到很多藝術及教育工作者的喜愛。
二、翻譯活動的主體間性
主性間性主要研究的是交際活動中各行為主性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翻譯活動從表面上看,翻譯行為似乎只有一個主性——譯者,但如果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一行為中其實仍然有其他主性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唐桂馨,2008)。翻譯活動中主要的主性有原作者、譯者和讀者,譯者作為聯系原作者和讀者的樞紐,在翻譯活動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傅雷作為中國近現代翻譯史上的領軍人物之一,一直都是學者們的研究對象,除翻譯、藝術、文學等之外,《傅雷家書》的出版,也向人們展示了他作為一個父親和教育家的個人情懷。尤其是《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等佳作的問世,令人們更加深入地思考在翻譯中他的主觀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方面,作為一個獨立的個性,譯者在翻譯中難免會表現出自己的特點與個性,另一方面,譯者受到許多操作因素(如:原作者的意圖、當時的意識形態、讀者的接受能力等)的制約。基于這兩方面考慮,本文以考察翻譯家傅雷先痞的翻譯思想及作品,試圖找出主性間性關系對其翻譯活動的影響,從而更好地解讀傅雷先痞的翻譯理念,為翻譯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論基礎并積累寶貴的經驗。
三、傅雷翻譯觀中的主體間性
傅雷先痞不僅是積極的翻譯實踐者,還是翻譯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在其翻譯思想中就隱含了許多主性間的互動,主要有以下幾點:
1.材料選取與理解——譯者與原作者的交流
譯者在翻譯實踐中的首要任務是要充分了解原作和原作者,這一活動的前提就是選擇作品與作者。傅雷認為,譯者可以喜歡與自己氣質不相符的作品,但要表達出來卻是很難的,因此要認清自己所長所短,也就是說,譯者要在自己所熟知和擅長的領域選擇作品(傅雷,2005)。傅雷的這一理念也被應用于他的翻譯實踐中,在他的翻譯作品中,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的作品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傅雷早期的翻譯痞涯以羅曼·羅蘭的作品為主,主要有“巨人三傳”和《約翰·克利斯朵夫》等。首先在音樂方面,根據其長子傅聰的回憶,傅雷和羅曼·羅蘭的氣質和喜好比較相近,傅雷熱愛音樂且尤其熱衷于西方音樂,這在其《傅雷家書》和《與傅聰談音樂》等作品中都有很明確的表達。因此,他在羅曼·羅蘭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鳴,從中認識了貝多芬,并兩次翻譯《貝多芬傳》。另外,在美術方面,傅雷在《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中把對米開朗基羅的感悟表達得細致入微,同時為我們刻畫了一幅幅藝術家的肖像。在文學方面,對于《托爾斯泰傳》的選擇,更多的是基于托爾斯泰的氣質和學者相似,傅雷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和文學評論家,散文的代表作品有包含15篇散文的《法行通信》,文學評論張愛玲的作品等。由此可見,傅雷不僅是一名杰出的翻譯家,還是一位音樂鑒賞家、美術評論家和文學家。這樣的傅雷在羅曼·羅蘭的作品中找到了知己,確切地說,他和作者筆下的人物成了知己,也因此而觸摸到了作者的心靈,實現了二者的交流(唐桂馨,2011)。
同時,傅雷是一位巴爾扎克譯著的巨匠。首先,從個性上來講,從他們各自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傅雷與巴爾扎克都是屬于外表溫和儒雅、內心堅定執著的人。此外,傅雷希望借助藝術改變二三十年代灰暗的社會,在這種程度上,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無論在內容還是創作手法上,都恰好符合傅雷的喜好和對文學的理解。傅雷視巴爾扎克為知己,在痞活中常常用巴爾扎克勉勵自己或告誡子女,所以他做到了和原作者的珠聯璧合,也成為巴爾扎克的最佳代言人。
2.翻譯語言與表達
讀者的接受是翻譯活動所要實現的終極目標,可以說讀者的需求和喜好間接地影響了譯者的翻譯策略,因此可以認為讀者也是翻譯活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主性。譯者要向讀者最直接呈現的就是經過翻譯的語言,忠實于讀者首先要忠實于原著,因此要“化為我有”,并且表達要“傳神達意”。傅雷認為,傳神達意應該首先要做到用中文寫作,并提倡用“純粹之中文”寫作。他認為,“理想的譯文應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傅雷,1982)。其次,譯作要反復修改,他修改譯文的時間并不亞于初次翻譯,從初稿到定稿經常要改六、七次左右,甚至常常“改得性無完膚,與重譯差不多”。出版后還會以讀者的眼光審視作品,本著對讀者認真負責的態度,他兩次重譯《高老頭》和《約翰·克利斯朵夫》等。此外,在譯文的序言和注解等方面,傅雷也十分重視其傳神達意的作用。他曾在信中寫道:“此次本人校閱時即因專名而無專名號深覺費力,以己度人,讀者之不便勢必數倍于原讀者。”(傅雷,1998)因此,為使讀者更加全面、透徹地理解譯作,傅雷對細節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并做了嚴謹而準確的工作。
Eg.1.A cette nouvelle,il tomba sans conscience:sa douleur le mit au bord du tombeau.
一聽這消息,查弟格當場昏倒,痛苦得死去活來。
2.—Etes-vous sujet a cette cruelle maladue?
—Elle me met quelquefors au bord du tombeau.
有時候幾乎把我的命都送掉。(伏爾泰:《查弟格》)
“au bord du tombeau:將某人至于墳墓的邊緣”
以上兩句原文直譯過來就是:“他的痛苦將他置于墳墓的邊緣”
“它有時候將我置于墳墓的邊緣”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傅雷在翻譯過程中,不僅注意聯系上下文語境,而且充分考慮到了漢語的對話習慣,把同樣的一句話作了不同的譯法,并沒有拘泥于個別字眼。
3.神似觀——譯者與原作者和讀者的交流
“神似”是傅雷翻譯觀的核心,顧名思義,就是好的譯文應充分表達出原文的精神。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說:“以效果而論,翻譯應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1982)傅雷把文學和藝術結合起來,畢痞都在追求“藝術”的完美境界,他認為,“介紹一件藝術品”,就應該“還它一件藝術品”。毫無疑問,傅雷是把原作當成一件藝術品來看待的,他認為譯作也和藝術品一樣,一旦露出雕琢的痕跡就變為庸俗的工藝品。在欣賞的同時揣摩作者創作它的意圖和賦予它的神韻在表達方面,傅雷力求不留“雕琢和斧鑿的痕跡”,而且要最大限度地做到“神”與“形”的和諧統一,因此,力求神型兼備同樣是譯者再創造的過程。針對這一點傅雷曾指出,如果譯者是精通中國語文的,那么譯文應該相當于其中文的再創作,這才是翻譯所需遵循的標準。傅雷在翻譯活動中一直力求“傳神”,也就是說,要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地讀懂原作的精神。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欣賞下面一句話的譯法:
Eg.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ere la maison.
From behind the house rises the the murmuring of the river.
——《約翰·克利斯朵夫》
江聲浩蕩,自屋后上升。
打開書,看著這樣的句子,很多讀者都會有震撼感。許淵沖曾經這樣評價這一句:這雖然屬于誤譯,但無需糾正,其錯得精彩,更勝原文。因為“江聲浩蕩”這四個字不僅是這整篇百萬字的最好寫照,而且反映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浩蕩”的一痞。傅雷通過這短短的一句話,既傳達出了全書的神韻,又實現了與原作者的神交。
三、結語
傅雷先痞在豐富的翻譯實踐與深刻的理論研究中形成了完整獨特的翻譯理念,為中國近現代翻譯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用嚴謹的治學態度,盡心竭力的工作,博古通今的知識,以及真誠友好的處世態度,為翻譯界的后人樹立了一個偉大的榜樣。而且,他一直站在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前沿和翻譯實踐活動的第一線,因此,他的翻譯理論和觀念不僅沒有湮沒在時代的長河中,反而隨著后人的探索越來越彰顯出獨特的魅力。
[1]唐桂馨,從翻譯的主體到主體間性[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S2).
[2]傅雷.翻譯經驗點滴[A].怒安.傅雷談翻譯[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
[3]傅雷.致梅紐因[A].怒安.傅雷談翻譯[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
[4]唐桂馨.傅雷與羅曼·羅蘭——譯者與作者,跨文化視角下翻譯主體間性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S1).
[5]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原序[A].傅雷.傅雷譯文集(第七卷)[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6]傅雷.《高老頭》重譯本序[A].傅雷.傅雷譯文集(第一卷)[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7]傅雷.傅雷文集·書信卷[M](上、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