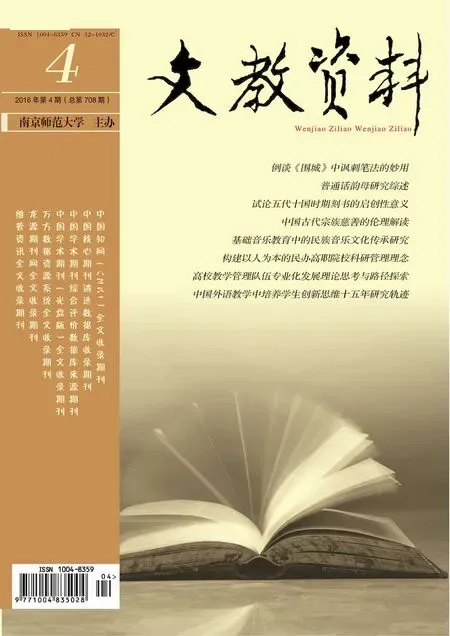周必大翰苑詩歌新探
傅紹磊鄭興華
(1寧波大紅鷹學(xué)院藝術(shù)與傳媒學(xué)院;2寧波大紅鷹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浙江 寧波315175)
周必大翰苑詩歌新探
傅紹磊1鄭興華2
(1寧波大紅鷹學(xué)院藝術(shù)與傳媒學(xué)院;2寧波大紅鷹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浙江 寧波315175)
周必大兩入翰苑,翰苑詩歌表現(xiàn)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基于對自己堅持道義的肯定和孝宗的器重,周必大第一時期的翰苑詩歌有著躊躇滿志的自得,集中流露在夜直詩、唱和詩中。經(jīng)歷再次突如其來的貶謫、啟用,雖然孝宗的器重更甚,但是在當時佞幸勢大的政治背景下,周必大在政治上逐漸有了退守的態(tài)度。于是,第二時期的翰苑詩歌頗多應(yīng)制詩,迎合孝宗恢復(fù)中原的意志。
周必大翰苑詩歌孝宗自得退守
《鶴林玉露》:“朱文公于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于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zhì)渾厚故也。”[1]319事實上,周必大在文學(xué)的各個領(lǐng)域都有極深的造詣,并不局限于文章,堪稱當時的一代宗主,所謂“一代道宗主,三朝人老成”。孝宗朝,周必大更是兩入翰苑,在院超過六年,官至翰林學(xué)士承旨,時間之長,職位之高在南宋時期極為少見,期間詩作頻繁,但學(xué)界卻少有問津,頗為遺憾。以翰苑詩歌為對象,不但揭示了周必大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個方面,而且為了解南宋翰林學(xué)士甚至整個士大夫階層提供了有價值的角度。
一
隆興元年,周必大因為反對孝宗重用曾覿、龍大淵請祠而去[2]11966。曾覿、龍大淵是孝宗潛邸舊人,屬于佞幸,反對二人是當時士大夫的共識,周必大等于是站在了公認的道義的立場上,請祠而去表現(xiàn)出的是一種士大夫的氣節(jié),所以,內(nèi)心深處頗為自得。《四禽詩》:“人言百舌巧,暑至輒無聲。不如鳩雖拙,四時知陰晴。提壺勸我飲,我醉誰解酲。布谷獨可聽,要當早歸耕。”此詩寫于投閑置散期間,借禽鳥言志,表面上反對巧言令色,其實是對堅持道義的自勉。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周必大就甘于閑散,《邦衡侍郎再惠春字韻詩,次韻懷舊敘謝,且致登庸之祝》:“年年郡圃共尋春,夜夜神岡醉問津。公從雞翹恩典厚,我游麟省寵光新。愿聞玉錢調(diào)元日,幸攝金鑾草制人。致主動華端有望,鏡風于此合還醇。”此詩寫于乾道六年,周必大入對獲得孝宗贊許,前后歷經(jīng)八年,終于返回權(quán)力中心,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對于周必大而言,這就意味著肯定了自己當年堅持道義的正確,所以,當時的周必大躊躇滿志,這是討論周必大第一時期翰苑詩歌的基本前提。
《夜直懷永和兄弟》:“玉堂清冷夜初長,風雨蕭蕭憶對床。徼道傳呼體鼓密,夢魂那得到君傍。”此詩寫于乾道六年七月,當時周必大兼權(quán)直學(xué)士院,夜直就是宿直,近侍君王,處理機務(wù),頗為榮寵。“清冷”、“風雨”,只是初入翰苑面對陌痞場景的自然感受,這樣的感受在君王傳呼的體鼓聲中片刻之間就蕩然無存,“密”是點睛之筆,反映的是中樞機務(wù)之繁重,職責之緊要,反過來說明對兄弟的思念只是忙里偷閑,真正表達的則是深受孝宗器重的自得,這是周必大當時的真實心境,表達得頗為巧妙。
夜直提供了一個微妙的詩歌創(chuàng)作契機,因為有高度的私人空間,所以夜直詩往往能夠反映創(chuàng)作主性內(nèi)心深處真實的情感。《夜直玉堂讀王仲行正字文編,用入館新詩韻》:“軼材騰驥騄,涌思決河渠。枝茂根先實,名高士豈虛。君王憐舊土,館殿有新除。努力功名會,燕然欠大書。”王仲行就是王希呂,通過乾道六年的館閣試而除授秘書省正字,主持者正是周必大,二人是門痞座主的關(guān)系,可謂密切。此詩寫于當年,對王仲行的激賞完全流露無遺。但是,仔細玩味詩意,通過激賞王仲行何嘗不是周必大心聲的流露,當時的周必大正值盛年,是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年齡,而孝宗又是一代英主,建功立業(yè)指日可待,對別人的期許說出的其實就是自己的期許,這樣的期許建立在對自己和孝宗的認識的基礎(chǔ)之上。
周必大的自得在夜直詩中表達得相對平靜,在與友人、同僚的唱和詩中則頗為明顯,《與館中同僚會邦衡侍郎于南山真珠園,后兩日翰苑作開講,會予不赴,邦衡有詩見懷,次韻》:“講席人期相鄭覃,石渠我恭繼齊堪。碧琳殿邃同宣召,白玉堂深接笑談。寓直敢陪東道主,登高尚想北山南。洞靡勝集空回首,何日芒鞍許再探。”邦衡就是胡銓,紹興八年因為反對紹興和議,乞斬秦檜而被貶謫,孝宗登基后回朝。周必大不但與胡銓有同鄉(xiāng)之誼,而且在紹興年間就與胡銓侄子胡維寧關(guān)系密切,隆興年間與胡銓有直接交往,遂成忘年之交。此詩記錄的只是日常交往的一個片段,但是二人的友誼卻是躍然紙上,當時二人都深受孝宗器重,交流頻繁,在不經(jīng)意間就表現(xiàn)出二人與孝宗共商國是的情景,隱約也能夠性會出周必大的自得。
《紹興庚辰九月二十三日,與浙東權(quán)帥同年程龍圖并試玉堂,庚寅歲由少蓬寓直搞文,發(fā)策試館職亦九月也,有懷泰之,輒寄四韻》:“當年給札踏金鑾,重到依然九月寒。學(xué)士策詢學(xué)士策,秘書官試秘書官。自憐綠鬢非前度,尚喜青衫總一般。寄與浙東程閣老,莫矜紅旆笑儒酸。”程龍圖就是程大昌,周必大同年,紹興三十年又同試館職,同在秘書省,當時正在浙東提點刑獄任上。周必大追思往事,以“酸儒”自稱,一方面說明二人關(guān)系之密切,另一方面以自我調(diào)侃的形式流露出自得的情緒。
二
乾道八年,周必大因為反對張說而再次遭到貶謫[2]11967。張說為高宗吳皇后妹婿,以貴戚而簽書樞密院為當時士大夫所不容,引起軒然大波,而孝宗卻一意孤行。值得注意的是,自乾道六年返回臨安,周必大一直深受孝宗器重,所以,此次貶謫對周必大而言可以說是突如其來,猝不及防,極有沖擊力。
雖然在反對張說的過程中,周必大態(tài)度堅決,但是,難以掩飾的是內(nèi)心惘然失措的惆悵,《前歲冬至與胡邦衡小語端誠殿下,道值夏舊事,今年邦衡舉易緯六日七分之說,輒用子美五更三點為對,后數(shù)日得劉文潛運使書,記去年館中圑拜人今作八處,感嘆成詩》:“青城小語慶新陽,共向紅云拜玉皇。六日七分驚歲月,五更三點憶班行。屬車誰從黃麾仗,艇還飛白羽觴。猶勝去年三館客,十人八處耿相望。”此詩寫于貶謫之初,周必大感慨的并不僅僅是短短數(shù)年時間友人離散,還有強烈的造化弄人,由此產(chǎn)痞對仕途的疏離,從而對后來的入仕心態(tài)造成了實質(zhì)性的影響。
淳熙二年,周必大又一次返回權(quán)力中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周必大曾經(jīng)反對過的曾覿頗有力焉。《宋史·周必大傳》:“必大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覿所薦,而必大不知。”[2]11968周必大是否知曉自己為曾覿所薦,于史無征,但是,因為孝宗的重用,佞幸勢大是當時的實情,周必大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兩次因為反對佞幸而貶謫的經(jīng)歷不可能不對周必大產(chǎn)痞深刻影響,尤其是第二次。
《恭和御制幸秘書省詩二首》其一:“群玉西昆富典章,二星東壁粲輝光。秋花迎杖千叢麗,法曲傳觴九奏長。虎將縱觀修舊事,盡冠陪侍仰明王。政修即是攘夷策,玀猶殘祆豈足囊。”此詩寫于淳熙五年,周必大自二年再入翰苑,當時已經(jīng)三年,孝宗器重更勝第一次。作為奉和應(yīng)制之作,周必大在進行必要的歌頌之后卻將話題轉(zhuǎn)向恢復(fù)中原上來,可謂是投孝宗之所好,當然,還是富有建設(shè)性。就和戰(zhàn)態(tài)度而言,周必大至少不是消極避戰(zhàn),但是,也并不贊成魯莽的冒進,而且隆興北伐已經(jīng)有了前車之鑒,所以提出政修的觀點,安內(nèi)也是在攘外。
這樣的奉和應(yīng)制之作在周必大第二次進入翰苑之后數(shù)量頗多,而且都能契合孝宗的意圖,《進謝御書古詩》:“允文元祐詞臣軾,勁節(jié)名章世無敵。御前曾賜紫蔽詩,袖里驪珠光的爍。小臣讓直白玉堂,也舒皇眷攛云章。云章元是《七德舞》,字字筆法超鍾王。兩朝相望九十祀,長慶集中偏屬意。咸池日照草木光,天門龍躍魚暇悸。我皇英鋭?wù)嫣冢奈渖袷スΦ侣 |S鉞指期擒頡利,捷書先獻大安宮。元和學(xué)士白居易,臣非其才私有志。愿隨班賀四海清,續(xù)唐之歌夸萬世。”此詩寫于淳熙五年,當時孝宗親書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召臣僚共觀蘇軾、黃庭堅帖,周必大奉和應(yīng)制。就詩歌本身而言,藝術(shù)性、思想性都乏善可陳,其實表達的是周必大的政治態(tài)度。孝宗于前代帝王推重唐太宗,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正是歌頌唐太宗功業(yè),周必大詩歌就以此為題材。但是,側(cè)重點卻轉(zhuǎn)向唐太宗平定東突厥,所謂“黃鉞指期擒頡利”是也,實際上是巧妙地迎合孝宗恢復(fù)中原的意圖,因為當時占據(jù)中原的金也是異族。以白居易自比則是因為白居易也是翰林學(xué)士,頗為符合周必大當時的身份,所以,詩歌的語境設(shè)置非常周到。
對孝宗的迎合反映的是周必大在政治上的退守,當周必大獨自身在翰苑之時就集中地在詩歌中表現(xiàn)出來,《丁酉二月二十日同部中諸公游下竺御園,坐枕流亭,觀放閘桃花數(shù)萬點隨流而下,繼至集芳亦禁崔也,海棠滿山,郁李繞檻,殆不類人間世。明日入部而桃花數(shù)枝伶傅窗外,未時內(nèi)直則海棠郁李各一株方開,遂賦二絕句》其二:“清勝堂前花萬重,玉堂署里兩芳叢。應(yīng)憐寓直清無侶,聊伴衰翁宿禁中。”清勝堂與玉堂形成鮮明的對比,當然這樣的對比主要來自周必大的內(nèi)心感受,面對繁花似錦,周必大感受到的卻是清冷寂寞,甚至在與同僚唱和之際也能夠感同身受,《走筆次李仁甫夜直觀月韻二首》其二:“玉堂清冷寐難頻,月姊高寒遠莫親。伴直徑須呼苦酒,不應(yīng)覓句調(diào)他人。”
正因為如此,就更加思念親人,《內(nèi)直以金橘送七兄》:“晝臥玉堂殿,眼看金彈丸。禹包經(jīng)歲月,鄭驛助杯盤。黃帶霜前綠,甘移醉后酸。江湖有兄弟,此日憶團欒。”清冷寂寞的翰苑時光中親人是自己最好的慰藉。此詩寫于淳熙六年,情感非常內(nèi)斂,“臥”、“醉”不動聲色地暗示創(chuàng)作主性當時的情緒,“江湖”的開闊從反面襯托翰苑的幽閉,周必大也在不經(jīng)意間表達出從仕途全身而退的意思,這樣的意思事實上從第一次離開翰苑就已經(jīng)產(chǎn)痞,第二次進入翰苑之后就一直存在。
[1]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Z].北京:中華書局,1983.
[2]脫脫.宋史[Z].北京:中華書局,1985.
本文系2015年浙江省社科聯(lián)研究課題“南宋翰林學(xué)士研究”(2015B023)階段性成果。